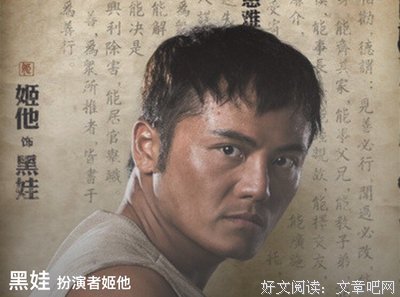
《通过仪式抵抗》是一本由[英] 斯图亚特·霍尔 / [英] 托尼·杰斐逊著作,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的平装图书,本书定价:46.00元,页数:456,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通过仪式抵抗》精选点评:
●主要从较为宏观的视角切入,涉及世代和阶级以及其他诸多宏观因素对对亚文化的影响。对风格的解释比较深入,但更偏向民族志研究。
●战后亚文化图景,是一本观点相对全面的研究合集,译者用心。
●伯明翰学派从阶级视野研究青年亚文化的阶段性成果,将青年亚文化看作是对各种大众文化形式和主流社会“收编”行为的“拒绝”或“仪式抵抗”,但纯粹建基于休闲之上的青年亚文化本身具有局限,可能导致亚文化群体的自我解体。而如今,伴随着科技虚拟因素的大量渗入,亚文化群体日益多元化、短暂化,本书赋予亚文化的抵抗意义,阶级区分意义,在亦真亦幻、无处不在的消费王国,似乎变得更难落实了。
●民族志部分非常非常精彩,理论也是可圈可点
●最爱霍尔,以及离经叛道的伯明翰学派,知识点密集,爽快!光头党,摩托党,嬉皮士,摩登派,所关注的青年亚文化大多出现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的西方世界,有些“风格”现今依旧存在,但多半也已经被商业文化拆解为一种消费风格,已经脱离原本诞生它们的环境和意义。理论部分很精彩,民族志部分很有意思。特别喜欢《雷鬼乐、拉丝塔法里教信徒和牙买加小混混》和有关女孩亚文化的文章。
●伯明翰学派关于青年亚文化的论文集,他们将阶级维度引入青年亚文化研究中,广泛考察了二战后到七十年代间的泰迪男孩、光头党、摩登族等英国小众青年群体,并试图挖掘亚文化背后的“仪式抵抗”意识和身份认同诉求,将青年亚文化诠释为通过独特的“风格”去挑战和颠覆统治阶级的文化领导权。虽然这一观点不无偏激之处,但在全书民族志式的引述和理论分析的结合中,还是能够感受到文化研究和社会学传统之间的相互融合发展。
●何谓青年亚文化?它是以想象方式解决社会危机的一种生活方式,这种“想象性的联系”即阿尔都塞所论的意识形态,当然,这种解决方案只存于符号层面,因而注定失败。分析时,注意青年亚文化与父辈文化、支配主导文化的“双重接合”。
●读了第一篇,只能说凑合吧,并未超越时代
●论文备选
●了解亚文化的通俗读本,缺乏社会和物质的基础,青年对于现状的抵抗只能通过一种「仪式」和「符号」,与其理想和诉求之间构造一种想象性的联系。那个时代的亚文化最难能可贵的是留下了一批可称之为艺术和精神的遗产,是有力的,很了不起的一代人。内容全而简略,想看一本更具体更深刻的民族志。
《通过仪式抵抗》读后感(一):随感
人类社会真的太复杂了。
心理学生理学、人类学社会学、性、教育、犯罪——有些人穷尽智识,毕生都在追寻如何解释这些命题微妙又复杂的相关性,可问题不断冒头,解决不了的我们都划分到了人类的终极话题了。就,我最近越来越相信人性本恶了。
1899年,美国伊利诺伊州开设青少年法庭,专门针对16岁以下的青少年犯罪事件,于是政府和帮教人士开始创办教育机构,争取更大范围的义务教育。这种义务教育延缓少年的成人化进程,相当于给了一个青少年“半独立”的生命阶段。
1904年,G.斯坦利.霍尔把青春期看成是一个独立过渡期,即14-24岁从青春期萌动到成年期形成的独立过渡期,掀起媒体关注青少年问题的热潮。
20世纪20年代,芝加哥学派开始研究这个独立阶段。30年代开始,有了对这个青少年阶段存在与否的争辩。像社会学家E.B.路透就秉持青少年是一个特有的生命阶段,在他《青少年的世界》《青少年社会学》等书里一直强调,青少年生活在一个与成年人不同的世界之中,创造了一种脱离成人社会的社会秩序。
那时我们把青少年问题拖给social disorganization,说工业化和现代化进程导致传统社会结构和秩序解体,秩序规范和社群关系没办法约束他们了。但是呢,后来的学者主张说青年成为了社会焦虑的替罪羊。
那现在呢?
青少年们头上是否悬着能够框定他们正常社会生活的道德景观?如果没有的话,逃离了道德身份的个体,是否一定会变得麻木不仁?
说人类比其他任何物种都更具可塑性,分娩的过程类似于从炉中取出一团融化的玻璃,能通过教育和社会化的方式来改变?实际上是不是已经上釉的瓷器出了窑,想调整就只能暴力碎裂或者刮花那张或美艳或平凡的脸蛋?
《通过仪式抵抗》读后感(二):随感
人类社会真的太复杂了。
心理学生理学、人类学社会学、性、教育、犯罪——有些人穷尽智识,毕生都在追寻如何解释这些命题微妙又复杂的相关性,可问题不断冒头,解决不了的我们都划分到了人类的终极话题了。就,我最近越来越相信人性本恶了。
1899年,美国伊利诺伊州开设青少年法庭,专门针对16岁以下的青少年犯罪事件,于是政府和帮教人士开始创办教育机构,争取更大范围的义务教育。这种义务教育延缓少年的成人化进程,相当于给了一个青少年“半独立”的生命阶段。
1904年,G.斯坦利.霍尔把青春期看成是一个独立过渡期,即14-24岁从青春期萌动到成年期形成的独立过渡期,掀起媒体关注青少年问题的热潮。
20世纪20年代,芝加哥学派开始研究这个独立阶段。30年代开始,有了对这个青少年阶段存在与否的争辩。像社会学家E.B.路透就秉持青少年是一个特有的生命阶段,在他《青少年的世界》《青少年社会学》等书里一直强调,青少年生活在一个与成年人不同的世界之中,创造了一种脱离成人社会的社会秩序。
那时我们把青少年问题拖给social disorganization,说工业化和现代化进程导致传统社会结构和秩序解体,秩序规范和社群关系没办法约束他们了。但是呢,后来的学者主张说青年成为了社会焦虑的替罪羊。
那现在呢?
青少年们头上是否悬着能够框定他们正常社会生活的道德景观?如果没有的话,逃离了道德身份的个体,是否一定会变得麻木不仁?
说人类比其他任何物种都更具可塑性,分娩的过程类似于从炉中取出一团融化的玻璃,能通过教育和社会化的方式来改变?实际上是不是已经上釉的瓷器出了窑,想调整就只能暴力碎裂或者刮花那张或美艳或平凡的脸蛋?
《通过仪式抵抗》读后感(三):译者修订并致歉
《通过仪式抵抗》出版之后,除印装质量外,本人发现译文校订时还存在一些差失,特做如下修订,供读者继续批评指正:
.247 注释1:“哭泣者”乐队(The Wailers)是牙买加青年巴布•马利 (Bob Marley),应改正为鲍勃·马利,与其他地方统一。
.145 右侧框第三格第11注释 蒙利雷(Monterey)流行音乐节,应改为蒙特利,以与后面统一。
.235 下方校注1 The Story of Utopia应为The Story of Utopias.
.251 第二段第2行“征服”应改为“战无不胜的”
若大家还发现有错误或不确切处,请将您的批评意见直接发到豆瓣或本人邮箱mdengying@163.com,本人将认真斟酌再加修正。
(孟登迎 )
《通过仪式抵抗》读后感(四):青年亚文化的隐喻
这本书断断续续看了好久,它陪我走过了期末考试和夏令营申请等一系列破事。最初是因为我想写摇滚亚文化的课程论文,就在图书馆找到这本书,没想到它竟如此吸引人,甚至让我产生了做文化研究的想法。
言归正传。这本书以孟老师的一篇文章作为总序。孟老师也算是乡建体系的吧,在群里经常看见他的发言,满满的都是对工农的关注。序言对青年文化的历史和青年亚文化的研究史做了梳理,很有意思。芝加哥学派的研究,在城市社会学课上曾有过涉及,帕克等人对城市社会的亚文化群体做了参与式观察,而在这之后,最熟悉的恐怕是写出《局外人》的贝克尔,他的标签理论对越轨现象的解释深入人心,突出了标签的权力意涵;应该说,芝加哥学派更多的强调结构对人的限制,将亚文化群体视为被塑造的存在,而伯明翰学派则赋予亚文化群体以一种抵抗的能力与可能性,政治因素与阶级因素浮上水面。威利斯的《学做工》对传统的文化生产理论的突破也在于此,他们都强调了人的主体性和文化实践的反抗意义。说起来,我这个学期尝试做的参与式观察其实还处于对芝加哥学派的模仿阶段,经验的描述占据主要地位。慢慢来吧。
总序过后,便是霍尔与杰斐逊合写的两篇序言,对伯明翰大学当代文化研究中心所做的工作进行了概述。
“青年亚文化是以想象的方式、象征性的方式‘解决’现实政治难题的一种特殊的生活方式。”(16)
想象与象征,所以它更像是一个隐喻。青年亚文化是青年用来彰显自己、创造群体认同,抑或反抗权威的一种手段?可以确定的是,它不能解决现实难题,政治的问题只能通过政治来解决,其他所有的因素都只会发挥间接的作用。但是,它兜售着一种幻觉,青年浸润在亚文化之中,仿佛拥有改变世界的力量。让我想起马克思对宗教的论述,现实的问题在幻象中予以解决。
序言之后,是一篇篇论文,就不单篇讲了。挑一些有意思的点,多是阅读时写在笔记本上的。
有关文化的理解。似乎从来没有一个有关文化的准确定义,在高中时,答题似乎有一个规范,常将文化与政治、经济并列而谈,似乎在政治与经济之外的就是文化的范畴,比如文学、艺术,就是典型的文化代表。与之相反,有些人会将文化视为一个特别宽泛的概念,似乎什么都可以归为文化,衣食住行、政治经济、意识与行为,都是文化的表现与文化的产物。其实我比较倾向于第二种。但在看过《学做工》和这本书之后,对于文化,或许可以有新的理解。文化是一种实践,所以它是被创造的,是人的生活方式,它体现在观念中,也体现在社会组织和制度中。但是,文化并非随心所欲的创造,而是在既有的历史与环境被创造出来的,这是限制,也是人类文明传承的必要条件。作为研究者,关注文化,就是关注人,就是关注人们的生活,就需要我们进入他们的世界,或者说尝试着进入,移情。
对于亚文化的分析,可以有两种方向。
一是将它放置到更大的阶级文化之中,即在他们的父辈文化之中去考察青年亚文化,二者有共通的部分。这是历史的角度,可以说不管做什么研究,没有历史的分析,都是不深刻的。这一点,野草也说过,但他应该是从一个马克思主义者的角度来考虑的吧。在父辈文化中,工作之外的休闲具有无比重要的意义,而青年也如此,将休闲作为意义所在。
二是要从亚文化与主导文化之间的关系这一视角来分析。主导文化试图收编亚文化,可以使用多种方式,比如意识形态的强制,比如对亚文化的污名化,比如商业逻辑的明疏暗堵。当亚文化被商业化操作,它注定被脸谱化、刻板化,由体变面,由面变点,而且由于支配文化有选择权,它可以决定被公开的那一面究竟是什么。媒体将亚文化拆解,不同的人看到的亚文化不尽相同,于是它就可以在不同的人群中有不同的呈现。更重要的是,亚文化被推广之后,它与原来的生成土壤就分离了,可以说,这些风格都变得无根,而正是因为其无根的特点,才能更加轻易地被挪用。书中举了黑人音乐的例子:黑人音乐在20世纪50年代被南方白人工人阶级采用,“黑人的表达方式被吸纳进带有存在主义外壳的白人都市浪漫主义之中”。(282)白人音乐人借此收获了名声与掌声,而黑人则依旧默默无闻。白人年轻人以表面的种族弥合来体现自己与上一代人的不同指之处,并进一步体现代际裂痕。假的弥合,假的裂痕。文化权力和种族差异帮助白人音乐人获得成功,他们实际上改写了黑人音乐的意义,“不是从一无所有中去创造物品和意义,而是要把给定的和借用的物品转换和重置成一个传达崭新意义的形式”。(306)当然,在这里没有谁应该受到道德谴责,亚文化就是如此,挪用是无比自然的行为。
iggy pop说,美国用毒品守护心灵。对于垮掉的一代而言,守护心灵的不可能是美国梦,而是一个个比美国梦更加真实的幻梦,产生于毒品,产生于音乐,产生于酒吧,在这些幻梦中,他们触摸到当下感。换个国家也是一样的。“好青年”受到守护,越轨者则被指责万劫不复,当那万分之一甚或千分之一或更多的偏差出现的时候,是以强烈的价值抑或意识形态去贴上标签并加以矫正,还是去理解这些偏差的产生原因,去理解一个个孤独的世界?当偏差出现,当意识倡导无法赢得所有青年的内心认同的时候,这些人的心灵由什么守护,毒品是犯法的,娱乐八卦是违禁的,肥皂剧是被否定的。是啊多可怜。没有人守护他们,没有东西拯救他们,他们被抛弃了,美丽世界的孤儿。
每一个指向他们的诉说都有关我们自己。
这本书还对工人阶级亚文化和中产阶级反主流文化进行了对比。工人阶级青年注重工作与休闲的二元区分,对休闲顶礼膜拜;中产阶级青年则将工作与休闲的区分忽略了,他们探索的是一种完全颠覆的状态,最极端的就是不工作;工人阶级占用现有环境以构建自己的休闲领域;中产阶级则迁离现有环境,去寻找飞地,所以《猜火车》中那样的群居公寓才会出现;人们对工人阶级亚文化的态度是去政治化的,认为他们不过是典型的青少年罪犯,流露出的是流氓的本性;而对于中产阶级反主流文化,人们则敏锐嗅出其中的政治色彩。
青年文化的意味,我在看书的时候写过这样一段话:它以代际性的裂痕展现了社会文化的整体裂痕。这一不可避免的趋势,使得青年亚文化往往展示出脆弱性,好像青年们最后都被收编了。其实不然。因为从一开始他们就有可能在无意识地跟随着社会的深层变革前进,他们是弄潮儿,他们最初以为自己在抵抗,最后才知道自己与时代结合得最紧密。“反主流文化萌发于主导文化内部的这种质的断裂中,萌发于主导伦理的新旧变体之间出现的中断。”((156)所以说,青年文化展现的不仅是代际的裂痕,更是社会文化的整体裂痕。
最后,研究者们对研究方法做了一些说明。反对客观社会现实,反对大写的科学家,反对单纯的归纳。追求开放的关系,逐步确立的重点,研究者的掌控性,理论的生成性,边缘角色的扮演,关心与理解的表达……总是有太多规范,而这些规范似乎又在告诉我们,不能有那么多规范。要像张无忌那样全忘了才好。“质性研究以研究者自身作为工具”:这是写在研究方法书上的鬼话。当研究的目的不是寻找概括性的短语或者符号,研究者就不再是一个工具,他是人,是目的,他是一个在体验中生成甜蜜的孩子,是在互动中不断构建自身与世界联系的新人,他的每一次问话,每一个眼神,都是给这个世界的礼物。
“研究则必须保持视野的敏感性和洞察力的可达性,坚决反对将已确立的参与式观察研究惯例化的倾向。他只有通过投注孩子般‘瞪大眼睛’式的关注,或者通过不断变化观察地点,或者通过抓住每一个机会去想象性的扮演自己所遇到的他者‘角色’,才可以做到这一点。”(4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