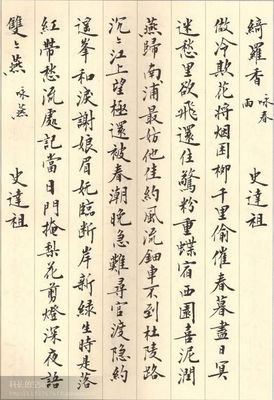
《唐宋传奇集》是一本由鲁迅校录著作,北方文艺出版社出版的513图书,本书定价:46.00元,页数:2006-11,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唐宋传奇集》精选点评:
●妖比人有情
●女子与才子豪侠相遇,幻梦和史实交织,精彩极了。希望它在高中教材里能露个脸,让大家试读一下,总会有人喜欢的……是吧?
●选得还行。
●白话版翻译的倒还不错,但显然是画蛇添足了嘛。
●在唐传奇的世界里,女性的美好让我流连忘返
●哦,这5颗星是给鲁迅的。白话什么的我现在不想看。
●故事中的故事
●恩 花了好几年 算是一点点全部看过去了吧 霍小玉永远的最爱 赵飞燕传别致生动 开河记和梅妃传出乎意料的好 李师师外传帝王之辞 其他都说烂了 无双 飞烟 绿珠 为上品。
●不过才子佳人
●这套书的价值只有薄薄一册.厚厚那册做参考用.
《唐宋传奇集》读后感(一):《莺莺传》心理笔记
想得很美,而社会不能成全你,因此自怜。因物喜,因己悲,根源在个体遭遇和社会结构规范的冲突。要理解个人,首先要理解个人心理的社会背景。唐朝的性观念真的像传说中的那样开放吗?贞节观念真的淡漠吗?如果真是,那么张生向红娘表明心意时,怎么结果是“婢果惊沮,腆然而奔”?可见丫鬟觉得礼数之外的男女交往是可惊、可羞的,但至于是不是可耻,还不可知。惊和羞,是社会风气并不流行之故,但不一定可耻,就像改革初,人们对婚前性行为更能接受了,因为人口流动,城市化,很多个性的、自我的东西出来了,而且现实经济关系改变了,子女在他乡打工、工作,比父辈挣得还多,父母之言也就没威力了,但要聊天说出来,还是会羞,会惊,因为毕竟不流行,非常态,不像现在,奉子成婚已经是种模式了,朋友很平常谈论性事也不奇怪。所以,从丫鬟的反应,那一惊,一逃跑,以及后来又说,“郎之言,所不敢言,亦不敢泄”,可见唐朝的婚嫁、性观念里,非礼交往还是很严重的,至少让长辈知道了是不得了的,保持贞节是普遍的,丧失贞节是少数的,像莺莺本来“贞慎自保,虽所尊不可以非语犯之”,对张生也不搭理,“张生稍以词导之,不对”,这才是女儿应有的自觉。
但是张生又能说出“若因媒氏而娶,纳采问名,则三数月间,索我于枯鱼之肆矣”,可见男人心中,不明媒正娶而直接在一起是合情、合理,有正当性的,他觉得爱之深之切就可以抛开程序礼仪,也就是说,婚前性行为并不是不合时宜的,如果那于时代是万恶的,像中国宋明理学那样的存天理、禁人欲,并且认为唐朝“闺门不肃,礼教不兴”,“唐源流出于夷狄,故闺门失礼之事不以为异”《朱子语类》,那么张生说这话简直就是强盗,跟抢压寨夫人一个性质,就好比如今的利比亚男人如果说:“我爱你,但是我想在娶你之前跟你上床”,那么他一定不爱她,因为婚前性行为在利比亚是可以乱棍打死的罪孽,他对她没有一丁点的保护之心。
所以对比保守的,又对比开放的,大略可知唐朝是介于保守和开放之间的。至少在唐朝男性眼中,张生并不是始乱终弃的十恶不赦者,“时人多许张为善补过者”。他的行为似乎既没有违背法令,也没有违背道德。就连莺莺都说:“始乱之,终弃之,固其宜矣,愚不敢恨。必也君乱之,君终之,君之惠也。”莺莺认为,始乱终弃是“宜”,宜不就是合理的事吗?既然合理,他的背弃最多是可恨、可伤心,但不至于可谴责,可责备。她虽深怜自己深情,“骨化形销,丹诚不泯;因风委露,犹托清尘”,但也潜意识认为儿女之情这是女子所耽,而男儿有仕途志求,如果把儿女情看得很淡,也是志向所驱使,堪称志向坚秉,所以莺莺会说出如果张生“达士略情,舍小从大,以先配为丑行,以要盟为可欺”,她自己就骨化形销,丹诚不泯。她料到,并且认可张生的选择,因为人必然会根据社会结构规范下的理性选择来揣摩他人的行为,并且以“公共领域的规范思维”来表示理解。但她内心必然是抗拒,悲痛。个人境遇和社会结构有了严峻的冲突在这里。
之所以能发生这样的冲突,当然唐朝那既开放又保守的社会状态是原因之一。《故唐律疏议卷第十四户婚》明确有言:“诸卑幼在外,尊长後为定婚,而卑幼自娶妻,已成者,婚如法;未成者,从尊长。违者,杖一百。”也就是源据这一言,网上有流行的话说“《唐律·户婚》规定:子女未征得家长同意,已经建立了婚姻关系的,法律予以认可,只有未成年而不从尊长者算违律。”狗日的要查找百度百科、流行说法的原始论据还真是浪费了我很多生命,但一想到顾彬在没有电脑的时代读遍中国古籍来研究唐传奇,我也真是觉得我可能并不适合读历史。总之,这一句,的确给张生对莺莺的追求披了一件合理性的外衣。唐朝男女大可以私定终身,再让家长知道,反正已经有夫妻之实,唐律也承认,任由“婚如法”。张生也的确有娶莺莺之意,文中有句:“张生常诘郑氏之情,则曰:‘我不可奈何矣’。因欲就成之。”只因张生要赴京赶考,所以事情耽搁了下来。
但其实,他们之间是毫无社会结构规范的反对和束缚的。莺莺虽非豪门,但是家产殷实,张生虽然科举得中,但也是寒门出身,所以门当户对的,连红娘最初都提议他直接走“父母之言,媒妁之命”的路。毕竟在唐朝,由父母等长辈主婚,出婚书,下聘礼,走一走那张生嫌太长的过程,“若因媒氏而娶,纳采问名,则三数月间”,这才是正道。凡事儿女在外私定终身的,成了事实就算了,不成的,还是得听父母主婚,否则“违者,杖一百”。
可是后来,张生断了念想,时人还认为他断绝和莺莺的关系是好事,因为张生说莺莺这种尤物,为蛟为螭,变成什么可怕的都不一定,他法力浅驾驭不了,“时人多许张为善补过者”,当然,这里的时人是男性群体,是男性群体的集体思维,而淹没泯灭了女性的声音。在我看来,莺莺不过是有些抑郁质,情绪变化无常,给人的压抑感很强,张生你不爱她就算了,干嘛编说法来贬低她。
《唐宋传奇集》读后感(二):读唐传奇三则书札
春天里的一日,在中国古典戏曲赏析课上初遇《莺莺传》,虽然早已对它与《西厢记》剧本的关联有所了解,而始终未曾真正细细品读过,这一读,竟是“一往而深”了。
《莺莺传》之前,先重新认识元稹此人。对元稹的印象,最深是他的菊花诗和悼亡诗《遣悲怀(三首)》,今读《莺莺传》,一言蔽之,笔下尽是一片“珍重”:菊花诗道“此花开尽更无花”,是教人对于光阴、季节、生命力的珍重;《遣悲怀》中想起从前与妻“落叶添薪仰古槐”的窘迫,而今“俸钱过十万”,却只能“与君营奠复营斋”的遗恨,和“昔日戏言身后意,今朝都到眼前来”的惘然之感,人总是在还拥有时轻言失去,哪知这世间一切再永恒也终有无法把握的那一天,于是回头看时才懂“珍重”二字之贵之难;《莺莺传》中更是缠绵悱恻之后便各自行路去,只是当时莺莺是明白的,那一封复给张生的书信,“千万珍重,珍重千万”,竟是一个女子把自己的一生都寄托在了这两句简单质朴的叮咛中,可惜张生不懂这一句“珍重”的重量,那个社会的官宦世界也不容许这样的“珍重”。元微之一生多情,却也负了望江楼畔的薛涛,“珍重”二字,如何容易?
翻阅日本小南一郎先生的《唐代传奇小说论》,了解到《莺莺传》的主题中其实有对唐代社会色爱与婚仕的关系的探讨,从当时官僚世界的常识来看,男子进入官界,为了谋求官职就必须与原本共同生活的女性斩断关系,与门第适当的女性结婚。小南先生以为,对于斗志昂扬的科举派年轻官僚来说,虽然当时自己主动选择了“婚仕”的世界,但在巨大的政治挫折之下,对于这样的选择又心起疑惑,孤独的心中不断浮现的是“婚仕”之前,那位可以与自己会心一笑的女性的倩影。官僚世界那种极端的、不近人情的观念使他们反思,张生的“尤物”之说,不全是个人品性的暴露,更是那个时代官宦世界的“潜规则”,传奇小说的故事本身,最开始是从这些年轻科举派的“谈话”场合被制造与流传出来的,所以《莺莺传》虽为一悲剧爱情故事,但有的不仅仅是爱情而已,还蕴含着年轻科举派在婚仕之际对官僚阶层不近人情的观念与规则产生的深深的疑惑,而正在此时,唐以前根深蒂固的门第观念其实正在动摇,传统官宦制度控制下的社会观念(包括文人士大夫的观念与民间的观念)都受到了冲击,并开始显现出新的萌芽。
同样的,《李娃传》与《霍小玉传》都是在婚仕制度笼罩下才会发生的爱情故事,而《李娃传》却不是遵守,而是尝试突破,且最终在小说里成功了。妓女李娃最终成为郑生的正室夫人,郑生及其父在婚仕规则与色爱世界之间,选择了后者,然而在现实世界中,这是举步维艰的,小南先生认为这只是一张“空绘图”而已,但它的确提供了一种新的可能性,为密不透风的严室打开了一扇窗户。
而不管是《莺莺传》抑或《霍小玉传》,虽然都以色爱世界的失败而告终,但也都使做出这样选择的男主角受到了或多或少的“惩罚”,如《莺莺传》中张生在多年后欲以哥哥身份重见莺莺而不得,只得到了莺莺的两首含有怨愤和惩罚之意的赠诗;《霍小玉传》中的李生亦在小玉死后经历几次婚姻而都不得安宁,遭到了小玉“阴魂”的报复。但仔细分析,莺莺仍是制度与爱情中的受害者,两首赠诗虽可以羞辱张生并可能引起他无限的悔恨,但女子的一生仍是这样悲哀地度过了,张生的回头没有解决任何实际问题,二人终究是陌路了。因此,《莺莺传》中虽然借助爱情悲剧写出了对官宦社会婚仕规则的怀疑和反思,但是它在承认现实社会体制的牢固性后,最终仍然设置了一个让两人老死不相往来而能各自安好的乐观结局;李生虽然得到了报应性的下场,但并不是因为无情制度的改变,而是借助了豪侠相助、鬼魂作祟这样的怪异事件才得以实现,所以,根本上,《霍小玉传》还是逃避了对官宦世界无情规则的质疑,用怪异事件的发生给了心有不平的读者们一个交代,然而在现实中既没有豪侠人物出手相助,也不会有灵异事件的发生,依赖这些超越日常的力量去解决问题只能是叙述者提供给人们的激动幻想,女性仍然是这一规则下的牺牲品。总而言之,《莺莺传》《霍小玉传》都曾经做过怀疑的努力,但最终还是回归到了社会的主流观念中去,但至少它们之中已经显现了中晚唐社会意识转变的生机。
中唐时期传奇小说以男女恋爱题材为主,然意义不止于恋爱本身,其后更隐藏着唐代社会的诸多面貌,比如唐代的城市格局与阶层划分的密切关系,如唐代独特的丧葬仪式与主办机构“凶肆”,如引起故事发生发展的复杂的人际关系,及形成此种关系的社会制度,都是小说极有价值的部分。除去才子佳人的恋爱教训,有太多用现代思维无法解读的东西值得去关注和探究。无论古今,皆有“深情”,亦有“无情”,但在不同的时代却往往会发展出不同的故事,给人以想象,给人以悲壮,让人能够退回到百年前一个纯粹热烈的世界,这也是读故事的迷人所在。
《唐宋传奇集》读后感(三):遥窥正殿帘开处
——《流红记》《梅妃传》《赵飞燕外传》等
就像普通女孩不可能成为韩剧女一号,古代平民妇女也很难成为传奇的主角,只有神鬼、妓女、宫廷命妇之类的身份才有一丝距离以便文人们穿插艳情的遐想。恐怕是多了“皇权”可供意淫,比起妓女神鬼,宫廷内闱显更具有血腥的色彩,宫廷女子的倾轧、幻想和苦难显得尤为诱人。
一、倾轧
《梅妃传》描写的是玄宗后宫梅妃和杨贵妃争宠的故事。杨贵妃入宫前,梅妃“侍明皇,大见宠幸。长安大内、大明、兴庆三宫,东都大内,上阳两宫,岁四万人,自得妃,视如尘土,宫中亦自以为不及。”可自杨贵妃入宫后,玄宗对梅妃“宠爱日夺”。梅、杨二妃两人展开了一场旷日持久的大撕逼,对骂“梅精”“肥婢”,大清早“捉奸”,活色生香。安史之乱爆发,玄宗带了杨贵妃细软跑,梅妃死于刀兵,杨妃薨于白绫,家国之乱面前后貌似盛大的宫斗争成了过家家的笑话。
如果说梅妃和杨妃没啥亲缘,她们的背后可能站着不同政治力量的话,那《赵飞燕外传》中的赵飞燕、赵合德这对嫡亲姊妹之间的关系更为微妙。进入汉成帝后宫后,飞燕为后,合德为昭仪。在汉成帝告诉赵合德“吾昼视后,不若夜视之美”后。她“即以不夜珠为后寿。终不为后道帝言。”用“姐姐我给你买了个包包”的方式,达到破坏姐姐在成帝眼里“夜视之美”的目的,心机可谓深矣。赵飞燕对妹妹赵合德也是嫉妒的,汉成帝这个hentai喜欢偷看合德洗澡,“赵后知帝见昭仪益加宠幸,乃具汤浴,请帝以观,既往,后入浴,后以水沃,愈亲近,而帝愈不乐,不终幸而去。”明显,赵飞燕的天真近乎于愚蠢,她将自己对妹妹的嫉妒公开了,而且不明白皇帝就喜欢偷窥的刺激,结果适得其反。不过在飞燕给成帝带绿帽子被发现的时候,赵合德还救了姐姐一命,原因是她清楚“臣妾缘后得备后宫,则妾安能独生?”赵飞燕一旦被拔掉,赵合德立刻失去了后宫里的一条大腿,还可能面临新的竞争和威胁,对家族和个人都不利。君主必须广育子嗣,通过广泛的支系来拱卫专制。子息的有无和多少对后宫女性来说是命运交关。蠢姐姐赵飞燕为怀孕私通外子,被发现后险些被杀。她便诈托有孕,产期临近只好派遣心腹骗买民间男婴,因为婴孩吵闹而闷死数个,最终仍不得成功,赵合德表示听完我就呵呵了。既然我生不出,你们就选择死亡吧,于是杀死了其他怀孕的后宫女子和她们所生的皇子。(姐姐:“是在下输了。”)
二、幻想
《流红记》讲的是于佑在御沟边捡到一片红叶,叶上有诗一首:“流水何太急,深宫尽日闲。殷勤谢红叶,好去到人间。”经过多重偶然之后,于佑与红叶题诗的宫女韩氏巧结良缘。 这样一种罕见甚至很反常的情况,反映了广大后宫女同胞的内心的呼号——我要过正常的夫妻生活!
再看《唐玄宗恩赐扩衣缘》——“开元中,颁赐边军纩衣,制于宫中。有兵士于短袍中得诗曰:“沙场征戍客,寒苦若为眠。战袍经手作,知落阿谁边?蓄意多添线,含情更著绵。今生已过也,重结后身缘。”兵士以诗白于帅,帅进之。玄宗命以诗遍示六宫,曰:‘有作者勿隐,吾不罪汝。’有一宫人自言:‘万死!’玄宗深悯之,遂以嫁得诗人。仍谓之曰:‘我与汝结今生缘。’边人皆感泣。”到了明代,天然痴叟对这一故事进行改编,写成短篇小说。小说中的唐玄宗听到这一事件时的最初反应是“大怒”,若不是杨贵妃的巧言劝谏,唐玄宗对“有意寻私”的宫女是准备“赐之自尽”的。虽然小说中的唐玄宗恩准了宫女与军士的婚姻,但他在下诏时却附上“后人不得援例”——万一大家都以这妹子做榜样,皇家的威严和利益不保。
《无双传》里的王仙客和无双最后得以大团圆,经过几重离别,十余人死于非命。也许是作者耽于猎奇,但也说明抱得宫中美人几无可能,屌丝们看看就好,不要多想。
三、抗争
很难说抗争的行为有效果,毕竟我们从来只看到坚固的高墙和撞墙破碎的鸡蛋。然而自由人格无时不在内心呼号,一些皇宫里的妹子还是越界行动了。
有的宫女在皇帝无暇一顾的情况下,与别的宫女搞百合(名为“对食”),有的宫女则与宦官结为“夫妇”(名为“菜户”)。《汉武故事》云: “女巫楚服著男子衣冠,帻带绶,与皇后寝居,相爱若夫妇。上闻,穷治侍御、巫与后诸妖蛊咒诅,女而男淫,皆伏辜。废皇后,处长门宫。”女巫楚服居然敢挖皇帝墙角,结果只有选择狗带。
对后宫女子红杏翻不对是出墙这类现象的描写以《醒世恒言》中的《勘皮靴单证二郎神》较为著名。该小说叙后宫女子韩夫人与假扮二郎神的庙官孙神通私通。结尾作者之所以让她“躲过”了惩罚大约是出于对她的同情,其实她的结局更可能是被杀或终生囚禁。
谈起以自杀退场的人,人人都会先说起她的死,好像自杀变成了她人生的终极目的。《迷楼记》的就是故事从宫女侯夫人的死开始。人们只知道自尽前侯夫人留下的宫怨诗,是多么细腻地反映了一个得不到君王宠幸的后宫女子复杂、沉重的痛苦,以及死前对生的留恋。尽管她死后炀帝大的肆怀念表彰是多么鲜花着锦烈火烹油,是否足以使得逝者在九泉之下有一丝慰藉,又给众多的同样处境的生者何种感受呢?
寥落古行宫,宫花寂寞红。
白头宫女在,闲坐说玄宗。
只可说玄宗,不可说肃宗。
《唐宋传奇集》读后感(四):补江总白猿传拾遗
一、文人相撕?
《补江总白猿传》开篇云故事发生于“梁大同末”,欧阳纥生于大同四年,大同纪元共十一年,故“大同末”欧阳纥还不足八岁,绝不可能是兰钦的“别将”,也未成婚。那么《传》以欧阳纥为主角,意图何在?
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中言“(欧阳)纥……子(欧阳)询以江总收养成人,入唐有盛名,而貌类称猴,忌者因此作传,云以补江总,是知假小说以施诬蔑之风,其由来亦颇古矣。”汪辟疆《唐人小说》亦云“唐时风气,往往心所不嫌,辄托文字以相垢,如本传(《 补江总白猿传 》)及《周秦行纪》皆是已。”可见唐时风气托文词相诟,今之读者看起来精妙诡谲的小故事,暗藏着政治斗争的机锋,机锋指向不是欧阳纥而是他儿子欧阳询。《补》彰显了我国骂人优良传统——问候你祖宗,于是欧阳纥悲伤的扮演了一回谦儿哥的爹王老爷子(又名于德纲,郭小宝)的角色。
那么问题就来了,泼脏水的人是谁呢,和欧阳询什么仇什么怨?
先来看看欧阳询是何许人,据《旧唐书·欧阳询传》:“高祖微时,引为宾客。及即位,累迁给事中。询初学王羲之书,后更渐变其体,笔力险劲,为一时之绝,人得其尺犊文字,咸以为楷范焉。高丽甚重其书,尝遣使求之。高祖叹曰:‘不意询之书名,远播夷狄……’。”传虽然短,但是已经透露了俩关键信息: (一)欧阳询是高祖还没发家时候的老朋友,。(二)字写的是武德朝第一。“开元通宝”上那几个字就是他写的(想想人名币上印着你的字)。 还编修了《艺文类聚》和《陈史》,宝宝在高祖身边那真是红极一时。这时候难免有人眼热,但还不敢冒险对红人做什么。
咣当一声玄武门之变,一朝天子一朝臣,李世民做了皇帝,就把他虞世南扶了上来,虞世南“忠直博学”能写能画,深得太宗赏识。虞世南死后,欧阳询尚在,太宗却对魏征说“无人可以论书”,因为太宗最崇拜王羲之书法,虞世南曾师事王羲之后裔释智永,是王书的嫡传,而欧阳询“书出于北齐三公郎中刘泯”,并不为太宗所亲。初唐欧、虞、褚、薛四大书家,实为两派,虞、褚、薛为一派,询为另一派。这儿的褚是褚遂良,这货素有称霸书坛的野心,曾问虞世南“吾书何如智永(虞世南的师傅)?孰与询?”可见压人一头的野心之甚。虞世南死后,褚正要接过虞的旗帜,以继承人的身份才能充分得到太宗的信任,而欧阳询的存在无疑是一个巨大的威胁,必须把他搞臭。而褚遂良打压政治对手,谄媚太宗的文字也多见于史传,诬谤欧阳询是极有可能的。《补》写作时间推测当在虞卒后,欧卒前,极有可能是褚遂良授意手下文人作。
二、流变
钱钟书言“猿猴好人间女色,好窃妇以逃,此吾国古来流传俗说,屡见之稗史者也。”可见“猿猴盗妇”故事是一个较为常见的民间故事母题。“猿猴盗妇”的流变经历了两汉六朝逸事实录、唐代文人遐想、宋元明道佛宣教三个阶段。
1.缘起:
自汉以来,四川民间就存在大量存在的猴玃盗女传说,“猴玃盗妇”题材在汉代蜀地画像石中也频繁出现,成为了各种文学艺术作品的故事素材。汉焦延寿《易林》 卷一 “坤之剥” 即载:“南山大玃,盗我媚妾。怯不敢逐,退然独宿。”晋代张华的《博物志》卷三“异兽”记载:“蜀山南高山上有物如猕猴,长七尺,能人行,健走。”《博物志》记载,“猳玃” 盗取美妇所衍生的后代所组成人猿杂交的群落,是由,它们与人无异,皆以 “杨” 为姓,有明显的生理特征“玃爪”,聚居在蜀中而形成族群。
之所以会在四川等地有这样的故事,一方面是此处多山,多猴玃的生存环境。蜀道之难阻隔了许多人,也为当地抹上了神秘的色调,这种神秘提供了一系列想象的暗示。猴子与人交媾生产出的后代在相貌、 智力和行为方式上会怎样?西南地区彝羌等族人,长相与中原汉人殊异,他们是否是猴子与人的后代?
2.早期佛教故事影响:
佛教传入中国后影响逐渐增长,尤其是佛教故事因其情节和趣味性广为传播,也有人认为从情节的构建来看,《补江总白猿传》 应该是写作者在中国古而有之的 “猳玃盗妇” 传说的基础上嫁接汉译佛经中的罗摩故事创作出来的。
《六度集经》中的《龙本生经》记载了这样一个故事:从前有一个菩萨为大国王,育护众生,声动遐迩。而他舅舅也在另外一个国家为王,性贪无耻。舅舅兴兵欲夺菩萨国,国王为使子民免于战乱,便和王后亡逸山林。海有邪龙,迷恋王后美貌。便化为梵志,入山禅定,骗取国王信任。然后在国王出去采野果的时候盗挟王后而去。于是,国王便踏上了寻妃之路。后来在寻妃路上遇到被舅舅夺去王位的猴王,他帮猴王打败猴王的舅舅,夺回王位。猴王便发动手下的众猴帮国王寻找王后。 最后,在化为小猴的帝释天神的帮助下终于杀死了邪龙,夺回了王后。此时,他的舅舅也死了,臣民寻求旧君,他便又回去做了国王。
3.道佛争胜:
唐宋以后佛道二教抢地盘,纷纷对民间流行的 “猿猴盗妇” 故事进行宗教化的改造,譬如白猿盗妇是为了道家通过“房中术”的内丹修炼,而不是像此前文本里的兽性需要。宋元话本《陈巡检梅岭失妻记》中既有释家长老规劝猴精向佛,也有道教真人施法降妖。颇有意味的是,宋元话本《陈巡检梅岭失妻记》中,佛家不如道教,而在明代小说《会骸山大士诛邪》 中,佛教渐占上风。
此后“猿猴盗妇”的故事逐渐褪去其早期对艳情、异兽的好奇,转向宣扬道、佛法力的教化故事。降妖伏魔也是老百姓喜闻乐见的主题,其流变应合了俗众对民间文学的心理期待。
三、猴赛雷
白猿登场时,“有物如匹练,自他山下,透至若飞,径入洞中,少选,有美髯丈夫长六尺余, 白衣曳杖, 拥诸妇人而出”,风流倜傥、俊秀洒脱的美男与众绝色美人嬉戏场景与之前的沉重氛围截然相反。“见犬惊视,腾身执之,披裂吮咀,食之致饱”则又是一转,,使文本忽生一抹妖异浓艳的亮色。食色性也,但多数人终究囿于“发乎情而止乎礼”的伦理道德训诫,白猿的“好色好酒”恐怕也表现了以作者为代表的部分世人对这种审美意识的自觉审视。
后来白猿书简被烧的“怅然自失”和“木叶之初,忽怆然”则揭示了白猿丰富敏感的心境以失意士子的苍凉口吻隐约道出了外物永恒而生命有限的巨大落差。死前自叹“此天杀我”岂不让人回想起当年西楚霸王“天之亡我,非战之罪”的悲怆?想来白猿修行千年,却依旧“将得死罪”,唯托天命才能令自己屈服,竟有了一丝希腊悲剧的意味。“顾诸女汍澜”以及临死前为保儿子而“大叹咤”,显然已成为与你我同类的拥有情味之人。
可见白猿的形象充满着文人的瑰丽想象,却也能嗅出明显的文人情怀。尽管这篇传奇是讽刺之作,但读完却觉得此文中的白猿比欧阳纥更加有血有肉。
《唐宋传奇集》读后感(五):动真心者则为受压迫者,读《霍小玉传》和《李娃传》
霍小玉传》和《李娃传》要放在一起来看,并不是因为什么“都歌颂了低贱女子对爱情的忠贞,揭露了封建社会对妇女的践踏”,或者什么“都写了唐朝才子佳人的故事,反映了唐朝士人的精神面貌”,这些共产体的文艺评论还要继续践踏中国文艺多久。。。
要放在一起来看,是因为互为补充。读了《李娃传》,才能不骂李益软弱,明白他得知母亲已定下表妹卢氏为亲时“逡巡不敢辞让”其实深可同情。今人以今人之爱情观,骂他竟然一丁点力争的意思都不表示,绝情负心软弱如此。但《霍小玉传》明明白白告诉今人,他胆敢争取,其后果统计规律上很显著,就是他父亲一巴掌拍死。“以马鞭鞭之数百。生不胜其苦而毙,父弃之而去。”还好那毙在此不是死,而是扑倒意思。父亲不知道他为妓女流落街头时,尚还洒泪于亡子,知道亡子没亡,就干脆打死,免得他丢人显眼。为一个妓女丧志?那种大逆不道,轻则不给你寄钱了,重则打死打伤永世不见。唐朝门族、等级观念如此伤筋动骨,谁敢抗争?郑生也算是“消极抗争”了,心中至情,被李娃设计逐出妓院后没有立即写信回家骗父亲讨要些银子,而是情苦念重,抑郁不得出离,故身心颠沛流离。李益也有消极抗争,他假托要为给百万聘礼筹钱,“事须求贷,便托假故,远投亲知,涉历江、怀,自秋及夏”。他就挨时间。他以为时间可治愈小玉之恨,“生自以辜负盟约,大愆回期,寂不知闻,欲断期望”。他不是不力争,而是他非常明白惨局,郑生都浑身溃烂了都。他只是在矛盾中无声地痛苦,虽身未受鞭笞,而心已受千百遍。
当然,今人会说,既然《李娃传》里的郑生可以为李娃亡产败金,连功名都不考了,那么霍小玉的男人就不能放弃些什么?可见还是李益贪心功名,一攀高门,所以负心。说是这样说,说得好像悲剧是由个人的选择中来。但以我愚见,《李娃传》和《霍小玉传》的悲剧,都只是结构性的,还不是个性的。
李益和郑生的行为不同,并不因个性的不同,而因在同一结构的不同位置。李益本就是闻名天下,“丽词嘉句,时谓无双”,唐史上真有其人的;“先达丈人,翕然推伏”,在唐代科举制度里,社会名声好,有前辈引荐的,阅卷的就会给个高分儿,因为阅卷是不“弥封”的,李益的考前自我营销显然是到位的、成功的。何况李益已经“以进士擢第”,只不过由进士到当官还需要经过“科目选”,已有进士出身身份的,选一科目考合格,才能授官,所以李益有了三年的等待期。他非常明白自己的处境。人的本能会让自己很清楚自己的处境。李益清楚自己在等待之间想要的不过是风花雪月感官富足人生正途之外的游戏,故事第一句就道明了,他内心“自矜风调,思得佳偶,博求名妓”,不过是看得起自己的风流,想要一场风流,也因此才会在霍小玉提出“妾年始十八,君才二十有二,迨君壮士之秋,犹有八岁。一生欢爱,愿毕此期。然後玅选高门,以谐秦晋,亦未为晚,妾便舍弃人事,剪发披缁,夙昔之愿,於此足矣”时,他感到惭愧。小玉是真爱,可以放弃自己,成全他想要迎娶“五姓女”的门阀地位心,而自己古佛青灯度残生,小玉可以如此至情,豁达,他却只是自矜风调,一场游戏,所以他羞愧。但他清楚自己的前程,只要不搞出什么迎娶前罪臣霍王爷的小女、如今的倡妓的大新闻,就一定会走向人生巅峰。话说回来,有几个人肯为了一个女子,放弃自己的人生巅峰?你会为了一个年轻貌美的女子,就放弃做谷歌的总裁的机会吗?你会为了一个地位卑下但合你心意的女子,就放弃创造阿里巴巴神话的机会吗?人对自我的成就总是有极高的幻想,这可以驱逐其他一切幻想。
相比之下,郑生是什么角色呢,不过是个自小有些聪明、赴京赶考的秀才,顶多是带的钱够他在京城花两年,钱多得让他父亲以为他是“以多财为盗所害”,但前途还未定,声名也谈不上,更因为跟李娃混了一年,也没在科举界用功做自我营销,科举无望了,钱花得也差不多了,对李娃是“倒过去”的情感依附关系。
是郑生需要李娃更多一点,而霍小玉需要李益更多一点。
古今世界一样,谁站在被需要的位置,谁就有主动权。
所以李益选择放弃,李娃选择放弃,李益不看好他和霍小玉的爱情在自己人生中的位置,李娃不看好郑生这个人在自己人生中的位置,其实是这个逻辑。
假若霍小玉也同样不以爱情为首位,那么他和李益,不过是好聚好散,不会有什么悲剧,但恰恰霍小玉当爱情为生命,这才让李益震惊,霍小玉对爱情的那种坚韧不拔让他震惊,因为他没有。
而假若郑生也同样没有那么多情,如果他不是“生怨懑,绝食三日,遘疾甚笃,旬余愈甚”,而是立即托书给父亲让他寄点钱来,想必他随便编几句话,半年的生活费还是骗得来的,那么他和李娃后来也没有故事了。但他没有,他只是日夜的悲伤,他和霍小玉是一样的,把爱情看得很重呢,即使过去了几个月,仍然在悲戚里,“每听其哀歌,自叹不及逝者,辄呜咽流涕,不能自止”。
所以在同一个社会结构里,未必总是一方是受害受压迫者而另一方总是强者,未必总是这样,人是从结构中受益还是受害还要看人在其中的态度,对其他人的依附。在《霍小玉传》里女人是受压迫者,而在《李娃传》里男人是受压迫者,其本质是一样,动了真心,产生了依附,因而动真心者成受压迫者。
读了《李娃传》,才能明白一个地位卑贱女子能说出“不邀财货,但慕风流”的话,真正是“有一仙人,谪在下界”,霍小玉就是仙女一枚,并且她对李益动心了。李娃那样的不过是妖姿要妙,又“与通之者,多贵戚豪族,所得甚广,非累百万,不能动其志也”,就是有色,有钱,又只为了钱,因为她明白和士人的恋爱是不能当真的,士人们没得势时喜欢她们,得势了就要娶高门贵族的女子,“士之耽兮,犹可脱也,女之耽兮,不可脱也”,李娃一开始就很理智,她肯定不会为了一个郑生这样的人物就像霍小玉那样死去活来的做了厉鬼也不放过李益。
所以李娃的骗郑生,设计逐他出门,也是深刻同情的。但是郑生对她动心了,已经到心愿和她有子嗣的地步了,所以李娃可以用“与郎相知一年,尚无孕嗣。常闻竹林神者,报应如响”的借口轻易地骗得他流落街头。
还是那句话,动真心者是受压迫者。《霍小玉传》里,压迫者李益终受内心折磨。《李娃传》里,郑生其实和霍小玉一样,个性的结局本该是为情死的,但是白行简对他大概有十万分的同情,让他和李娃在雪夜乞食相逢,李娃感其至情,终对他“晨昏得以温凊,某愿足矣”,压迫者李娃终于救赎了罪过。
《李娃传里》两情在磨难之后,其父因她于他有恩而诚意赞成婚事,其实还是结构性的。如果霍小玉不死,将来战乱中救李益,李益也可感念其恩情,说服他父母。所以终究,两个故事是同样一个结构性的悲剧,也可成同一种结构性的喜剧。
结构还是那个结构,唐朝的门阀观念之下士大夫和倡妓之间的爱情。能使这一结构有故事的,必有宁为情而死的个性。但悲剧之因,不因个性,而因结构;而悲剧里,动真心者是受压迫者。
但居然到最后,《李娃传》不但不称赞郑生至情,还赞李娃“倡荡之姬,节行如是,虽古先烈女,不能逾也”。也不知道唐朝士族的思维是怎么回事,反正明朝冯梦龙是明眼人,在《情史》里转录《李娃传》为《荥阳郑生》并文后曰:“世览《李娃传》者,无不多娃之义。夫娃何义乎?方其坠鞭流盼,唯恐生之不来。及夫下榻延欢,唯恐生之不固。乃至金尽局设,与姥朋奸,反唯恐生之不去。天下有义焉如此者哉!幸生忍羞耐苦,或一旦而死于邸,死于凶肆,死于箠楚之下,死于风雪之中,娃意中已无郑生矣。肯为下一滴泪耶?绣襦之裹,盖由平康滋味,尝之已久,计所与往还,情更无如昔年郑生者,一旦惨于目而怵于心,遂有此豪举事耳。生之遇李厚,虽得此报,犹恨其晚。乃李一收拾生,而生遂以汧国花封报之。生不幸而遇李,李何幸而复遇生耶?”
说了这么多哦,其实就一个理,《霍小玉传》和《李娃传》并没有个性的悲剧,只有结构性的悲剧,唯独一种个性,是用情至深的个性,但但凡是个爱情故事,也必然须有用情至深之人,所以也不算什么个性,所以这两个唐传奇,终究是结构性的悲剧,是唐朝士大夫阶层对科举、门族的痴心,是一个时代对于成功的幻念可以抹杀一些美好的东西,而时代对人的条条框框如此之多,让人无法抗拒。放到如今,这样结构性的悲剧也还是有,但是少了,毕竟时代人口流动特别大,你想要逃脱亲朋好友的品头论足是很简单,迁徙,到北上广,到其他二线城市,一份工作,结婚生子,过年可以不回家,一年不回家,十年不回家,接父母亲人来玩一玩就行了,谁也不要管谁太多,更何况,也管不着,大家不再是抬头不见低头见了,不过一年见一回,过过嘴瘾,多问你几句,社会习俗的压力已经不是制度性的束缚了,你怎么想,怎么看,全凭自己个性,总盯着负面看的,就骂这个社会压力太大,但其实都是个性的问题。这个时代有很多的故事都应该归结为个性的问题,但这个时代的文艺还十分钟情于结构性的问题。电视剧里演的全都是什么天帝、皇帝、王公贵族,和什么民间女子,或者家族关系一定要嫁给别人的女子之间的情愁,那些社会结构而致的悲剧的确深恸人心,但这个时代不同了,人格个性的不同、所致的选择不同、结局不同甚至悲喜剧的差别,应该有更加触动灵魂的力量。是的,这个时代的中国开始讲灵魂了,个体了,也应该多一些关于个体人格、选择的悲喜剧成为主流了,不要再让那些成为小众文艺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