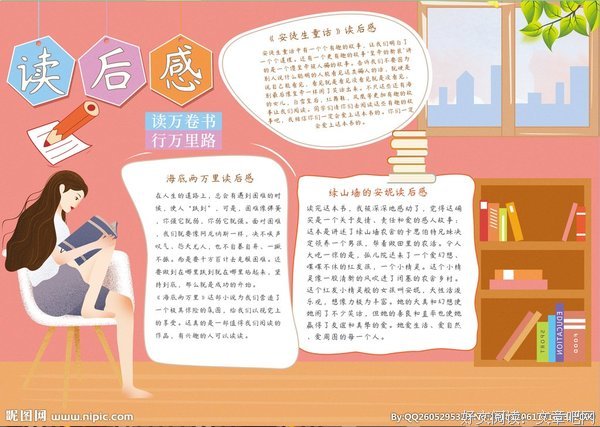
《寻羌》是一本由王明珂 撰文/摄影著作,中华书局出版的平装图书,本书定价:30.00元,页数:189,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王明珂的“反思性研究”倡导史学向个体的人转换。民族史的民族志强调“以史为纲”、“出古入今”,与人类学民族学切片横截面式的批判解构不同,它是纵向延伸的、建构的,将田野与史料相结合,在不断的历史回溯中修正与阐释人们的族群记忆。作为一本田野杂记,这本书是上升到学术之前不可或缺的感性材料,是通向“羌在汉藏之间”、“华夏边缘”、“英雄祖先与弟兄民族”等课题的重要阶梯。
●王明珂刚到羌族聚居区的时候面临的那种人类学理论与社会现实之间的张力给我很大震撼。可以看到他在田野调查中的温情与冷静,这很难得。照片很好。得看看他的那两本书了。
●书很好读,信息量很大,比起《羌在汉藏之间》容易读,而有效信息并不少多少,当然,缺了史料分析。
●想去做田野!
●作为一个生活在汉人村落的少数民族,作为一个完全汉化了的少数民族,作为一个同样处在资源激烈竞争之地的“西南夷”,作为一个从小听大人们“摆白”长大的娃儿,书中的很多描写都会引得我会心一笑,也更能从自身的角度去理解王明珂所见的羌族社会。
●与《蛮子、汉人与羌族》诸多重复,但照片跟多一些
●以前看《羌在汉藏之间》的时候被那信息量所震惊,倒是这书让人知道他到底是怎么在做,也算是袪魅了。
这是一本配合照片的田野杂记,来呈现作者十几年的寻羌之旅中所见、所闻,介绍各地羌村民众生活与沟中的文化、传说。一本名符其实的民族志调查。羌族内部是多元的,与外部的互动也没有清晰的界线。正如王明珂说的那样,我们所关注的“民族”认同与区分,过去在那里并不存在或并不重要。用“近代建构论”的观点来解释,羌族在历史上是一个模糊而不断变动、漂移的群体,他们处于汉、藏两族之间的族群缓冲地带,即族群的边缘,于是便随着两族势力的消长而改变其范围。在新中国成立进行民族识别之前,他们并不自觉为羌族。之前说到的羌族老人自称“我们藏族”,就是很好地说明了这一点;而将北川附会为“大禹故里”,也是汉与非汉少数民族之间分野模糊的证明。
《寻羌》读后感(二):历史上有没有一个羌族?——读《寻羌》
王明珂这本《寻羌:羌乡田野杂记》出版于汶川大地震后一年,他当时的田野地点恰恰在四川西北部的松潘、茂县、汶川、北川和黑水等地,使得这本书除了是对自己近十年的田野生涯进行回顾之余,多了些许纪念的味道,有些遇到过的人和地方再也不可能重逢了,在他看来,即使没有这次地震,羌族社会的剧烈变化也不可能暂停“脚步”,地震只是加快了这种进程。
王明珂之所以选择羌族作为研究对象,是因为羌族身上所具有的“非典范”特征,或者说“异质性”和“边缘性”。在近代民族主义史观的影响下,我们的历史书写通常以“民族”作为不言而喻的“实体性”的历史主体,羌族的历史亦是如此,从有信史记载的商代开始,“羌”便是“华夏”对西部疆域异质族群的称呼,随着秦人的崛起,羌人进一步西迁河湟之地,然后南下来到青藏高原和成都盆地之间的川西高原的河谷地带。从典范的中国民族史叙事看,虽然历经上千年,但是使得“羌”之为“羌”的血缘、语言、文化等要素一直保存和传承下来了,古今的羌族没有太大的不同。
在王明珂看来,这种典范的历史叙事,忽视了“羌族”并不存在的历史事实,“羌族”不存在,不是说历史上被华夏称为“羌人”的人群不存,而是说今天的“羌族”正是因为接受了这一套典范历史叙事,才成为“羌族”的。受后现代学术思潮的影响,上世纪70年代之后,民族“实体论”渐渐受到诸多学者的质疑,“想象的共同体”开始成为民族/国族研究中的主流理论范式,“民族”的构建特性也逐渐被人们所了解,构建论主张并没有那种从历史起源到现在一以贯之的实体性民族,民族是在现代性条件下的产物,由知识分子创造出来凝聚国民认同的新事物,相比于民族实体论,民族建构论更强调民族的主观认同层面。
在中国民族史的研究中,王明珂认为“羌人”成为“羌族”发生在上世纪60年代“民族识别”政策之后,书中他讲了一件特别有趣的事,青片乡有位老人在解放初参加在四川召开的各民族会议,会上胡耀邦送了一件藏袍给这位老者,老者讲述往事时不自觉会一口一个“我们藏族”,这句话引起了陪同王明珂的当地干部的不满,“跟他们说了好多次,我们是羌族不是藏族,他们就是记不到!”由此也可以看出,在民族识别前后,被称为“羌族”的这些人在身份认同上的模糊性,在第一本研究羌族的专著《华夏边缘》中,王明珂称“羌”是生活在华夏西部“漂移的族群边缘”之上,这里是华夏人的西部边缘,也是藏人的东部边缘,正好对应成都平原和青藏高原的地理环境。
王明珂在田野调查时发现了一个显著的现象,过去这里的寨子存在“一截骂一截”的现象,寨子下游靠近汉文化的人群称上面寨子的人是“蛮子”,上面的人说更上面的人是“蛮子”,这一歧视区分,更根本上是由人类资源共享和竞争的“社会本相”所“决定”。我们需要思考的是,是什么样的社会情景决定了华夏人称呼西方的异族人群为“羌”,进一步还可以追问,在华夏人的边缘发生变迁的时候,又是什么样的社会情景使得华夏人接受他们曾经称之为“羌”的人为“汉”。
这其中最重要的便是人们用以谈论族群源流的“历史记忆”,包括各种文本书写和口传神话等,王明珂借用考古学遗存的隐喻来说明“历史记忆”:为何作者如此取材(特定的人物、事件和象征意义);为何如此组织、制造(特定的文本结构);作者期望借此说明什么;如何操作和使用社会记忆(文本),并与其它社会记忆相抗衡;最后,在社会权力中,这些记忆如何被保存、遗忘、修改和推广。
王明珂在书中多次称赞黎光明上世纪20年代在川西北所做的田野报告,黎光明在田野报告中丝毫不隐瞒自己的“偏见”,他甚至不知道“社会结构”为何物,但这并不妨碍黎光明用一种“文学化”的手法把所遇见的人和事突显出现,细致的描述给人身临其境的历史感。所以在这本书中,除了可以对上述主题有所了解外,你也能感受到作者笔下一个个鲜活的面孔,爱“摆”的周老师,寡言却精通各种“羌语”的毛老师,热情却不幸牺牲在汶川地震中的正寿。
这些人有血有肉,一如这块土地,有丑恶、善良、悲壮、幽默。
《寻羌》读后感(三):寻羌:另外一种生活
最近一段时间,对西南一带的古文化比较感兴趣,因此手边放的书都是这方面的。而这本王明珂的《寻羌:羌乡田野杂记》,则是在图书馆里看到后,翻了翻,看是写川西羌族历史的,就顺手借了回来。
王明珂是台湾专门研究羌族及中国边疆史的,在卓越网上看到了好几本他写的书,想买,但又不知道写得如何,就一直将书放在了收藏夹里。这本书不算是学术著作,只能算是旅行笔记,是一本关于作者十年来到羌族地区进行田野调查的杂记。不过读起来倒是非常有趣,图文并茂,文字也很生动。在书中作者讲述了他在羌乡所见所闻所感,讲述了他在那个遥远边鄙之地的朋友们,讲述了生活在那个地方的民族的生活,讲述了发生在那里的故事,而这些故事这些生活是我们所不了解的,能够给我们带来不一样的体验。
我们看书的目的,一是获得新的知识,了解一些新的观点;再就是从书中体验到一些我们无法自己亲身获得的体验,增加自己人生的经验与阅历。《寻羌:羌乡田野杂记》一书,虽不是一本学术著作,从书中也看不到作者对于羌族的研究,但我们却能得分享他的体验。毕竟,像王明珂这样十多年来,每年都去四川羌族地区呆在几个月的人并不多,如他那样了解羌族文化与习俗的学者就更少了。
王明珂从九十年代中期第一次来到四川,来到羌区,在这里,他结下了一生之缘,也由于有了鲜活的事例与体验,让他的研究别开生面。作者在四川羌区十年来的田野调查,除了观察到羌族地区的雄奇地貌、古朴风俗及神奇传说之外,他接触得最多的还是人,是那些生活于羌区的居民。这些虽然已经逐渐汉化,但依然有着强烈民族传统与特色的羌民们,给王明珂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也给予他从生活到工作诸多方面的帮助。同时,他对于羌地这些淳朴居民的描写,也成为书中最为有趣,也给读者最多感慨的段落。
作者所去的羌地,即是四川汶川大地震的核心区域,即汶川、茂县、北川及松潘等地,这里正是羌族聚居之地。对此,在我们的媒体报道中提及得并不多,其实,大地震对于羌族群众的伤害更大。许多的羌民失去了生命,失去了亲人,失去了家园,作者的一个朋友即死于地震。然而,他们仍然是很乐观地看待着生活,正如他们长期处于困厄之中,面对我们难以想像的生存条件,却依然从艰辛中寻找生活乐趣一样。作者在本书的开头,即写了一段羌族的传说,说是地壳原是由木块及铁组成,在被火烧或者锈蚀穿后,现在的地壳是由石头组成。现在的人比当时的矮小多了,但地球也稳定下来,只是偶尔动一动,人类也就生存下来了。这则传说可以说是对汶川地震的一个预言,却也充满着乐观的情绪。
在这个我们看来是异常贫困的地区,他们却世世代代在这里生活着,并享受着生活的乐趣。山寨里的青年男女,唯一的赚钱渠道就是进森林里砍几根树木到集市上卖钱。天还未亮就得进山,天黑方能背着重达二百多斤的木材回家整理好,第二天一大早又出山,去集市卖,回到家时又是天黑。整整两天的辛劳,所能赚到的钱,只有三十元。不过,这已经让他们很快活了。在他们的眼里,这就是生活,有什么好值得抱怨的呢?当一位山里的老人听说山外有人因病而自杀的事,很是不理解地问到,人为什么要杀死自己呢?是的,他们自认自己的命很贱,只值一元钱(作者在书中写过一个小女孩的故事),但毕竟也是上天赋予的生命,一样有着存在的价值,一样有着快乐的权利。
当然,他们也有着对美好生活的期盼,但目的异常的简单,就是让儿子娶上媳妇,将女儿嫁到一个条件更好的寨子里去,不要过上父辈那样艰苦的生活。不过,这也是羌族延续多年的传统。也许,会有人认为他们这样的生活没有意义,对于生命来说太不值得。那么什么样的生活有意义呢?什么样的生活状态才是幸福的呢?我们生活于大山之外,生活于繁杂的城市之中的生活就一定幸福?我们物质丰富的生活就一定比物质匮乏的生活更具有意义?恐怕谁也不敢这样说。近年来,羌寨的年轻人也有走出深沟,到大城市里去的。作者曾听到一个羌民很自豪地谈起他在成都的儿子,同时又听到他的担忧,“城市里比山里的烦恼更多啊”。这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来体认生活,很难说清对错。对于生活有着不同的体验,这才构成了丰富的世界。
书中对于羌族历史的探寻以及传说的介绍,也颇为吸引人。虽说此书并非学术专著,更多是田野考察,不过,这种民族及人类学的田野考察,势必涉及到民族的历史与民俗的内容。书中多次提到上个世纪二十年代由中研院史语所在该地区所做的调查,提到一个叫黎光明的青年学者。他做了大量的调查,也写了很多考察报告。报告写得很有趣,一点也不像学术报告,更像是一份鲜活的观察实录。不过,靠着他的这份报告,让我们能够真实地感受到当时羌民羌俗。后来,黎光明放弃了研究工作,做了当地的一个县长,最后被匪徒杀死。
关于民俗,总是与一些神秘而奇怪的事件联系到一起,而这些神秘之事又总是被我们斥之为荒诞,并力图去年其神秘色彩,并按照自己的理解,以清晰的逻辑来勾勒出来。其实,这种清晰的符合逻辑的叙述,已经失掉了民俗的原滋原味。而在王明珂的书中,他则尽量地将故事的原态记录了下来,让读者能够体验到民俗的神秘之处。如他对于羌族的“毒药猫”的传说的叙述,让我们就有一种身临其境的感觉,对于这种神秘的传说,就会留下异常鲜明的印象。其实,这样的民俗,这样的传说,不管其荒诞也好,迷信也好,它是有其内在逻辑的,这也是一种另外的生活,一种我们无法理解但值得尊重的生活,毕竟这样的生活传统已经持续了上千年。
《寻羌》读后感(四):实地考察的经验之谈(对书中经验的部分总结)
摄影对于这样一本田野调查的随笔来说显然是极其重要的 设想这本流水帐一样记述访问羌语区各乡寨的传统习俗的小册子 如果只有文字 对于大多数来说读来肯定是枯燥的 但是作者设计成每一页的文字都辅以文字的形式 而且每一张的头一页整页是一幅质量极佳的当地风景摄影 宛如一个相册的封面照(封面和封底也配图) 这样下来可读性就提高了 "情怀"也体现了出来。
作者按照地区把整部作品分成七章 每章讲一个地方的见闻。大多数的内容都是在记录当地人讲给他听的故事,作为人类学家 通过故事来理解当地人的身份认同是如何构建的 又是如何随时代变化的 选取这些故事看似随意 其实还是根据作者所采用的理论框架来选取的 具体的理论观点总结在了作者的原创学术作品《华夏边缘》和《羌在汉藏之间》中。
对于我这样一个受过语言学的理论训练 并且有志于进行语言学田野调查的人来说 作者在这本随笔中讲述的许多行程中的准备工作的细节是最具有价值的。
一旦选择一个地区/文化来作为自己调查的对象 就需要了解这个地方的硬件设施和建立人际网络
作者无疑在这两个方面极为擅长。
(1)对于硬件设施: 作者几乎每年一次(据他自己说 只有在美国访学的一年中断)往返于羌区各地, 熟悉地形,环境,交通。
“我租了一辆车,先花上七天时间在整个羌族地区走一遭---由成都经汶川到茂县,往北到松潘小姓沟,再回头经茂县,土门到北川,由北川返回成都。这一旅程是为了选择安排往后进行田野考察的据点,但也让我见识到此地山之峻,谷之深,道路之险。”
大多数田野调查涉及的地方交通都不那么方便 那么租车,乘当地的车辆就变得很重要,多次游历和了解这些交通信息是必备的准备工作
有时光乘车不够,还需要自己不惜体力步行,所以非常辛苦,而需要检验自己的身体是否能够承认这种步行的要求也是一项准备活动:
quot;在小姓沟的埃期村,我花了五个小时爬上海拔四千多米的高山...这一行程证明我还能爬山,这是作羌族田野研究的最基本要件。“
“在此川马能发挥他们卓越的爬山能力,坡度太大时,人下马,拉着马尾由马拖着爬上山"
许多意外无法完全防范 也需要做好准备,包括在旅途中抛锚的住宿问题 和找到朋友帮助解决问题:
quot;...与泥石流、山崩、破车、坏路斗争”
另外出发之前对于这个区域相关的学术与流行媒体上的信息 作者也显然着意搜集了:
”那几年 大陆电视台播放一部有关黑水解放历史的电视连续剧,根据一本名为《陆上台湾覆灭记》的书..."
quot;那几年...我将他(黎光明)的手稿反复读了好几遍。由于如此熟悉,后来我每到松潘、镇江关、牟尼沟等地,一景一物都让我仿佛觉得黎光明以及他报告中提及的喇嘛,土官都活在眼前。"
后勤方面,建立大本营也是必要的。以城市化较高的,讯息齐全,与外部连通性强,购物方便的市镇作为大本营 规划出行路线和进行修整,作者就提到了自己是怎么做的:
quot;汶川...县城古称威州镇,这是羌族地区的行政与文教中心。从一条沟到另一条沟的中间,我经常到汶川住上一两天。。。。汶川县城也是我的”讯息中心“,四面八方各沟的民众常来县城办事、购物,做点小买卖,因此我可以打听到各地路况,以及我要找的人在不在沟里。”
用来分析语言的一个重要的题材就是 “讲古” (在研究搜死宾阳平话论文时得出的结论),因为在民间传说中保留的语料往往具有口语的特征。
最后,随身的录音 录像 摄影设施需要齐全,尤其有时有具有罕见价值的口头资料的场合,比如作者提到的过新年的集体跳舞庆祝场面,当地特有的羌族端公法事仪式,以及在520地震之后为保存濒危文化 邀请90岁的婆婆到宾馆房间去录像现场唱尼萨史诗这样的场合。
(2)作者的人际网络、交际能力非比寻常 确实适合从事人类学的工作(或者去做销售)。书中提到的几个故事都可以看出作者的有心,擅抓住难得的机会。
”我曾在台北市最繁华的天母访问一位黑水老人。过去他是苏永和加的"娃子", 曾随苏逃亡。那天我们坐在靠路边的咖啡屋内,老人戴着墨色眼睛,谈话间他不准我录音。“
甫到考察的地方 就开始结交朋友,使朋友掌握的信息与人脉资源为自己的调查服务:
quot;我到北川的第一天,泽元便安排。。。几位北川人作我的"报导人".正寿之外的几位北川朋友都较年长,也都十分熟悉地方掌故与文史资料。“
作者专心于构建长期的, 固定保持联系的人际关系,随着时间推移作用会愈来愈大,比如90年代中旬认识的几个朋友,后来在当地做官员 掌握了更多可以帮助作者调查的资源与信息:
quot;2001年我打北川过,特别去看望正寿、泽元,当时正寿已到县委工作,泽元也当上了北川民族宗教事务所局局长"
通常情形下,当地的知识分子是最宝贵的知识来源。
”威州师范学校的几位老师,当时曾参与羌族文字创作及教育推广。他们热衷于采集、研究羌族文化,因此那几年我们成了工作伙伴。“
”我以松潘埃期沟作为较藏化的田野点,北川...为较汉化的田野点,而茂县永和沟居于两者之间。威州师范学校的周老师是茂县永和沟人,毛老师则是松潘埃期沟人。他们俩是对我的田野工作帮助最大的羌族朋友,可以说,若没有他们的帮忙,我可能无法完成这些研究。“
知识分子和政府官员可以直接去拜访和结交,但是更多的民间朋友还是要靠更加耐心的办法。由于擅长聊天,所以会在与人闲聊中找到自己想找的地点的人,获得实地考察的机会,仍然是擅长捕捉机会和有心 得来的机会:
“在与他们的闲聊中,几位来自蒲溪沟的老师邀我们到他们家乡耍耍,我欣然接受邀请。”
《寻羌》读后感(五):个体经验的卑微与丰美
前几天周末下午去三联书店,赶上《70年代》新书发布会,嘉宾有李陀、李零、徐冰三位,也没有怎么仔细听讲演与讨论,不过却记下了徐冰讲到的一件往事。
徐上世纪九十年代刚到美国时,曾和艾薇薇合住过一阵,有一天,艾薇薇从图书馆借回来一卷录影带,俩人一起看,这盘录影带的内容是Beuys在课堂上给学生讲现代艺术——徐、艾等人要去美国寻找的东西。然而,徐冰说,事实上,他后来所得到的东西,并不是那盘录影本身所给予的。那卷录影带带给他困惑:在那些学生在课堂里听Beuys讲现代艺术的时候,他自己在干什么?他想起来,当时,他在中国的农村劳动。于是,他接着想,究竟自己和那些学生相比,是少了些什么,还是多了些什么?
于是,后来西方媒体问起他说:“你来自那么保守的一个国家,怎么能做出如此现代的艺术?”徐冰说:“你们是Beuys交出来的,而我是毛泽东交出来的,Beuys比起毛泽东,那简直是小巫见大巫了。”
究竟少了什么多了什么呢?很明显,少了所谓的文化知识、艺术理论……然而多了的,却是实实在在的生命经验,是的,经验是不可复制的,可遇不可求。
我曾经和一个近八十岁的老人聊天,他生于上世纪30年代初,小学赶上侵华战争,初中赶上日本投降,国共内战,高三高考的时候,正是49年共党要进北平的时候,后来上了燕京大学,毕业留校,之后便伴随中国上世纪后半叶的风风雨雨,直到80年代末去国……
听他娓娓讲往事的时候,历史是另外一番面貌,比起课本上宏大叙事和官方基调来,个人历史活生生,即便场景对于时隔半个多世纪的人说是陌生的,然而喜怒哀乐却相通,而且很容易为人理解,回首往事,老人对于历史的荒诞,没有仇恨,有的却是更深沉的省思。
刚开始谈的时候,有时候他会用自己的经验给我一些忠告,我往往有自己的看法,还会辩论,然辩论后却感到自己的无力,因为,如果我没有办法充分理解并感知他的经验的话,又有什么理由去驳斥前辈的忠告?
那时我便想起电影《一一》,童年的洋洋因为不和变成植物人的婆婆讲话,而被妈妈批评,他说:“可是我真的不知道说什么,婆婆已经那么老了,我以为我要说什么,她都知道。”洋洋想要的和爸爸想给的不是一回事,洋洋又说:“爸爸,我看见的你看不见,你看见的我看不见,那我怎么知道你看见了什么?”这两句话,我印象太深刻。人人从生到死难道是一回事嘛?那怎么还是有那么多的冲突与互不理解呢?如果我们理解起个人来都如此困难,那我们还如何宣称说理解历史、社会与艺术?
由此,我又联想自己曾经的西北行,2004年夏天,我直接从北京飞到乌鲁木齐,然后从乌市沿北疆跑到南疆,最后回到乌市,做火车往敦煌,再到嘉峪关返京。
走之前,听说过很多惊心动魄的故事,不外那些动荡叛乱的事。就像文本和现实一样,这些东西任你在脑子里想,和你真去了体验,是不一样的。
北疆的风格更偏向中原一些,像乌市、库尔勒这样的城市,绝不逊于内地大中城市,但南疆的民族风情就完全不一样了,那对于一个长期生活在中原的人来说,完全是另一番模样,很新鲜也有些不适应,却没有任何排斥,因为接触到的维吾尔老乡都非常的憨厚淳朴,大家在一起根本不是一上来政治或者民族,都是日常生活吃穿住行的交流与沟通,没有那些被人贴上去的政治符号和民族标签。更多的是,人与人享受偶然相遇的那份喜悦。尤其是一路陪伴我们的司机师傅,他是哈萨克人,会好几门语言,一路上给我们很大的帮助,他的身上,那股实在的真诚劲儿是很多受了高等教育的人反倒没有的。
我的个体经验再次和政治叙事发生了矛盾,我承认,这只是我私人的经验,不足以有代表性,而政治问题是一个无比复杂的问题,是一个小我根本很难理解的,但是我只是想说的是,这些问题在一个普通的百姓那里或许根本是不存在的,在那里,每天一家人的吃喝拉撒睡才是真理是王道。
生活与经验总是实在琐碎的,其中的人们或许不识文字不通理论没有知识,他们的一切却在不断地被表述被描绘被分析被说明,然而,他们才是生活的主角,旁人无法取代。如果研究他者,不是为了找到自己,那么他者有什么意义?知识、结构、表述、理论……又有什么意义?
回到《寻羌》吧,我想我明白为什么会有这本书,作者要用书写抗拒遗忘与流失,很多他的朋友和他曾经留恋的羌藏村寨在大地震后都不复存在,去年的下半年,我曾经有过几次和王老师聊天的机会,那时候,川西羌族的种种则是绕不开的话题,我只是听他讲,插不上嘴,唯一的回应,就是好奇地问东问西。
除了那里人们的生存环境和生活方式外,“一截骂一截”和“毒药猫”的现象,是我印象最为深刻的,因为这类现象并不特殊,它们在不同的地方都以各种形式存在着。
纪念自然是写作的初衷,然而我相信老王还有一个深意,即对人文学术和学者本身的追问。作者的寻羌之旅开始于1994年,当时他已经拿到哈佛大学的博士学位,并得到中研院的终身聘职,但是首次进入内地来到四川,亲身经验却颠覆了他许多已有的理论知识,对于“早已熟悉充满拗口的学术词汇、艰涩的西方理论”的他来说,这一次的经历和震动让他明白,什么才是真正的反思性认知。
原打算一次严肃的“田野调查”,同行的田野探勘队员却是“一车老弱妇孺”,而“喝白酒、爬山、接受村寨与城镇羌族朋友的热情招待,与泥石流、山崩、破车、坏路斗争”便是十年来探勘活动的缩影。
原本打定主意要找到一个“与外隔绝,有经济生产、社会组织到宗教信仰皆自成体系的村落”做典范人类学的田野调查,在自认为找到了这样一个村子的时候,一觉醒来,头顶天花板却贴着一张台湾青春偶像林志颖的大幅海报,作者没有像有些人类学家那样有意忽略“土著”家中墙角边的可口可乐罐那样,而是如实地记下了这一切,并开始修正自己对人类学、对人文学术那些先入为主的观念。
正是在这平实而自觉的想法驱使下,出现在作者田野手记中的,是一个又一个鲜活的个体和生命经验,还有人生的无常、命运的坎坷。如果终究要回答的是“我是谁”这个问题,那么我们就没有理由忽略个人,空谈社会、世界、人类。因为,即便作者熟读过涂尔干《自杀论》,当真正面对一个自杀了的羌族百姓时,他却发现学术似乎离得很远,对于那些百姓来说,他们心中想的,不外乎一家人温饱,为儿子娶媳妇盖房子,将女儿嫁到条件更好的村子里去……
在川西地区的实地考察和羌族百姓的真实共处,作者积累了大量鲜活的材料,不乏有趣的瞬间,在《寻羌》一书中都有详细记录,而也只有从这个材料中提炼出来的分析,才是真正有意义的学术工作,那便是作者的另一本书《羌在汉藏之间》。
寻羌之旅最大的收获,是让作者明白,学术归根到底,需要摆脱价值偏见、学科偏见、主观偏见、世俗偏见等等现实因素时,还是要回头来解决现实的问题,正是知识与现实之间的这种二律背反,使得知识的修炼,实际上成为一种性命的修炼。
有回聊天时,王老师曾讲起布迪厄《区隔:趣味判断的社会批判》,强调说,学者一定要时时警醒自己要反省自身偏见,当时让我联想到佛教思想,当我说出这个想法时,王老师说,有时候学生找他在书上签名,除了写对方的名字和自己的名字外,他都不知道写什么好,于是经常就写“破法我二执”,我一听一愣,心想,这份自觉,也许正是他不断追求学问精进的最大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