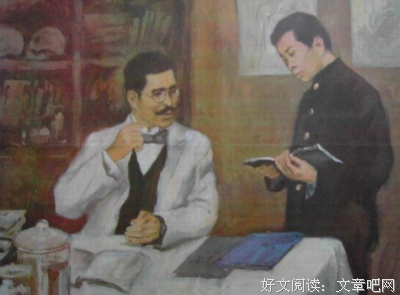
《异乡人》是一本由(法)加缪著作,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的精装图书,本书定价:38.00,页数:152,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一定是第二次读了。 人每天都在渲染自己的情感。 可以看出聪慧、普通、正常的冷漠
●日常和荒谬
●“这是我的生活方式,只要我愿意,它也可以完全是另外一种。”
●就是局外人。。。
●默尔索这样的自由疏离主义,或者是之前我看到的一个笔名:冷眼旁观,他们甚至对于自己的遭遇依旧不予干涉,也许他们才是真正内心有一腔热情的人,我不得要领。
●我不确定社会上是否会存在一个纯然的“默索尔”,但我能感到我有与他一样的地方——在有些时候,不愿说谎。
《异乡人》读后感(一):这只是一部小说啊。
加缪说他写莫索尔有这个境遇是因为在这个社会没有遵循这个社会的“游戏规则”,比如说莫索尔为什么没有在母亲的葬礼上哭泣。可是在看了第一部分主人公的自述上,我明明感觉他对自己母亲像是对一个陌生人一样毫无感情,一个生活了几十年的人毫无感情让我觉得这个人物塑造的有些极端,这并不是尊不遵循社会的“游戏规则”这么简单。
加缪还在序中说了,莫索尔是个老实人,不想说谎掩饰自己。“这个说谎不仅是指鹿为马、扭曲事实,还是夸大其词;而如果从违心之论的角度来说,就是过分渲染自己的感受。这是我们每个人每天都在做的事,为的只是方便行事”。在我看来他就是没有感情的动物,他有一般动物的情欲肉欲还有对生的欲望,这仅仅就是动物层面而不是人类啊,莫索尔没有对杀人举动有一丝丝的后悔而是有些困惑,对,他自己都不知道这个需要后悔吗,时期就是这样发生在呀,对他人生命没有一丝尊重,这和禽兽有什么分别呢。
本书为一让我震撼的是大量大量的心理描写,让我不自觉将自己的是非观代入其中,我很难不以我现在的价值观去评判这个人,但是,这么较真干嘛,这只是一个小说啊,并不是真人真事改编,描写这些心里的人也不是一个杀人犯啊。所以我被无形的代入了作者的制造的一个漩涡中,这也是这个作品的伟大之处。
地点:阿尔及利亚-阿尔及尔,非洲北部,与西班牙隔海相望,地中海气候。
仿佛一个话剧,平淡的太阳、天气、街道等等撑起了上篇,平淡中透露着零星的快乐,但是那是默尔索眼中的世界,平静,客观,云卷云舒。
下篇因为一场意外而变得丰富,审判长、检察官、陪审团、律师、监狱牧师、养老院的人、曾经的“朋友”(也许“过客”更为合适)纷纷入场,原本默尔索作为个体的感受、情绪都被一瓦解又重新构建。当感受、情绪被解读,一切都变得不纯粹,默尔索依旧用局外人的眼光看着这一场辩论,思绪依旧被太阳、温度、汗水、扇子带走。他冷静、“冷漠”。也正是这个特质被重新解读,让他走向生命的最后。可是也是一个异乡人,他感受到自己的“冷漠”并无情绪的接受属于自己的迟早要到来的黎明。
文中默尔索多是“无所谓”的,不在意的,认为很多事情与其无关。为数不多的情绪表露是偶尔听到对自己的带有偏向性的判决,可是这些思绪也很快被天气、温度、太阳、汗水带走。真正的发怒是在与监狱牧师会面的时刻,为数不多的自我独白和感情释放,让默尔索宣泄了这一情绪饼充分阐述她的世界。读者也第一次这么直面他的内心。愤怒过后是自我揭示的平静。如果说曾经默尔索无所谓,那么这时他说自己“冷漠”,并欣然接受“这世界温柔的冷漠”。
一个“冷漠”的过客被处死,这便是世界的准则。客观承认自己情绪的人仿佛变成一种犯罪。每种情绪都来自自己,如何解读又是别人的事情。没有过度渲染的感情仿佛成为一种错误、一种和弑父一样严重丑陋的犯罪。如加缪自己所说默尔索是我们所应得的唯一“基督”。那么何必在意他人的解读呢,和俗世的规则呢。欣然接受这世界温柔的冷漠吧,将其作为自己的衣帽,作为异乡人的个体变不回那么孤单。
《异乡人》读后感(三):《异乡人》美国版作者序
阿尔贝·加缪,1955年1月8日(张一乔译注)
许久以前,我便曾以一个连我自己也承认非常矛盾的句子来总结《异乡人》:身处于我们这个社会,任何没有在母亲葬礼上落泪的人,都有可能被判处死刑。我想表达的只是本书的主人翁之所以被定罪,是因为他没有遵守游戏规则。从这个逻辑来看,他在自己所生存的社会里是个异类,游走在每个孤独、感性的个体边缘。这便是为什么有读者会试图将他当作一个泯灭天良、十恶不赦之徒来看待。然而,若是能进一步探询默尔索是出于什么样的缘由,而不照游戏规则走,就能对这个人物有一个更确切,至少是更接近作者意图的印象。答案很简单,就是他不愿说谎。
这个说谎不仅是指鹿为马、扭曲事实,还是夸大其词;而如果从违心之论的角度来说,就是过分渲染自己的感受。这是我们每个人每天都在做的事,为的只是方便行事。与表象恰恰相反的是,默尔索不愿意这样做。他言必属实,毫无保留,拒绝掩饰自己的情感,这让社会大众立即感到了威胁。例如,接受审讯时他被要求按照惯例,承认对自己的罪行感到后悔,他却回答与其说是后悔,不如说是困扰居多。正是这其中的细微差异,导致他罪无可恕。
因此对我来说,默尔索并非道德沦丧之徒,而是个毫不矫饰的可怜人;拥抱烈日,在那之下容不下一点灰色地带。他非但不是冷血无情之人,内心深处更存在着一股热情,出于固执,始终为这份对绝对与真理的热情所驱使。尽管这个真理只是不愿发表与自己实际的情感和认知相左的违心之论,但缺了这一步便永远无法战胜自我,做自我完全的主宰。
所以,将《异乡人》解读为一个毫无英勇之处的人,甘愿为真理而死的故事,虽不中亦不远矣。我还曾说过同样矛盾的另一句话:“我尝试以我的主人翁形塑出我们所应得的唯一基督①”。经过我的一番解释,大家就会了解到我说这句话没有任何亵渎神明之意,而仅是出于作者对于自己创造的人物原本所应有的、带点揶揄自嘲的特殊情感。
(①此处是将默尔索因追求自己内心的真理而获罪与基督受难相比,然而默尔索并非救世主,此为吾辈凡人所应得。)
《异乡人》读后感(四):异乡的局外人
读的是张一乔的译本,书名为《异乡人》,国内许多译本译为《局外人》。后一个译名会引发另外的联想,更切近于关乎人与外界关系的讨论。初读的时候觉得小说叙述者是一个空心人,但加缪自己在序言里否认了这点。加缪说他不愿意说谎,他第一句话就很诚实,他忘记了自己母亲死的日期,葬礼上也没有哭。萨特说这本小说的每一个句子都像一座座孤岛,的确如此。
但这样的人就该被判死刑吗?默尔索没有遵守社会规则,但不能否认他本质上也十分冷漠和麻木。这种与众不同的超离可能也让其有了一些不一般的魅力,让女性妄想接近,但真的可能吗?这个人物放在现在语境里可能也可以称作佛系,但佛系更是一种自嘲,是无可奈何。在默尔索那里,也并不存在这种无奈,因为他是无所谓。从个体而言,默尔索是无趣且单薄的;但就社会而言,即便无趣和单薄的人,也有存在和享受他自己乐趣的自由和权利。每个人都有选择自己生活的自由,即便这个人选择成为孤岛。小说的表现手法真是高超,默尔索眼里看到的世界,邻居,老狗,都是对照和映射。和玛莉的相遇,简直是难得的一束光,但还是失去了。默尔索应该也是有一丝丝后悔和不舍的,包括一些痕迹,一些回光返照,默尔索也想起了母亲,但他不愿意去承认,继续麻木,以为这样,会没有悲伤。当然也不会有快乐。尽管很短,但这部小说的解读是异常丰富的。这是好作品的特征。
默尔索尽管诚实,面对暴劣冷漠的世界他也只能报以消极的反抗,他只是用“个体无意识”替代了集体无意识。他的内心真的一片荒芜,但对此毫无讳言,也没有动力说谎。这种“反抗”是不合作,但也不建设,这位小说的结局增加了荒谬和虚无感。 小说的结尾部分有这么一段:
“为了替一切画上完美的句点,也为了叫我不觉得那么孤单,我只企盼行刑那天能聚集许多观众,以充满憎恨和厌恶的叫嚣来送我最后一程。”
读到这恍若是阿Q再临,希望在看客面前再表演一番,但他们的心态又是完全不同的。这也许是东西方不同的麻木方式,阿Q式的麻木是完全认可了这个世界的荒谬并成为荒谬的一部分,而默尔索则对之加以拒绝,尽管他仍然害怕孤单——他们的区别在于阿Q并不明了什么是孤单,他只是爱热闹。
加缪的存在主义首先是一种消极自由,可以这么理解:当人类投身于社会的准则,在利益与立场之间抉择,为了达成目的或者意愿而充斥谎言、萌生恶意、遍布奴性、邪恶丛生,甚至不择手段,在集体无意识的推动下,那些不假思索、自以为是的表达与行为便自然而然成了真相,身处异己的境况并不意味着自我谬误,越混沌愚昧,越要保持清醒,纵使独自忍受痛苦,也不同流合污;即便被大多数人视为“局外人”,也要奋起对荒谬予以反击。
加缪在《西西弗神话》里明确了这种自由和悲观,“在他离开山顶的每个瞬间,在他渐渐潜入诸神巢穴的每分每秒,他超越了自己的命运。他比他推的石头更坚强。”这里面蕴含的消极和自由也是对保持个体主体性的自我安慰。唯此,无所归依。
前一周也读了加缪的一些剧作和政论集,加缪始终对极权主义保持警惕,他甚至厌恶阿尔及利亚的民族运动,这为加缪带来了无尽的攻击,包括曾经的友人萨特。历史证实了加缪的担忧和恐惧,独立后的阿尔及利亚最终成了专制国家。托尼朱特在《未尽的往昔》中评论加缪是一位天生与自己、与自己的世界合不来的人。而这一特点在他早期的这本小说《异乡人》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作为作者,加缪对默尔索的感情也是矛盾的,他一方面一再赞扬默尔索的诚实和不妥协(见美国版序言),另一方面,对默尔索的描述中,又可以发现加缪的批判和不以为然的。这两种情感的张力构成了小说文本的丰富性。完全赞同默尔索和将默尔索作为社会主流排斥的边缘人进行彻底否认都不会是加缪的本意。
在诺贝尔获奖演说中,加缪宣称“对于我们明知之事决不说谎,以及对压迫进行抵抗”。在他的处女小说《异乡人》中,加缪只完成了第一步,而终其一生都在对第二步进行可能的探索和尝试。悲观和荒谬是加缪的底色,但他并不愿意在其中“永恒轮回”,这是加缪的可贵。可能也是悲剧所在。抵抗没有尽头,抵抗可能会走向乌托邦的另一端。
《异乡人》读后感(五):异乡人·译后记
说来幸运。我在接下《异乡人》这本书的翻译工作之前,并没有读过它的任何一个中文译本。
之所以说这是一种幸运,主要是我对个人文字作品的一种偏执使然:不爱咬文嚼字,堆砌辞藻,更惯于反复琢磨,在用字遣词上偏向与他人不同。所以,如果当初在接手时,已经熟读过其他译者的版本,于我反而是一种负担,甚至更要经过一番纠结。
《异乡人》是加缪最为人所熟知的经典之作。任何人在翻译生涯中能接到这部作品,应该都会感到非常幸运,更何况是像我这样一个一点也不多产的译者。其初版于2009年9月在台湾地区上市,刚好是我从事这个行业满八个年头之际,此时的我对法译中的工作已经驾轻就熟。能在那样水到渠成的时刻接到这部作品,又怎能说不是一种幸运?
这份幸运也并非全然无迹可寻。加缪不仅是小说家、哲学家,也是位剧作家,他从大学时期即对戏剧产生兴趣,其后也陆续创作了如《卡利古拉》等多部名作。而我从高中毕业后一直到留法期间,学的也都是戏剧,可以说那一度是我在彷徨的青葱岁月的出口和心灵依归。或许正因如此,后来我才能有这份机缘。
个人最熟悉的同时期剧作是另一位存在主义代表人物萨特的《无路可出》。萨特与加缪不仅同为20世纪法国文坛闪耀的巨星,还曾是惺惺相惜的挚友;尽管后来两人的友谊因为在政治理念上的分歧而画下句点,为后世无限唏嘘,人们还是热衷于对他们从相知相惜到毅然决裂的前因后果的追问,乃至将之视为一种瑜亮情结进行探究。
《异乡人》是加缪的第一本小说,于1942年一出版便广获好评,隔年萨特便发表了一篇颇为知名的书评,文中特别以“美式叙事法”来形容加缪在这本书中的行文方式;这一段有关《异乡人》文风的解析,似乎也是萨特整篇长评中最常为人所参考、引用的。此种风格是如此鲜明和独特,从故事一开场便教人无法忽视:“今天,妈妈走了。又或者是昨天,我也不清楚。我收到了养老院的电报:‘母殁。明日下葬。节哀顺变。’这完全看不出个所以然。也许是昨天吧。”《异乡人》开头的短短两行文字,居然用掉了七个句号,且没有一丝不妥。萨特称本书的句子就像一座座孤岛,是加缪刻意为之,是巧妙精湛之所在,也是我当初在翻译时希望忠实保留并清楚传达作者原意的原因之一。
除此之外,萨特对本书之所以命名为《异乡人》,也提出了自己的看法。首先,故事的背景所在地阿尔及利亚的首都阿尔及尔,对法国人来说已经是一个“异乡”。接着,萨特在书评中大量引用了加缪同年发表的《西西弗神话》,来解读这部作品所欲阐述的人生于世的荒谬处境:日日重复着同样的工作,在没有任何心灵依归和希望之下,宛如放逐于世。“没有明天,因为人终将一死。”最后,萨特提到的论点,与加缪在1955年为《异乡人》美国版所撰写的自序如出一辙:“加缪所欲描绘的异乡人,正是因为不愿接受社会游戏规则而引起公愤的无辜者之一。他就像生活在不属于自己的国度,对其他人而言他也是个异乡人。不过,这也是有些人会喜欢他的原因,像对他有所依恋的玛莉,恰是因为觉得‘他很奇特’;……至于我们自己,阅读本书的时候,因为对荒谬的感觉还不熟悉,只能徒劳地试着用习以为常的道德标准加以评断——他对我们而言也是个异乡人。”无疑地,《局外人》或《局内局外》相较于《异乡人》是更为直观的译名,但后者显然更值得玩味。在当时的法国文坛,出生于非洲的加缪某种程度上也像个“异乡人”,虽是题外话,可探讨之处依然颇多,跟作者的联结也较之《局外人》来得更为深厚些。
加缪无疑是个说故事的高手。书中的每个当下,都是现在。就算不去剖析背后的含义,单纯当成一个故事来阅读,《异乡人》也足够引人入胜:每个段落都有事件发生,环环相扣,绝无冷场。时隔近十年,重又翻开这本原文仅有短短五万余字的作品,我仍旧为其充满魔力的文字不由自主地吸引,也不断忆起当年越是为作者才华所倾倒,越是战战兢兢斟酌推敲的过程;尤其在问世超过半世纪的今天,《异乡人》的译文依然几乎无须任何注释辅助,便能直指人心深处,令我折服。
何其幸运,在众多译本中,我的《异乡人》能获得读者的青睐,希望珍藏此书的朋友都能感受到我对它的钟爱。唯有经典经得起一再反刍演绎,任时光推移,越显其价值。
——译者 张一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