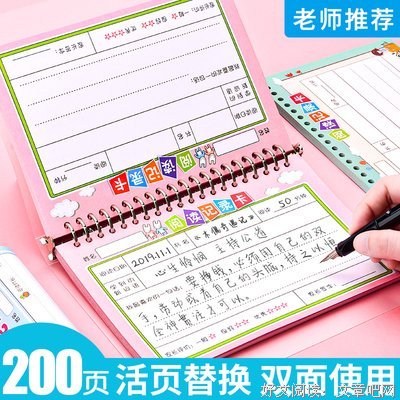
《悲欢的形体》是一本由冯至著作,雅众文化/新星出版社出版的平装图书,本书定价:45.00,页数:272,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我坦言我不会读诗。
●1950年代之后,诗风瞬变
●[2019年第35本书]在横躺的字句里寻找我的遗失,这无情的是非惹人徘徊。命运的青山暮色笼罩、心神的琴弦烟雨彷徨,原来我失掉了自己的幻想。一次两次,我仿佛没有悲剧,也没有希冀。
●冲着作者看的,冯至是中国现代诗的第一座高峰,这本书几乎囊括了其精华,更好地了解整体诗歌印象。
●冯至的十四行诗应该是最高了,受到了里尔克的影响,形式上像石头,但诗意如流水萦绕,这本难得封面流丽,价钱也不低,可惜的是诗人在新中国建立后的诗歌便不那么好看了,不管怎样,冯至的水平在中国是数一数二,也给未来的诗人做出了最好的示范
●北游自叙,泪啊。
●选读。冯至所受的旧诗影响,由于年代隔阂,个人难以感悟。抒写的感情也是被前人近乎写尽了的,并未在新诗形式上有所超越,也没有情感/体验上的惊奇,很局限。
●我们的生命在这一瞬间, 仿佛在第一次的拥抱里 过去的悲欢忽然在眼前 凝结成屹然不动的形体。 “一生常耻为身谋” 20年代,40年代,50年代,80年代
●那时……
《悲欢的形体》读后感(一):断片情字,清浊自知
假若,少字欲多情,假若,读来都看作空寂了然,那么长长悠悠的岁月,逢得便是顺遂,逢不得,变成了星空长河里闪烁无光的点缀。
天,翌日便升腾,化作风雨,化作朝阳,化作稀疏沙哑,近似人间烟火气,远则无往来。但,逐字逐句,埋了疾风,藏了冬霜。
读冯至的诗,值得人间相逢,困隙时分,阳光微微,晕开水渍,都是谦卑的心。
1.散文《一棵老树》 生死循环 时间的意义 人生哲学 生命的悲哀 移植后的水土不服
《一个逝去了的山村》
鼠曲草 “一个小生命怎样鄙弃了一切的浮夸,孑然一身担当着一个大宇宙”
3. 《伍子胥》
仇恨 冯至的“故事新编” 社会现状 宇宙(宏大的世界观) 物我合一的境界
新和旧 新生 命运 城父 林泽 you滨 江上 溧水 吴市
“独行潭底影,数息树边身。”
我们的生命在这一瞬间
仿佛在第一次的拥抱里
过去的悲欢离合忽然在眼前
凝结成佁然不动的形体
5.自然 草木灵性由物及人人物合一 净化
中国的奥德赛 “炼字”(贾岛)细腻
6.出逃 逃亡
7.未完结 第二次的出逃就是 “死”
8.白/欧/ 恰到好处 古代语调 (传统)凝练典雅 含蓄
9.传统美学风格(20年代) 朦胧 悲哀 但不痛苦
德国存在主义熏陶(40年代)中国的新诗
《悲欢的形体》读后感(三):断了又续的,是你的琴弦
我是从里尔克那里认识冯至的。《给青年诗人的十封信》很受过几阵追捧,冯至的译笔珠玉在前,此外的译本都有些如同枯草。又说他是“最为杰出的抒情诗人”,冯至的十四行诗、四十年代的创作,不仅是他个人的高峰,也是现代诗歌史上的里程碑。被赞誉多了的,不容易读出惊喜来,已有很多人将它们解读得很好,比如黄灿然老师的导读,你会发现这些第一眼并不刺激的诗块,要怎样的反复地念,咬下每一个字词每一个标点甚至每一个跳行与空格——像正在写这首诗那样去读一首诗,才能识辩出更深广的妙处来。
相比于艺术上和思想上已然成熟的诗作,冯至在二十年代初出茅庐的两个集子,更容易叫人惊讶,恰恰因为它的——“粗糙”。却可爱亲切,有青年人特有的多情。那个时候一开始作诗,他便留心格式与音律:通常有小巧而匀称的句式,全篇押韵。这个特点他一直保留,后来去德国留学,受了里尔克与歌德艺术的影响,在体式与语言风格上,锤炼出如雕塑一般的诗歌质感,也是建立在从前实践的基础上。
透过许多的少年诗,识出初学者的笔墨。小诗《暮雨》中,黄昏、雨声、暮雨,落花飞絮将诗境一点一滴隔绝出来,闲寂的情调更趋近于宋词。这首显然是从更长的《初春暮雨》删改而来,他说:
我总是这样朦胧; 今春的落花飘絮, 已经把我的心儿埋住。朦胧与纤细,叫我没想到的是,年少的冯至也曾这般的柔婉,诸多的寂寞哀愁化作想象。徐志摩的情“浓得化不开”,踏着舞步;冯至没有那般公子气,看得出来他叫心事牵绊着,他的感情在暗自地追寻,唱着歌谣:
我流过一座森林, 柔波便荡荡地 把那些碧绿的叶影儿 裁剪成你的衣裳。我流过一片花丛, 柔波便粼粼地 把那些彩色的花影儿 编织成你的花冠。……(《我是一条小河》)丁香花,你是什么时候开放的? 莫非是我前日为了她 为她哭泣的时候?海棠的花蕾,你是什么时候生长的? 莫非是我为了她的憧影, 敛去了愁容的时候?燕子,你是什么时候来到的? 莫非是我昨夜相思, 相思正浓的时候?……(《春的歌》)不论“相思”是虚是实,在迫近之后最终似乎总要拉开距离:“我的诗也没有悦耳的声音,/读起来,舌根都会感到生涩”(《无花果》)“为她唱些‘春的歌’,/无奈已是暮春时候”(《春的歌》)。也许这一切的想象都开不出花,有顾影自怜的意味,但经过内心与笔尖的河流反复地歌咏,所结的“无花果”一天天味浓、成熟,成为日后珍贵的果实。
可以看出冯至诗歌写作初期,便自觉塑造了“歌者”的形象,并以歌谣的形式来组织诗体抒情与叙事的展开。比较直接的如《春的歌》《在郊原》《风夜》等中重章叠句、排比、顶真,很容易让人想到《诗三百》,来自于民间歌谣的国风;还有《吹箫人的故事》《蚕马》这样的长篇,设计了一个“唱诗者”来讲述民间故事,也让人想到古希腊史诗歌手荷马。歌谣般的旋律,随着诗句和篇章一起流动,冯至的诗,固然也是浪漫的,但也如同他在格律上的约束一般,他克制了那种肆意煽情的抒情方式。到了二十年代后期《北游及其他》一集中,已经可以看到冯至在意象上的洗练,做了更多长句的尝试,歌咏的调子较从前更舒展从容了。在抒情中加入静默的沉思,“我要静静地静静地思量,/像那深潭里的冷水一样。”沉思的气质阔大了他的歌,情感和语言也超越了前一时期的单薄,血性、凛冽、厚重的各个面向开始展现,使其的情感复杂得多。
我寻求着血的食物, 疯狂地在野地里奔驰。 胃的饥饿、血的缺乏、眼的渴望, 使一切的景色在我的面前迷离。……我跑入森林里迷失了出路, 我心中是如此猜疑: 纵使找不到一件血的食物,怎么 也没有一支箭把我当做血的食物射来?(《饥兽》)冯至自述自己创作的历程,二十年代、四十年代、五十年代、八十年代,一阶段跳过一阶段,一程并不连着一程,就像他早早地写过那样:“续了又断的/是我的琴弦”。
《悲欢的形体》读后感(四):冯至与里尔克的相遇
在冯至最好的诗歌中流淌着德语文学的血液,对他产生最大影响的人应该是里尔克(歌德也有重要影响,不像里尔克如此明显)。
1930年底,冯至赴德国留学,主修文学,兼修哲学、美术史。四五年前,冯至已阅读过一些里尔克的作品,比如《旗手克里斯托弗·里尔克的生死曲》,印象非常深刻,限于条件无法进一步阅读。1931年,手头并不宽绰的冯至下了决心,用四十马克买来《里尔克全集》,随后认真翻译了《给青年诗人的十封信》。次年,他又翻译了里尔克的一些短诗,摘译了《马尔特·劳利兹·布里格随笔》。
这部随笔小说是一位性情敏感的丹麦青年诗人的回忆与内心独白。冯至会摘译其中两部分,很可能是因为他在其中读出了自己的身影。“我在这儿坐在我的小屋里,我,布里格,已经是二十八岁了,没有人知道我这个人。我坐在这里,我是虚无。然而这个虚无开始想了,在五层楼上,一个灰色的巴黎的下午……”当时,冯至同是28岁,同是远离故土,同是苦思着自己的文学抱负。里尔克塑造马尔特自我关照,冯至从马尔特身上又看到自己,可谓心有戚戚。
摘译的《布里格随笔》最著名的是关于“诗是经验”的一段阐述:“为了一首诗我们必须观看许多城市,观看人和物,我们必须认识动物,我们必须去感觉鸟怎样飞翔,知道小小的花朵在早晨开放时的姿态……我们有回忆,也还不够。如果回忆很多,我们必须能够忘记,我们要有大的忍耐力等着它们再来,因为只是回忆还不算数。等到它们成为我们身内的血、我们的目光和姿态,无名地和我们自己再也不能区分,那才能得以实现,在一个很稀有的时刻有一行诗的第一个字在它们的中心形成,脱颖而出。”
这段诗论更新了冯至对诗的认知,以往他觉得诗更多是情感的抒发。里尔克接触罗丹之后所信奉的“艺术创作本质上是辛勤劳作”的观念也让冯至对写作的态度变得更加隐忍克制。在三十年代,冯至几乎没有写诗,经常阅读里尔克的作品。除了热爱之外,里尔克一些作品的晦涩也延宕了冯至对他的阅读,比如《杜伊诺哀歌》和《致奥尔弗斯的十四行》绝非随便读读就能真正理解的作品。在这漫长的苦读中,冯至并没有因自己创作不足而惋惜,他曾这么回忆:“那时每逢我下了一番功夫,读懂了几首里尔克的诗,都好像有一个新的发现,所感到的欢悦,远远超过自己写出一首自以为满意的诗。”
除了文学观念上的变化,里尔克的文学尝试也直接影响了冯至的创作。1941年,冯至在西南联大任教,十年几乎没有动笔,长年积累的经验让他有了写诗的冲动,然而冯至在二十年代习惯的形式不适应他所要表达的内容。他想到十四行诗,但又担心十四行严格的音韵会带来较大的束缚,里尔克的《致奥尔弗斯的十四行》就起到了榜样作用,格律可以根据诗的内容作出调整。
冯至的十四行诗每一首都句式整饬,而首与首之间长短不一,没有统一的音节要求。在韵式上,这些诗作也相对自由。一些诗节采用了交叉韵,另一些诗节中则采用环抱韵,冯至在这些作品中耐心地拿捏着气息的起落,有时沉敛,有时轻快,使得诗作保留了足够丰富的音乐性。
在形式之外,里尔克某些作品的气息也萦绕在冯至的十四行里。如果细细品味,不难察觉《我们准备着》、《什么能从我们身上脱落》与布里格那段“诗是经验”的论述在气质上非常相似。而冯至的这些十四行中所潜藏的个人意识、对时空的感知、对世间人事的洞察,与《致奥尔弗斯的十四行》也有诸多相通之处。冯至于1987年在联邦德国“文艺艺术奖”颁奖仪式上致谢,提及了写作十四行的一些细节:“有时在写作的过程中,忽然想起从前人书里读到过的一句话,正与我当时的思想契合,于是就把那句话略加改造,嵌入自己的诗里。”他将里尔克惊闻凡尔哈伦与罗丹去世时写下的话,改写进了《蔡元培》一诗,歌德书信里的话改写进《深夜又是深山》。冯至对此的态度非常平和:“我这么写,觉得很自然,像宋代的词人常翻新唐人的诗句填在自己的词里那样,完全是由于内心的同感,不是模仿,也不是抄袭。”
更有趣的是,翻阅这本诗集,我们能看到《十四行集》的出现令人惊奇。这二十七首诗是在一年内写就的,前后的作品与之没有多少发展或延续的痕迹。这组杰作仿佛从天而降,是缪斯的一次恩赐,与里尔克在穆佐古堡写作《杜伊诺哀歌》、《致奥尔弗斯的十四行》的方式有着惊人的类似,仿佛诗人半生的苦苦求索,在某个特殊的时段终于得到回报。然而,这也可能是残忍的,因为在这些杰作完成之后,诗人不得不忍受余生的文思枯竭。冯至在创作完《十四行集》生了大病,从此之后他的写作离这组诗歌变得遥远。
如此梳理冯至与里尔克的关系,并不是为了贬低其在诗歌创作中的成就。冯至在十四行上的努力,为汉语诗歌提供了罕见而珍贵的沉思式书写,他在这组诗中进行的音乐性尝试也为汉语新诗展现了重要的向度,而且这种音乐性与诗作中弥漫的思索、抒情融为一体,极具典范意义。
我们可以将文学史看做作家们互相角力、搏斗的历史现场,我们也可以将之视为作家们互相启发、隐秘继承的精神流变史。冯至对此说过的一段话,用来形容他与那些影响他的诗人们的关系非常合适:“我不迷信,我却相信人世上、尤其在文艺方面常常存在着一种因缘。这因缘并不神秘,它可能是必然与偶然的巧妙遇合。”
《悲欢的形体》读后感(五):0221
这本书是和根梓去南京时在先锋书店买的书,由于实习兼职和找工作一直也没有时间翻阅,趁着疫情偷闲,读着小诗,记录下以下几首,触动心灵,还有一些片段。
自己不会写诗也不会读诗,只是浏览文字,偶尔会有碰撞,但是我相信多看看就会好些。
别友
好一个悲壮的/悲壮的别离呀/满城的急风骤雨/都聚在车站/车站的送别人/送别人的心头了
雄浑的风雨声中/哪容人轻轻地/说些委婉的别语/朋友,你自望东/我自望西/莫回顾,从此小别了
赞颂狂风暴雨/因为狂风暴雨后/才有这般清凉的世界/我失掉了什么/啊,车轮轧轧的声音/重唤起我缠绵的情绪
梦一般寂静地过去了/心里没有悲伤/眼中没有情泪/朋友,你仔细的餐/餐这比什么都甜/比一切的苦味都美味吧!
(思念刚离别的朋友们,由于爸爸得病的关系,也没有好好告别,未来期望大家加油!)
怀友人Y.H
当燕子归来的黄昏/我一人静静悄悄/在你旧居的窗前/梦游一般地走到/寂寂静静/我轻轻地叫着你的名儿/窗内仿佛有人答应/我傍着窗儿痴等/但是窗儿呀总是不开/一直等到了冷日凄清/朋友啊,你那时在哪里徘徊?
那夜风雨后/正像是我们去年的一天/满院嗅着柳芽看/满地踏着残花瓣/寂寂静静/我轻轻地叫着你的名儿/云内仿佛有人答应/我靠着树干痴等/但是阴云呀总不散开/一直等到了夜阑更深/朋友啊,你那时在哪里徘徊?
我像是古代的牧童/失掉了他的绵羊/我像是古代的诗人/失掉了他的幻想/寂寂静静/我轻轻地叫着你的名儿/远方总有人答应/我望着凄艳的夕阳/我望着幽沉的星海/望得我心滞神伤/朋友啊,你那时在哪里徘徊?
桥
最美的诗“你同她的隔离是海一样的宽广。”
“纵使是海一样宽广,我也要日夜搬运着灰色的砖泥,在海上筑建起一座桥梁。”
“百万年恐怕这座桥也不能筑起。”
“但我愿在几十年内搬运不停,我不能空空地怅望着彼岸的色彩,度过这样长、这样长久的一生。”
原野的哭声
我时常看见在原野里/一个村童,或一个农妇/向着无语的晴空啼哭/是为了一个惩罚,可是/为了一个玩具的毁弃?/是为了丈夫的死亡,可是/为了儿子的重创?/啼哭的那样没有停息/像整个生命都嵌在一个柜子里/在框子外没有人生/也没有世界/我觉得他们好像从古来/就一任眼泪不住地流/为了一个绝望的宇宙
我们有时度过一个亲密的夜
我们有时度过一个亲密的夜 / 在一间生疏的房里,它白昼时 / 是什么模样,我们都无从认识 / 更不必说它的过去未来。原野— / 一望无际地在我们窗外展开 / 我们只依稀记得在黄昏时 / 来的道路,便算是对它的认识 / 明天走后,我们也不再回来 / 闭上眼吧!让那些亲密的夜 / 和生疏的地方织在我们心里:/ 我们的生命像那窗外的原野 / 我们在朦胧的原野上认出来 / 一棵树、一闪湖光、它一望无际 / 藏着忘却的过去、隐约的将来。
(原来以前和现在的爱情都一个模样,大家都贪恋***,认识的朋友都是:“在吗?看看?看看下面?挺好看的我也不差出来见见吗?约吗?” 而我贪恋的,是心灵上的交际,在深夜陪我聊生活,批评我教育我该怎么解决问题,可以认真看我写的东西挺我分享的歌,也可以给我分享他的心得,而不是单一肉体的结合。我想象海绵一样汲取你的营养,成长变成优秀的人和你在一起,而不是你所想的***)
片段
把过去的事想了又想/把心脉的跳动听了又听/一切的情/一切的爱/都像风吹江水,来去无踪/
生和死,是同样的神秘/一个秘密的环把我们套在一起/我在这秘密的环中/解也解不开/跑也跑不出去
你躲在这无人过问的、世界的一角/发出来这无人过问的、可怜的声息
不要总是呆呆地望着远方/不要只是呆呆地望着远方空想
金钱驱使着神鬼/神鬼庇护着金钱/它们说:“我们从来不懂,什么是理想,什么事尊严。”
我这一生都像是在“否定”里生活 / 纵使否定的否定里也有肯定 / 到底应该肯定什么,否定什么?/ 进入了九十年代,要有些清醒 / 才明白“人生最难得的是”自知之明”
像作者一样思考,二十二年中可真的有过真正的欢欣?可经历一次深沉的苦闷?可曾有一刻把人生认定?可曾真正读过一本书?可真正地望过一次日月星辰?我可曾真正地认识自己是一个怎么样的人?慢慢想,仔细想,不曾有过,有过,不曾有过,不曾有过,有过日落,不曾有过,零落的记忆不曾记得自己有过欢欣时刻,梦里也没有,每一本书的记忆点过了几周之后几乎没有,只是一味的记录,像现在。我只知道此刻自己想干什么,却不知道为什么和该怎么做。
再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