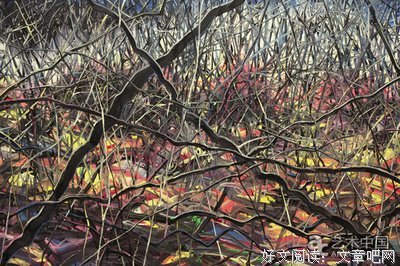
《关于他人的痛苦(全布面精装)》是一本由[美] 苏珊·桑塔格著作,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的全布面精装图书,本书定价:48,页数:152,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我们与他们。想象力与同情。艺术(影像、技巧)与现实(痛苦、同一平面)……
●第一本苏珊桑塔格的书。书写的很好,就是很薄的一本书标价48啊 才一百多页啊 字的间距还有点宽。上海译文快成抢钱出版社了
●身份,是什么人将照片用于何种用途,受害者的身份;暴力,“奇观社会”;柏拉图《理想国》中一直在发展一种关于精神功能的三重理论,理性、愤怒或义愤、食欲或欲望(弗洛伊德超我、本我、自我);残缺尸体的吸引力;所谓集体记忆并非纪念,而是规定;怀念是一种道德行为,本身有其道德价值,深植于人类天性;历史上对战争的看法,与现在不同,达·芬奇,艺术家的目光必须不带怜悯,图像必须足够震撼,而在这可怕中含有一种具有挑战性的美;拍照即是定框,定框即是排除;观看VS思考;眼睛与大脑连结,大脑与神经系统连结,系统通过那个过去的记忆和现在的感觉瞬间将信息传递出去吧,因此照片既是对现实某个时刻的忠实复刻,也是对现实的解释;灾难与人的距离,灾难发生在异国。
●镶满镜子的数码大堂里,我们每个人都在这场影像的战争中被共情腐蚀。
●影像对于痛苦的传播,放大,美化。政府对于影像的选择性公开,目的性得强化“集体记忆”。“我们”是否能够通过它真实感受到远距离的痛苦,以及移动时代爆炸般的新闻所带给人的感受力丧失,寻求刺激。影像的传播触及更加庞大的产业,国家利益。个人的异变只是一个反应链的中间形态,作为最鲜明的动向被观察和探寻,而它某时却是最重要的。影像给大众带来的感受与娱乐性双重影响,只能说不知道人心中的良知到底能走到多远。
●每回读桑塔格都感觉那么亲切
●面对(战争照片所透露出的)他人的痛苦,不管是表现出漠然、同情还是性奋,最主要的还是思考。桑塔格是会引导你思考的作家。
●对论摄影提出的观点进行深一步地论述,摄影该如何实现反战,以及摄影是在什么情况下能够真实地反映战争。
《关于他人的痛苦(全布面精装)》读后感(一):痛苦与快感
像解一道谜题,一步一步,得出关于媒体的关键作用,关于拍摄苦难与道德的争论,关于人性中的痛苦与快感,关于当今社会信息的迅捷与麻木的作用。
在这里,我有个小小的思索,关于人群的聚集和控制,关于信仰。社会本质上需要的稳定,自然不能够让他人利用平台的聚集以及信息联通做出违法的事情。所以在景观社会与消费社会诞生的同时,抖音、短视频的兴起,实际上充当了一种个人化的爱好,并达成书中所述的"麻木"。这里的"麻木"不是贬义词,恰恰是现今社会所需要的"稳定"基础,如果换一个词,应当是"习惯"。
在书的末尾,对美国的阐述入木三分,而其过去的所作所为,也同样试用于现今世界上,由美国插手的一切。
于是,地球上其他的国家,不自觉的成为了《楚门的世界》里的楚门。要成为美国眼光里的奇景,就要历经战火,让他国的痛苦成为其快感的来源。这是一件残忍且正在发生的事情,而前几天才有新闻说,阿富汗在打一场持久战,现在已经不需要结果了,他们只是在享受一种获取快感的过程。
《关于他人的痛苦(全布面精装)》读后感(二):球球书摘——关于他人的痛苦
照片拥有统合两种相反特色的优点。照片的客观可信性是固有的。然而,照片永远有必不可少的观点。它们是真实的记录——与不管多么中立的文字记述不同,它们无可辩驳——因为那是机器做的记录。它们是真实的目击者,因为有人把它们拍下来。 伍尔夫宣称,照片“不是争论,它们就是事实直接对眼睛所说的未经加工的声明”。摄影师的意图并不能决定照片的意义,照片将有自己的命运,这命运将由利用它的各种群体的千奇百怪的念头和效忠思想来决定。--------照片具有的独立性,但与此同时,在进入“世界”,照片的意义和功能同时也具备了“从属”属性。
拍照即是定框,定框即是排除照片没有伦理,但摄像师有。而摄像师的伦理观,则彻底的展现在他的摄制对象以及摄制范围。
照片的真实性问题: “我们要求摄影师是爱与死的偷窥者,要求被拍摄者未意识到相机的存在——乘其不备” ------“真实性”在新闻、纪实类摄影中具有最高地位。 P49-51."<1945年二月二十三日硫磺岛升国旗><俄国士兵在德国国会楼顶升旗><一九四零年德国闪电战伦敦-废墟读书>
-------照片的真实性,是否为策划,是直到越南战争时期才被充分确定,而这一确定,对于这些照片的道德权威来说,是至关重要的 ------- 真实性背后蕴含的道德力量(真假之别),促使部分新闻从业者宁愿舍弃“策划”照片可能带有的警醒作用,而服膺于更高的道德权威。
捕捉一次实际发生并为它做永久的防腐,是只有照相机才能做到的52。
现代人最重要的期望和道德感情,是深信战争是畸形的,尽管可能难以阻止;和平才是常态,尽管可能难以获取。怜悯可引起道德判断,如果怜悯像亚里士多德所说的那样,被我们当成对蒙受不幸者的愧疚之情的话。但怜悯绝非灾难性不幸事件中的恐惧的自然伴生物,而是似乎被恐惧稀释(分散)了,恐惧(害怕、惊骇)则往往淹没怜悯。达·芬奇的意思是,艺术家的目光必须不带怜悯。图像必须够震慑,而在这可怕之中含有一种具有挑战性的美。---p66-67改造是艺术的本质,但是摄影作为灾难和应受谴责事件的见证,如果它看上去像“美学”的,也即像艺术,就会备受抨击。摄影的双重力量——提供纪录和创造视觉艺术作品——在摄影师应该或不应该做什么的问题上,已制造了一些引人注目的夸张。-p67《关于他人的痛苦(全布面精装)》读后感(三):在“惊呆”与“麻木”之外
关于战争、暴力与痛苦的影像能够唤起我们对苦难的的抵抗吗?一直以来,现代社会将这种人道主义式的期许,不假思索地安置在新闻影像上。这是一种技术性的期待——人们期望作为技术的摄影,能够用大众化的、本雅明式“机械复制”的图像,将过去非经验的事实经验化(“成为发生在另一个国家的灾难的旁观者,是一种典型的现代经验”),以此唤醒人道主义意义上的普遍同情。《关于他人的痛苦》一书的论述起点,似乎正是这样一种人道主义式的期许——无论是伍尔夫的《三几尼》还是弗里德里希的《反战之战》,都是“用逼真的画面呈现恐怖”,以此“使大多数人明白战争的疯狂和恐怖”。但对于桑塔格而言,批判此类“意义阐释”式的艺术理想已经是“老生常谈”了,《关于他人的痛苦》,与其说是她对阐释的又一次批评,不如说是对她自己成熟思想的再反思——在“惊呆”与 “麻木”之外,作为形式的摄影在苦难的话题上,在现代性的语境下,能够剩下怎样的话语。
一、善变的阐释与脆弱的同情
伍尔夫们的想象中的照片,沾染着理想主义的一厢情愿。而事实是,“如果与对象之间有了距离,照片所说的,便可做多个角度解读”。摄影对于再现场景的权威性,并不能传递为符号解读的权威性。人们对于远方的痛苦,呈现着罗兰·巴特式的“神话”与“作者已死”的理解状态——“摄影师的意图并不能决定照片的意义,照片将有自己的命运”。
“我们确实有些相同的反应”,伍尔夫在描述观看战争影像的体验时如是说。恶心、惊诧、怜悯……一切人们可以想到负面情绪,构成了“共识的幻觉”的所有证据。然而,这一切都是基于那些被“伍尔夫们”认为是理所应当的阐释基础上的。桑塔格指出了这种理想的困境——寄希望于让照片制造共同体的人们,不会去质疑作为共同体的“我们”究竟是谁。“我们”不是理所当然的,在任何战争面前,被首先在意的,不是有何苦难与苦难几何,而是“何人被杀与被何人所杀”。在善变的阐释面前,人道主义者的影像以及建立在它们之上的同情,多么容易滑向理想的对立面。
现代社会,对痛苦阐释的对立面当然不仅有居心叵测的煽动。在桑塔格的话语中,对痛苦的展览,与其说是单纯的展示,毋宁说是一种“合谋”。作为大多数的人们,在观看、被告知、被接纳入群体的悲愤与哀叹后,能够剩下什么呢——我们似乎难以找到“重访”的径路,难以控诉与责备。痛苦与扭曲的影像,在现代性与大众文化语境下,难以成为可靠的符号——它可以是伴随着激情与欲望的娱乐,也可以成为个体身份的麻醉剂——观看者与暴露在视野中的苦难,是一种虚假的移情,我们劝说着自己,仿佛已经感受到了受难者的切身之痛,因为我们在感受着、怜悯着,所以我们作为远方的观看者,绝无可能是施害的同谋,而是高尚的清白者。
同情,在一切流变面前,是最脆弱的情感。
二、作为意义的痛苦与作为形式的痛苦
图像,仿佛与生俱来的承载着一些我们不愿面对的现实。德布雷在他的《图像的生与死》中提到,“图像的诞生有一部分是与死亡联系在一起的,古老的图像之所以从墓冢里冒出来,正是为了拒绝虚无、延续生命”。漫长的历史中,我们总试图在记载着痛苦、挣扎和死亡的图像中寻求一些意义。
保罗·克罗赛在《绘画的暴力》中指出,有一种暴力艺术是具有象征意义的作品。这种作品最显著的特征,是它拥有符号之外的指向性,也就是其“意义”所在。这种指向性可以是叙事功能的——艺术对暴力与痛苦进行再现,唤起观看者的某种情感,以实现某种建构;它也可以是表达功能的——作品通过对暴力的刻画,隐晦性地传递某种价值取向,以形成某种现实性导向;它在更高程度上可以是美学功能的,但美学追求之下往往也具备前两者的意涵。
通过战争的影像反抗战争,通过战争的痛苦反对战争,实际上就是挖掘战争摄影的意义指向。这种挖掘的手段是对照片的阐释,所挖掘的意义是作为模糊不清的类的人们的同情和对战争的畏惧。事实上,在这种语境下,摄影师们的35毫米胶片,与《马拉之死》、《格尔尼卡》并无二致。然而,摄影相比于绘画,永远离现场更近——这意味着它的真实和权威,也意味着摄影师对于它的意义的无能。
德勒兹说,作为意义的暴力是一种“具象”,而“具象”即是一种“俗套”。我想苏珊·桑塔格所拒斥的,同样不是任何一种具体的阐释,而是试图在摄影中寻求特定意义的行为。在她看来,作为意义的痛苦并不是那么掷地有声——“这类影像无非是提醒我们去注意、去反省、去了解、去检视掌权者就巨大灾难提供的辩解是否合理”。我们被影像唤醒记忆,去质疑和评判,但记忆驱赶不走战争,“和平就是为了忘却”。
桑塔格说过,“(艺术)它本身就是某物。一件艺术作品就是世界中的一个物,而不只是关于世界的一个文本或评论”。她也许只想将关于他人痛苦的影像,看做形式本身。在她看来,试图站在和平的人道主义的视角去追求战争摄影的意义,就像偏要去读懂卡夫卡的批判一样,是“智力对于艺术的报复”。
当影像被解读的意义本身无意义,它仅剩下形式。
三、在“惊呆”与“麻木”之外
桑塔格在她更早的著作《论摄影》中有一句经典的论述,“影像使人惊呆;影像使人麻木”。彼时喊着“照片创造了多少同情,也就使多少同情萎缩”的桑塔格,正站在批判现代性的立场上反思着摄影意义的衰变。彼时,是现代性操控着摄影的表达;此时,摄影已经纳入了现代性本身——“不会有什么‘影像生态学’。不会有什么‘守护委员会’出面来实施恐怖配额”。
我们很难说桑塔格比从前变得更加悲观,她只是从对摄影的意义的思考,转向了对摄影艺术,尤其是直面苦难的摄影艺术形式本身的思考。她一以贯之地反对阐释、反对被塑造的意义。《关于他人的痛苦》,表明了桑塔格对自己的再反思,现代性仍然汹涌澎湃,而思考却依旧杯水车薪。
我不愿也无法以线性的、体系化的方式去评论《关于他人的痛苦》,那样只会陷入桑塔格自己所厌恶的“深度阐释”的漩涡之中,仅以以上文字作为对这本札记的一些感受。
《关于他人的痛苦(全布面精装)》读后感(四):新闻摄影——述说远方的故事
把远方的故事定格,留住悲痛,也呼唤共情
2015年叙利亚3岁难民“沉睡”海滩的一张照片,一下子把欧洲的难民危机带到世界人民眼前,英国、奥地利、德国、加拿大、阿根廷等多国相继表示将允许更多难民入境;1993年《饥饿的苏丹》把内战中苏丹的苦难转播给全世界,引起各国政府的广泛关注。有人把这两张照片放在一起,配上文字
Still the same? Still the same遇难的叙利亚小男孩儿饥饿的苏丹相同吗?无论从相片的主人公的遭遇还是相片想表达的意图来说都很相似,但这些都无法消解这两张照片的意义。战争带来的苦难、悲痛往往有着震撼人心的力量,而更为可贵的是在看到他人的悲痛时观众心中的共情和悲悯。摄影记者相信这样一颗悲悯之心,并愿意为之去往第一现场,把这些故事带到人们的眼前。这也是我所理解的新闻摄影的内涵,述说远方的故事,或者更聚焦一点,是述说远方的苦难。
苏珊·桑塔格的《关于他人的痛苦》一书的主题是战争,讲述的是远方的苦难如何以照片的形式被记录、被解读、被使用。在书中桑塔格谈到很多,例如照片是否能反映真实,因为它们是在摄影家的意图下产生、被利用它的各种群体赋予文字说明和意义解读;照片记录的苦痛记忆能否产生预期的效果,因为在一些人不过是以猎奇的心态冷观,或者当过多的苦难影像呈现在人们眼前,迟早会令人厌倦和麻木。因此,也有译本将“regarding the pain of others”译为“旁观他人的痛苦”、“审视他人的痛苦”,大多数情况下人们被苦难刺痛,然后选择闭上眼,或者发出一声哀叹,继续一头扎入生活之中。眼前的苦痛总是比远方的苦痛更显著。尽管如此,桑塔格提出合理、有效的反思,但同样提供了对这些反思的质疑。
首先,影像打破了时空的距离,让共情更有可能发生。我们每个人都是一个原子,哪怕知道我们每眨一次眼睛就有1.8个生命消逝、4个新生命诞生,也并不会产生任何的波澜。可当这些数字背后有了真实的影像、鲜活的故事时,我们却很难不为之所动。
相机是历史的眼睛 ——桑塔格当快门按下的那一刻,被定格的那一瞬间就成为了人们记忆的一部分。摄影师的镜头对准的地方,对于人们关注什么、注意到哪些危机和灾难、如何去评判都产生了重要的影响。这时,新闻摄影是带有使命感的。
让人们扩大意识,知道我们与别人共享的世界上存在着人性邪恶造成的无穷苦难,这本身似乎就是一种善如果说当年如芬顿这样的官方委派记者在克里米亚战场上拍摄的照片还只是为了营造一些战争的正面形象的话,更多身份、立场的摄影家到达战争前线拍摄促成了该状况的改变。到了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大量关于越南战场的照片越发变成残酷现实的真实记录。对于战争苦难的反映引发人们的关注和反思,最终掀起反战的浪潮,加速战争的结束。摄影爱好者刘拓去了150个世界遗产,其中包括位于阿富汗的贾姆宣礼塔、伊拉克的伊什塔尔门、泰西封的薄砖拱券这样一些受到军事管制的遗址,说不定哪一天这些遗址就从世界上永远地消失了。而照片借助大众媒体呈现在世人眼前,作为留给未来的礼物。
当我们认识到照片可能隐藏着虚假的风险或者被曲解的可能性时,我们对待它的态度也更为谨慎。第58届荷赛的当代热点类组照一等奖、Giovanni Troilo拍摄的《欧洲黑暗之心》因造假被取消了获奖资格,在“后真相”时代,揭穿一组照片、获得真相是相对简单的。这组照片因违反真实性和摄影家的职业道德信任原则而被取消了荣誉,但照片映射出的比利时南部这个衰退的城市沙勒罗伊却进入了人们的视野,工业制造业驱动乏力、工厂关门、失业率上升、犯罪率上升等现实问题让这个城市陷入衰颓。照片的使用者带有私利的考量和各种各样的目的性,但照片本身仍是部分真相的反映。正如李普曼所说:“新闻首先不是社会状况的一面镜子,而是一种突出的事实的报道。”这部分被照亮的黑暗对于社会的发展来说仍有着重要意义。
《欧洲黑暗之心》组图之一而即使是提出“照片创造了多少同情,也就使多少同情萎缩”的桑塔格,也反问自己说,是这样吗?并没有证据表明照片的影像在不断递减,观奇文化在消解照片的道德力量。1957年第一届世界新闻摄影比赛举办以来,从来没有减弱对战灾难的持续关注。第59届荷赛的突发新闻类单幅一等奖颁给了Warren Richardson的《新生的希望》,一名男子正将怀中的婴儿送过匈牙利和塞尔维亚边境阻挡难民的铁丝网,照片的质量并不高,却令目之者为其动容。这些照片提醒着我们,尽管世界的大部分地区在和平之中度过了几十年,但战争从未在这个世界上消失。就像我们所认同的荷赛的意义——
永远要对人类自身的困境发声《新生的希望》但是我又不愿仅仅将摄影局限在苦难之中,而更愿意称之为述说远方的故事。其最重要的价值在于打破隔膜,消解距离。摄影记者的镜头会记录下1971年联合国大会上乔冠华的仰天大笑,也会走进农村拍下乡村小学中苏明娟对读书的渴望;会捕捉出国参赛的运动员们无数汗水换来的高光时刻,也会跟随在外打工的游子回到故乡……无数的影像汇聚起来,勾勒出我们对时代的认知与记忆,记录着时代的改变也改变着时代。
《关于他人的痛苦(全布面精装)》读后感(五):解码战争影像——关于《关于他人的痛苦》
## 编码和解码
与诉诸文字的信息记录形式相同,影像,或者本书更加着重探讨的“照片”,同样可以被视为一种语义混沌的“符码”。生产者,也就是照片的摄影者通过编码,将影像转化为一种开放的话语系统,引入大众视野,再由其受众进行解码,形成新的意见和意义,完成意义的再生产。这就是斯图亚特·霍尔提出的编码解码理论。
以霍尔的理论为纲,或许我们能够更加条理清晰地认识这本《关于他人的痛苦》,或译《旁观他人的痛苦》以随笔的形式究竟探讨了哪些问题,以及是如何深入这些问题的背后,从多个角度剖析“看客”心理的。作者苏珊·桑塔格所做的,就是从受众的终端切入,围绕着战争影像的编码和解码,去反思在霍尔的理论中这个被一笔带过的过程混合着何种**复杂的情绪**,以及是如何在人类**心理、社会和历史**的多重影响之下被塑造而成的。
## 意义的再生产
桑塔格提出的第一个问题是,受众是谁。
在伍尔夫那里,受众是谁并不重要。她从女性主义出发,从战争的照片中却获得了和男性律师相同的情绪:厌恶,恐惧,反战。伍尔夫回到了“我们”,但正如桑塔格反复使用的“有教养”一词所暗示的那样,伍尔夫与那名无名律师所达成的统一,也不过是一小群远离战争,受过教育的和平主义者所达成的统一。
倘若所有的观看者都能从同样的符码中解读出同样的意义,那么显然一切的讨论都不再有存在的必要,霍尔的理论与传统的信息流通理论也并无区别。显然,事实并非如此。
询问受众是谁也就是在询问受众与照片、受众与照片所呈现的事件之间的关系。伍尔夫与律师远离战场,在他们眼里,照片中的人只是普遍意义上的人,照片记录的究竟是克里米亚战争还是巴以冲突无关紧要,死者是无辜的百姓还是作战的士兵无关紧要。但对于政府和军方,对于民族主义者,对于参战的士兵,对于这些离战争更近,与其更加密切相关的人群而言,照片中的人的身份,是如何死去的,是谁造成了伤亡和废墟才是首要问题。引起和平主义者反战情绪的照片另一方面也可以成为烈士的英雄勋章,甚至激发更大的仇恨和更深的冲突。
“To frame is to exclude.” 正如编码者不可能不带有立场地去记录(甚至刻意构造场景),解码者的身份和立场也在塑造着影像的意义。
值得注意的是,战争照片的传播并非是从摄影师(最初的编码者)直接指向受众(最终的解码者)的*(毕竟在桑塔格的时代,Social Media还未成为一个概念。那么或许值得当下的我们思考的是,Social Media在改变了传播样态的同时,又对“旁观痛苦”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照片往往要经过一个“中间商”的二次传播,才能从其生产者手中抵达最终消费信息的受众。这个“中间商”的扮演者可能是政府和军队宣传机关,可能是反战人士,可能是新闻媒体,也有可能是策展人。同样的,这些机构和个人也有着各自的立场,会借由添加Caption,乃至进行审查,压制某些特定的照片,来引导受众的解码。
正如桑塔格所说:
gt; Photographs had the advantage of uniting two contradictory features. Their credentials of objectivity were inbuilt. Yet they always had, necessarily, a point of view.
gt; The photographer's intention do not determine the meaning of the photograph, which will have its own career, blown by the whims and loyalties of the diverse communities that have use for it.
## 理解痛苦
如果说上述的观点放在传播学理论的框架内来看尚显不足为奇的话,我想桑塔格的深刻性更多地体现在她能够跳出战争摄影这一行业,从历史、艺术和人性的角度去理解痛苦与旁观痛苦者。
痛苦是西方艺术中的重要主题*(这是个非常有意思的话题)*,桑塔格认为,西方艺术中表现的痛苦,往往是“神祇和人类愤怒的产物”,这决定了在西方早期艺术呈现中,痛苦总是与宗教的神圣性挂钩。痛苦唤起的是一种超越性的经验,无论是殉道,神惩还是灾难,都在鼓励观看者的参与,换言之,这些艺术呈现的目的是肯定性的,背后总是隐藏着某种赞许和邀约。直至17世纪平民所遭受的无妄之灾成为艺术呈现的题材,这种“痛苦艺术”才被赋予了否定性的力量。
今天我们早已清楚地认识到,摄影兼具机械记录的客观性和摄影师取景构图处理的主观性。但或许在照相机刚诞生之初,在人们的意识中,照片的意义只在于记录而非艺术呈现。直至今日,我们依然会在潜意识里将照片默认为真实的图景,对于照片的真实性有一种不由自主的期待。因此,摄影一开始并不属于艺术的领域,战争摄影起初也并没有继承上文提及的这种艺术的批判力量。桑塔格回溯战争摄影的历史,也不无失望地发现战地记者留下的最初的影像也不过是政治宣传的产物。
摄影的艺术性得到普遍共识之后,回望并承认战争影像中的艺术性美感便令人隐隐不安,乃至陷入道德困境*(说到底,这也就是艺术与道德的问题)*。“欣赏”照片中的痛苦景象听起来似乎并不道德,但在西方传统“痛苦艺术”的浸淫下,我们依然会不由自主地想起神圣的宗教场景。这是几千年来文化传承留下的反射弧。
桑塔格甚至更加辛辣地指出,窥视痛苦有如窥视裸体,这种欲望与人类本我的冲动、与宗教的超越性追求交织在一起,成为了战争影像残酷性背后商业逻辑的出发点。正是因为痛苦场景对人性本能和文化迷因的刺激性,在信息泛滥的今天,媒体也更倾向于用这样的影像来留住**消费者**的视线。但信息泛滥本身损耗了信息的强度,受众愈加麻木冷漠,正如对任何现代性的批判指出的那样。
桑塔格纠正了自己曾经在《论摄影》中提出的部分观点。她并不过分谴责照片的艺术性,不谴责人性的本能和商业性,她甚至认为现代性的批判者们依然带有精英主义者的自大,妄图“根据那些对战争、对大规模不公正的恐怖完全缺乏直接经验的新闻消费者的心态,来概括一般人对他人苦难做出反应的能力”。再一次,桑塔格强调,受众个体的身份、立场和感受才是重要的,痛苦的影像再怎么泛滥,每个人仍旧会对与自身相关的痛苦感同身受,新闻消费者的麻木并非就意味着道德沦丧,因为一个心智和道德成熟的成年人不可能**“永远对堕落感到吃惊”**。因此,任何overgeneralized的批判都过于极端。*(我想很多读桑塔格的人都陷入了误区,依旧只停留在了桑塔格所说的“现代性批判者”的层面,跟随着他们去批判人性,批判商业性,没有更深一步地理解桑塔格本人的想法。而如果只停留在这个层面,我们就会很自然地以为桑塔格的论点也不过是陈词滥调)*
## 记忆、思考与共情
如果旁观者战争影像引起的任何**情绪**——愤怒,绝望,恐惧,好奇——都是正常的,都是可以理解的,都无可非议,那么在当下,战争影像究竟还存在着什么样的意义?
桑塔格只是朦朦胧胧地提到了“记忆”和“思考”。
照片近似于记忆的存储形式,比起文字,照片更容易使我们铭记于脑海。当历史性的影像一代代流传下来,这些影像便成为了一种民族记忆。问题是,集体性的记忆是一种建构性的记忆,而建构性的记忆可以被篡改,被压制,甚至是被规定,汇入意识形态。有时,为了更伟大的事业或和平,有些记忆必须被遗忘,有些仇恨必须得到谅解。我们很难评判记忆建构者行为究竟正确或者道德与否,但我们必须知道,正如照片的意义可以被生产、解构、扭曲和再生产,记忆也并不全然可靠。
于是我们所能做的只剩下思考。
gt; Such images cannot be more than an invitation to pay attention, to reflect, to learn, to examine the rationalizations for mass sufferings offered by established powers. Who caused what the picture shows? Who is responsible? Is it excusable? Was it inevitable? Is there some state of affairs which we have accepted up to now that ought to be changed?
总的来说,桑塔格的文章依然是批判而非建构的。读完桑塔格的作品只能让人感觉到一种深刻的无力感。战争影像并不能促进世界变得更好,旁观者的目光往往带着下流的窥私欲,旁观者永远不可能通过影像来理解战争的残酷性,照片并不可能替代体验,真正拉近我们与痛苦的距离。作为一个理性的个体*(尽管桑塔格嘲讽伍尔夫的狭隘,但值得玩味的是,桑塔格自身的批判和倡导也只是精英主义的)*,我们要警惕谎言,要避免麻木不仁,要保持思考,但思考并不引导我们走向任何一个方向。
大抵清醒总是痛苦的,于是我们用简简单单的同情掩盖无能,以显示我们尚有人性。
gt; So far as we feel sympathy, we feel we are not accomplices to what caused the suffering. Our sympathy proclaims our innocence as well as our impotence.
我无来由地想起《仿生人会梦见电子羊吗?》里面的默赛主义(Mercerism)。也许在一切希望毁灭之际,唯有同情和共情,才能证明人之为人。
题外:读完桑塔格之后感觉不整理一下内容和想法就和白读了一样,毕竟原文观点、例证和驳论像是打散了的生鸡蛋一样黏糊糊的一团。写的过程中又有了新的思考,所以霍尔那套东西只能算个引子,写到一半就扔了。总算是可以说自己没有白读白写。好久不写review,真的是手生了。
另,本文用Markdown格式书写,没有进行文本转换。强烈希望豆瓣编辑器可以加入Markdown功能。我真的找不到一个好用的编辑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