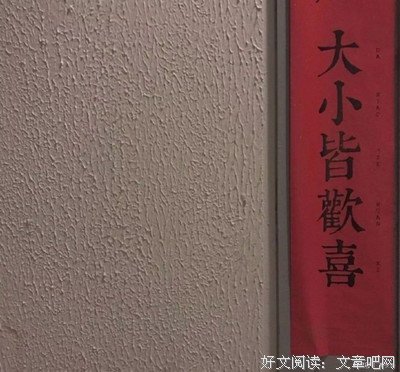
《倾诉》是一本由[爱尔兰]伊芙琳·康伦著作,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平装图书,本书定价:39.00元,页数:213,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生活的残酷是你无法回避,你不是过客,你是戏中人。在这本书中你遇到的是一群失落的人,在渴望亲情中跋涉,在寻找自我中迷茫,孤单,游离于社会之外。需要被倾听,渴盼被温暖拥抱。一群小人物,就在你我之间。笔调有点忧伤,文字侵染忧郁。读起来略沉重,却无比真实。
●短篇小说集。小说大多采用倾诉的口吻铺展开来,这点倒正如集子标题(虽然只是取其中一篇的题目,但越读越觉得恰如其分)。文字有条不紊地诉说着生活的故事,人生的醒悟,讽刺的现实。书中的大部分小说都关于爱情(也有关于亲情等)和生活,而二者又自然地与女性联系得更为紧密,我倾向于将它们看做是作者为今日女性的发声,无论描述的现状好坏。不过这也可能是我知道作者的女性身份,所以先入为主的感觉。但无关紧要,因为我在乎的只是从中读出关于人生的感想。
●不是我的菜啊
●不理解一直创作这样千篇一律的作品的乐趣何在。了解了作者对女性的关怀意图之后,读一篇和读十篇都是一样的感觉,文体相同、题材相似、文字空洞,看似在描述细节可毫无连贯性和条理性,译者也完全没帮上忙。
●呓语小说。
●琐碎仔细,生活片段,很多生活细节,女性视角,阐释了某种意义上的生活,给我一点点向往的感觉。
●《倾诉》是伊芙琳·康伦最新的短篇小说合集,收录了从以往作品中精选的10篇和从未发表过的9篇新作。这些短篇小说均以大都市为背景,描写了形形色色的“生活失控”的都市人,脱轨和游离是他们的常态,质疑和试探是他们的策略。康伦的语言犀利、直接、幽默,善于描写平淡生活中的意外转折,这部合集很好地体现了她的风格。
●只有几篇读过之后能留下一点印象
●试读了第一篇,第一段话就蒙圈了。机翻后稍加整理,也就这样了。2018.10.16 寸步难行,弃。2019.10.20
《倾诉》读后感(一):那些怨恨,琐碎,日常
一直以来身边的女性朋友们,有一个奇怪的现象,生了女儿的妈妈都爱打扮,各种精致修饰,生了儿子的妈妈大多邋遢一些,对孩子的心也更重一些。我不明白为什么,不知道是不是在当下,还是有很多重男轻女的声音,嗡嗡的作响……
我无法体会婚姻里的那些怨恨,却深深的明白,周围人的困境,很多话我不愿说出口,任由这些事情就这么发生着,好像那些怨恨从未走远过,一代又一代的继续,留下许多坑洞,坐等时间渐渐填平,要说这是什么,这就是婚姻的真相,原来彼此怨恨,是多么琐碎的存在,是多么日常的存在。
这是一本悲观的书,里面集结了许多故事,那些远在异国的片段,似曾相识,这注定是一本不受欢迎的书,乐观的人觉得太悲伤,而真正陷在悲伤里的人,却讨厌它把这悲伤暴露的如此明显,为什么,我连骗自己的理由都没有了。
这是一个群体的悲哀吗?这是一个时代的悲哀吗?我不知道。
我只得尽一己之力,去了解这种悲哀,并且告诉自己的女儿,如何能够避免这种悲哀。
《倾诉》读后感(二):为“她”而诉,为理解而歌
《倾诉》是爱尔兰作家伊芙琳·康伦的短篇小说集。集子名称取自首篇标题,此篇中,某著名作家开设课程培训新秀,在课堂上讲述了一则人生故事,亦真亦书,似在教授小说创作之法,细腻的情节和讲述者的情感却又让人感觉他在倾诉自己的内心。本以为小说集的取名不过是单纯地来自首篇,在向后阅读的过程中,我才发现原来全书就是男男女女在倾诉各自人生。
本书语言的主要特点是将读者置于“倾听者”而非观察者的位置。书中各篇大部分采用讲述的口吻展开故事,有的(如《还有,苏珊》)甚至整篇都由单个人物繁絮冗长的话语构成,勾画的情境也多为日常简单的生活场景,格局不大,所以倾听者很自然就坐在各位主人公的对面,听其慢慢倾诉。
除此之外,以女性人物和爱情故事为主也是本书的主要特点。这或许是我先入为主,先注意到作者性别的缘故,但相信即便在不知作者性别的情况下,通过品读书中细腻文字,准确把握女性心理,树立独立女主角形象,也会倾向于猜测这是女性作家的作品。
其实,跳出具体的文字来看,这个特点也并不特别。关于爱情和生活,不管现代社会如何强调对男女一视同仁的基础,我们也似乎总会觉得女性天生与它们联系更为紧密,这就好比我们幼年哭泣时多喊“妈妈”一样——女性仿佛有天然“亲情感”的因子。
当然,伊芙琳不可能只描写女性,男性也是爱情和生活的组成,她的故事也给予男性空间,还有一些以男性视角观察情感世界。另外,书中还有关于亲情、友情的故事,但从根本上说,这些都只是方法和途径,她最终是为了表达对女性命运的关注,支持女性独立自主和觉醒,消灭偏见与歧视,比如描写兄妹情深的《最后的告解》:兄妹二人无话不谈,互为知音,在外人眼中,妹妹是屡屡“行为出格”的怪女人和“刺儿头”,而在哥哥眼中却永远是自己纯粹的妹妹——这种“哥哥式”的理解或许就是治愈偏见的最终解药吧。
《倾诉》似乎是“泛女权主义”的产物,是女性作家的顾影自怜,还可能在日益重视女性权益的今日让人觉得小题大做,但我们也的确应实事求是地看到,女性为失败的爱情和生活付出的代价远高于男性,而失败后各人的境遇不同与落差往往比失败本身更让人沮丧,所以,“题目”并不小,而且很有必要。更何况,如果连她们自己都放弃为生活和命运哭泣、欢笑与歌唱的话,那谁又会在意她们的声音呢?
《倾诉》,为“她”而诉,为理解而歌。
《倾诉》读后感(三):冰冷的火花
当我满足地吞下最后一口草莓果酱面包,却总是会看到遗留在棕色泛光的桌面上难以忽视的白色干屑。当完美的圆反复出现细微的缺口,细碎剥落的平面渐渐成为遗留的丑陋,而美好的碎片则成为了癌,分布在每一次呼吸的气流中,割伤一个又一个幸存者。这种不完美几乎是无可避免的,当话语开始运转,倾诉具有了排出异物的功能,而“异物”的意义随着流动的过程由细微逐渐扩大,这时我们才发现那些白色小点下的巨大跟盘有多么摧枯拉朽的破坏力。
在《倾诉》中,这种排异的着力点放在了女性身份上,由此衍生出的生活碎片却是广泛弥散的:暴力、欲望、责任、背叛、遗弃、困惑……在这些复杂思绪带来的细微崩坏中,女性面临着更为明显的挑战。伊芙琳·康伦通过不同的人称变化、视角变化,甚至是《倾诉》一篇中作品与现实的对比理解中不断充实着“倾诉”的母题。倾诉的意义在于何?
与倾诉最契合的《真彩深红还有,苏珊……》与《还有,苏珊》用完全地倾诉语态向苏珊吐露着女性的困惑与反抗。不论是倾诉者还是倾听者,她们的形象都在仿佛不相干的碎片语序中得到重建,在第一篇中,女性地位和形象的缺失在这种重建中一点点拼凑起来,这些碎片既是伤口也是能量,倾诉中裹挟的不公化为正面袒露自己内心的勇敢,和轻快地反抗的态度。“当一个人溜出子宫,在他还未被告知一切时,只能是普通的”。而第二篇则更贴近一种私密无序的倾诉内容,最终归落于日常的寒暄,一种形式的发散和本质的回归。
或许倾诉主题的琐碎感强烈到无法忽视,影响阅读感,但这确实是最贴切的表达。既会放大破坏物也会蓄积力量,倾诉是一个分解之后整合的过程。多数篇目在倾诉的内容上呈现着无序的广泛表达,而化为第三人称文本则通过人为的铺设隐晦而完整地显露出表达人情感的核心。在这个绵长的过程中,深层的、广阔的冲突(尤其是有关男性与女性的情感与地位冲突)通过琐碎的叙述拼凑出一幅激烈而空虚的图卷。在各个故事里,人们身体距离那么近,心却遥不可及,想要触碰的人被挡在外面,想要孤独的人却被窥探,窥探别人的人碰到了全然无法想象的滑稽事态……生活的齿轮总是无法完美地运转,在掺杂着无法磨合的损毁的颗粒声里,人们所认知的平静表象在倾诉的分解中不堪一击,那些事平常而重大,在沉静的文字下爆裂出冰冷的火花。“这是成年人做的事情,是在某人的眼睛里制造阴影,是用手轻轻地从某人的脸上往下抚摸,如此接近皮肤,却并不碰上去。”
伊芙琳像空气一样在日常中弥散,而她的女性意识汇聚成倾诉背后颇具分量的形状,这之中既有温和积蓄的力量,也有锐利如刀的话语。正如最独特的《倾诉》一篇,这里的倾诉者并不是讲故事的大作家,而是故事的内容本身,倾听者也并非散在于在场的所有人,而是聚焦于女性新人作家。这种话语意义与针对性的强调将倾诉变为更广阔的集合,而在最后也强调了倾听者理解的重大意义。
我们既感受着倾诉和它表现出的隐含内容,又在大多数时候作为倾听者或者纯粹的第三视角去梳理自己的内心。“也许是在于你的想法,即关于她们对他的想法究竟是怎么看的”。倾诉与被倾诉交织成一张思维的大网,我们在其中感受,并寻找着自己的路。
《倾诉》读后感(四):失控陀螺
如果仅仅从《倾诉》中的19则短篇小说为作者伊芙琳·康伦寻找一幅侧写,我恐怕会选择这样的句子:“她……成了一个尖酸刻薄的女人,不过有时候她满不在乎。在她想象中自己可以聪明一点,不过在家里她和所有人一样得擦洗锅子。”又或者,更豁达一些,“就让生活的严肃征服那偶尔从眼前一晃而过的浮躁吧。”
生活固然严肃,伊芙琳·康伦的叙述却往往更接近口语的温度,以绵延不绝的气势逼近读者,喘息之间尽是触手可及的细节,同时以其中强烈的荷尔蒙调制出压迫感。话语是彼此黏连的玻璃碎片。情感是气息腥甜的身体接触。《倾诉》作为短篇集的标题和首篇将氛围控制得很好,在这里,倾诉琐碎绵长而几近暴力,带着攻击性和目的性奔往某个不存在的终点,奔往男男女女之间难以互相理解的永恒矛盾。
尽管着力于描写女性的困顿与斗争,伊芙琳·康伦却并不认为自己是个女权主义作家,她如此解释道:“我认为,一个人只能定义为‘作家’,而不是‘女权主义作家’。准确地说,我是作家,同时也是女权主义者,女性意识影响了我对写作题材的爱好。”在她笔下,女人们直面自己内心的欲望,她们的性与爱渴求坦诚相待,却又无可避免地在都市的纷扰浪潮中搁浅。《夜不归宿》里,从过于孤独的环境中成长起来的女孩试图靠男人的爱抚获得慰藉,却因此被幸福拒之门外;而在《真彩深红还有,苏珊……》中,对话者拒绝为女性冠上“普通”或“不普通”的标签,因为她们理应享有平等待遇,因为她们“变化多端,难以描述”,绝不应该被简单地定义。
是的,伊芙琳·康伦的“倾诉”恰恰是在用定义来反对定义。她清楚人们对彼此认识的局限性,男人们眼里看到温顺贤淑的妻子,作家笔下的女人试图与命运抗争却一败涂地,公园里晒娃的母亲们打探着邻居的秘密,这些都来自真实的生活,却又真实得不那么绝对。真实只存在于左右摇摆进进出出游离不定的生活间隙,人们隐秘的内心依次打开,彼此倾轧,互相接纳便成了极端困难的事情。于是家庭作为人类生存境况最具说服力的基础单元,被拆解重构,于是人们意识到爱与激情的虚无缥缈,隐忍的忧伤与对无尽远方的渴望为他们带来隔阂与伤害,而家庭妇女仍然“星期天早上到公园里沉思何为欲望”。
2014年,伊芙琳·康伦被提名“爱尔兰桂冠小说家”,被称为爱尔兰最具原创力的作家之一的她,也书写着那片土地的历史与现在。在一些故事里,她将女人与男人的距离,拉伸成隔海相望、爱尔兰与不列颠的隐喻,似近实远,仍然处于自由和阶层的矛盾之中。而当她描写那些涂着血红色唇膏去大街上刷反天主教标语的“失控的一代”,这不仅仅是宗教信仰的冲突,更是对沉闷的社会现状的不满。
作为我所钟爱的爱尔兰作家之一,伊芙琳·康伦的惊喜之处在于精细、尖刻与优雅之间的巧妙转换。她笔下有这样的句子:“托马斯·麦格克像是被暴风雨肆虐了一般,这天早上他的血管里充满了青春和衰老,没有多余空间留给他自己的年纪。”她的文字如同弹跳运动一般在不同风格之间切换自如,句式灵动且富于深意,往往在不经意间便跃入微小又令人感动的细节。而终究,一切在酸甜苦辣啼笑皆非中崩塌,生活像失控的陀螺,无可救药地滚向明天。
“对亲吻和抚摸抱以如此的期待,这或许是她对人之常情的一种误解,她在其中扮演什么角色并不重要。”
《倾诉》读后感(五):“深红”的本色
现在,如果我写一本书,我会站在我们的立场,承认一些事情。
——伊芙琳·康伦《真彩深红还有,苏珊……》
与伊芙琳·康伦短篇小说集《倾诉》同名的短篇小说《倾诉》大体上预示了全书的叙事。在短篇小说《倾诉》中,一位爱尔兰大作家对着一群女作家讲述那位再普通不过的女人霍普的故事,留下“这是真实的故事。你们可以用它,我不想要了。你们的故事就在面包和葡萄干里。”的告诫后,轻快地走开了。在大作家所讲述的故事中,女性霍普(英文原文是Hope,希望),等孩子长大后终于能在邮局打零工的家庭妇女,梦想着通过自己的攒钱带着孩子们离开丈夫。然而,这看似可期的希望实际上遥遥无期,钱总是还不够。最终带给她切实的希望的,却是姨妈留给她的遗产,这个从天而降的希望让她具备了跃出丈夫的圈禁的充分条件,可这一越轨的希望却迅速彻底地毁灭在丈夫的枪下。霍普死了。但问题的关键并不在于大作家所讲述的那个故事,而在于女作家们如何看待大作家的想法,再确切些,女人们如何看待男人对女人的想法。大作家关注的是在面包和葡萄干里的故事,而M所震撼的却是霍普面对丈夫的胁迫时,“夺门而出,用尽力气飞奔”的姿态,恰是这个未完成的姿态阐释了什么是“希望”,并解说了霍普的内心。
因此,在《真彩深红还有,苏珊……》一文中,康伦借叙述者的话语明确地亮出了自己的文学理念,即女性在历史、在文学中实质上始终是缺席的,由男性所建构的话语体系剥离了女性本体的属性,例如对爱的给予与需求、享受性快感的正当性、疼痛等体验的漠视。在康伦看来,男性“或许会称我们为深红(注:与女子常用名斯嘉丽读音相同),但并不把它当作一种真正的颜色”,即在男性看来,这个斯嘉丽与无数个斯嘉丽等同。而她本书所做之事,就是从那位爱尔兰大作家的刻板讲述中突围,站在女性的立场,在倾诉中承认一些事情,在承认中恢复“深红”的本色,使颜色成为颜色本身。
例如《比阿特丽斯》,截取了比阿特丽斯从出轨到回归R这么一个时间段,铺开两条叙事线索,一方面隐身的叙事者倾述比阿特丽斯发生“那件事”的前前后后细节,另一方面,比阿特丽斯以日记的方式自我倾述发生“那件事”前前后后的心理波澜。比阿特丽斯与R过着无性生活,在一次西爱尔兰假期尾声时的假日晚会中结识了他。他的出现点燃了比阿特丽斯的希望,她像飞蛾一样地扑向他,她所渴望的不仅仅是肌肤之亲,更是在场的生命体验,而他也只是被动地接受着,未敢主动踏出一步。这种看似平等的情感中,却存在着错位与间隙。因此,当比阿特丽斯再次带着行李出现在他的面前时,比阿特丽斯所展示出来的全部倚重让他感到恐惧,对于他来说,这爱太过复杂,他无法接受,不,他不敢接受,他怯弱,他只能是客厅墙上挂着的飞翔的鸭子。在比阿特丽斯的自我倾诉中,她深爱着他,但又因背叛而对R充满了罪疚感,而对这种忠诚与背叛、有爱与无爱的痛苦界定中,比阿特丽斯没有像他那样选择了回避,而是以倾述的方式去忏悔这不合时宜的真情袒露,在自我咀嚼中,既是确认痛苦,也是确认爱,即便这爱被放逐到冰冷苍白的海里,失去了色彩。
但我疑惑的是,以缺席方式存在的R是否也应该对此感到罪疚,也该忏悔呢?不仅仅R始终沉默,《夜不归宿》里诺拉的前夫汤姆同样是沉默的。这位自嘲是“从浴室窗口爬进来”的诺拉,孤独得甚至渴望挨打的诺拉,在未遇到汤姆之前,把孤独情境的摆脱希望寄托于异性的亲吻与抚摸,曾经的迷失堕落成了诺拉的原罪,丈夫汤姆在情人口中得知了诺拉的过去,于是,汤姆占据了道德至高点,用分手、夺取孩子抚养权的方式制裁诺拉。可是,汤姆就比诺拉更为清洁吗?显然没有。汤姆不过是把诺拉作为道德感的诱因,用诺拉曾经的不洁来佐证自己此时的清洁,来宽恕自己此时的不洁之罪,重新确立自己的道德优势。甚至,汤姆早就想丢弃诺拉了,不过是在等待一个有利的诱因罢了。更悲哀的是,诺拉不仅被汤姆所弃置,也被“我”以及那些所谓的朋友们所弃置。“我们像处女般悄悄行走在教堂走道上,装模作样得无以复加”,“我们”同样在生活中不同程度地有过欺骗、失信、背叛等行为,但互相隐瞒着,为自己成功的欺骗伎俩而暗自兴奋,并试图在与诺拉的划清界限中获得道德感。小说的最后写道:“啊,茴香酒上来了”。多悲哀啊,诺拉至始至终都是作为被讲述的、可随时停止甚至结束的客体存在着,又有谁在意她的倾诉?
比阿特丽斯也好,诺拉也罢,她们都是霍普的鬼魅,渴望跃出庸常的日常之外,去体验爱,但无奈纷纷搁浅在岸滩上,不论还能否回归,事实上都已被放逐在苍冷的海水之中了。
伊芙琳·康伦笔下的《倾诉》细腻而琐碎,柔软而绵长,看似毫无恶意,却因为太过真实而直接刺向人隐蔽的内心,以及人无法逃脱的困境。人被圈限在家庭的社会单元之中,互相欺骗,互相倾轧,互相厌恶,却也互相拥抱。谈不上是爱,还是不爱。而例如家庭之类的社会单元看似填补了人的情感空洞,但更为悲哀的是,身体如此缠绵的两个人在灵魂上却是如此的疏远隔阂。
你在倾听中感知不到这其中是否汹涌着强烈的爱憎,情感被淡化,甚至被隐匿了。希望就像是爱尔兰海里的水,平静地,亘古地流动着,流动着,却因为被放逐在了绵远的时空中,而彻底地失去了触摸拥抱的可能性。如此想来,更让人绝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