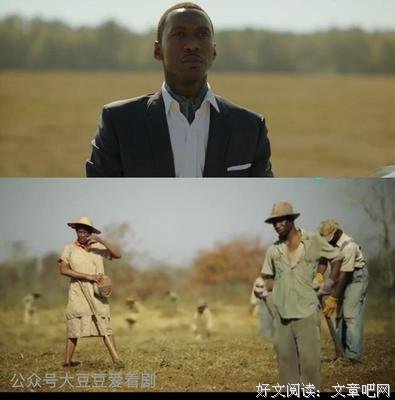
《农奴》是一部由李俊执导,旺堆 / 拾崔卓玛 / 强巴主演的一部剧情类型的电影,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观众的影评,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农奴》影评(一):沉默就是力量
不要以为这部片子多么意识形态。
单从影像风格上,整部电影的沉稳和悲悯非常厚重。
可以说,就像那些悠久的老苏联电影。
我记得我只是看的投影仪,而那种沉默的力量击中了我的心脏。
藏独分子见TM鬼去!
《农奴》影评(二):老电影中的经典,值得收藏
作为80后,面对浮躁的都市生活,污染的环境,突然很怀念以前蓝蓝的天,静静的小城,碧蓝的大海。所以,最近就爱上了老电影,想从中找到一些儿时的影子。碰巧看到了这部电影,看完后,竟然有想保留的冲动。难得的好剧,特殊的历史和人文背景,决定了,在那个时间,那个地方,有一段血泪史,和一场抗争的风暴。
新中国历史上有很多类似题材的影片,说实话,水平良莠不齐。但这部剧,不论是剧本,演员,还是规模,用当下的话说,算是良心剧了。
《农奴》影评(三):1
1964 新中国成立15周年献礼片
政治上:新中国第一部在西藏拍摄、西藏演员参与表演的影片,再现农奴们悲惨生活命运。
艺术上:创作团队坚持使用黑白胶片,还原西藏土地上那段真实发生过的奴隶历史。
艰辛的创作背景
1951年西藏地区迎来解放
1959年西藏地区平叛,废除农奴制度
1963年《农奴》上映
导演李俊(第二代导演),与冯一夫合作执导过故事片《回民支队》
拍摄过《闪闪的红星》《归心似箭》《大决战》等一系列新中国成立之初的著名影视经典
到西藏实拍
强烈的反差艺术效果
摄影师韦林玉:“黑白胶卷最能展示凝重的基调,而且黑白片也有一种历史沉默。”
哑巴的隐喻
生而为人的发声权
《农奴》影评(四):小布尔乔亚们不高兴了
什么?小布尔乔亚心目中的圣地,能被康巴汉子净化心灵和阴道的西藏,竟然如此落后?砍手剥皮?
不可能!
一定是gcd在捏造事实无脑黑!
什么?西方媒体也称赞解放农奴?
不可能!
那是民主国家媒体的败类!
什么?民主是社会主义苏联的口号?
不可能!
苏联偷了西方国家的口号!
什么?西方国家的口号是自由?
不可能!
都是你们瞎编的!
不可能!
农奴每个人都生活在天堂
没有砍手砍脚挖眼剥皮
都是假的!
农奴和奴隶主称兄道弟!
农奴平均收入二十万美金
农奴每个人都有私人飞机
西藏就是天堂,奴隶主就是活菩萨!
什么?解放军竟然剥夺了农奴当奴隶的自由!
侵犯人权!破国
《农奴》影评(五):我们能从《农奴》中学到什么
《农奴》是1963年完成的作品,很大程度上带有政治色彩,但极具时代特色。 1、音乐的特色 因为是藏族同胞的电影,所以音乐上极具特色。电影中有三处有唱词的音乐,一是强巴因封建势力压迫,决心不再开口讲话,用了“哥哥你听我唱”;第二次是解放军战士死去,“如青松”的歌颂音乐;第三次是结尾,歌颂毛主席的音乐。 2、转场的匠心——转场的顺畅,构图上的艺术 而电影在视听语言上,能很好地做到“说到哪转到哪”孩子三次成长都自由切换,而开场不久,强巴父亲的鞭子也在主人家和自己家之间自由切换,导演很好地利用了这种自由,极大程度上增加了片子的可看性。 而另一方面,强巴母亲去接丈夫回家,渐渐走入门框,也象征着封建的束缚;师傅在教授强巴刷金像时,站在佛祖手心,暗示了小活佛玩弄平民的本质,嘲讽、命运的意味不言而喻。 3、剧本——台词的一语双关;例证性动作 《农奴》除了台词把控上,除了作为转场,还有更深远的意义。“无处可逃”“菩萨那么多双眼睛”“你再中邪就在劫难逃了”这些台词让人印象深刻。 剧本中的例证性动作也让人印象深刻——强巴从正常人到被逼迫决定不讲话,再到被解放军解救开口讲话;铁匠父亲被拷上,子承父业小铁匠被拷上,到后来在强巴的帮助下解脱镣铐。这实质上隐藏了一个民族从封建走向解放。而这些,也在结尾得到了点题。
《农奴》编剧黄宗江 导演李俊 电影意义: 问世于1964年,为新中国成立15周年的献礼片; 政治上:新中国第一部在西藏拍摄、西藏演员参与表演的影片,再现农奴们悲惨生活命运;艺术上:创作团队坚持使用黑白胶片。还原西藏土地上那段真实发生过的奴隶历史。 导演: 导演李俊。是中国著名的第三代导演;和冯一夫合作指导过故事片《回民支队》; 拍摄过《闪闪的红星》《归心似箭》《大决战》等一系列新中国成立之初的著名影视经典。 艰辛的创作背景: 到西藏实拍;选用西藏演员 强烈反差的艺术效果: 1、黑白 《农奴》摄影师韦林玉“黑白胶卷最能够展示凝重的基调,而且黑白片也有一种历史沉重感。” 2、开场秀美山川与低沉小号,悲苦百姓步伐,悲歌; 3、充满张力的美学构图——参拜佛像,一开始倾斜,摇信众;威严感,压迫感,如何用宗教压迫人民 老喇嘛失明 全景镜头,大小;手中。 哑巴的隐喻: 生而为人的发生权(10世纪——13世纪) 哑巴开口说话的第一个归属感,是解放军,是新中国。
《农奴》影评(六):从《农奴》中我们能学到什么
《农奴》是1963年完成的作品,很大程度上带有政治色彩,但极具时代特色。 1、音乐的特色 因为是藏族同胞的电影,所以音乐上极具特色。电影中有三处有唱词的音乐,一是强巴因封建势力压迫,决心不再开口讲话,用了“哥哥你听我唱”;第二次是解放军战士死去,“如青松”的歌颂音乐;第三次是结尾,歌颂毛主席的音乐。 2、转场的匠心——转场的顺畅,构图上的艺术 而电影在视听语言上,能很好地做到“说到哪转到哪”孩子三次成长都自由切换,而开场不久,强巴父亲的鞭子也在主人家和自己家之间自由切换,导演很好地利用了这种自由,极大程度上增加了片子的可看性。 而另一方面,强巴母亲去接丈夫回家,渐渐走入门框,也象征着封建的束缚;师傅在教授强巴刷金像时,站在佛祖手心,暗示了小活佛玩弄平民的本质,嘲讽、命运的意味不言而喻。 3、剧本——台词的一语双关;例证性动作 《农奴》除了台词把控上,除了作为转场,还有更深远的意义。“无处可逃”“菩萨那么多双眼睛”“你再中邪就在劫难逃了”这些台词让人印象深刻。 剧本中的例证性动作也让人印象深刻——强巴从正常人到被逼迫决定不讲话,再到被解放军解救开口讲话;铁匠父亲被拷上,子承父业小铁匠被拷上,到后来在强巴的帮助下解脱镣铐。这实质上隐藏了一个民族从封建走向解放。而这些,也在结尾得到了点题。
周老师课笔记:
《农奴》编剧黄宗江 导演李俊 电影意义: 问世于1964年,为新中国成立15周年的献礼片; 政治上:新中国第一部在西藏拍摄、西藏演员参与表演的影片,再现农奴们悲惨生活命运;艺术上:创作团队坚持使用黑白胶片。还原西藏土地上那段真实发生过的奴隶历史。 导演: 导演李俊。是中国著名的第三代导演;和冯一夫合作指导过故事片《回民支队》; 拍摄过《闪闪的红星》《归心似箭》《大决战》等一系列新中国成立之初的著名影视经典。 艰辛的创作背景: 到西藏实拍;选用西藏演员 强烈反差的艺术效果: 1、黑白 《农奴》摄影师韦林玉“黑白胶卷最能够展示凝重的基调,而且黑白片也有一种历史沉重感。” 2、开场秀美山川与低沉小号,悲苦百姓步伐,悲歌; 3、充满张力的美学构图——参拜佛像,一开始倾斜,摇信众;威严感,压迫感,如何用宗教压迫人民 老喇嘛失明 全景镜头,大小;手中。 哑巴的隐喻: 生而为人的发生权(10世纪——13世纪) 哑巴开口说话的第一个归属感,是解放军,是新中国。
《农奴》影评(七):【386】《农奴》——鲸鱼推荐872部好电影
《农奴》年代:1963年 / 国家:中国 / 导演:李俊 / 主演:旺堆、拾崔卓玛、强巴
聊到这部电影时你可以谈论以下话题
1、西藏农奴们的悲惨生活!
1951年,“金珠玛米”(即解放军)和平解放西藏。但是在1959年又发生了反动武装叛乱,此事在《达赖喇嘛:分裂者的流亡生涯》一书中有详细记述。鉴于此,八一电影制片厂拍摄了这部表现农奴血泪史的影片《农奴》,深刻揭露了封建农奴制度对百姓的的压迫。编剧黄宗江为此到西藏体验生活,了解了当地群众过去都过着怎样骇人听闻的奴隶生活,用三年时间写成了剧本。电影中强巴这个农奴从非哑巴到哑巴,再到开口说话,象征了西藏解放后非人到做人的历史性转折。他三次摔农奴主朗杰,将他的反抗意识表现得层次分明。
2、60年代中国黑白电影的巅峰!
如今很多人在回看《农奴》时,会被它高超精湛的光影设计所折服。李俊在那个彩色电影早已普及的60年代,依旧坚持用黑白胶片拍摄,是因为他觉得黑白色块的对比,可以表现出西藏农奴制统治下如同黑白地狱般的写照。比如电影一开始,农奴们在高原强光的照射下辛苦劳动,渺小的身影投入到了阳光遮蔽的阴影,而女奴们则在暗黑中艰难前行,如同在这个暗无天日的世道中痛苦挣扎。藏族地区的宗教音乐,也将那种动人心魄的感受传达出来,因而《农奴》被认为是中国17年电影中艺术表现特别是黑白造型最出色的作品。
全片最精彩的部分是这两处
怒点
第33分钟,强巴被强迫着给少爷朗杰当马骑,朗杰挥动着树枝抽打着他,旁边还传来女孩哄笑的声音,但即便如此,强巴也没有吭一声。农奴主对农奴的欺压到了令人发指的程度。
燃点
第79分钟,朗杰让强巴背着他赶紧跑,还催促着“解放军要来了,快点!”这时强巴终于压抑不住自己的反抗意识,将朗杰摔倒在地,两人缠斗在一起,终于在解放军的一声枪响后,朗杰倒下了。
今日头条:鲸鱼电影
《农奴》影评(八):导演说
不拘于常规叙事的黑白影像
1963年12月,《农奴》耗时一年后拍竣,这部由八一厂组成的创作班底及全部藏族演员倾力出演的黑白影片,被称为中国十七年电影中黑白片的巅峰之作。这部从叙事上看“记录性多于故事性”、“诗多于剧”的影片以其风格化的魅力,浑厚、博大、深沉的电影语言,在中国电影史上留下了独特的一笔。
四季在脚下,日月在天边这部电影在当时给人们留下了一个很明确的印象:西藏几乎等同于想象力所能达到的原始的人间地狱。拉舌头、扒人皮、挖眼睛、抽筋,活生生把人打死,奴隶社会的残酷和西藏宗教的阴森恐怖尽现其中。
到了80年代初,进入了民族突然觉醒的年代,人们开始从被“蒙蔽”了二三十年的愚昧状态里走出来,这是一个认清真实,认清自我权利的年代。在这个时期,罗中立的画作,那幅黝黑的《父亲》唤醒了全国亿万人民内心的伤痛,人们突然意识到我们的父亲是如此的衰老,如此的贫瘠。就在用《父亲》作封面的这一期国家美术权威刊物《美术》里,同时发表了陈丹青的“西藏组画”。这组作品用直接写实的画法,直面地表现了人生最赤裸的“真实”。人们感到惊异、震动、怀疑,或许当人们在现实生活中找不到出路的时候。正是青藏高原宽阔的胸膛接纳了众多期许“精神家园”的文化人。而“西藏热”也正是从那个时候开始升温。
有评论说“在艺术创作中,西藏经历了恐怖、写真、魔幻以后,现在逐渐进入了一种很具形式美感的阶段,可以称做是矫情的阶段。”想起《农奴》的诞生正是西藏平息叛乱、实行民主改革之后的60年代初期,正是文艺创作中“恐怖”描述的阶段。
但在看这部奇特的写实主义电影时,依然可以感觉到在一些情节的铺陈中浇灌出意识形态所认可的花朵,比如强巴与自幼相知相惜的兰尕骑马坠崖时所说:“相爱的人死在一起菩萨是能够原谅的。”强巴装成哑巴也被处理成一次心理上强韧反抗的过程,这几乎与同时期出品的苏联电影大师塔尔科夫斯基在《伊万的童年》中“安排”少年伊万的“失语症”惊人的相似。个人的渺小与孤独、悲凉与无奈。这样的情感在以“激越情绪”见长的十七年电影中称得上是一个“异数”。那些“说”的欲望的丧失并不意味着意志和情感的丧失。而那些被压抑的无法“说”的叹息用沉滞的镜头“写”在了胶片的深处。
每当想起这部影片就会想起一段歌词“风雨数十载,往事越千年,神山圣湖隔不断,茫茫略漫漫。雪莲花开佛光显,四季在脚下,日月在天边。”
不拘于常规叙事的黑白影像
《农奴》的故事发生在封建农奴制度下的旧西藏。影片也是黄宗江的扛鼎和压卷之作,1959年,黄宗江去了一趟西藏。在那里,他听到翻身农奴控诉过去农奴主的十恶不赦,也看到了在“世界屋脊“上生活的人们高唱颂歌的情景,后来又先后多次奔赴西藏体验生活,最后花三年时间完成了《农奴》的最后一稿。影片把整个农奴阶级的痛苦和觉醒通过一个农奴的遭遇和反抗表现出来。而这贯穿始终的人物就是——强巴。
角色:“强巴”是一个缩影“强巴”在西藏是一个比较普遍的名字,故事就是从强巴的出生开始,父、母先后被领主折磨致死,他自己也被活佛罚做哑巴,领主少爷经常把他当作马骑。小强巴在折磨下跑到山上望着滔滔江水说:“说话,叫我学马叫。叫我喊老爷,我不说,就是不说!”从此强巴成为了“哑巴”。后来他几次死里逃生,并在最后受重伤抱着活佛藏在佛像腹内准备发动叛乱的枪支,冲出火海。大旺堆说家里的祖辈都是农奴,父母就是农奴,而自己其实就是农奴的儿子,所以演强巴感觉就像真实的自己,在感情的表达上非常充分,至今回想起拍摄时的情景都历历在目。
机遇:从“上戏”到话剧团我一直生活在拉萨,唯独去上海戏剧学院学习的三年时间。在这以前我是在西藏的民族学院(以前的“西藏公学”)学习,1959年西藏平息叛乱之后,为了培养西藏的电影和话剧演员,国家来学校里招生,我就是那时被招到“上戏”的,去上海的有一批各个战线的人,我那时已有27岁了。从1959年9月到1962年毕业,西藏组建话剧团,我们就全部进入西藏话剧团,可以算是第一代藏族话剧演员。
1963年2月,《农奴》的摄制组进站,来了以后多方面商量想全部从话剧团寻找演员,当时剧团的演员们都很激动,因为这部电影将是西藏第一部故事片。当时也是出题目然后做即兴小品,经过导演和剧组人员的商量我很幸运地成为了“强巴“。
花絮:到北京补拍的策马镜头影片从拍摄到后期用了将近一年的时间,当时西藏的交通很不方便,条件也十分艰苦,为了真实我们在拍摄时所说的台词都用藏语,后来再配音。好在我这个人物从头到尾就基本没怎么说话,就是形体和表情上的语言,这把握起来其实更难。影片在西藏拍摄时基本没有遇到什么问题,外景和大部分镜头都是在西藏完成的,但是想起来至今印象深刻的就是跑到北京来补拍一组镜头。
那场戏是强巴带着兰尕策马狂奔到悬崖旁,影片都拍完了,剧组回到北京看过以后认为需要补拍,于是我们就从西藏赶来。找到北京郊区一个部队骑兵团,借用部队的军马拍摄,用的是机场的一段比较长的跑道补拍这组追捕的镜头,最有趣的是因为我们穿着藏袍、披着大红,军马不熟悉我们,演追捕我们的老爷的那个演员多次被摔下马来,鞋子被磨烂了,牙还被摔掉几颗。于是只好给了我们一个礼拜和马熟悉,每天穿着藏袍去喂马。现在在电影中看到的镜头就是那段在北京补拍的镜头。
影片完成后各方面的评价都很高,一方面可能是出于政治宣传的需要;另一方面也是因为影片确实很好。这段从奴隶走向社会主义的历程被反映到胶片上,也是艺术化的影像纪录的遗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