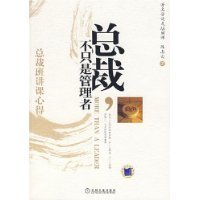
《不只是厭女》是一本由凱特.曼恩(Kate Manne)著作,麥田出版的416图书,本书定价:平装,页数:2019-12-7,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不只是厭女》读后感(一):为什么不只是“厌女”:The Logic of Misogyny
“于是,一个女人遭遇的厌女情结是某些男人的诗意正义。”
这本书其实主要讨论了以下几个问题:
1. 厌女是个人的还是社会的?作者认为对厌女的心理学理解,是一种“天真”不过的理解。这种理解的危险在于将拥有厌女情结的男性特别化:他们只是存在一种心理上的不正常现象,从而削弱了或隐身了厌女的社会政治机制。厌女是社会的,是政治的。“在这些情境里,因为父权规范与期待的执行与监督,女性比较可能遭遇到敌意。而这是因为破坏了父权的律法和秩序。”厌女情结的功用是执行和监督女性的“臣属姿态”。厌女情结应该用来指称任何在女性的行动背后构成背景的敌意力量。社会的厌女情结其实可以用来解释“Not all men”这种特殊化厌女情结的做法为什么很荒谬,以及“Yes all women”为什么是更为普遍的问题:因为它是社会的。
2. 厌女情结和性别歧视是一样的吗?作者在这里构建了两者的一种区别:性别歧视是父权意识形态的分支,而厌女情结是一种为此服务的支配体系,用来监督和执行其规范和期待的系统。“性别歧视是科学的,厌女情结是道德的,而父权秩序永远处于霸权地位。”而社会控制的机制便是,通过激励或抑制的因素,形成正向或负向的增强机制。
3. 女人在厌女情结中是什么样的角色?作者在这里的观点很有启发。作者认为,与其说女人在厌女情结中被排除在人性之外,没有被当作人类同类,不如说其实女性的人性在这个过程中被充分觉察了。甚至她的人性反而是问题所在:在厌女者眼中,她的人性被给予给了错误的对象,以错误的方式,因错误的原因付出。她并非不是人类,她是“人类付出者”,human givers。
如果要和上野千鹤子做对比的话,她们都察觉到了厌女的某种社会机制,但上野的厌女以病症的方式出现,讨论了男性如何产生厌女症。本书作者则将注意力放在女性身上,讨论这种社会机制如何使女性的臣属地位得以加强,而这也是作者副标题的用意,讨论“the logic of misogyny”,都是非常有启发、非常有益的讨论。
《不只是厭女》读后感(二):关于厌女暴力的一种解读
作为人类,我们的自由来自于透过其他形式遵守规则,以及修改、创造、突破和改变。
01
天真式的厌女情结认知倾向心理主义概念,它建立在一种恐惧症或深层厌恶的模式上,理解为一种心理上的不健康或不理性状态,而非社会权力关系系统性与可预测的表现形式。
我们应该将厌女情结理解成父权社会下运作的一种秩序体系,其本质在于社会功能而非心理学上的状态;其目的在于监督并执行女性的臣属角色,维持男性的支配地位。以直接和或多或少带有强制意味的方式,来制定和生产符合男权逻辑的社会关系。
父权意识形态以一长串机制支持其统治目标,包括女性对相关社会规范的内化、对女性独特的气质和偏好的叙事,以及将相关照护工作调为可以带给个人满足感、对社会而言有其必要、对道德而言有其价值,并且是酷、自然与健康的。女性遵从这些相关的社会角色时,理应要尽可能地看来自然,或看似是自由选择的结果,例如几个最明显的例子:充满爱意的妻子、奉献的母亲、酷女友、忠实的秘书,或好的服务生等。她永远是某个人的某个人,而鲜少是她自己。但这完全不是因为她不被认定为人,而是因为透过劳动服务、爱和忠诚的形式,她的人格被认定是归属于他人的。
在此社会关系之下与道德经济里,女性对男性有付出的义务而无提出要求的权力。女性被默认为是付出者。如果女性违反规定或拒扮指定的角色,或者付出得不够或付出对象的不正确,没有用正确的方式或正确的精神付出...未被女性尽职尽责满足的男性则有理由表现出气愤、怨怼,甚至惩戒。
厌女情结不需针对所有女性,相反它通常只针对特定女性,例如:那些避开或逃脱以男性为依归的服务角色的女性,或进入之于男性而言具有权力和威信位置的女性,以及女性主义者;另一方面,厌女情结和性渴望从某种角度说并不互斥。
父权社会的惩治方式多数是温和而无缝的,借由低成本方式对女性进行精神上的打压,例如:奚落、贬低、嘲弄、侮辱、毁谤、妖魔化,性化或去性化...带有轻视与轻蔑意味的对待,然后还有暴力跟威胁的举动:包括打沙包——亦即延宕攻击,或替代性攻击。
厌女者倾向因为女性的性别身份而普遍性地厌恶或仇视女性。几乎每一位女性都有可能受到厌女者的威胁和惩罚,一个女性很可能迫为其他女性可能的责任付出代价——亦即仗着她刚在那里或可能缺乏资源,故而在她身上发泄来自他处的挫败感,以重建父权的秩序。
02
我们需留意厌女言论说了什么又没说什么。
性别歧视是父权秩序的辩证部门,起着合理化与正当化父权关系的功能;厌女情结是父权秩序的执法部门,监督和执行父权秩序的主要意识形态。性别歧视是“科学”的,厌女情结是“道德”的,而父权秩序则永远处于霸权地位。
很多时候性别歧视能够得以运作,乃是藉由自然化性别之间的差异,使得生理差异与社会分工不同形成了合理化的因果关系。此处未被说出口的前提是“应该蕴含能够原则”,以及一种类似“无法则蕴含无必要”的心态。
性别歧视标榜理性中立。而事实上,在女性条件和男性相等的情况下,人们往往会下意识高估男性,并低估女性的优点。女性需表现得加倍优秀才能够一样地受到尊重、成功、被人赞扬等等。
一个女性的人性被认可,可能会使其错失许多的道德自由,并可能会在某些方面责任感过重,陷入虚假的内疚和羞耻不能自拔。
03
一个男人通常不会被置在一个得以支配所有或大部分女性的位置,但他仍然可以被视为是一完整运作中的父权制家长,他只需要在面对某个或某些特定的女性时占有支配性地位的就好,而这通常会在家庭或亲密关系里。
根据付出的差别性规范,女性时常被认为亏欠了某些男性或社会典型的阴性属性好处,而一名男性会被认为有权主张从某些女性身上获得它们,进一步说如果他没有被给予他所应得之物,他就会被允许索取这类好处,亦即从女性身上强制拿取却不用受到惩罚。
一名男性会攻击其他男性,与他是厌女者间没有冲突。他渴望能同时支配地位较高的男性与受她们吸引的女性。人们通常视针对女性的犯罪活动为随机并且无法解释的,而忽略其更广泛而深层的是厌女暴力形式中的一种形式。
在针对女性特定性别群体实施暴力的行凶者的眼中,很大程度上特定类型女性残忍地剥夺了他的所有物,这个被剥夺的所有物是女性她自己——她未留意或太过高傲以至于未能注意到他。他不仅仅觉得自己不被她看见,她让他觉得自己什么都不是、不存在、不被当成一个人。他的敌意源自他的需求未被满足以及后续因此而生的脆弱感。他因被拒发起的攻击经常指向夺去女性的社会资本与性资本。
在此类事件中社会倾向于同情男性的痛苦多于女性。如果一个男人有着好男人的人设与足够的社会资源,或一个令人心碎的落魄故事,那么人们就会百般找理由的捍卫他的名誉、维持他的清白。而对被暴力的女性,人们的沉默和否认助长了另一种暴力:无视她被伤害,改写她的叙事,甚至对其进行邪恶的道德角色的反转。她的私生活、爱情生活、过去的人生、家庭生活...都将是她沦为不幸者的客观理由。
《不只是厭女》读后感(三):两部厌女的比较
首先,什么是厌女?
按照Kate Manne在本书的说法,“厭女情結應該被理解成父權秩序下的「執法」部門,整體功能在於監督和執行父權秩序主要的意識形態“,也就是说,它的产生是出于维护或重新建立父权男女等级秩序的需要。这个定义似乎只是定义厌女的功用,回答的是厌女能做什么的问题,而不是厌女是什么的问题。我的问题是,按此说法,那么在父权意识形态没受到挑战的情况下,厌女是否就不存在?要回答这个问题,无可避免要清楚厌女究竟是什么。
如果说厌女是在父权秩序受到威胁后对女性产生的敌意与压制,那么一开始男性的优势地位和女性的弱势地位是如何被确立起来的?
如果没理解错,Kate在这里的解释便是引进了性别歧视(sexism)的概念,这个概念区分与厌女情结(misogyny)。与厌女情结捍卫秩序的功用相对应,性别歧视也是一种意识形态,但起着父权制秩序的合法化功用,是父权秩序的“辩证部分”。
性別歧視本身相信男性在陽剛的、高聲望的領域(例如知識鑽研、體育、商業和政治等)中比女性優越,同時他們在其中自然而然或甚至無可避免地會處於支配的地位;厭女情結則涉及焦慮、恐懼、維持父權秩序的渴望,以及致力於在它受到破壞時進行重建。
也就是说,性别歧视以一种表面理性的方式让人们以“正当”理由行使厌女,故“性別歧視之於偽科學,正如厭女情結之於假道學”,“性別歧視之於厭女情結,就像是公民秩序之於法律執行”。这可以阐释为什么会有厌女的问题,可以阐释这个男女秩序的根基所在,但并没有回答“在父权意识形态没受到挑战的情况下,厌女是否就不存在?”的问题
如果说在父权意识形态没受到挑战的情况下,厌女就不存在,则感觉与现实相背。在平常中不缺乏女性对男性的服从,但仍然受到男性的敌意。这种敌意难道不也是厌女吗?这种敌意当然不是性别歧视本身,而是性别歧视的一个结果表现。如电影”Thelma & Louise“里她们两人开着车在公路上,即使什么都没干,但仍然受到猥琐货车男的性侮辱,被骂“婊子”,或者你可以说她们两个是没干什么,但她们不是作为她们自己而遭受到的侮辱,而是作为一些女性群体的代表受到的侮辱,卡车男或许是在其他情境下已然受到某些女性的挑战,所以才挑起了他将Thelma and Louise视为这个女性群体的代表进行侵犯。就如原文所说,“既然在厭女的想像中,個別的女性經常成為全體的替代品或代表,那麼,幾乎每一個女性都有可能受害於來自某處、某種形式的厭女敵意。”
但我还是怀疑厌女只是在根深蒂固的社会规范体系遭到拆解的过程中才产生存在,将其视为一种意识形态下对女性的敌意,应在这个体制形成开始便伴随存在着,二者是共生关系,而没有严格的时间先后,即使有先后,那也是逻辑上的先后。
Kate对厌女的理解,与上野千鹤子对厌女原因形成的理解还是有较大区别的。Kate怀疑人道主义(humanism)的解释,她认为從父權價值的觀點而言,女性可以是人──有時候太像人了(“Women, all to human”),
“但如同我所展示的,羅傑並不認為女性是無心智的東西、物品、非人類或次人類生物,這也不是父權秩序裡一般女性的真實情況。相反的,女性的人類能力被視為虧欠特定他人,通常是同時維持著白人至上主義之異性戀關係裡的男性或他們的子女,
与将她们物化相反,在父权社会里,女性是被视为具有人性,被强加赋予了许多人阴性特征:慈爱、有同情心、注意力、情感的、照顾人的等等,男性认为自己理所当然的享用这些人性的使用权,如果女性违背了这些道德规范,就会受到男性秩序的惩罚。她被人称呼是谁的女儿,谁的妻子,到后来是谁的母亲,”她永遠是某個人的某個人,而鮮少是她自己的。但這完全不是因為她不被認定為人,而是因為透過勞動服務、愛和忠誠的形式,她的人格性被認定是歸屬於他人的。“
就是说她有人格性,只是人格性不是归属于她的,她失去了对自己人格的自主权。父权的意识形态以女性的人性为前提,把女性视为道德和社会生活里的人类付出者,在她拒绝付出时压制她们,这些行为带有去人性化的特质,但不代表将女性视为没有人性,而是承认她们具有人性,但加以利用、剥夺,采取去人性的手段对待她们。
上野千鹤子对厌女是什么的定义相对比较广泛一点,限定较小,简单说就是对女性的轻视、蔑视。她对厌女现象的原因阐述我是看的很爽的,有点醍醐灌顶的感觉哈哈。可能是Kate作为西方的白人女性,在受到性压迫的程度上相对不如在亚洲的女性明显,所以上野千鹤子的说法会感觉更加激进,有着极度的愤慨,看完后会有发泄的快感。
在上野这里,厌女症的理论解释是借用伊芙塞吉维克在《男人之间》里的“厌女症的理论装置”,即男性同性社会性欲望(homosocial)、同性恋憎恶(homophobia)与厌女症(misogyny)的三项配套机制。
简单说来,厌女症在上野这里,就是“不将女人视为与自己同等的性的主体,而是将女人客体化、他者化,更直接地说,就是歧视、蔑视。
男性同性社会性欲望(homosocial):男人通过将女性客体化来确认自己的主体,通过对同一客体的欲望,男人们相互承认对方为共有同一种价值观的欲望主体,相互承认成员”性主体“的男性同性社会性共同体,将没能成为男人的人和女人排除在外,这些集团之外的人,被冠以”女人“之名,并顺其自然地被视为低劣一等。让一个男人”成为男人“的,是其他男人,女人只是男人之间的纽带的媒介物,只是男人”成为男人“的道具,或作为”成为男人“的证明伴随而来的奖赏而已。与此相反,让女人”成为女人“的,是男人,证明一个女人是女人的,也是男人,女人的价值在父权规范里依赖于男性来体现。
同性恋憎恶是男人对自己被当作性的客体、丧失性主体地位的恐惧,即对被女人化的恐惧,他们需要确认这个集团没有掺杂异质的东西。
所以说,男性同性社会性欲望的建立是以厌女症为基础(将女人客体化),对同性社会性欲望的维系则是通过同性恋憎恶这个“检查机制”。
Kate Manne对人道主义理论提出以下质疑:女性也存在厌女症,若按人道主义的解释,女性是怎么会将自己的同类视为客体的?
上野也对这个问题进行过解答:
她们二人都承认女性也存在厌女现象,上野认为女性是可能将自己他者化的,一种通过自我厌恶,另一种通过将自己例外处理,但这两种方式kate都觉得不太可能。
我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是,在这个男性文化秩序里,男性会想破头地争取进入男性同性社会性集团,以获得自身身份的认同,对应的,那些被视为他者、被排除在外在的女性,则不会饥渴地主动将自己视为被压迫的女性集团的一份子,就如上野所说,女性的价值是男人赋予的,她们之所以成为女人,是因为男人,女人的同性社会性共同体并不存在,”女性集团“本身就是一个虚的构架,它的存在不是主动的、以确立自身主体性而建立的,在没有去抵抗厌女问题的意识之前,它是松散的甚至个体成员间是竞争关系。女性对自己的同性人群客体化不是不可能的,其实里面提到的“东电女职员”就是关于自我厌恶的一个很好的例子,还有一些女性则掩盖自己的女性身体特征(不符合男性审美),这些都是存在的现实。
Kate Manne 本人也承认,“女性和特权男性分别扮演付出者与取用者的角色,这会被女性与男性内化,因此,身为阴性气质俱乐部合格会员的女性同样可能会执行这些规范”。既然如此,那么她提出的“女性是怎么会将自己的同类视为客体的?”这个问题其实就不是根本问题,如果首先是男性将女性视为客体将女性排除在外,那在这种规范秩序下的女性也便能将这种客体化方式内化。这样,问题便回到了她认为男性并不是女性物化而形成厌女情结,反而是因为把女性太当人,但男性为了自身权力与地位,为了维护男性取用、女性付出的秩序,而不得不采取去人性化的方式对待女性。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男性用同理心可以将女性作为配偶、父母、子女、手足、朋友、同僚等正面关系来理解,但也同时认识到女性亦如男人自己一样可以有邪恶的一面,即被理解成对手、敌人、篡位者、不服从者、背叛者,这也是为什么”好女人“会被冠以“忠贞”、“忠诚”的美德。
既然一开始对女性也当人看,那么为什么结果偏偏是女性被去人性化地对待呢?为什么是厌女而不是厌小(对年少者的欺压)或者厌老等等?估计又要回到性别歧视的范畴。。总而言之,我同意她将厌女症视为一种意识形态来处理而不仅仅是心理学上的个人问题,但对厌女症的成因分析方面还是有待考量吧。
----------------------------------------------------------------
这本书关于证词不正义、受害者文化的观点还是挺受用的。
证词不正义是指身处臣属地位的成员对特定事物提出的主张,或对特定认物提出的指控经常会被认定为不太可信,这个不太可信不是基于事实证据,而是基于他们身为臣属群体成员本身。这也就有了“完美受害者”,即有过犯罪记录、或者是黑人女性这些本来在社会上就处于不利地位的人。这是受害者想要反抗成功的不利因素之一。
第二个因素是我们通常会将受害者想象成天真无辜、没有过失的。一旦我们怀疑或发现受害者犯过某些微小的甚至与案件不相关的错误时,我们便不情愿将其视为受害者,还很可能认为受害者自取其辱、自作孽。。
我们不仅将受害者看成只能是完美无辜的,还通常有将施害者看成一定是令人发毛、怪异、很不合群、很变态、缺乏人性的人。“他是正人君子,所以他不可能做出这种事”,但到底是应该根据他的行为判断他是不是正人君子先呢,还是用不经检验的正人君子作为绝对正确的假设去推论他的行为?何况很多性侵者在其他方面都很与常人无异,他们可以是你身边的看起来再正常不过的朋友,但并不能断定他们就不会有性暴力行为。
对受害者和施害者我们有着不同的严格标准,通常对受害者过于苛刻,对于处于支配地位的男性施害者,我们更倾向于宽容对待他们的罪行。同理他心就是一种偶尔会针对男性性暴力行为人所表现出的过度同情,通常是白人、身心健全、以及其他方面有特权的“黄金男孩”。如书里的例子,性侵者Brock Turner只被判了六个月服刑与三年缓刑,而且最终其实只服刑了三个月,在审判过程中,他的高超泳技被突出强调削减了罪行的严重性,法官也担心判决对Brock未来前途的影响,他父亲甚至描述儿子的犯罪仅仅是二十年的良好表现里二十分钟的行为。
受害者文化则认为受害者在争取注意力、矫情做作、太自我中心、过度夸大对自己的受害程度等。现在的女性主义便遭受着这样的攻击,认为女性主义者反应过度,而不会认为她们觉察到社会上的风险因子。这不得不让人忧虑:
对女权主义的东西看的越多,对现实世界先是失望,然后就越是近乎的绝望,Anyway,还是还给点积极的东西,受害者并不都只能被动的,不是只能被动地臣服于自己的受害者身份,在通过抗议与反抗的行动中,可以将被动化为主动,主动地去表演一个受害者的身份,去挑战这个不合理的秩序。由于大多受害者本身就是处于弱势地位,反抗本身困难重重,可能会引来更大的压制,但正因是”以卵击石“,更应”挺身而出“。“因為挺身而出可以是一種主體性的表現,與顛覆的行動;因為,它們使道德敘事脫離原本占優勢的、被默認的版本,並使得個人的遭遇在那些原本繼續漠視的人面前變得醒目。第三方可能會、也可能不會寄予同情,事實上,他們的敵視與怨懟可能會更強,而非減弱,但至少他們會知曉傷害的現實,或持續中的支配事實。”
《不只是厭女》读后感(四):对厌女情结的一个社会结构性阐释
“她的沉默成了冷冰冰,她的中立表达是愠怒,她的不注视是怠慢,她的被动是侵犯。”一、人们该如何认识和理解厌女现象/情结,或厌女情结的改良定义:通常上,厌女情结被人们天真、简单地理解为诸多个别主体(大多数是男性,也包括女性)蔑视、敌视、仇视女性的病态/非理性心理或人格问题,例如上野千鹤子所说的男人的“女性蔑视”以及女人的“自我厌恶”。在此之下,厌女情结就是厌女者所表现的样貌,而厌女者们则为符合某种特定心理状态(恐惧症或深层厌恶)的主体,进而人们要判定某人为真正的厌女者就要需要对其提供一种深层或根本的心理学解释。但由于理解他心在本质上的不可能性与模糊性,凯特·曼恩认为这种天真式理解使厌女情结成为一个太过偏向心理主义和个人主义的概念,或许一些个人主体可能会因为各种不同的原因而怀有对女性的敌意,但这类敌意的根源及共同之处在很大程度上则是出自于更广泛的社会制度(这个体制监督、惩罚、支配并谴责那些被父权视为敌人或对父权造成威胁的女性)里的行动、习惯和政策,因而厌女情结看似是一种个人化的行为选择,却更适合被理解为一种政治现象,对其提供一种社会兼结构上的解释,而非单纯的一种心理状态,这种心理解释在某些方面太过狭隘,致使厌女现象成为一个相对边缘且不含政治本质的现象,且无法帮助到它的受害者、攻击目标、以及其他被指控厌女但其实无辜的人。于是,凯特·曼恩对厌女情结的概念进行改良定义,指出厌女情结是父权意识形态核心且自然的一种表现形式,它“主要是整体社会体制或环境中的一个属性...这个体制监督、惩罚、支配并谴责那些被父权视为敌人或对父权造成威胁的女性。”(书66页)换言之,厌女情结是一个在男权社会秩序下运作的体系,它的目的和社会功能就是监督与执行女性的臣属角色以给予男性注意力与关爱,并维持男性的支配地位,于是那些被认定为未能符合父权标准的女性在其中比较可能遭遇敌意,主要包括“进入了之于男性而言具有权力和威信位置的女性,以及那些避开或选择逃脱以男性为依归的服务角色的女性”(书87页),而非所有的女性都有此种待遇,例如上述所说的自我厌恶的女性,这些女性不仅不会被厌女者们敌视,反而会被其赞扬和鼓励,毕竟惩罚与奖励、定罪与赦免的体系经常一同全面性地运作:当女性遵从性别化规范和期待、强制他人展现良好表现,并借由投入某些父权体制内常见的美德形式;或者当男性藐视了阳刚气概规范,对其进行惩罚和监督。总之概括说,厌女情结的基本表现形式就是在区分出好女人与坏女人的基础之上对后者进行惩罚以及对女性行为的监督。
电影《陷害布兰妮·斯皮尔斯》
同上
凯特·曼恩指出厌女情结是一个在男权社会秩序下运作的体系,它的整体功能是监督并执行其中的治理规范和期待,因而与其他和[压迫/弱势]与[支配/劣势]相关的体系、迥然不同的物质资源、各种带有鼓励或限制意图的社会结构、制度、官僚机制互相交织而成。但具体来说,它是透过一般性的社会规范执行机制、道德主义,其他人格层面上的负面概化、有阶序的社会行动,以及类似的过程进行运作,而这一切都建筑在人们对男女自然差别(如才能、兴趣、癖性和爱好)的刻板印象与根深蒂固的偏见基础之上,正如性别歧视那样,它的“意识形态通常包含了各种预设、信仰、理论、刻板印象,和广泛的文化叙事,透过某些方式来呈现出男女大不同,而如果这些不同为真、被传诵为真,或是至少可能为真,便会使得理性大众更倾向于支持、参与这个父权逻辑下的社会框架。性别歧视的意识形态也包括了替父权社会框架涂脂抹粉,将其描述成比真实面貌更值得向往且较不令人忧虑、失望或沮丧的存在”,(书123页)不同的是,性别歧视本身是学究式的理论,带有自满的意味,而厌女情结涉及了焦虑、恐惧、维持父权秩序的渴望,以及致力于在它受到破坏时进行重建,二者的关系紧密相连。
戴锦华老师的演讲:《当你愤而投身于网络战争的时候,对不起,你在为你的敌手贡献流量》
由于男性与女性的自然差别,社会对其进行了一种差别性规范,并发展出一种针对女性的“女性有所亏欠,或应该有所付出”的规范观点,即“女性会被认定亏欠了某些男性典型的阴性属性好处,或至少亏欠了社会,而一名男性会被认定有权利主张从某些女性身上获得它们。”(书170页)凯特·曼恩用付出/取用模型来具体解释这种现象,指出女性和男性特权分别扮演着付出者与取用者的角色,而女性所能付出的阴性属性的好处和服务有:爱意、倾慕、纵容、单纯的尊重、爱、接纳、照顾、平安、安全感和庇护;仁慈、同情、道德注意力、在意、关心与安抚等,且这些情绪和职责经常受到道德鼓励的捍卫:若被乐意且愉快地执行时,就有爱与感激作为激励;若没有实践这些职责,则会收回这些社会赞许;而男性所能取用的阳性属性好处与特权包括:权力、声望、公众认可、身分、名誉、荣耀、颜面、尊敬、金钱和其他形式的财富、位阶、向上流动,以及因为拥有身分高尚的女性的忠诚、爱和奉献等等而获得的地位,另外加之一些自由摆脱羞耻感、不必遭受公开羞辱的可能等东西。凯特·曼恩认为父权制就主要存在于这个付出和取用道德兼社会好处与服务的不平等性别化经济之中,在此之下,女性有义务给予某个人(通常上是一个在社会位阶上与她相当或高于她的男性)阴性属性的服务(事实上这些可能都是男性赋予女性的错误、伪造或虚假的义务),但却被限制或禁止拥有或从身处支配地位之男性身上拿走阳性好处并将此视为严重的不道德或耻辱,至少在他想要,或是渴望获得或保存它们的情况下是如此,而厌女情结就是透过这种道德劳动的性别化经济而稳固地运作。
凯特·曼恩在书中总结到,厌女情结包含了许多不同类型的从口头攻击这种微小伤害再到肢体攻击的谋杀等极度不同的伤害,具体包括责怪、怨怼、罪疚、惩罚、背叛、报复、不信任、位阶竞争、以及其他形式的羞辱、恶心和驱逐等行为,而在各种领域内的监督和执行手段,包括了性、母职、迄今为男性所有的空间、位置,以及传统上属于老男孩们的俱乐部,作者通过三个由厌女情结所引发出的问题来具体说明这个现象:
1. 当男性无礼地夺取了理论上女性应该要给予他的东西时,例如男性在婚姻内外对女性的性情或强暴,人们却倾向于原谅、遗忘并赦免这类由支配性男性所犯下的罪行,并且将我们的同情心扩展到他们身上,而非那些受害的女性。而这种现象通过“证词不正义”的方式得到了合理性的表达,即“当身处臣属位置的群体成员针对特定事务提出主张,或针对特定人物提出指控时,他们经常会被认定为比较不可信,因此他们身为臣属群体成员一事会被当成理由,使他们不被给予知者”,(书252页)例如女性的能力和信任度经常在不够合理的基础上被小看、被认定她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或不被信任、被认定她的主张较不诚恳、不诚实,乃至黑人男性因地位低于白人女性也经常遭到不正义的对待,而正是这种信用赤字或过剩经常支撑了支配群体成员目前的社会位置,并保护他们不至于从现行的社会阶序上跌落,即被指控、抨击、定罪、纠正或贬低。至于同理他心则是指在强暴行为中所表现出的一种偶尔会针对男性性暴力行为人所表现出的过度同情,而造成这种否定心理的原因一方面是由于人们对强暴犯的极端负面看法,认为一个光鲜亮丽、荣誉诸多的男性不可能也不屑于做出这种负面行为;另一方面则可以归咎于人们对受害者所遭受的伤害、羞辱和创伤的关怀不足,当人们将自身的忠诚给予强暴犯而转而责怪受害者时便改变了故事的叙事,这不仅将受害者从故事中彻底消抹,还增添了对其深刻的道德侮辱,如恶意猜疑受害者想从中寻求个人的复仇和道德惩罚等,而这便引出第二个问题。
2.当女性要求取用理论上她应该要给予他的东西时,人们则倾向于怀疑她不诚实并装腔作势,就算这种指控丝毫没有证据可言。而这体现了受害者文化的意识形态问题,凯特·曼恩指出人们对受害者的概念主要取决于某种特定的道德叙事,在此之中,一个主体被另一个主体以一种羞辱性或贬抑性的方式错误对待,从而产生一方是受害者(通常为女性),一方是霸凌者或压迫者,进而霸凌者是人们该怨怼、愤慨、不赞同、惩罚的人;而受害者是可怜、无助、被动、无辜以及人们理应同情的人,同时她也是注意力的焦点、是主角、是英雄以及被用来为有道德价值的目标服务。所以理论上,责怪受害者的行为是被认定为有道德问题的,但事实上,受害者关于强调个人自身受害经验的发声通常因其将个人放置于故事的中心而遭到他人的怀疑,被认为是一种取得第三方注意力、同情心和干预的花招,或是“被视为装腔作势和自以为重要,并且与此同时,是病态或脆弱的。人们觉得这个人凭借着想像力去专注与沉溺于她自己的故事里,而不是迅速地向前进;但是为了要前进,她不可能真的像(如上述所说)那般地凄苦、破碎。这样一来,就强化了伪善、虚伪、算计和自我中心的猜忌与指控”,(书299页)正如人们在面对各种性侵事件时对受害者女性的各种污名化理解与评论一样,仿佛女性都在扮演受害者。换言之,处于臣属地位的受害者若希望争取到正义和认可,会面对很多结构性障碍:(1)一开始不被相信,并被怀疑在骗人或疯了、歇斯底里等;(2)因所发生的事情而受到责怪,如穿着暴露等;(3)犯罪未能被妥善调查,如警员未认真对待家庭暴力案件等;(4)犯罪的证据因警方系统性的忽视或掩护而遭到摧毁;(5)女性的指控被轻视或不屑一顾,大事化小、小事化了;(6)犯罪被认为是随机且无法解释的,而不是被认同为广泛的厌女暴力形式中的一部分,或是藉由在其因果论述中置入可能是个人的或怪异的因素,如心理疾病,使得指控完全被撤销;(7)面对反向的指控,如自私、好斗、虚伪、操纵人心等;(8)被轻视,如看成太过敏感、幼稚、无法用成熟大人的方式来处理自己的问题;(9)被受指控者的粉丝和辩护者骚扰、威胁,以及可能被伤害。但即使这样,凯特·曼恩依旧支持强调一个人的受害经验,因为这有时候是为了促进团结,有时候视为了让个人成为叙事的中心以主动地重新塑造叙事,进而和占有优势并被默认的版本相互竞争。
3.当女性要求取用理论上男性所能取用的东西时,人们倾向于将之描述为贪婪、腐败、资格不符以及脱序的,从而使其落败给厌女者。这个问题最好的例证就是当女性在一个由男性所支配的角色上参与竞争,且其适任性不受质疑时,她们却普遍不被喜欢,且遭受社会惩罚和拒绝。心理学家指出这是因为人们经常不自觉地被鼓励去维持性别阶序,并藉由对争取晋升到高地位、阳性属性的位置,或用其他方式威胁要这么做的女性们施以社会惩罚,正如特朗普团队对希拉里的污蔑、民众对希拉里的恶心反应及其落败给前者的事实,凯特·曼恩认为厌女情结是导致这一结果的重要原因之一,而这个问题更生活化、普遍化的现象便是男、女性在找工作以及竞选领导时所面临的困境和不公平的待遇。
不仅如此,凯特·曼恩在此书中还谈及了伊斯拉维斯塔杀人案、有毒男子气概的家庭消灭者、有关母职的堕胎争议以及对人道主义的厘清等问题,这些都值得人们引申思考。但根本上,个人认为关于厌女情结的认识还是归根于人们对自身特权的认识与约束,正如作者所说,“即使并非全部,大多数的我们皆有某种形式上不正义、不配得到的特权,进而容易犯下这类错误:特权会让个人对自己的所有地盘产生一种知识上和道德上的错误认知”(书15页),换言之,在任何权力阶序里的卓越位置并不是其与生俱来的道德权利,人们需要在具体的情境中常自省和再认识。
女性如何书写自己的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