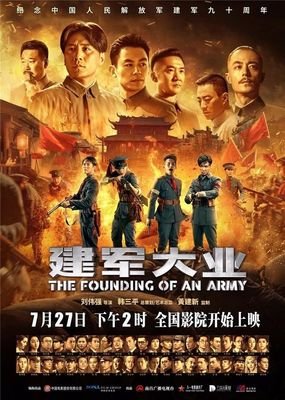
《革命前夕》是一部由贝纳尔多·贝托鲁奇执导,Evelina Alpi / Gianni Amico / 阿德里娅娜·阿斯蒂主演的一部剧情 / 爱情类型的电影,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观众的影评,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革命前夕》影评(一):迷茫之根:一个不可避免的循环
无产阶级目标有二,一要推翻剥削阶级,二要美好生活。可一旦变得舒适,无产阶级还叫无产阶级吗?同志们还是同志们吗?法布里奇奥为什么迷茫,又为什么妥协?
海底的淤泥上涌最后变成大鱼身体的一部分,但再也不会被叫做淤泥,无产阶级曾引以为傲的淤泥身份在自己的实践里被毁灭。
历史是人民创造的,但当人民觉醒想要创造历史的时候,历史就变成了虚无,真正的历史属于永远不会露面的人民。
《革命前夕》影评(二):暧昧
2019观影计划 No.16 #贝托鲁奇 《革命前夕》# 从莫迪亚诺那里学会了一个词,“暧昧”,在这部电影的语境下,我们可以理解为一种犹豫不定、没有一个坚定的内核支撑着你去心无旁骛地朝着一个目标去突破自己舒适的环境,打破自我理想和阶级现实的矛盾的心境。大多数的革命想法总会被妥协和消解,焦灼迷茫之后便是安静的循规蹈矩。贝托鲁奇用出色的镜头(比如开场时男主奔跑的脸部特写配合城市杂乱的人潮洪流),向我们展现了60年代意大利社会巨大动荡的社会图景,也借这部电影告诉我们,理想很容易一时冲昏你的头脑,陷入自我感动之后实际能做些什么需要极大的勇气和决心。革命意识不是昂贵独特的,思想的批判力在大多数情况下也打不过现实对社会再构建的重重阻隔。而活成自己当初最讨厌的样子,也并非羞耻的事情。这是一个人的自我驯化,也是一个社会从革命到文明新秩序约束的驯化,也是革命前夕社会未知命数交织的浮世绘。
《革命前夕》影评(三):"我希望所有东西都不会动"
看完Prima della rivoluzione的印象就是这几句台词:
quot;许多事情注定得发生,我注定得承受痛苦,你注定得饱受折磨。我存在是因为你的存在,现在我很安定,扎根在了一个地方。但我感觉自己再也不存在了"。(发布里奇奥的开场白)
发布里奇奥:"我不会用这一刻和别的任何东西交换,即使它消逝了,我也不在乎,我会原谅它。"
吉娜:"我不像你,我不勇敢,我是个胆小鬼。你绝对猜不到我想怎么样。我希望所有东西都不会动,一切就像一幅画一样的静止,我们在其中也同样静如止水。"
ynopsis里说这是一部柔和政治意识的影片,的确,只是政治的变动不过充当了背景和隐喻而已,总体而言,我还是觉得这是部爱情片。或者用《镜》的话讲,这是一个没有弑父的Oedipus的故事。
喜欢管风琴演奏的配乐,尤其是结尾处把吉娜压抑的情感通过起伏的旋律表现出来。和捷克电影Toubled Water里管风琴的作用有着异曲同工之妙。
《革命前夕》影评(四):痛苦/历史/永恒
看完感触最深的地方:两个场景,两段对话,结尾。 【场景一】吉娜和法布里奇奥在阿戈斯蒂诺葬礼上,吉娜的独白(大段镜头直接推到脸上,很有戏剧感),感受最深的是吉娜的不被认同感和没有回应的无力感,其中台词:我认为死亡同时最具生命力; 【场景二】在去老师家时,对面楼上小女孩一直在唱童谣:露西亚编织着亚麻,变成纸张见到了小丑!小丑又跳又闹。根本无视了吉娜问话甚至最后哭着叫停下的诉求;这两段我直觉上认为是吉娜的痛苦根本没有人在意。 【对话一】在老师凯撒家里,讲了人是不能改变的但历史可以,于是有了小故事:智者让年轻人舀水,年轻人经过了一生回来智者却问他舀水怎么等了一下午(象征了时间的永恒性,我强烈怀疑贝托鲁奇是黑塞的粉丝,简直和玻璃球游戏最后《印度传记》故事一模一样); 【对话二】在革命浪潮开始的情况下,无产阶级开始用暴力推翻政权,法布里奇奥和凯撒的对话:对资产阶级来说,意识形态只是假期!我认为自己经历了多年革命,在革命之前我就经历了很多,因为这总是在革命之前。 【结尾】意大利家族式婚姻场景的大合欢,却让我冥冥中想到吉娜和法布里奇奥其实就象征了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虽然相爱甚至能用暴力改写一些秩序,但永远改不了历史
《革命前夕》影评(五):空想的革命与扭曲的爱情
不管你喜不喜欢Bernardo Bertolucci的这部电影,你都不得不佩服他在构图,摄影,配乐方面的天才!他使整部电影都笼罩在如迷梦一般的气氛之中。(要知道,这只是他拍摄的第二部电影)
其实影片的风格很“百搭”,你能看出(当时)“法国新浪潮”对于Bertolucci的影响。你也能感受到影片的戏剧性之强,强到你能把它看作是一部典型的好莱坞电影。
再谈一谈影片中的主题——“革命与爱情”。
男主角是一个“社会主义者”,但他只是一个“空想社会主义者”,过着典型的“上层人”的生活,空谈着什么“阶级与压迫”。
女主角也就是男主角的阿姨,(也是对方的“情人”),物质生活相当富足,精神上却感到空虚与无望,(也是典型的,在 Bertolucci心目中的“上层人”)
影片就在这样如乱麻一般的线索中行进着,直到最后男主角和“门当户对”的女友结了婚,一首关于(乱伦)之爱的赞歌最后变成了“挽歌”。
直到影片结束,我也没有看出来,导演在影片中明确表达了他对于他所拍摄的这个故事的道德和政治立场。(和他后来拍摄许多影片一样,比如《梦想家》)。
顺便说一句,这也是我并不十分喜欢他的作品的原因。
《革命前夕》影评(六):迷茫的愤怒
作为贝托鲁奇的第二部作品,无论从故事内核还是电影形式来看,都深深的打上了专属于贝托鲁奇的烙印。记得菲利普.加瑞尔的《平凡情人》中女主对着镜头说出了“《革命前夕》,贝托鲁奇。”的字眼。贝托鲁奇的电影总是少不了政治元素,比如《同流者》里的法西斯主义与反法西斯主义。而作为共产主义者的贝托鲁奇,更是让《戏梦巴黎》里的房间充斥着毛爷爷元素。在《巴黎最后的探戈》里将萨特,波伏娃,加缪的海报贴在了墙上。而《革命前夕》在某种程度上与《戏梦巴黎》有相似之处。崇尚革命的共产主义青年,对这个被资本主义异化,被文化商品洗脑控制,被价值输出单向化的时代宣泄着不满。同时,又沉迷于情爱和欲望里无法自拔,在愤怒中迷茫,在反抗中变得虚无。这并不是某个时期特有的人群,而是任何时代都有。
影片中有大量的人物独白,尤其是前半段阿姨吉娜的角色,她悲伤,孤独,不断表达着自己的状态,疑惑,观点等等,像极了《广岛之恋》里那位来自法国的悲伤女人。法布里吉奥作为一个中产阶级出身的共产主义者,在整日批判着资产阶级的同时又享受着资产阶级的生活,所以他的迷茫是注定的。他的好友阿戈斯蒂诺因为资产阶级身份和无产阶级立场的割裂带来的困惑与迷茫让他最终选择了死在冰冷的河水中。而法布里吉奥则在纠结与迷茫中选择了妥协。影片中有大量他与阿姨乱伦的镜头,大量脸部特写将角色的情绪通过镜头放大,增加了情绪渲染力和代入感。这场禁忌之恋如同一场反叛,反抗世俗道德,这比反抗意识形态要容易许多。印象最深的是法布里吉奥和影迷朋友去电影院看了戈达尔的《女人就是女人》后坐在街边聊起了电影。朋友对电影侃侃而谈:在1964年,没什么东西比《夜长梦多》这部电影带来更好的感觉。电影是一个时尚的问题,时尚是一种道德问题。推拉镜头是一种时尚,尼古拉斯.雷拍摄的360度推拉镜头是最高的道德时刻之一。360度的推拉镜头,360度的道德。(在《同流者》中,贝托鲁奇使用了不少推拉镜头,尤其是马切罗和教授的妻子在房间里对话调情时的一个推拉镜头腔调十足)然而面对朋友的侃侃而谈,法布里吉奥只想赶快奔向阿姨的怀抱。两人在房间里亲热,游走,在床上闲谈嬉戏,丝滑的镜头配合着音乐在狭小的空间里穿梭,这也是贝托鲁奇的招牌,并且在《戏梦巴黎》中演绎到了极致。最后法布里吉奥娶了一个和自己门当户对的女人,这也可以看作是他彻底的妥协,之于革命,之于爱情。
《革命前夕》影评(七):九月:谁知道我们秋天的时候会在什么地方
许多事情注定要发生,我注定得承受痛苦,你注定要饱受折磨,我存在是因为你的存在,现在我很安定,扎根在了一个地方,但我感觉自己再也不存在了。
——题记
我知道你会离开,我的世界因没有你而从此暗淡,只因为你的存在,让我找到了生存下去的理由——现在,一切都过去了,就好像你从来没有出现过一样。
帕尔玛的天空依然阴霾,蒙蒙细雨下,我追逐着你的背影——那逐渐消失的一道光线。没有人能够理解我们相爱的那段日子,因为已经完全抛开了道德的樊篱。第一次见到你是在三年前的一次葬礼上,那时,我们并没有过多的交谈,你回米兰的时候,也没有向我告别。
日子就这样过去,我和我的朋友一样快乐的生活着,我们谈论政治,看着戈达尔和阿伦雷柰的电影,由于我出身资产阶级,在很多事情上都受到了阻碍。我也时常痛恨自己的出身,那天,我的一个朋友跳河自杀了,那天,也是你再次来到我家的日子。
我应该叫你阿姨,你是我远方的表亲,你的眼神那样的妩媚,我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就爱上了你,其实从一开始我就知道,结局也已注定。
和你在一起的那段日子,你像是花季少女般充满活力,时而娇艳动人,时而又若有所思。人世间最美好的时光莫过于和爱人朝朝暮暮,如影随形,但你却从来不曾开口说过我爱你。
我还是你的法布里奇奥吗?那个只属于你的亚历山大,曾经的日子已经远去,我知道自己对你不起,家族的压力,使我不得不娶一个贵族少女,她很单纯,也很美丽,但是却不能替代你在我心。
你的眼泪晶莹剔透的挥洒在空气之中,那蕴含了你眼泪的空气自此变得凝重,我的呼吸已不能自已。
还是想再见你一面我的爱人,我想让你在我的怀抱中说声我爱你,哪怕仅此一回,但我知道,有些事情无法说清。
意大利导演贝托鲁奇在重返家乡帕尔玛后首次拍摄了一部充满政治意识的作品,你可以从片中看到游行的人们,还可以看到那些热血青年在革命前夕梦想照进现实的困惑。法布里奇奥就是这样的一个青年,他和朋友谈论革命,在一次相遇中爱上了自己的姨母,在承受道德和爱情的双重压迫下,他终于逃脱不了现实的窠臼,和一个自己并不喜欢的女孩结婚。
就像很多上世纪六十年代的电影一样,贝托鲁奇营造了一场在政治形势下充满柔情的影片。一场黑暗到来前的黎明、狂风暴雨尚未来临的宁静,伴随着忧伤的小提琴,甜蜜的日子也落下了帷幕。
开头男主角大段的内心独白,以及机位的变换推移,这种叙事方法让我想到了阿伦雷柰的《广岛之恋》,两部作品上映的时间只相差6年,很像是一部模仿之作,又或许说是贝托鲁奇对阿式电影的一种新的理解?我也说不太准。这部电影唯一让我遗憾的是影片的结尾处,我认为他可以处理得更好一些,结尾有些仓促,虽然看起来有首尾呼应的效果,但是我总是觉得衔接的有些不自然,影片中着重泼墨于法布里奇奥和他的姨母身上,而那个只在影片开头和结尾出现的法布里奇奥的未婚妻,给予的戏份太少了,情结的缺失,往往会造成观众在影片理解上的障碍,反正让我总是有一种牵强附会的感觉。
最后说一下我给这篇文章起的题目,那是源自于影片中的一句台词,我想多少能够体现出当时那些有志青年的惆怅与迷惘的心态吧。
《革命前夕》影评(八):《革命前夕》:谁会在熟睡中醒来
原文地址: http://www.qh505.com/blog/post/5768.html
一切终结于一场婚礼:法布里奇奥和那个“单纯”的女孩结婚了;喜庆的现场吉娜流着泪吻着那些孩子;老人和孩子、男人和女人都在自己既定的生活轨道里——法布里奇奥说:“意识形态就是假期。”吉娜说:“现在是结束的时候。”当他们完整地拥有了一种现实的秩序,是完成了一场走向新世界的革命?还是解构了一次没有暴力出现的虚构革命?
而在回归现有秩序的婚礼之外,为什么凯撒还在给孩子们讲解《白鲸》?一个呼唤自由的人,一个批判法西斯的人,一个在“解放日”书写着意大利革命历史的人,是不是在现场之外还在构建着革命?两种场景被分隔开来,是“革命前夕”的迷失和革命之中的持续,未来将走向哪里?秩序怎么建立?在一个被终结的电影里,其实革命也成为了一个没有答案的词:它已经发生,它正在发生,它将要发生,而其实,它似乎永远没有发生,因为,“响起的钟声飘荡过整个过城市,他们睡得很熟。”
“他们睡得很熟,这真是一个丑闻。”字幕写在那里:“许多事情注定得发生,我注定得承受痛苦,你注定得饱受折磨。我存在是因为你的存在,现在我很安定,扎根在了一个地方。但我感觉自己再也不存在了。”法布里奇奥的开场白,在距离那场婚礼还遥遥无期的时候,他说到了“我”,说到了“你”,说到了存在,一种人称的关联只趋向于建立“我们”的关系:是因为我承受了痛苦,所以你必须饱受折磨;是因为你存在,所以我存在,但是,当“我感觉自己再也不存在了”,那个你是不是也早已经不存在了?“我们”其实从来没有机会结合在一起,就像最后在威尔第的歌剧《麦克白》演出的仪式现场,吉娜坐在底下的座位上,法布里奇奥和未婚妻坐在上面的包厢了,他们的眼神交汇在那里,但根本不是建立“我们”的一种形式——当法布里奇奥再次寻找吉娜的时候,座位上已经空空如也;当他也离开包厢,在大厅里遇到了吉娜,“她是我需要的单纯。”法布里奇奥说,而吉娜却对他说:“我讨厌威尔第。”需要和讨厌已经将他们分开成彼此独立的“我”和“你”;即使法布里奇奥问吉娜:“你比人个人都理解我,你现在还爱我吗?”在一个不需要答案的世界里,“我们”注定会成为分道而行的人。
许多事情注定要发生,但是在革命前夕,“我们”早就变成了熟睡的“他们”,变成了丑闻中的他们,甚至这个“他们”在一个人辗转反侧、一个人孤枕难眠中也被解构成彼此没有关联的个体,熟睡而假装醒来,即使遮盖了丑闻,也再也听不到响起的钟声,如此,“革命”也再也不会发生,“我认为自己经历了多年革命,在革命之前我就经历了很多,因为这总是在革命之前。”革命前夕,不是等待革命,不是需要革命,而是在革命到来之前,“我们”已经不存在了,“他们”早已经在丑闻式的熟睡中,整个世界或许只有凯撒还在那里讲述者革命英雄主义的《白鲸》,还在期待着一场轰轰烈烈的暴力革命。
为什么会熟睡?为什么不会醒来?为什么不会成为“我们”?塔列朗的引语似乎解析了为什么革命会在革命前夕覆灭,“那些没有生活在革命爆发前的那个年代的人,无法理解生活是多么甜蜜。”革命前夕,只有生活在这个时代,才会感觉到生活的甜蜜——这是一个悖论,当生活得如此甜蜜,怎么还需要革命?既然不需要革命,革命前夕的时代就是历史中的一个虚位,它不提供革命的必然性意义。法布里奇奥是生活甜蜜的男人?吉娜是生活甜蜜的女人?“我们”是生活甜蜜的男人和女人?在“意识形态只是假期”的世界里,在革命前夕放弃革命或许就是一种甜蜜的生活,所以熟睡而听不到钟声,所以在没有暴力的现实中走向一场婚礼,所以在爱情还存在的时候分道而行。
但是,在革命前夕,他们却感受到了一种死亡,法布里奇奥的朋友阿戈斯蒂诺无疑是需要革命的人,无疑是不熟睡的人,他被学校开除,他离家出走,他骑着自行车,摔倒在那里,“这一次是为了我父亲。”再次摔倒,“这一次是为了我母亲。”第三次摔倒,“这一次是为了我。”摔倒就像是行为艺术,他是想要和这个让他痛苦和备受折磨的世界告别,所以在那条河流里,“这是我第一次游泳”的他在冷水中死去,当这一种死亡被命名为“自杀”,是不是一个无产者的行为艺术?“我和自己斗争,我只能逃避。”逃避而选择自杀,是另一个自己杀死了自己,也是自己想要杀死活在革命前夕的这个时代,以及活在甜蜜生活中的人。他骑着自行车,法布里奇奥说:“我的父母是个贼,他们是愚蠢的人。”阿戈斯蒂诺问他:“你有什么资格评判他人?”
阿戈斯蒂诺死了,在连续三次摔跤而以行为艺术的方式杀死了自己,是走向了和法布里奇奥相反的路,不评判他人,却以自死的方式评判了自己。而法布里奇奥呢?似乎永远在评判他人的行为中为自己辩护。而吉娜呢?一个“传播思想、玩三角关系、一天洗三次澡”的女人,一个带着米兰时尚生活的女人,是不是也是生活在革命前夕的甜蜜中?她不像阿戈斯蒂诺是个无产者,是个自戕而寻找解脱的人,当然她也不是如法布里奇奥那样评判他人的人,“我不喜欢成年人,甚至不喜欢我自己。”她否定了自己,是因为在她看来,“只有一个办法能治愈我的痛苦,那就是别人。”她以别人为参照物寻找生活的意义,当他人成为自己的背景,当寻找他人为自己解除痛苦,这个所谓的自我也是虚无。
“吃和听到吃,像是吃了两遍。”这就是吉娜的生活,吃和听到吃,是站在自己和别人立场不同的生活,而有时候“听到吃”却解构了“吃”本身。她和法布里奇奥是一种亲戚关系,但是当这种亲戚逐渐变成所谓的爱,是不是用“别人”构筑了一个虚拟的自己——在乱伦的世界里,甜蜜一定是痛苦,选择就是逃避。她摸着自己的身体,像是“别人”在抚摸着自己,像是“别人”制造着甜蜜”;然后她吻着法布里奇奥,让他压在自己身上,是因为她在寻找一种“别人”建立的秩序,而一切都是为了逃避,“我在不属于自我的房间里,它太空了, 我感觉害怕。”只有在“别人”的世界里,她才能感觉到不害怕,才能感觉到自己的存在。
一个异化的资产阶级?当那个自我被否定了,那个“别人”一定会制造另外的痛苦:在阿戈斯蒂诺的葬礼上,她对法布里奇奥说:“认为死亡同时最具生命力,我常常梦见自己的死,现实太残酷了。”梦里她参加了葬礼,但是没有穿黑衣服,这是一种不在场,逃避现实进入梦境,却还是以不在场的方式看见自己的死;小女孩伊芙琳娜被父母关在楼上,吉娜看见从树上爬下来的她,伊芙琳娜对着她唱起童谣:“露西亚编织着亚麻,变成纸张见到了小丑!小丑又跳又闹。”一遍又一遍,吉娜疯狂地喊道:“停下!”但似乎无济于事,是“别人”的伊芙琳娜根本不在意她的呼喊;她找了一个富有的男人卡洛儿,被法布里奇奥看见,或者她故意让法布里奇奥看见,当法布里奇奥生气,“你现在自由了。”他说,而对于吉娜来说,无非是寻找到一个“别人”:“他对我就像对待妓女一样,他打我是对的,因为我要接受惩罚,如果发生火灾,发生战争,一切都是因为我。”一个“讨厌他们,讨厌孩子,讨厌家人”的女人,在空虚的世界里只能如此解构自我;最后她“爱上”了一个失去了私有财产的男人,男人的地产被抵押了,那个隆巴多池塘被抵押了,“他们会带着机器来到这里,这就是生命结束和幸存者开始生活的地方。”当资产阶级失去了财产,作为吉娜是不是可以在“别人”的世界里成为无产者?这一种爱的名义还是在逃避现实,还是在制造虚无。
阿戈斯蒂诺和吉娜,代表着友情和爱情?代表着自我之死和“别人”之死?那么,当法布里奇奥走在革命前夕的时候,他所想要存在的那个“你”又是谁?一个诅咒资产阶级不信耶稣人,一个说教堂成了国家无情心脏的人,一个骂父母是贼的人,一个谴责天主教扼杀了自由的人,似乎就站在了革命前夕,似乎就需要一场彻底的革命,他把阿戈斯蒂诺看成是牺牲,他把吉娜看成是自由,但是对于自己呢?永远迷失在寻找中。他和吉娜有一次看一部“电影”仿佛就是法布里奇奥生活的那个分裂世界。黑白的影像里,突然就出现了彩色的画面,而画面中的人就是法布里奇奥,他从街上走过来爬到了墙上,然后在墙上行走。观者是吉娜,一个需要“别人”解除自己痛苦的人,当她看见那彩色的世界,就如进入到和现实完全不同的世界,就如在“听到吃”的感觉中不需要吃的生活,但是在彩色世界里,法布里奇奥是制造者,也是在场者,但是这个在场却成为一种虚构:他在场,最后却从画面中失踪了;这是1962年复活节前夕,但是彩色世界里却是树叶泛黄的秋天。
为什么黑白世界会有彩色的场景?一种颠覆就是一种革命,而这种革命就是熟睡者的自我呓语,是将自己作为在场者的虚构,“你喜欢这部电影吗?”他问吉娜,就像爱上吉娜一样,法布里奇奥就是在这样的虚构中寻找革命的意义,当吉娜和卡尔罗在一起,法布里奇奥和朋友去看了一场电影:戈达尔的《女人就是女人》,一种影像化的革命实践,法布里奇奥看完之后对朋友说:“电影是一个时尚问题,时尚是一种道德问题。”他把电影看成是一种时尚,却把时尚看成是一种道德,所以他批判电影就像批判道德:“我无法忍受这些电影。”所以他批判革命,“人们盲目地接受一些东西,这让我害怕。一天的革命是没有用的,我需要一个新人,一个新世界。”所以当把革命的电影看成是道德问题,当把“意识形态”看成是假期,他只能进入到自己的那个彩色世界里,成为自我革命者。但自我革命的彩色世界又必须让他人观看,所谓的爱情,所谓的阶级,所谓的社会,所谓的宗教,在批判中才能证明一种革命性,而当这样的革命性成为自我的游戏,在革命前夕经历了诸多的革命,也其实是一种熟睡的状态。所以在法布里奇奥的革命观里,创造一种新秩序最后还是变成了“她是我需要的单纯”的小资产阶级的生活,这不是一天的革命,当然这也不是真正的革命,而对吉娜说的那句“只有你能理解我”又让自己在迷失中标注了一个看不见革命真正意义的“丑闻”。
革命前夕,有阿戈斯蒂诺作为牺牲者的自我戕害,有吉娜作为虚无主义者的自我逃避,有法布里奇奥渴望建立新秩序的自我迷失,他们都是在熟睡状态中,看见了革命的影子。但是当这一切都远离了真正革命,凯撒是不是就是一个成长起来的革命者?他用理论抨击意大利现实,他认为自己的理论不被人理解,他渴望人们找到世界的精神性意义,但是当吉娜要离开帕尔马去往米兰的时候,他跟在她的身后为她提包——当他说“人在特定环境下创造历史”,实际上他还只是一个等待者:等待者机会,等待着特定环境,在盲从的世界里,或许他只能用革命英雄主义的《白鲸》武装自己,一种文本,一种小说,何尝不是革命前夕如熟睡一样的虚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