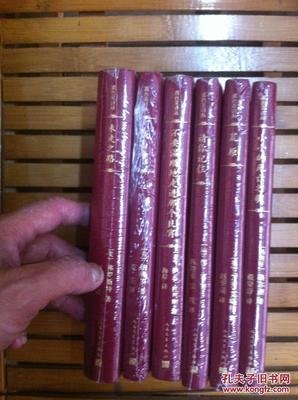
《不要温顺地走进那个良宵》是一本由[英] 狄兰·托马斯著作,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精装图书,本书定价:32.00,页数:252,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不要温顺地走进那个良宵》读后感(一):贵社需要一个处女座编辑
我读书不多,但是遇到这种排版还是头一回。
说实话,我都怀疑是不是这么排版自有深意,可是又觉得不像。
加上前面的印刷的重影,我几乎可以认定出版社赶工制作出来的劣质产品。
不多说了,上图吧。
《不要温顺地走进那个良宵》读后感(二):我觉得随意组合诗名就是一首诗了……
比如……
《很久以后》
很久以后,当我醒来
我看见夏日的男孩
我的英雄裸露他的神经
—
心的气候进程
在我缤纷的意象里
在我敲开之前、在你脸上的水
假如我被爱的抚摸撩得心醉
哦,为我打制一副面具
—
时光,像座奔跑的坟墓
当初恋从狂热趋于烦扰
在悲伤之前
请静静地躺下,安然入睡
——————
《我和时光贼子》
我渴望远离
我与睡眠作伴
我梦见自身的起源
我的世界是金字塔
—
悲伤的时光贼子
在骨头上寻肉
据说众神将捶击云层
而死亡也一统不了天下
——————
喜欢的四首
《穿过绿色茎管催动花朵的力》
《不要温顺地走进那个良宵》读后感(三):我看见时光将我谋杀
--------
这个春天掩埋一只春鸟
---------
谢天谢地
终究会存在某种必然
假如爱得不够真 那便不是爱
不断失败之后终成真
-----------
假如暧昧足矣 甜蜜的谎言足矣
空洞的言语就能承受所有的苦难
并治愈我的伤痛
------------
像春天在邪恶中碎裂 骨骼敲碎四月
--------------
此生未知的一切最为安全
-----------
我不能像白痴一样
谋杀季节和阳光 优雅和女孩 我也不能压抑美妙的苏醒
-----------
时光残酷的杀死我
“时间不会谋杀你”上帝说“绿色的虚无也不会受到伤害谁能砍去你未曾吮吸的心 绿色 不生不灭”
我看见时光将我谋杀
---------------------
有一个女孩疯如鸟
死尸般逍遥自在
她睡在狭小的料槽 还漫游于尘埃
我也许一定得
忍受最初的幻影 去点燃万千的星云
《不要温顺地走进那个良宵》读后感(四):如果真是这样,我会不屑死去!
《序诗》
挽着云彩的渔夫,跪向
落日下的渔网 . 在上帝加速夏日消亡之际
涛涛洪水此刻如花盛开
《一旦晨曦不再驻留》
醒来吧,我的沉睡者,迎着阳光,
小镇早起忙碌的劳动者,
离别在此醉生梦死的马屁精;
光的栅栏大片坍塌,
除了敏捷的骑手,人人都被摔下,
而世界悬挂在树梢。
《在你脸上的水》
你的床笫将铺满珊瑚,
你的潮汐将游动起蛇群,
直到大海所有的信念消逝。
《是否有过这样的时候》
是否有过这样的时候,在这儿童乐园
他们伴琴声跳舞可解内心的烦忧?
曾经有过这样的时候,他们看书落泪,
时光却让蛆虫留意他们的踪迹。
苍穹荧光下,他们身处险境。
此生未知的一切最为安全。
空中广告牌下,失去臂膀的人
有双最干净的手,正如无情的幽灵
未读不受伤害,盲人的眼看得最真切。
《一旦灯笼闪亮》
我在公园玩耍时抛出的球
始终没有落地
《我渴望远离》
如果真是这样,我会不屑死去;
《二十四年》
我红色的血管灌满金钱,
朝着小镇最后的方向
我昂首前行,直至永远
《羊齿山》
哦,我蒙受他的恩宠,年轻又飘逸,
时光赐我青春与死亡
尽管我戴着镣铐依旧像大海一样歌唱。
《不要温顺地走进那个良宵》读后感(五):疯狂狄兰的向死而生
英国评论家乔治·麦克白斯在论及狄兰·托马斯的诗时,不无感慨地说,“仿佛经常是那些最难懂的诗最容易给人模仿。”这里涉及到两类诗,一种是“难懂而好”的诗,一种则是“难懂而不好的诗”。毫无疑问,文学史已经证明,狄兰的诗章属于前者。
年轻时代的狄兰托马斯狄兰·托马斯(Dylan Thomas,1914—1953),二十世纪英国著名诗人,浪漫主义、超现实主义的伟大诗歌创作者。他的诗句常常围绕生与死展开,精致如光而热烈如酒。他往往于大醉之后以梦幻与非理性的文笔,颠覆了传统语言与客观事物之间的界限, 用诗歌代替呐喊,向生死爱欲等一系列哲学本质命题发出呐喊。1935年夏,他和另一个诗人杰奥弗雷·格力克森在波尼格尔共度假期,他们戏仿诗人华兹华斯的方式,向群山高喊 : “ 我们就是死者!” 。可不久,这种向死亡挑战的欢悦,变成了关于死亡的沉思苦想 , 诗人无法把它解脱,从此成为诗人创作的拐点。他之后创作出来一系列向“死亡”挑战的诗歌,如《而死亡必不可称霸》和那首著名的《不要温和地走进那个良夜》,这首写给病危中的父亲的诗,极具震撼力,怒斥光明的消逝也意味着对死亡的抗击和不屈。
《星际穿越》里面出现了这首诗 暗指人类进入宇宙的悲壮大义。狄兰·托马斯肯定“死亡”在生活中的中心地位,因为没有对死亡的恐惧,就无法体味生之甜蜜。作为英国诗歌史由传统向现代过渡时期产生的伟大诗人,狄兰托马斯被认为“开创英美诗歌史新篇章”。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的中国文坛引起极大轰动。不幸的是,1953年11月9日,托马斯本人因连喝了18杯威士忌而暴毙,三十九岁便英年早逝,也难怪后世称其为“疯狂的狄兰”。
《不要温顺地走进那个良宵》读后感(六):咆哮,咆哮
诗集 海岸/译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2015年12月一版一印 ISBN 9787020108411
“不要温顺地走进那个良宵”。在我不了解狄兰·托马斯之前,这个题目太有诗意的诱惑了,而且让我直觉想到的,是爱情,是欲拒还休,是缱绻缠绵。可是等我用一种低沉、温和、故作深情的口吻朗读了半本之后,才迟迟地意识到错的实在荒唐——这是要用摇滚的愤怒和狂热同时又阴郁的激情来读的诗!从此我的声音越来越大,语调越来越激烈,我读他的那些欲望、读他的那些愤怒、读他的感性、读他的诗意、读他的生和死亡。
老实说,托马斯的诗是不容易懂的。他是基督教徒,诗里面有很多典故和宗教意象,外行人看不出来,看出来也不明白;另一方面,他想表达的东西是深深埋藏在他诗意的意象之下的,同时又是超脱了现实主义的深层次的潜意识的释放;可他又并非完全地超现实主义,他把这些材料用某种秩序加以遴选、加工、编排、诗化。他的诗是很别具一格的。
狄兰·托马斯有相当一部分诗琢磨琢磨,主题其实就是四个字:热爱生命。而他的这种热爱并非通过直白的赞颂,而是反过来,通过和死亡的抗争。写到这儿我忽然觉得上句话讲错了,他或许不是“热爱生命”,而是热爱这种打破桎梏的抗争。现在有必要来说说诗人本人,他就是余华所说的那种喝酒喝死的传奇人物:一九五三年十一月五日,在诗人第四次开展赴美诗歌朗诵之旅时,他连喝了十八杯威士忌导致酒精中毒,四日后在纽约暴毙,年仅三十九岁,应谶了自己早年活不久的预言。他的死亡固然是文坛和诗歌精神的一大损失,但是,这种“出格”的死亡方式对于作家的身份而言,却不能不说传奇而浪漫,太白醉酒坠湖捉月骑鲸是后人附会,但也反映了只有诗人才配得上这样传奇的死亡。如果配着他的诗来看,这种死亡则更具有神秘的魔力。
不要温顺地走进那个良宵,
老年在日暮之时应当燃烧与咆哮;
怒斥,怒斥光明的消亡。
临终时明智的人虽然懂得黑暗逍遥,
因为他们的话语已迸不出丝毫电光,
却不要温顺地走进那个良宵。
善良的人翻腾最后一浪,高呼着辉煌,
他们脆弱的善行曾在绿色港湾里跳荡,
怒斥,怒斥光明的消亡。
狂暴的人曾抓住并颂唱飞翔的太阳,
虽然为时太晚,却明了途中的哀伤,
不要温顺地走进那个良宵。
肃穆的人,临近死亡,透过炫目的视野,
失明的双眸可以像流星一样欢欣闪耀,
怒斥,怒斥光明的消亡。
而您,我的父亲,在这悲哀之巅,
此刻我求您,用热泪诅咒我,祝福我。
不要温顺地走进那个良宵。
怒斥,怒斥光明的消亡。
这首诗是托马斯在一九五一年九月为他临终的父亲所作。那个曾经被我误以为象征充满诱惑的爱情的“良宵”显然并非如此——它代表着死亡的永夜。诗人在目睹垂老的父亲被死神一步步攫入永远阴森的暗夜之时,发出了怒斥的咆哮,他并非惧怕死亡,而是不甘心向人类的永恒公敌显露自己的懦弱和屈从,他反对顺从地接受命运的无情安排,即使无法改变结局,他也要选择奋战、燃烧、怒斥,他要彰显人的力量,或者说并没有点名的那个词——“意志”。他用意志来谴责死亡的不公、追问死亡的权力来源、反抗死亡的暴政。那么他是失心疯了吗?不,他并非搞什么神秘主义的精神病病人,除了歌颂反抗精神,死亡在托马斯心中同样有所寓意。我们知道,诗人生活创作的二十世纪前半叶是一个多么恐怖的时代。他在伦敦既目睹了婴儿烧焦的尸体,也看到过百岁老人在黎明的空袭中丧身,死亡象征着那个时代强加在人类身上的不幸,象征着造成这些不幸的法西斯、政治家、战争和炮火,象征着精神所遭受的痛苦。不得不说,托马斯虽然是一个烟枪和酒鬼,但更是一位用诗作枪的战士,他拒绝了理性和忍受,他向奇异的梦境中寻找宣泄口,向绝望的命运发出怒斥的咆哮。他藐视命运(《而死亡也一统不了天下》),心怀希望(《不幸地等待死亡》),他走进那个良宵时,手里端着十八杯烈火一样的威士忌,脸上一定带着轻蔑的微笑。
当然,他的诗中同样涉及了爱、欲、信仰等永恒的主题,我所说的只是我感触最深的一面。
二〇一六年的最后一本诗集。
(2016/12/30)
《不要温顺地走进那个良宵》读后感(七):该从杜鹃声中感知春意(自存用)
尤其当十月的风
尤其当十月的风伸出寒冷的手指痛击我的发丝,
受制于蟹行的太阳,我踏着烈火而来
在地面投下一片影子,蟹一样爬行,
我站在海边,倾听群鸟的喧鸣,
倾听渡鸦咳叫在冬日的枝头
我忙碌的心一阵阵颤栗,当她
倾泻音节般的血液,倾吐她的话语。
也被关人言词之塔,我留意
地平线上树林般行走的
女人身姿喋喋不休,以及公园里
一排排孩子星星般显露。
有人让我塑造你,用发元音的山毛榉,
用橡树根须的声音,从荆棘丛生的州郡
告知你音符
有人让我塑造你,用水的言词。
在一盆羊齿草后面,摇摆的钟
告诉我时辰的讯息,神经的意图
盘旋于茎秆的花盘,在雄鸡啼晓时,
宣告早晨降临,并预报刮风的天气。
有人让我制作你,用草地的标志,
草符告诉我知晓的一切
透过目光挣脱蠕虫似的冬天。
有人让我告知你渡鸦的罪过。
尤其当十月的风
(有人让我塑造你,用秋天的字符,
蜘蛛的话语,以及威尔土喧闹的山岗)
握紧萝卜般的拳头惩处大地,
有人让我塑造你,用无情的词语。
心已耗尽,一股股疾奔的热血,
预警狂暴即刻来临。
站在海边,倾听群鸟鸣叫黑色的元音。
我与睡眠作伴
我与睡眠作伴,它在脑海亲吻我
任岁月的泪水酒落;入睡的眼睛
转向光,仿佛月亮一样开启我。
我因此调整脚跟,随着身姿飞翔,
坠入了梦境,飘向上浮的天空。
我逃离大地,赤裸着,飞越风雨,
抵达远离群星的第二重地界;
我们哭泣,我及另一个幽魂,
我母性的目光,闪烁在树梢;
我逃离那重地界,羽毛般轻盈。
“我父辈的地球叩动它的轴心歌唱。
“我们踩着的土地,也是你父辈的土地。”
“我们脚下的土地孕育成群的天使
羽翼下那些慈父的脸庞多么亲切。”
“他们不过是些梦中人。吹口气,就会消失。”
消失,我肘边的幽魂,露出母性的目光,
正如我吹拂天使,迷失于
云岸,相连每一片攫取墓穴的阴影;
我将梦中的伙伴吹回到他们的眠床
他们酣然沉睡,全然不知自己的幽魂。
随后空气中活着的万物
抬高了嗓音,而我攀上言词,
用手和毛发拼写自己的幻象,
人睡多么轻盈,在这污秽的星星
苏醒多么沉重,从那世俗的云层。
时光的阶梯向太阳生长,
每一级响彻爱或终将消逝,
寸寸跳动着男人的血液。
一位年迈疯子仍在攀缘他的阴魂,
我父辈的阴魂正在雨中攀缘。
在此春天
在此春天,星星飘浮虚无的天际;
在此乔装的寒冬,
骤降赤裸的天气;
这个夏天掩埋一只春鸟。
象征符号选自岁月
缓缓地循环四季的海岸,
秋天讲授三个季节的篝火
和四只飞鸟的音符。
我该从树林辨识夏天,而蠕虫
竟能显露冬的风暴,
或太阳的葬礼;
我该从杜鹃声中感知春意,
而蛞蝓该教会我如何去毁灭。
蠕虫比时钟更能预报夏天,
蛞蝓是时光的活日历;
如果永恒的昆虫说世界消逝,
那它又向我预示什么?
《不要温顺地走进那个良宵》读后感(八):直率的诗意
首先我要说实话,这本狄兰·托马斯的诗集我并没有全部看懂。因此你完全可以认为这篇文章是在扯淡。
《星际穿越》在国内上映后,狄兰·托马斯多了很多中国读者。那首在电影中出现的《不要温顺地走进那个良宵》也成了他最广为流传的作品。可惜读诗总是要一些诗性的,散文小说容易被人看懂,诗却不尽然。我又不愿意承认自己没有诗性,所以我宁愿相信这是在读诗方面的偏好不同导致的。
我向来以为,一个诗人的诗集总是平庸的诗作多于优秀的诗作,尤其西方诗歌在意象、审美、典故、音韵上都和中国人的诗有很大的不同,再经过一道翻译的加工,读起来就更让人陌生了(不过很多时候,外国诗的美感就来自于语境不同所带来的『陌生化』),因此一本诗集里能有几首印象深刻的就实属不易。
不过,狄兰·托马斯的风格大体上还是很容易让人接受。他的性格是比较外露的,生性奔放热情,不像一些诗人过于纤细敏感,这使得他的诗篇有着明亮的色彩和直接的表达。虽然许多人将狄兰•托马斯看作是超现实主义的诗人,但他本人却不甚赞同超现实主义那种混沌的态度,他曾说:
『他们(超现实主义者)并未塑造这些词语或按一定的秩序加以整理,在他们看来,混沌即形式和秩序。这对我而言似乎太过自以为是,超现实主义者想象从潜意识自我中随便捞出些什么,就以颜料或文字记录下来,本质上就存在一定的趣味或一定的价值。我否定这一点。诗人的一大技艺在于让人理解潜意识中浮现的东西并加以清晰地表达;才智非凡的诗人的一大重要作用就在于从潜意识纷繁的无形意象中选择那些将最符合想象目标的东西,继而写出最好的诗篇。』
秉承这一原则,狄兰·托马斯围绕生、欲、死三大主题进行创作。艺术就是这样,提纯萃取生活中最本真的事物,用最精炼的语言毫无保留的展现在你眼前。这三大主题实际上就是人生的主题,并且构成一个循环的整体,生催动着欲,欲创造生命,生的结局是死,而死又复归新生。
这样的世界观,在这本诗集中,《一个冬天的故事》给我的感触最直观:
《一个冬天的故事》不论是原作还是翻译,都是一首绝美的诗,这是一首5行×26小节的长诗,一个男人的沉默哭喊升华和一个山谷的静谧热闹复归相联系。
诗的开头两小节便充满着平滑的漂浮感,为全诗定下了宁静而流动的基调:
『 一个冬天的故事,
飞雪炫目的湖面暮色飞渡,
圣杯形的山谷浮动农庄大片的原野,
雪花迭现的手心无声无息地滑过
秘密航行中牛群苍白的呼吸,
『 星星漠然陨落,
雪中透着干草的气味,远处的山坳
传来猫头鹰的哀鸣,冰冷的货舱
运载农家的牛群冒出羊白色的雾气,
在这河流交叉的山谷,故事就此开始。』
在安详的宁静岁月里,一个不被外界打扰的山谷,按照自己的时刻运作着。最初是静谧,暮色渡过令人眩目的湖面,雪花在空气中飞舞。沉睡的山谷渐渐苏醒,早起忙碌的人们迈出家门,苏醒的村庄变得沸腾。
一个男人点燃心火,走出家门寻找失落爱人的踪迹。随即鸟群在水域觅食,飞雪挟带着露珠的声音和落叶一起歌唱。当男人屈首哀嚎,迷失在被风雪埋葬的爱情中时,一名舞者还在白色的草地上恣意放纵。沸腾的村庄开始狂欢,烤肉发出滋滋的声响,岩画上的图腾随着号角舞动,雌鸟振翅飞过高耸的山林。
周围的一切将男人抛弃一般,『热闹是他们的,我什么也没有』,打着旋的风雪从他身边掠过,膨胀的马群踏过围场,所有事物竭尽所能地舞动着,达到高潮。
衣衫褴褛的诗人独自走向岁月的终点,在长途跋涉后的恍惚中,他看到他的新娘。黑色的鸟群缓缓降落归巢,温暖的篝火逐渐熄灭,成片的飞雪开始碎裂。山谷的狂欢被春天掩埋,群山回响起圣歌,男人与他的新娘在世间旋转,到达圣洁的天堂。
这个境地的繁华与他的生似乎没有关系,平静却与他的死息息相关。可是仔细想一想,男人就像是这个精巧的山谷八音盒里的发条,所有的一切都围绕他转动,你看不见,但是整个村落的兴衰都由他牵动,所有的景都是他情感流动和喷发的背景,山谷最沸腾之时就是男人情绪最喷薄之时,当他完成升华人世间的一切也就落下帷幕,世间再也没有比这更协调自然的事了。全诗被强烈的对比和统一贯穿,所有的风景和人成为一个妙不可言的整体,像是一个风雪球里发生的故事。
另一方面,整个由平静到喧腾最后复归的过程,颇象征着人的一生。狄兰·托马斯向来喜欢以生死欲望作为主题,《一个冬天的故事》也不例外。相比他其他那些单写一个主题,或者几个主题相对独立的诗作来说,《一个冬天的故事》的走向更加清晰,一眼就能够看出来,这些新生、繁育、衰落、死亡的过程就在这一个小小的风雪球里发生。
从生到死,继而获得新生,这样的轮回在现实中怕是要经历不短的时光,而如此宏大的内涵,却被狄兰·托马斯空前凝缩在130行的小诗里,时间不过一天,空间不过“圣杯形”的山谷中。在如此微小的时空里,生死兴衰完成了一次交替。这首纯净的诗,像一颗高纯度的白水晶,蕴集了人生的智慧,甚至于因为太过浓缩,而让人心惊。
这种感觉,有些像王维《辛夷坞》中那句:『涧户寂无人,纷纷开且落』。一种命定的自然规律,在字里行间体现出来,因为超越了普通人的时间感受,而特别的具有宗教感和悲剧性。
除此之外,狄兰·托马斯还有许多值得慢慢品读的作品:
《十月献诗》以旁观者的视角,随气流的变化游览乡村风景。节奏清新自然,叙述缓缓铺开,像一幅宁静悠远的田园画。
《祈祷者的对话》以临终女人的丈夫和儿子,两个男人的心情作对比,让人想起中国千年前杜甫那首《月夜》:『遥怜小儿女,未解忆长安』。
《在白色巨人的大腿间》则直露的表达对生的渴望,对大地的赞美和感激,为原始的爱和欲歌唱,同时融入了对自然的赞颂和关怀。其他表达此类主题的还有《穿过绿色茎管催动花朵的力》《我看见夏日的男孩》等等,风格都是明快活泼,读起来即使有些微忧伤,但仍能看见日光倾城。
最后,愿各位在消极失望或困苦之时,都能『不要温顺地走进那个良宵』,只管去『怒斥,怒斥光明的消亡』。
:这一版的封面设计非常的有逼格,红色烫金压花磨毛布,仿佛自己在读一本非常有格调的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