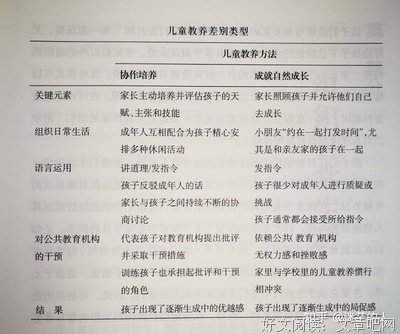
《比萨诗章》是一本由[美] 埃兹拉·庞德著作,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的平装图书,本书定价:36.00,页数:272,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比萨诗章》精选点评:
●庞征博引。最后一章里的一句“To be men not destroyers”作为全人类的墓志铭再适合不过。
●政治不正确的背后隐藏着浪漫主义价值体系,比艾略特更为纯粹,才华也更渊博,布考斯基一段时期的偶像,称其为“伟大的诗人”。
●庞德很像是“维基百科”时代以前的词语处理机,也就是台自动作诗的电脑。审美上驱逐了“美国”,他的词源更偏爱欧洲和东方趣味,这种对创造的模仿的放大法和肆意阐释,形成了其庞大的“花架子”。有点可惜,谢阁兰死的太早了……
●译者校对版,可惜不是精装。
●看得很晕 真的!
●对不起,我尽力了
●看的时候觉得庞德很爱女人啊,愿我得他一份风流韵致,私下想把这翻译成比萨诗卷,书写在中国古老的竹卷上,滚动着打开,让那些古老或现代的时间与空间展现在读者面前,才是阅读庞德诗歌的正确模式,让庞德塑造的蕴含了风雨的宝石一般的诗歌放出光彩,另外,爱极了庞德关于晶体还有铁粉玫瑰的概念,非常浪漫非常温柔,令人为之心醉
●军训太适合读狱中写就的诗歌了,庞德写得破碎、意象交叠,絮絮地叨念着那些传说、他走过的每个地方、中国的方块字,而其中不乏闪光的句子。 “在六座绞架下/宽恕,请宽恕我们所有的人”
●庞德太难读。他的诗太过丰富,读起来就一点也不轻松,像是在啃一块硬骨头。整个读下来,并不清楚知道他的主题。也许没有主题吧。他用自己独特的语言,节奏,意象,来诉说着他对这个世界的悲伤,自己的破碎。希望他的诗可以有全集。这样零零碎碎地读,无法深入他。
●学会东方用典的庞德,唯希腊词条的一如既往地炫技,诗,我们都知道,不可承受太多
《比萨诗章》读后感(一):救世主和阶下囚
“做男人,不做破坏者。”
这是美国诗人伊兹拉·庞德设想作为他的巨作《诗章》最后一行的诗句。然而具有戏剧性的是,庞德在二战期间乃至毕生的近法西斯行为,于世界看来就是一种破坏行为,他也可能成为一个别人眼中的“破坏者”,而非“男人”。
然而抛开他的经济学和政治学上的偏执想法,他在《比萨诗章》中是“男人”,却是极其复杂的“男人”。
“天堂不是人造的,地狱也不是人造的”
“高贵的岛屿/诅咒那些以武力征服的人/那些以势力为唯一权利的人。”
“正义的和平并不一定/会消除未来的战争”
他是诗里的救世主,慈悲于天下众生,高傲地自认为货币政策、银行存在的权利应由他决定。
“军队用语包括差不多48个词/一个动词和分词,一个名词 屎/一个形容词,一个无性别的词组/作为某种代词/从看守的棍子到妖妇或淑女”
“只有影子进入我的帐篷/当人们从我和日落间走过”
他也是诗里的阶下囚,同现实一样,失去自由而产生的失落、卑微感从每个字挥散开来,像初生的牛犊因碰壁而疯癫胡闹。
庞德的《诗章》不仅仅将东西方文明的精粹包含其中,也将个人的品性和经历写入并进行一定的神化。拥有拜伦式英雄,又拥有艾略特式小人物,矛盾因激烈反抗和虚无堕落而从诗句中涌出。
包罗万象和纹路清晰,正如同救世主和阶下囚同时存在于一具躯体,两者贯穿《比萨诗章》,造就其独特的伟大。从希腊神话、古罗马神话到中国古典哲学、世界文化人物,再到现实世界的建筑、店铺、食物和记忆深处的遭遇。难以想象,一个凡人企图以几十年时间,写出一首长诗,将几千年的世界文明复刻其上。
《比萨诗章》读后感(二):纷繁而隐蔽
比萨之笼与诗页比萨之塔,映现于庞德的囚笼远处,蓝天被铁栏分割,而混凝土冰冷坚硬且潮湿,隐约的远山时常闪现它神圣的光芒——如果要说,诗人的境遇亦即这诗文的场景。
翻尽诗集的表面,磅礴的庞德,纷繁的庞德,在立锥之地搭建起记忆之台和诗之高塔。古老的传说、陌生的语言、阅读的经验、历经的故事、思绪的幻景,结合他现实的执念全部融于一炉,因此时常,我找不见进入它的通道,只能瞥见那些闪光,而其每个侧面总是令人疑惑。
庞德常常写出对高利贷、资本社会之鄙夷与批判,这些内容反复的出现,甚至让我有种他以此立诗的感觉,他也的确积极地仰慕着政治生活的活动者们。事实上,翻过这些内容,其他的部分占去了更大的空间。但是,无论从形式上还是从实际内容上,它们都太散,太不连续,像长长的火车搭载无数的不同的人,行驶于纸面,如果只是去巡视,那排排而来的文字大概让我觉得单调。偶尔那其中的人站到窗前,与我的经验连接起来时,我便感到这火车的内里纷飞的各式时间。
或者,让诗句本身成为一种单纯的流动——无限的印象,像花瓣之雨落在读者的口舌与眼睛里,即使一无所知,新的朦胧的知觉在诗人的反复提及下却会以新的起点走上前来。
译者在后记强调了注释的重要性,确乎如此,注释显示出细节,一定程度上构建了诗歌之塔,它们本身搭载的记忆、观念、象征是诗歌的一部分,即诗歌的“未完成”。尽管如此,对许多诗文,我仍然难参其奥,他仅仅给出形象,而形象对于读者之陌生,要靠读者全然用耐心——学术的或者爱好者的——去给出解读。如果我不愿仅仅满足于诗文之闪光和诗文之表情,我便必须如此。而我显然没有在这种方式上探出多远。
开始读庞德有一方面是因为想看看中文在他身上造成的投影。结果如我所料,仅仅是一个侧面的投影。中文使用者在他的文本面前并无优势。说意象,其堆叠与组合,其不连续性,这似乎是中国诗习以为常拿来言迩意遐的基本模式,但庞德堆叠他的意象,依靠的完全是他新创的逻辑,加上典故、形象的陌生,本身便不是在汉语文化语境下,他立足的真真切切就是西方古典的东西,他以此为基点辅助以东方的一些东西。这给我一个感觉,他对汉语汉字、东方故事的解读是纯粹以自己的观点去进行的,有些的确切中要点,另一些他也只是作为诗歌的结构部件在使用,由此他的诗歌陌生化、隐晦化,在那似有似无的东方意蕴中,他把我看不透的什么藏在了里面。
至于“新”,就“新”而言,他如此构建语言,的确能最好地实现更新这件事情。但如布洛茨基怀疑的,是否真正地被更新了,却是值得追问的。
庞德到老年仍旧挂记着墨索里尼。他追悔往事,追问过去,仍旧没有放下对墨索里尼的认同。诗章第一百十六章是出色的一章,他的诗章,我认为大概在其中写明白了。
无论我是认同他,质疑他,从诗句中得到感受、被诗句拒绝,庞德对我来说无疑是个神奇的人。又如艾略特在《荒原》题词所言,是“高明的匠师”。在他自己心中,他大概像他的句子:
A little light,like a rushlight《比萨诗章》整体分割性的长诗,阅读起来,其体验是独特的。它更晦涩,更纷乱,它似成整体,也不是《嚎叫》那样全然的疯狂幻象,它让我猜不出边界,根本上说仍旧是平静向内的。诗文本身,等待更多人的解答,需要更多高明的读者,我看我自己,愚钝有余,勤奋不足,想来诗文是不能在我之上更多地显现了。不明其所指,观其所往。
愿诗文能为更多人所“顯”。
《比萨诗章》读后感(三):你说呢?艾略特
题目是诗人提及艾略特我觉得很好笑的梗,里面针对这些谈及的想法就不说了(菜是原罪)口是心非之虽然不喜欢但是做了笔记。记不到看什么书的时候也经常用“棠棣之花,偏其反而,岂不尔思,实是远尔”“未之思也,夫何远之有”有缘的话应该会闪出来告诉我。
p22 最伟大的是在
违章犯法的人身上找到的
慈善
当然不是说我们提倡
但是小偷小摸
在一个以大偷大盗为本的制度里或许只算随大流而已
p52 这液体肯定是
思维的一.部分
不是象征
而是成分
在思维的构造里
是动因和功能宛若尘埃之 与喷池
p66 就是说,人愈老愈愚蠢历尽磨难,
除了情感的质量
其余都无关紧要
最终一在脑海里刻下痕迹记忆不灭的地方
p68 “双眼,(失去了) 想找一个
会说他的方言的人。我们
谈论山谷里的每个小伙子和姑娘可当他病退回家
他伤心至极,因为他能摸得出
他家母牛的一根根肋骨……”
p116 若偷盗大体上是政府的
主要动机
则肯定会有小偷小摸
只要社会主义分子以他们花里胡哨的东西作掩护
p120 “别以为倘若其最轻微的爱抚从我心中消失
你就获益了
我无法好好爱你
假如我不爱女辈”
p129 月亮的脸颊肿了
当旭日把西边的一层层架子和一排排大军照亮,云与云相叠
老伊兹折起睡毯
我从未错待过晨星和夜星
p177 汝曾否游于恶风之海穿越永恒之虚无,当木筏离散,水流淹我,
为了那些饱尝辛酸的人们
以不同时代的三位圣人的名义波培图亚,阿加萨,阿纳斯塔西亚洁白无瑕地,我将走进
让其安息
不已之为
纯洁之女皇
我造的泪水淹没自己
晚了,太晚了,我才知道你的悲伤
花甲之年我仍然硬如后生
p192汝之双目骤然戕我
吾望其美瞬息即逝
p230
在地铁车站
魅影 这人群中 的脸:
花瓣 黑湿的树枝上 一片片
p258 你能跨进伟大的光之橡子吗?
可是美丽并非疯狂
尽管我的错误和失败围了我一圈”
而我并非神人一体,
我无法让它凝聚一团。 若家中无爱, 则一无所有。饥荒的声音听而不见。
美居然产生在如此黑暗的背景里,
榆树下双重之美——
被松鼠和蓝松鸦拯救?
“我对狗爱得越深”
《比萨诗章》读后感(四):《比萨诗章——庞德诗选》译序——黄运特
我开始翻译庞德的诗歌,是在二十多年前。我刚从北大毕业,来到美国南方腹地,人生地不熟,文化绝缘,处境维艰,靠开一家中餐小馆谋生,整日忙于炒菜、端盘子、送外卖、刷碗、拖地板等等。一天晚上打烊时,我接到一个电话,是当时正在美国访学的南京大学张子清老师打来的。他说国内一家出版社想找人翻译庞德的《诗章》,问我是否感兴趣。身陷囹圄的我,怀着一种初生牛犊不怕虎的精神,欣然答应了。
此前在大学里,我只读过庞德的短诗,领略过一点他的意象派风采,至于他的长篇《诗章》,老师没教,学生也不敢碰,原因是太难啦。接了翻译任务后,我硬着头皮上阵,选择了《诗章》里最精彩的部分——《比萨诗章》,做了大量研究,最后花了两年多时间,把它翻成中文。
那时的世界尚未进入网络时代,隔洋联系还很困难,所以《比萨诗章》译文在国内出版后的情形,我当时也不清楚,只是听说卖得还不错,甚至得了一个什么图书奖,尤其颇受诗人们的欢迎。二十多年后,我有一次在湖南长沙开会,遇到诗人王家新,他居然能背得出我译的《诗章》片断。此前在美国见到欧阳江河,他也是鼓励我继续翻译《诗章》。而杨炼在1999年就曾经在国际庞德年会上宣称:“庞德的《诗章》只有在汉语里才完美。在黄运特的译文里,庞德的诗歌计划好像最终完成了。”这些诗人的反应,当然让我感到欣慰,也让我汗颜。我深知自己译文的不足,多年来一直想找机会弥补,给热衷的读者献上一个更好的译本。所以当湖南文艺出版社编辑找上门来时,我觉得总算可以实现自己的一个心愿了。
庞德是二十世纪英美诗坛上的一位巨匠,也是争议性最大的人物之一。看你跟谁说话,只要提及庞德这个名字,一般你会听到三种不同的反应:(1)他是一位好诗人,只可惜他政治上反动;(2)他政治上反动,所以我们不应该读他的诗;或者(3)他的诗蹩脚难懂,政治上又反动。当然,庞德的诗歌思想与他的政治经济主张的关系非常复杂,不是短短一篇译者序言能够解释清楚的。不过,浏览诗人的生平经历,尤其是他创作《比萨诗章》时的个人处境和历史背景,我们或许可以对这个问题稍有了解。
伊兹拉·庞德于1885年出生在美国爱达荷州的小城海莱市,在宾夕法尼亚州长大,1905年毕业于汉密尔顿学院,次年获宾夕法尼亚大学比较文学硕士学位。他在文化保守的印第安纳州的一所大学任教几个月后,因生活作风问题被开除,此后一直旅居欧洲。1913年庞德遇到著名中日文学与艺术研究领域的先驱者欧内斯特·费诺罗萨(Ernest Fenollosa, 1853-1908)的遗孀,受她委托,开始整理费诺罗萨的遗稿,并对中国诗歌文化产生浓厚的兴趣。庞德于1915年出版的《神州集》(也称《华夏集》),就是以费诺罗萨的笔记手稿为基础,创造性地重译了十几首汉语古诗,在英美现代诗坛刮起了一阵中国风。
此后庞德又热衷儒家哲学伦理,认为盛传几千年的孔子思想是整治现代西方社会诟病的良药妙方。作为诗人,他尤其欣赏孔子对“正名”的定义。这个概念出自《论语·子路篇》:“子路曰:卫君待子而为政,子将奚先?子曰:必也正名乎。。。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庞德认为儒家“诚”的概念,不仅是为人之道,更重要的是对事物的正确定义,如《诗章》里写道:“而‘诚’的原则/一脉相承,才有西格斯蒙多”(《比萨诗章》第七十四章)。强调“名正言顺”的孔孟之道,跟庞德的政治经济主张一拍即合,尤其是他对金钱概念的理解。庞德认为现代社会的万恶之源在于货币价值的定义不确切,让投机者从中牟利,混淆是非。他尤其痛恨放高利贷的金融机构和银行家,认为这种“无中生有”的经济手段并非真正的“生产”:一位农民种一棵苹果树,结了苹果可以拿来养家充饥;而一个高利贷者榨取利息只是剥削,是“不自然”的生产,有悖天道人伦。自古以来,不管是带着种族歧视色彩的想象,还是现实里的真实人物,不管是莎士比亚《威尼斯商人》里的夏洛克,还是现代社会的金融大亨,放高利贷者往往是犹太人。因此,庞德把批评的矛头指向了犹太人,由此他走上了跟纳粹法西斯同流合污的邪道。
1945年5月3日,法西斯已经倒台,二战已接近尾声,旅居意大利的庞德正在家里翻译孟子,突然听到有人敲门,是两位意大利游击队员,要奉命把诗人带走。庞德顺手往兜里揣了一本孔子的书(盗版的商务印书馆理雅格译本)和一本中英词典,就跟士兵走了。他以为这只是一个误会,自己应该可以很快回家,但这一去就是十几年。他被捕的原因是他曾经为墨索里尼政府的罗马电台做过广播节目。每周二十分钟左右的节目里,他先是朗诵一段自己的《诗章》,然后发表反战言论,劝说在欧洲打战的美国官兵放下武器,不为军火商和放高利贷者卖命。按美国的法律,这是叛国罪。他很快就被送进比萨附近的美军监狱,在那儿他端坐在一个露天的铁笼里(见图1),遥望远处的斜塔,一边蚂蚁啃骨头般地翻译《大学》和《中庸》,一边构思创作他的《比萨诗章》。从某种意义上讲,《比萨诗章》是庞德跟儒家思想的对话,而话题就是拯救天下。那时的世界是满目狼藉,欧洲一片混乱,诗人心目中的理想国遥不可及,自己也成了阶下囚。颇具象征意义的,《比萨诗章》悲壮史诗式的开头是写在一张厕所手纸上:“梦想的巨大悲剧在农夫弯曲的双肩”。
11月,庞德被遣送回美国待审。次年,以精神病为名义,庞德被免审,关进华盛顿特区的圣伊丽莎白精神病院,软禁了十二年之久。此间,在1948年,他的《比萨诗章》出版,获得美国国会图书馆颁发的博林根诗歌奖,引起轩然大波。1957年,经过许多文化界名人的多年努力,庞德被释放出院,立即前往意大利。在那里,他继续创作《诗章》,翻译四书五经,直到1972年在威尼斯去世。
鉴于庞德与中国的不解之缘,翻译庞德具有特殊的意义。这次利用修订《比萨诗章》译文的机会,我又选译了几篇重要的《诗章》和短诗名篇,以便中文读者对这位影响深远、极具争议性的诗坛巨匠有更多的了解。至于庞德的诗歌之梦,或者说,他的中国梦,是否在我的译文里实现了,有待读者、专家定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