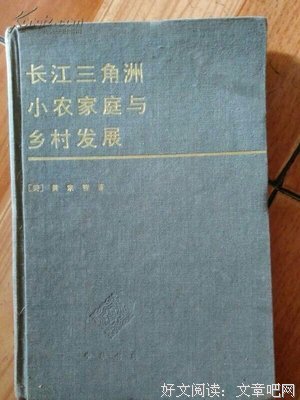
《长江三角洲小农家庭与乡村发展》是一本由黄宗智著作,中华书局出版的平装图书,本书定价:29.00元,页数:458,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长江三角洲小农家庭与乡村发展》精选点评:
● 在数次浸淫了《华北小农》里的过密化之后,再看这本里面的论述总感觉在兜圈子。 但不是黄宗智拿不动刀了,而是我个人飘了。 其实田底、田面分析的还是很详尽的,但可惜我也已经略有耳闻,所以感觉还是味同嚼蜡。 不过不失为中国农民学经典,毕竟也绕不开。 最后面关于农民发展性的问题很尖锐。其实“农民的命运从不由农村决定”也不是新鲜事了,但是只有认识到这一点才算是农民学走到头了。 相比较《华北》的前近代,这本里的现当代还是比较深入的,毕竟材料多呀!
●略讀的,和華北差不多範式。
●今天的一切都所来有自。
●在做上海皮影戏研究的时候,对作为背景的近代上海农村这方面提供了很大的帮助
●[补标]
●换了个地名而已。
●好多地方还是不懂。
●黄一直在强调中国农村过密化的问题,同时又宣称斯密、马克思、舒尔茨的经典模式无法解释这一区域的过密化问题,我认为是作者对以上三人的理论的理解不透导致。
●理论核武器
●和《华北的小农经济》一脉相承,分析思路类似,不过具体研究的区域不一样,一个代表北方旱地,一个代表南方生态条件比较好的地方,而且有华北的基础,这本书也加入了很多对华北和长三角的对比,还有长三角1949年前后的对比分析,但结论仍旧是小农家庭的“过密化”生产,乡村“没有发展的增长”。
《长江三角洲小农家庭与乡村发展》读后感(一):重读黄宗智的书,不满意
这本书实际上涉及的问题是human capital and history,也就是农业劳动力marginal return的降低。又,分清华北和江南的不同,是比较重要的。另外,这本书关于明清之际的讨论总感觉遗漏了些什么,特别是明代和清代的财政制度。这本书最大的问题是没有用数据给出一个很好的story,比如如果说过密化是由人口压力而造成的,有没有可能做一个曲线图表明过密化的程度和人口增长的相关关系;如果说过密化造成了农业劳动力边际回报的下降,可不可以给出一个历史曲线图来。
《长江三角洲小农家庭与乡村发展》读后感(二):读书笔记一则
1、思想观念也要现代化
作者在本书中讲到,长江三角洲农业经济商品化程度自唐、宋时期就很发达,但是为何没有发展成为资本主义呢。作者认为主要原因之一是农民并不是以盈利为目的,而是满足于温饱。纵然,按照“道义经济学”的观点看,生存是农民第一要务。但是一个地区的历史文化传统、人的思想观念在一个地区的发展飞跃中,也起到了很大的作用。人的思想观念,也需要现代化。说到这,我想我的一位山西同学和我说过的一段话。“山西这么穷,为什么全国各地却很少见到山西的乞丐?那是因为,山西人都很懒,不爱动,总喜欢守在家里,就是穷得再厉害,也不肯离家。”一个地区的人的思想观念,确实会很大程度上制约着这个地区的发展,就好像我这位同学说的,越穷越懒就要更穷,陷入一个恶性循环。要发展,人的思想观念就必须要更新,这是前提。
2、《华北》与《长江》的“过密化”
我是在阅读完《华北的小农经济与社会变迁》之后,再来阅读这本《长江三角洲小农家庭与乡村发展》(以下简称《华北》和《长江》)的。可以看出,两者有些不同,后者在空间上转移到长江三角洲地区,在时间上延伸到1949年之后,从而为丰富前者的若干结论带来了新的证据和解释概念。但无论在基本的研究方法上,还是在最为核心的主张上两者保持了一致。而两者最核心的概念,就是“过密化”。当然两本书的“过密化”,还是有些差别的。在《华北》一书中将其定义为:大农场得以就农场的需要变化而多雇或解雇劳力。家庭式农场则不具备相似的弹性。在生计的压力下,这类农场在单位面积上投入的劳力,远比使用雇佣劳力的大农场多。这种劳力集约化的程度可以远远超过边际报酬递减的地步。“过密化”的概念只限制在农场劳动的范围之内。而在《长江》一书中,黄宗智提出了另一个概念“过密化增长”,用以解释与似乎长期相对停滞的华北不同的长江三角洲地区在明清时期明显的社会和经济发展:农村家庭年收入的增长,不是来自单位工作日报酬的增加,而是来自家庭劳动力更充分的利用,诸如妇女、儿童、老年劳动力,以及成年男子闲暇时间的劳动力。这就是“过密化增长”。农村富余劳动力参加手工业生产成为了“过密化”的表现形式。简单说,我觉得作者把“过密化”的理论分析框架扩大了,不仅分析了农场劳动,还分析了农村副业手工业。同样的概念,杜赞奇在《文化、权力与国家——1900-1949年的华北》用来分析了国家政权,提出了影响至深的理论。“过密化”的理论这么好,是不是放在哪都用得上呢。假设一下,当初作者把用在《长江》中的范围用在《华北》的研究中,把《华北》的研究范围用在《长江》中,又会得出什么样的结果呢。
《长江三角洲小农家庭与乡村发展》读后感(三):读后感与记录
本书的博大精深是值得赞叹的。作者运用丰富的史料,以扎实的微观证据论证自己的宏观看法。总结而言,作者认为明清以来长三角地区的商品化并未像斯密或马克思所言推动了资本主义萌芽,相反,农业商品化带来的是小农家庭生产(而非“地主—小农”雇佣关系的经营式农业)越来越密集,农业生产走向劳动力过密型/内卷化增长(因此中国农业是土地效率高但劳动力效率低的产业),且农业市场的发展也并非资本主义所见的牟利市场行为(而是处于生存边缘的谋生行为)。总之,同作者笔下的华北小农经济一样,明清以来的长三角农业长期属于糊口农业性质,或称“贫农经济”;而农产品的商品化并不一定像马克思笔下的英国范式一样为中国带来资本主义萌芽,因为为了糊口而变卖产品或劳动的市场参与者与一个为资本积累而积累的企业单位是完全不同的。
甚至到社会主义集体化时期,关注农业总产出而非单位日劳动效率的政治指标也并未改变以劳动边际递减为特征的过密化农业现象,因此中国农业长期处于“没有发展的增长”。而似乎在作者看来,过密型农业的真正扭转始于20世纪80年代的农业改革。正是由于城乡之间真正双向的要素流动的开放(尤其强调乡镇企业为主体的乡村工业化过程。本书成于90年代初,可理解作者对此的独特关注),农村中大量劳动力得以转移到非农领域就业,才缓解了农业生产中劳动力的过密化投入现象。换句话说,长三角地区正是向非农领域转移长期积压于农业中的劳动力,因此提升了农村人均资源占有,才真正走出“贫农经济”阴影。这让我想起上次提问刘守英老师时候获得的对农村发展真正出路的启发:在于农村产业的多元化经营。似乎是同一理论范式。
除了丰富严谨的论述主线外,其他附带论点也时常让我有惊喜。例如,作者用华北与长三角的不同治水方式尝试解释两地不同的社会组织形态:长三角水系复杂且气候多雨,除了大江大河可由县及以上的国家承担外,小型的水系仍需村一级规模的合作(如圩田),因此长三角地区宗族村与地方士绅角色突出;而华北的水利工程要么是非由政府承担的黄河大堤,要么是一家一户使用的小型水井,因此并未形成长三角那样“国家政权—地方士绅—农民”的富于变化的三角关系,农民更多地直接暴露于与国家的关系中,租佃率较低。也正因此,共产党在华北地区通过抗税的号召(抵抗国家政权,而非抗租——抵抗地主)才能成功将小农纳入阵营。又如,在最后作者勇敢面对其论点所隐含的关键问题,即中国为何保持高人口密度时,提出了多子继承制度的解释:欧洲的一子继承制意味着只有父亲死后继承了田产,才能获得经济独立,这便可能形成晚婚,而其他兄弟必须另谋生路,自然也难以保证结婚率;而中国多子继承制在父亲在世时就能分家分田,每个儿子均可早日获得经济独立,有机会早婚早育。此外,作者在此提到的多子继承制与中国“地主制”(或用“士绅社会”概念,区分于欧洲“领主制”)的关系也值得一提:多子继承制必然带来土地的分割,长期下去,如果一个小农继承了不敷家用的土地,那就必需买/租田以谋生,这带来了中国长期以来相对于欧洲而言更活跃的土地流转,再与科举制度结合,形成了特殊的士绅阶层,以及中国古代社会以活跃为特点的社会流动。
总之,收获很大。期待开启第三本的阅读。
《长江三角洲小农家庭与乡村发展》读后感(四):对两种生态系统的一点认识
《长江三角洲小农家庭与乡村发展》(以下简称《长江》)的主线是非常明晰的,即长江三角洲在1350年之前,农业生产就非常成熟,以致于1350年之后这块地方的农业生产率一直没有太大的改变,即使跨入近代,商品化有所发展的长三角,其过密化还是持续不断。而49年之后的农业集体化尝试,非但未能改变“没有发展的增长”的趋势,反而重复和加深了这种趋势。只有始于70年代末的改革才使得长三角的农村经济摆脱了过密化。但是作者又指出,这种发展的动力并非来自意识形态的改变(换句话说,在当年的意识形态下,农业产量还是增加),也非来自生产组织的变革(从集体化到家庭联产承包。这就是说,集体化下的农业产量也是呈增长趋势的),反而改变了意识形态和生产组织之后,农业产量停滞不前,但是劳动生产率却提高了。这种发展的动力来自于农业外,来自于乡村的工业化。
不过,除了这条明晰的主线之外,还有一条似乎若隐若现的副线:长三角村庄的社会整合;国家、士绅与农民的关系(或者是国家与基层社会的关系);由此涉及到长三角与华北两种类型的村庄的比较。如果说主线是侧重对乡村经济发展的考察,那么副线就是偏重政治与社会的分析。当然两者并不是截然二分,而是认识长三角社会的两个侧面。
长三角在近代的变化是耐人寻味的。本身商品经济的发达,又加上帝国主义的入侵,使得长三角成为了高度商品化的社会。按照我们的常识,商品化接下来就会导致社会分化,然后就是社会矛盾激化,由此产生动荡、运动甚至革命。就如魏斐德在《大门口的陌生人》中所指出的,华南社会亦经历了人口增长、商品化、帝国主义入侵,由此导致阶级的联系强化,而家族的联结弱化。这种联盟行为,“不可避免地使阶级-宗族的平衡以不断增长的力量互相反对”,自1849年之后,“阶级就开始居于宗族之上了”。在加上家族领袖们广泛地参与团练、公所、社学,“所有这些变化破坏了宗族维持的社会平衡。到1845年时,社会开始分化为富裕者、贫穷者两部分,血缘关系不再能够模糊阶级利益了。”社会的两级分化,家族控制力的急剧降低,使得“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加入超越宗族的秘密社会”。(122至132页)但是长三角却有着不同的发展轨迹:这里的宗族集团依然强大(第八章),而且社会也比较具有弹性,丝毫没有要爆发革命的迹象。共产党的动员能在这里失去了效果,革命在此地停滞不前。反倒是商品化程度相对较低的华北成了叛乱与革命的温床。在这里,近代以来发生了捻军、义和团和共产革命等。这中间的差异,关键何在?作者的逻辑大致如下:
生态系统——农业、手工业的发展程度以及由此导致的其他就业机会的多寡——土地占有形态及其转让方式——村庄整合方式、与国家的关系——社会是否稳定、革命动员的效果(这些因素之间的关系错综复杂,这里只是尝试给出主要的思路)
《长江三角洲小农家庭与乡村发展》读后感(五):小总结
黄宗智可谓是农业领域的祛魅大师,将马克思的阶级主义、舒尔茨的经济形式主义、波兰尼的实体主义三种农业分析范式、和施坚雅的共同体理论,以及对资本主义萌芽的确信、集体化的批判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赞誉等等历史观念全部打碎在华北和长江两个农业领域。分析出中国小农是在极度过密化和阶级分化基础上形成的生存导向的农业结构。
这本书比《华北》丰富的部分在于对长江三角洲农业特点的总结和对建国后农业发展的分析。
“直率地将,80年代的市场化农业在作物生产上并不比在1350至1950的600年间或集体化农业的30年间干得好。”
商品化非但没有削弱小农家庭生产存在的基础,反而刺激了这一生产,并使之成为支持商品经济的基础,商品化不是减少了而是增加了妇女和其他农民家庭成员进入生产领域。而长江三角洲的经营式农业由于商品化城市化经济带来的充分就业机会、当地的多层次劳动结构(妇女的工作隔离)及经商和读书的更高收益而导致的劳动力成本相对高昂而逐渐衰落。而对比之下,长江三角洲的农业高度家庭化,家中妇女老幼辅助劳动力劳动力参与经营,导致了手工业和农业的高度集约化和低成本。“不断增长的人口压力迫使农业和手工业的收入下降时,两者的结合只能是越来越强。两者只有相互依靠,才能使小农家庭维持生计。这就形成了小农家庭赖以支撑生活的双拐”
农民参与市场生活的主要内容是缴租、支付生产开支、出售和纳税,这些都是为了生存的理性行为而非追求利润,这种商业关系“不是城乡交换的互惠关系,而是受剥削和为活命挣扎。部分贸易是由农村剩余向城镇的单向度流动构成的,其主要形式是纳租而非交换。“”小农买卖的大部分产品是马克思主义所谓的‘小商品’一类的生活必需品。土地市场很大程度上仍为不可转让的原则支配。信贷市场为互惠原则和维持生计所支配,而长工劳动力市场则为社会关系所支配。女工、童工的生产劳动力供给与市场机会之间的差距,说明并证实了农村存在着就业不足和剩余劳动力的事实。“
“这种生存边缘的经济可能支持高度的商品化,但这样的商品化只带来极其有限的积累和生产性投资。它主要出于剥削和谋生,不应混同于资本主义生产俱来的商品化,后者伴随着创造剩余、并为投资生产而积累的资本主义生产者的兴起。西方近代早期及近代,市场发展和资本主义化的关联实际上是偶然的,甚至是例外的。我们不能以这种模式去了解世界各地各个时代的所有商品化进程”
帝国主义的入侵并非像二元论者认为的只影响城市地区,帝国主义引起了一个新的经济体系的出现,把城市工业的发展通过商人的中介与农村的过密化联结到一起,农户的生产总值甚至人均生产总值增加了,但或曰的手工织布业只是在减低单位工作日收入的情况下提供了额外就业机会,而与此同时,家庭化农业也使长江农业土地具有高度稳定性。
土改之后,旧的国家政权、士绅或地主、农民的三角关系被新的国家政权与农民的双边关系取代了,定购定销定产的三定政策不仅把整个小农家庭经济纳入国家计划,还将农民推向了集体化道路,但集体化形式之下仍是原有过密化和集约化农业形式,瞎指挥和官僚主义并未像印象中的对农业产生过显著的错误作用。在集体化时期,妇女加入了生产队伍,而家庭副业仍以自留地、养猪和手工业的形式存续下来,并在改革后产生了新的副业形式。
集中化时期通过农业劳动力来源的增加、政策协调下的水利建设、现代农业投入的增加,农业得到了大规模的稳定发展,但属于边际效益递减的“没有发展的增长”,生产形式没有得到现代化变革,仍是低人均生产率的“过密化集约农业”,“从这一角度看,30年的集体化的经历缩短和重复了自1350至1950年6个世纪中没有发展的农业增长情况。”
而80年代小城镇工业的兴起使大量村民转入农业,过剩劳动力投入了各种农业外就业,农业的个人劳动生产率得到了大量提升,但个人生产率提高及化肥使用规模提升带来的几年增长剩余,使“改革的拥护者把这些进展大多归功于他们心目中家庭农业的积极性”,而水利设施的缺乏维修,滥用化肥和难以满足专业化耕作需求导致的农业总产量的停滞和下降证明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只是一种“没有增长的发展”,是农村工业而非市场化的家庭农业带来了真正的劳动生产率的提高。
中国的工业化和城市化是自上而下的,工业化不是首先在小型乡村工业中发生,而是在城市工厂中产生,进而将磨损的设备和低收入的经营逐渐转入小城镇和农村。“半工半耕村庄”主要是国家政权下的强制产物,被户籍制度强制约束在内,官僚制度下农村工业的发展一方面使农民有机会摆脱农业生产过密化而提高人均生产率,然而却将农民地位降低到官僚制度强加的社会经济阶层最底层。
“农业与手工业之间、城乡之间的社会分工不但没有出现,农业与手工业在小农家庭中的结合反而加强了;商人没有进入生产领域,商人资本也没有转化为工业资本,他们依然与生产相分离,仍依赖于商品和资本的流通来牟利”
“庞大的劳动力供应抑制了为节约劳动而资本化的动机,并迫使农业朝过密化方向演变”
“我猜测:以多子继承制的小农经济为基础的中央集权制的确立,使早婚和普遍结婚的习俗长期延续,由此促成了较高的生育率;近代欧洲人口变化主要取决于生育率,而中国人口变化则决定于死亡率”大量农业劳动力剩余就是中国能比中世纪欧洲供养更大和更复杂城市的关键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