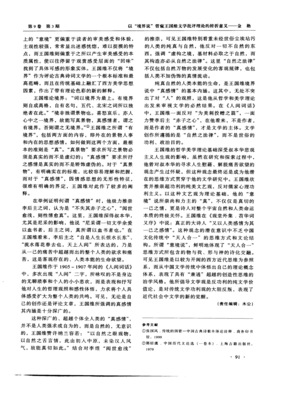
《王国维及其文学批评》是一本由叶嘉莹著作,河北教育出版社出版的平装图书,本书定价:20.50元,页数:411,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王国维及其文学批评》精选点评:
●叶先生写静安先生治学和批评理论,何尝不是夫子自道。更难得的是让门外汉如我也能一气读完,不忍释卷,这才是大家。
●读此书,再读叶朗《中国美学史》中涉及王国维的章节,便会发现,同样一种事实,在不同人眼里,差别竟会这样巨大。且叶朗对王氏境界说评价并不高。
●补标
●为了写本科毕业论文读的。。
●不喜欢。
●今人论王国维先生,似无出迦陵先生之右者。
●通透。
●我认为只有对中国古典诗词与西方文论的造诣皆深如叶嘉莹先生者方能研究王国维的文论。细细看下来,洵乎其言。叶先生对《人间词话》中几个重要概念的解读让人信服。
●此书第一部分王国维的生平可作为知识分子精神史研究的案例
●叶嘉莹-王国维-叔本华-萨特
《王国维及其文学批评》读后感(一):只说此书
相对于重点的第二编,倒是第二编对静安先生生平的介绍和对其死因的探讨更让人有兴趣。对静安自沉原因的分析很有陵迦特色,也很有道理。其实在并无太剧烈生活变动的情况下,静安自沉应当有着多方面的复杂原因,抵抗或者厌世,恐慌或者愚忠,也许或多或少都有一点,再去问他也只能得一“只欠一死”的答复罢了,无是无非或者皆是皆非。
《王国维及其文学批评》读后感(二):吾儕所學關天意,並世相知妬道真
偶閱《迦陵文集》卷二,題曰《王國維及其文學批評》,靜安先生孑然獨立,空谷幽蘭之質頗會於心。夫人之至潔者,多磨礪於世。如靜安先生知、情兼勝,求索信、愛,悲苦生焉。人世之缺、醜、惡與其尋美善之心相角逐,而其心憂鬱,天性悲觀,避世不及,托之學術,暫得美善矣。古來情勝於知者,筆之於書,則成文學,其情豐盈激蕩,或陳人世悲苦,或求團圓之境。知勝於情者,不為情所累,所感悲苦亦少,唯求單純於學問,遮掩人世真相,忽忽一生而已。靜安先生則情、知并勝,遂有初期情會文哲悲心之苦訴,繼以知悟古史考據之純聲。寅恪先生輓詩“吾儕所學關天意,並世相知妬道真”,誠相惜之語也!考據之學,其事皆古,遠於生活,繆先生謂“可以暫忘生活之慾也”。夫人之生於世,或執迷而漸醒於暮,或洞觀而頓悟於晨,緩疾皆見人生醜惡真相。獻初先生有詩云:“窺見人間真相后,仍舊一片熱忱心。”靜安先生自沉昆明湖,情、知所交攻也,知求愈真,其愈不忍視人世污穢,而其情愈烈。情知化文,同三光洞幽古今。唯其蓮花之心,熱忱難尋,竟以死終。
《王国维及其文学批评》读后感(三):迦陵可谓观堂先生之异代知己
叶先生尝言:
陈寅恪……在为王氏之〈遗书〉撰写序文时,乃不禁发为议论,曰:「寅恪以为古今中外志士仁人往往憔悴忧伤,继之以死。其所伤之事,所死之故,不止局于一时间、一地域而已,盖别有超越时间地域之理性存焉,而此超越时间地域之理性,必非其同时间地域之众人所能共喻,然则先生之志事,多为世人所不解,因而有是非之论者,又何足怪耶!」于是陈氏乃寄望于另一时间与地域之来者,曰:「呜呼!神州之外,更有九州,今世之后,更有来世,其间傥亦有能读先生之书者乎?如果有之,则其人于先生之书钻味既深,神理相接,不但能想见先生之人,想见先生之世,或者更能心喻先生之奇哀、遗恨于一时、一地,彼此、是非之表欤!」其后,叶先生引卡夫卡 〈一个绝食的艺术家〉(A Hunger Artist) 及《庄子·秋水》 篇中「鸱枭吓雏」的寓言为喻,感慨当今之世,上文陈先生期翼的那样理解静安先生之人,恐怕 是
「神州之外,更有九州,今世之后,更有来世」,也是难于共喻的了读文至此,不仅同意叶先生的感慨,亦心下黯然。然而,回身细想,叶先生这本著作本身,难道不就是「怅望千秋一洒泪」的异代知己之言么?
静安先生泉下有知,足感欣慰。
《王国维及其文学批评》读后感(四):王国维的忧郁
(评的不是这本书,而是我年少时懵懂感受的王国维。对王国维诗学研究最有成就者,我以为是叶嘉莹和佛雏。)
一
苏珊·桑塔格在为本雅明的《单向街》所作的长序中称本雅明是个总带着“一种深刻的忧郁”的人,而这种气质贯穿了他的一生以及所有的作品之中。她极细腻地分析了这种气质:敏感、孤僻、隐藏的激情、爱沉思、身体孱弱、行为古板等等,并与本雅明的生平对证,文字透出一种让人感伤的宿命色彩,而这时我眼前出现的影象,却是我国一代宿学的王国维。
两人的确有一定的可比性,两人都生在国运飘摇,战火连绵的时代。本雅明身为犹太人,在纳粹横行时,仍苦留在他认为是文化阵地的欧洲,他在回绝美国友人的邀请信时,说他宁愿成为欧洲最后一个知识分子。大战发生后,本雅明自杀在逃亡的路上。而王国维,沿着这气质一路行来,其悲剧的结局,似乎也是注定了的。
二
王国维忧郁沉潜的气质、天才的禀赋,早在少年时已有显露。甲午前后,“新学”开始生行,二十岁的王国维在上海传播新学的农学社学习。一日创办人之一的罗振玉到馆很早,听到有人朗读《庄子》,音节苍凉,大奇,而那人即是王国维了。另一种说法是罗振玉在一个学生扇头上见到王国维所题的“千秋壮观君知否,黑海东头望大秦”的句子,“乃大异之”,遂结识王国维。两种说法都十分美妙,近乎古人结交的一些雅事。总之,罗振玉对王国维十分赏识,引为弟子,从此,王国维的治学道路及以后的生平都与这位古史学家、清室遗老分不开了。
二十二岁的王国维曾在罗振玉的帮助下留学日本,他的气质决定了他选择研究什么。“体素赢弱,性复忧郁,人生之问题日往复于吾前,自是始决从事于哲学”。王氏忧郁的禀性与叔本华的悲观哲学一拍即合,比之苏东坡初读《庄子》那种若有夙契之感。
三
在王国维近十年的哲学、美学研究中,援引叔本华的哲学体系,诘难“仁义”,贬我国学术的“一尊”“道统”,高扬“纯粹美术”《包括文学艺术》,当时真是发前人之所未发,而《红楼梦评论》应是其中最放光彩的一部著述了,这是红学的一部真正的开山之作。
一部伟大的作品也许不是给一个问题一个终极的解答,而是把一个问题提到需要终极解答的高度。王国维在篇中反复诘问,男女之爱“自何时始?来自何处?”叹这是“人人所有”而“人人未解决”的大问题,在中国文学上解此问者,三千年间仅一部《红楼梦》而已。王氏最早将《红楼梦》划为“此宇宙之大著述”,当与《浮士德》并称,是最高悲剧的代表。王氏忧郁的气质再次醒目地显现,他迷恋着一种具有启示般的悲观主义。人格的高尚并不与快乐幸福相偕,倒常与悲为邻,正如美学上的崇高多与悲剧相联一样。而悲剧中那种不知不觉的日常的力量,常规的伤害才是最让人无力抵挡的,也是最深重的。“金玉以之合,木石以之离,又岂有蛇蝎之人物,非常之变故行于其间哉?不过通常之道德、通常之人情、通常之境遇为之而已”。戴东原曾说:“人死于法,犹有怜之者;死于理,其谁怜之!”这才是悲剧中的悲剧。
四
“来日滔滔来,去日滔滔去。适然百年内,与此七尺遇。尔从何处来?行将祖何处?”王国维在疲于哲学中的“可爱”“可信”之争后,将自己对人生的悲悯、怀疑,都化入诗词和文学研究中了。王国维把人生看作“天下至弱者”之一,侧身天地,俯仰悲悸,草草生死,终古难度!这与帕斯卡尔称人类为“能思想的芦苇”是相通的。他的词集名为“人间”,也无非出自忧生、悲悯一念而已。
王国维写出划时代的《人间词话》和《宋元戏曲史》后,时世也愈发纷乱了,辛亥革命一起,王国维随着罗振玉等清室遗老东渡流亡。这一批人应是广义上的文化遗民,他们几乎都是一代学者,他们珍视的传统文化随王朝一起现出末世衰乱的景象,眼见一个整体的文化、伦理价值体系的行将崩溃,他们不仅是一个王朝的凭悼者,更是一种文化的凭悼者。
王国维此时在学术道路上又经历了一个重大转折。或是在罗振玉的影响下,王氏开始返经信古,深悔其少作了。“自忽以前所学未醇,乃取行筐《静安文集》百余册悉摧烧之。”从此转治古史学。人到中年,终觉年轻时对传统的驳斥有轻薄之嫌,即奋而烧书,决绝如此。人随年岁的增长,对此世才有更深的体会,身在传统中的王国维终觉体会了传统的妙义,它毕竟乘载了三千年的文人之梦,可这传统本身已面临浩劫了。
王国维此时只是一个悲凉的凭悼者。凭悼即是一种回忆,凭悼文化也是如此。王国维从此把自己埋进了进行回忆的材料之中。苏珊·桑塔格说:“忧郁的人对人缺乏信念,是因他们有更好的理由对物具有信念。这物呈现为残片或废墟的形式。”王国维正努力在断瓦残片之中辨认着中国文化的昔日身影。
从性格上,忧郁的人喜好译解神秘的事物。王国维沉入甲骨残片、西域简续的破译中后,在经史小学、甲骨金文、汉晋简牍、西北地理、蒙古史等研究中,都蔚成一代大师。但此时衷心更甚,即在甲骨学上的结晶大作《殷周制度论》中,王国维也流露出怅望周孔的感伤。他在上海时,曾与哈同的学生庄敬严肃地演习古礼,亲自设计搭盖“芦殿”,叹之为“极美之事”。“五四”以后,王国维蓄起了辫子。王国维早在留日时即已剪发,是时博仪也早去了辫子,辜鸿铭虽也有此举,但毕竟是显名士风态,而一向刻板的王国维则是面对一种文化无法挽救的陨落,摆出了一个世人皆废我独持的悲壮姿势,这与他最后走向死亡的路已不远了。
五
有一个现象不知有人注意了没有,王国维只肯出任研究院的导师,而不肯出任大学教授。章太炎曾著文反对过新式教育,认定兴学校不但不能使学术日进,反而必定使学术日衰。这未必是名士故作惊人之语,而是章太炎洞察了官学与私学、西式教育与中式教育的传播方式间的差异。就普及教育和传播知识而言,官学与私学各有长短,不必强分轩轻;就其学术发展的开拓和贡献,私学的确胜过了官学。王国维曾说:“以学问为羔雁,”“以官奖励学问,是剿灭学问也。”而私学则更像学术自由争论、辩难的阵地,是孔子说的“有教无类”的范所,师生间也容易多一些感情交流。中国文化的传播到了深刻处,就有了一定的隐秘性和神秘感,类似佛家的传心。这是说对一个整体意义不可能分割而授,只能顿悟而得。这是一种东方文化的气质。倘若如西方学术一般,分科严谨、条理精密,以固定清晰的概念统而授之,难免对国学内蕴有损。这应是当时的国学大师康有为、章太炎等力主废科举之后,又发出了斥学校教育的言论的真正原因。王国维当时并未公开发言,想必也是深觉其意的,他连清华研究院导师都是在博仪的面谕下才勉而为之,那只是带几个固定的研究生,已经类似当年的私塾了。
六
行事刻板,对自己毫不宽容也是忧郁的人的一种特征,他们常常是自剖的大师,毫不留情地自我惩罚,带点自虐的倾向。如帕斯卡尔、克尔凯郭尔、尼采、卡夫卡、波德莱尔、鲁迅,甚至本雅明。他们几乎都不能善终。
王国维在治学上严谨,在政治伦理上也一样地一丝不苟。他不同于其他的传统学者文人,像事鸿铭、林琴南那样的对西学破口大骂,他有相当深厚的西学素养,溥仪曾说:“新旧论学,不免多偏,能会其通者,国维一人而已。”王国维不只是立足于文化旧营垒的人,他研究传统不可避免地以西学作为比较的参照系,运用科学的新方法,但他明白不可随意比附,所走的只是中国文化本位的路子。他并不是表象的那样保守,但他对国学的衰落却露出了绝望的忧伤情绪。王国维曾因困扰在“可爱者不可信,可信者不可爱”的哲学研究中不能两全时,而放弃了哲学。在传统和西学又难两全时,他能放弃什么?这是两种大文化之辩,而且时代已经做出了选择,一切都在合情合理中进行,那么不知不觉、不可抵挡,就像一贯坐马车的权贵,开始改乘汽车了一样,他还能说什么呢?他终于放弃了,放弃的是自己的生命,“只有靠生命来拥抱文化了”。
一九二七年,博仪被迫出宫、李大钊遇害、叶德辉在长沙被军阀所杀,清代遗老纷纷逃难,罗振玉也避入某国使馆。而王国维坐着一辆人力车来到颐和园,悄然自沉。称:“今日干净土,惟此一湾水耳!”王国维早已痛心目睹他心仪的古国文化在一步步式微殆尽,而作为旧文化最后的象征——紫禁城,也人去楼空了。时局纷乱,也要波及他的书房了,他走前的一日对学生说:“我受不得一点辱!”后在遗书上云:“五十之年,只欠一死,经此世变,义无再辱”。王国维用自己迷恋的悲剧形式遽尔撒手,才及中天而殁,甚至遗书中也未多说他心中的矛盾和无奈,只让后世之人去深哀痛惜和费心猜度了。
陈寅恪说:“凡一种文化值衰落之时,为此文化所化之人,必感苦痛,其表现此文化之程量愈宏,则其所受苦痛亦愈甚;迨既达极深之度,殆非出于自杀无以求一己之心安义尽也。”《《王观堂先生挽词并序》》这实是同类人兔死狐悲之叹,陈寅恪是真了解王国维的人。
苏珊·桑塔格在她的序言中最后说:“他带着所有残篇断简、他的抗议态度、他的沉思和梦想、他的无尽的忧郁,和他向下望的双眼,将在最后审判面前,对他所占据的全部位置和一直到死对精神生活的捍卫,作出辩护。”这同样适用于王国维。这些忧郁的天才总是过分的敏感,莫名的痛苦,最终为他们的忧郁气质和天才的某种偏蔽所累,走着一条近乎宿命的长道,直至上苍收走了他们,而这也是注定了的。
(199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