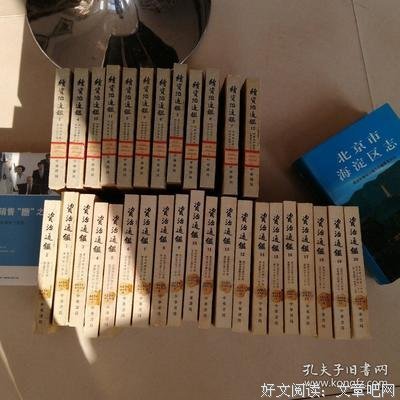
《续资治通鉴(全十二册)》是一本由毕沅著作,中华书局出版的平装图书,本书定价:478.00元,页数:6020,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续资治通鉴(全十二册)》精选点评:
●与资治通鉴相较,各有所长。事有利弊、人有得失、论有涓细不失理之当然。
●好差劲。
●复习宋辽金元历史的好材料,没有某些人说得那么不堪。可以从书中明显看到,清代对于人名的音译,有着自己独特的一套体系。
●陕西省省委书记编的书,文笔实在不敢恭维。 宋代详看,元代粗读。着重于真仁时期祖宗之法形成,对夏,对辽关系作为参考。
●有两本续资治通鉴,上下云泥,莫浪费了时间。
●仿照司马光的《资治通鉴》,李焘的《续资治通鉴长编》,但没有司马光的才学和功底,又没有李焘的专业态度和考究精神。北宋已经有了李焘的《续资治通鉴长编》,你又来了一个,还断章摘句。还不如直接编写《元史》,写细致彻底一点还有点参考价值。贪大求全,可惜各方面差得有点远。
●远不如资治通鉴,是历史古籍中较下等者,毕沅不学,乃至于此。
●其实不如通鉴远甚...
●草草看过一遍(准确说就是大臣奏章撕逼部分基本没看)……目前感兴趣的方向还是在宋以前……但是可以感觉到毕沅比司马光的水平差多了
●续通鉴无温公之论,唯有叙事,是画龙者不点其睛也~
《续资治通鉴(全十二册)》读后感(一):闪光点在于本书考异部分
不知道怎么回事,对《续资治通鉴》的评价不如《长编》来得高,但是我觉得《续资治通鉴》的考异还是有《长编》遗风的。虽然记事不如《长编》详细。屈万里先生的古籍导读里推荐的关于宋朝的入门书就是《续资治通鉴》。去年五月开始看的,断断续续。编年体的书写得比较琐碎,我相信这不是这本书的不足,是所有编年体的书都存在的。如果初学者一头直接扎进《长编》恐怕会把你的耐心耗尽。
《续资治通鉴(全十二册)》读后感(二):看不下去了
这本书读了三周左右,实在读不下去了,放弃。
文采很一般,比资治通鉴差多了。
叙事也乱糟糟的,跟司马光学,可是好多“自此始”真的没人关心啊。
完全没有享受的感觉。
总是看到太平盛世的时候心里舒服些。
王小波李顺的造反又TM被美化了。
看到宋太宗说吕端“大事不糊涂”,想本朝太祖是不是也看过,回去一查,那肯定是《宋史》。
《续资治通鉴(全十二册)》读后感(三):缺点明显,糟糕透顶
《续资治通鉴》是一本读来味同嚼蜡的编年体史书,这一点与《资治通鉴》对比而读感觉尤其明显。其缺点已不乏史学家指出,就我个人而言,过年回家带了好些本续资治通鉴本打算好好补补宋史,结果无一册能终卷,总结起来以下缺点尤其明显:
一、辽金元人名全用乾隆译法,读来令人崩溃。
二、宋金战争期间歪曲历史,几乎完全不讲金兵烧杀抢掠之事。和《三朝北盟会编》对比,可见其所述何等歪曲。
三、于辽、金之历史叙述过于简略,每每都是"辽主如××","金主如××"。和《资治通鉴》叙述南北对峙历史之水平相比,不下天壤之别。
于宋元历史而言,此书史学价值低下,又不适合阅读,如今价格亦昂,还不如老老实实读些宋辽金元史为好。
《续资治通鉴(全十二册)》读后感(四):读史散记-读《续资治通鉴》
宋太祖开宝九年(976年),太祖赵匡胤想迁都洛阳,诸臣劝阻不听,最后当时为晋王的赵光义也出面劝谏。太祖说:“迁都洛阳还不算完,时间长了还得迁到长安。”并解释说,“之所以西迁,是为了据河山之险而裁去冗兵,以安天下。”赵光义说:“在德不在险。”太祖不答,在他离开后,对左右之人说:“晋王说的固然很好,但是不出百年,天下民力就要殚竭了。”(卷八)
90年后,英宗治平二年(1065年),岁入一亿一千六百一十三万,官费、军费等支出却达一亿二千零三十四万,入不敷出。四年后,神宗熙宁二年,王安石任参知政事,开始变法。
真宗景德元年(1004年),辽国萧太后与圣宗大军深入宋境,直指澶州。汴京震动,一度有迁都之议,后来在寇准力促之下,宋真宗御驾亲征。十一月,辽方南京统军使萧挞凛在巡视战阵时被宋方伏弩击杀。辽人夺气之余,勒索岁币三十万匹两后与宋方缔盟,史称“澶渊之盟”。(卷二十五)
此事功过不必评价,只知百余年间,宋辽和平得以保持,实是当时苍生之福!
但是1104年,完颜阿骨打起兵时,所遭遇的正是两个110年民不知兵的国家。
如何评说?
宋仁宗庆历年间,时知鄞县的王安石“贷谷与民,立息以偿,俾新陈相易,邑人便之。”这大概就是青苗法的原型试验了。
可是当熙宁二年(1069年),青苗法在全国推行时,味道一下子变了。且不言政府高利贷的正当性与否,最大的问题是,强势的政府有能力强行摊派贷款给平民。管你缺不缺钱,贷款交息!
王安石不是不明白这个道理。推行此法前,苏辙曾给他详细剖析其中利害,王安石也认为苏辙说的有道理,并为之逾月不言青苗。可是当民间高利贷为害时,他还是把政府比富民更强势这一点抛在了脑后,推行新法。(卷六十七)
其他种种新法,也大都有这种设计合理、但是给恶吏留下执行漏洞的问题。
看出这些问题的韩琦、欧阳修、富弼、司马光、苏轼、范纯仁等等一一对神宗及王安石本人苦劝,然后一一被贬出京。
司马光对神宗评价王安石说:“有人说王安石奸邪,臣以为不至于。他只不过是不懂得事理人情、又执拗而已。(但不晓事,又执拗耳。)”窃以为这一评价非常中肯,也非常厚道。
闻誉则喜,闻谏辄怒。君主如此,会谄媚满朝;权臣如此,一样会谄媚满朝。
上面提到的诸位正直有守的大臣被斥去,自然会有小人向利而动。
宁州的一个通判,名邓绾,说青苗、免役等法施行后,“民莫不歌舞圣泽。以臣所见宁州观之,知一路皆然,以一路观之,知天下皆然,愿勿移于浮议而坚行之。”接着被任为集贤校理、检正中书孔目房公事。邓绾乡人对此事的无稽都是又笑又骂,邓绾曰:“笑骂从汝,好官我自为之!”(卷六十八)
于是《宋史·奸臣传》的诸位一一登场,并形成强大势力。
元丰八年(1085年),神宗病逝,司马光在宣仁太后支持下尽废新法,斥去变法派。
苏轼力劝司马光部分保留免役法,司马光执意不从。苏轼只好长叹:“又是一个拗相公!”
神宗刚去世时,时知扶沟县的程颢说:“司马光要入相了。应该与元丰大臣共事,如果先分党与,它日可忧。元丰大臣全都嗜利,如果他们自己变自己的法是最好的,不然,衣冠之祸未艾也。”(卷八十三)
很不幸,司马光并没有听到程颢的建议,听到了也不见得会力行。太后去世后,哲宗亲政,改元绍圣,寓意继承圣人先父的变法遗志,衣冠之祸也就开始了,其名“党争”。
史书称新法派为“小人”,因为这所谓新法派大多并不同意新法,他们只是以支持变法为工具,讨好权臣与君主,然后“好官我自为之”而已。
哲宗之后,即是徽宗了。旧党又一次在太后支持下短暂执政后,徽宗亲政,年号崇宁,意即推崇熙宁,任用的是曾经支持司马光尽废新法、又助章惇重行新法的新法派蔡京。
当时有所谓“六贼”,蔡京、童贯居首,其中还有一位叫王黼,宣和五年时专门负责与金国交涉收回燕山。旧时辽国使至,都不示以华侈,并且尽量带着绕远路,防止辽国生觊觎之心。王黼为早日成就复燕大功,与金使都是以七日自燕山至阙下,凡四五往反皆然。人又浅薄,每次都陈列尚方锦绣金玉瑰宝以夸富盛。于是,金人生心矣!(卷九十四)
这就是变法的遗产之一,党争的直接后果:劣币淘汰良币。
徽宗第二十女,名嬛嬛,封柔福帝姬(即公主),生于政和二年(1112年)。靖康二年(1127年),正值二八年华,其美丽大概可以从她的经历中想像。
其时金军破开封,向宋朝索要海量犒军金帛,宋室无力足其数,乃以女人作抵,名曰“和亲”。 帝姬、王妃一人准金一千锭,赵嬛嬛也以一千锭金的价格卖给了金国。等到金军北退时,她已受辱有孕。三月二十九日,她因不会骑马,从马上摔下小产。此后依然要受负责押送的国禄的欺侮。四月初四,盖天大王见国禄与她同马,杀国禄,弃尸于河。想将其抢去,被劝止后一同北上。抵达金都后,大概因过分虚弱憔悴,一直被争抢的她被弃于洗衣院。(《靖康稗史》)
此即所谓“靖康之耻”的一个缩影。岳飞歌之泣下,辛弃疾歌之泣下,金庸歌之泣下。
宋高宗对金国的恐惧,感觉是深入骨髓,王夫之说他“窜身而不耻,屈膝而无惭,直不可谓有生人之气矣。”同意。但是“考其言动,察其志趣,固非周赧、晋惠之比也。”同意。
南宋孝宗乾道四年(1168年),金世宗秋猎,七月己卯,对点检司说:“一路上庄稼长得很好,要是扈从里有人给踩了,我治你的罪!”
八月乙巳,南宋度支郎官刘师尹请逐渐裁减因军须增加的赋入以宽民力,宋孝宗说:“朕未尝妄用一毫以为百姓病。”(卷一百四十)
宋孝宗与金世宗俱是一时英主,孜孜求治,爱民纳谏。这一时期,是靖康以后读得最为舒心的部分。
再往后,就是一个个奸臣轮流把持朝政,驯至南宋之惨烈灭亡了。
至于元朝,没什么想说的。
始读此书于今年1月14日,今日读毕,用时十月。其间每若有所思,择要记于此,算不得见识,甚至不确定是否正确。总之,一篇“读后感”罢了。
——2014年11月1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