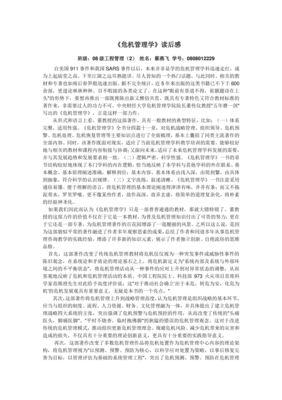
《理论的危机》是一本由[新西兰]斯科特·汉密尔顿 (Scott Hamilton)著作,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的2018-7图书,本书定价:精装,页数:,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理论的危机》精选点评:
●怎么说呢 我以为阅读过程应该是超爽的 结果不然
●这书虽然穿插了不少汤普森的小故事,但是读起来不轻松,一方面汤普森的经历就是斗争的一生,有对有错,另一方面,你需要对汤普森或者他们新左派的历史经历稍作了解,再去看这书更舒服。可惜,《共有的习惯》涉及到的内容少的可怜。
●理解自身所处的文明、文化与地域特性,乃至追溯家族的血脉与记忆,并加以创造性的接合与运用,知道自己从何而来又往何处去,这种做学术的方式其实是一种形而上学的实践。 当然这种去政治化的读后感,可能会把汤普森气活。
●好好的博士论文怎么写成思想(八卦)传记了,没劲
●当学术八卦来读还不错,但是缺少对他们观念发展的探讨。
●其父其兄,原来如此。
●已购
●“特里休就是我啊”
●需要系统地阅读一下EP Thompson的书……不过起码对英国新左派的一些脉络有所了解了。虽然似乎不是我想看到的书XD书中有一些小瑕疵:P.73倒数第三行的《188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应为《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P.80中间引文的倒数第二行“退变”应为“蜕变”,P.221的《理论的危机,或:一个错误的太阳仪》应为《理论的贫困,或:一个错误的太阳仪》
●八卦成分略多,但不影响全书的阴郁色调,EP汤普森的一生,就是这样一种失败挫折与受尊重而被孤立的一生。 “汤普森在反核运动中的高度成功恰恰是工人阶级失败的产物。那些以工人为基础的,曾经不可一世地支配着战后社会运动的各种组织,到1980年代中期的时候都已严重衰退。共产党和工党都被内斗所消耗;他们在不断流失成员,就像他们所代表的工会组织一样。汤普森政治生涯的可悲的悖论在于,他的声名和表面上影响力最大的十年,恰恰是他的名字所代表的那个阶级最失败的十年。”
《理论的危机》读后感(一):《理论的危机》(作者:斯科特·汉密尔顿)
在中国,英国人E.P.汤普森(Edward Palmer Thompson,1924-1993)是广为熟悉的一位左翼历史学家、思想家。受身为作家兼诗人的父亲(生前曾经在印度殖民地从事教育工作)影响,他同时也是诗人,尽管少有作品得到同辈诗人认同。有的情况下,国内对他的介绍会尤其强调是《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作者,突出书名,而不是使用通常的“代表作”等表述。读者一旦知道该书作者是他,无须赘述,通常便可大概知道其在20世纪学术史上的地位。
《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于1963年首版,让时年39岁的E.P.汤普森名声大噪,而很大程度上,他也由此真正被认为是英国第一代新左派最关键的人物。新西兰青年学者斯科特·汉密尔顿的《理论的危机:E.P.汤普森、新左派和战后英国政治》即围绕他展开,包括他的思想主张、价值选择,以及所得到的赞誉和争议。而之所以要取名《理论的危机》,也是因为E.P.汤普森在1978年曾经将自己的一些政论文章以《理论的贫困》为题结集出版,在左翼思想内部(包括佩里·安德森等)引起过轰动、讨论和误解。如今,斯科特·汉密尔顿夹叙夹议的手法,既表达了对E.P.汤普森的一种理解,也再现了英国政治的某些侧面和时刻。新京报·书评周刊-2018年8月25日“书情”
《理论的危机》读后感(二):EP汤普森简要年表的整理
由于对西方新马克思主义理论不甚了解,本书的阅读过程并不轻松,这里只整理一个简单的年表:
1936-1946,汤普森自称为是“英雄的十年”,包括了其长兄在执行保加利亚反法西斯任务时被捕牺牲、其父1946年去世等对汤普森影响十分重大的事件。英国共产党执行人民阵线政策,团结大量知识分子在反纳粹的统一战线一面,二战后工党政府赢得大选,汤普森对于马克思主义核心观念形成。
二战后,青年一代开始抛弃英共乃至马克思主义,思想界转向右倾,其中1956年因赫鲁晓夫公开批判斯大林、匈牙利事件等导致英共人数锐减,汤普森也离开了英共。汤普森在这一时期写出了名著《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获得巨大声誉。
1950年代末-1960年代,他与佩里安德森等新新左派展开争论。1973年汤普森与波兰前马克思主义者科拉科夫斯基展开争论,1978年写出《理论的贫困》。70年代主要与阿尔都塞争论。1980年代他站在反核裁军的舞台上获得高度成功,然而这正是工人运动在政治议题上急剧衰落的另一种表现。他在晚年致力于调查哥哥在二战时牺牲的经过,,出版《越过边境》一书,与年轻时对哥哥牺牲一事的评论相比,他此时更强调人类的能动性在国家及其战争机器面前的不值一提。晚年的汤普森越来越不那么“马克思主义”,譬如他对父亲所代表的的自由主义政治与文化传统的评论显示出与后者某种程度的和解。
以下摘抄数条阅读时会心一笑的片段:
.8:汤普森相信,只有在资本主义的边缘才可能发现针对这一体系的最强有力的替代物。(晚年的马克思也是如此认为)
.20:他说从父亲那里继承的观念是:任何政府都是不能相信的。(这个评论让人有一种无政府主义之感)
.51:汤普森本身并没有想要成为一名历史学者,后者更像是一种意外收获。他也认为历史学者没有必要为了说明自己的观点而堆砌材料取信读者,因为读者迟早都要相信学者有能力给他们带来正确的判断。(汤氏的这一见解,对今日的脚注越来越长、裹脚布式的学术论文也非常有惊醒的意味)
.276:在与阿尔都塞的争论中,汤普森十分警惕前者着意区分什么是“科学的马克思主义”,此外是非科学的,他认为自己感兴趣的是“对历史的理解,而非马克思学”。(汤普森似乎无意向阿尔都塞那样建构一套自给自足的理论体系,他追求的更多是在历史的语境中理解马克思的理论。)
.281:James D. White: Karl Marx and the Intellectual orgins of dialectical materalism 一书根据对马克思晚年手稿的研究发现,马克思已经意识到资本主义并非自发发生,它的发生始终得到国家行动的持续支持。(这一段让人很有Polanyi的感觉,原来马克思晚年已经有这样的看法了!!!)
《理论的危机》读后感(三):E.P.汤普森:一名诗人,一位诚实的社会主义者
本文摘选自《理论的危机:E.P.汤普森、新左派和战后英国政治》,[新西兰]斯科特·汉密尔顿 著,程祥钰 译
出版时间:2018年7月
出版社:上海人民出版社
《理论的危机》读后感(四):E.P.汤普森的未竟之业
汤普森也许是与 "自下而上的历史学"联系最紧密的人物,毕竟同名的论文就是他写的:“history from below”,1966年的《泰晤士文学副刊》堪称石破天惊。(不过事实上似乎只是一份二三页的宣言,毕竟history from below的做法早已经体现在《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中了),当然这本小书里其实并没有提到太多关于《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这本书的内容。作者的重中之重是一本没有中译的汤普森的书:《理论的贫困》。但对于汤普森来说,这本书却不可谓不重要——这位历史学家倾注心血介入现实的政论。
值得一提的是,虽然《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中主角阵容庞大,是那些所有被侮辱与被损害的工人,但其地理范围却局限的很——英格兰。汤普森的研究时期是英国征服世界大片土地的时代,当时大英帝国正冉冉升起为世界的日不落帝国,但它几乎没有承认——或者说几乎没有体现这一现实。这就更加奇怪了,因为汤普森在写这本书的时候,全世界的去殖民化斗争正迫使英国人与帝国主义伦理道德进行斗争,而他本人也是深谙这些问题的殖民传教士的后裔,书中对此深有提及。他的经典文本为20世纪末最进步的英国历史创造了一个岛国模板,不知不觉中竟使 "小英格兰 "的怀旧观念合法化,这种怀旧观无疑在脱欧中体现的淋漓尽致。看来,这可能也注定了汤普森晚年的一种保守化倾向和最终那种“英格兰的特质”捍卫者形象。(《英格兰的特质》也是汤普森的文章名,在这本小书里有讲)
据说,按照EP汤普森出现在两份未发表的文件中的对后殖民世界的延伸思考,“一种地方化的叙述或许是他对英国人长期以来非法宣称能够为其说话的地区应当注意保持沉默的谦逊努力。”但无论他隐含的目标如何,EP汤普森的 "小英格兰 "聚焦点已经被证明是历史学的一个累赘,因为它是对英国历史上一个深度国际化时代的粘滞的地方性描述。至今我们仍不得不在补全汤普森记录的这个属于英国工人阶级的故事所失去的维度。而且很遗憾,这种地方主义已经助长了撒切尔时期编制的狭隘的国家历史课程、已经助长了今日英国人对帝国主义的失忆。斯图亚特-霍尔就在1988年抗议说:国家框架根本不能为我们服务,殖民的历史使人们无法想象汤普森在追忆和力图恢复的那种具有固定的边界和特性的特定社区和传统。更何况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汤普森在寻求摆脱帝国主义的救赎时,对英国社会历史的狭隘框架恰恰使他否认了那些英帝国主义的债。
事实上,英国工人阶级的产生与英国在印度的活动密不可分——印度保持了大量生产军品的高需求,并提供了英国工业竭力模仿的手工棉布。工业革命造就了英国工人阶级,同时也毁掉了印度的手工纺织业。历史学家们长期把汤普森无懈可击的英国工人阶级故事当作理想,浪费了数十年的时间,徒劳地在其形成的废墟上寻找它的类似物。导致我们现在才开始明白,世界其他地方的主体性正是由产生英国 "规范 "的历史过程在不同的方向上形成的。
这一点汤普森其实是有意识的,他仔细阅读过法农在《全世界受苦的人》(台译:大地上的苦难者 似乎更好一些)中所做的判断:不要 "模仿"西方,西方的文化和制度在道德上和实践上都明显地破产了,欧洲正在 "走向深渊"。萨特借来做欧洲的解药,EP汤普森则略带同情地承认, "不仅可以理解,而且是不可避免的",但他对 "西方"已经"没有什么可以提供了"的结论提出了激烈的质疑:因为他努力试图恢复一种另类的截然不同的“英国”价值观——激进的人文主义价值观——这在一定程度上是一种反抗式的救赎精神。“对我们来说,”他解释道,“‘欧洲的游戏’永远不会结束”:“如果‘我们的’传统失败了……那么我们就应该修复它”,而不是草率地得出结论:“西方产生的人文主义价值观已经堕落到无法挽回的地步”。他不正是努力在发现一个不同可能的英国?一个价值观与帝国主义没有任何必然性联系的英国?
所以,汤普森的未竟之业究竟体现在哪里?
作者很耐心的描绘出了一种孤高而阴郁点色调——这种色调的出现,我觉得是在汤普森与第二代英国新左派论战的时候:出版《理论的贫困》,本来他就在《理论的贫困:或一个太阳系仪的错误》对作者戏称为“巴黎之鹰”的阿尔都塞大加批判,现在又对着台下的伊格尔顿吼:“我们必须打倒英国的阿尔都塞主义反人道暴徒伊格尔顿!”
环视四顾,原来都是他的论敌——这种感觉。
汤普森所竭力捍卫的英格兰激进遗产就是他对论敌“英国意识形态”的挑衅的回应——以佩里安德森为代表,第二代英国新左派(总体而言是托派,张亮教授总结的,我自己也觉得就是)声称,与“其他国家”不同,根深蒂固的传统主义、经验主义和地方主义使英国的工人阶级过于温顺和从属,而知识分子则过于守旧和浅薄。汤普森呢,则把自己沉浸在“英格兰的特性”中,上文提到的《英格兰的特质》就是他1965年关于这场争论的文章的标题,是为了捍卫他在历史研究中发现的前辈们激进的遗产——“革命遗产”:“持不同政见者的传统”,属于英国激进者的异议时刻。不过我们知道这些价值观是通过与其他传统的接触而形成的,就像EP汤普森自己激进的价值观一样(来自印度)。他也知道这一点,他批评他的对手认为“民族文化之间存在密不可分的分歧,这是不现实的”。但既然这场辩论关乎英格兰的救赎,那就必须成为他的焦点。毕竟恢复那种“英国”工人阶级的社群主义和自由主义价值观的赌注很高:赎回英国的人文主义和激进价值观。
那么汤普森的激进主义来自哪里呢?父,兄,奥威尔——作者提到的三个重要人物。
老爱德华是一个英国人,但是在印度的经历让他将矛头指向了大英帝国的暴行以及用来掩盖暴行的秘密和罪恶而虚假的宣传,也塑造了他对历史学家技艺的热情信念——将其作为反对国家的揭露真相的手段。这位前传教士利用 "赎罪 "这一宗教词汇,承认并试图救赎历史,使其摆脱了早先作为帝国殖民统治同谋者的话语角色:"我们过去对印度历史的书写也许比我们在印度所做的任何事情都更值得令人憎恨。"这也导致老爱德华和尼赫鲁、甘地、泰戈尔很有交情。这也是为什么汤普森觉得自己 "与印度文化紧密相关",因为这是"父母的遗产"。EP汤普森最终以 "外来的敬意 "这个作者说是既谦逊又疏远的框架公开拥有了这份父亲的遗产——这是他1993年关于父亲与泰戈尔友谊的书的标题。不过他父亲根本不是完全没有问题的好人形象,作为大英帝国的公民,他在印度的形象可能依旧是符合萨特在法农作品里写的那句“杀死一个欧洲人真是一件一石二鸟的好事!”为什么这么说呢?他父亲站在英国人立场上,弄出一种含糊的自由主义——即主张承认印度是印度自己的、具有自治地位,但是为了大英,应当拒绝让印度完全独立。
汤普森对父亲此种做法的评语是:这就好像他既想用他的笔挑战殖民统治,因为残酷血腥的殖民统治总是引发紧急情况,又想向大英帝国的殖民统治者们保证,在紧急情况下,统治者可以指望他拿起一支最好的步枪去为之战斗。
汤普森和哥哥则都是世界主义战士。哥哥弗兰克在1944年被杀害之前在中东从事情报工作,当时他在劳伦斯和拜伦的启发下执行了与塞尔维亚和保加利亚的游击队联系的行动。弗兰克最后的令人心碎的死亡给弟弟爱德华·汤普森漫长的生命中投下了破碎的阴影。他发表的第一篇散文即是关于南斯拉夫游击队的。1947年,汤普森选择去协助南斯拉夫修建铁路。多亏了父亲和兄长,爱德华·汤普森从小就“认为政府是虚伪的和帝国主义的,并认为自己的立场应该是对政府怀有敌意的。”哥哥弗兰克的死也加强了这种看法。1946年父亲去世后,面对“英国反历史的官方机密法案”,EP汤普森继承了家族的斗争式优良传统,并且致力于解决哥哥去世之谜,并得出结论:“国家理性与历史事实处于永恒的战争状态”。
对于奥威尔,汤普森的态度就是很复杂了。作者有写,他很喜欢奥威尔的文学和诗歌,在三四十年代也是奥威尔启发他直面那些过去未曾直面的东西。导致战后很快他就开始批判斯大林主义。这里依旧回到《理论的贫困》,那里有一篇作者重点提到的《鲸腹之外》——而丹尼斯•德沃金则写道,“针对佩里-安德森将知识分子理解为激进运动的理论家——而非建设者——的观点,EP汤普森捍卫了'典型的英国激进知识分子实践概念,它建立在知识分子和工人之间尽可能广泛的交流基础上。知识分子的位置是在斗争的 内部,阐明'那些被统治阶级的经验和愿望'。”他追溯到奥威尔(1940年)的文章《鲸腹之内》(Inside the Whale,1940年),这篇文章在面对全面暴力时吹嘘了一种非合作的不抵抗主义,而这也是荒谬。“我们必须离开这条鲸鱼。”EP汤普森在1978年恳求道。
父亲的经历与人脉也导致了汤普森的一次出国访问:
1976年,在尼赫鲁的女儿英迪拉-甘地(Indira Gandhi)领导下的紧急状态期间,EP汤普森对印度进行了为期六周的重要访问,这是他写出《理论的贫困》(1978年)的关键推动因素之一。抵达印度后,EP汤普森受到了热烈的欢迎,以感谢他父亲与已故首相尼赫鲁的友谊。他把自己童年时对尼赫鲁的回忆录了下来。然而,目睹了英迪拉抛弃其父亲民主原则的程度之深,他很快就对印度的现状感到失望。更糟糕的是,莫斯科领导的印度共产党非常支持她的镇压措施,不辞辛劳地创造理论上的抽象概念来证明紧急状态的滥用是多么的合理。这次访问让他深感不安,因为西方现代化理论(自由进步叙事的更新版本)与莫斯科主导的社会主义理论原来能够如此深度的融合:两者都设想由知识精英通过自上而下、资本密集型、技术驱动的发展,将进步强加给国家。在他看来,这两种人,其难以得到汤普森欢迎的政治视野是无比庸俗的。
老爱德华也培养了兄弟两个对拜伦式英雄的迷恋——那种为受奴役人民牺牲,从而赎回英国罪孽的诗人英雄形象。比如作者说,1936年在加尔各答的时候,他用自己的战时英雄主义笔调写信给大儿子弗兰克,谈到某些人 "被某种东西所抓住,......使他们有一种命运感,使他们无所畏惧"。他谈到了那些时不时出现以挽回国家不道德形象的英雄们,回忆起拜伦为希腊事业而牺牲的情景,他想知道:“今天一个人能通过一种姿态来实现任何重要的事情吗?"
正如汤普森在《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中所说的那样,他的拜伦主义明显地体现在他所宣称的目的是要把历史上的失败者 "从后人的巨大屈辱中拯救出来"。但这也表现在那些推动他历史学工作的当代政治目标上。他一边写这本书,一边指导在他的历史机构的工人教育协会学生,领导极具群众基础的 "核裁军运动"(CND),并和朋友们在英国建立了 "新左派"。二战这场战争,以及它在日本原子弹爆炸中的结局,使爱德华·汤普森对那些经常为殖民主义辩护的进步叙事产生了更深层次的怀疑——这一叙事是要从马克思本人清算起的。他在书中告诫说:'我们的判断标准绝不应该是一个人的行为在后来的演变中是否合理。“毕竟,我们自己并没有走到社会演化的尽头。”至关重要的是,他希望过去的那些'注定要失败的努力(或行动)'可能会产生'对我们尚未根除的社会罪恶的洞察'。EP汤普森对 "失落的努力 "的敏感,让人想起瓦尔特·本雅明1940年去世前夕的坚持,"曾经发生过的一切都不应被视为历史的失落",以及他希望 "被救赎的人类 "能够体验到 "过去的完整"。(本雅明《历史哲学论纲》)1931年,虔诚的卫理公会历史学家赫伯特-巴特菲尔德(Herbert Butterfield)也驳斥了这种"历史学的辉格解释"的基本观点——即历史学家的工作是对过去的人作出道德判断。因此在这个去殖民化时期里,人们希望重塑和挽回英国的身份认同,也即汤普森所追求的工人阶级社群主义价值观——而不是像奥威尔在法西斯主义时期那样,长期吹嘘的(英帝国)统治阶级的家长式价值观。
笼罩在汤普森对英国历史写作的一个重要分支承诺就是实现道德和政治上救赎性的民主目的,这个目的是由反殖民主义的联系和对话造成的。如果说EP的地方性聚焦掩盖了这些动机,那么这种联系本身的力量,以其所有的开放性和跨国萌芽,仍然是他的激进主义的核心——在专制主义笼罩在世界上空之时,这种普遍的人文价值,值得我们回顾。
最后,回到1963年汤普森的《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序言:
因此,本书不如说就是一组论题彼此相关的论文集,而不是首尾相连的叙述文。在选择这些论题时,我常常意识到我正在向流行的正统观点挑战,比如说,这里有费边社的正统观点,它把工人群众看成是自由放任政策的被动的牺牲品,只有少数一些卓有远见的组织工作者不在其例(其中最突出的是弗朗西斯-普雷斯)。经济史学家以经验为基础,他们也有他们的正统观点,他们把工人看成劳动力,看成移民,看成一系列统计数字的原始资料。此外,还有所谓的“天路历程”正统观点,它在这一整段历史时期中上下搜索,要找出各种各样的先行者一一诸如福利国家的先驱、社会共和国的前辈、以及(最近流行的)理性工业关系的早期实例等等。当然,所有这些正统说法都有一定的道理,它们都扩大了我们的知识面。但对第一、第二种观点我要说:它们很容易忽视工人群众的主观能动性,忽视他们在创造历史的过程中自觉作出的贡献;对第三种观点我要说:它用后人的眼光来看待历史,而不顾及历史本来的面目。只有成功者(即他,们的愿望预示了后来的发展的人)才被记住了;走不通的路,迷失的事业,还有那些失败了的人则统统都被忘记。 我想把那些穷苦的织袜工、卢德派的剪绒工、“落伍的”手织工、“乌托邦式”的手艺人,乃至受骗上当而跟着乔安娜.索斯科特跑的人都从后世的不屑一顾中解救出来。他们的手艺与传统也许已经消失,他们对新出现的工业社会持敌对态度。这看起来很落后,他们的集体主义理想也许只是空想,他们的造反密谋也许是有勇无谋;然而,是他们生活在那社会剧烈动荡的时代,而不是我们;他们的愿望符合他们自身的经历。如果说他们是历史的牺牲品,那么他们现在还是牺牲品,他们在世时就一直受人诅咒。 我们在作判断时,就不能把这一点作为惟一的标准,即人的活动是否被后来的历史发展所证实。不管怎么说,我们自己也不是在社会进步的最终点上,工业革命时期,人们失败了的某些事业,也许能让我们看清至今仍须整治的某些社会弊病。此外,还有两个特别的原因使这个时期尤其引人注目,就是:第一,在这个时期,人民运动特别注重平等与民主的原则,我们虽然时常夸耀我们的民主生活方式,但在那些关键的岁月里发生的事,却又常常被人们忘记或忽视;第二,今天这个世界,大部分地区仍存在工业化带来的种种问题,存在着为建立民主而带来的各种问题,这些问题,和我们在工业革命中的经历相比何其相似——那些在英国失败了的事业,说不定会在亚洲或非洲取得胜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