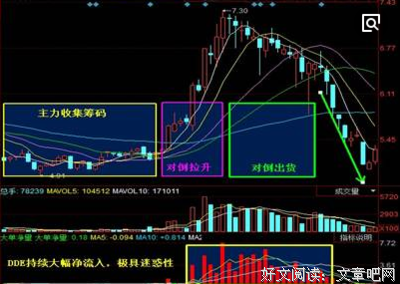
《對倒》是一本由劉以鬯著作,獲益出版的335图书,本书定价:78,页数:2000,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對倒》精选点评:
●这个版本很好,刘以鬯在序言里有写,是他的友人在他心情低落时帮他出的,不仅收了《对倒》的长短两个版本,而且附录了许多关于《对倒》的评论。
●20151205-20151208
●今天看到消息说刘以鬯先生去世了,遗憾,这才看了他的第一本书。说的是浪漫和偶然。
●这种写法给我打开了新世界的大门……
●虽说完成顺序上长篇在先短篇在后,但由于看的时候先读了短篇,反倒觉得优于长篇。短篇相当于缩减版,留白非常多,而且“将记忆当作燃料”的淳于白与“将想象当作燃料”的亚杏间“间接关系”的发展与对称感异乎寻常的强烈,行文格式上的对称双线也更清晰。长篇发展到2/3段后,有大量关于香港楼价和治安的忧虑,前后重复多次,实在不太必要。这版还有大量辅助资料,不过价值不太大,评论居多。无论如何还是很喜欢刘以鬯,以及他对于文学形式“新与美”的不断追求。P.S. 小说名译自法语Tête-bêche,邮学名词,指一正一负的双连邮票。作者灵感来源于这样一套慈禧旧票,想必是这版封面上那张,装帧的出版社也费心思了。P.P.S. 学校的popular books只允许借一周,可以治治我这懒人。
●没有《酒徒》好看。1972年。
●很有用意地写短篇小说
●双线格局,意识流动,看似无事,不厌精细。
●冲着电影《花样年华》把这书看了,感觉双线手法有点王家卫电影的感觉。 - 那是种难堪的相对。她一直羞低着头,给他一个接近的机会。他没有勇气接近。她掉转身,走了。
●关于回忆与期待
《對倒》读后感(一):电影,梦与都市
小说中的淳于白和亚杏都是都市中的漫游者,他们的行走有点类似于梦游的性质。淳于白是在回忆过去,换的是精神分裂症,而亚杏一直在幻想未来,可以说她是白日梦或偏执狂的患者。
对于自我的观察以及自体性爱体现出了大都市里的孤寂状态。在都市中,每个人都是原子化的个人,有着各自独立的精神状态,都是以个人的形式汇入到集体。金钱的逻辑开始支配人们的生活、支配人们的感情。小说中,亚杏所有自我想象的逻辑都是金钱和性的逻辑的延伸。 电影屏幕的场景变成亚杏想象的根源。在一定程度上,亚杏是文化工业的牺牲品。而“生活中的戏剧”表明生活本身已经被戏剧化了,生活在模仿电影。
《對倒》读后感(二):私人对倒
2020第一本书。一本标题里有“2”的书。
第一感几乎是本香港的达洛维夫人,只不过一个是战后重创的日不落帝国,一个是战时避难促成泡沫经济的香港。如果说前者关于人物欲说还休的情感和情绪是在暗指殖民主义梦碎的余威,那么后者贯彻始终的各色臆想则更服务于凸显现代化进程中个体与个体的脱离。
两条看似不相关的平行叙述以特定的物品(如街道、各式标签化的路人、姚苏蓉的歌、车祸、电影等公共场合,以及镜子、天花板、梦境等审视自我的途径)关联起来,乍看有种达洛维夫人式的意识流写作风格。但细看这种流的连接是错落的,是参差的,总是同样的句子差着一两节,并且态度是大相径庭的——尤其是性别态度。
一个幻想千百种浪漫未来,一个把时代个体的回忆当燃料,归根结底都是对现实(新闻)的解读,进而厌倦、逃避、失望,在公共交通和大众媒介里寻求在场。
二人相聚在戏院观影,相貌也才由得彼此的眼介绍出来——于是又变成老男少女的语境,一树梨花压海棠,何况海棠自出场便拎着一只梨。相聚之后叙述视角从自由间接引语转为间接引语,但直到这场相聚结束,二人之间也只有无声的误解,作者的声音同时代背景悄然退场。物理层面的联结,精神层面的断裂,自南北来,各奔东西。
对倒,Tête-bêche,一正一倒的双连邮票。如镜中人,是对立或互补,终归是二元。要么破二为众,要么合二为一。
归根结底,刘以鬯还是写了个私人故事。
《對倒》读后感(三):对倒是个好剧本,作为文学却颇有瑕疵
个人见解,欢迎批判。
被王家卫的花样年华吸引过来,同时觉得“对倒”是个颇为意味深长的名字,它在邮票学上指一正一倒的双连邮票,感觉用它来形容人的关系还挺酷的。
看完这篇小说,第一映像是它真的太适合改成电影了。平行蒙太奇和各种镜头设置的灵感,让人能看到故事发生时的完整画面。但是我依然觉得它的文学建树被豆瓣严重高估。作者本人说自己“写过没有故事的《对倒》”,然而他很明显在塑造两个人物擦肩而过的故事,他加入许多情绪渲染,利用物质和街景强调人物心理世界。像这样的设定,在情节三角中被称作小情节故事,它有自己的讲究,而不应该被误以为是“没有故事”。
虽然情绪渲染占了主要部分,不代表作者应该把大量人物幻想堆砌在小说里,描写和修辞也是真的太过于琼瑶,女人满脑子嫁嫁嫁,男人满脑子回忆回忆回忆,这两人不过是住在同一个不算大的地方,偶然遇见了彼此,但他们没有持有对生活同样的疑问和思考,也没有因为遇见彼此产生一个不可逆转的心理变化(虽然表面上他们的生活都没有改变)。这不是一个好的对生活的剖析,个人看不出男女主角的关联在哪里。而且两人的幻想被重复太多,重复的同时又没有加入新的冲突和理由,导致索然无味。比较适合初中生看,作为一种情感的启蒙。
不过我很喜欢他对市井生活的琐碎描述,很生动。以及利用穿牛仔裤的路人来拉近两个主人公的距离。如果这位作家晚生几十年,一定会成为一个成功的电影剪辑师。灵感是很棒的,它能和王家卫的思维发生化学反应,衍生出经典的《花样年华》,实在是很幸运了。
《對倒》读后感(四):见微知著,而且有点让人醉熏。
“亚杏走出旧楼,正是淳于白搭乘巴士进入海底隧道的时候。”
故事就这样开始了。两个不相干的人,他们的生活切面和意识片刻在作者营造的时空里,被许多的陌生人,现实的戏剧交错在一起。最后电影院相遇,但只是你看我一眼,我看你一眼。排排坐下的一个钟里,使各自的生活场景和经历对上头。然而,随着散场各奔东西,一切又分开到“正常”的状态。作者似乎用必然的逻辑开偶然的玩笑。不同个体的世界永远只是岸上和岸下的区别。
这使我觉得这是一个关于探索个体存在形态,性质和它的可能性的故事。
为了对倒成像,情节显得散断,但虚线的缝隙中能散出匆匆人生的味道。大构架的叙述方式如果可以让人客观一生,那么小而精的描写则一定能激起内心最深处的共振。
从他们的视角,一些微不足道的场景给放大到跃出纸面,直逼我们的记忆角落,它们突然变得如此熟悉,就像我曾经也在里面逗留过,甚至发生过什么的。
于是主人公的回忆变成了集体记忆。对,这也是一本关于记忆的故事。见微知著,而且有点让人醉熏。
以下是我喜欢的句子。作者很冷静地去讲述,句子有举重若轻的机巧,也有无限况味的张力。
淳于白:
属于那个时代的一切都不存在了。
给记忆中的往事加些颜色,是这几年常做的事。
救护车来到,使这出现实生活中的戏剧接近尾声。
亚杏:
将来结婚,找房子,一定要有好的环境,近处绝对不能有公厕。
事实上,展现在眼前的一切都是看惯了的。
她固执地认为年青男子应该留长头发,应该穿“真适意”的牛仔裤,应该将右手塞在裤袋里,应该用牙齿咬着香烟。
她觉得自己最适宜唱这首歌,而且唱得很好。
将肥皂擦在身上,原是一种机械的动作。当她用手摩擦皮肤上的肥皂时,将自己的手当作做了别人的手。
必定是一部好电影,要不然,怎么会有这么多观众?
何况,她长得一点也不丑。
风扇开动时,有风,怎会积聚这么多尘埃?
《對倒》读后感(五):穿过海底隧道时,你会想起什么?
少女亚杏和中年男子淳于白,在繁嚣的都市里,看到相同的人事物。少女憧憬金屋娇贵,当上明星,有白马王子的未来,中年男子回首物资充裕的过去。而处于现实的此时此处,却都徒留白日幻想和失意‘。
小说的开头,是从上海避战乱迁居香港二十年的淳于白坐着公共巴士穿越海底隧道的心理活动,想到他人对香港的评价,想到自己这只南来的北燕在港岛这么些年来受到风俗习惯差异和财产、社会地位变迁的冲击。而少女亚杏的出场,更是带着真实扑面而来的市井气息,被白蚁蛀掉的木楼梯嘎吱作响,手里拿着姨妈给的梨子,心里想着一朝发财给爸妈买房,自己当上明星,交上帅气的男友,过上锦衣玉食的生活。不过是些升斗小民,是些不切实际的白日梦想,却非常真实。
在刘以鬯的小说叙事里,你会感觉到一种时空感,颇为动心的字句有两处——“亚杏走出旧楼,正是淳于白搭乘巴士进入海底隧道的时候”,这一句出现在淳于白的出场和他半生的浮沉荣辱的交代之后,亚杏拿着梨子从木楼梯走下来,之后的章节安排,便是一章淳于白一章亚杏的交叠,他们生活在港九这天地,在各自的生活轨道里,而把他们串联起来的是他们各自碰到的相同的人事物:在银色灯柱下撒尿的那只像头猪的黑狗,金铺被抢劫以后,混乱的场面,街坊四邻的议论以及茶餐厅里母亲早逝,被父亲没有耐心严厉呵斥却一直念叨着想吃雪糕的小男孩... ...
经过了这么多的相同场面引起亚杏和淳于白的不同心理反应和感受以后,他俩终于在一场下午五点半的电影里相遇,很多人去看,座位只剩下视野不好的G46和G48,淳于白先到场,选了G48,亚杏没有选择地买了最后一张影票,他们互相看了一眼,淳于白觉得亚杏长得不差,青春气息逼人,亚杏呢,在自家楼下捡到情色画报以后,唤醒了性幻想,却觉得眼前这个中年男子举止猥琐。两人没说上话,相遇的结果是当晚,两人都做了一场梦,亚杏梦见自己跟英俊帅气的男子结婚,淳于白则梦见自己年轻了二十岁,与裸体的亚杏在床上(没交代是否不可描述),小说在第二天淳于白拉开窗帘,看到“窗外有晾衫架,一只麻雀从远处飞来,站在晾衫架上。稍过片刻,另一只麻雀从远处飞来,站在晾衫架上。它看它,它看它。然后两只麻雀同时飞起,一只向东,一只向西。,行文至此处,戛然而止。麻雀的场景,正如亚杏和淳于白在电影开场前对望了一眼,散场后,亚杏朝南走去,淳于白朝北走去。日后,他俩有没有再相遇,或者,生活有没有交集,都不再重要。重要的是,《对倒》呈现了一种常见的生活场景和人生际遇。
不清楚刘以鬯是否跟王家卫一样,出生在上海,后迁居香港,对上海文化有深沉的迷恋。但可以确定刘以鬯本人由20世纪四五十年代香港大规模迁入上海人的经历或者听闻。小说的语言具有很明显的粤语表达和香港文化,比如赛马比如类似于彩票的马票,淳于白看到“横财就手”竹竿上的马票,心下想到自己不会去买那廉价的美梦。
有意思的是,刘以鬯的叙述,真有一种在逛街的感觉,他是按照人在街边铺面上走的时候,视线所到之处来描绘的——“照相馆隔壁是玩具店。玩具店隔壁是眼镜店。眼镜店隔壁是金铺‘金铺隔壁是酒楼。酒楼隔壁是士多。士多隔壁是新潮服装店。”然后故事场景,就自然而然过渡到新潮服装店发生的事情了,真的是很有香港特色的描述,不论语言、场景和思维模式,有点儿期待伍韶劲在2017香港巴塞尔艺术展的装置作品《二十五分钟后》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