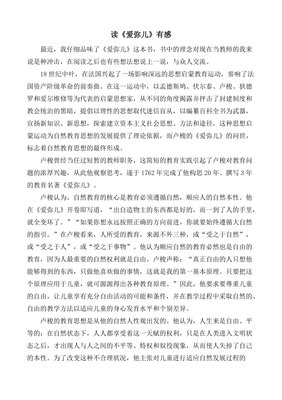
《一场夭折的中国文化启蒙运动》是一本由林伟然著作,UMI Company出版的平装图书,本书定价:38.00,页数:210,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一场夭折的中国文化启蒙运动》精选点评:
●一场夭折的中国文化启蒙运动——阶级斗争理论和文化大革命
●终于读完了自己“读了”很久的书,译者水平有限,人名翻错了不少,比如李鸿永,翻得不伦不类,让人不知所言。这本书最好的是第一章,问题意识很好,如对社会冲突论的批评,提出意识形态的重要性这点也很好,并且意识到了阶级斗争理论所带来的多重效果,这非常好。可惜论证不充分,材料是官方公开出版材料,而且没有做辨别,不过,作为先驱,还是抱着同情之理解,毕竟96年的时候宋永毅还是刚刚开始做文革研究的资料搜集工作,不过,我还是很希望能看到林伟然分析自己提供给迈斯纳的材料。毕竟,那个时候,历史学并没有进入文革研究的领域,直到今天,我们还是不得不遗憾的说:我们并没有比林伟然高到哪里去~
●有新意而未有大突破,局中人的偏见影响客观性
●可以与邓力群的国史回忆录对读。通过对海外文革研究的各种教条的批判,这位至死不渝的造反派坚持文革虽然失败,仍是一场真正的思想战。最后两章他谈到造反派与改革后自由主义思潮的关系,可惜这一部分并没有充分地展开。而整本书把讨论封闭在思想领域,也有明显局限。但这都不能抹杀这本书的价值
●1。材料的问题;2。时间上的论证问题,为什么谈“启蒙”全用的是70年代末80年代初,乃至那些出了国的人搞起来的东西呢,需知民运人士的代表性究竟有多大。
●逻辑混乱
●mcfarquhar死的时候 就老想到这个人 想起来以前一直觉得mcfarquhar跟这个人是一伙的 所以印象就很好 就 无产阶级文化大❂❂ 就是好 酱
●根据分析了解,wge这场运动有私心部分,起因是之前的三年饥荒。觉得它是改革,甚至还要说成是启蒙运动,也是强而言之。这样说,怎么样才是彻底启蒙?要怎么进行彻底?愚信是启蒙?粉碎四什么人?
●读着读着,五味杂陈,想哭。后记挺感人的。
《一场夭折的中国文化启蒙运动》读后感(一):我想买这本书,因为他曾任过我们小学老师,留着纪念,有朋友告知那里可以买的到?他在英德硫铁矿锦沄分矿小学任教时给我留下极深刻的印象,加上对文革历史感兴趣,所以很希望买到这本书。。。。。。。
。林伟然老师,给我最深的印象是:他还在锦潭小学当老师时,就住在旧矿部,有天旁晚我和另一同学到他宿舍,现在也不记得为什么去找他,当时他跟覃世保老师住一起,我们一进门,我看到他彼着毛毯在看书,因为是天气寒冷,当我走近一看是(毛泽东选集第五卷)是最新发行的,他说:今晚上我准备看完他。当时我想,我看几天都看不完,他一晚看完,内心真佩服,現在想起来他对文:,史,哲很感兴趣,在那个年代他一定读了很多书。我记得他教我们不知是物理,化学时,上课一开始都引用一段毛主席语录。
《一场夭折的中国文化启蒙运动》读后感(二):真相就像是橄榄油,它总会浮出水面。
治病救不了中国人。
中国的落后,不是别的,是思想的落后,有的人说民主,民主。不改变思想不可能有民主,这不是耸人听闻。
我说一个最简单的例子,在农村,老百姓就没有民主的思想,让他投票,总觉得治理国家是读书人的事情,自己完全意识不到自己是国家的主人,在这样的国家,哪怕是普选,也不可能得到真正的民主。
文革是一场伟大的思想解放运动,但是要解放思想,甚至不是一场文革就能改变了,几千年的封建思想残留,治理国家似乎是知识分子的特权,现在很多的知识分子就有这个思想,谈民主,你自己就没有是民主。
没有思想的解放,就没有民主,哪怕是有,也是欺世的民主,假得民主。
要改变人们的思想,一场文革是不够的,现在的国家连一个开国领袖的书都能禁,这样的国家,怎么会有民主?!
《一场夭折的中国文化启蒙运动》读后感(三):忆林伟然 -- zwp
转帖者曰:莎士比亚说过有两样东西可以超越死亡1、你所留下的后代;2、你所留下的著作。
我和伟然可以说是在同一个村子里长大的。最后一次见到他的时候是在1968年,之后各奔东西,在他后来的上山下乡、回城、招工、考大学和留洋的日子里我再也没有见过他,也不曾有过任何一点他的音讯。一直到2008年广雅120周年校庆初三甲班聚会的时候我才知道伟然已于1997年病逝于异国。小蓓送给我一本伟然的博士论文(中文译本)名为《一场夭折的中国文化启蒙运动——阶级斗争理论和文化大革命》。阶级斗争和文化大革命都是我们这代人经历过的,但我这个没有太多思想的人要读懂一位思想者的论文可说是勉为其难,读着读着我就会想,伟然的这些思想是从哪来的?我试图在我的记忆里寻找与伟然有关联的往事,试图在他的论文里寻找那些往事的印记。
我们的村子坐落于珠江南岸,一排一排像营房一样的民舍就建在一个个稍事平整过的黄土岗上,那土黄里带红,还夹杂着非常细腻,柔软的白色粘土。儿时的我们总喜欢收集这些白粘土,然后将它们捏成各式各样的小玩意。伟然家那用细竹子围起来的后院紧靠着进村的铺了石子的大道,光着脚在上面走,钻心的痛。那个时候时兴赤脚。偶尔有汽车或马车经过扬起灰尘,后院里的植物总盖着一层厚厚的尘土。我有时经过,隔着竹围栏与伟然说会儿话,他兴致勃勃地给我说他家种的和喂养的东西,在那物质匮乏的年代这一片小小的天地里喂养的鸡、鸭、还有兔子、葵鼠什么的给村民们带来许多乐趣。
村子很大,很新,看得出来这一排排平房刚建好不久。那形状特别的瓦说是劳改场的人做的。村里的家庭主要来自电讯、邮局、航运,还有美院。村里的学龄儿童很多,除了一所公立小学外,还办了一所民办小学。其实我是上了广雅之后才认识伟然的。在村里他上的是公校,我上的是民校。两所学校靠得很近,我们放学经过公校的时候,公校的学生会一边唱着“民办老师无教育,教埋的学生偷腊肉。”一边用石头袭击我们。那么点年纪就学会了歧视。不过我想在当时的混战中谁也没少动手,我相信伟然也在其中。
我们的“民办老师”班主任当时为我们还真没少花心血,为了我们考上好学校她两口子一起在家里给我们补习。后来文革的时候她被整得家破人亡,说她过去是三青团。不管什么团,或为热血青年,或为生活驱使。有一件事困惑了我许久,为什么伟然能上公立学校,而我和我的伙伴们只能上被歧视的民校?当时负责报学校的人说因为我们二年级才来到村里,公校已满额。可是同在民校的泱从一年级开始就已经是村里的居民了。假如是公平竞争,写着一手娟秀的钢笔字的泱不可能上不了公校。前不久给泱打了个电话终于搞明白了,当时是按出生日期排列,年长的先被公校录取。泱当时被分到民校,一年级的临时课室就设在地主塘后面的“鹅寮”,从二年级开始才有了新建的课室。看来伟然可能比我们年长几个月吧。
不管是公校还是民校,孩子们的生活在村子里充满了乐趣。在池塘边和水田里捉青蛙,钓鱼,钓虾。捕麻雀,弹玻珠,拍公仔纸,放风筝,骑牛。还有弹弓叉,火药枪什么的。离学校不远的地方有一棵大榕树,每天放学的时候孩子们最喜欢到那个榕树头玩耍。挑担卖咸酸的总在那里候着,一、两分钱的三捻干、酸黄瓜就能吸引住这些嘴馋的孩子。我最感兴趣的是补镬,在我心目中补镬佬是天底下第一能工巧匠。看他把风箱拉得 “扑哧”,“扑哧”响,炉子里的焦炭喷出炽白色的火舌,旧铁镬敲成的碎片在茶煲柄做的钳锅里慢慢熔化,提取铁水的小勺也是用粘土和铁丝现做现烧的。最后的一道工序就是用毡布盛着铁水,在铁镬的破损处来个“上下夹击”将破损补好。村口也是一个好去处,摆地摊变戏法的,卖跌打药的,代写书信的,还有打马掌的,好像还有算卦的。后来这些靠穿街过巷和摆摊谋生的慢慢不见了,大概都回乡耕田或进工厂了吧,不过那阶级烙印可是抹不掉的,那个时候时兴讲阶级,讲出身。不同阶级之间你争我斗,惨了这些学龄儿童,从小小年纪开始就带着这阶级斗争的心理阴影慢慢长大。细想一下,后来出了那么多红卫兵也就不奇怪了,这应该也是伟然研究的东西。后来经济困难了,有人在村口摆卖点番薯,鸡蛋什么的。那个时候的孩子饿得慌,有一天,班里的一个男生眉飞色舞地告诉我们说家里刚收到亲戚从香港寄来的一罐花生油,趁父母不注意他把盖子拧开咕咚咕咚就喝下去几大口,那个香啊!馋死我们这些听故事的。
上了广雅之后,我们只有星期六才回到村里来。公共汽车在村口有个站,有时也碰巧与伟然同乘一辆车,下车后他先到家,我还得走一小段路。五、六十年后的今天,村子早已不复存在,那些黄土岗早已被推平,上面的房子说不定早已建了又拆,拆了又建好几遍了。但翻开地图居然还能找到一个叫“五凤”的地名,当年这一片属“五凤公社”。在广雅的三年正是求知欲最旺盛的几年,我对实验室里的各种仪器特别感兴趣,课本里的东西没记住多少,印象最深的是贪玩。在我的记忆中当时的伟然在班上并不出众,既不是“三划鸡”、“二划鸡”,也不是科代表,不过有时也会为了一些问题与人争得面红耳赤。在足球场上总能看见他玩得很开心。记不清楚他是不是共青团,那个时候共青团对于十几岁的孩子来说是非常向往的东西。
后来文革开始了,不上课了,就像一部分同学一样,伟然也在学校里进进出出。很多的时候他是在读书,也与人辩论。那个时候读书和辩论是很时髦的事,当然,下棋和“练大只”也是每天的功课。我想伟然对阶级斗争理论和文化大革命的兴趣从那个时候就开始了。我对那些书不感兴趣,糊里糊涂的就把那段时间给打发了。不过一次与伟然的郊游我记得很清楚。那是1968年,伟然邀我一同到郊区农村去。伟然知道我手巧,也知道我有一枚红卫兵印章,那个时候就认这么一块木头,这大概是我被邀请的主要原因吧。我们背着蚊帐,草席,毛巾,牙刷,一路走去。对于他来讲,这是“农村调查”,大概是效仿当年的毛润之。对于我来说,反正是糊里糊涂的打发时间,出外换换环境也不错。走着走着,伟然会提出一些问题与我讨论,当然他也不指望我有什么反馈,总不能光走路,不说话吧。说实在的,那农村的景色还真不错。我们在大队部里把桌子拼起来睡觉,从水井里吊水冲凉,在合作社里买吃的。…… 最后我们决定折返广州,而回程是在长途汽车里度过的。…… 几个月之后,我们被运送到农村,这就是文革历史中著名的老三届“上山下乡”运动。自那以后,我再也没有见过伟然了。
* * *
前不久,我把伟然的论文转送给了我的兄弟——一位文革研究专家,希望把伟然的这个非常独特的研究介绍给更多的人。匆忙之下竟忘了拷贝一张伟然在书中的照片,照片中伟然手捧红宝书站在天安门前。找来微缩胶卷版本,我感慨,这四百多页的“鸡肠字”凝聚了伟然多少心血。在《谢辞》里有这样的文字:“本论文献给我所属于的文革造反派的一代人。我曾经与他们分享的经验、激情和理想是我这项研究的取之不尽的来源。我真的相信,理想是比现实更真实。”;“……在中国,我应该感谢很多我的老同学和朋友,尤其是杨倩辉、何碧芬、叶芳兰和傅毓灵……”。我感到伟然也在谢我,也谢我那块木头。我会对他说,不用谢,没有我你照样能做那毛润之式的“农村调查”。其实,较之对他的文革研究我更感兴趣的是与他相处的往事和在村子里的愉快童年。假如今天伟然还在,我会对他说,不如把这篇论文献给所有的人,造反派、保守派,还有那些在这场血腥的革命中死去的和幸存的人。
* * *
伟然的论文发表于1996年,距今也有十几年了。我们今天有更多的资讯和更广阔的视野,更有各种不同的观点。但伟然的论文仍不失为一部重要的文革研究专著。
源地址:http://xgylsjly.blog.hexun.com/87344066_d.html
《一场夭折的中国文化启蒙运动》读后感(四):无名学者林伟然及其文革研究
唐德刚先生曾提到,美国的博士学位需要过五关斩六将,故博士论文的质量很高;有些人终其一生做研究,其后的成绩却再也无法超过博士论文的水平。
纯属机缘巧合,近日得到一部美国威斯康星大学博士论文中文译本,名为《一场夭折的中国文化启蒙运动——阶级斗争理论和文化大革命》,作者林伟然。据译者李玉华《译后记》所述,林伟然“与共和国同龄”,1997年去世;1996年获威斯康星大学博士学位,导师是在台湾和大陆均鼎鼎有名的林毓生先生;《译后记》提及“我们大学的同窗好友”李公明已“功成名就”,则可推测作者1982年毕业于华南师范大学历史系。译者李玉华为作者遗孀。
在这个网络资讯极大丰富的年代,小有名气之人无不能在互联网上查到相关资料,只有这位林伟然先生,在各大搜索引擎几乎查不到任何踪迹。键入中文“林伟然 威斯康星”或其他关键字如“林伟然 林毓生”等等反馈都是零。用作者英文名字和论文英文题目在互联网检索,总算找到唯一一处引用,在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一位学者的著作的脚注中。按一般经验判断,如该论文已在美国公开出版,似乎引用次数不会如此之少;另据以往阅读所知,似乎美国的博士要在论文出版后才正式授予学位(如胡适的“假博士”风波所提示)。再搜,似乎同在威斯康星州的马凯特大学曾有一名叫“Lin Weiran”的学生,学习年份在1988-1991年,因无其他资料而无法确证。看来,这也是一位“思想史上的失踪者”,只不过失踪在北美大陆。
《译后记》自述其家庭在美的奋斗史,十分感人。作者于1997年去世,“当时,我们唯一的女儿才十二岁。承受着丧夫的悲痛,我不仅挑起养家糊口的担子,还要即为人母又为人父。生活在中西文化的边缘,我像很多在国内接受完正式教育才出国的家长一样,常常感到不能与在美国长大的孩子完全沟通。如何帮助孩子走出丧父的阴云,是我当时最大的难题。有很长一段时间,我要陪伴在孩子的床边,直到她沉沉入睡,以便她被噩梦惊醒时,身边还有摸得找着的亲人可以给他安慰。此后的5年,保证孩子身心健康,培养孩子成了我的主要任务。日复一日,我奔忙于我的电脑系统工程师的工作、女儿的钢琴课、女儿的网球比赛,还有她在美国学校里那些大量的科研工作和社会活动,我不时感到心力交瘁,疲于奔命。2002年,女儿终于高中毕业上大学了,这不仅意味着她的长达成人,最令人欣慰的是,她不仅以全校第一的最好成绩毕业,而且还获得了美国总统青年学者奖,这一美国高中毕业生可以获得的最高荣誉。恐怕这也是冥冥中伟然的在天之灵呵护着女儿的成长……”
著名党史、国史研究专家廖盖隆1988年在为王年一《大动乱的年代》一书写的序言中曾郑重表示:我们都不愿意“‘文革’在中国,‘文革学’在国外的现象出现。”20年过去了,廖教授的愿望实现了没有呢?恐怕未也。林伟然在本书第一章开头即说:
“据统计,西方社会出版的有关文化大革命研究书籍和文章必中国近代历史上任何一个时期的研究著作都要多得多。”而起码在近十年来,中国有关这段历史的研究著作,应该是相比任何近现代史的其他时期要少得多。前辈学者愤愤然的“敦煌学在中国,敦煌学在国外”的先例,似乎有在此领域重演的趋势。
作为文革的亲历者,林伟然有着纯国外学者所缺少的无可比拟的优势,很容易用自己的经验直解否定一些“隔靴搔痒”式的理论推导,当然这不等于他所提出的解释就是无懈可击的。
旧的阶级斗争理论,重点在于对地主阶级、资产阶级等及划作对立面的其他阶层如之时,由党组织发动群众加以斗争,以保障社会主义成果。而由毛泽东在文革前期所启示、由部分造反派所发展的新阶级斗争理论,强调的是反“党内的走资派”“当权派”“特权阶层”等,矛头所指,则是以前以“党组织”面貌出现的曾经绝对正确的官僚体系。作者在本书中对毛泽东发动文革的思想根源和国内国际形势的压力未能作出深入分析,只是简单地提出了毛的民粹主义倾向对发动群众闹革命的影响。
书中引用了大量文革期间非正式出版物如红卫兵小报对“特权阶层”滥用权力、生活腐化的揭露,其可信度需要打点折扣,然而也并非都是空穴来风。遗憾的是,文革非正式出版物的汇编,只能在海外才能找到,“敦煌在中国,敦煌学在国外”的旧话又要重提。据说在文革初起之时,美国相关机构已经派人在罗湖桥出入境大厅外向回乡探亲的港人搜集此类“情报”,用一句老话来说,真是“帝国主义亡我之心不死”!这些揭露,略举数例,目的在反映造反派的绝对平均主义倾向的强度,其真实性无法保证。凡出现人名的地方,用汉语拼音第一个字母代替:
“一篇文章描写前广州市长ZS的房子是这样记录的:ZS的豪华房子里有四个大衣柜,每个价值800元,三张席梦思床,每张价值600元,一张桌子价值800元,一张价值几百元的沙发,两张价值各3,000元的地毯。六把电风扇,一个电冰箱,和一个电炉。还有两个照相机,九个晶体管收音机,一个留声机和一个录音机。报告同时还揭露了ZS包租了广州最好的宾馆的一层作为他个人的住处,他还用公家的钱举办了很多豪华宴席。广东省的党委书记ZZY,据说有自己的私人体育场。南方局党委书记TZ被控告为他个人建造了一座豪华房子。”(第118页)
“TZ到工厂劳动时,宣布他不吃肉,以便表明他和工人生活的一样。但事实上,他花了不少于10,000元在吃人参,这些钱可以‘买10,000斤猪肉’。”(第120页)
“文化大革命以前,广州的学校被分为四等。广雅属于最高等的学校,一些干部子弟虽然他们的分数连最低等学校的入学分数线都没有达到,却仍然可以进入广雅中学。例如,一个干部的孩子,他的数学入学考试只有零分。却仍然被招入了广雅。”(第122页)
放在今天,市长的这些东西难入富人法眼。市场经济给了更多的人一个享受物质、分享权力的机会,宜乎激进主义、平均主义在改革后逐渐失去号召力。因之,作者将文革后期至八十年代初新阶级斗争理论及其衍生物(大民主、巴黎公社模式、反特权)当作未完成的“启蒙运动”,是笔者不能苟同的。与五四相比,这一阶段的某些思想火花,既未达到相应的高度,亦缺乏可操作性;何况,由精英来“启”群众之“蒙”,在当下恐怕是“政治不正确”的单相思。公民的自我解放才是正途;若火候未到,点火者只是自焚而已。
作者的结论,倒是极为耐人寻味的:“文化大革命的流产,使中国人民不但放弃了对思想意识形态的探究,同时放弃了思想意识形态本身。而抛弃了思想意识形态,也就放弃了逻辑的论证及理性的思考。没有一个牢固的道德基础,中国人民只能从属于一种不受限制的市场经济的支配。”或许是受制于博士论文的格式,作者没有由此作进一步的引申,这是十分令人遗憾的。正是在文革中,群众对道德、理想、精神追求的热情被过度挥霍,耗尽了所有的能量,才使得今日的市场经济体系带有一切“庸俗”的特征,精神追求在受到极度嘲弄之后的强力反拨,是对物质的极端崇拜和对道德的不屑一顾。今日中国的犬儒主义,乃是文革非自愿怀孕的产儿,而播下了龙种终于收获跳蚤,经手各方似乎皆脱不了干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