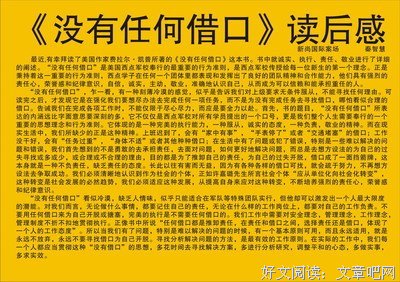
《神圣的存在》是一本由【美】米尔恰•伊利亚德著作,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平装图书,本书定价:48.00元,页数:459,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仿佛是《神圣与世俗》的扩充版
●哈哈,俺的伊利亚德。
●兼收并蓄。符号与象征。禁忌往往是人们恐惧的,有神性的往往是具备伟力的,对农耕社会有益的。有趣的是,其中的很多意向都梦到过。朋友曾经在特殊状态一下,觉得未来的人会生活在宇宙中的一颗树上。而在印度神话中,宇宙就是一颗倒生的树。
●人改造自然,改造的过程也反作用的改造了人;原始人的文化和信仰起源于自然,社会关系需要自然对象及衍生的符号参与。人与自然关系的变化,也就是意味着原始符号的社会功能沉默,人不被自然控制,却要被内部创造的符号所建立的关系控制。关键是,天道无私无欲,俗人却私心多欲,离自然越远,人的内部控制越盛。
●好多啊,看不进去。。。
●2018已读03。伊利亚德的著作常读常新,宗教研究的反化约论进路自他开始。伊利亚德所考察的是一种宗教形态学,即“神显”,亦即神圣观念的各种表现。这部《神圣的存在》可视作《神圣与世俗》的扩充强化版,不但详尽阐述了其方法论,更对不同的神显形式分章节仔细讨论,材料丰富且分析精当,个人认为是了解伊利亚德学术思想的首选入门书。
●一个对着太阳、天空、大地、植物、石头、时间、空间的象征体系,借此理解自身在宇宙中的位置。
●第一章讨论宗教的具体表现形式(神显),第二至九章讨论具体的崇拜类别以及与之相关的象征符号、神话仪式,第十章、十一章是神圣空间与时间两个维度,第十三章是象征(符号)的整体性叙述。
去年在北京单向街书店看到这本《神圣的存在》,吸引了我的好奇。神圣的、宗教的世界观在被现代人的科学意识所消解。神圣还能存在吗?神圣存在何处?神圣对文明的价值是什么?当我决心用心阅读时,它开启了我重新看待世界的方式,而这正是我需要的。
我一直怀疑自己固有的思维方式,我越读书认知越习惯于既有世界的样子。但世界的魅力在于复杂和多样。我尝试以世俗、科学、哲学、艺术、宗教等不同系统认知世界。每种系统都涉入不深,这几乎是不努力的结果,却意外防止了思维的保守。对世界保持敬畏与好奇,用短暂的一生观察“实相”和“存在”的外显。
这本书的意义就是用原始人的“前宗教”状态的研究,以早期的丰富材料体验神圣的存在。
《神圣的存在》读后感(二):伊利亚德:凡人阿,别忘了去看上帝!(内容与标题无关,我只是读的很辛苦)
《比较宗教的范型》是伊利亚德《比较宗教学史导论》的英译本名称。作者米尔恰·伊利亚德以十年之功,将世界范围内的神话、经文及相关的神话学和人类学等相关研究攘括其中,写成此书。
如其前辈和他的后来者一样,伊利亚德试图回答宗教是什么的问题。而有关这个问题的回答,当时风靡一时年鉴学派曾给出一个经典的解释——宗教即社会。
据说伊利亚德年轻的时候是个风流而叛逆的青年,他自然不会同意这种“化约论”的解释。在伊利亚德看来,宗教因其神圣而只能是其本身,历史的或者社会的因素只能是它原型发挥作用的契机,而无法成为决定其的力量。因此,“比较宗教的范型”实际上指的就伊利亚德通过世界范围的神话及其相关研究,其中在方法论上不仅包括所谓的“精英”也包括“平民”的信仰,不仅注重作为整体的观念,同样也不放过个体(大师、宗教改革家)的一套理解、解释。伊利亚德相信,通过如此一番综合而谨慎的方法,或许能描绘出宗教本质的画卷。
尽管,伊利亚德使用的参考文献囊括甚广,实际上几十万字的引用与论述大体可以归为如下三个方面:世界范围内的神话结构的一致性;神圣性、力显、神显如何在仪式中重现;以及神话的综合、碎片化、扩张,以及幼稚等发生的原因。
在第一个问题上,伊利亚德从欧洲到亚洲,从史前到古文明,例举了从天空的崇拜到至上神,从大母神的崇拜再到各种具体的事物(植物、水、月亮、大地)的崇拜,作者相信,尽管细节存在着不同,但作为神话的结构,世界范围内的神话都有着类似的原型结构。而这种原型是超越文化的,是伴随着人类文明的初始便存在着的。伊利亚德拒斥所谓“自然神”式的解释,即宗教产自原始人对宇宙未知现象的恐惧。相反,作者更相信,原始人从仰望星空体验到的壮阔与宏伟这一现象学的原因才可能是人们宗教情感的最直接、根本的原因。
人类宗教的统一范型被揭示后,则是伊利亚德与年鉴学派的真正分歧之处。因为在其他地方,强调仪式,神圣与凡俗的划分,禁忌与危险等经验层面上的论述,作者与年鉴学派的宗教观并无根本的分歧。如果说,涂尔干经典的“集体欢腾”强调了仪式的生成作用,那么伊利亚德所强调仪式的重要性则与他有着根本的不同。这个关键的节点就在于“互渗滤”这个概念上。如果说,人们在集体欢腾中感受到了实在的力量,那么实际上,人们感受到的力量实际上是“社会”的力量流溢到参与者的身上。伊利亚德不同意此种看法,他认为不存在这样的神圣与凡俗事物之间力量的相互流动。仪式所以具有神圣性、力量,是因为它“重复了一种超越模式或模型”,即伊利亚德所谓的神话原型。创世行为的复现,才使得仪式一次次的具有神圣性的特征。这里,问题的关键点在于“社会决定论”多少不可避免的带有进化论的色彩,有关宗教信仰的意识形态的改变,取决于社会本身以及社会间的互动。相反,伊利亚德的复现论则彻底断绝了宗教神圣性的进化论色彩。因为真正有力量,具有神圣意义的是原初的神话范型,任何复杂多样的仪式只有满足于创世神话的结构才能发挥它的宗教效果。这样,神圣的起源永远是指向人类原初的创世时代。实际上,年鉴学派强调了现实层面的意识生成的神圣特性,而在伊利亚德这里,原初神话原型的观念才是一切神圣事物得以实现的根本根本原因。(若参见列维-斯特劳斯对现象学的吐槽,再看伊利亚德的宗教现象学方法,或许会有意思——他们都强调了人类的某种思维结构的统一性,但列当然觉得自己是科学家,但二者的真正差别到底在哪里呢?)
第三个问题,作者讲到了宗教信仰的低级化问题,即“神圣之物”的泛滥。作者指出,这也恰是神圣辩证法的表现形式。一来,神圣的事物总有向凡俗事物扩张的需要与动力,二来,正是这种扩张的表现,让人们更加随意的将凡俗的事物视为神圣的。即作者在最后章节强调的象征体系的问题。在作者看来,原型神话存在一套内部各要素相互关联的结构,事物只有在这个象征结构的内部才能获得其神圣的位置。而又因为神圣结构的扩张的性质,这个象征体系也在不断的扩张,因而才有了神圣事物低级划的现象。
如果用一句话来概括本书作者的意图,那就是:永远不要忘记我们追求神圣、超越的人类本性,而那本性来源于人类所以是人类的那个时刻。
本书的阅读感受差极了,如这里的“阅读”指的是逐字阅读。所以我就要把这个观后感写的“飞”(飞的意思就是我合上书看着屏幕写!)一点。如果只想了解作者的大体意图的话,只读第一章和最后三章就行(或者跳着读都行)。如果想体验作者思索的纹理(虽然我觉得挺零散),比如要发现互渗滤和复现的差别,从而发现作者拒绝进化论的根本动力的话,还是要逐字逐句的看。
不介意强迫症患者观看......
《神圣的存在》读后感(三):重新感受宇宙
有句歌词说:“星星在文明的天空里再也看不见。”——这句话如果用比较宗教学家伊利亚德的概念来解读,那就是:星星对现代人来说,不再是一种“神显”,也就是说,星星不再被认为体现了宇宙的神圣性;人们可能对星星怀有一些浪漫的想象甚至航天征服的理想,但却并不觉得它是一个超自然的存在。换言之,现代人对日月星辰难以产生一种宗教性体验,也因此,我们不容易感受到永恒。
现代文明本质上是一种世俗文明,整个空间和时间都被“去神圣化”了。大部分人都生活在都市这样的人工环境下,对自然的感受是疏离和淡漠的,虽然人们亲近自然时仍感到喜悦,但却很少会引发一种敬畏和神圣的心灵冲动。这也是人们难以理解那些远古神话和风俗的根本原因。它们虽然仍会时不时在我们的生活中浮现(比如中国探月航天工程仍以嫦娥奔月的传说命名),但却只是一些有趣而零碎的片段。因此,要想清楚地知道古人为何要创造那样的神话,其背后到底蕴含了什么深意和象征,我们必须换一种方式重新感受宇宙——也就是说,像古人一样将宇宙设想为无限、永恒、神圣性的唯一根源。
在《神圣的存在》中,伊利亚德不厌其烦、分门别类地列举了天、太阳、月亮、水、石、大地、植物、农业丰产、圣地、神圣时间等十大类“神圣的存在”。简言之,原始人的宇宙与现代的相反,它是一个“圣化的宇宙”,人人都分享着宇宙的神圣性,万事万物都可能成为显示神性的征兆和表象。就像南方壮族传说中蛙是大神和图腾,在怀有这样观念的人眼里,蛙就不再是普通的蛙,而是雷神和雨水的象征,它可以主宰着人们的农业生产收成乃至整个社会的命运。在人力无法主宰和控制自然力的时代,人们通过对神圣征兆的认定和祈祷来消除心情的紧张焦虑,以此在心理上获得一个绝对的支撑点。
古代地球表面有着许许多多彼此隔绝的人类文明,因此也就有无数个宇宙,因为每一个文明都会倾向于认为自己所在的社区是宇宙的中心,是宇宙的支撑点,他们在这个自己构筑的小宇宙中象征性地庆祝整个宇宙中发生的事情。不但如此,人们还迫切地希望那个神显能够周期性地重复自身,通过这样的仪式,他们确认自己的幸福存在。伊利亚德将这种愿望称为“天堂的乡愁”:古代人普遍存在这种渴望,即回归到那个远古的黄金时代,重新获得一种神圣状态——在基督教神学中,那是人类堕落之前的伊甸园,在中国儒家传统中,则是尧舜时代的三代之治。
原始人的这种基本冲动有助于我们理解许多现象。例如无论在西藏,还是秘鲁的印第安人遗址马丘比丘,人们经常将宗教场所修建在山顶上,以现代人的观念看,在这样的地方生活,食物饮水等基本需求都极为不便,很难想象当初为何会选择这样的地点。但对一个具有宗教体验的人来说,高山是最接近天空的,具有一种天然的神圣性,是神的居所,因此世界各地神话中主要神灵一般都居住在高山之上,如希腊神话中十二大神都居住在奥林匹斯山顶。高山也常被视为宇宙的中心点和支撑点,是大地和天空相遇的地方,在此最有可能接近神灵。
中国是世界主要文明中宗教影响力最为弱化的一个例外,高度发达的史学和文字传统在两三千年前就已侵蚀了远古神话,因此中国的神话传说大抵都支离破碎。正因此,中国人要想理解祖先对宇宙的感受,才格外需要比较神话学的研究,否则仅靠一些孤立的证据,想要完整地复原上古中国人的神话思维,几乎是不可能的。
本书中作者很少提到中国神话,但他丰富的例证和谨慎可信的结论却能给我们以极大的启发。举例来说,古代传说和两汉画像砖均表明中国人始祖之一的伏羲、女娲是人首蛇身的形象。从中国古籍中找不到可以说明为何他俩下半身是蛇形的证据,这一形象就成了一个神秘符号。但比较神话学可以从世界各地的许多神话中证实:蛇在原始人心目中普遍被视为长生不死的象征(因为蛇每年蜕皮,犹如复活),常常和雨水、大地联系在一起,在古希腊神话中雅典等城邦的祖先的形象也同样是人首蛇身。又如神农氏尝百草的传说,中国人常将之理解为一个造福百姓的医学英雄,而伊利亚德告诉我们:“有时,植物就是神。”采集草药也是一种仪式,它绝非一种植物,而是“一种充满神圣的实体、缩小的生命树、包治百病的资源”。
阅读这本书无疑是一个令人愉快的体验。不仅是因为作者渊博的学识和洞察力,也因为古人对宇宙神圣性的丰富想像力本身就足以使人赞叹。和他们比起来,现代的传奇故事看起来并没有脱离他们几千年前就划定的圈圈。尼斯湖怪兽的传说和金•凯瑞的《变相怪杰》虽然沾上了现代色彩,但实际上却与上古神话有着高度的精神一致:即认为水具有巫术力量,水中生物或盛巫术力量的器具都沉在海底或湖底。更不用那些述说年轻人付出许多努力后战胜一个个艰难险阻最终夺取宝物的故事——这是许多武侠小说和动画中的经典情节,例如《圣斗士星矢》——而这一构想的根本来源正是出自“鬼怪守卫的不死符号”这一神话母题。
这种包含变化的延续性非常重要,虽然伊利亚德研究的范围只是宗教学和神话学,但他阐述的许多结论同样有助于我们理解现代社会和政治的某些现象。按他的洞察,每个神话,都讲述了一个发生在从前的事件,由此提供了一个先例和范型,此后人们的仪式和行为都是在重复那个神话的原型。任何神圣形式或崇拜不管如何变化多端,都具有这样向某个原型的回归。其实现代政治的运作何尝不是如此?在纳粹德国时代,希特勒上台后每年都要隆重纪念最初发迹的“啤酒馆暴动”,将它理解和渲染为一个神圣事件,其目的则是为了预示下一个同样的神圣事件,因为它不断地强调德国青年要像当年的啤酒馆烈士一样无条件服从和绝对信任领袖。由此,这个原本普通的啤酒馆和事件就成了一种“神显”,被赋予了远远超过它本身的意义。这一切,难道也仅仅是神话吗?
《神圣的存在》读后感(四):《神圣的存在》的读后感
有句歌词说:“星星在文明的天空里再也看不见。”——这句话如果用比较宗教学家伊利亚德的概念来解读,那就是:星星对现代人来说,不再是一种“神显”,也就是说,星星不再被认为体现了宇宙的神圣性;人们可能对星星怀有一些浪漫的想象甚至航天征服的理想,但却并不觉得它是一个超自然的存在。换言之,现代人对日月星辰难以产生一种宗教性体验,也因此,我们不容易感受到永恒。
现代文明本质上是一种世俗文明,整个空间和时间都被“去神圣化”了。大部分人都生活在都市这样的人工环境下,对自然的感受是疏离和淡漠的,虽然人们亲近自然时仍感到喜悦,但却很少会引发一种敬畏和神圣的心灵冲动。这也是人们难以理解那些远古神话和风俗的根本原因。它们虽然仍会时不时在我们的生活中浮现(比如中国探月航天工程仍以嫦娥奔月的传说命名),但却只是一些有趣而零碎的片段。因此,要想清楚地知道古人为何要创造那样的神话,其背后到底蕴含了什么深意和象征,我们必须换一种方式重新感受宇宙——也就是说,像古人一样将宇宙设想为无限、永恒、神圣性的唯一根源。
在《神圣的存在》中,伊利亚德不厌其烦、分门别类地列举了天、太阳、月亮、水、石、大地、植物、农业丰产、圣地、神圣时间等十大类“神圣的存在”。简言之,原始人的宇宙与现代的相反,它是一个“圣化的宇宙”,人人都分享着宇宙的神圣性,万事万物都可能成为显示神性的征兆和表象。就像南方壮族传说中蛙是大神和图腾,在怀有这样观念的人眼里,蛙就不再是普通的蛙,而是雷神和雨水的象征,它可以主宰着人们的农业生产收成乃至整个社会的命运。在人力无法主宰和控制自然力的时代,人们通过对神圣征兆的认定和祈祷来消除心情的紧张焦虑,以此在心理上获得一个绝对的支撑点。
古代地球表面有着许许多多彼此隔绝的人类文明,因此也就有无数个宇宙,因为每一个文明都会倾向于认为自己所在的社区是宇宙的中心,是宇宙的支撑点,他们在这个自己构筑的小宇宙中象征性地庆祝整个宇宙中发生的事情。不但如此,人们还迫切地希望那个神显能够周期性地重复自身,通过这样的仪式,他们确认自己的幸福存在。伊利亚德将这种愿望称为“天堂的乡愁”:古代人普遍存在这种渴望,即回归到那个远古的黄金时代,重新获得一种神圣状态——在基督教神学中,那是人类堕落之前的伊甸园,在中国儒家传统中,则是尧舜时代的三代之治。
原始人的这种基本冲动有助于我们理解许多现象。例如无论在西藏,还是秘鲁的印第安人遗址马丘比丘,人们经常将宗教场所修建在山顶上,以现代人的观念看,在这样的地方生活,食物饮水等基本需求都极为不便,很难想象当初为何会选择这样的地点。但对一个具有宗教体验的人来说,高山是最接近天空的,具有一种天然的神圣性,是神的居所,因此世界各地神话中主要神灵一般都居住在高山之上,如希腊神话中十二大神都居住在奥林匹斯山顶。高山也常被视为宇宙的中心点和支撑点,是大地和天空相遇的地方,在此最有可能接近神灵。
中国是世界主要文明中宗教影响力最为弱化的一个例外,高度发达的史学和文字传统在两三千年前就已侵蚀了远古神话,因此中国的神话传说大抵都支离破碎。正因此,中国人要想理解祖先对宇宙的感受,才格外需要比较神话学的研究,否则仅靠一些孤立的证据,想要完整地复原上古中国人的神话思维,几乎是不可能的。
本书中作者很少提到中国神话,但他丰富的例证和谨慎可信的结论却能给我们以极大的启发。举例来说,古代传说和两汉画像砖均表明中国人始祖之一的伏羲、女娲是人首蛇身的形象。从中国古籍中找不到可以说明为何他俩下半身是蛇形的证据,这一形象就成了一个神秘符号。但比较神话学可以从世界各地的许多神话中证实:蛇在原始人心目中普遍被视为长生不死的象征(因为蛇每年蜕皮,犹如复活),常常和雨水、大地联系在一起,在古希腊神话中雅典等城邦的祖先的形象也同样是人首蛇身。又如神农氏尝百草的传说,中国人常将之理解为一个造福百姓的医学英雄,而伊利亚德告诉我们:“有时,植物就是神。”采集草药也是一种仪式,它绝非一种植物,而是“一种充满神圣的实体、缩小的生命树、包治百病的资源”。
阅读这本书无疑是一个令人愉快的体验。不仅是因为作者渊博的学识和洞察力,也因为古人对宇宙神圣性的丰富想像力本身就足以使人赞叹。和他们比起来,现代的传奇故事看起来并没有脱离他们几千年前就划定的圈圈。尼斯湖怪兽的传说和金•凯瑞的《变相怪杰》虽然沾上了现代色彩,但实际上却与上古神话有着高度的精神一致:即认为水具有巫术力量,水中生物或盛巫术力量的器具都沉在海底或湖底。更不用那些述说年轻人付出许多努力后战胜一个个艰难险阻最终夺取宝物的故事——这是许多武侠小说和动画中的经典情节,例如《圣斗士星矢》——而这一构想的根本来源正是出自“鬼怪守卫的不死符号”这一神话母题。
这种包含变化的延续性非常重要,虽然伊利亚德研究的范围只是宗教学和神话学,但他阐述的许多结论同样有助于我们理解现代社会和政治的某些现象。按他的洞察,每个神话,都讲述了一个发生在从前的事件,由此提供了一个先例和范型,此后人们的仪式和行为都是在重复那个神话的原型。任何神圣形式或崇拜不管如何变化多端,都具有这样向某个原型的回归。其实现代政治的运作何尝不是如此?在纳粹德国时代,希特勒上台后每年都要隆重纪念最初发迹的“啤酒馆暴动”,将它理解和渲染为一个神圣事件,其目的则是为了预示下一个同样的神圣事件,因为它不断地强调德国青年要像当年的啤酒馆烈士一样无条件服从和绝对信任领袖。由此,这个原本普通的啤酒馆和事件就成了一种“神显”,被赋予了远远超过它本身的意义。这一切,难道也仅仅是神话吗?
《神圣的存在》读后感(五):神圣并不“神圣”
伊利亚德提及"it is the scale that makes the phenomenon"。这个问题被很多人注意到了,布劳在《社会生活中的交换与权力》中提到宏观论和微观论,多伊奇在《真实世界的脉络》中尤其提到,世界有许多层级,比如原子物理作用构成分子,分子化学作用构成生命体,生命体相互作用构成社会。正如布劳注意到社会学不能简单归结到当个个体的心理上,伊利亚德也注意到宗教现象在很大程度上也是一种社会现象。布劳和多伊奇都看到了问题,并正确分析了问题,但是伊利亚德虽然看到了问题,但是他跟涂尔干一样,没能清晰地分离出问题。所有的社会研究都面临这样一个局面,个体作为actors,在群体的层面上构成一种群体逻辑。伊利亚德和涂尔干所强调的都是,群体层面上曾显出patterns,正如本书的标题patterns in Comparative Religion那样。所以他们两个都排斥对个体的分析,伊利亚德还嫌弃进化论(应该是指宗教的进化论,跟Frazer有关系)。我认为,任何不跟进化论合作的社会理论最终都是空中楼阁。所以伊利亚德和涂尔干的理论都存在很大的缺陷。
伊利亚德说,只有把宗教当做宗教,才有可能去认识它。假如结合伊利亚德所谓自己“灵感一现”想出来的见解的轶事,这种错误也倒是可以理解的。伊利亚德饮用Roger Caillois的话说神圣和世俗对立,这个说法和涂尔干一摸一样。但是这句话对于分析宗教,没有什么帮助。伊利亚德还说,一开始给宗教下定义没有任何意义。这句话和Weber在The Sociology of Religion开头说得一摸一样。
伊利亚德说,最伟大的经验不仅在内容上有所相似,在表达上也经常是相似的。这种错误就不可原谅。在说这句话的时候,难道伊利亚德就没有想想,小的经验上内容是否相似?在表达上是否相似?比如人的表情,人们的手势,不同的语言之间,不都存在相似性。这只是说明,人的基因智能是类似的,仅仅存在一些文化的差异而已。伊利亚德提到“菩提树”的敬拜源于“它具体体现了在生命的不断更新中宇宙的神圣意义”。我认为大部分神圣,至少在最初,大部分神圣的来源在于对难以驾驭的laws and principles或影响到生活中不确定性部分在具体事物或事件中的体现。人们之所以把这些物、人或事件神化,是因为人们没有把握能力,对人来说是神秘的。这种神秘,超出了人的能力,所以人们是敬畏的,而敬畏是人的一种本能的反应。所以,人们一方面赋予“神圣”,一方面敬畏。畏惧因为有危险,超出了人类的掌握;敬是跟超力打交道的一种方式。在现实生活中,人们同样是采用同样的方式对应“超级力量”,无论是这样的人还是物,所以人们对有权力的人就是敬畏,对有异常的人就是敬畏,对异常的事物、事件,也都是敬畏。这是一种自我保护的最佳策略。伊利亚德提到神圣显现曾出现在renew地方、任何对象上,任何事物都曾被作为神显过。我认为这个说法是错误的。只有异常、新奇的,或人们一开始就无法掌控的对象或事件上才有可能会被认为赋予神圣的特征。我认为关于宗教的进化论基本上是对的。埃利亚的自己也提到宗教存在进化,闪米特人对Baal和Belit的崇拜转移到了怼对耶和华的崇拜是因为后者“达到了更完满的程度”,“代表着一种神圣的普遍模式”。伊利亚德认为是因为后者的开放性导致它代替前者,所谓开放性,难道不是作为meme的传播性更强所致。
伊利亚德说,石头崇拜并不是崇拜所有石头,而是因为形状、巨大、或其他某些特点比如灵验或power,或跟仪式有了关系,或因为某些偶然事件等。并且引用A. C. Druyt的话说,如果猎狗总是运气极好,那么它就是一个measa,会使Toradja人感到不自在。以伊利亚德总结说,新奇、异常的事物、现象,比如南瓜香蕉的异常,都被看作隐蔽神力的显现。这些都证实了我上面的说法。伊利亚德还提及Nalagasy人眼中的不详之物“最早到该岛上来的马匹、传教士带来的兔子、一切新奇的商品,尤其是欧洲的医药”,然而并“不能持续太久”因为“只要这些事物广为人知并得到控制……他们破坏事物秩序的神力就会丧失”。蜂蜜和小麦可以增加“力量”,但力量太多是危险的,对应的是这些东西有营养,但是有时候也会吃出毛病。引用Gennep的描写,士兵不吃战死的斗鸡,打仗的时候不能在战士家门口杀死雄性动物,这些都是所谓的魔法逻辑。
伊利亚德说,人们对神圣有一种矛盾的态度,一方面希望跟神加强联系,一方面又害怕跟世俗失去联系。这种表达不对。他还说,“这种对待神圣的矛盾态度不仅在对神显和力显的否定中”,显然他把很多问题杂糅在了一起。人们对于神圣的矛盾态度正如我前面所说,对神秘有一种本能的怕,对超力还有本能的向往。这是对前者的矛盾态度。但是对“尸体、灵魂、任何污秽的食物”的矛盾态度,在于人们跟尸体灵魂有双重关系,污秽食物又双重属性,就好像制作成大便性状的蛋糕,或者大便制作的蛋糕,或者里芬斯塔尔的《意志的胜利》,都会引起人们的矛盾心理。这一点接近哈奇生的说法,虽然他的结论是错的,但是他的发现确是对的,他说美感是一种直接的感官产物,因此有些东西虽然有用,我们依然会觉得丑;有些东西即使知道有害,同样还会觉得美。简单说吧,就是一种adaptation。伊利亚德说,“不习惯的、不寻常的显现一般会引发恐惧和退缩”。不妨说,不寻常的东西都会引发人们的警惕和退缩、恐惧,这是一种自我保护反应。假如人类第一次见到蛇、老虎,就欢呼一生跑上去,早绝种了。人的视觉系统同样也是为识别异常准备的,日常我们会对眼前看到的大量静对象视而不见,但是突然的动作却能本能侦测到,这就是一种适应。但并非所有的新奇都会被认为是神圣显现,毕竟有些东西会很快被发现并非不能掌握的异常,而只是经验上的异常,前面已经有例子。此外,即使有些东西经常遇到,但是依然会恒定被认为神显。比如Hume曾提到的大自然中出现的秩序,比如动物的规则形状,以及Muller提及的在大自然中看到的无限。原始人惊奇的并非一些显著的意外。比如,他们惊奇于鸟的飞翔能力,或者老虎的有害性。正如列维布留尔提到的东南亚的人认为存在一种邪恶物质,沾染到了有些植物上,使得这些植物有毒,也沾染到了老虎身上,使得老虎吃人。这样,这种神显的范围就超越了伊利亚德所提及的范畴,毕竟,如果印第安人看到鸟会飞而感到“不寻常、不习惯”,那他们就真的是justify了布留尔认为他们是一群智障的看法了。
伊利亚德说,Ogibwa印第安人中长得畸形或难看的也取一个巫师的名字,在刚果(Reade)矮子和白化病被奉为巫师。神经质和神经病都有可能发展为巫师。这些都是人们对未知的敬畏。现在谁还对这些异常敬畏?人们都开始看不起甚至嘲笑这些丑、残,因为不再是未知的,而且知道这是一种低劣。人们依然对未知和强力敬畏着,只不过对象在不断更替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