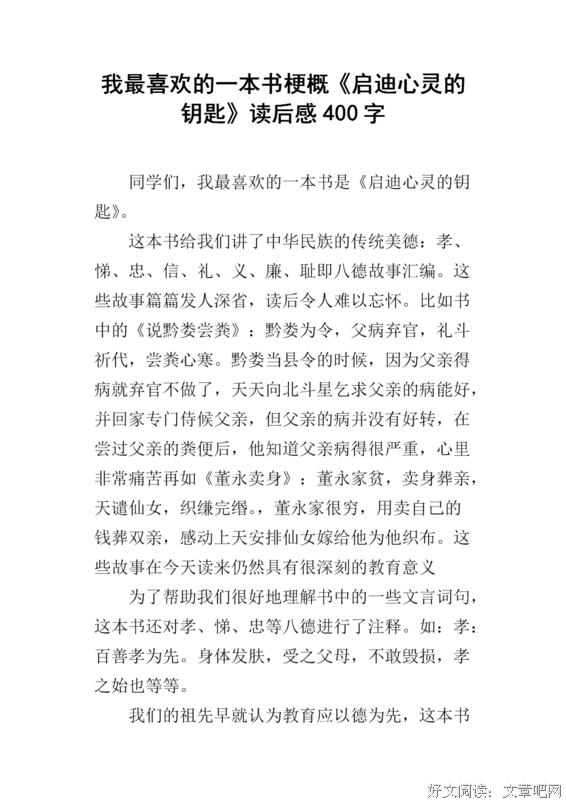
《梵澄先生》是一本由扬之水 / 陆灏著作,上海书店出版社出版的精装图书,本书定价:15.00元,页数:139,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为先生打五星。
●读完了《梵澄先生》。 喜欢扬之水的文字,是一种有味到极处的淡,人也淡到近乎没有人情味。用梵澄先生的话说,雅到让人无法忍受了。相比之下,陆灏陆公子无论文字还是情趣,风尘味道就浓多了。 他们笔下的梵澄先生,固然是学术等身,超凡脱俗,但总让人觉得人生的一种悲凉。
●“知高适否,四十岁以后方学诗,岂非卓然大家。”
●梵澄是至情至性人,杨之水是矜持人,典型的“一头热”。 “这实在不是一本书,而是一本寂寞呀。”
●落花轻拍肩,独行悄已觉。
《梵澄先生》读后感(一):还是应该找个老伴儿
读到前半部分末尾,“先生已处于抢救状态,失去意识,只有吐气之功而无呼气之力。……”忽然感到非常悲惨,和前面其乐融融的叙述形成很大反差,种种学术啊之类的事情也显得遥远了。说不清楚。好像真能给人安慰的还是亲人、亲情、友情,学问也只是外物,精神不过是种冰冷的支撑。还是应该找个老伴儿,交点文化学术圈儿以外的好朋友。唉
《梵澄先生》读后感(二):直觉
2、事实证明丛书癖就是看过的东西换了包装也要再买回来。所以我很心疼的重买了这几万字。
6、陆文在说什么不详。
《梵澄先生》读后感(三):纪念梵澄先生
这是一本很喜欢但是又不忍读的书,分两段,前一段所记徐梵澄先生和杨之水先生之间的交往较为精彩,后一段陆灏先生的追忆文章与前一段有印证。喜欢的原因是观摩高手过招,有醍醐灌顶般的开悟。不忍读是觉得人情冷暖,虽远不至于晚景凄凉,但是寂寥感却挥之不去。梵澄先生“不了解行情”,没懂得的人去珍惜、照顾。所谓君子之交淡如水,这清淡却让人感到分外沉重。
梵澄先生有才学气度,扎实淡薄,于趣味上不刻意追求,待人处事不似洒脱之人,跟陆灏先生似乎南辕北辙。而杨之水先生则稍嫌机器,喜怒不形于色,拒人于千里。当然这都是臆想罢了。
可能是觉悟不够,书中的梵澄先生对鲁迅、王阳明、左传的推崇、对词和红楼梦的不以为意、对西学的忽略,我都不解其意。或许像他所说,毋妨存疑。
书虽小,读起来却每每垂泪。走在梵澄先生走过的路上,寻找他模糊残缺的身影,获得一种终极的安慰感。这是我要感谢和纪念的。
《梵澄先生》读后感(四):牛皮看穿
总觉得这样的书,是轮不到我这种人来评价的,只摘抄几段食事吧,一旦涉及这个话题,文字格外可喜。
当然几段长些的没打出来,爱看的人自然会去看书,我自己也打算再看两遍。
书送至,径送往梵澄先生家,时已将及六点。先生一再留饭,说:我这里有三个馒头,我只吃一个,你吃两个。乃婉谢。于是为我沏上一杯咖啡,并一定要我喝下去。
***
告别之时,硬塞给我两个橘子。先是不受,后先生说,这是对朋友所表示的好感,便觉再推似有不敬,遂收下。
***
(谈及生日……)因问将如何度。答曰:有什么可度?练字,读书,写文,如此而已。昨日尝倩工友购鱼一条,或可烹而食之。你来正好,共进午餐,如何?这里有上好的咖啡,为你煮一杯。
一一婉谢。少坐即辞。
***
昨接梵澄先生电话,约我今天去吃鸡,答曰:去是一定要去的,但鸡不吃了。午后乃如约前往。
《梵澄先生》读后感(五):为将来而活过的人
可能很少人知有徐梵澄这么位先生。这不奇怪,梵澄先生一生独身,低调、朴实,常年在印度游学,晚年归国,就任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所员。他默默耕耘在翻译、教执领域,研究大多涉及古印度哲学,舍功名,自享静寂。我亦仅知梵澄先生学术背景一二,未尝跟随钻
研高深学境,大体只能根据以前读其译著而揣摩先生。然而每每思及,常叹服连连。
翻读日前书肆偶得小书《梵澄先生》,速速读毕,对先生更添一份亲切感。想起几年前第一次读先生译著《苏鲁支语录》,折服于先生文、白相衬的书写,将尼采箴言呈托无遗,也引发我继续求读尼采著述的欲望。先生年少求学德国,回国后师从鲁迅先生,是我国最早推介尼采哲
学思想的翻译家,后“为系统翻译介绍印度古代精神文化典籍《奥义书》到中国来的先驱者……为印度三圣之一圣哲室利·阿罗频多思想的研究者和传播者……是纯粹为学术为思想而生而死的一生。应该说,先生为中国现当代学术思想作出了特殊的贡献”(页120)。然而每每念及这样的学术大家而鲜有人知,常叹息。
幸好有案头这本小书,它以简洁文字追忆梵澄先生,必定会让更多人知悉先生的可敬。书册分两部分,分别由扬之水女士和陆灏先生书写与先生交往的点滴回忆,一为“日记中的梵澄先生”,一为“吉光片羽”,一并“谨以此册纪念梵澄先生诞辰一百周年”。在扬之水女士的日记中可见梵澄先生的孤寂,梵澄先生写道:圣则吾不能/我学不倦/而教不厌也(页6)。还写道:人入暮年,可有孤独感?答曰:余可为之事,固多也。手绘丹青,操刀刻石,向之所好;有早已拟定的工作计划;看书,读报,皆为日课;晚来则手持一卷断代诗别裁集,诵之,批之,殊
为乐事,孤独与余,未之有也(页17)。然梵澄先生又告诉“大妹”(即扬之水女士):“几日前访老友贺麟,他已八十七岁,虽鹤发童颜,却步履维艰,口中嗫嚅难为言,因觉无限感慨……希望你能常来。我一个人是很寂寞的。”问之“过节时,不会有人来拜年吗?”答“鬼才来!”再问“是穷鬼,还是富鬼?”先生不觉笑起来,随即答道:“其实鬼也没有一个。”(页35)。同样的孤寂在陆灏先生的文字中也见:先生说每天要写写字,有时也一人摆弄棋谱。我问经常有人来看他吗。先生说经常没人来(页114)。“我去看先生,曾劝他写回忆录,他说人是为将来活的,不是为过去而活,所以不值得写……”(页128)先生曾说有一宏愿,就是欲打通三大宗教,”可惜老天没有多给他更多的时间,这项浩大的工程完成的可能性极小(页136)。
种种点滴故事,不由地为“曾为过去而活”的人留下了悲苦的隐喻。或许先生将希望留给了未来,而假以时日,风云变幻之未来,又怎是先生的乐于所见呢?先生或许被更多更多的年轻人遗忘了……
“独行悄已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