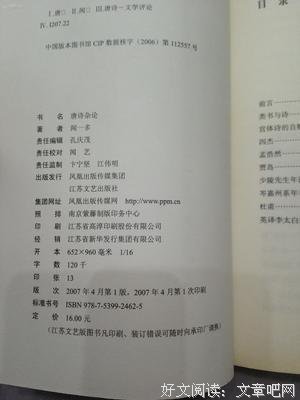
《唐诗杂论》是一本由闻一多著作,中华书局出版的平装图书,本书定价:18.00元,页数:296,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唐诗杂论》精选点评:
●只看懂了宮體詩的自贖和太白詩的英譯等幾篇……年表對我沒什麼用= =
●还行吧,没有特别戳中的点
●天妒英才
●前半本的文章都挺好,后版本都是教学提纲手稿整理,只有骨架没有血肉
●大家
●不故弄深奥理论,读了让人懂得诗歌评论,其中“宫体的自赎”尤其精彩。
●印象最深的還是四杰與陳子昂。“不廢江河萬古流”,以及古今獨步之清理。
●风格鲜明。
●用老师的话说,闻一多这辈子做了多少事啊,又写诗,又搞学术,又投身革命……真是有价值的人生啊。这个小册子可棒。
《唐诗杂论》读后感(一):《杂论》杂记
《类书与诗》 学术——文学
《宫体诗的自赎》 宫体诗的堕落: 由意识到文词,由文词到标题,逐步的鲜明化;恐怕只是词藻和声调的试验给他们羁縻着一点这种作诗的兴趣……原来从虞世南到上官仪是连堕落的诚意都没有了。 宫体诗的自赎: 1、卢照邻《长安古意》:得成比目何辞死,愿作鸳鸯不羡仙 庾信:以非宫体代宫体 卢照邻:以更有力的宫体诗救宫体 卢、骆:巨篇+感情的力量 2、刘希夷《代白头翁》:年年岁岁花相似,岁岁年年人不同 汉晋,感情返归正常,宇宙意识 3、张若虚《春江花月夜》
《四杰》 卢骆(刘张)【破坏,乐府新曲】——王杨(沈宋)【建设,五律】 负破坏使命的,本身就得牺牲,所以失败就是他们的成功。人们都以成败论事,我却愿向失败的英雄们多给予一点同情
《孟浩然689-740》 真孟浩然不是将诗紧紧的筑在一联或一句里,而是将它冲淡了,平均的分散在全篇中 浩然属襄阳,襄阳属浩然 孟浩然的诗,诗的孟浩然
《贾岛779-843》 释子,酸涩,调剂
问题: 1、闻一多的新诗探索与唐诗研究的具体关系?(宫体诗的自赎——新月派的格律) 2、中国古代的学术传统,与现代学术的比较 3、待看:关于唐诗的总论、年谱和专题讲稿
《唐诗杂论》读后感(二):五十年间似反掌
给三星,是因为我觉得不适合我和其他很多初学者。
理由如下:
(1)
读之前,我先看了傅璇琮的导读,其中说:闻先生在本书中的几乎所有重要观点,都被后来学者们质疑。又说,从专业学者的角度,考虑到时代,不应太苛刻。
读后,确实感到有偏颇的嫌疑。因此我觉得根基不够的来读,尤其是有闻一多的名号,恐怕不容易真正领悟到闻先生的成果,而受到局限和束缚。
(2)
感到这本小书收编内容很杂,有类似花边小品的“宫题诗的自赎”等,也有较专门的“少陵先生年谱会笺”。
一般读者恐怕读年鉴的兴趣和需要都会比较少。
以上陈述完毕。不过爬上来写书评却是完全不同的缘由:
这两天先讲那些小品似的软文先翻了,然后居然奈着性情将占主要篇幅的 <岑嘉州系年考证> 和 <少陵先生年谱会笺> 都看了。
将其中觉得有趣的诗句统统摘出之余,因为读的太快。一天之中即经历了从杜甫出生到去世的大事记(诗作辅证),不禁有些头晕目眩,生出:"人生天地间,忽如远行客" 的感叹。
再回过头去读 工部出生时,孟浩然二十二岁,李白、王维并十三 岁。实在五味杂陈。几小时前读到这里我还特地作笔记说这段真可爱,此刻却已经看完对工部死亡地址的种种讨论了。
用工部的诗说,便是:"五十年间似反掌" 吧。
《唐诗杂论》读后感(三):直抵灵魂深处——一篇跑偏了的《唐诗杂论》读书笔记
直抵灵魂深处
书目:唐诗杂论
著者:闻一多
版次:中华书局 2015年6月北京第1版
2015年6月北京弟1次印刷
在阅读《唐诗杂论》后,我们不难发现,闻一多的唐诗研究分两个层次,一是诗人生平创作的考证以及唐文学史料的整理,二是作家作品的综合研究和文学史的宏观研究。而在研究过程中,他在学者的身份中加入了诗人的灵魂。诗人更为关注自身,更能把握自身情感微妙的变化。这种特质使得他将唐诗研究变为了一种自身与诗人的双向交流,在研究中审视自身,审视诗人。他会在严谨研究中更多了几分诗人的情感体悟,又或是找到自身与唐诗人的契合点,有时研究角度的选取无不透露着他的价值取向与理想。在我看来,便是诗史思的结合。让他的唐诗研究具有独特眼光,并且生动形象。
从诗人到学者的身份转变,只是内在形式的转变。他仍在诗中畅游,将自己现代诗人的才情、思维方式体现在了古诗研究中。努力的进入诗人们的精神世界,他笔下所描写的,更像是唐代诗人们的人格。他既分析了诗人的内在心里和精神世界,又联系了时代背景,文化思潮而充分的阐述了诗人的个人人格与文化人格,直抵灵魂深处。
这表现在书中他对杜甫、陈子昂、孟浩然、贾岛以及初唐诗人的评论中。作者评论他们的诗先从描绘和分析他们的人入手,因为,“人是当如其诗的。”在闻一多的唐诗研究里,有诗人的肖像描绘、性格分析、思想的解剖、精神世界探索,从外在形象到内在精神世界,从个体存在到社会价值,共同构成了闻一多唐诗研究的基点。
作者在这一本书中主要写了初唐诗人,但他的视野却放在了整个唐诗与诗人。就他所描述的杜甫、孟浩然、贾岛、陈子昂等就代表了四种文化人格:以孟浩然为代表的道家思想型人格,以杜甫为代表的儒家思想型人格,贾岛代表的佛家思想型人格。出世与入世,救市与避世等等矛盾,以及在这些矛盾影响下所养成的中国文人的性格思想和精神追求。理解了诗人的人格,也就理解了诗人的诗。这便是作者的深意。
五四以来一直强调的个体解放、独立自由。人们热衷于打破外在生存的各种条条框框的束缚,而忽视了自我内在人格的自由。 然而,闻一多在唐诗研究中对自我生命存在与唐诗人生命存在进行了双向的融合和直抵灵魂深处的探究。我们享受着闻一多所体悟到唐人唐诗的 “诗”与 “真”,更让我们自身体悟到贾岛的“人生的半面”、 “四杰”珍视自我生命存在的性情抒写、孟浩然“诗如其人,或人如其诗”的独立品格、“类书式”的初唐诗中“情”“志”的矛盾与分裂等诗性传统。藏于我们内心深处的内在精神此时也被闻一多点醒了,进而内在驱动着我们进一步去探寻这些超越历史时空的诗性传统的魅影。
《唐诗杂论》读后感(四):《唐诗杂论》个人收获
该书是后人从闻一多先生所著的各类书籍及文章中整理而来,朱自清先生说闻一多先生的《唐诗杂论》“将欣赏和考据融化的恰到好处,并且创造了一种诗样精萃的风格读起来句句耐人寻味”。起初我也野心勃勃的想要吃透这本书,但学力却过于浅薄只能望洋兴叹,书中有些内容高屋建瓴,而以我积累的知识做地基尚且不足,所以是边看书边看先生提及作家的诗歌集。读完之后有三点感受;一是再次感叹于我国古代经典浩繁艰深以及自己道行微末:二是先生在文中提及的明吕坤所言“史在天地,如形之景。人皆思其高曾也,皆愿睹其景。至于文儒之士,其思书契以降之古人,尽若是已矣。”:三是感谢所有治学先辈、讲学老师用他们的文字、书籍、课堂……为我们接近经典、了解历史文化架起了一座座桥梁。 该书由九篇文章组成分别是:«类书与诗»,«宫体诗的自赎»,«四杰»,«孟浩然»,«贾岛»,«少陵先生年谱全笺»,«岑嘉州系年考证»,«杜甫»及《英译李太白诗》。 一、《类书与诗》 作者这一篇文章所说的范围是唐代开国后约略五十年,从高祖受禅起,到高宗武后交割政权。总的来说,作者对这一时期的文学是一种鄙夷的态度,他认为这一时期不能算作唐代文学的头,只能把它看作六朝的尾,甚至这一时期的文学本身不具备任何价值在文学史上不能有任何位置。在这一时期中文学被学术同化,一方面把文学当作学术来研究,一方面又用一种偏于文学的观点来研究其余学术。于是在这一背景下诞生了一种“畸形”的产物——类书(事之书,兼收四部,而非经非史非子非集,四部之内,乃无类可归)作者特别列出了李善(绰号“书麓”史书说他“淹贯古今,不能属辞”“释事而忘意”)来说文学被学术童话的结果,只顾“事”不顾“意”,类书家采事而忘意。其次,作者说初唐诗构成程序的几个阶段“劈头是“书麓”,收尾是一首唐初五十年间的诗,中间诗比较散漫、零星的“事“,逐渐地整齐化分化”。最后作者十分激烈的批评了太宗一味追求文辞上的堆砌,说太宗的修辞不过是文辞上的浮肿,就是文学上的皮肤病,且魏征一诗坛的局外人的《抒怀》被选家选作代表这一时期的代表作,使后人来看不免觉得有些戏谑的意味。 二、《宫体诗的自赎》 作者给出的宫体诗的定义是指以梁文帝为太子时的东宫及陈后主、隋炀、唐太宗等几个宫廷为中心的艳情诗。且作者认为这一时期没有任何一个诗人,也不是空白是一个污点。作者认为那个时期(谢朓已死陈子昂未生)整个宫廷内外,人人的眼角里都是淫荡,那一时期的“诗“从意识到文词,从文词到标题,逐步的鲜明化是一种文字的赤裸狂,究竟是作诗还是一种伪装下的无耻中求满足。 在窒息的阴霾中,宫体诗迎来了洗涤它的狂风暴雨——《长安古意》,卢照邻在其中一手挽住了衰老的颓废,交给他如何回到健全的欲望,一手又给他欲望的幻灭。再到“一抔之土未干,六尺之孤何托”的骆宾王《代女道士王灵妃赠道士李荣》中一气到底而又缠绵往复的旋律之中欣欣向荣的情绪。离开卢、骆,我们有遇到了刘希夷。刘希夷《公子行》中的痴情话是我们从未在宫体诗中听过的,一种健康的常态的爱情却在宫体诗中贵为珍宝。《代白头翁》中的“ 今年花落颜色改,明年花开复谁在?已见松柏摧为薪,更闻桑田变成海。古人无复洛城东,今人还对落花风。年年岁岁花相似,岁岁年年人不同。寄言全盛红颜子,应怜半死白头翁。”他又从蜣螂转丸式的宫体诗一月而到了庄严的宇宙意识。最后来到张若虚的《春江花月夜》,宫体诗到此处却变得干净了“ 江畔何人初见月?江月何年初照人?人生代代无穷已,江月年年望相似。不知江月待何人,但见长江送流水”相较于卢照邻点出“昔时金阶白玉堂,即今唯见青松在”、寒山子冷漠地凝视“未必长如此,芙蓉不耐寒”刘希夷的悲叹“明年花开复谁在”张若虚那不卑不亢、冲融合易的态度展现了他更夐绝的宇宙意识“不知几人乘月归,落月摇情满江树。”最终洗净了宫体诗的污浊。 三、《四杰》 四杰是唐诗开创期中负起了时代使命的思维作家,他们都年少而才高,行为浪漫,遭遇悲惨。作者由四杰的徽号的功用和适用性入手,将其分为了两个小宗“王杨”“卢骆”。 首先是年龄,“王杨”比“卢骆”平局小了十余岁,可以算作两辈人。(所以杨炯的“愧在卢前,耻局王后”有了另一层意思,杨比卢小得多,且按照关系来说是卢的后辈,所以愧在卢前,但与王是同年,名字在王后,说耻局王后是不甘心的意思) 其次是性格,杨炯据裴行俭说较为“沉静“,而王勃除了擅杀官奴也较为安分。反观卢、骆,从《穷鱼赋》、《狱中学骚体》来看卢并不安分,而骆更是博命徒。 再看友谊,卢、骆二人有骆的《艳情代郭氏答卢照邻》,王、杨二人有王的《秋日饯别序》、杨的《王勃集序》可证。但卢、骆与王、杨之间却看不出如此紧凑的关系。 最后从“诗“方面来看,卢、骆擅长七言歌行,王、杨专工五律。由于他们选择的形式不同,他们的使命也就不同。卢、骆的歌行是乐府新曲又是宫体诗新的发展,所以卢、骆是宫体诗的改造者。而王、杨的时代是台阁移到江山与塞漠,五言八局的五律到王、杨才正式定型。 四、《孟浩然》 作者从孟浩然的画像说起,张洎说他颀而长,峭而瘦。再说孟浩然的隐居,正值开元盛世的孟浩然的隐居是为隐居而隐居,而非像其他人是为出世而隐居,与他相似者也只有陶渊明了吧。最后说到孟浩然的诗,前人说他量和质不多,特别是苏轼说他“韵高而才短,如造内法酒手,而无材料”作者也说对于别人,诗是孟浩然的精华,对于孟浩然诗是人的糟粕或是人的剩余。但在我看来诗却是孟浩然的自我刻画如“垂钓坐磐石,水清心亦闲。鱼行潭树下,猿挂岛藤间。游女昔解佩,传闻于此山。求之不可得,沿月棹歌还。” 颀而长,峭而瘦的风神散郎的姿态沁入整首诗中,我们读起来,又跃然纸上,像是及时投影。东坡说他质不够,可孟浩然在乎这些吗?作者文中所说东坡自己的毛病就是才太多。深以为然 五、《贾岛》没有读过太多他的诗歌未细读。 六、«少陵先生年谱全笺»、«岑嘉州系年考证»一为杜甫详细的事迹年谱,二为岑参诗中可考证的部分,是以诗证事 七、《杜甫》 明吕坤曰“史在天地,如形之景。人皆思其高曾也,皆愿睹其景。至于文儒之士,其思书契以降之古人,尽若是已矣。”作者是怀着这样的心情去写下这篇文章的,他并未给出杜甫诗作的相关分析,而只是像一个说书人一样的去描述杜甫的相关事迹,如他年幼时的刻苦读书,观公孙大娘弟子舞剑。他成长的心路历程,他的抱负,他与李白的相遇相知……仿佛一个的电影长镜头,为我们娓娓道来,看完却只能唏嘘。 八、《英译李太白诗》不感兴趣,未读。
《唐诗杂论》读后感(五):《唐诗杂论》读后感
如果百度一下闻一多,会发现他的身份并不单一:诗人、学者、爱国主义者、民主战士。对于这些身份,朱自清曾评价到:“(闻一多)学者的时期最长,斗士的时期最短,然而他始终不失为一个诗人,而在诗人和学者的时期,他也始终不失为一个斗士。”这句话似乎很绕,但确实是概括出了闻一多的一生与品性:致力于学术研究的同时不失诗人的气质与情怀,致力于文学的同时不失斗士般批判的眼光,致力于传统文化的同时不忘时代与民族的责任。这样的闻一多,学术研究对他来说,更像是寄托了他个人追求的一种自我探索的方式。
是什么造就了这样的闻一多呢?如果按“学者”闻一多的研究理念,我们要搞懂“诗人”的闻一多,恐怕得先仔细考证他的生平,仔细研究他所处的历史时代了。不负责任一点,大致可以说是因为近代中国的复杂时代环境。西方经济、政治、文化的影响,加上战争动乱、民族危亡等问题的涌现,再结合主观的觉悟与情怀,身处这个时期的闻一多拥有这样多的“身份”便不足为奇。而他笔下的著作自然也逃不掉时代和他自身性格的烙印。《唐诗杂论》也不例外。
《唐诗杂论》虽说是学术著作,但全文语言无一不带有着散文和诗意的影子。作为诗人的闻一多,他能与文中所评的诗人产生一种共鸣,从“诗”与史实中去寻求“诗人”的品质,发掘诗人的真实一面,而在这不断的发掘中,作者对“诗人”的自己也有了更深的认识。这种“个性”与研究对象的融合,或许表明闻一多已经在不知不觉中“创新”了一种文学研究与文学评论的方式,而这种“新”方式也从侧面展现出当时的时代变化特征。
闻一多的诗人气质与个性是如何在书中体现的呢?在读完《唐诗杂论》一书后,我发现闻一多仿佛在帮我进行古代文学的“查漏补缺”,因为如今文学史上重点提到的大家——初盛唐的李白,中唐的韩愈、白居易,晚唐的李商隐,他都没有过多提及。除了杜甫,他所重点书写的如刘希夷、张若虚、孟浩然、贾岛等似乎都不是文学史研究的主流,但仔细类比一下,便会发现这些诗人都有着某些共同点:在唐代的政治体制下不能得志,身处时代边缘漫游苦吟,坚持不平则鸣。闻一多评价贾岛时说:“说晚唐五代之崇拜贾岛是他们那一个时代的偏见和冲动,但为什么几乎每个朝代的末叶都有回向贾岛的趋势?”,“可见每个在动乱中灭毁的前夕都需要休息,也都要全部的接受贾岛,而在平时,也未尝不可以部分的接受他,作为一种调济,贾岛毕竟不单是晚唐五代的贾岛,而是唐以后各时代共同的贾岛。”这种时代意识的思考,让闻一多对贾岛产生了由彼及此的惺惺相惜之感。而在对张若虚、刘希夷的评价中,闻一多就直言:“人们都以成败论事,我却愿向失败的英雄们寄予点同情”,可见,闻一多注重的是诗人对人生诗味的品悟,看重诗人在个人与环境的关系中所牵引出的超越时代的哲思。这正如他在《宫体诗的救赎》一章中所表明的,刘希夷对宫体诗的拯救在于情感的“重返常态”,而张若虚的拯救则是“宇宙意识”的思考,这是更深一层的境界。从这些诗人的取舍中,我们便可以看出闻一多的主观情感,而这种情感在描写杜甫时达到了一个顶端。
从语言方面来说,作者的人格魅力、《唐诗杂论》的诗意在幽默生动的语言中也得到充分展现。如评价唐太宗对诗的理解是“文学的浮肿”,是“文学的皮肤病”。又如在《宫体诗的救赎》一章中,作者说宫体诗的“堕落是永无止境的”。而在讲到后期宫体诗的僵化时,他又形容宫体诗人们“已经失去了积极犯罪的心情”。这些语言幽默诙谐又不会喧宾夺主,精简点出文意、表达作者情绪的同时还能博读者一笑,这种愉悦的互动不是单纯的学术著作可以给予的。这种文采语言的运用更多集中在描写杜甫的一章:闻一多将李白与杜甫的相遇比作太阳与月亮的碰面,更把他们的相遇与老子孔子的相遇相媲美。这个比喻文采斐然又恰到好处,即使是现在也常常被我们引用,可见闻一多文采语言力量的精准与魅力。
在《唐诗杂论》中,对杜甫的描写可以说占了全书的一半,除却《少陵先生年谱会笺》与《岑嘉州系年考证》两篇以考证史实为主的篇目外,《杜甫》一篇可以算是作者诗人气质的集中体现。散文式的语言、直接式的抒情、浪漫的想象、艺术性的故事结构都在本篇中有所展现。在《杜甫》一篇的引言中,闻一多曾直接发出慨叹:
“我们要追念,追念的对象在哪里?要仰慕,仰慕的目标是什么?要崇拜,向谁施礼?假如我们是肖子肖孙,我们该怎样的悲坳,怎样的心焦! 看不见祖宗的肖像,便将梦魂中迷离恍惚的,捕风捉影,攀拟出来,聊当瞻拜的对象——那也是没有办法的慰情的办法。我给诗人杜甫绘这幅小照,是不自量,是读裹神圣,我都承认。因此工作开始了,马上又搁下了。一搁搁了三年,依然死不下心去,还要赓续,不为别的,只还是不奈何那一点‘思其高曾,愿睹其景’的苦衷罢了。”
这段文字可以说是作者在解答为何自己要做杜甫研究,甚至也解答着为何自己要致力于中国古典文学的学术研究。这是一个学者,也是一个诗人的内心独白。在引言的后半部分,闻一多激动之处甚至直接引用了华兹华斯的诗歌,可见,作者“诗人”的共鸣已经达到一个极点,不表不快。而在《杜甫》一篇的正文中,开篇便是一段细腻的故事描写,杜甫不再是一位“被介绍”的人物,反而成了一篇故事的主人翁。文章结构构思巧妙,里面还有运用到插叙等手法,已然是一篇生动的人物传记。从杜甫早年到后来的漂泊、与李白相遇,闻一多都在描写中加入自己的想象,艺术性地还原当时的情境,细节之处也面面俱到。在描写杜甫小时扑枣时,身为哥哥的杜甫心中的想法、细节的动作甚至是呼吸的愉悦,闻一多都写到了。与其说写的是杜甫,不如说在很大程度上是写的闻一多理解的杜甫。这种艺术性的描写,不仅在还原一个更丰满的杜甫,更多的也为我们展现了一个多情的闻一多,一个极其想书写真实的杜甫而不得的闻一多。
在对杜甫的讲解里,最令我感受深刻的是最后一段作者对李白杜甫在济南同游时光的描写。前面一大段一大段杜甫生平的叙述在最后一段归于平静,杜甫的一生仿佛也随之戛然而止:天性中就是出世的李白与一时愤慨寻求出世的杜甫同坐,夜色、星光、枣树都自在而平静,“谪仙人”李白依然对求仙之事侃侃而谈,一旁早已厌倦学仙的杜甫心事重重,不愿接话,直到话锋一转,谈及现实国家的弊病才打起精神一语三叹。一旁斟酒的隐士范十沉默不语,“或许他有意见不肯说出来,或许他压根儿没意见”。这坐中最苦闷哀愁且一辈子都走不出这苦闷的,怕只有那执着于“致君尧舜上”的杜子美了。闻一多细腻的想象、点到为止的留白,可以看到他对杜甫“竭尽全力”的追寻,这种追寻不单指历史的真相,更是指对杜甫人格的苦苦追寻。“凤凰你知道是神话,是子虚,是不可能的。可是杜甫那伟大的人格,伟大的天才,你定神一想,可不是太伟大了,伟大得可疑吗?上下数千年没有第二个杜甫”。文到最后,与其说是杜甫感动了我,不如说是闻一多感动了我。再联系先生一生的命运,也许他已经在对这些诗人的研究中寻求到了自我 ——千百年来诗人的命运,似乎冥冥之中都有所相似,贾岛是属于后来时代的,杜甫又何尝不是属于后来时代的,闻一多就这样将自己融入了自己的研究对象中。而正如他研究这些诗人一样,细腻的生平考证、诗作研究是必要的基础,结合闻一多的生平与著作,我们也许同样能还原出一个斗争着的“诗人”闻一多。在我看来,仅是一本《唐诗杂论》,闻一多诗人、学者、斗士的形象已经呼之欲出了,回首再看朱自清的评价,可以说先生在每一个身份上都当之无愧。
跳出文本,我想说的是,能选中这本书算是一种幸运。因为我抱着看学术著作的低落心情翻开它,最后却被作者的人格魅力与文学造诣所愉悦了。从前我们读书,最喜欢问自己的就是“学到了什么?”其实,有目的地读书是很累的,要对本书中的观点、考证进行批判,论证作者观点、考据的正确与否,就我现在的水平还不能够,主观情感上也不太愿意——百年来研究唐诗的学者太多了,但闻一多只有一个。闻一多研究唐诗,追寻的是人格的共鸣,而这种苦苦的追寻又感染着身为局外人的我,敦促我对自己人生产生思考,只这一点,就已经很值得了。然而,话又说回来,如果有那么一天我能够得上与这些伟大人格的诗人们产生共鸣,到那时,我会是高兴多一些,还是悲哀多一些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