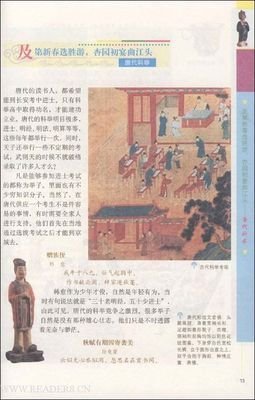《唐诗百话(全三册)》是一本由施蛰存著作,陕西师范大学出版总社有限公司出版的平装图书,本书定价:88.00元,页数:857,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唐诗百话(全三册)》读后感(一):施蛰存与唐诗
文/毛乐耕
施蛰存先生称自己的写作、研究是开了四扇窗:东窗文学创作,南窗古典文学研究,西窗外国文学翻译,北窗金石碑帖研究。
在这四扇窗中,施蛰存的工作都做得有声有色,成绩不俗。这其中,在古典文学方面,《唐诗百话》是他对唐诗学研究作出的重要贡献。这本书为唐诗在当代的推广和鉴赏提供了一个优秀的实用文本,出版以后,反响很好,2015年12月被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列为首届向全国推荐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普及图书。
说起来也有点偶然,施蛰存原来并不专门研究唐诗,他只是一个爱好者,平时喜欢读唐诗,有所发现有所感受时,也随时作一些札记。
1977年,正是“文化大革命”结束不久,上海古籍出版社的编辑向施蛰存组稿,希望他能写一本古典文学方面的书。施蛰存经过考虑,向出版社提出写一本关于唐诗欣赏方面的书,用串讲的方法选讲几十首唐诗,使它们能够代表整个唐代三百年的诗风,书名就叫《唐诗串讲》。这是施蛰存研究唐诗的缘起。
方案定下以后,施蛰存就开始写作。可是几个月下来,施蛰存遇到了困难。他发现,这本书并不好写。在讲解一首诗的时候,常常会碰到许多与此诗相关的问题,例如诗中典故的意义,例如诗所反映的时代、政治背景,例如诗中涉及的社会风俗,例如某一种诗体的渊源流脉,等等,这些问题都需要解决,才能让读者读得懂,看得明白。施蛰存认识到,写这本书与自己平时的阅读不同。平时阅读,是以自己的水平为基础,凭自己的直觉去理解就行了。现在要写这本书,许多问题都要重新作专门的研究,而且要达到深而透的程度。而要进行深入的研究,还必须首先作一些基本的校勘、考证工作,还要熟悉唐诗印行、研究的历史和各家的观点。这样,写书的实践就倒逼着施蛰存重新对唐诗进行更为深入的研读和探究。
施蛰存一边写作,一边研究,一边总结,在书稿写作的过程中,他又适时调整了方法,将串讲改成漫谈,书名也相应地改成《唐诗百话》。历时八年,施蛰存终于拿下了这部书稿。
《唐诗百话》1987年9月由上海古籍出版社首次出版,在当时就产生了影响。以后,1996年5月,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将之作为《施蛰存文集:古典文学编》第一卷再版,2001年12月修订重印;2011年2月,又将其作为《施蛰存全集》第六卷校订出版。这三种版本,初版本因出版年代较早,收在“文集”“全集”中的受众面又比较少,都已难以满足读者的需要。2014年,施蛰存哲嗣施达先生又授权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了上、中、下三册的“最新修订版”。这个版本,是目前比较通行的一个可用的版本。
施蛰存自己说:“这本书的问题是写得不上不下。”其实这不是此书的“问题”,而恰恰是此书的特点和优长。不上,正好说明这本书既有研究的深度,又不深奥难啃,而是通俗明白,适合普及。不下,也正好说明这本书不是人云亦云,东抄西摘的大路货,而是有施蛰存自己精深的研究在其中。这是一本雅俗共赏的书,既可供学术研究者参考,更能让当代广大唐诗爱好者亲近。美国耶鲁大学将此书作为该校中国文化学习课程的指定教材,应是十分恰当的。
在我看来,这本书是一部独特的唐代诗史、唐诗通论。在历代唐诗学研究的基础上,施蛰存也选择了将全部唐诗按初唐、盛唐、中唐、晚唐四个时期来展开品评的思路,但他另有自己的心得见解。他认为,这四个时期,不是对唐诗发展史的分期,而是对唐代历史发展的分期。唐代社会、历史的发展,自然又会影响到唐诗的发展。对于唐诗的成就而言,他认为中唐并不逊色于盛唐,甚至要高于盛唐。他说:“盛唐是唐代国家形势的全盛时期,而唐诗的全盛时期却应当排在中唐。”
在本书的写法上,施蛰存也是匠心独运。他采用了以人带诗,以诗带识(知识)、以诗带史的方法,这是别具一格的。“百话”中的“话”,大部分都是以诗人为纲,带出其具有代表性、特殊性的作品来,在介绍诗人、品评作品的基础上,再根据需要,抓住契机,随机性地介绍唐诗乃至中国诗史的相关知识,介绍唐代的职官、典章制度、社会历史等方面的背景内容,让知识的介绍与诗歌的鉴赏相辅相成,融会贯通。
初唐时期,施蛰存列出王绩、王勃至陈子昂、王梵志等八家;盛唐时期,列出王维、孟浩然至李白、杜甫等十家;中唐时期,列出张志和、李冶至姚合、寒山子等二十五家(中间自然包含韩愈、刘禹锡、白居易、李贺等);晚唐时期,列出李商隐、温庭筠至韩偓、韦庄等十七家(中间自然包含杜牧);一共六十家,唐代的重要诗人和许多重要作品都包含在其中,同时还以施蛰存自己的眼光发掘了若干有特色的诗人及作品。在每一时期的品评结束以后,施蛰存还专门再写一篇“馀话”,对一些需要说明的问题进行补充交代、归纳总结。这样,纲举目张,脉络清晰,重点突出,清楚明白,形成一部独特的唐代诗史、唐诗通论。
在诗作的选用方面,施蛰存也有自己的考虑,尽量避开一些“熟面孔”,另选一些新作品,以取别开生面之效。如白居易,就避开了《新丰折臂翁》《上阳白发人》《涧底松》《卖炭翁》《红线毯》等,新选了《两朱阁》;避开了《长恨歌》《琵琶行》,新选了《霓裳羽衣歌》。杜甫的“三吏”则避开了选入教材的《石壕吏》,另选《新安吏》。再如韦庄的《秦妇吟》,“这是我国封建社会中篇幅最长的叙事诗”,在我国“失传了一千年”。“近几十年,《秦妇吟》从敦煌石室中被发现以来,还从来没有人选读,今天要找一个印本也不容易了。”“为了免得它再度失传”,施蛰存将《秦妇吟》全文录入,进行了详尽的讲解。从这些方面来看,《唐诗百话》也是一本有自己面貌的唐诗新选本。
《唐诗百话》不仅具有诗史的价值,同时还是一部唐诗知识的实用辞典、百科全书。
唐代是中国历史上一个诗歌大繁荣的时代,涌现出许多杰出的诗人和优秀的作品,形成了诗歌创作争奇斗艳的美学高峰。在唐代,古体诗、乐府诗得到了新的发展,近体诗产生并成熟定型,长短句(词)有了一个良好的开端,还有许多关于诗歌的实验也在不同的诗歌群体中或诗人的实践中进行;诗句的字数,也从《诗经》的四字句为主,经汉魏六朝的五字句为主,再到唐代的七字句流行。所有这些关于诗歌的形式特征、美学特征、产生原因、发展脉络、风格流变、成败得失等问题,都需要予以考察和论证,阐释和评断,而要完成这项工作,没有广博的知识和精深的学力是不能胜任的。然而,施蛰存在这方面却做得很好。
例如关于绝句这一特定的诗歌形式,施蛰存书中专门有一篇《唐诗绝句杂说》,从“什么叫绝句”说起,比较了“古绝句与近体绝句”的异同,介绍了绝句这一诗歌形式的变化和发展,说明在唐代,绝句是“律诗”的一种,而所谓“格律诗”,已经是现代人弄混淆了的一个概念。唐代的时候,称古体诗为“格诗”,近体诗为“律诗”,而我们现在所说的律诗、绝句、排律等概念,只是在宋元以后才被人区分开来。对于绝句写作的结构问题,施蛰存还精心选择了三种不同的诗例,用实证进行了讲解分析,从专业的角度来看很有深度,内容也很丰富,令人大开眼界。
再如除了四言诗、五言诗、七言诗、长短句以外,还有一种六言诗。这类诗歌,虽然作品较为少见,是诗歌创作中的一脉支流,但毕竟存在。施蛰存在书中撰有“六言诗”一讲,从其起源于楚歌开始,经汉魏直到唐代,通过一些作品实例,说清了它的来历与流变,它在诗歌发展特别是长短句发展中的作用与影响。
这样有深度的知识点,在《唐诗百话》中可以说是时常可见。例如唐人之间为什么以家族的排行相称,唐人诗中为什么盛行用典,唐人对前人诗句的点化,唐代游仙诗的起源和作用;讲杜甫的律诗顺势把律诗中对偶的各种形式介绍清楚了,讲王昌龄的《芙蓉楼送辛渐》专门将唐代关于冰壶的典故和来历作了细致的考辨,讲韩翃的《寒食》则普及了寒食节的知识。关于解读唐诗的种种问题,无论是在内容方面还是形式方面,常常能在书中找到明确详实的答案。
施蛰存写《唐诗百话》,积累和掌握了丰富的资料,深入细致地进行比较、鉴别、考证、分析,达到了通与透的境界。从唐代开始,多少年来,唐诗研究已经形成了专门的学问,资源材料林林总总,各种说法让人眼花缭乱。面对前人的大量成果,施蛰存常常有自己独到的见解,他并不拘泥于前人的结论,对前人的一些说法,他认为不对的,都能态度鲜明地指出来,进行讨论和匡正。有些古人没能解决的疑难问题,施蛰存也能借助自己的学力、根据自己的研究提出新的见解。
例如秦韬玉的《贫女》,施蛰存就直率地说:“这首诗的总的意义,虽然人人都能了解,其中间二联却直到今天没有人能完全理解。”接着,他列举了前人的有关讲解,指出:“我认为,这两联四句,他们都讲错了。也许历代以来读此诗者,也都是这样讲法。那么,这首诗一向没有人完全理解,也说不定。”态度相当明确。
再如韩愈《山石》诗中前有“天明独去无道路”之句,到后面又出现了“嗟哉吾党二三子”的说法,施蛰存指出:“‘吾党二三子’和上文的‘天明独自去’似乎有些矛盾。他这次游山,恐怕是和两三个朋友结伴同行的,要不然,为什么说‘嗟哉吾党二三子呢’?但如果有两三个人同行,又为什么说‘天明独去’呢?看来这个‘独’字,不可死讲,不能讲作‘独我一人’,而应讲作‘只有我们几个人’。《项羽本纪》叙述沛公兵败成皋时,‘独与滕公出成皋北门’。又在鸿门宴上‘脱身独去’,其实当时还有从人。这里的‘独’字也是同样用法。”这样的解读,是何等精细,何等深妙。
还有,关于李颀诗《听董大弹胡笳声兼语弄寄房给事》的诗题,这个诗题复杂拗口,特别是“语弄”二字,难倒了许多人,导致“这个诗题至今没有被弄明白”。施蛰存经过细致考辨,令人信服地说清了这个诗题,“为唐诗学者解决(了)一个问题。”
当然,对有些诗作或字句,施蛰存在解说中也有少许地方坐得过实或解得不够妥当,这些,就需要读者和专门的研究者通过讨论和争鸣来解决了。
来源:中华读书报
《唐诗百话(全三册)》读后感(二):唐诗百科全书
先说扣一星的原因,非常贱,因为有些字我不认识,书里没注音。我说了这个原因后,我妈给了我一本字典。
一个词语,每一位诗人有他特定的用法;一个典故,每一位诗人有他自己的取义。每一首诗,宋元以来可能有许多不同的理解。如果不参考这些资料,单凭主观认识去讲诗,很可能自以为是,而实在是错的。——施蛰存
全书正文共100篇,上册收入“初唐诗话”“盛唐诗话”,中册收入“中唐诗话”,下册收入“晚唐诗话”和全书名词索引,并附录了施先生有关唐诗研究的文章若干,以便广大读者阅读和研究。
第一次读施蛰存的文章,觉得作者很实在,《王绩:野望》中,作者分析者首诗,从历史考据到历代文人的批语都有,可是作者写出了自己的观点,不是盲目的写出自己的观点,而是写的有理有据,却在最后谦虚的写到:我这样讲“以意逆志”,没有文献可以参证。但是恐怕也只有这样的讲法,才比较讲得通。
文字通俗,道理易懂,反正我是看懂了。后面附的施蛰存对于唐诗的发展历程的文章也很好,看完以后对唐诗的发展有了大致的了解,需要系统梳理的读者,可以看看。
从时间轴上,分成了初唐、盛唐、中唐、晚唐四个部分,如果希望读某个时期的唐代诗歌也很方便查找。
我最喜欢鱼玄机的
赠邻女
羞日遮罗袖,愁春懒起妆。易求无价宝,难得有心郎。枕上潜垂泪,花间暗断肠。自能窥宋玉,何必恨王昌。
以前一直不知道整首诗,只知道“易求无价宝,难得有心郎。”这次读这本书,作者从写作背景,社会背景,历史背景,文化背景整首诗的意思分析了这首诗,不光让我长了知识也更喜欢这首诗了。
《唐诗百话(全三册)》读后感(三):做好了被喷的准备
施蛰存,叶嘉莹,李零的书最近几年都在大火,无奈尝试很多次都看不进去这几位大师的书。前两位都是写诗词鉴赏的,后边这位写过关于孙子兵法的书。先说诗词鉴赏的,通篇旁征博引的,各种考证,学术气息很浓,感觉特别专业,叶老甚至使用了西方文学研究的方法来研究中国诗词了。可是我还是看不进去,原因很简单,看起来绚烂华丽的东西,恰恰缺少写书人对美丽诗词的激情,缺少写书人对诗词作者的理解,这种书作为文学研究即可。李零的《兵以诈立》通篇不是在讲自己对孙子兵法的理解,反而都是考证,从哪出土了啥,有几种版本,我就想问了,你把书写成这样直接归类为考古学不就算了?
诗词作为文学作品最重要的是感人,不是各种炫耀和考证,有些东西从考证上是错的,但是不妨碍美感不就好了?兵法这种东西最重要的是对思想的理解,考证半天对于普通读者的意义在那?
《唐诗百话(全三册)》读后感(四):“知人论世”读唐诗
“知人论世”读唐诗
文/Sofia
有人说:“熟读唐诗三百首,不会作诗也会吟。”
不知别人如何,总之,从小到大,我也算读了几首唐诗宋词的,但是我总觉得自己腹中草莽,并无什么锦绣文章,不会作诗,甚至连“吟诗”也谈不上。每每想起林黛玉的那句“口齿噙香对月吟”,我便觉得与“风雅”一词,大约我今生也是无缘的。
不过,有时候,我也会想:我算是读过唐诗的吗,又或者算是熟读唐诗的吗?
是,那些流传千古、脍炙人口的名言佳句,譬如“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又如“飞流直下三千尺,疑似银河落九天”,再如“年年岁岁花相似,岁岁年年人不同”,用词浅显,易于理解,却意味深远,让人铭记于心,这样的诗句,读了便不会忘记,需要引用时,亦可信手拈来。
但是,另外一些也曾“熟读”过的诗句,到此刻,依然能脱口而出,只是我们真的理解它们的含义吗?
譬如,王勃的“城阙辅三秦,风烟望五津”一句,当年的中学语文老师早已仔仔细细地依据教科书、教辅材料一字一板地解释过这句诗的含义。但是,正如各门学问均需推敲研究一般,唐诗的探意,原来也是有争议,也是可以著书立说写成一篇论文的。
直到今日读施蛰存先生的《唐诗百话》,我才知道原来对于“城阙”和“风烟”的含义竟然有如此众多的讲究。我深觉涨姿势了。亦感觉自己不曾“熟读”、不曾读懂过唐诗。此前所学,不过是死记硬背,不过是借用了被今人鄙视嘲讽过的八股文的学习方法。
其实,字意、词意、诗意的新解,不过是我读《唐诗百话》的一个小小的收获。
《唐诗百话》对我的一个重要影响在于,这本书打开了一扇门,一扇通往另一种思维的大门,一扇开拓崭新视野的大门,让我见识到中国古代诗歌文化的源远流长、博大精深。
是的,我们知道风雅颂,我们也知道赋比兴,甚至,语文功底好一些的人,可以清晰地说出这几个词汇的意义。可是,我们知道它们的由来和各朝各代的解释吗?
是的,我们知道绝句,甚至可以随口吟出“窗含西岭千秋雪,门泊东吴万里船”这样以《绝句》命名的诗来。可是,我们知道何为绝,何为绝句吗?
是的,今天有不少人喜欢纳兰容若,也有不少人知道纳兰善于化用古典诗词。可是,我们知道,唐诗中有一些让当时人和后世人均惊艳万分的句子亦是化用前人诗句吗?
读施蛰存先生的《唐诗百话》,我真心觉得获益匪浅,受教颇深,的确是“听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
在《唐诗百话》中,施蛰存先生还提出了中国古代文学批评的一个术语——“知人论世”,意思是学习一切文学作品,必须先了解这个作品及其作者的时代背景。
这让我想起了拉斐尔的圣母像。倘若不知道拉斐尔的艺术追求,也许我们会误以为他的圣母像只是纯粹的缺乏仙气,而非对人性的呼唤。
亦如杜甫。一向以忧国忧民形象行走在诗歌的历史长廊之中的杜甫,除了“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这样沉重的诗句外,其实,也曾写过“香雾云鬟湿,清辉玉臂寒”这样旖旎的诗句。若不能“知人论世”地去读唐诗,恐怕还会以为这首《月夜》是他人借用杜甫之名而作。
只是,要做到“知人论世”地去读唐诗,又谈何容易?非数十年潜心钻研,又如何能够揭开唐诗的面纱一角?
幸好,有施蛰存先生的这本《唐诗百话》。施蛰存先生颇有一种旧时文人的感觉,腹有诗书,金玉内藏。无论是乐府,还是“言”“律”“绝”,都能旁征博引,洋洋洒洒地说个透彻明白,让人沉浸其中,在读唐诗的同时,更对中国的传统文化涉猎一番,受益匪浅。
《唐诗百话(全三册)》读后感(五):《唐诗百话》为什么值得读?(转毛晓雯 南都书评)
毛晓雯
作家南都书评链接
在进入正题之前,我们先来欣赏美国现代学术史上最滑稽的一个玩笑。相信我,这玩笑能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唐诗百话》的优势所在。
纽约大学物理学教授索科,向当时最富盛名的美国文化研究学刊《社会文本》投了一篇论文,并很快获得了发表。论文题目为《超越边界:通向一种量子力学的变化诠释学》(Transgressing the Boundaries: Toward a Transformative Hermeneutics of Quantum Gravity),且慢赞叹标题的高大上,正文比标题更加贵气逼人,通篇皆是诸如此类的宏论:“物理的‘真实’与社会的‘真实’一样,实际上都是一种社会的与语言的抽象观念。”“曾被视作常数而通用的欧几里德的π(圆周率常数)和牛顿的G(万有引力定律常数)如今已暴露了其不可避免的历史局限性,其数值也因新的科学发现而起了相应的变化。”
从标题到内容,这篇论文完全叫人摸不着头脑。但是文中出现的“变化诠释学”、“社会与语言的抽象观念”等高端措辞,以及五光十色的主义和理论,又让人感到此文不容小觑。
按照通常的惯例,这还不是高潮,高潮在于文章发表之后,索科跳出来公布了事实真相:读者读不懂该论文是正常的,因为就连作者索科,也不知道自己在写什么,这只是一个玩笑。他仅仅是模仿近年来在学术界大行其道的学术文体,搬出各种看上去很了不起的学术术语和后现代语汇,胡说八道了一番。然而就是这样的满纸荒唐言,却让读者既望而生畏又肃然起敬,没人怀疑作者的水平,只恨上帝没多赏赐自己一点智慧。
索科的玩笑,证实了当代学术圈的风气——动不动就搬某某主义来虚张声势,或引用先锋理论来狐假虎威,认真治学的没几个,整天挖空心思发明不知所云的新名词。而当代的读者,亦总是习惯于膜拜那些艰涩难读的作品,被它们华丽的外表所迷惑,以为不知所云的背后一定隐藏着宇宙奥义,其实,良药未必苦口,难以下咽的东西很可能就是糟粕。
在当今的阅读环境下,一个文本,不管水平多高、营养爆表,若读起来太过艰涩,也算不上功德圆满。因为阅读门槛太高,就等于在通向真理的道路上人为设置了小怪兽,绝大多数人不具备打通关的能力,只好停在半路哭泣。最好的文本,是那些阅读起来流畅愉快,内涵却一辈子都琢磨不完的文本。施蛰存先生的《唐诗百话》就是典型中的典型。因此,虽然多次重版,在今天仍值得推荐。
《唐诗百话》六十多万字,全篇没有一句难懂的话,没有一个刁钻的词,没有一条故弄玄虚的后现代理论,却深刻挖掘了关于唐诗的一切——格律、辞藻、典故、艺术特点、写法沿革,诗人们或繁华或悲凉或喜乐或仓皇的一生,以及与唐诗有关的唐史。任何一个识字的人,都能在这本书的指引下,找到中国人的精神原乡。施老说自己把《唐诗百话》写得“不上不下”,这哪是不上不下?分明是深入浅出、举重若轻。
文字活泼轻快,内容却颇具分量,作者分析问题之精妙,堪比福尔摩斯。以初唐诗人王勃的名诗《杜少府之任蜀州》为例,关于蜀州究竟是何地,自古颇有争议,作者就像破案一般,做了一番严密的推理:“蜀州即蜀郡。成都地区,从汉至隋,均为蜀郡。唐初改郡为州,故王勃改称蜀州。但当时成都地区已改名为益州,不称蜀州。故王勃虽然改郡字为州字,仍是用的古地名。向来注家均引《旧唐书·地理志》所载‘蜀州’作注。这个蜀州是武后垂拱二年(公元686年)从益州分出四县设置的,其时王勃已死,他不可能知道有这个蜀州。” 作者三言两语便将问题剖析干净,三言两语的背后,却是多年的考据工夫。
而此诗的首联“城阙辅三秦,风烟望五津”,历来有人将“城阙”理解为京城长安,作者又一次发挥侦探素质,揭晓了谜底:“按‘城阙’二字,早已见于《诗经》。‘佻兮达兮,在城阙兮’,这是《郑风·子衿》的诗句。孔颖达注解说:‘谓城上别有高阙,非宫阙也。’他早已怕读者误解为京城的宫阙,所以说得很明白,城阙是有高楼的城墙。只要是州郡大城市,城头上都有高楼,都可以称城阙。王勃和孔颖达同时。他当然把‘城阙’作一般性的名词用,并不特指京都。”
别小看“王勃和孔颖达同时”一句,这恰是作者推理的精妙所在。读古诗词,我们时常觉得某些字词难解,那是因为我们始终无法跳脱现代人的视角。我们很容易忘记,同一个词,在不同的时代有不同的解释。要知道唐人如何解释“城阙”,不应以后世任何一个时代对“城阙”的理解来解释,而应听听唐人自己怎么说,于是施老找了与王勃同时的唐代大学问家孔颖达的解释做佐证,问题便迎刃而解了。你看,读《唐诗百话》,学习的不止是唐诗,还有诸多治学的技巧,《唐诗百话》还可叫做《论学霸的自我修养》。
《唐诗百话》不仅对唐诗本身作抽丝剥茧的分析与品鉴,还时不时对与唐诗有关的人事发表精妙通透的议论。
孟浩然的《岁暮归南山》诗,劈头四句很出名,“北阀休上书,南山归敝庐。不才明主弃,多病故人疏”,将怀才不遇的忧愤之情描摹得淋漓尽致。这首诗有段著名的公案,“有一天,王维在宫中办公,私下把孟浩然请进去闲谈。忽然玄宗皇帝来了,二人大惊,孟浩然赶紧躲在橱下。王维不敢隐瞒,只好直言请罪。皇帝听说是孟浩然,就说:‘这位诗人,我已听人讲起过,还没有见到。”当下就叫孟浩然出来,并问他:“带了新诗来没有?’孟浩然回说没有。皇帝就要他念几首新作品,孟浩然就念了‘北阙休上书’这一首。皇帝听了很不高兴,说:‘你自己不要做官,怎么诬蔑我,说我弃你呢?’于是命他仍回终南山去。”
关于这段公案,评论家们多半都站在了孟浩然那边,认为错在封建社会的统治阶级不能辨识贤才,导致了下层知识分子的悲剧。施老的看法却截然不同,他认为“《归南山》一诗既消沈,而且有怨愤之情,把自己的穷途潦倒归咎于‘明主’,做皇帝的当然听不进去。”皇帝也是人,皇帝也有人类的通性,普通人尚且喜欢听好话,何况万万人之上的皇帝?不讲究沟通的技巧,难怪孟浩然一辈子穷愁潦倒。——这种以人性为出发点的议论,即使在今时今日也难能可贵,更别说是在《唐诗百话》成书的上世纪70年代了。
70年代的学人作文艺评论有个通病,那就是阶级观念先行,聊什么都能扯到剥削阶级和平民百姓的对立,诗中提到茅屋漏雨,评论家马上就要一把鼻涕一把泪地抨击万恶的旧社会;诗中提到歌舞升平,评论家立刻嫌弃说这就是百姓痛苦的根源。
但施老是一个奇迹,身处以苦大仇深为主旋律的70年代,竟能摘下阶级观念的有色眼镜,在最大程度上就诗艺论诗艺、就事论事,换句话说,就是不用政治绑架文学与生活。我以为,这才是《唐诗百话》最可贵之处。
《唐诗百话(全三册)》读后感(六):只愿你,见素抱朴,不忘初心
白驹过隙,人生短暂如云烟。于我而言,时间应该浪费在诗情画意的好时光里。
在这个愈来愈喧嚣、浮躁的时代,还有几人能够回到质朴初心,闲来无事时,于月下窗前,吟吟哦哦一番唐诗,过一回古人闲情逸致的温雅生活。想来,能过上这样温润素朴生活的人,大抵是越来越少了。
于现世,社会越来越复杂,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愈来愈疏离,我们忙着赚钱养家,忙着美貌如花,忙着运筹帷幄,忙着潇洒落拓,而很少有人,忙着读书,更不用说能够真正地静下来,品味一回中国古典文学里唐诗的魅力。
当然,你肯定会这样认为,柴米油盐酱醋茶的物质保障都还解决不了,哪有时间静心读书?又或者,工作的事情乱如麻,很多任务需要完成,很多环节需要打通,根本没时间读书。不过,在我看来,如果自己不想做一件事,无论怎样的说辞,都是借口。
只是,一直毛毛躁躁、忙忙碌碌的你一路走来,过得好吗?你总是很少读书,身体累,思想更累,因为你没有想过放松,没有想过饶恕喧闹人群中忙于生存的自己。身体要行走在路上,要为生计奔波这是正确的,但在奔波的途中,我们也不要忘却与灵魂对话,自我省视,不要让步伐走得太快,而丢下了思想。
于我而言,诗词吸引我的地方是它独一无二的意象美以及古人对生活禅意美的追求。这种美,就好比是只要一壶茶,一卷书,一张琴,落花、流云、溪水,这些微小的细节便能构造出一个清幽的环境,能够明心见性。我们生活的快乐不必用声色犬马的事物来衬托,一些幽微的事物亦能让自己愉悦。想来,我们若是能以古人的慢,缓解现世的躁,这理应是消解生活障碍很好的方式。于是手头拿到的这套《唐诗百话》(修订版)就值得好好一读了。
今天的我们重读唐诗,不是“倒退”,而是帮助自己更好的“出发”,读唐诗就好像是在与古人进行一场无声倾谈,谈春夏秋冬各自季节该做的事,谈日出劳作日落而息,谈趣闻物什,谈日月流年。如若你能沉淀下来静静地读这样一本书,就能从书中感受到不同的智慧。我曾经写过这样一句话:“忘记传统并不可怕,因为每个人都有自我选择记忆的权利。真正可怕的是以掩目捕雀的方式告诉自己,古典传统文化为‘过时之物’。”
如今,越来越多的人喜欢给传统文化贴“时尚”、“市场化”之类的标签,而逐渐淡忘古典传统文化本身内在的属性,甚或,有些人选择走马观花瞭望唐诗,并非亲身体验唐诗的诗意之美。当我们过多地崇拜外国文化热闹的时候,可否挤出浮生半日闲的静默时光,远离纷杂尘嚣,温故一回我们自己的古典传统文化。
在我看来,今天的我们对待古典传统文化缺少的不是信仰,而是传播。之于古典文学,他就好像是岁月沙场上的战士,难以抵挡兵荒马乱的时代,难以抵挡翻云覆雨的变化,仅靠支零破碎的内心支撑着。而我们,却作壁上观,不去解救奄奄一息的“他”。
还好,《唐诗百话》给唐朝弥足珍贵的往事留下了一丝凭证。施蛰存先生的这套《唐诗百话》不愧是方家呕心沥血之作。全书分为上中下三辑,由初唐诗话、盛唐诗话、中唐诗话、晚唐诗话四个方面入手,明着是解唐诗,暗着又在说历史,宛如一部“唐诗百科全书”。
书中,作者旁征博引,既有自己独到的见解,也引用了别人的观点,逐字逐句的解析,包括典故、字词、韵律等,让整本书显得锦上添花。施蛰存用的字词省简,他以深入浅出的笔法一针见血道出自己领悟出来的唐诗。比如评沈佺期《遥同杜员外审言过岭》这首诗他这样说:“我们把这首诗作为初唐七言诗的样板。”又比如王维《五言律诗三首》中他这样说:“都是正面描写,并无比兴,没有什么寓意,也并不歌颂什么。”对于唐诗,施蛰存认为“唐代诗人用力于炼句,讲究诗句精警。”
施蛰存先生的这套《唐诗百话》在学术上十分严谨,其遣词造句也不死板,因为其中糅合了作者的感性妙答。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修订版再版较之于旧版本而言,在文字校对功夫上更加细致,图书装帧亦精美,华东师大版中不见了的初版名词索引也予以恢复,里面还有一些诗人肖像,符合了如今“图文时代”读书的要求。这样一套唐诗“鉴赏辞典”,是一直陪伴我的枕边书,闲暇时,烦闷时,翻几首山水田园诗读一读,看看施先生的解读,既是学习,也是享受。
文艺的说,这套《唐诗百话》是一味药,能让越来越浮躁的我们得到缓冲,让每一个人都能够静下心来感受一回唐诗里的韶华流光,生活物事。
直白的说,这是一套古典文学类关于唐诗的入门书,让初学者既对唐诗的发展脉络有一个掌握,也能一叶知秋,通过此书了解唐朝历史。
文/沈善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