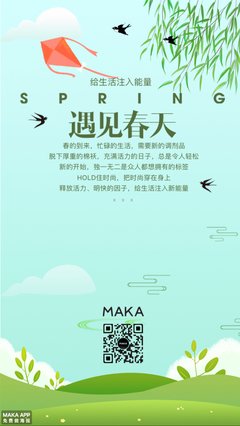
《茶馆》是一本由王笛著作,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的平装图书,本书定价:59.00元,页数:490,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茶馆,随随便便都能扯出一背篼蜀香往事。下头这本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有简体版了。
●王笛使用哈贝马斯“公共空间”的概念去研究老四川的茶馆,固然有方法论的新意,但方法论上被白左殖民,这是中国学术界的大问题。如果没有此种自觉,后果很麻烦。
●生动,尽管对于这样的大部头,资料稍显单薄,作者自己很好地理解了成都
●将茶馆作为一个“公共空间”进行社会微观史的研究,把历史中大多数的平凡的普通人的日常生活中不能离开的茶馆在成都的近代史演变中所发挥的功能以及它在历史发展之中的变迁,重新构建了晚清以及民国(1900-1950)的整个社会生活,尤其是后记,作者以满怀深情的笔触抒发了地方传统在国家大一统的压力下地域特色必将不断消失远去的这种乡愁,令人动容,同时作者也深知这种地域特色,必然随着国家对于地方的统一管理下不断渐行渐远,从每天曾经一片一片的卸下门板的一爿小店到如今高楼大厦鳞次栉比的成都街市,无处不是在国家统一化浪潮下复制粘贴出来的现代城市,而这种乡愁的味道也离我们越来越远,随着新移民的纳入以及统一化的建设浪潮以及公众的失忆,这种乡愁注定只能飘散在历史的烟尘之中和拆迁的灰土一样沉入地下的深处。
●史料的丰沛、组织的精密和前言结语的画面,令人赞叹。横向物类、细节、关系对时间、事件线索的分割,与其说扬长避短,毋宁说是微观史才实践。理论分析主要集中于导言各章篇末,涉点广泛,劳工、性别、行会、媒体、秘密会社、地方精英诸公共空间功能角色元素一应俱全,国家改造、空间要素的中西比较也不算太糟。但糟糕的是在乡愁与技法之外,似乎也确实没有别的收获。
●蝼蚁般的人和事,随着时代消散无形,谁想帮他们写书立传? 功利如我是不会想了。。
●选题和视角都值得学习,但作者反复尝试的理论升华并不成功。“知识精英VS市井大众”、“西方模式VS本土文化”、“国家权力VS地方传统”,对这三对关系的分析浮于表面,丰富生动的细节反而被困在了常见的西方理论模式里,导致这些看似分明的价值对立更像是其本人的想象。另外读过之后更觉得老舍先生真是太了不起了。
●虽然关注的是微观事物/空间,视角上受到文化史转向的影响,但在对象的观察上并不那么注重探讨再现、观念等文化史一般关注的东西,讨论还是在比较传统、宏大的脉络,比如都市商业史、现代化进程中国家/社群/个人的权力博弈等语境中展开。在资料上十分下功夫,记录了不少有意思的故事和民俗,在这一点上也算是微观史学的优势了。
《茶馆》读后感(一):《茶馆》
多方主体在茶馆休闲、娱乐、会友的公共生活;茶馆的经营与管理;国家权力,地方权力,精英,大众等在茶馆这个舞台上的博弈等等都写得十分精彩。相信作者今后一定是一位大家,他研究的内容涉及历史,政治学,社会学,人类学,文学,艺术等,而且文字十分感人,通俗易懂,可读性很强。 作者不是作为一个旁观者在冷冰冰地进行描述,书中饱含一个土生土长的成都人对家乡地方文化的热爱与敬佩。他有一种使命感,要为祖辈们作史的使命感,而他也确实做到了。以茶馆为切口,把1900-1950年的成都生动地展现在读者眼前。以下是很喜欢的一句话: “弱小而手无寸铁的茶馆经理人、茶倌和茶客们,在这五十年的反复鏖战中,任凭茶碗中波澜翻滚,茶桌上风云变幻,他们犹如冲锋陷阵的勇士,为茶馆和日常文化的最终胜利,立下了汗马功劳”。
《茶馆》读后感(二):“泡”出来的区域微观城市史研究 ——以王笛著《茶馆:成都的公共生活和微观世界,1900~1950》为主兼及作者其他著作与学术史钩沉
城市,是当今人类生活的主要空间,城市的面貌及形制承载了大多数人的生活,在这个由人构成的复杂空间里,每天都在上演着各式各样的故事。亚里士多德主张的城市生活就是使生活成为可能,但是它的终极目标是使生活有价值。当大都市正在成为我们不得不居住的城市时,这一格言在今天看来是讽刺性的。然而亚里士多德是正确的,仅仅在庇护场所生存并不能满足人类,因而即使是在大都市中,我们也必须使生活有价值,这意味着要为人类的感情、观念、信仰以及追求内心生活提供精神的空间。[1]“公共空间”以及其中的人们作为重要的载体却常常能够被人们所忽视,充盈在其中的文化意境在“精英视角”下被无情地冲淡。王笛正是看到了其中的意义和价值,运用新视角、新材料和新方法,以茶馆为核心,试图重建历史上的公共空间,《茶馆:成都的公共生活和微观世界,1900~1950》[2](The Teahouse: Small Business, Everyday Culture, and Public Politics in Chengdu, 1900-1950)本书也就应运而生。关于本书的讨论不只在内容以及叙述对象的层面,更重要的是作者的视角以及方法论的问题,西方观念融入中国研究后究竟会呈现出是么样的效果;这种实践是有益的尝试,还是会将传统学术引入歧途;中国学者怎样才能拥有适合自己的话语?这些问题都蕴含其中,本文试图通过各个侧面的分析来为这些问题找到属于自己的答案。
《茶馆》读后感(三):民族志与社会理论
落地蓉城,刚好读完。 先说书:引子和尾声两章极其精彩。开卷让人回想起《尼加拉》开头那个为荣誉而死的国王。只有人类学才能不断地为我带来这样的高光时刻。 这本书最好的写法其实是沿着引子写下去写成一本小说,然后接上结尾50年一梦回首。 中间11章有10章论述和1章结论,总体来说写得不怎么样,10章论述的安排铺陈没有新意,只是简单的史料罗列和分类,第11章强行升华做理论比较,可谓生搬硬套莫名其妙。据此,总的来说如果说王笛的想法是做一个哈贝马斯社会理论的经验研究,那无疑完成度是很差的。 王笛其实拿着一批相当有价值的材料,令我觉得尤其有理论空间的包括文化精英的删诗活动(那个叫《杀子报》的话剧太有意思了,我昨晚做梦甚至都梦到了)、袍哥帮会与地方自治、军阀期间四川的武装化、团练问题等等,深究下去都很精彩,但文中就平平带过了。 但以此指责王笛这本作品是失败的是无理的,因为为理论提供某种质料恰恰不是民族志的意义所在。民族志的活力和意义正在于那些理论系统无法统摄的细节。在这个意义上,民族志材料越是无法归置于什么理论之下,这些材料才越有价值。 我看来,《茶馆》真正的结论是那个尾声,作者最后亲自在1950年的蓉城降临,作为一个不可说的已知未来的见证者,他用这本书表达了对成都人最普通的共同生活的热爱和怀念,这种十分个人性的情感恰恰构成了《茶馆》的精彩及其意义,在这种情感面前,哈贝马斯什么的真是毫不重要。 大概一个90年代的普通青年对这样的茶馆真是毫不陌生,对我自己来说,高中逃学去的网吧,大学隔壁寝的空座位,有灯之前的夜晚紫操,这些共同生活的场景才是日复一日的模糊岁月中最鲜亮的标点。
《茶馆》读后感(四):茶馆以及生活方式
王笛的《茶馆:成都的公共生活和微观世界》,是目前为止我视野所及对茶馆最宏大的历史叙事。在这个喜欢总结不喜欢根究的文化氛围中,我们总是习惯拿一些总结陈词来定义某种生活,却少了那份历史叙述的冲动与勤奋。所以,对这本书,我首先就怀着敬意与感激。
一个问题却是,茶馆为何成为成都的一种显著生活方式?那些混杂的记忆与历史到底要如何呈现?王笛采用新旧图像与虚实文本来凸显茶馆的物质空间引发的社会、经济以及政治问题。
在颇具诱导的开篇中,时间似乎是定格的:“1900年1月1日,农历己亥年腊月初一,即20世纪的第一天,这正是一年中最冷和白天最短的时节。”就是在这样一个平淡的清晨,许多人做了同样的一件事,踏着霜露,走进茶馆,开始了自己的早茶生活。
来茶馆的人不一定都会喝茶,有看戏的,有谈生意的,也有来评理调解的……茶馆的功能因此被放大。然而可惜的是,这些问题作者并没有进一步讨论。王笛太在意他所理解的西方理论在成都的对应关系,故削弱了那些文本与图像的价值。
也因为研究主体的关系,作者抛弃茶而切入茶馆,必然会带来研究的致命缺陷,怎么看都会陷入欧洲咖啡馆的窠臼之中。由茶馆这个物质空间带来的性别观、族群观以及地方文化与国家文化的关系,一旦演变成中文便显得生硬而粗糙。考察茶馆的诸多功能,如果失去比较对象,比如青楼,比如堂会,比如茶会,就必然有着过分夸大的嫌疑。
另一个层面上,如果对比英国之下午茶会,那么中国茶馆很显然就是公共领域。在中国概念里,天下为公,缺乏的恰恰是私人空间。所以我觉得宋代以来最了不起的一点正是茶空间(茶寮)的独立出现。王笛忽略对茶的考察,让茶馆的来源变得可疑起来。■
文/周重林(刊于河北青年报)
http://www.hbqnb.com/news/Html/book/2011/830/20254091274855.html
《茶馆》读后感(五):洗煤炭的活儿
“如果他(作者)说他要给茶馆和茶客撰写历史……他们(茶客们)可能会用典型的成都土话把他嘲笑一番:‘你莫得事做,还不如去洗煤炭……’”
可是,作者兼译者王笛还真去“洗煤炭”,而且绝没让人失望。
在野草书店看见它时,我是被“茶馆+成都”吸引的。待把书名看完《茶馆——成都的公共生活和微观时间,1900-1950》,大抵知道它和《叫魂》差不多,是微观史类型的研究。
我认同作者以细微见精彩的角度,也赞赏作者对小人物命运历史的关怀和重视。西方研究方法的严谨和准确,使得哪怕是注释都尽可细读,从中发掘出趣闻。正文从茶馆这个舞台下笔,梳理茶馆和社会、经济和政治的互动关系,探讨了在历史的进程中,“落后”生活方式所代表的独特地域文化和无为而治的城市生活在近代多舛的历史进程中,在一出出的悲喜剧中,为现代化进程和国家权力的强势逐渐渗透和蚕食。尽管它们真正的质变应该发生在20世纪的后半叶,但量变一旦开始,便覆水难收。我也更喜欢《引子——早茶》和《尾声——寻梦》两折,文笔精彩,情感真挚,引人共鸣。
在书中,作者为那个传说中的老成都画了细致的地图,附上了古老的照片,对于一个基本没有坐过茶馆的新时代文青来说,这本书似乎更像是给了我一双眼睛,在飞逝的时光中,重逢一些附着在老成都历史上渐行渐远的人物、旧闻和传说,让我回溯经历一次百年前黑白昏黄的日常人生。中国的历史热衷帝王将相,文学偏爱才子佳人,会有什么人去为茶客、为堂倌、为艺人、为小贩不惜笔墨?他在尾声中,更是热烈颂扬在变幻的历史中恪守日常生活的习俗,在卑微的生命历程中遵循自由的传统,在强力的压迫中挣扎生存的人们:
“他们不会想到,在这位小同乡的眼中,他们就是历史舞台上的主角。在过去的五十年里,他们所光顾的茶馆,他们视为理所当然的坐茶馆的生活习惯,竟一直是国家权力与地方社会、文化的同一性和独特性较量的“战场”。他们每天到茶馆吃茶,竟然就是他们拿起“弱者的武器”所进行的“弱者的反抗”。这也即是说,弱小的而手无寸铁的茶馆经理人、堂倌和茶客们,在这五十年的反复鏖战中,任凭茶碗中波澜翻滚,茶桌上风云变幻,他们犹如冲锋陷阵的勇士,为茶馆和日常文化的最终胜利,立下了汗马功劳。”
正如王笛盛赞平凡的人们的伟大力量一般,我亦盛赞王笛为平凡的人们著书立说、在被人忽略的微历史中挖掘闪光的种种贡献以及他尊重升斗小民历史价值的深厚的人文情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