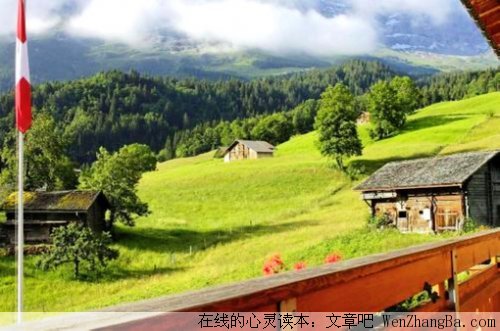
阅读是一种幸福的时光,在幸福的时光里,感叹时光的流逝正像一位哲人所说的“逝者如斯”;是的,阅读马永欢老师的《踏雪寻梅》,就是一种享受的过程,我们会随着作家一起坠入到”寻梦”的探索之旅中。
“海畔的青石向海心亭延展,青石上方的一排垂柳也随之延展。哦,今天我游览洱海的终极目标海心亭,要到了。海心亭,2010年的春节,我来过一次,今天是第二次,岁月匆匆,你的容颜又如何?借亭赏海又怎样?
垂柳下,立着一块宣传铁牌,书写着总书记的深情期望,‘一定要保护好洱海!——’红色的语句,宛若一缕红色的曙光,照耀着一望无际的洱海,催人奋进,抒写洱海的新篇章。
我走进海心亭,亭依然,水依然,而不同的是,水更清了,游客更多了,飞鸟横空出世了,我感慨万千,意气风发。北边,一艘轮船乘风破浪,卷起“千堆雪”;东南方向的碧波青山新楼,如同优美的画卷在韶光中舒展;西南方向的清波群鸭,以及两岸的高楼大厦,在如同轻纱的海雾中讴歌时代的辉煌;西北方向的海鸥、轮船、高低错落的现代建筑、若隐若现的苍山,在春光中辉映。远观这些景致,让我的思维开阔,情感纵深。由远及近,在淅淅沥沥的春雨中,有的游客举伞游观,有的游客坐亭远望,有一伙游客站立亭内用手机兴奋地拍摄,我冒雨走近,走进拥挤的陌生的人群。轮船向北进发,海鸥展翅南飞,风雨无畏。海鸥是洱海的精灵,不是一只两只而是无数只,有的高飞有的低飞有的潜入水中,洱海就是它们快乐的天堂,也是四面八方游客相聚春游的乐园。“保护洱海就是保护大理发展的根基”,此时此刻我深刻领略。
春雨连绵,海风阵阵,清波泛起,飞鸟环绕,泳者似歌,目光所及,心怡咏叹。海心亭,我留恋难返的情感天堂。”(《春天外出》)
当我还在为作家的文学“寻梦”之旅击节三叹之时,南宋诗人陆游的一首诗,突然闯入我的脑际,久久盘桓不去:“僵卧孤村不自哀,尚思为国戍轮台。夜阑卧听风吹雨,铁马冰河入梦来。”时值68岁的陆游退居家乡山阴,即使在病痛缠身、家国飘摇,山河破碎的困境之下,一代大诗人保家卫国的理想不渝,爱国激情始终在胸膛内涌荡,铁马冰河的梦想也会在病痛的头脑中出现,这对于一个伤病缠身、将近古稀之年的老人来说,激荡的该是怎样的激情与豪情?
这难道不是对马永欢老师最真实的写照?这难道不是对坚守回族文化最高的致敬?这难道不是对家乡永平、大理乃至云南故土风物的深深眷恋和赤子之情的真实流露?马永欢老师的文学梦正是因此而来,这是一种怎样的担当,更是一种极为重要的责任使命意识,虽遭遇各种挫折艰难,仍然初心不忘,砥砺前行!
这是《踏雪寻梅》散文集传达给我们的最为诚挚的感情。文贵言志,《踏雪寻梅》正是言志达情最好的工具。言志与缘情体现出来的美学趣味也是有差别的,“诗言志”和“诗缘情”是中国古文学和古文论史上两个重要的诗学范畴。随着陆机《文赋》“诗言情而绮靡、赋体物而浏亮”的提出,对文学的认识所谓“诗缘情”就是说诗歌是因情而发的,是为了抒发作者的感情的,这比先秦和汉代的“情志”说又前进了一步,更加强调了情的成分,进一步摆脱了“止乎礼义”政教道德的束缚,这是魏晋时代文学自觉的重要表现。从魏晋开始,“诗缘情”出现并经历了与“诗言志”对立而后趋于统一的过程。从“诗言志”到“诗缘情”体现了人们对事物的认识从流到源、由表及里的一般规律,也体现了人们对诗歌本质认识的深化。
具体到《踏雪寻梅》这部散文集,散文的特点,我们最常引用的一句话就是“形散神不散”现在基本不讲了,散文的写法有很多种,我们讲过“文无定法”,如果散文都这样讲授、这样写作,变成一种僵化固守的模式,那将是散文的悲哀,更是文学的倒退。从这个意义上讲,“诗言志”、“ 诗缘情”就有了进一步探究的种种可能性。这里所说的“诗”在我们可以理解为“散文”,或者可以理解为广义的文学创作。言志与缘情,如何在散文创作种得到进一步的统一,是个值得探究的文学课题。当下的散文创作,反映生活和社会的种种变迁,反映个体人生的种种遭际,既是时代发展的要求,又是人生追求的必然体现。
马永欢老师的这部散文集,散文集《踏雪寻梅》共分为五辑,第一辑为情感之歌,第二辑为精神之旅,第三辑为心灵之韵,第四辑为写作之镜,第五辑为思想之春。五辑的散文创作过程,言志、缘情的结合有了进一步的发展。作家在其《后记》中这样表述:“散文,从不同角度极力表现我内心的踏雪寻梅的精神,极力表现梅花精神在我心中扎根、生长、向上的执着,极力表现梅花情愫在我的文学人生历程中芬芳的纯粹。当然,表现的文学艺术性,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但我将自我肯定,但会以此为起点,不但继续寻觅散文之‘文’,而且要追寻散文之‘质’,追寻‘文质’辉映的散文的最高境界。”
是的,文质并重,言志与缘情,说到容易做到难。文学创作的甘苦,正如人生一样冷暖自知。言志与缘情,文和质,诗歌与散文,如何交融在一起,甚至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这不是说做到就能做到的,这里既有文学素养的磨砺,还有人生阅历、社会经验的种种化学、物理、生物作用才能做得到的,更有机缘巧合和顿悟的种种偶然必然因素在里面,这正是文学神奇与着迷的地方,或者是说文学是无用的,亦或是文学是大用的,无用之大用,正是文学的又一特征,区别于其他学科,存在于意识形态的上层建筑中。
“碧波荡漾,一只野鸭漂浮着,似乎安静地做着一个美好的春梦。走在岸边的我,停下脚步,注目欣赏,无不喜悦。跨越西洱河的大桥,神奇地把两岸的现代化城市相连,也使我的目光由近及远地领略水、桥、房、灰色的天空组合的图画。这几天是倒春寒的时节,天气特别的冷,但我此时此刻的内心是温暖的。
过了大桥,一群野鸭在两岸的水间,长长的排列着,嬉戏着。春暖鸭先知,鸭群的热闹,也是我的。于是,我就着岸边的红色叶子花拍照,一幅美轮美奂的摄影作品,瞬间诞生。我对岸的一个古色古香的亭子,在美好的时光中,与碧波相连,与我身边的红色叶子花相连,与春天相连,与我的心情相连,因此我拍摄存念。一条打捞垃圾的小铁船,泊在岸边,倒影在清水中,似乎在整装待发。这劳动工具的姿态,这一页轻舟,也令我思量一番,赞美一番。我且行且游,我视野中的洱海越来越辽阔,苍茫。休整的游船泊在岸边,水中的一群野鸭嬉闹着,与游船保持一定距离,动与静的结合的图景,令我兴奋。
春风杨柳万千条,岸边的垂柳一排排,抽芽展绿,正迎接一个崭新的春天,洱海的春天美如画。无论是近景或是远景,都是迷人的。因此,我一步一拍摄,拍摄洱海的不同景致。公路边洱海畔的一个景致,简直令我倾倒,放慢速度欣赏。海畔的青石大大小小,浅水中的树木高高低低,水中两根铁杆牵系着的一只小铁船,还有青石上方的红色叶子花,构成的一幅画面,令人百看不厌。船的倒影,树的倒影,不仅十分的清晰,而且蕴藉着猜不透的动人故事。”(《春天外出》)
《春天外出》以作家行程为线索,记录下作家“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的心路历程,融个体的生活琐事、赠书、采风、情感经历、婚宴流水席的习俗为一体,展现回族白族等滇西民族团结、其乐融融的画面,表现当下回族等少数民族人的生活状态和蒸蒸日上的幸福生活。不事雕琢,人物、风俗、毕肖毕现,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
在我看来,这段文字能较好地将文与质、言志与缘情、读书与生活、艺术与生命很好的结合在一起,可以看做作家成功的示范之作,值得读者花费更多时间阅读,也值得作家进一步升华自己文学创作才华,提炼更为精美的艺术珍品。
努力不一定有所回报。这五辑散文文与质是否很好的结合在一起了,这五辑散文的言志与缘情是否契合,这就需要评论者和读者做进一步的甄别了。
正如作家所说的那样:“极力表现我内心的踏雪寻梅的精神”、“ 极力表现梅花精神在我心中扎根、生长、向上的执着”、“ 极力表现梅花情愫在我的文学人生历程中芬芳的纯粹”。在我看来,文学正是作家人生开出的一朵绚烂的生命之花,芬芳了世界,给予了这个世界向上、向善的无穷动力。
单单从这个意义上,我就要为这样一位播火的回族作家点赞!
是为序!
张勇,男,河南新野,文学硕士,文学评论者。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会会员,河南省作协会员,签约作家。创办《黄河会》《草庐文学》等刊物。曾参与编纂《南阳历史文化大辞典》、《赢在中国》《大国律师》《向公正致敬》等系列丛书,现任职于某大型企业集团。作品多发表于《中华读书报》《新华书目报》《中国地名》《文学报》《宁夏大学学报》《华中师范大学研究生学报》《昌吉学院学报》《宁夏大学校报》《躬耕》《六盘山》《山东商报》《新消息报》《半岛都市报》《贵阳晚报》《江苏作家》《青年文学家》等刊物。
[1]张勇.仰望与躬耕的境界[J]. 教育.2016,(13):48.
[2]张勇.躬耕不辍,行路不止[J]. 艺术教育.2007,(5):12-13.
[3]张勇.采棉[J]. 回族文学.2019,(4).
[4]张勇.探寻祖克慰散文艺术世界的建构[J]. 躬耕.2019,(7):62-64.
[5]张勇.从信任里闪现出的光芒 ——杨永汉短小说印象[J]. 躬耕.2019,(3):63-64.
[6]张勇.从信任里闪现出的光芒[J]. 躬耕.2019,(3).
[7]张勇.村魂之呐喊与寻绎 ——党栋长篇小说《村魂》赏析[J]. 躬耕.2019,(10):63-64.
[8]张勇.村魂之呐喊与寻绎[J]. 躬耕.2019,(10).
[9]张勇.“感兴诗学”视域下的《对话别廷芳》[J]. 躬耕.2017,(1):63-64.
[10]张勇.城市和家园的双重变奏[J]. 躬耕.2017,(10).
[11]张勇.城市和家园的双重变奏——李永普诗歌赏析[J]. 躬耕.2017,(10):63-64.
[12]张勇.长恨歌密码[J]. 躬耕(传媒天下).2017,(10):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