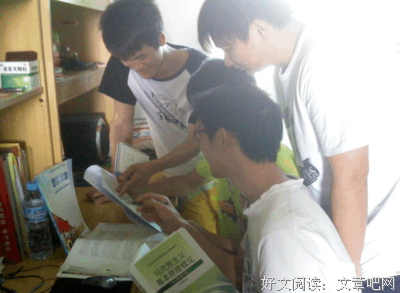
《心寂犹似远山火》是一本由[日]斋藤茂吉著作,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的精装图书,本书定价:49.00元,页数:240,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心寂犹似远山火》读后感(一):斋藤茂吉的调色盘
斋藤茂吉诗作的字里行间铺满了缤纷色彩,写出了他对生活的敏感视觉体验。如海边的仲夏红日、珠贝鲜红、浪尖青光等;睦冈山中的落日红霞、银色雪山、泛白的石滩等;Ohiro里的朱红色的庙堂、素白的藤花、麦浪金黄、琉璃色的草实等。在这些众多的色彩当中,红色是最常被提及的,表现了茂吉血液里浓烈鲜活的生命力。也许是因为青年时的学画经历,茂吉熟稔的用笔触定格四时轮转及人在世间的发生。 本书个人比较喜欢《赤光》里缠绵缱绻的“Ohiro”连作和遣词古朴真挚的“离世的母亲”连作;以及《白山》里有对人生命运深度感悟的“东云”连作和气韵生动的“边土独吟”连作。 本书的译者序简明介绍了短歌诗体、连作和曲调的概念,另外在译后记中谈及了诗歌翻译的问题、短歌的风格。这些内容延伸了作品本身,可以运用到对其他短歌诗作的理解。
读完《古今和歌集》后第一次读斋藤茂吉的短歌,从《赤光》到《璞玉》、到《灯火》、再到《白山》,读完如同和斋藤一起走完了他的一生。相较古今调的纤巧,斋藤的短歌显得冲淡平实,选取的意象都很寻常,却能在“险峻之处(引用了译者的词)”给人以会心的一击。
我对山川草木虫鱼总有一种偏爱,因此和斋藤的短歌很合得来,斋藤在连作《现世之身》的第一首就这样写道:“宽叶细叶/雨落在新绿的森林/变柔和的/还有我的声音”。在他晚年的诗集《白山》当中,常有大病初愈就去到山川之间的情形,“病愈初行最上川”、“大病初愈/来这寒土之上”。也许是山川能开阔人心,在飞花落叶的自然的推移中,斋藤对“过半的平生”的伤老之情却不多,是在深夜里牙齿松动疼痛都觉得“我心却宁静”的人。全书中最得我心的一首短歌即是在病愈后怀抱着“自然的赐予”——联系上下的两篇来看应当是栗子——写的,“如山里/落下的栗子/我是新时代/不甘落下的/一介老生”。
斋藤是能在自然中将声音柔和下来的人,故而也有十分充沛的情感,为离世的母亲和分别的恋人写下许多怀念的短歌,还在《璞玉》中为自己的祖母写了《冬山》和《寒风》两篇连作,读完使我想起自己的外祖母,“祖母做的蘑菇汤/喝一口/想倚在她的胸膛/待睡意袭来”,每个人的祖母都有一道最拿手的汤,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味道。斋藤给恋人Ohiro的情诗中我最喜欢的是关于纤草庙堂的一首——“漫无目的的徜徉/摇摇晃晃/来到浅草/朱红色的庙堂”。斋藤会在浅草的庙堂中做什么呢,连作中没有提,只知道买了浅草“寂寞”的煮鸡蛋而已。我想到胡兰成在日本清水市的观音堂怀想小周小姐:
我投了一枚铜币,礼佛已,稍稍伫立了一回。今生里我与训德,是金玉姻缘也罢,是木石姻缘也罢,单这小小一枚铜币落到奉纳柜里的一声响,已够惊动了三世十方。胡兰成在世人眼里的名声不算实在好,引用他的这一段叙写惟是我作为读者一厢情愿的猜测罢了。可是对于生别的恋人,在神佛观音面前能做的除了遥祝福泽不尽似乎也别无他事了。
斋藤茂吉的短歌不同于以往读过的小林一茶、松尾芭蕉等人的俳句,他并没有俳人使我感到的远意,反而真实得像身边人。除了标题引用的那句之外,年轻的斋藤在《忏悔之心》里还写了一首可爱的短歌,“今夜想学习/然而/我却在床上/打瞌睡”,既然如此,我老去以后,应当也会有斋藤的宁静的心吧。
《心寂犹似远山火》读后感(三):连雨不知春去,一晴方觉夏来
第一次接触斋藤茂吉的诗歌,即新颖又好奇,刚开始看的时候还有些朦胧,生疏,后来慢慢的有一些感觉,一点一点的深入才发现其中的奥妙,这真的是一本值得一看到书本,如茫茫心海里,孤帆谁与同,就是如此的独特不一,甚是美好。
都说在读任何诗集前,必不可少的为了解其诗人,斋藤茂吉旧姓守谷,是家中的老三。由于家境贫寒,茂吉15岁便只身前往东京,作为养子来到同乡的斋藤纪一氏家中,1905年,他以夫婿身份入籍,与斋藤家的女儿辉子立下婚约,从此改姓斋藤。同年,他受到身为精神科医师的养父的影响,入读东京大学医学科。在追求职业理想的同时,茂吉也没有放下从小对和歌的喜好。24岁那年,他加入著名歌人、正冈子规的弟子伊藤左千夫门下,正式从事和歌创作,其处女歌集《赤光》于1913年出版,立即在文坛引起轰动。这部作品继承了正冈子规的“写实主义”,将《万叶集》歌风中的日本传统与西欧现代精神相融合,为短歌注入了新的活力。就连著名作家芥川龙之介也不由赞叹:“我看诗歌的眼光,并不源于其他人,而是斋藤茂吉让我对诗歌开了眼......” 在此后的几十年,斋藤茂吉创作了上万首短歌,但他仍然视自己的主要身份为医生,作歌只是副业。值得注意的是,茂吉的短歌作品里有很多是“连作”(相当于组诗),例如为悼念生母而作的《离世的母亲》(共59首)、表达对恋人思念之情的《Ohiro》(共44首)等。这种创作方式使得一首首短歌形成内在的结构关联,极大地拓展了短歌的广度和深度。日前,斋藤茂吉的短歌集《心寂犹似远山火》由雅众文化译介出版,精选茂吉不同创作时期的代表作300余首。
前次为认识诗种,短歌,日本和歌的一种诗体,且和歌中多为短歌诗体,因此后世每当提起和歌时则多指的是短歌。短歌之于日本,我认为,正如古诗词之于中国,已成为日本文化中不可忽视的一部分,且生命力经久不衰。当我读起《心寂犹似远山火》里的短歌,有一词语由心而生,即 “一歌一会”。
品尝对于作家创作的成果即作品,在读者方面能动地玩味其写作活动的过程,这就是作品欣赏。就如品尝食物那样,将食物放入口中,细细咀嚼,放在舌头上,仔细品味食物的各种味道。欣赏文学作品与此并无区别。面对一部作品重要的是首先深入作品,用自己的牙齿细细地咀嚼,用自己的舌头品味。有些人听了别人品尝结果的报告,便觉得像亲自品尝过一样。认为那作品就是那个味道,然而这不是真正的品尝。就如同仅仅听说牛肉营养价值很高,并不能变成自己自身的营养一样,不管听了别人多少欣赏的语言,都不能使自己的感性受到磨练,也不能丰富自己的人生体验。不吃牛肉就不会知道牛肉的味道和营养价值。同样,文学作品也必须亲自去品尝。就如同仅仅听说牛肉营养价值很高,并不能变成自己自身的营养一样,不管听了别人多少欣赏的语言,都不能使自己的感性受到磨练,也不能丰富自己的人生体验。不吃牛肉就不会知道牛肉的味道和营养价值。同样,文学作品也必须亲自去品尝。有的人一接触作品就以高深莫测或者过于复杂为理由半途而废,将其抛在一边。优秀作品虽然并非都难懂,但其精华之处也非轻而易举就能吃透的。要在耐心地反复玩味,不断捉摸中逐步理解它的妙处,半途而废是没有收获的。一定要晓得作品欣赏是一种锻炼,通过这种锻炼,欣赏能力才能提高。
《心寂犹似远山火》读后感(四):短歌中的诗意,是这个时代的奢侈品
日语中有一词语“いちごいちえ”,由日本茶道中发展而来的一个词语,常译作“一期一会”。短歌,日本和歌的一种诗体,且和歌中多为短歌诗体,因此后世每当提起和歌时则多指的是短歌。短歌之于日本,我认为,正如古诗词之于中国,已成为日本文化中不可忽视的一部分,且生命力经久不衰。当我读起《心寂犹似远山火》里的短歌,有一词语由心而生,即 “一歌一会”。
拿到书的一瞬间,和风的设计之美从封面就扑面而来,而极简之道、审美之心、风雅之感、静谧之美等自然体悟的日式美学,也同样全部凝结在短短几行的短歌之中。短歌绝不是艰深晦涩的,当你读短歌的时候,怦然入心之感是一种心中有口上无的东西,被诗人写出来了。短歌凝结了作者刹那间的生命体悟和感觉之心。短歌看似简单,小小、短短的诗章,短小却不单薄,里面藏着无数的秘密,豪迈而不草率,似大海之静谧,读完内心早已满是澎湃波澜,这或许就是日本文学的灵魂。
在书中,我最爱的篇章是Ohiro有关的三节。说到此,如果对日本文学感兴趣的话,一定听说过芥川奖,他就是以日本文坛巨匠,《罗生门》《竹林中》的作者芥川龙之介命名的奖项,高中时期的龙之介偶然一次机会读到了赤光的初版,似如一个崭新的世界出现在了年轻的龙之介眼前,他说斋藤茂吉让他对诗歌开了眼,而Ohiro就出自赤光。失恋时亦或与所爱之人分离时,“万物昏暗/我唏嘘长叹/星星在东方隐现/也黯然无光”。到了夜里依旧在想她时,“熄了电灯/夜黑茫茫——/君远在何方”。孤单单漫步到了浅草寺,“买了浅草的煮鸡蛋/一路回家/寂寞弥漫”,鸡蛋变得更加无味。就算是去上班也打不起精神来,“今天也/坐上火车出勤/遥想着远方/那悲伤的人”,而当我们失恋伤心,不过只能诉一句“苦”。
在这个事事都在计算时间成本,事事都求高速运转的时代,我们似乎读一首短歌的时间都没有,更何况追求那诗意的生活。那我们为什么还要谈论短歌的作品带来的诗意?主要因为她似“奢侈品”,主要因为她的“非必需性”。从某种意义上说,短歌、诗歌、古词等能为我们带来心灵上的慰藉,让我们能享受诗意的生活才是这个时代最大的奢侈品。因为奢侈品的最大特点不是贵,而是稀少。如果仅以数量论,千百年来保留下来的精品诗歌、短歌仅仅靠的就是爱她的人们口口传唱,就保有量看远比豪车、豪宅、钻石珠宝等这些称得上是奢侈品。“奢侈品”是一种超出人们生存与发展需要范围的,具有独特、稀缺、珍奇等特点的消费品,因此奢侈品是非必需性的,没有奢侈品照样生活的好好的。从这个意义看,生活中的诗意真的是非常之符合,特别是所谓的生活“非必需性”,可以算是为诗意量身定制的,对生活和生存来说,诗意几乎一无用处。开门七件事柴米油盐酱醋茶,与诗意毫不相干,吃穿住行,与诗意无关,生活没有诗意的人,看起来依旧活得活蹦乱跳。套用诺贝尔文学奖作家莫言的话说:诗歌最大的用处,或许正在于她的“一无用处”。可以想象,如果我们真的不再谈论诗歌,如果诗歌真的就此灭绝,会如何?是的,诗歌是理性沟通以外的一种重要的语言,是灵性的对话,是跨越时空的理解与体悟。因为有诗歌,丰富会在诗作里加浓,而匮乏会在诗作里稀释,在平静中激起波澜,将平淡日常升华添彩。
说了这么多,可能依旧是无法切实的说出,什么是短歌之乐、诗意之趣,那么我来说一个你一定知道的人物,动漫作品《樱桃小丸子》中丸子的爷爷樱友藏老先生,如果你看过这部动漫作品,一定能感受到樱友藏老先生在生活中,利用短歌俳句来记录生活的点滴乐趣之美好……
只要有明天就充满了光明希望,友藏,希望的短诗。
春天的天空,连水珠都动身远游去了。
孙女泡的茶点滴美味在心头,让我潸然泪下。
高晓松说的,生活不止眼前的苟且,还有远方的诗歌和田野。
《心寂犹似远山火》读后感(五):茫茫心海里,孤帆谁与同——茂吉和他的短歌
一
短歌是日本和歌一种诗体,是由三十一音节组成的定型歌体,格式为“五七五七七”的排列顺序。在奈良时代,该诗体相对于长歌其称作短歌,平安时代以后,相对于汉诗其称作和歌,从明治时代后半至现在,相对于新体诗其又被称作短歌。日本除短歌外尚有更短的俳句,它保留了连歌上之句的“五七五”的十七音节格式。
短歌始于公元六七世纪,根据日本现存最早诗集《万叶集》记载,第一首和歌作于公元757年。和歌是受中国古代乐府诗,特别是五言绝句和七言律诗的影响,因此出现短歌“五七五七七”的形式;即使是长歌,最后也是以“五七五七七”结尾。它以和音为基础,多用枕词、序词,声调庄重、流丽。历史上留下了许多至情至性之作,有些更是天籁之音,作为日本文学的一种独特形式在历史上留下了异常清丽的风景。
雅众已出版两本日本古典短歌集《夕颜》和《古今和歌集300》斋藤茂吉(1882—1953),正是一位在近代日本文学中成就斐然、举足轻重的歌人,被后人誉为近代歌圣。他既是诗人和作家,也是一个著名的精神科医生。
1882年,他出生于日本山形县上山市,是守谷家的第三个儿子。家中清贫,小学毕业时家里曾考虑把他送入附近的寺院学画画。
十五岁那年去了东京,作为养子来到了同乡的斋藤纪一氏家里。斋藤氏在东京浅草经营着一家私人的精神科医院。到达东京上野车站的茂吉,惊叹地发现,世上竟然有这么明亮的都市的夜晚。
1905年,他作为夫婿入籍,改名斋藤茂吉,与斋藤家的女儿辉子立下了婚约。
托腮沉思的茂吉茂吉从小喜欢和歌,但真正令他对诗歌开眼的是二十三岁时,他在东京神田的书店借阅的正冈子规(1867—1902)遗稿第一集《竹之乡歌》,惊叹感动之余,立志作歌。同年,茂吉考入东京大学医学部。
二十四岁时,茂吉加入著名歌人伊藤左千夫(1864—1913)门下。左千夫去世后,他继任主流短歌刊物《兰社》编辑,其自身歌作、歌论也多在此刊物发表。
二十七岁时,茂吉从东京大学毕业,成为医生。也是在这一年,他第一次出席了文坛巨匠森鸥外(1862—1922)组织的观潮楼歌会,结识了北原白秋、石川啄木等诗人。那是文坛群星灿烂的年代,而茂吉注定也是其中闪亮的一颗星星。
1913年,划时代的歌集——斋藤茂吉的处女歌集《赤光》出版刊行了。这本诗集在整个日本文坛引起了轰动,对日后的日本的诗坛产生了不可磨灭的影响。这年,茂吉三十一岁。
大名鼎鼎的芥川龙之介,是二十世纪前半叶的文坛巨匠。他曾写道:“高中时偶然读到初版的《赤光》歌集,一个崭新的世界在我眼前出现了……我看诗歌的眼光,并不源于其他人,而是斋藤茂吉让我对诗歌开了眼……”芥川对茂吉的推崇和友情,一以贯之,在他患病时,也时时去茂吉的医院求治。
1921年,茂吉的第二册歌集《璞玉》出版了。同年十月,他从神户登船,远赴德国留学,于1924年10月获得医学博士学位。在回国的航船上,茂吉接到养父的青山脑病医院遭火灾全烧的电报,多年搜集的书籍和资料也不幸毁于一旦。归国后,茂吉四处奔走,花一年时间重建了医院。两年后,接了养父纪一的班,担任医院院长。同年,茂吉成了短歌结社《兰社》诗刊的编辑发行人,其创作实力显露无遗。
在此之后,茂吉几十年笔耕不辍,创作短歌,写随笔、评论文章,著作等身。有日本评论家认为,以旺盛的创作力弥老不衰的,除了文豪夏目漱石外,就当数斋藤茂吉。他一生出版歌集共十七册,作歌将近一万八千首。与此同时,茂吉终其一生是个职业的精神科医生。他总是说,自己是个医生,作歌不过是个副业。茂吉和辉子育有二男二女。有意思的是,两个儿子后来百分之百地子承父业,都成了作家,也同时都是职业的精神科医生。他的小儿子、作家北杜夫(斋藤宗吉)曾一针见血地指出,在父亲心中,九成都被诗歌所占据,专心专念的,都是文学
北杜夫(1927—2011),日本作家、精神科医生。1960年以《在夜与雾的角落》获第43届芥川龙之介奖;1998年以《斋藤茂吉传》获大佛次郎奖。作为一位多产的作家,他的作品风格多变,深受年轻读者追捧。二
年轻时的茂吉受到西方美术、哲学,尤其是尼采思想的深刻影响,将《万叶集》歌风以及西方文化都化为其短歌的血肉。
他于1913年出版了歌集《赤光》,将日本的传统思想与欧洲现代精神融合在一起,充满对生命的肯定和对人的感情的珍爱,在质朴明朗的青春活力中,透现出哀愁孤独的心情,富有想象力和表现力,成了近代短歌的高峰之作。
后来,他经过一段官能上具有艳丽色彩的时期,茂吉逐渐进入到沉静孤寂的现实境界。在他心目中,短歌,必须表述鲜活的生命,描写和透视出自然和生命之间的深层联结,从而进入“实相观入”的境地。围绕着源于正冈子规的“写生”之说,在茂吉的眼里和手上,短歌创作最终发展形成了“自我的生与自然浑然一体”的文学表现之路。
从某种角度来看,茂吉的文学是大器晚成,逐渐走向成熟的。处女歌集《赤光》刊行时,他已经三十一岁。第二本歌集《璞玉》于1921年出版,茂吉时年三十九岁。《赤光》的出版在当时引起了轰动,从学生、知识分子到平民阶层,无不一读为快。究其所以然,是其表现的内容和手法,令人耳目一新,把有着悠久传统的短歌创作带入了崭新的境地。
茂吉闪耀近代诗坛的代表处女作《赤光》他写了去海边的新鲜感觉。茂吉是在山里长大的孩子,小时候没见过海。当他第一次见到海,海风的气味、缤纷的贝壳,都给他带来了新鲜的体验。他写出了和自然一体的喜悦和跳动的心情,以及活泼鲜活的生命。
他写了在冬天的深山里劳作的伐木工人。在严酷的生存环境中,人们身上透现出来的不仅有生命的顽强,还有源源不断的生命能量。皑皑白雪里,令人看到了强劲的希望。
他写了和母亲的死别,也写了和恋人的生别。以短歌的体裁,运用情景交融的写生手法,竭尽一身的情感之力,茂吉写下了人间的生老病死、自然的四季流转。
茂吉是从山里走出来的,他一辈子待得最舒心的也许还是在故乡山形县的山里。尽管他站在科学和文学的前沿,但他的精神故乡,常常是在故乡的泥土里,在“藏王山”山谷中,在“最上川”河流上。据说他常常说带着浓厚乡音的日语,而且可能是故意而为之。在他游学欧洲时,当地日本领馆的办事人员回忆说“从没听到过这么浓重的东北口音”,茂吉的乡土情结可见一斑。这种内在的乡愁,在他原生的诗歌生命里,定然是难以枯竭的力量源泉。
北杜夫曾断言,尽管《赤光》《璞玉》是他父亲的杰作,但在他去世四年前刊行的歌集《白山》,才是他的巅峰之作。如果说《赤光》的关键词是崭新,《璞玉》的是清新,那么,茂吉的晚年之作《白山》,可以说是他炉火纯青的绝唱。
茂吉家乡 山形县位于山形县的斋藤茂吉纪念馆三
茂吉的短歌作品里,有很多是“连作”。所谓连作,即是组诗的形式。短歌的连作,起自正冈子规;而子规的弟子、茂吉的师父伊藤左千夫,则是首次将其系统化提出来的歌人。斋藤茂吉在此基础上,善用连作来赋予表达主题的整体感,把短歌连作发展成具有内在结构关联、整体一气呵成的组诗。联想起短歌(和歌)的源流是中国古代的乐府诗一说,似乎觉得连作于短歌的发展历程来说显得理所当然;但实际上,短歌回归这一源流,时间上已经越过了千年。
连作的成功运用,直接扩展了短歌的表现宽度和深度,使得短歌这一文学形式成了近代日本文学的一大基石。一首首短歌在捕捉一个个瞬间,并使其定格的同时,连作的内在联系串联起来形成了一幕幕的故事画面,在主题的明确表达背后,奏响了一个缓慢而强力的副旋律。茂吉的短歌作品里,最具此故事渲染力的当属《赤光》里的“离世的母亲”连作五十九首,以及“Ohiro”连作四十四首,令人读来动容,印象深刻。
评论家吉本隆明(名作家吉本芭娜娜的父亲)对茂吉的歌作研究颇多,对茂吉赞誉有加,认为他是把日本短歌传统和系列化歌风集于一身的大诗人。而且,因为长寿(那个年代的诗人多数短命),茂吉的创作腕力数十年敏锐不减,其风格从紧迫到沉静,得以完全成熟并充分展现。
与其他歌人相比起来,茂吉作品里的一个显著特点是声调/曲调的高度运用。所谓曲调,其实就是诗歌内在的韵律、节奏乃至旋律。用汉语来类比,就类似宋词词牌里的长短句、平仄韵、入声去声等。必须指出,但凡诗歌,首先是语言和原声的表达,韵律会如影随影地嵌套其中。而韵律本身,是文字和意象表现之上的弦外之音,往往敏锐于耳。不论是哪种语言,音乐式的美感来源于合适的韵律和音步,以及诗句流转本身带来的节奏感,或延绵不绝,或变幻明灭。茂吉的歌作,正属此道上流。
除了曲调以外,茂吉作品的另一个特点是色彩浓烈。在万叶时代,传统的短歌舒缓展现,有“写生”的朴实无华,也有与之相应的心理描写;而在短歌和文学的近代化过程中,以茂吉为代表,引入并实践的是“感觉”的描写,把作者的感官、感觉驱使到表达的最前线,为短歌带来强力的色彩感,迎来并进入一个彩色写生的近代。斋藤茂吉正是短歌近代化的一个主要的领军人物。
近代短歌的另外一个著名诗人土屋文明,曾和茂吉在短歌结社“兰社”里相识共事多年。他对茂吉有一个入骨三分的评论:“如果他没有师从伊藤左千夫,而去参加新诗阵营的话,他的天分更是能有超越一百分的发挥。”这句话,从他们长年的交往来看,自然分量很重。茂吉在短歌领域里的创新,使短歌这一文学形式能与时俱进,充分赋予并展示了其真正的近代性,使其得以成为近代日本文学里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四
茂吉在茫茫世间,一己肉身在现世和隔世中徘徊,遍尝着孤独。这孤独孕育着诗人的心灵,化成他笔下充满感情而富有张力的诗句,犹如一叶孤帆,驶向人生的海洋,其中有漫长的孤独,有与波涛的决绝,也有对梦想的坚持。
即便是在青春绽放的岁月里,茂吉仍然是孤独的。他从乡下来到东京,寄居于养父家里。在海边,他吟道:
漂流上岸的海藻像极了陆奥家乡的春草一样的哀愁大学毕业后,茂吉来到长崎当医生,在这个偏远的海港,写着他无形的孤独:
早饭升腾起白色的饭气我想,这是静静的港湾的颜色母亲死别时,在病榻旁,他诉说着揪心的孤寂:
终宵床边寐慈母濒死期 夜静蛙声远似闻天上来而与恋人的生别,茂吉也陷入深深的离愁和寂寞中:
心寂犹似远山火君别去几多愁日渐衰老之时,茂吉品尝着战争后,山河破旧的孤独:
雪化成了水滴溶入夜色在拂晓万物无声在茂吉众多的代表作中,最为世人所知的作品,当数他描写母亲死去的情景的一首:
红颈燕两只梁上立慈母死感觉敏锐的茂吉,在这揪心的一刻,他注意到燕颈的红色;而这对雌雄燕子立在屋梁上,似含有佛教的临终使者的意象。两只象征性的小鸟,让临终的悲哀充满了庄严的孤独,令人怎不慨叹生命的慈悲和无常。
茂吉这首《红颈燕》因被选入日本教科书中而为人熟知。茫茫心海里,孤帆谁与同。令人欣慰的是,在这个世界的某一角落,若有人能倾听并理解你的孤独,那么,孤独也将消逝无痕。我们徜徉在茂吉的文学世界里,似乎读懂了诗人的心声。
译者
高海阳
2019年12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