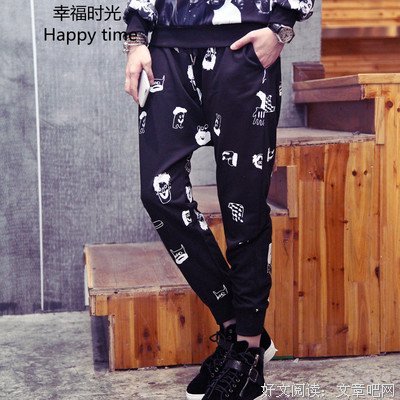
本乡的初中距离我们家很近,只有3里路。那时,自行车还是一种比较稀缺的交通工具,一般人家一家人才有一辆。我们家也有一辆大金鹿,但我在家中排行老小,很多时候是轮不到我来骑的。春夏秋冬,不管烈日暴雨还是寒风大雪,我每天都是早晨、上午、下午至少三个来回。冬春季节,还要上晚自习,就要一天四个来回,八趟下来,就是二十多里路。每趟最快也要用二十分钟的时间,这样一天下来,仅花在路上的时间就将近三个小时。当然,步行上学的不止我一个,我们村与我一样的初中生也大都是步行的。每天放学,我和小伙伴们成群结队地往家走。一路上我们说说笑笑,不知不觉也就到了家。到了家是容不得片刻耽误的,特别是早饭和晚饭,否则,就要迟到了。母亲知道我上学时间紧,也就早早地把饭做好,盛在碗里,冷到正好吃的程度。只要我一迈进家门,就狼吞虎咽一番,接着把碗一把推给母亲,抹抹嘴就匆匆走出了家门。
每次,往往是我前脚刚走进校门,后脚预备铃也就响了。这样,学习时间也就只剩下了课堂。然而,我当时也并没有觉得怎么紧张,反而感觉学习是一件很轻松的事情。那时候,书包不重,除了课本,各科还有一本同步训练。上面的练习做与不做是全靠自觉的,老师一般不检查。作业也不多,除了主科作业外,其余副科是没有任何作业的。就是主科作业,数量也绝对不多,我们语文除了每两星期才做一次的作文外,基本上没有任何书面作业。自然,那时也就没有听说过“减负”这个名词。不像现在我的学生,只语文作业本就三四个,作文本、作业本、日记本还有摘抄本,“四座大山”压得学生喘不过气来。虽然,我是语文老师,但是,我也是“人在江湖,身不由己”。考试是有的,每学期一次。试卷发不发我是没有什么印象了,反正是老师不当众念成绩,也不把成绩张贴在教室里,更不按成绩来决定学生的座位,自觉不自觉地真正做到了对学生成绩严格保密。相比之下,我们现在对学生成绩的重视程度早已今非昔比,学生早已不叫“学生”,而应该叫“考生”了。张贴成绩早已成为学校不成文的潜规则,按照成绩来选座位自然也是常有之事。据说,这是鼓励先进、激励后进最为有效的办法。
初中毕业那年,学校还分中专指标。我想考中专,路近,上了中专就可以端上“铁饭碗”了。参加了学校组织的中专预选,没选上,也只好报考高中了。填报志愿时,班主任孙老师见我报了一中,忙说,还是明年准备考中专吧。我无语。
高中虽说是在县城,但那时的县城也不比我们乡下好到哪里去。整个县城只有一条窄窄的马路,两边还都是简陋的平房。何况,我们的学校只是在县城的边上,四周是一眼望不到边的庄稼地。高中的生活自然是比我们初中紧张了许多。每天除了吃饭、睡觉,就是学习,有时就连做梦还在上课呢,好在还有一个完整的星期天,我们可以自由支配。作业也较初中多了起来,除作业本外,还有一项重要的作业就是试卷。以前在初中视若山珍海味的油印试卷,在这里几乎成了家常便饭,几乎可以天天见到。一学期下来,各科试卷放在一起,厚厚的一摞,很是壮观。考试也多了,除了每学期两次的期中期末大考外,还有各任课老师平时的小考,但对考试成绩老师似乎抓得不是很紧。三年中,我经历了大考小考无数,却很少见到自己的考试成绩,就连自己考入高中的成绩也不知道,不是我不想知道,而是没人告诉我。高中三年,关于成绩的记忆,只有一次,还是最后的高考,我考了502分。
那一年,我一举考上我们家乡小城的一所师范专科学校。
蓦然回首,我把记忆的长镜头拉长,探过去,还依稀窥得见来时的脚印,或深或浅,或清晰或模糊。我知道我所走过的乡村教育之路虽打上了深深的时代烙印,但更多的是属于我个人的、心灵的一些东西。回忆过去,不仅仅是一种怀念,更是一种反观。在今昔对比中,也许,能使我们今天在轰轰烈烈的素质教育改革中少一份狂热,多一份冷静;少一份盲从,多一份理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