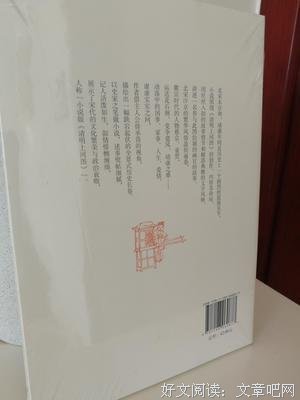
《汴京残梦》是一本由[美] 黄仁宇著作,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的2018-4-1图书,本书定价:42.00元,页数:,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三星半。从语焉不详的几条历史记录开脑洞的小说。从这个角度说写得并不算好看。
●读得我好难受。。。
●没想到“梦”这个字的落点居然在这里。 一开始看到徐对柔福动情,还是有点惋惜的。 再一想来,可能是平时看惯了一味的科普,看到情爱居然无端觉得多余了起来。 如果没有结尾的OE和这段情,这个故事也一定会缺点什么吧。
●在十分熟悉的大背景下,我看到了自己完全不熟悉的新人物,并为之揪心不已。
●2019·080: 记得在《本源》中看丹·布朗评价高迪,惊讶其对建筑艺术品鉴能力之高。黄仁宇先生将《清明上河图》联想出一段完整的人生来,无论爱情故事写得多么不尽如人意,我总之是佩服,尤其是作画部分还是精彩,黄先生是懂画之人。
●第一次读老先生的书竟然是他的小说。一个画为起,国为中的故事,人的命运跌转起伏,世事弄人。
●清明上河图同人文,书中插画为作者所画。这还是史学大家黄仁宇么?敬仰之情犹如滔滔江水,大神大神!
●想起了城市史课上说的“画中的秩序“,很有意思。(每次看黄仁宇的书总是要后知后觉的从后记里发现作者的深意)
●在看"宋徽宗"时忽然想起好像还看过这本书
《汴京残梦》读后感(一):管中窥豹
从万历十五年开始初识黄仁宇,印象里他的历史写法是从重要的历史人物出发,解读重要的历史进程,演绎出一番历史观念。感佩于作者大名,遂拜读了他的历史小说。
不得不说汴京残梦的笔法很细腻,从语言到情节,都尽量的做到还原与真实,刚翻本书时,但觉生涩拗口,不过随着故事的发展,理解起来也相对容易了一些,只是其中很多历史事件与历史词语也是初次相识,读起来确实艰涩不易。
大概的故事情节还是易懂的,一出才子佳人的悲情剧目,一幅山河破碎的历史画卷。但更吸引我的是书中对清明上河图的解读,从最初精妙绝伦的画面的时空设计,到三道屏风法的纵深画法,十字街头的倒“之”字绘制,以及一些人物故事背后的绘画技巧,让我对清明上河图更加敬畏,原只觉得这幅画好看生动,了解了它背后的一些绘法后,更觉此画珍贵难得。
可是让我处于云里雾里的也是本书的故事,是历史抑或是虚构,读的过程中不自觉的有一丝荒诞之感。作者从看似平静祥和的世道中慢慢道出背后潜藏的巨大危机,继而引发的山河破碎中,写出了爱情的悲欢离合。总而言之,历史学家还是历史更好看些,这些爱情故事还是小说家们写的更缠绵悱恻吧……
《汴京残梦》读后感(二):拐角看到黄仁宇的好
最早在大学接触黄先生的文章,对他提出明代中国人过于重视道德一点,印象颇深。工作后粗略读过《中国大历史》,本是冲着先生的大历史观去的,翻开却发现如此庞大的书名背后,却仅20万字左右,极薄,细处新见迭出,总体却像极了本科通史讲义,还是给西方学生普及历史的那种,中国历史专业学生读之,则不免有不够学术之感。故当时读此书我虽作了很多笔记,却并未有读来酣畅淋漓的快感。作为历史专业学生的我,不自觉地在此书中找全新的研究视角、极具证据力的史料、绵密严谨地推理论证⋯⋯希望却都一一落空。后来读《万历十五年》依然如此,再后来就有了人民的名义,大家仿佛都在读先生。而黄仁宇三个字,于我则彻彻底底成为一个抽象的大名鼎鼎如雷贯耳的符号。我敬他尊重他,但实际并不能具体说出他的好。后来我慢慢明白,自己读先生之书所抱着的希望,是历史专业训练的结果,很有些过于学术。而先生的研究方法,则与一般学术研究范式不同,这也是他虽受大众热捧,但一直不见容于美国乃至我国的学术界之重要原因。
换个角度,才能真正欣赏先生之书。所以我倒觉得最能体现先生历史书写方式之美的,倒并非那些颇有争议的中国大历史万历十五年。这些话题过于严肃过于政治,以不甚细究的方式书写,自然会有议论。《汴京残梦》这样的历史小说便不同了,它不着意研究深刻宏大的历史命题(或曰政治命题),但举凡崇宁新政 党锢之祸 官僚体制 金人入侵 靖康之变的政治命题皆有所涉猎作为宏大背景;同时又不忽略政治史之外历史的多样呈现:造船业间的师徒传承,北宋末年透视法绘画的细致呈现,开封府的地理位置、人口数量及构成,宋词的审美与青楼之间的关系,北宋末年流行歌曲、美食及服饰,底层士人和士兵的工作生活困惑,底层百姓生活⋯⋯这些才是更大意义上的历史呀。何况我们还能顺便跟着主人公谈一场底层书生和受宠公主的恋爱。什么证据力逻辑论证研究范式,完全可以弃之不顾,也完全不会有人因之置喙。
自然,我们也不必深究书中徐承茵和柔福帝姬之间爱情来得太突然,不必在意叙事方式西方化与否、起承转合巧妙否、人物心理描绘细致否……因为作者要读者关注的,读者自身更在意的,不是小说,而是这历史的呈现。本书所呈现的作者并不深怀家国历史之忧,只认真讲一个故事,呈现一段历史,有如史景迁般的单纯,如是而已。作为读者,跟着作者穿越一回大宋,发出一声叹息,足矣。
《汴京残梦》读后感(三):汴京残梦,梦里残章。
《汴京残梦》
楔子部:
——你写的是小说,还是历史?
——历史小说。
——这就是了,究竟还是小说。小说者fiction也。Fiction者,寓言也。
历史只注重事实何以如是展开……历史小说虽不离现实,,但是要兼顾应否如是展开,是否另有门径。因此务必迎合读者心理……
——那么我这文稿,你以为是话本的,应如何处理?
——放弃它,一切重来。
首先,黄仁宇先生终究在此本97年出版的历史小说中认知到历史与文学的创作差异,敢于自我否定历史化的文学真实性,避免历史导袭窠臼,突破历史纲要和文学小说在史实真实性的二元差异,从敢为己先的角度看,无论这本文学性的历史小说作品创作水平如何,都足以钦羡黄先生气魄。
其次,敢于放弃,敢于重来。如覆倾之际的大宋王朝,尽管历史最终也没有给大宋重来的机会,但是笔者敢于向历史作主观性判断的第二次选择,或许也给我们再看历史又一视角。
主文部:
先为徐成恩,后为徐成因,终为徐成茵的徐同志堪称北宋间文人倾向典型化的缩影,与李功敏等皆不遇适时,更换法度,废科举,由学校,面对新法旧法不免有被左右为难之势。
1)苏子的“有罚有不罚”、“有赏有不赏”,正与所谓“标准”的政治化、文学化、艺术化等问题相适应。正由于无法对“标准”统一与模糊倾向有所确立,历史才会让时间和实践告诉当事人和后代人所谓“答案”的终极标准。
2)政治与艺术相通,文学的真实性与审美性,人文性与工具性讨论久已有之。政治的问题模糊性终究比文学的模凌两可可怕。
3)小徐同志和柔福帝姬的爱恨纠葛,不是黄先生写作强项,不惊心动魄也不爱得深沉,历史和政治限制太多,引用白居易的诗歌不能说是恰到好处,有点缺乏心向往之的才子佳人气质,先生可能诗学研究正多,是不当来点诗艺科普,也是可爱。
装帧: 满分; 书名满分;黄先生怀抄小画模拟《清明上河图》部也可谓亮点,上图为敬。
《汴京残梦》读后感(四):繁华万千,黄粱一梦
原本是想入手黄仁宇先生的《万历十五年》,偶然间看到这本,就忍不住一起入手了,因为封面设计得太有意境了,尤其是以瘦金体书就的“汴京残梦”四个字!
北宋汴京的繁华,从《清明上河图》中便可窥见一斑。这本书便是以《清明上河图》的绘制为线索,从画学谕徐承茵的视角,描写从宣和五年到靖康二年世事沧桑巨变,繁华盛世,转首间不过黄粱一梦。
汴河滔滔,清明不再。历史长河奔腾不息,不论是徐承茵还是柔福帝姬,都只不过是江水中的细小沙砾罢了,纵然缱绻情深,怎奈何福薄缘浅?
他可以纵观五年之前还没有和心爱之人邂逅时的情景,要不是沉湎着现今是靖康二年,或者什么建炎元年。让它倒退回去,只说于今又是宣和五年吧。
这是第一章,是故事的开始,却也是故事的终结。
徐承茵初到汴京,本是为着参加科考,以求功名。然而由于新政“废科举,兴学校”,徐承茵阴差阳错入了画学。然塞翁失马,焉知非福。入画学使得徐承茵与《清明上河图》结下了不解之缘,更是因此得遇心爱之人。作者通过制图过程中的波折,将北宋末年的文化繁荣与政治衰败娓娓道来,所谓见微知著。
全书二十一章,最得我心的要数第十四章,也就是图成之后,张择端评图的那章,当中对《清明上河图》许多细微之处,进行了细致地品评。此处列举一处:
对于画中多次出现的一些闹市纷争的场景,张择端如是作注:
“这些地方都表示小人不闻君子之大道的结果。也是他们未体会到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意义。以小喻大,我们也可以看出一切争端的始点……虽说君子要忠厚,不为已甚,我们也不能对这些欲生乱阶的情形全部置之不闻不问。你(徐承茵)熟读《左传》,就知道小不忍则乱大谋。我的办法是在这一尺横宽的范围内将一切纠纷的地点细处重复地画出,便以后阅图之人不能忽视我张择端奉着圣旨广为规劝的意思。”
可见,作者眼里的张瀚林是个入世极深的人,作图是亦想着规劝天子,告诫后世,胸中丘壑,笔底波澜,可谓君子。其实作者读者都清楚,这些话都是黄仁宇先生对《清明上河图》所做的注解,不过是借张择端之口说出来而已。可是,叫人稍感遗憾的是,不知道张瀚林构思作图时是否真怀着这样的初衷,还是说只不过是后人解读?我当然更愿意相信是前者,若是信了后者,那这幅图不过是一副死物,正是前者才让它流传近千年而灵魂不死。
只是这样想着,不免有些伤感,历经千年留传下来的诗书字画浩如烟海,未必每一件都有如此幸运。若是作者笔下乾坤为人所不查,或者是被误读,岂非抱憾终天?不论如何总是不得圆满。不如换个角度,或许这样的缺憾也成全了它的美,正是因为这留白,才有后人无尽的遐想。
至此,我实在是渴望能够一览《清明上河图》的真容,只是难得展出,如果有机会,一定要亲眼看看!现在,只好努力回想去年暑假在开封博物馆看过的《清明上河图》摹本,可是却发现只在脑海中留有大概的印象,细节之处无甚印象了,只深恨自己当时未曾读过这本书!
还有不得不提的就是徐承茵与福柔帝姬的感情线了。这里必须摘录承茵回忆他与福柔相知相爱的一段文字:
『难道绿窗新语,烟雨传奇,你读“‘见关’莺语花底滑”,我读“‘瞰关’莺语花底滑”还不令人寻味?谁不知道“瞰”即是“见”,而且句中也带着芳馥的气味?他们之间还有“紫径撷英”如此离奇之事端?又有“苏堤对岸人畔柳”水中看去的倒装法?再随着“九嶷山里深处,洞庭湖岸近旁”的两地相思,这不全是古今带着流风遗韵的人物也难能遭遇的机缘吗?
可是至此看出:“此情可待成追忆”,一切都已既往。今生无望已是大势所趋了。他一生只见过她三次,这第三次,很可能为最后一次。他为什么要在道别时说出“天上人间会相见”的不吉祥语?可能此句已成谶语,他还害怕金人还要将她派嫁番王。这时候救护不得,自己卧在荒郊,坐骑待毙……』
这样的爱情实在是太浪漫了,说是附庸风雅也罢,但在我心里这才是真正的浪漫悲歌,“虽不能至,然心向往之”。但是第十章末(是二人第二次见面),我个人认为实在是太过仓促,有些难以接受,稍显突兀。可能作者毕竟还是一个历史学家吧,在人物刻画和情感描写上不尽如人意。
历史小说,虽是小说,但终究脱离不了历史,或者说历史才是真正的内核。作者通过细腻清新的文字展现了北宋末期汴京一片繁华景象,但终归积弊日久,已成沉疴,此时的北宋不过是强弩之末罢了。作者给徐之同乡陆澹园安排了一个审计官的身份,借他的口揭露了北宋冗军冗费,官员腐败,早已是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再是变法也难动根本。又有李功敏因言获罪,庙堂之上有人翻云覆雨,只手遮天。建艮岳,修雁池,还有花石纲之事,如此种种,北宋倾覆早已成定局。
只是北宋倾覆之后又当如何?帝王贵胄尽数被金人虏至北地,柔福帝姬的结局从“靖康”二字出现便可预见,而她和承茵的情缘也随着纷飞的战火湮灭在无情的历史长河之中。
在动荡的时代,《清明上河图》的命运也并无不同,只能是随着泱泱大潮赴往未知之途。
《汴京残梦》读后感(五):频年踯躅 皆成梦幻
这是一篇规规矩矩的书评,给黄仁宇先生的历史小说《汴京残梦》
历史学家果真是天生的小说家,那小说之荒诞离奇,哪里敌得过千百年来人之言行。
画中尚是一派“八荒争凑,万国咸通”,转眼间画外便已经“山河破碎风飘絮,身世浮沉雨打萍”
宋末靖康前后,恰是应了一句“兴也勃焉 亡也忽焉”
一时笔兴笔落,便是“频年踯躅成梦幻,几度驰驱付尘烟”——
所谓“残梦”者,无头无尾,若是明遗民张岱先生将《陶庵梦忆》一卷写成自传体,也不过如此吧……
已识乾坤大 犹怜草木青
黄仁宇先生的史观,落笔总是宏阔,上来便是“万历十五年,四海升平,无甚大事可叙”“张择端为我书制图”,乍一眼看去颇有些古时楚狂歌而过孔子之感。
便是以细腻情节与描写取胜的小说,亦难逃史家气息。
儿时读历史,自是颇重一家之言,因而每每遇到北宋新旧党争,便困顿头疼——科普类通史对于王安石新法多有赞誉,大加渲染“三冗”之弊;而林语堂先生《苏东坡传》则是逢新法必反,凡新党皆是趋炎附势之辈;新旧党魁王安石与司马光两人均是传统意义上的“正面人物”,写得一手漂亮文章,为国为民无可非议——最终只能勉强解释为激进与保守固有之争,而王荆公又缺识人之明,小人借机上位终至靖康乱象。而东坡先生置身新旧两党之间,自是郁郁而不得志,实乃时局所迫。
而黄先生显然不屑于单纯在学界的争议中多添一笔,他不过借主人公徐承茵在后王安石时代的经历,借坊间漫谈、借太学生清议隐隐点出史观些许——
“百官自是百官,大家总免不了胸中利害”,即便是“你将一些人贬官,甚至流放,称之为奸党邪党,他们仍然官官相护,留下的‘正人君子’内亦是如此”。而“哪一派哪一党得了皇上信任,占了优势对方总感到威胁,他们总要提出一个相反的名目,或者是一个对立的方案”,因而“王安石一派重功利,不含糊马虎;苏东坡、司马光等人就主张一切大而化之,雍容为一切之根本”。此番无谓的矛盾与对立不断升级,以至不到你死我活再无解:“又是熙丰小人,又是元佑正人;只是不久奸党成为了君子,君子又成为了小人”,甚至延伸至天象与书画,“既有太白星于昼间出现,前任画正之锱铢必较;则有日当食而无亏,新来主持的浑然无是非曲直”。
于是到最后“像方田法、免役法,本身都不失为善政,可是经过党派的争执,总是做得不是太过,就是不及”,说到底便是“你要朝此方向进展我偏不合作,必定要拖垮你为止”的屁股决定脑袋之争。
更何况于“如是国家有任何兴革总是上有钦差,下有采办,他们才是权力最大、获利最大。“
这何止是论及新旧党争,简直是针对现代代议制民主弊病的一番至论,振聋发聩。
而与此同时,又有黄先生在剧情间隙三两闲笔,兼为主人公的心理与作者的史论。从作画的笔墨浓淡,到透视法、计量学、梁山方腊之乱,再到造船工艺、南北漕运、活字印刷,如同一个真实时代的吉光片羽,隐约透出几分“八荒争凑,万国咸通”(《东京梦华录》)的盛世图景下几不可闻的杂音,自靖康年倒看来又是唏嘘。其覆盖面之广,信息量之大,又足以令做惯了史料解析题的文科生瞠目结舌。
如此比来,我所一直景仰的雨果先生在《圣母院》《悲惨世界》之中的闲笔便显得单调且局促多了——
如是见微知著,举重若轻,信手拈来又能点到为止,方见大历史学者之格局。
浪漫主义外壳下的宏阔历史
《汴京残梦》所谓残梦者,掺杂了十足的感性与幻想,终至梦醒之日破碎一地。如此壮烈的浪漫主义难得地浸润了笔调平淡的全书的两条主线:主人公徐承茵参与旷世名作《清明上河图》的画作,以及徐承茵与柔福帝姬不知何起、亦不知何终的爱情。
《清明上河图》一节贯穿始终,笔法最是传统。因一画而功成名就的张择端学士的形象亦是正派间带可爱:出身卑微而临危受命,通晓作画之法而又礼贤下士,官场上足以变通机变却能够急流勇退,如党争狂热下的朝堂一股实干的清流,似乎带了黄先生些许理想主义色彩。
而叙述又至是平淡无奇,文白相间却毫无炫技之嫌,嵌入的诗词又恰如其分,颇得明清小品之意趣,尤其是以大段文字描摹《清明上河图》的一章:
“河畔有一个收纳人点验布袋;还有一个经纪人坐在布袋上,用手划斥乞讨之人离去。这穷伧还存在觊觎之念,一心想收捡残留在地上的枣子。当中也加入一个‘打抽丰’的汉子,他索性趁着晴天在大街之上解衣扪背索蚤。一把万年伞则暂时扔放在地上。还有一个瞎眼算命人,被人牵引着过街。”文采斐然,商贾、驼工、官员、小贩、游手好闲的混混渐次登场,排挤责斥、急切疏懒,不一而足,画中时景跃然纸上,颇得张岱《西湖七月半》白描之神韵;边上还配有简笔临摹画,轻佻可爱,仿佛能从中窥及一位须发皆白的华裔老人,手握一支小笔,在光影迷离的纽约街头一面想象那个“辉煌”时代,一面一笔一画描下那些不合时宜的小人,轻拍画板再得意端详一番的情景,情势见忍不住轻笑开来……
黄先生书中自绘图与原《清明上河图》而主人公徐承茵与徽宗二十女柔福帝姬的爱情线则姗姗来迟,及至书中段二人才因帝姬扮演轿外侍女的争议一事初遇。而尾声中则记叙了此书的缘起于《宋史》中一句模糊而解释不明的“内侍自北还,又言柔福在五国城,适徐还而薨”,又给这段爱情平添几份悬疑与悲情色彩。
全书以爱情线为引,以情之跌宕喻国运艰困。本该是个爱情故事,而爱情篇幅却少之又少…
文中的爱情片段实是局促,何况两人还是贫寒举子与皇室公主的所谓“旷世奇恋”。首见面争执,次见面就从畏缩到猛地亲吻,然后除开主人公大篇幅的心理碎碎念,便就只余下那几首来回言辞晦涩的情诗了。没有辗转反侧,没有肌肤相亲,随随便便就走到了海誓山盟,无论黄先生反复强调情感是如何真切,被现代恋爱观浸润许久的读者总是不得共情。
据说黄先生是根据自己初恋的亲身经历所写的这段感情,也难怪,战乱与飘摇的时代是容不下感情的卿卿我我与矫揉造作的。
抑或是,黄先生醉翁之意不在酒,借爱情故事的外壳讲述了一个比男女情爱宏阔得多的故事——
一个“困惑而尚未绝望”的北宋末年,一段《清明上河图》粉饰背后的汴京残年,就这样在仓促的爱情当中缓缓流淌开来。仿佛一位暮年老人被问到初恋时破碎而冗长的絮叨,涵盖了太多太多情爱以外的复杂情愫。
据说黄仁宇夫妇甚是喜爱戴维·伽特森的《雪落香杉树》,甚至最终意外身死在前往观看其改编电影的途中——亦恰好证明黄先生志不在纯爱故事的庞大野心。虽然《香杉树》表面记叙了一则意外发生的悬疑“谋杀案”,并借此牵扯出初枝、伊什梅尔、天道三人交错陡转的“三角恋”故事,但显而易见,全书探讨了一个远大于此的主题,有关少数族裔的社会融入,有关人心的狭隘和偏见,有关人生的偶然性与命运,不一而足。
若是黄先生确实有意在自己熟悉擅长的领域一定程度地模仿自己喜爱的《香杉树》,那我想从各个角度来看,他都成功了——即使面对看惯了现代遥想古代的婉转缠绵小说的读者的大加鞭挞。
不过,黄先生人像的画技,实在是不敢恭维呀
(欢迎看我给《雪落香杉树》的书评:香杉树、落雪以及掩埋的记忆
黄先生书中自绘柔福帝姬与原《清明上河图》频年踯躅成梦幻
黄仁宇先生在《万历十五年》中称其书为“一个大失败的总记录”,即不论主要次要人物皆是身败名裂,没有一个功德圆满,究其原因,则“当日的制度已至山穷水尽,上至天子下至庶民,无不成为制度的牺牲品”。
此亦是《汴京残梦》一书的最佳注脚——
即便是后世著名的昏君“番番”徽宗赵佶也不免哀叹“为君难”,奸相蔡京在文中亦是多受尊敬,其所提“丰亨豫大”颇有公共投资大兴基建以兴流通的现代经济的影子;而传统的正派人物,临危受命而挽狂澜于既倒的太常少卿李纲在或战或和的大政决策间如履薄冰,却终究报国无门;才华横溢而被提拔负责《清明上河图》画作的翰林学士张择端颇有些艺术家天真而偏执的孩童习性,却连领赏归乡的微薄愿望也未能实现。
王安石、司马光、蔡京,宋江、方腊、辽国,你方唱罢我登台,整一幕大戏分明在文中金人机械降神般挣逃不出的黑暗中落下帷幕。李功敏受牵连,陆澹园兵败,楼花月自尽,徐苏青离婚又复婚,柔福帝姬被掳不知所踪……
即便主人公徐承茵一改优柔寡断的性子,一骑北向为红颜,也无丝毫亮色。
就像承茵在江西愤懑吟诵的诗句:“频年踯躅成梦幻,几度驰驱付尘烟”。人人身居其位,却又都如徐承茵一般跌跌撞撞,身心俱疲而无能为力。
其间不知多少困顿悲苦,多少命运纠葛,覆巢之下安有完卵,人不过是大河里飘荡的浮萍,偶然翻上水面,偶尔又跌入河底,身不由己,任其推搡。
文中论及命运时感叹“可知红颜薄命,千古皆然”。可在如此时代下,薄命的又何止是红颜……
居于如此粉饰太平时代的局中人,自是进退失据。居庙堂之高,处江湖之远,无人得以幸免。
结果不可避免——
靖康之耻,山河破碎;旧识隔绝,名画蒙尘,爱人不知所踪……
及至结尾,惶惶然间戛然而止。
而后承接到原先还觉不知所谓的首章,句句泣血,待到最后叹一句:“不要沉湎于现今是什么靖康二年,或者什么建炎元年。让它倒推回去,只说于今又是宣和五年吧…”
方觉恰好接上一句“都云作者痴,谁解其中味?”
话说《红楼》如此说来亦不过是家族破落,安得如是“寻寻觅觅,冷冷清清,凄凄惨惨戚戚”之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