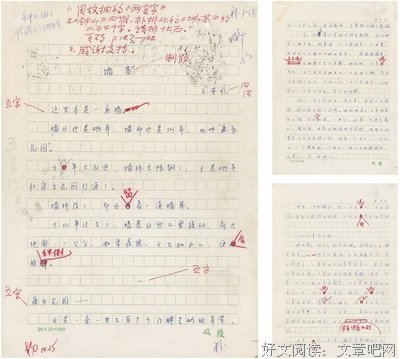●鸟从天上落到地下,其实全是因为彷徨。彷徨消耗了它们的体力和信心,还有希望。飞得越高就越危险。 ----王安忆《长恨歌》
●女人的诡计全是从爱出发,越是挚爱,越是诡计多端。 ----王安忆《长恨歌》
●世界变成一条无边无岸的河,没有来路,没有去路,人在其中就不是漂,而是浮。 ----王安忆《众声喧哗》
●花好月好,长聚不散。 ----王安忆《长恨歌》
●这短篇小说的小世界,是独立的,却一定不是孤立的。这也是小说的最重要的物质之一,那就是他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也不是从石头缝里蹦出来的,它一定与我们的人生有关。这是小说的“入世”性质,它不是虚无的产物,这是因它的现实材料所决定的。无论你如何予它翻唱的面目,他始终是人间的心。要说小说是艺术中最俗的一门,所以,他也是最容易被人们忽视其独立性的一门。这两者之间的关系,是可穷我们一生去了解与发现的。而在这里,在短篇小说里,大约是更加显得尖锐和极端,因为短篇小说的体积会使它具有较大的封闭性,就好像一些笔记小说,或预言式小说,写一点雅趣的哲理,说是提炼出来的,提炼出的也是金丹,没有骨血和骨气。好短篇却是有渊源的活水。这又取决于写作者的看世界,就是前面说过的那 ----王安忆《故事与讲故事》
●许多人的历史是在一夜之间中断,然后碎个七零八落,四处皆是。 ----王安忆《长恨歌》
●本来要靠时间去抹平,哪经得起这么翻来覆去的提醒,真成了刻骨铭心。 ----王安忆《长恨歌》
●但是,我往往缺乏主见,我觉得所有的场地都敞开了,再也没有墙壁,使得你落笔之后就无法寻找藏身之处,不知如何收场,如何表达,并且让你那些有失统的言行不再受人尊敬。 ----王安忆
●有多少故事在街道上行走,走走停停,又停停走走。有的刚开个头,有的将要收尾,还有的正在中途。 ----王安忆《悲恸之地》
●她自己家的月亮是天井里的月亮,有厨房的烟熏火燎味的;这里的月亮却是小说的意境,花影藤风的。 ----王安忆《长恨歌》
●他深知聪敏和坚定全来自孤立无援的处境,是自我的保护和争取,其实是更绝望的。 ----王安忆《长恨歌》
●耐心是百折不挠的东西,无论于得于失,都是最有用的。
得失都是心上留痕。 ----王安忆《长恨歌》
●这时刻,他们就像深秋天气里的两片落叶,被风卷着,偶尔碰着一下,又各分东西。 ----王安忆《长恨歌》
●过去,她的生活就像在吃一只奶油话梅,含在嘴里,轻轻地咬一点儿,再含上半天,细细地品味,每一分钟,都有很多味道,很多的愉快。而如今,生活就像她正吃着的这碗冷泡饭,她大口大口咽下去,不去体味,只求肚子不饿,只求把这一顿赶紧打发过去,把这一天,这一月,这一年,甚至这一辈子都尽快地打发过去。 ----王安忆《流逝》
●她的心掉在了时间的深渊里,无底地坠落,没有可以攀附的地方。 ----王安忆《长恨歌》
●艾草味里,所有的气味都安静下来,只由它弥漫,散开。一年之中的油垢,在这草本的芬芳中,一点点消除。渐渐的,连空气也变了颜色,有一种灰和白在其中洇染,洇染成青色的。明净的空气其实并不是透明,它有它的颜色。 ----王安忆《比邻而居》
●六月栀子花开。 ----王安忆《长恨歌》
●栀子花全开了,雪白雪白的,唯有她是一身红;树上的叶子全绿了,水也是碧碧蓝,唯有她是一身红;房上瓦是黑,水里的桥墩是黑,还是唯有她是一身红。这红是亘古不变的世界的一转瞬,也是衬托那亘古的,是逝去再来,循回不已,为那亘古添砖加瓦,是设色那样的手法。 ----王安忆《长恨歌》
●她们也不知在哭些什么,有什么可哭的,只是觉得心里有一种无法挽回的难过。上午十点钟的阳光从梧桐叶里洒在她们身上,晶片似的,像水银。 ----王安忆《长恨歌》
●我远远不懂每个人都当有一件终身信守的东西,这东西凌驾于肉体与精神之上,使我们的行为不至于盲目, 再因盲目而苦闷。这东西于各人有各自不同的形式,内涵却是一样的。 ----王安忆《杏茶》
●时间就像一个漩涡,顺序在变化。过去、现在、将来,一并在水流两岸呈现。 ----王安忆
●她想,“老”这东西真是可怕,逃也逃不了,逼着你来的。 ----王安忆《长恨歌》
●暮色流进窗户,像是温暖和稀薄的液体,一切都蒙上了一层膜。物体,空间,声音和气息,全变得隔膜,模糊,不很确定。唯有那炉膛里的火,陡地鲜明起来,热烈起来,激励人的身心。这是火炉边最温情脉脉的时刻,所有的欲望全化为一个相依相偎的需求,别的都不去管它了。哪怕天塌地陷,又能怎样呢? ----王安忆《长恨歌》
●缺缺相乘,最后是一座废墟。 ----王安忆《长恨歌》
●这是他们称为祖先的人物,是他们寄托血脉之情的人物。当他们摇摇摆摆走在游行队伍中,有前不着村后不着店之感,好象一支孤旅。 ----王安忆《悲恸之地》
●他(刘庆邦)的短篇不企图告诉什么道理,用它来说明“语言不是短篇”是再好不过了。他的短篇开头的部分甚至有些散淡,你会担心它收不拢尾,可是到了末了,你却惊异它的完整。他们从来不是有头无尾,也不是故弄玄虚,它们老实本分,不耍滑头,恪尽职守。这里其实是需有自信和能力的。如今,半拉拉的故事特别多,有故意不收场的,但至少有一半是收不了场的。刘庆邦从来不做这样的事,是规矩,也是有办法。 ----王安忆《故事与讲故事》
●书面语和口语有着各自的文学危险,在它们身边潜伏着各自的陷阱,稍不留神就会失足坠入。前者是拘谨,不免会失于刻板,染上漠然的表情。叙述过于疏远对象,便缺乏了痛痒相关的同情;后者则极易流于俚熟,与对象走的太近,失去了批评的距离。反之,如若两者融合得好,取长补短,笑过去是神奇的。在诗里,我觉得冯梦龙整理的《挂枝儿》、《山歌》就是极好的范例。俗情俗字嵌在了文雅的格律里,产生的韵致岂是一个“俏”字了得!在小说,当推《红楼梦》为上上品,书面语和口语之间自如的进出和过渡,浑然天成。烟火人气熏然,一片世间景象,却又有仙道氤氲。是从天上看人间,歌哭逼真,几有贴肤之感,但不是身在此山不见真相。 ----王安忆《故事与讲故事》
●虚无就虚无,过眼就过眼,人生本就是攒在手里的水似的,总是流逝,没什么千秋万载的一说。想开了,什么不能呢?王琦瑶的希望扑空了,反倒有一阵轻松,万事皆休之中,康明逊的那点爱,则成了一个劫后余生。 ----王安忆《长恨歌》
●我希望你们不要过于追求效率
效率总是以目的论的
事实上 我们都是处在过程中 这是生活的本质 ----王安忆
●刘庆邦的小说中,你可以看到这样的惊喜与热情,他是以另一种特别动人的温存态度表达出来的。而且,几乎所有的真正好作者笔下,都会有这种很柔软的情绪流露。这种情感注入在作品里,是他们的边缘曾显出一种接受而不是拒绝的形态,似乎可以随时融入进那恢宏的背景,却始终没融入,而是一个闪亮的斑点。它们就像一种有生命的、全身都张开呼吸毛孔的活物,那样有弹性,活泼泼,有力量。在刘庆邦的小说里,你会有这样浑然一体的感受,它们每一片都很好,你可以不朝窗外看,但有窗口和没有窗口就是不一样。这就是刘庆邦的世界。短篇对于他来说特别重要,因为他们是最好的体现刘庆邦世界的方式。 ----王安忆《故事与讲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