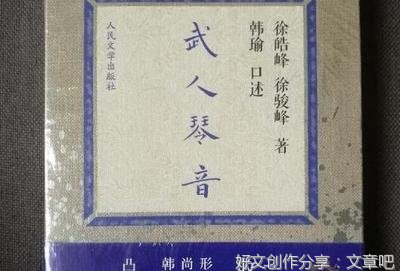
《琴人》是一本由杨岚著作,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 我思Cogito出版的平装图书,本书定价:49.80,页数:320,特精心收集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琴人》读后感(一):《琴人》前两部分试读报告
【按:一日,我思的朋友说,他们有一本待出版的书稿,不确定是否有出版价值,想找人试读给点评价。遂有本试读报告。】
https://athenacool.wordpress.com/2021/12/31/%e3%80%8a%e7%90%b4%e4%ba%ba%e3%80%8b%e5%89%8d%e4%b8%a4%e9%83%a8%e5%88%86%e8%af%95%e8%af%bb%e6%8a%a5%e5%91%8a/
杨岚:《琴人》,我思|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22年3月。 (本文据出版前试读本写作)
子扉我 2021年冬至 季风异次元空间三世
《琴人》读后感(二):琴弦上的变奏人生
杨岚的《琴人》,是一部让我意外的作品。
意外之一,这是作者的首部作品,从书中得知,作者初中毕业后就浪迹各地,而作品文字之优秀与沉思的品质,着实让我惊讶。
意外之二,我读过几部琴之书,高罗佩、林西莉、杨典、严晓星等人的作品,大多侧重于古琴的文化论述,林西莉与杨典谈及身为琴人的经历,他们要比杨岚人生顺畅,而杨岚那种来自民间的自发性的学习,不仅就学艺而言,在更大的范围内让我有共鸣。
琴的前身是树,琴的形制是人。杨岚给我的感觉,有点像是一株山地里长出来的树,一个自由自在的人,向往宽阔的天地、阳光雨露与不那么猛烈的、和煦的微风。杨岚原来不叫杨岚,岚,取山气缭绕之意,表达怀念与追求。
杨岚的老家在贵州县城,父亲是矿区安全的监管人,日常工作就是在各处山地穿梭行走,父亲对杨岚的影响是很大的,序言致辞:“这本书献给爸爸。”开篇描写父子在山中的情景,是父亲从小将这种对自然的亲近之心灌注在他的心里,父亲也理解杨岚休学的决定,任他以十六岁的年纪就独自在全国各地游走,就这一点,没几个爸爸能做到吧。
河北石家庄,河南嵩山、洛阳,江苏扬州,浙江杭州、宁波、安吉、雁村……杨岚背着一把半废的古琴,走走停停,偶尔在某地休驻一段时间,一年半载,留不长,又走了。一般来说,大多数学艺经历的书籍作者都会凸显自己的辛苦和认真,但是,杨岚的状态有很大的差异,他并没有强烈的要学琴的渴望,他仿佛不很清楚自己想要的是什么,仅仅这种游离的状态就成了他生活的意义了。
这也是古琴吸引杨岚的起初原因吧。我以为,琴之道,根本在“独”。它是一项一个人的活动,抚琴人仿佛自处于独特的空间,排斥其他声音的加入,抚琴是一种坐禅自省,是一种与“道”的直接沟通,是与心灵中深奥玄秘的一些东西的交流。古琴之特别,还在于它不仅是乐器,每首琴曲都有故事,牵涉悠久的历史与往昔景象,琴曲是丰富的叙事文本,琴之声,是出世的,又常常是忧愤的、不平的鸣响,所以,琴,最得文人喜爱,它本身就有象征意义,琴棋书画,琴在首位。现代文人哪怕不会弹奏,也常会在房中、案上、壁架搁置一具。
琴,是复杂的。杨岚也是复杂的。他并非刻意地去复古、追古,他要的是追循自己的内心。他有种特殊的本领,就像水融于海,每到一地、陌生的地方,他结识朋友的速度好像都很快,很容易就与周围的人融洽相处,得到各种帮助和人们的信任,接纳他成为一员,也能得到当代名家如成公亮先生的指点,但是,更多的时候,杨岚沉浸于自我的摸索,他聆听许多古曲,钟爱管平湖先生的演奏,阅读大量古籍淘炼需要的资料,在根本上,他最爱的仍然是那种“独”的状态,那种自然发生、随心而动的生活。
他起初自学斫琴,后来学琴是这样的,后来把斫琴作为工作,他还是这样的,没有明确的目的,想做那就做做看吧,弄来一堆木头,也没人指点,也不懂木头的质地、做琴的要旨,就上手去做了,觉得不满意、不像样,就劈了当柴火,另换一批、一种制法,他又是能忍耐的,大漆之痒之难受,我在赤木明登的《漆涂师物语》里也读到过。杨岚慢腾腾地斫琴,一把琴,从年头到年尾,也没能完成。偶尔,赶在秋光之前,想要合着时节,就几天的时间,他却没日没夜地赶了出来。他说,斫琴人,也是琴斫人。我想,斫琴于他,要紧的正是“斫”,刀劈斧砍,凿去了许多,他只要那剩下的、适合的那么一些,琴面和琴底合上,轻轻拨弄,乐音低而回鸣。
这个人,好像要的就是这样的活法,渐渐地,这本书,慢慢转向了厚沉,那些有关琴的感受,从个人经验走向了文化体验,像一株树从土里长了出来,自然地葳蕤成了自己的风景。
《琴人》读后感(三):跳下水去
我从来不听古琴。或者说得更具体一些,我从来没有产生过把古琴的录音透过播放设备放出来给自己听的冲动。看这本书到中途,看杨岚写得心潮澎湃,就在睡前找来成公亮先生的《袍修罗兰》全曲,八首,排好顺序按下播放关灯准备接受催眠。听了大概半小时的样子仍然毫无睡意,我叹口气坐起来把曲子停了,换成“528Hz超快熟睡自律神经治愈音乐3小时无广告”,很快睡着了。
古琴现场倒是听过不少次。都是在杨岚家,有时候只有我,有时候和一群朋友一起,听他现场弹过许多次。感觉还是很妙的,你知道,现场音乐无论怎样都远超录音,尤其是古琴这种东西,自带呵斥效果,杨岚双臂微抬刚一按住琴弦,我就想起退潮的画面:沙啦啦啦虾兵蟹将们都被潮水拽住退到舞台外,海鸥收拢翅膀小心地打了个嗝。
为了证明我可以理解古琴的好处,我至少能列举以下三个优点:1、古琴是降温的音乐,夏天听杨岚弹五分钟马上汗落了。2、古琴是催眠的音乐,有次几个朋友使杨岚鼓琴,后半首曲子我们静静听鼾声和琴声的交响——有一友入睡甚快,大家不忍喊醒他,于是聚众忍俊。我本已困极,因场面过于有趣,反没了睡意,只好暗自羡慕。3、古琴是猎奇的音乐,你在当代几乎很难拥有这样的经验:一个琴师面对面地奏给你听,如果没有恰当的渠道和机缘的话。相对而言,无论管风琴还是尺八还是三味线,都仿佛要容易一些。
由上可知,我基本属于和古琴艺术绝缘的三俗人群,所以由我来读这本书甚至是品评就非常可疑了。然而我不仅读下去了,甚至有些放不下——直到杨岚开始写古琴的历史和掰弄琴曲琴艺的桥段,我才开始犯困。这本书的前半部分写得妙趣横生,有点像武侠小说——或者文侠小说——只要读者诸君善于联想,它完全可以是一个想入非非的15岁少年执拗又狼狈地追寻武功心法奥义、在机缘与努力之下终成一代大侠的故事。让我们来一起读下面一段:
这时你稍微替换几个词就变成了武侠小说,比如:
而这本书的后半段则是杨大侠虚怀若谷投桃报李,将自己成名的绝顶功法的精义解说出来以流芳后世。让我们来试读下面一段:
同样稍作联想,就会变成:
更不用说杨岚还写了不少技术性的桥段,比如:
我真的是爱死这种技术性描述了,它也让我开展联想时信手拈来,一切都显得那么自然:
好了,我暂且按捺住改编整书的冲动,把这个工作交给善学的读者诸君;更何况,如果真有严肃的古琴爱好者看了这篇破玩意儿,也很容易断了捧读本书的念想。但我的意旨其实是严肃和强烈的:我真的很期望杨岚闲下来不弹琴时,能捣鼓一本武侠小说,或者,一本关于侠客的书,它想必非常非常好看。
二〇一五年前后,我曾经想要把杨岚的成长经历写下来,写成类似都市怪谈的样式。为此,我前后找他长谈了两次,也录了音,光是速记的提纲就记了两千字。因为他的故事实在是百转千回疑窦丛生,教人扼腕、捧腹和惊叹,动机的时间线缠绕在一起,有的线索他自己也记不清孰先孰后,还有一些画风突变的支线剧情(比如他突然迷上登雪山的其事二三),造成写作的极大困难。我约莫写了准备的材料的四分之一到三分之一,因为懒惰,终究还是停了笔。前日读罢这本新书,又从废纸堆里找出当年写杨岚的那篇文档,本想把它完工凑数作书评,但七年前的稿件实在不忍卒读。我很高兴杨岚终于写下了自己的故事,虽然比起他真正可以讲的全部故事——不仅仅是关于古琴的——这本书里写的仍仅十中取一。
我不知道古琴在音乐分类学上是否可以被归类到极简主义里去,但我隐隐觉得杨岚对极简主义的兴趣来源于他想从这条脉络上给古琴寻找出路。不过“出路”这个词可能有些矮化他,因为杨岚真的对古琴的传承没有任何士大夫式的责任感——或者所谓文人的自觉。他的出发点源自强烈的个人主义喜恶,而非任何对法统、道统或师承的弘扬。与此相匹配的,是一个艺术家的天然自觉,是他对音乐的绝对诚实。当我们总在提醒自己“忠于自我”的时候,杨岚的自我从来都是他的核心推力,任由自己一路磕磕绊绊走到今天。他的诚实同样贯穿了这本书的始终,不仅铺垫了他斫琴的艰辛,也为他带来了古琴演奏者身份的焦虑。
古琴是属于古代的乐器,并且在古代中国的时间长河里固化了,它不再更新形制,而杨岚作为一个现代人必须诚实地面对他和古琴之间的时间冲突。用他自己的话说,“好像我的性格是如果不把一件事情在逻辑上理顺,就很难心安理得地做下去。”他用了很久去寻找这个今人奏古琴的“自然的位置”,最后他找到了,并且在书中也做了许多次不同的阐述,也就是他无法抛开今人的经验去演奏古琴,那样是不诚实的。你虽然无法踏入古人踏入的同一条河,但唯一诚实的方式即是“跳下水去”,在他演奏的时候,他即是承载了现代阅历的自己本身,道法自然,他的古琴曲也当仁不让地是具备现代性的当代音乐。由此,他也将自己和崇古、仿古、恪守传统的“原教旨主义者”们做了切割。然而这其中的复杂性并不是如此容易就能切割清楚的,杨岚自己显然也一直意识到这个问题,他自身就有强烈的崇古情绪,他显然也知道自己是在想象中“营造一个诗意的时空”,演奏者的动机是时空上溯的,演奏者沉浸在这样一种对古代时空的想象之中,在现在的心理术语中我们称其为“移情”。当我们赋予移情合法性的同时,对因循旧制的窠臼的批判就显得道貌岸然。从事态之外旁观的话,这种分裂似乎不仅源于人与人个体的不同,而本质上是对一种艺术化石的态度的分裂,是在新文化运动之后一直到今天从未停息过的,对我们的文化基因里“反刍式进步”的漫长而苦涩的反思和争执。我们的文化传统那么好,却也那么糟。
如果这还不够的话,杨岚在书中对于时间本质的思考则更加频繁,这可能更能揭示他当下的关注。毫无疑问,我们和已知世间的万物都处在时间的枷锁之中,尽管我们大多数人不需要整日思索过去与未来、当下与永恒,但杨岚却不能不想。毕竟,他双手扶琴,响起的全是绝唱。他说“嵇康临刑的《广陵散》是中国音乐史上最重要的现场”,前前后后写了不下三四回,读之无不触动——是刑场也是音乐现场,搁在今天我们会说嵇康真的挺躁的;他试图从考察时间的本质出发,将音乐的即时性同永恒性划下约等号,虽然在这一点上他似乎没有十分的把握——在这里我要特别称赞一下杨岚的语文,他的书写是诗性和理性的叠加,他的词汇谱是不确定性和专业性的叠加,为友许多年,我从没读过杨岚的写作,所以也没想到他可以写得这么好。要知道,这种旷古的怀思一不小心就会写成“我吹过你吹过的晚风,那我们算不算相拥”的制式共情。
就时间的本质也许我也无法再贡献更多的价值,但我可以对一些意象稍作补充。就拿嵇康的《广陵散》行刑现场来说,这首曲子,连同世间曾经演奏过的所有音乐一起,它的物理影响(声波)仍然遗留在现实世界的微观量子描述之中。我们经历的每一个现实瞬间都是由过去的每个瞬间的模态发展而来的,这其中,没有任何信息会丢失,它只是转化成了我们无法读取的形式。另外,如果你相信可观测宇宙整体也遵从庞加莱回归,那么终有一天,嵇康会再次走上洛阳城外东石桥南的行刑台,看时间尚早,再次奏响一曲《广陵散》,留下他最后的波纹。而你我也必定再次不在台下的观众之中。
写到这里我一下子觉得似乎写完了。我本打算写写这本书里让我觉得值得探讨的关于自由、教条、异域、梦幻的微妙话题,但讨论一分明就会落下乘,我也花了太多篇幅去插科打诨,而读者诸君自当保留去原书中品评的愉悦感。《琴人》是杨岚的第一本著述,对于完全不了解作者是何方神圣的普通读者,它似乎成了一本过早的自传:琴人杨岚不是先以琴而是先以书闻世,这看起来多少有点滑稽。所以解决之道就是期待杨岚的第二本书,虽然我们都还不知道那是什么,但我盼望他能写出脍炙人口的故事来。到那时,读者诸君想必挖出这本《琴人》啧啧称奇:没想到,这家伙搬弄丝竹的本事也挺唬人的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