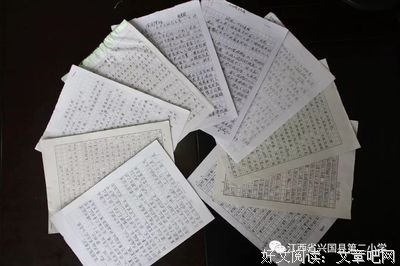
《语言的第七功能》是一本由[法] 洛朗·比内著作,海天出版社出版的平装图书,本书定价:48.00元,页数:428,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语言的第七功能》读后感(一):《语言的第七功能》
《语言的第七功能》
很难想象一部小说里能够包含着那么多的语言学学术知识。
一本书,里面提及到英法德俄美等众多欧美国家、中日亚洲国家,甚至还有来自非洲的、东南亚等国家的人物。小说里面人物的国籍非常广泛,并且对于不同国籍任务的外貌刻画以及语言表达又都是如此精辟。此外,作者对于当时的社会大背景以及全世界的历史事实掌握的又是如此的广博深刻,不得不让人佩服。
拿到这本书,第一眼是——语言的第七功能(La septieme fonction du language),视线下移,会看到—— “谁杀死了罗兰巴特” 这行文字,此时你会疑惑:这到底是一本专业学术书本,还是一本小说。
小说开头就写罗兰巴特被车子撞伤,送进医院。警官巴亚尔以及警官的顾问学者——西蒙涉入调查此案。调查过程中发现罗兰巴特的撞伤及死亡是因为一份关于语言第七功能的文件。小说也跟随者案件调查的深入逐渐进入高潮。
在小说中,作者提到了语言学术的问题、斗争时的武器装备、男女间的两性欲望、放纵麻醉自我的酒精毒品等等。另外,一场场语言辩论、一首首音乐欣赏、一次次追踪遇险服装啊、没事啊、语言学家们的名字啊、学术界各位泰斗的著作啊
读着读着,便被作者这浩瀚的知识储备倾倒了。
总之,佩服洛朗比内(Laurent Binet)这种看似“天马行空”,其实又细思缜密的写作手法,更折服于他缜密的思维认知与广博的知识储备。
苦瓜晓花
2018.01.23
本月16日和室友打赌一周读完这本书,赌注是是十个大橙子。
谢谢这次打赌
《语言的第七功能》读后感(二):梦蝶的不只是庄周
我觉得我是被困在一部小说里了如何知道现在到了他人生这本小说的第几页每个人不都以为自己是人生的主角你怎么知道你不是在一本小说里?怎么知道你不是活在一个故事里?怎么知道你是真实的?你是傻了还是怎么的?真实,就是你活着。就这样。自己到底是在被一个蹩脚的作家操控?必须像对待神明一样对待这个假设的小说家就好像神明总是并不存在就因为他是存在的幸好他只是一个蹩脚的小说家不值得他人敬重也无须依从他的安排想要改变故事的进程永远都不算晚故事的结局掌握在主人公手上这个主人公就是我当小说里的人物开始怀疑自己是否只是小说中的角色 当漫画里的人物开始怀疑自己是否只是存在于漫画里 当正在做梦的你开始怀疑自己是否真的是在做梦
那么,怀疑的原因是什么? 是生死攸关之际 是巧合和诡异的频繁出现 还是不合逻辑的轮番上演?
《语言的第七功能》读后感(三):罗各斯俱乐部的辩论(整理)
*比赛规则
两人对抗,抽一个主题,即由是否回答的一般疑问句,或是赞同或反对,两个辩手为不同的立场辩论
五分钟的准备时间,先介绍主要观点和论据,随后开始辩论
整个辩论过程时间不定,裁判可随时判定辩论结束
同等级别抽签决定谁先发言,不同级别则是等级低的一方先发言
*等级划分
善言者→善辩者→演说者→辩手→逍遥派→雄辩家→诡辩家····→普罗塔哥拉
*主题
文字还是口语(p159)
→柏拉图和苏格拉底
如果不是柏拉图,那么苏格拉底的思想,包括他在《裴多篇》中对口语的称颂,将无人能知
*天主教和马克思主义(p201)
第一位辩手提到了亚西西的方济各、乞丐帮会、帕索里尼的《马太福音》、工人神甫、南美洲解放的神学、把商人从神庙中驱走的耶稣,最后的结论是耶稣是第一个货真价实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
(大获全胜 3)
第二位辩手成功地论述了人民的鸦片,佛朗哥和西班牙战争,教皇庇护十二世和希特勒,梵蒂冈和黑手党的勾结,宗教裁判所,反改革,十字军东征,对杨·胡斯、布鲁纳、伽利略进行的审判。
(无济于事 0)
*足球和阶级斗争
球员和其他人一样是无产者,而俱乐部老板窃取了他们的劳动力
*知识分子和权力(最让人紧张的一场辩论)
知识分子,上层建筑的公务员,参与构建领导权。知识分子总是陷于“经济合作”的逻辑中,有组织或传统,他们总是为权力服务,现存的权力,过去的,或者将来的。
葛兰西:所有人都是知识分子,诚然,但并非所有的人都能在社会中占据知识分子这个职位,这个职位致力于让民众自发地表示赞成。知识分子的救赎?今天还有谁能实现救赎?历史性折中,一派胡言!妥协导致恶果。(青年)
当一个人能为无声者发生,他就配得上知识分子的称号。所有的知识分子,如果正确地在做他能胜任的启发性研究工作,如果那时他的志向,即使他在为权力服务,也是在反对权力,真想总是革命性的。(老妇)
有人要挑战普罗塔哥拉,谁去挑战,谁就是偷走第七功能的人
为弄清真相西蒙连跳4级晋升为逍遥派,再赢一次,成为雄辩家,就有资格得到挑战赛的入场券。
符号学理解分析解码,用作防卫;修辞学说服击败,用作进攻。
*古典和巴洛克(主题是艺术史,辩论地点是威尼斯)
对手:巴洛克,即鼠疫。威尼斯的历史只是与鼠疫的漫长对话。我们宣称的古典都是经验论的,我们谈论古典,但从没见过,古典不存在。
西蒙:古典不存在,那么威尼斯就不存在。古典的定义,秩序和美、奢侈、平静、享乐(波德莱尔);经典、文化(越有文化就越有趣,就越丰富)、智慧、讽刺、微妙、惬意、克制、安全(生活的艺术),这也是威尼斯的定义。巴洛克和古典,这两者并非对立,威尼斯就是证据。
*以温柔之姿行癫狂之举(出自16世纪法国诗人龙沙)(P365)
埃科:转化为温柔与力量是否对立
以温柔之姿行癫狂之举的就是诗人,诗意的狂乱。诗歌不算艺术,不算技术,而是神圣的灵感。诗人的体内住着上帝,他是上帝的第二种形态(苏格拉底对话伊安)。诗人是疯子,但那时一种温和的疯癫,创造性的疯癫,而非毁灭性的疯癫。
《语言的第七功能》读后感(四):谁杀死了罗兰•巴特?
在沉浸于阅读的夜晚,我偶尔会想起一位朋友说过的一句话:“我总是情不自禁地沉迷于自己喜欢的那些思想家和作家的死亡场景中,比如本雅明之死,比如罗兰•巴特之死,这里面或许存在着某种冥冥之中的东西。”这是一种阅读的“偏执”。我似乎也是如此,在阅读中往往也对这类的信息心生敏感,记忆犹新。在读到洛朗•比内的《语言的第七功能》时,我第一时间就想到了我那位朋友,他们是同一类人。
先从一则著名的轶事开始。对罗兰•巴特有兴趣或有所了解的读者,一般都会听过它,它跟巴特的死亡有关。那是1980年2月25日,巴特在参加完一场“大人物”的聚会(与密特朗总统用完午餐),在返回法兰西学院的路上,正想穿越斑马线时被迎面而来的一辆卡车撞倒,之后在医院不治身亡,后来人们在车祸的地点写上了一行大字标语:“开得慢一点,您可能会轧死罗兰•巴特。”
关于巴特的死,流传有各种各样的说法。其中曾为巴特立有大传的 蒂凡尼•萨摩约 (Tiphane Samoyault)在书中试图告诉我们,车祸并不是巴特死亡的决定性原因,因为从2月25日发生车祸到3月26日的逝世,足足有一个月的时间,他的健康状况本在好转,但后来急转直下。那么,是谁杀死了罗兰•巴特?这个无法完全确定的问题,或许就让洛朗•比内无比狂热,所以才有了《语言的第七功能》这部小说的诞生。
洛朗•比内以这个问题为书写的锚点,在小说中展开了他奇异而丰富的想象和构想。他以一种埃柯式的反讽提出,罗兰•巴特是被谋杀的,之所以被谋杀是因为他身上有一份罗曼•雅各布森未公开的文件《语言的第七功能》。据说只要掌握了这种功能,在任何情况下都能用语言来控制和战胜他人,可以让任何人为之做任何事。
巴特被撞之后,警官巴亚尔负责调查,后来又请来了年轻的语言学家西蒙参与此案。正在进行总统竞选的吉斯卡尔给他们的任务是找到这种第七功能。而这将一大批声名显赫的理论家和文学家都卷了进来:福柯,萨特,德里达,德勒兹,阿尔都塞,萨义德,西苏,索莱尔斯,克里斯蒂娃、艾柯……在这个案子中,他们都有嫌疑!随着调查的不断深入,叙事越发扑朔迷离,而思想的火花也随之不断绽放……
穿梭于这个披着悬疑外衣,贯穿了各种理论话语的故事文本,仿佛只在一口气之间。酣畅!淋漓!情节不断推进,情绪不断发酵,但最后还是回到了这个问题之上:正如巴特这个角色所意味的,现实与虚构的界限似乎被消解了。那负责参与调查整个事件的巴亚尔警长和西蒙最终也进入了理论与叙事的谜团中,分不清自己是作为何种角色而存在的。
载于280期《深港书评》阅读专栏
《语言的第七功能》读后感(五):杀死罗兰巴特的心情
洛朗·比内想要杀死罗兰·巴特的心情,我很理解,跟中学生痛恨马克思、牛顿和鲁迅是一个道理。可以设想:某天凌晨,洛朗·比内写符号学论文写到心力枯索,愤然在电脑屏幕上敲下几个大字——杀死罗兰·巴特!没想到,简简单单一句话,枝条伸展,就成了一部洋洋洒洒35万字的长篇小说,真是解恨又争气!
#符号学、阴谋论、神秘主义、谋杀、探险、八卦,通通是我热衷的元素。#
【符号学是一个古怪的玩意儿!】
小说前半段,花了大量篇幅细数索绪尔、埃科、巴特、福柯、德里达、雅各布森等学术大咖的理论贡献,科普编码、解码、能指、所指、隐喻、选择轴、结合轴、元语言、征象等语言学基础知识,既是讲解给“大老粗”巴亚尔警官听,也是为整部小说的核心线索做理论铺垫。符号学,原本就是个尴尬的学科,埃科称符号学是所有学科之母,但一切能指所指隐喻修辞的纷繁解释,完全可能被指责为牵强附会。为什么詹姆斯·邦德的代号是007?有人说,这是英国海军情报机关破译的德军密码代码,有人说,原作者伊恩·弗莱明经常乘坐007路公交车。语言学家西蒙却说,00代表死亡和虚无,7代表保守和恢复秩序。此番解释有道理、无意义,不妨碍它引人入胜,特别是对于我这种阴谋论爱好者。
【知识分子是权力的盟友还是敌人?】
词语的多义性永不枯竭,可理论的实用性要如何验明正身?作者直接大跨一步:雅各布森已然发现,语言还存在第七种功能,这一功能如同咒语,可以蛊惑人心,操控大势。世界观设定往往来源于作者的自我排解,社科类学术工作者终于凭此扬眉吐气,但其实,语言的力量从未被世人忽视,不然,那些锐意激昂的辩手以何为战?小说后半段对辩论场的描述着墨甚多,其中几个辩题很有意思:“文字还是口语?”“危机正是在于青黄不接”“知识分子是权力的盟友还是敌人?”“以温柔之姿行癫狂之举”……语言的第七种功能对于众人,与其说是震荡学术界的大革命,不如说是“提升内力”的“武功秘籍”,拿到TED演讲、辩论节目大行其道的今天,更失玄妙。小说里面,争抢秘籍致多人牺牲性命后,语言第七功能的唯一用处,是帮密朗特赢得法国总统大选的电视辩论,真让人失望,生出一点黑色幽默感。
【巴黎是一场流动的盛宴。】
很多时候,学术圈的八卦故事,比娱乐圈更有嚼劲。小说的背景板都是熟面孔:花神咖啡馆里,萨冈给萨特捶背,替他念填字游戏的谜面,可惜波伏娃不在;晚宴上,拉康的情人用脚挑逗贝纳尔·亨利-莱维;阶梯教室里,莫妮卡·维蒂用爱恋眼神看着安东尼奥尼……更别说,福柯、埃科、德里达、雅各布森等教科书里的人名直接牵涉案中!名流云集的黄金时代,开车时,的确可能一不小心就撞死个罗兰·巴特!案件展开过程中,作者极尽所能地贯彻阴谋论和神秘主义,象征符号堆砌满满,至于故事的谋篇布局,比不上《达芬奇密码》,也总比《傅科摆》有意思吧!
【诗意的狂乱。】
尾声中,西蒙在现实和虚构之间错乱,面对从天而降的杀机,他想知道是不是扮演上帝的小说家试图杀死他,却没有成功,试图给他启迪,却没有解释明白。尽管,这是个蹩脚的小说家,或是个迟钝的编剧,但改变故事的进程,永远不算晚。毕竟,我是主人公!我是主人公吗?小说家或编剧了解我的所作所为、在乎我的所思所想吗?我是主人公!这个世界,因我的视角而存在,我理所当然是主角!可就主人公而言,这是一个合格的故事吗?这是一本能读懂的书、一集能期待的精彩吗?小说家该做什么,主人公该做什么,我们真真切切明白吗?我们壁垒分明、旗鼓相当吗?我们到底是哪个我?(举手承认,后半段,只是我自己的絮絮叨叨。)
附上书中让我痴笑的句子:
“他难逃全世界所有文学从业者的通病,第一次上别人家,总是要好奇的看看人家书架上有哪些书,即便有时这并不是他们登门拜访的本意。”
微信公众号 huluanzhangchengzi
《语言的第七功能》读后感(六):德里达的胜利
《语言的第七功能》是小说中一份令人趋之若鹜的文件,人们相信只要得到它,就可以成为世界的主宰。故事中的人物翁贝托•埃科解释说,这一切都源自奥斯汀对于“言有所为”(How to Do Things with Words),以及语言之操演(perform)功能的揭示。语言不仅可以叙述和再现,还能推动事件的进程。你在说话的同时,一些事情已经改变了。而语言的第七功能,便是将操演性发挥到极致的效果。据说,掌握了这一功能的人,就可以“说服任何人在任何场合干任何事”(《第七功能》,218页)。但是,埃科说道,一旦这份文件被其他人知道,其效果便会减弱。这有点像魔术师的工作手册,其内容必须绝对保密。一旦大家都学会了这种戏法,它也就不足为奇了。因此,必须消灭所有的副本,有时,甚至连反复表演同一个魔术都不被允许。
此处的论调,使人想起奥斯汀那个经典的例子,以及德里达对其的精彩辩驳。奥斯汀认为,同样一句话,比如“我宣布你们结为夫妻”,如果出现在婚礼上,那它就是正宗的行为句(performative);如果是戏剧舞台上的一句台词,则不具有行为句的效力。德里达则说,戏剧对婚礼的重复和模仿,恰恰是婚礼上这一“行为句”能够产生效力的前提条件。因为,只有一句话已经成为了惯用的程序,能够在舞台上被重复,它的效力才能在生活中被大家所认可。类似的辩驳也可以原封不动地搬到小说中来:《第七功能》的副本非但不该被蔑视、被销毁,而且,正是它的存在赋予了“原件”主宰世界的权力——如果真有这种可以无视人物、场合、事件而永恒存在的权力的话,确保“语言的第七功能”可以顺利地施行。
现实中的德里达如此,而故事中的德里达,也正用这样的观点有力回击了奥斯汀的支持者希尔勒。他提出,所有的语言其实都已经是副本和引用,我们需要重复已经使用过的词汇,否则对话者将无法听懂。(《第七功能》,300页)看到最后,我们会发现,德里达的这番话堪称谶言。人们不惜互相残杀也要得到的那份文件,其实是伪造的。“原件”从最初便已经是虚假的副本。“从一开始,我们追寻的就是一场空。”(《第七功能,402页》不仅如此,试图销毁所有副本的人也付出了惨痛的代价。索莱尔斯一心想得到这份事关语言功能的秘笈,靠它战胜逻各斯俱乐部中的大师级辩手。依照文件的指示,他在辩论中采用了梦呓般的语言,字不成句,句不成篇。这种具有绝对独异性的语言,的确符合他、文件的所有追寻者,以及奥斯汀的支持者们的设想:只此一份,无法复制,永不外传。为了确保这种独异性,索莱尔斯和克里斯蒂娃夫妇不惜杀死它的持有者巴特,以及所有可能得知文件内容的人,而这一行为也招致了宿命般的后果:索莱尔斯在辩论中所讲的话,评委和听众们根本无法听懂。这一结果证实了德里达的预言,语言的“可重复性”才是制胜的关键。更有意思的是,索莱尔斯手中的假文件,其伪造者正是德里达本人。这份在偷龙换凤之计中匆匆而就的伪作,有意或无意地将“胡言乱语”的策略教给了索莱尔斯,从而最终令他的论敌自食恶果。
那么,《第七功能》的真实内容,究竟是什么?究竟有什么方法能让人获得语言的绝对力量,一劳永逸地成为辩术大师?故事的结尾处,候选人密特朗在总统大选前的辩论中展示了这份秘笈的力量,它也的确让他赢得了大选。在辩论中,他雄辩、精准、有力,但除此以外,再无特别之处。他与对手正常地交锋,就如同逻各斯俱乐部的每一次辩论,观众也通过电视转播顺畅地观看这场竞赛,没有任何理解上的障碍。这一次,密特朗胜出了。那么下一次呢?《第七功能》又如何发挥作用呢?谁也不知道。
根本没有什么神奇的、一劳永逸的辩论方法。这不仅是通过总统大选反映出来的事实,也正是密特朗成功的秘诀。小说指出,他只看重眼前,即“要在辩论中打败吉斯卡尔”(《第七功能》,第399页)。换言之,他只想在某一特定的、具有时效性的事件中发挥语言的“操演”功能,因此并不在乎是否有旁人(除了对手吉斯卡尔)也拥有这份文件。他看重当下,因此也承认过去与未来,肯定重复和变异。他清楚自己的这番话会在观众的电视机里不断重复,也会在之后的各种场合中不断重复,并在无数的重复中不断发生变异。但他并不在乎,他只想要赢得这次大选。而他的演说之所以能够发生效力,也正取决于这种对于重复的肯定。或许在之后的某一场合,他还想要再赢得一场辩论,但那将是完全不同的情况。那个不被允许看到文件的对手会改变,他在辩论中的措辞会改变,甚至文件上的文字本身也会改变。
故事中途,希尔勒为了争抢文件而杀死了德里达,但那番关于“可重复性”的精彩论述却早早揭露了这份神秘文件的实质,并帮助密特朗赢得了大选。语言的效力取决于它在不同语境下的可重复性和可变异性,所谓的绝对权力和极致操演根本就不存在。德里达的幽灵飘荡在故事上空,以一种隐晦的方式取得了最终的胜利。而在故事的外部,现实中的德里达也没有停止战斗。1982年,他在《世界报》的采访中回应与希尔勒的论战,指出语言的操演性不仅无法与语言的叙述性完全分离(叙述句与行为句经常呈现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状态),而且其效力取决于大量的、且总是敞开的“文本”(短语、手势、语调、场景、各种标记等)。(德里达:《语言》)正如小说的结尾,人群欢呼着庆祝密特朗的胜利,他们反反复复呼喊着他的名字,但“新任总统并不在场”(《第七功能》,406页)。他没有出现。他即将到来。
《语言的第七功能》读后感(七):夏尔凡白衬衫与黑色雪铁龙:八十年代的符号学冒险游戏
,—— 评洛朗·比内《语言的第七功能》
文 / 杨植钧
载《新京报书评周刊》2017年4月22日,B06
雪铁龙DS,亦即“女神雪铁龙”(Citroën Déesse),因其机翼横截面般的腰线、蔑视万有引力的空气感和富于未来感的优雅外壳而深深打动了包括罗兰·巴特在内的众多法国知识分子的心。在《神话学》(Mythologies)中,巴特称赞其“天降凡尘”,有如一座哥特教堂,是“日常神话”的一部分。巴特想必会因为撞倒他的是一辆保加利亚洗衣工开的小卡车而不是一辆雪铁龙DS而死不瞑目——不过,在洛朗·比内的小说世界中,有辆幽灵般的黑色DS时刻隐藏在那些想要追查巴特之死的“真相”的人的附近。两双眼睛正透过挡风玻璃窥视着已故哲学家身边的一举一动,就像透过詹姆斯·邦德的纽扣孔看着符号们那看似无序的布朗运动。
《语言的第七功能》(La Septième Fonction du langage)的开篇是一个陷阱:打开书,迎面砸来的就是作者洛朗·比内关于索绪尔符号学的大段引用。藉此,它展示了自己虚假的骨骼肌理:一部学院小说,文人小说,语言学小说,引文小说?然而读者很快就会发现,此书并非一部高冷的学术小说,而是一个由比内设计的巨型闯关冒险游戏,其间不乏毒舌与吊诡。通过把声名卓著的符号学家罗兰·巴特解释为八十年代法国政治权术与学界斗争的牺牲品,比内把我们带入了一场符号与伪符号翻飞的的风暴之中。
八十年代的法国,哲学咖位具有造神的威力。和思想革命与认知颠覆的初衷相悖,耳熟能详的明星大师们都逐渐变成了学术神坛上的壮丽石像:巴特,福柯,德里达,阿尔都塞,索莱尔斯,克里斯蒂娃,莱维,德勒兹……洛朗·比内的目标非常明确:在这些石像身上撒尿。为了完成这幅波普风漫画,比内选择了富有纪念意义的一年:1980年。在这一年,政治生涯一直不走运的弗朗索瓦·密特朗在电视辩论中强势压倒保守派的吉斯卡尔·德斯坦;美国网球公开赛中,老将比约恩·博格和新秀约翰·麦肯罗贡献了一场为后世津津乐道的“世纪大战”;全世界都在跟着Supertramp摇滚乐队《逻辑之歌》的旋律恣意起舞;符号学家巴特刚刚结束了和总统候选人密特朗的午餐,在海狸路上陷入迷离沉思,然后突然就被车像破布偶一样撞倒。来自文化界、学界和政界的大事件小细节在《第七功能》中被马赛克一般拼砌起来,颇有点帕特里克·德维尔(Patrick Deville)式历史万花筒小说的味道。不过,比内笔下的历史是一种调皮的解构,就像一只钻到时代衣服下乱窜的跳蚤。他的视角带着阴郁的、近乎窥淫癖的快感;透过他用旷世脑洞打开的裂缝,我们窥到了哲学和语言学大师们“真实”的一面:
福柯,性欲过剩的基佬,终日出入于同志桑拿,一边被来自阿拉伯的壮硕小伙口交,一边说着拙劣的冷笑话;德勒兹,不爱剪指甲的男人,只对网球赛电视直播感兴趣;索莱尔斯,傲慢的花花公子,嘴上说着没人能懂的密码碎片,心里想着4P;克里斯蒂娃,诡计多端的女人,和保加利亚秘密警察狼狈为奸;拉康,带着情妇去勾引其他男人,不时发出一两声魔性的猫头鹰尖叫;莱维,整天穿着他那件夏尔凡牌的白衬衫,扣子全开:“上帝死了,但我的发型依然完美”(现实中的莱维的确说过此话)…… 至于在大洋另一边的美国佬,也没能躲过比内的阴险笔触:乔姆斯基、扎普、希尔勒……当然还有帅T朱迪斯·巴特勒:“我是男人,我要操你。你现在感受到我的言后行为了吧,嗯?”
比内对于学院趣事老梗和撕逼丑闻的熟悉程度不亚于写出了《小世界》(Small World: An Academic Romance)的大卫·洛奇(David Lodge),两人都在一种游戏性的概念肚皮舞中展示了当代学术圈生态,辛辣反讽了学界诸神们剪不断理还乱的私生活。不过,比内显然更无下限:他往往从一个简单的梗出发,把它夸大和扭曲到具有核弹破坏力的地步:福柯当然没有当着学生的面手淫(不过,谁知道呢?),巴特勒当然没有打算同时操一个玉女和一个硬汉。比内没有拘泥于现实中发生了什么,他注重的是这些人留给后世的印象,是他们遗赠给我们的堆积如山的概念,是世界对于诸神的刻板印象和肤浅解读:《第七功能》不是一幅低俗的学术春宫图,而是其反面:通过玩弄各种轶事和口头禅,它把学术大家们的精神简化为一连串可以重复生产的、僵死的符号,把他们的生命简化为一出掉书袋的概念假面剧:这恰恰是大众对他们所干的事。比内一方面通过漫画式的展示把大师们拉下神坛,另一方面又通过这种可笑可悲的、轻小说或地摊读物式的人物素描而讽刺了学术界乃至吃瓜群众们对大师及其理论的流行图式化批量生产。在经常出现的高冷学术概念和低俗语境的并置中,涌出了爆炸性的幽默和令人不适的荒诞感:群交中的言外行为和言后行为,在阶梯教室里花式做爱时想着德勒兹书中的欲望机器和无器官身体……当然,还有本书那具有终极统治力的“操演性”——一个在语言学课本中无处不在的简单术语,摇身一变成了一份力量足以让人征服宇宙的绝密文件。
《语言的第七功能》是一部伪语言学小说,却是一本真正的侦探与冒险小说。其实,就其“观察”“解码”和“侦破”性质来说,符号学和破案术之间有着绝佳的亲和性:“人类语言不能表达一切。身体会说话,物品会说话,历史会说话,个人或集体命运会说话,生与死也会说话,而且是以各种方式不同地在对我们诉说。人是一台释意机器,只需一点点想象力,就能随时随地看到符号。符号学起航征服广袤的世界。”懂符号者得天下。能够和各种符号对话的人天生就是破案奇才。巴特本人对詹姆斯·邦德的浓厚兴趣也绝非偶然。《第七功能》主角之一、虚构的万森纳大学年轻教授兼博士生西蒙·赫尔佐格,就是这样的一个人:为了追寻一份语言学家罗曼·雅各布森留下的可以凭借语言力量控制他人和征服世界的文件,对语言学一窍不通的警官巴亚尔请求西蒙当自己的破案助手。这对性格互补的破案组合令人想到探案小说中常见的二人组:柯南·道尔的福尔摩斯和华生,塞耶斯的彼得·温特西和邦特,斯托特的尼禄·沃尔夫和阿奇·古德温……正如在经典侦探小说中那样,这两人之间也存在着某种“搭档效应”:孔武有力、厌恶知识分子的汉子巴亚尔,作为密特朗权力网络中的重要棋子,一开始对大学里那些长发鸡胸的学生和教授嗤之以鼻,后来却在西蒙的影响下开始像后结构主义者一样思考;清癯的符号学家西蒙,一开始极其憎恨国家和权力机器,最后却在破案能力和辩才的施展中看到了自己对权力的暗暗渴求,最后成了不弱于巴亚尔的出色警探和冒险家。
比内的哲学-侦探小说设计让人想起帕特丽霞·邓克尔(Patricia Duncker)上世纪末的著名小说《致幻的福柯》(Hallucinating Foucault)。在这部糅合了诺特博姆和拜厄特风格的作品中,沉迷于哲学和语言学的博士生主人公在撰写一篇关于作家保罗·米歇尔的博士论文。阴差阳错中,他踏进了被囚禁在精神病院中的同性恋者保罗·米歇尔的思想世界,同时也因后者的死而被卷进了一场涉及权力话语的阴谋之中……米歇尔的原型就是米歇尔·福柯。在《第七功能》中,西蒙也是一个深入权力、阴谋与罪恶热核的解码者,追查的也是一位哲学家死亡的真相,不过与邓克尔奇诡博学的风格相比,比内的破案惊奇更接近于黑色电影的冷硬血腥,同时又不乏各种戏仿好莱坞商业黑帮和警匪片的桥段:枪战,暴力,爆炸,追踪,逃生……少不了的还有B级片般的情色插曲。无处不在的秘密警察和黑帮打手,用雨伞杀人的高级密探,图书馆里和在打印机上的火辣性爱。还有幽灵般闪现的跟踪团伙的车子,就像丝袜里藏着的匕首一样冰冷迷人。在后结构主义与犯罪电影的双重编码与戏仿中,比内展示了自己自由穿梭于各种符号、象征、影像母题乃至“日常神话”之间的才能。就连全书的核心,那份被称为“语言的第七功能”的机密文件,也是一个希区柯克式的道具:一个“麦加芬”(MacGuffin),触发全书的追踪与悬疑情节的神秘之物,一个不需要实体的欲望对象。在语言学故事的框架中,智性的“阅”与欲望的“悦”有机地结合在了一起。
为了解开手持“语言的第七功能”文件的巴特被杀之谜,巴亚尔和西蒙结伴走过巴黎的大街小巷,出没于各所大学的阶梯教室、同志浴室、夜总会、咖啡馆、火车站……并最终深入到一个光怪陆离的神秘神团内部——一个以膜拜语言、宣示辩才和用(伪)逻辑击溃他人为宗旨的“逻各斯俱乐部”。该俱乐部的内部会员制和邪教仪式感让人想起某些血腥的搏击俱乐部,或者共济会之类的秘密结社,或者《玫瑰的名字》(Il nome della rosa)中的修道院。深入逻各斯俱乐部内部的西蒙,可类比为埃科笔下的圣方济各。“逻各斯”在埃科的修道院那儿是一个深层运转机制,在比内这里却成了目的本身,成了一种辩术崇拜的表层形式。有趣的是,这个雄辩俱乐部的最高辩者“普罗塔哥拉”就是翁贝托·埃科本人——比内小说世界中的埃科。1980年正好就是《玫瑰的名字》出版的那年,而小说中的“埃科”也在与侦探二人组的接触中获得了写作此书的新灵感,历史真实和文学虚构交叠为一个里外互相转换的莫比乌斯环。
不过,比内在书中致敬《玫瑰的名字》的做法在某种程度上却是失败的:不可否认,“逻各斯俱乐部”中展开的几次辩论都非常精彩,而且在主题上多和小说的情节发展有关联(比如“知识分子和权力的关系”“书面语和口头语的优劣”),可是从故事主干来说,这个俱乐部的运作和“语言的第七功能”文件的侦破并没有直接关系,更像是一种旁出的、修饰性的枝节。至于“逻各斯俱乐部”本身,则带着强烈的阳物逻各斯气质:父权的金字塔等级制架构,对于语言(象征秩序)的崇拜与操演,还有输掉比赛的代价——切掉手指或睾丸,都是一种对阉割的表演,作为对失败的“逻各斯驯兽师”的去阳惩罚。比内本人当然也意识到这点,并且让花花公子索莱尔斯失掉了睾丸——尽管他在对战埃科的比赛中调用了拉康式的密码语言,也没能摆脱败北的宿命。比内的问题在于他把一切哲学、语言学和精神分析的概念和论据和都作了一次字面上的表演——正如埃科在《诠释的界限》(I limiti dell'interpretazione)中所说的,他陷入了一种自己诠释自己的无节制的、严肃的具体化之中——这对于文学语言来说几乎是灾难性的,它让一切都变成一种可笑的彩排,一种捂嘴说话的蹩脚腹语。比内并没有去“诠释”或“理解”这些来自精神科学各领域的观点,他只是“利用”了它们。他的小说不是面向文化精英的激辩,只是一种为普通大众而写的八卦圣经,套在一个中学语言学教科书的框架里。
比内选择在2015年发表《第七功能》决非偶然:2015年是巴特的百年诞辰。小说一发表就引起了多方指责,其中不乏来自被作者在书中割掉睾丸的菲利普·索莱尔斯。而比内更是为弑妻的阿尔都塞找到了一个解释:因为他的妻子把他拿到手的《第七功能》文件当成垃圾扔掉了。来自法国知识界的反感和责难这反而促成了本书的全球畅销。正是利用这些一本正经的道德审判,作者构建了他那充满迷宫和岔路的符号帝国:《语言的第七功能》这本小说本身就是某种具有潜在操演力量的文本,它宣告了八十年代学界越演越烈的学术和政治争斗的漫画化,而没有知识背景的读者会在潜意识中把小说语言的真实默认为历史的真实。严肃的道德责难则表明了此书的所谓“危险性”——虽然它本质上只是一个吊儿郎当的符码游戏。不过,游戏或许正隐藏着最深不可测的危险。从这个角度审视,《第七功能》远不是一部插科打诨的笑剧;它是一次关于语言权术、媒体造势与沟通困境的沉思。
借助这种元语言主题,比内不可避免地闯进了元叙述的领域。小说最后,侦探西蒙再也无法分清自己到底是真实存在的人物还是一个虚构文本中的“编外人物”,因为谁也不知道能够操纵和表演“真实”的第七功能的起始点。可能只是一个文本宣告了他的存在,可能只是一句话把他生了出来:“必须像对待神明一样对待这个假设的小说家,就好像神明总是并不存在,就因为他是存在的。”可能就连我们,读者,也只是某种虚构和操演,在构成我们自身的符号原子中往外窥探。而通过言说而创造我们的巨大的作者,必然是一个酷爱游戏的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