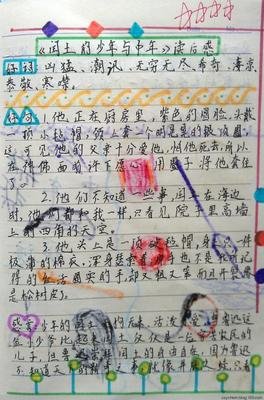
《童年不会消失》是一本由草白著作,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平装图书,本书定价:46.00,页数:244,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童年不会消失》读后感(一):喜欢草白和她的书
认识草白,从看她的散文开始。后来,又看她的小说,也是一样的喜欢。
看草白的文字,就像走进一条旷野的溪流,一个又一个浅滩上,密布着许许多多的原始又坚硬的石头。我说它原始又坚硬,代表的是草白对待文字一贯的态度,她似乎没有写他们,她只是第一个发现者,指给我们看看而已;在这个过程中,草白不评判,不争论,不管状物,还是写人,从来都是那么超然和冷静,就那么平平常常地一指,就让我们跟着她发现了一个完全不一样的文字天地。
这说明了草白超拔的素材组织能力和文学表达能力,也是这两个能力,让草白保持了文学创作的高产和质量,当然,草白还是一个就是热爱学习作家,她是一个永远值得人们去期待的人!这些,跟我一样喜欢草白的人们,只要看看她的最新作品《童年不会消失》,就会,一目了然。
《童年不会消失》读后感(二):为了告别的写作
草白
《童年不会消失》成书了。
在写作此书之前,我写过很多有关童年的文字,直到找到那种感觉——那不仅是童年带给我的感觉,更是语言和存在带给我的。
如何将经历过的岁月,转化为笔下文字,这是一段漫长的旅程。
童年早已消失,如今的我站在一个安全的地方,远离慌乱和恐惧,作漫长而徒劳的回望。我甚至会对那段时间是否真实存在,感到怀疑。
特别是当我住到城市的小区里,房子的四周没有山,地平线被高楼阻挡……更感到一种说不出的慌乱,我是谁,怎么会在这里。我好像从来没有真正地生活过,从出生到死亡,我不能拥有任何生活,只有纸上生活。被虚构出来的一切。
如今的我,要是还生活在家乡那个熟悉的环境里,就不可能写作。很多年里,过去的一切于我完全模糊了。它们变得陌生,好似成了另一个人的经历,另一种存在。这种陌生感带给我叙述的焦虑,以及重构的可能。
通过一些古老的方式,并不存在的道路,那条由词语铺设而成的道路,我回到童年的河边。鹅卵石,腐烂的家禽骨头,芦苇丛里水鸟的啼鸣……所有这些,告诉我古老的经验永远不在事故发生的现场,而在我们的回望里。
现在,我们能看到什么,我们究竟看见了什么?
我并非想赞美或诅咒那个真实存在过的童年,也不关心在任何一段时间里收获的眼泪与欢笑。当时过境迁,这些都变得毫无意义。而写作,是所有的“时过境迁”后,终于发生的事。
当我写作这本书的时候,我不知道自己是离童年更近,还是远了。
阿兰•罗伯—格里耶曾经说过:当人们写作自传时,重要的是人们自我想象他们的过去,他们自己的存在方式。
某种意义上,《童年不会消失》是一本关于童年的传记。它是另一种形式的自传。我想象着自己的过去,可能经历过的生活,我热衷于在文字中进行各种自我的搭建和拆毁,以完成一种虚构之目的。我在这本书里所经历的童年,比现实中所经历的,更具有一种完成的意义。好像此书的写作,对我贫瘠的童年生活进行了弥补和拯救。
关于童年,除了那些片段和残缺,我不可能知道更多;但有这些片段和残缺就够了。在写到那部分生活的时候,我感到自己是幸福的。人生和写作的旅途中,我们丧失了太多可能性,却保留下了其中一种。
《童年不会消失》读后感(三):关于《童年不会消失》的一些可行性猜想
文/ 刘梦
——有人执着向前,也有人迷恋过去。
历史的玫瑰总会把我们引向没有走过的通道,凡是过去,皆为历史。那就是说,我们所谓的回忆只是一些感觉,真实既是混乱又很模糊。
对草白本人来说,总是关于一些温情的,悲伤的传闻,这大概与她总是不断地,一遍又一遍不厌其烦地探索那些幽暗之地有关。她不用去追寻,一些道路会引领她到一些地方。在这些苦涩的道路之中,只有一些会让我们觉得既熟悉又陌生。那里就是童年。回忆或者爱的种种,充满了灰烬和温柔。
温情大概是我们最后的坚持。
过去到底是什么呢,我想知道它到底能告诉你什么,这比它代表着什么更为重要。假如把时间平展开来,就会发现在这一平面上,过去和未来处在相等的位置,生和死在同时发生,成长和衰老是同一回事。这总是相关的,没有人能抛弃其中一个,这是我们称之为生命,所组成的部分,有可能繁盛浩大,也有可能简单直白。
她似乎在发问,怀疑自己已经拥有的东西,就连对痛苦也不能肯定,只是她得不到真相,真相在过去的时间里是没有的。疑问把她困在里面,很难想象她的笔不会发生一点歪斜。是否真的是这样,还是说真的有此必要,她一遍一遍地写下一些事,不是同样的事,但总是那些人,差不多的人,存在过的人,后来又消失的人,她得不到关于他们的任何真相。那么,她就无法把她心中的真相说出来,告诉我们。她觉得她不再需要真相了,她只能写。
写,在写中制造答案,既然真的答案完全没有。在没有语言的地方说话。写,为了克服遗忘。这大概就是这本书所要尝试去做的事,很难说它做到了什么,遗漏了什么,这是一种对虚无之地的探索,要看到真实,就必须拨开一层厚重的迷雾。而想要看清自己比看清别人还要困难,无异于从海中区分一滴水,从火中取走一束固定的火。
我想说的,是这本书其实在创作上比它看上去要难,当然所有的创作都是艰难的,我只是想说明它并不是一本完全代表了实在和非虚构的一本书,它到处都充满了暧昧的时间的烙印。以及基于对救赎和自我救赎的误解,她觉得没有什么好怜悯的,她的看似悲怜的语言后面,都有一个冰冷叙述的意图。她只是在说,一些事实。而这事实,是她的心。
所有的一切都是基于她的,从开头时她早就知道了结尾,她可能想到某些时间,一些模糊的感觉,更多的是不确定性,似曾相识的感觉,对于某个事物的想法重新涌上心头,只不过,这件事物从此就带有了某种感觉的阴影、韵律和基调。故事发生了,故事又发生了一次。
在所有的时间里面,唯独过去的那些才是我们,回忆在不经意中前来,沉默的眼睛,松弛的嘴巴。干瘪的痛苦和遗忘的无助掺杂在一起,一旦开头,就紧紧地贴着悲伤前行。
现在的我们是过去的我们所有的集合。但是她却把它提了出来,穿过时间的内心,是那时候而并非现在这个时候,不是除此之外的所有时间。她放弃了用一个成年人的观念看待,因为她知道,不是这样。不是带着抒情的咏唱调,不是温暖。什么都不是,除了一些东西落进了深井,除了这天在下雨,而那天没有,除了死。
这些故事是她用一个孩子的角色写下来的,不去区分善恶好坏,不去总结,不戴着成年人的脸孔。在这本书里,只有一个叫草白的孩子,在说话,在害怕,在喜悦,在迷失。单纯就是单纯的人单纯而不自知。而一个单纯的人就在这文字里成长,思索。然后,她和你一样长大。然后,她就会和你遇见。
《童年不会消失》读后感(四):与童年相遇 ——读草白散文集《童年不会消失》
文 | 陈 峰
在2014年第二届储吉旺文学奖中,草白发表在《文学港》的散文《青鱼街》获得了优秀奖。此后,了解到她出生于三门,现居嘉兴,2008年开始创作散文,2010年开始写小说,曾获台湾联合文学小说新人奖短篇小说首奖。
阅读草白的散文,让人心情愉悦,她有着化繁为简的艺术能力。叙述简简单单,语言干干净净,带着植物的清香,就像把飘浮在半空中互相缠绕的事物一一拆解开来,归置在自己该有的位置上,恢复原始的样子。
《童年不会消失》是草白新出版的散文集,也是她的首部散文集,如她所言:“这册小书记录了我生命之初遇见的人,看到的景,度过的日夜。不仅是记录,更是回忆和虚构。”
童年是每个作家创作的精神源泉之一。草白以她敏感细腻的情感体验,丰富奇特的想象力,给读者复原了一段天真而神性的童年时光。
在《鹅》一文中,她这样描写道:“鹅是院子里老房的母亲养的。这位红眼睛的老妪,其家庭成员都温良顺从,唯有这只鹅跋扈嚣张。”读来让人会心一笑,当这只鹅啄了一个小孩子的额头,小孩子向老妪告状时,老妪这么说:“哎呀,我从来不知道,它那么喜欢啄人,我养它可不是让它啄人的。可它从来不啄我们的呀。我也没办法同它讲。你说我怎么能同一只鹅讲话呢?”这样的阅读体验是令人轻松且愉快的,文章短小而血肉丰满。
在《对它说》这篇中,描述了一棵枣树,因为结果子少了,祖父想要砍掉它,祖母忍悲大叫:“不要砍它呀,它知错了,它一定改!”就这样,枣树的命保住了,它肯定听到了他们的对话,觉得性命堪忧,因害怕产生了一种拼命结果的力量。果然下一年,枣树硕果累累,听话、乖巧到出人意料。
最后,作者发现,村里的树几乎都有被刀斧砍过的痕纹,“肯定是有几年,它们不听话了,言语吓唬不成了,给它们一点疼一点教训,让它们长长记性吧。”
草白总能从小事件或小场景中洞见世事人伦的真相。一棵枣树,在作者的描述下,拥有了听懂人类语言的能力,它和主人达成妥协。这种充满灵性的叙述,恐怕只有童年的视角才能发现和表达。
当下的散文经历着叙事的转向,这本书借鉴了小说处理中线条勾勒的简练手法,让书中的每个人物通过细节和对话站立起来,如傻女人、小贩、接骨人、苏州女人、做戏人、讲鸟语的人、乡村医生、哭灵人、关魂婆……他们以不同的样貌出现在村里,或荒诞或滑稽,或清醒或昏聩,他们走向读者,呈现了各自的命运遭际。
如《讲鸟语的人》,叙述了哑巴与他人的交流越来越少,与鸟的交流越来越多,渐渐掌握了鸟语。无意中她怀孕了,村里的人背着哑巴的男人,拉她去做了人流,因为村里有一个哑巴就够了。
“哑巴与鸟的交流越来越有兴趣,特别是那些候鸟,由于飞过许多地方,夹杂着各地方言而来,尤其值得她反复领悟、揣摩。因为对鸟语有意识地模仿,逐渐纠正了她在语言方面的弱点,她从没有如此得意过,原来自己的嗓音里竟藏着那么多秘密。”
作者似乎天生就有通灵的能力,擅于变形,把哑巴内心的“小确幸”用超现实主义的手法表现出来,其实这“小确幸”里,有无奈也有残酷。这样的叙述带上了魔幻和轻喜剧的元素,犹如一个寓言,意味深长。
生老病死是乡村的日常生活,书中记录了乡村中一些生命的消逝,草白用文字真实地呈现人在面对死亡时的各种情景,用词冷静节制,既展现了冷峻的一面,也有乐观的一面。
就像爷爷埋在地里的番薯,“只有吃到这些甜润、酥软的番薯时,我们才会想起,那些远去的人,那些走丢的事物,可能正在一个温暖如春的地方等着我们。”
或许,回忆本身就是一种虚构。可惜,有一些通往童年的道路被风吹散了。
原文发表于宁波日报,链接:http://daily.cnnb.com.cn/nbrb/html/2017-12/08/content_1086262.htm?div=-1&from=singlemessage&isappinstalled=0
《童年不会消失》读后感(五):灯灯:谈草白《童年不会消失》的自我救赎之路
文 / 灯灯
从“消失”到“不会消失”
——谈草白《童年不会消失》的自我救赎之路
一、
我很荣幸,作为《童年不会消失》的最早读者,甚至是还没有成书之时,关于此本书,我和我的朋友草白对此本书之间,所作的交流,以及它后来所呈现的秩序和修改,是在我期待之中,即:我可能会知它的面貌,它的出现方式,而我所不知的,是我再次面对它时,我以一个什么方式,存在,和言说。
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内,我没有对这本书作只言片语的谈论,我也认为,我是在等一个合适的时机,这个时机,是心灵的,也是际遇的。我也相信,一个人,哪怕是面对一本书,哪怕是面对书中,通往童年的路径,他,和她所面对的,也是自身。
所以,当我回到自身,当我,再次以一个读者的身份,重新进入草白所叙述的童年,我惊讶我的感觉和从前不同,我惊讶地发现,我现在的感觉,可能和之后,也会有不同。
我说的是,这是一本让人在不同时候,都会有新发现,和新领悟的书。
鉴于我的再次阅读经验,我希望读者,不要简单把《童年不会消失》当作对童年的追忆来读,一是在很大程度上或会辜负作者的潜在期望;二,基于我的再次阅读经验,我想说的是,或许我们可以,把它当作一种对存在的探索,一种真正意义上的顽强来读。时空变转,在地理和心理上发生位移的童年(或者过去所发生),我们应一种什么样的心态去相遇,和寒暄?
在很多时候,也包括现在,我固执的认为,相对于童年而言,童年草白一直在原地,她未曾长大,但她一次次被动接受长大的催促,她不知命运是什么,但她一次次认为命运不在此在,而在彼处。这个彼处,在我的想法里,是脱离现在(童年)的彼处,是无论如何,是和此处(童年)发生了心理和地理上的位移,而无论在哪,只要脱离了此在,它,很可能就是光亮的存在。
然而,为什么会这样呢?对彼处永远存在自己也说不清的向往?
与此同时,我也固执地怀疑,我的朋友草白,为什么要脱离“此处”而寻找可能存在可能不在的彼处?在“此处”和和“彼处”之间,救赎之路在哪?回到此书上来说,童年消失,和童年不会消失的自我救赎之路在哪?而我尊重她所有的努力(包括潜在,包括从未有潜在,而是我一厢情愿的解读)此书出来以前,我也以为是她把自己留在了原地,记忆的原地,童年的原地。在整个童年之中,少年草白懵懂无知,但有形的的问题,在多年后成年草白身上,都有了回应,都有了口吻。
二、
如果我说,我以为此本书的出现,是这么多年来,成年草白,对自身的一个回顾和清算;如果我又说,在童年草白懵懂之时,已有一个成年草白在多年之后在等待,如果我继续说,这么多年,我的朋友草白,一直在等一个合适的时机,对童年慌乱、不自在、恐惧、害怕、想要逃亡又对未知不安、向往,同时在充满无限问询和期待的自己之间,寻求一条自我力量救赎的道路……那么你呢,你怎么看?
三、
事实上,在很长一段间内,我以为是有一个童年草白需要被救赎。我以为的是,在并不温暖也不美好的童年之中,作者草白(特指童年草白),一次次经受着相同乡村命运的洗刷,这种命运在草白记忆中,不温情,甚至也没有多少美好可言,然而,正是这种不温情,甚至也没有多少美好可言的记忆,使童年草白的形象定格了,即恐惧、害怕、不知所措、想要逃亡……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在此书出来之前很多年内,我以为成年草白之所以不知疲惫的做着同一件事,即一次次往返于记忆和想象混合的童年乡村,一次次靠近童年中黑暗的自己,是期待多年后有足够的力量,将童年的草白实现一次真正自我意义上的救赎。由此,童年的草白才在黑暗中真正消失,而相对于“真正消失”而言,因为“已消失”,才“永远不会消失”了,“童年”因此稳固了,相对意义上的绝对意义,显示出悲怆的底色。
在那么长时间内,我为我的发现,心生悲凉,或者欣慰。后来我发现,我错了。
四、
是的!我必须承认我错了。而此书所探讨的,即使是我在标题之中,所说的从“消失”到“不会消失”,即使是“童年”,我想,即便是再仓促的读者,也可能体验到从“消失”“到不会消失”的多重意义。回到此本书上,与其说“童年不会消失”,不如说“死亡不会消失”的延伸追问,不如说,是童年草白,在所看见、面临的乡村事物中,面对一次次次死亡,在童年的黑夜中,所睁大的双眼。
而我们会在她疲惫稚嫩的双眼中,看到各种消失:比如,狗是被人活活鞭死而消失的;水池边的亮光,是因为殉情少年男女而闪亮,闪亮之后也消失了;然后是爷爷的消失、唱戏的人的消失,然后是作为劳动者的父亲不知所踪……然后,然后是譬如朝露的,“凤”的消失,语文俞老师的消失,在宿舍外,喊着我(作者)的名字,男孩的声音的消失……
那么,这一连串的“消失” ,意味着什么?那么这一连串的“消失”,因为“消失”而不可能再“消失”了,意味着什么?这之间,是否存在我们所希望的,愿望的救赎之路?
如果我们把这些发生的事,认定为童年,它就是童年。如果我们把它认定为更远一点,在时间和空间,更远一点,或者我就可以说,在此书中,与其说对童年的追忆,不如是说对死亡的清点……在草白笔下,乡村是突兀的,典型的、戏剧和寓言的;草白的乡村,具有普遍意义,但又超越了普遍意义,这可以是任何一个人的乡村,有过乡村经验的人,都可找到它的原形,比如疯女人,念经的祖母,比如叛逆的哥哥,比如棺材匠……所有的人物,是亲人也是陌生人,是远亲也是近邻,所有的人物,都像一个个乡村符号,通过各种变形,凝聚和汇集,形成扑面而来的,对死亡的熟悉和亲切,亲人的死,朋友的死,乡邻的死,最后,它一定会形成和作者草白一般的追问和怀疑:“从消失”“到不会消失”,我们的童年存在过吗?我们存在过吗?我们应该如何存在?
五、
我无法想象多年后,我的朋友草白,是以多大勇气,再回到童年?事实上一个人回望童年及童年的故乡,童年和故乡已不在;当作者草白,在对童年乡村的事物,亲人的回忆,已越过普通意义上的追忆,而带着思虑的勇气,而带着怀疑,以一种成年后的清醒和冷峻,再次回到不逃避也不愿逃避的乡村之中,无论是亲人或是乡邻,又或者是一株树,当它们在作者的记忆中不断修改而死亡也飞速的转换着虚构和现实之间的镜头,那些变形,典型,突兀的乡村人物,一个个的面对死亡本身,死亡熟悉地像一个邻居,再也不是那么可怕,甚至在某个时辰暗淡地发光……直到所有人和死亡为邻不自知,被命运捉弄,也不自知,直到死亡以一种邻居的身份出现,成年的草白,无所知但已知,无所解但求解,她不温情,也不怜悯,甚至对自身也是如此,也显露出草白在此书中所探寻的一条路:一种迷茫,冷静,淡漠,渴求,对望并不对峙,对村庄中人性无知的批判,和对自身不可知的救赎之路。
六、
而最后。仍有一个追问:对存在而言,从“消失”到“不会消失”,除了死亡本身,永远也不会消失了,救赎之路在哪?
《童年不会消失》读后感(六):童年不会消失,死亡也从不缺席
文/邹汉明
南方大多数的乡村,其实类似。不仅村庄的布局类似,包括村庄最主要的内容——人与人的关系、人物的命运也大多类似。因此,作家记录一己的村庄,一己的童年,仍无可怀疑地具有普适性。而这种普适性,总归是文学得以优良存活的一个因素。
一个有过乡村童年生活的人是幸运的。我把草白归列在这少数幸运的作家里头。草白这个笔名,就来自乡村,有一股南方乡村蓬勃的青草的气息。
与大多数回忆性散文一样,草白回望过去的时候,首先想到并开始记录的,是她童年的村庄。不过,她与其他作者还是有着根本的不同——她不面面俱到,她做减法而不做加法。她甚至没有给这个书写了一本书容量的村庄一个名字。她以沉思、探寻的笔调,专把村庄中最主要的元素——人以及人的命运抽离、呈现到读者面前。换言之,她以小说家最擅长的处理人物的方法,去处理她在这个村庄所经历的童年,特别是去处理他们的死亡。
小说家的着眼点首先是人,草白在处理人的时候,从来没有回避罩临在人物身上的死亡。书名“童年不会消失”,某种意义上,其实是一种反话。草白不是说“如今,所有通往童年的道路都被风吹散了”吗?但我知道,还有一条道路,始终没有“被风吹散”,那就是每一个人的宿命——死亡。死亡这个词很突兀,但它是回避不了的。作家也无需回避。草白说童年不会消失,这句话的后面,应该还有一句:死亡也从不缺席。草白与我一样,都来自村庄。当我们走出村庄几十年,回顾头去一看,那些我们熟悉的左邻右舍,这会儿不是全变成了黑乎乎的墓碑吗?这就是一个“被风吹散”的人世啊。
草白在处理人的死亡、人的命运上显现出来的力量和分寸感,在这一代年轻的作家中非常少见,这使得她的作品整体上给人一种冷峻的色调。草白行文干脆果决,不黏不滞,语言中带有沉思的品质。她叙述的调子冷静而苍凉,同时也保持着自己的语速,有着刀子切入皮肉的狠劲。读完她的新著,其中的不少篇章,说出来简直吓人一跳,不过十万字的篇幅,弥散开来的死亡意识,就像这本书的黑色封面一样浓烈。
小说家着笔死亡、处理那么多的死亡,我以为是有原因的。如果不是偏见,那么,没有理由不相信作者的话,所谓死亡,用草白自己的话,就是“人物自身命运的呈现”。这多少让我想起多年前抄录的达·芬奇,西方的这位大艺术家对于死亡有过一次很有智慧的表达:过去我以为自己是在学习生活,其实是在学习死亡。这里,死亡与生活,构成了一条线段的两个头。不用说,对死亡的关怀大抵来自对于生活的看重。说到底,掂量死亡这个词,需要作家拥有强大的内心。很高兴,这些年,通过阅读、写作、思考,交游,草白的内心涵养了文学真正的力量。
幸运眷顾草白。但草白也有她成长过程中刻骨铭心的不幸。也许正是这种不幸,她才那么敏感于死亡的追述吧。我隐隐约约知道,她的父亲,很早就得病去世了。认识她多年,也并不曾听她讲她的父亲。早年聚会,大家也刻意回避这个话题。好在时隔多年,我们终于看到草白自己站出来讲述她的父亲了。长文《劳动者不知所终》中,草白记录了父亲的几个镜头:永远戴着假领子,后来是穿着散发黑色橡胶气味的蓝色工作服。草白的父亲像乡村所有的父亲一样,也喜欢参加牌戏赌博。而这个曾经挑了最好的柿子给了女儿的父亲,终于因生计而把一条命交给了一家有着严重污染的橡胶制品工厂。草白通过追述父亲其后的离世,认识到今天这样一个具有哲学性的命题——“人居然必须要通过一份工作才能活下去,这个事情包含了人生绝大部分的荒谬。”《劳动者不知所终》一文,也因此蕴含着对于父亲这个劳动群体的人文关怀,作家对于这个群体的生存境遇是有所控诉的。当然,草白冷静的叙述,内省,使得她笔力下沉——好在草白在沉思中压下了对于存在的愤怒。她的文字世界,由此也有了她自己的零度呈现。每一个读者,都可以在她沉思的叙述里找到自己的答案。
作为女儿,草白对父亲有一种骨子里的亲近。很多年过去,她“还是无法接受父亲已经死亡的事实”。偏偏,命运取走了这份亲近。从此,也难怪草白“所有关于父亲的梦都笼罩在死亡的阴影里”。须知,任何一个父亲的死,都是发生在一个家庭里的大事。草白通过《无边的寂静》一文的写作,直接写下了对于重病以及弥留之际父亲的记忆。这时候的草白,有力量也有能力写下她生命中那一段残酷的记忆。她把这一生目击到的最重要的一次死亡经历勇敢地描绘出来。她写得克制,冷静,文字里没有掉泪,甚至没有悲戚,但我相信,一定有泪滴掉落在她心里,只有在这样的一滴泪中,死亡被一秒钟一秒钟地放大。死亡历历在目,必须面对。这里,我仍读到一个女儿对于父亲的痴情:“我没觉得父亲已经死去……真实的父亲仍在另一个世界里完好无损。”我曾经读到中勘助描述他亡姐的文字,草白描述父亲的死,不比中勘助逊色。这是可以泣血的文字,是人生的不幸换来的一座文字的纪念碑。
乡村不仅是由活着的人构成的,同时也是由众多的亡灵构成的。抵达童年的路有无数条,通过追述个体的死亡而抵达童年——特别是抵达童年的恐惧,这当然是便捷的一种,而且是很文学的一种。书中描述爷爷的死、外婆的死、舅舅的死、表哥车祸而死、同学自杀而死、捕食者被蛇咬死、父亲的牌友岳的老婆喝农药而死、父亲的票友凤罹患子宫癌病死、恋爱中青年男女的死……以及村子里其他男人、女人、小孩、乞丐的零零总总的死,这些触目惊心的死,在草白的书写中,都是活生生的,并非向壁虚构。死亡的镜像也丰富了草白作为一名作家最锐利的乡村经验,在很多人试图遮遮掩掩的地方,草白勇敢地把它说了出来。而关键是,她说得那么好。这一点,我以为关乎她的创作观念。草白曾固执地认为,她这部书“不仅是记录,更是回忆和虚构”。在草白是观念里,记录(纪实)与回忆是对峙的,有区别的,那么,她应该是把回忆当作创造来看待的吧。至于回忆是不是虚构,限于篇幅,这里就不再展开了。
死亡收割一切,也保存一切。死亡白色的质地,构成了这部童年视觉的录鬼簿墓碑一般坚硬而沉甸甸的分量。爷爷、奶奶、外公、外婆、父亲、母亲以及七大姑八大姨,这些真实的乡村人物,在书中自有他们自身命运的呈现。草白的乡村,草白的童年,草白的汉语,包括她挥霍的汉语里的痛楚,由此鲜活、生动、具体——也不会再消失了。
2018年2月26日
《童年不会消失》读后感(七):另一种童年叙事 ——读草白散文集《童年不会消失》
文 | 郑润良
与同代的其他作家相比,草白出道时间算是比较迟的。2008年草白开始写散文,10年开始写小说,至今已成果颇丰,以鲜明、独特的个人风格赢得普遍的赞誉。
《童年不会消失》是作者的第一部散文集。在一次访谈中,草白曾将自己写作的初始契机与自己生育后的思考关联起来,“天亮时,我得以解脱。好像死里逃生。后来,我一直想,那个清晨的空虚感所为何来。显然,俗世生活中最重要的事情都被我提前完成了。我还能做什么呢?还有什么更有意思的事情在等着我?如何从泥淖般的俗世生活中脱离出来进入一种精神性的创造中,哪怕只享片刻欢愉,这是我一直以来苦苦思索着的。或许,写作是我命定的职责,之前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有一天让命运之神来启动它。它是我藏在我体内秘不示人的暗器。如果说一个人写作必须得有点理由的话,这就是我的理由吧。生活如此虚空,时光转瞬即逝,在平庸喧嚣的人世纷争中快速耗尽这一生,并非我所愿。写作或许是我能找到的最好的精神衣钵,它保护着我,慰藉着我,让我不再那么害怕时间的流逝。”
从这段写作自白中,我看到了两点,一个是草白具有一般写作者所不具备的面对内心真实的巨大勇气。一个刚刚成为母亲的女人不是想着如何哺育刚刚来到这个世界的儿女,反而希望从泥淖般的俗世生活中脱离出来。这种叙述迥异于“伟大、无私”的母爱的相关叙述话语,让我们与一个作家的灵魂深处直接相遇。同时,也可以看出草白的叙述不是那种滥情的叙述,她的文字是节制的、简约的、带有内在的自省和朴素的风格,她不会让自己进入各种约定俗成的情感鸡汤叙述中,而是会引领读者冷静面对人生与现实的真相。这两点在她的新作《童年不会消失》中得以淋漓尽致地展现,我们也因此得以看到与主流的叙述方式不同的另一种的童年叙事。
与我们通常所看到的温情脉脉、诗意化的童年叙事不同,《童年不会消失》让我们看到的是一个贫瘠、苍白甚至带有几分阴郁色调的童年,‘’死亡”是其中的一个关键词。
《暗杀》记录了童年的“我”虐杀小生命的过程,“那些在池塘里挣扎蚂蚁,多半是被我遗忘掉的。除了死亡,它们没有别的出路。我还杀死过打盹的苍蝇,疾走的甲虫,更多无名的生物,被我伸手一抓,命运从此改变。……我杀死一个生命,无数个生命,如此轻易,却毫无愧疚之情。”
一个乡村儿童之所以如此轻率地对待小生命,或许是因为对周围“死亡”事件的耳濡目染,使她已经习以为常。死亡是乡村的日常生活。这部书记录了许多乡村生命的折损与消失。
“我的活泼开朗的女同学忽然自杀了,她的尸体被人从水库里打捞上来,僵硬的手掌里居然握着一根纤弱的水草。” “那些和我们一起上学的人,有一天,忽然不来了。她们或者自己病了,或者家里死了亲人,来不了了。小娅的眼睛被班里男生的铅笔芯戳到,去外地看病,病是看好了,却再也没有回到我们身边。菊的母亲喝农药死了,她要在家里照顾瘸腿的父亲,还有弟弟妹妹,也不来上学了。” (《十月的罂粟花》)
“那些肉体与精神的隐忍者,等到忍不下去的那天,再来白房子找他时,已经无可救药了。而那些经常光顾白房子的人命运也好不到哪里去。因为各种药片和针剂的长期入驻,他们的身体早已岌岌可危……村里人慢慢知道,一个人的死亡与疾病无关,与医术无关,如果他必须得死,那有什么办法呢?”
在贫瘠的乡村中,死亡无处不在。还有被残忍打死的狗,“那天,她去了集市,等她回来的时候,只看到一截血迹斑斑的铁链锁被丢在门厅外头。据邻居说,杀狗之人缺乏技术,整个过程持续太久。这狗是被活活鞭死的。这之后,我们家再也没有养狗。”(《狗》)正如《死神派来的人》一文结尾所言,“在强烈的生中,无时不在的死的阴影,等在暗角,如觅食者遇见他的食物。”
在面对这些带有几分阴郁色调的乡村图景时,作者的笔触是格外冷静的,乃至于有意使自己保持在一种“零度写作”的状态中,不轻易流露自己的情感。比如,面对父亲的死亡,“我没有觉得父亲已经死去,我什么感觉也没有。眼前的冰柜,冰柜里躺着的人,人脚下的长明灯,以及时不时地会爆发的哭泣声,都和父亲没有关系……我当然没有悲伤,甚至不知悲伤为何物。”从某种意义上说,草白的文字让我们联想起萧红对乡村“生死场”的冷静而瘆人的描述。二者在书写题材与风格上的相似之处使我们不能不感喟百年来乡土社会中底层人群的命运的改观依然是一个无比艰巨的过程。
但是,死亡在草白笔下也有暖色的一面,比如爷爷的死,“三十年了,一个洞穴无声无息地等在那里,等着每年清明节那个垂垂老矣的人来给它锄草、斩棘、上供,直到那个人被敲锣打鼓的人群抬到这里来。”(《给自己扫墓的人》)这是一种安详的死亡,也表现了乡土生死伦理中达观的一面。
这无疑也是乡土伦理中最具生命力与想象力的一部分,就像爷爷埋在地里的番薯,“只有吃到这些甜润、酥软的番薯时,我们才会想起,那些远去的人,那些走丢的事物,可能正在一个温暖如春的地方等着我们。”
《童年不会消失》记录了童年记忆中乡土的残酷与诗意。记录是见证,也是一种再造。“童年不会消失”,那些在乡土消失的形形色色的人和物以文字的形式得以铭刻,他们不会消失。“在驾驭这些篇幅不等的文字时,我的确感到过一阵短暂的欢乐。或许,这是我在这个世上唯一能拥有的东西。”文字的真正价值,恐怕就在这里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