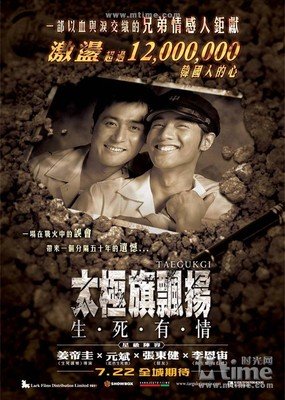
《什么是电影叙事学》是一本由戈德罗著作,商务印书馆出版的245图书,本书定价:17.00元,页数:2005-10,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什么是电影叙事学》精选点评:
●很理论性的理论读物,适合深度研究的电影叙事学。
●可惜的是没时间仔细看,就只能草草还了。
●其实可以不必如此晦涩
●终于读完了,理论并不算特别难懂。影视叙事学的早期作品,奠定了一些基础概念。
●不错的电影叙事学书,逻辑清晰
●若斯特在热奈特、麦茨和拉费的基础人对电影叙事学的重要问题一一进行梳理与回顾,在借用热奈特的文学叙事理论和麦茨的大组合段理论的基础上提出了对于影片叙事分析的重点:空间、时间、词语和画面以及视点问题,解析了叙事学常用的两种分析方法,深入浅出,大量实例。
●在热奈特和麦茨的基础上推进的工作。“大影像师”,是否需要在叙事学中引入这种“拟人化”?分析“最后一分钟营救”的时间性和空间性是一段极有启示性的尝试。“叙事的时间性”一节可加入对歌舞片/印度电影程式的探讨。对“听点”/听觉聚焦的部分可以再延伸。
●好的理论读物就该从艺术本体上考虑问题,对术语进行精确地辨别和使用,不混淆,不臆造,不为理论而理论。一本薄册子,基本上涵盖了电影叙事学的所有问题,考虑到了每个方面的多重性,举例偏重生僻的欧洲电影,理解起来略有障碍。
●许多区分都是为了理论而理论,实际上意义不大。
●如果滤出重点,就很简单。 而言要全读懂,未必太难。
《什么是电影叙事学》读后感(一):声音与画面,双重叙事
想起来看并寻找到这本书是想搞明白 两个让我觉得神秘的东西:一是蒙太奇神奇的表达能力,这是属于画面的;二是声音与画面在一起叙事时神奇的化学反应。这种直接而明确的目的让我憧憬一次充实而顺利的思想旅行。
不过,进去以后,才发现:关键还是“叙事”。而阻碍我理解的,好像是我们的教育。教科书上充满铺陈,而不是富有诗意的简洁;老师们擅长演示,而非叙事。我现在甚至觉得,我们都很难拉开一段距离去欣赏一段漂亮的叙事,去体味心灵与媒介之间的化学反应过程。
看这书,像是 在吐出教育对心灵的毒素。
《什么是电影叙事学》读后感(二):笔记
叙事学:
托多罗夫:主题叙事学,关注被讲述的故事、人物的行动及作用、行动元之间的关系
热奈特:语式叙事学,关注人们讲述所用的表现形式,叙述者的表现形式,作为叙事中介的表现材料(画面、声音、词语),叙述层次、叙事的时间性、视点。
什么是叙事:一个完成的话语,来自于将一个时间性的事件段落非现实化。
1. 一个叙事有一个开头和一个结尾,整体性与无穷无尽的现实世界对立
2.双重时间段落:事件时间+叙述时间,画面——描写——叙述
3.任何叙述都是一种话语,对叙事的感知使得事件非现实化
什么是电影叙事:
画面不等于单个词语而是一句陈述;
电影画面的含混性,很难用一句陈述概括,因为画面show instead of telling。
电影诞生之初:单一镜头,地点、时间、行动三一律
电影处于书面叙述和戏剧演示之间:
不是完全narration,也不完全是演示monstration:不是同时性的演示;摄像机的运动可以约束和引导观众的视线
多重叙述:
电影的复调性:电影的基本叙述者、大叙述者的声音与第二叙述者即次叙述者的声音的重叠没有一定之规,展现出话语的多样化。
基本叙述者即影片的交流负责人是一种机制,操作各种表现材料对其作出安排,组织叙述方式,向观众提供各种叙事信息。
《什么是电影叙事学》读后感(三):电影,叙什么事?!
终于又把《什么是电影叙事学》读完一遍。这是读第三遍,读起来还是那么兴致盎然。好书确实是经得起一读再读的。这虽然是一本本薄薄的小书,但却把电影叙事学的关键问题讲得一清二楚,两位作者(安德烈·戈德罗、弗朗索瓦·若斯特)探讨了电影叙事的双重性特点、电影叙事的研究方法、词语与画面的关系以及空间、时间和视点等基本但绝对重要的问题,对每一个方面,作者都给出了细致入微又非常令人信服的解释。汉语电影学界涉及叙事者甚多,但似乎大都懵懵懂懂纠结不清,没见到哪位在电影叙事方面做出比较到位的和有说服力的研究。所以,对叙事学和电影研究感兴趣的同学,都可以读读这本小书。本书的译者刘云舟曾留学法国,认识作者之一,又以电影叙事作为其博士论文主题,他的翻译很值得信赖。
本书的两位作者谦虚地表示,他们不企求详尽地探讨所有可能的叙事学研究的领域,期望读者在他们止步的地方继续深入下去。下面这几段文字抄自结语,值得我们思考和学习:
“一个书写的叙事绝不是一个电影的叙事。对此,只要一个理由就可以说明,前者是单一性,后者是复调性的。这个平庸的确认并非对研究部发生影响。怎样谈论电影的‘叙事’?电影叙事者不直接显现出来,而处在隐蔽的状态下进行引导。‘视点’在一本小说中可以具有什么含义?无论如何,小说都不能直接运用目光。只有通过不同媒介之间的不断比较,这类问题才能得到答案。例如,电影因为演示行动与戏剧类同,因为使用言语与小说相似,如此等等。但这种戏剧性,或言语性的系数在影片中有所变化,就因为影片同时运用多种多样的表现材料。所以,这些比较不能脱离符号学对材料的思考靠来进行,这在叙述、空间、时间和视点的阐述中已经涉及。
结果,小说研究领域所建立的某些概念显然需要重新探讨,例如,影片分析将聚焦分为认知的、视觉的和听觉的聚焦。返回也是合理的,文学叙事学需要在晚辈电影的推动下开展新的探讨。其实,这就是我们应当得到的教诲。今天,不再可能固守于边界确定的研究领域,叙事学理应是比较的,在于不同媒介的对比中向前发展,否则,它就没有存在的理由。当然,这一观点遭到一些抵制,这是因为电影在某些人的头脑中依然只是一种纯粹的娱乐,即使一些非常有见识的人认可某一学科可以‘严肃地’谈论电影,也很少从谈论电影的学科那里借鉴一些此学科所创建的模式。然而,必须对此习以为常:概念的完善只能依靠在不同的对象上检验这些概念的有效性。文学叙事学对电影叙事学的成果加以再思考,并用于自己的分析会有很多收获。就像索绪尔认为语言学只是符号学的一部分,文学叙事学也只是叙事学的一部分。同样,电影叙事学理应考虑其他视觉艺术和形象表现的叙事学发展,例如,有关戏剧的,或者连环画的叙事学。”
《什么是电影叙事学》读后感(四):《什么是电影叙事学》读书笔记
l 前言
作者在前言中就提到了符号学与叙事学的关系:符号学在电影领域的最初发展正是受到叙事学问题的一些“传染”,就像麦茨所说,电影将叙事性“深深嵌入自己的体内”,这很快把他引到“虚构故事”的道路上。不过,麦茨的主要目标介于巴赞的传统和语言学的模式之间,旨在表明电影中的世界怎样成为话语,也就是思考电影画面的符号学属性,因此,麦茨更加注重思考电影语言的表意能力,较少思考电影所显示的讲述能力。
术语“叙事学”是托多罗夫于1969年提出来的,但更多归功于热奈特,他将其提升为显贵的学科。
初期影片是单视点的,意思是只有一个镜头,无论它们展现什么叙事,都很少是一种完备形式的叙事、一种充分建构的叙事。
“互介性”概念:重新阐明电影与接受它的其他媒介进入新世纪所形成的关系。
电影理论上的两个著名对立:叙事性——戏剧性。
列举了两个研究者不同的研究范围和方向,得出结论:两个研究者在以下问题上具有一致看法:叙事学对于理解影片的叙事是必要的,然而它还应该以其他学科的研究成果不断的充实自己(例如历史学),并且见自己的目光投向电视或数字画面这样一些新的研究对象。
l 导言
课前思考:
电影叙事问题:电影怎样讲述一个故事?
叙述问题:谁说?谁讲述故事?
词语和画面的关系问题(通常来说是视听关系问题):怎样从书写的叙事转变为视听的叙事?
讲述事件的视点问题?
如何表现事件的时间长度?
什么逻辑支配这种闪回类型?
电影的时间性是怎么运作的?
【希望看完这本书你会知道,不然你就白看了!!!羞愧不羞愧!】
l 一、口头叙事、书写叙事、影片叙事
举例:病人向精神分析学家讲述他的一段童年经历
这是一个比较简单的情形,从叙述方面说,建立在两个人面对面的基本配置上:一个人叙述(这是叙述者),另一个人倾听他的叙事(这是受叙者)。
为什么说它简单?因为它假设只有一个明现叙事者和只有一个叙述交流活动,当两个对话者面对面的时候,这一活动就在此时此地发生。面对面的在场是口头叙事的基本特征之一,它在互相在场的一个叙事者和一个受叙者之间运行,这就使它有别于小说这样的书写叙事。
【书写叙事与口头叙事的差别:】
与书写叙事不同,口头讲述是直接和即时的,这意味着它既是“立即”、“同时”发生的,也是“无中介”的。书写叙事一方面是以“迟到的方式”传到读者的,因为它的接受和它的发送不在同一时刻;另一方面,这是通过一本书/一份报纸的中介而读到它的,这是一种媒介传播,来源于一个事先的写作行为。
所以,口头叙事是在现场进行的,而书写叙事与影片叙事一样,是不在场运作的。
口头叙事
直接的、即时的
无中介
在现场进行
书写叙事
迟到的
媒介传播,有中介
不在场运作
在探讨叙事学这门科学时,应当注意这些叙述机制的区别。例如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古希腊时期,几乎任何叙事都以安排讲述者和听讲者同时直接地在场为前提。
l 二、叙事学和电影
热奈特借用托多罗夫的“叙事学”术语,把自己的叙事学称为“语式叙事学”,它有别于“主题叙事学”,按照同样思路,我们可以区别表达叙事学和内容叙事学。
类别
关注点
领军人物
表达叙事学
关注人们讲述所用的表现形式为主:叙述者的表现形式、作为叙事中介的表现材料(画面、词语、声音等)、叙述层次、叙事的时间性、视点等
内容叙事学
关注被讲述的故事、任务的行动及作用、“行动元”之间的关系等等,倾向于关注叙事的内容,完全独立于表现形式
【对于这一研究领域,任务的行动由影片的画面和声音、还是由小说的词语来表现通常并不重要,甚至可以忽略不计】
格雷马斯
麦茨:“有两种不同的研究,它们不可以互相取代:一方面是我们尝试的叙事影片符号学,另一方面是关于叙事性本身的结构分析,它将叙事当作是独立于运作载体的(影片、书本等)。……被叙述的事件,对于叙事载体符号学(尤其是电影符号学)”是一个所指,对于叙事性符号学就变为一个能指。”
本书关注语式叙事学,是表现形式叙事学。这是依据我们给予中介载体的优先地位:叙事首先通过某一中介被赋予形式,然后才呈现出来。电影/视听整体的中介不同于文学/连环画的中介。
l 三、结构主义浪潮的一份遗产
历程:
叙事问题和所谓的“叙事性”的问题在60年代由列维·斯特劳斯推动的结构主义思潮的进程中,吸引了像热奈特、托多罗夫、格雷马斯、麦茨以及罗兰·巴特、布雷蒙河艾柯这样的研究人员的兴趣。这一时期,也发现了普罗普的重要著作:《民间故事形态学》
麦茨:电影如何表示连续、进展、时间的间断、因果性、对立关系、空间的远近等等,这些都是电影符号学所面临的中心问题。
l 四、先驱者之一:阿尔贝·拉费
拉费对叙事下的定义建立在与“世界”的对比上:
1、世界无始无终,相反,叙事是按照严密的决定论安排的;
2、任何电影叙事都有一个逻辑的情节,这是一种“话语”;(可以参考今天我讲的悬疑片里说的,每一种类型片都有故事线,悬疑片有故事线和逻辑线)
3、叙事由一个“画面操纵者”、一个“大影像师”安排;(拉费用“大影像师”这一概念表示操作画面的机制,指一个不可见的叙述策源地,不是指一个具体的人或人物)
4、电影既表现又讲述,与仅仅存在着的世界不同。
拉费认为叙事与现实的世界是相互对立的。
l 电影与叙事
我们认为大多数影片就是在讲述,然而我们到底是依据什么来辨认叙事的呢?
作者一开始就抛出了这个问题,然后举例麦茨提出的识别叙事的五条标准:
l 一、什么是叙事?
1、一个叙事有一个开头和一个结尾
任何作为产品的叙事都有“终结”,当然,有一些影片会暗示后面的发展,连续剧或者像一些美国大片如《星球大战》、《洛奇》等,就避免回答观众提出的所有问题,而设置一些不确定的线索,以便能够据此组织新的故事;也有一些影片将我们带回到出发点,让我们处于一个没有重点的螺旋状态中,如《不朽的女人》;还有一些影片看起来只是在更佳包罗万象的事件整体中抽取一部分行动系列让我们看到,如《马耳他之鹰》。无论悬置的结尾还是循环的结尾,都好不改变作为产品的叙事的本性:任何书本都有最后一页,任何影片都有最后一个镜头,角色人物仅仅在观众的想象中才能继续活下去。
对应标题,即使一部影片明显的装作以截取和讲述一个人的数小时生活为目的,这一段时间过程也还要服从一个安排的顺序,至少要假设一个起点和一个终点,很难与我们的实际生活顺序相吻合。
《游击队》中,女主角以寻找丈夫作为开头,以“偶然得知丈夫已死”为结尾,这里的“偶然”绝非意味着给我们看到的是一个“未经加工的现实片断”,如果“这一叙事线索的单纯性丝毫不归功于经典结构方法”,它也远非一段截取现实、如实记录的“报道”。“偶然”的对话出现在结尾这一事实并不比开头的相遇更加意外,它们两者构成叙事的统一性。
【这个我不太明白,大概能理解是说“即便故事中再怎么偶然,其实都是必然的安排”】
为什么说叙事与现实的世界相互对立?
因为叙事形成一个整体(亚里士多德:有一个开头、一个中段和一个结尾),这一整体语影片本文相一致,影片本文构成一个“事先的、实有的话语单元”,应该强调指出,对于麦茨来说,首要的正是产品的整体性和统一性。
2、叙事是一个双重的时间段落
任何叙事都调动两个时间性:被讲述事件的时间性,属于叙述行为本身的时间性。【这不就是故事时间和叙事时间嘛】麦茨认为应该区分“事件所经历的顺序时间”和“阅读能指段落所用的时间”。后者“对于一个文学叙事是阅读所用的事件,对于一个电影叙事是观看所用的时间”。
从这个角度来看,可以得出:叙事的功能之一是在一个时间中处理另一个时间。叙事有别于描写(在一个时间中处理一个空间),也有别于画面(在一个空间中处理另一个空间)。
麦茨用电影叙事来表明这三种可能性:【麦茨我懂了!麦茨我爱你!】
1)广义上的叙事,作为我们所说的本文,可以包含描写。描写不是叙述,因为描写没有满足双重时间性的标准。描写的身份很特殊,它们既占有叙事时间(它们的能指被时间化),又只对空间才有价值。所以,叙事中既存在叙述,也存在描写。【例如沙漠切了好几个镜头,这就占用了叙事时间,但这几个镜头也仅仅只表现了空间】
2)这种能指的时间化(就是叙事)将叙述和描写在一个共同的范畴里结合起来,又使它们与画面相对立,画面是瞬间的,是人们固定下来的一个“时刻”。感知一幅描写的画面,不也是要求一段观看的时间过程吗?这一时间过程就置身于能指中。
对于符号学家来说,电影中可能存在一些先于叙事活动的时刻。
3、任何叙述都是一种话语
麦茨用“话语”这个概念表示拉费所说的叙事与现实世界相对立。符号学家认为,现实世界是无人述说的,而叙述则是一种话语:由陈述句组成的一个系列,必然会反映出一个陈述主体,这并不意味着任何话语都是叙事,人们可以为了辩论、证明、教学而说话。
叙事也不是与我们无关的存在物,它是由一个“讲述的机制”,就是拉费所谓的“大影像师”表述出来的。在任何叙事中,这个“讲述的机制”被“必然地感知”,它就是“必然在场的”。在某种程度上,对大影像师的感知相当于它作为陈述主体的存在。
4、叙事的感知使被讲述的事件“非现实化”
如果“现实”是无人述说的,它更有理由“永远不讲故事”。就是说,当我涉及到叙事时,我知道它不是现实。有一些小说或影片取材于真实的故事,但麦茨认为观众绝不会将它们混同于现实,因为它们不像现实那样,处于这里和现在。【讲述肯尼迪被杀案,就是把它当作已经脱离当时的过去事件,在电视上解说一场比赛,就是把它放入远离它的另一个空间、一个他处,这也是创造一个想象的地形图,将一些异质的地点在同一时间联系起来。无论如何,这些都不再是现实】
5、一个叙事是一系列事件的整体
麦茨将叙事放在它的整体中考察,把它看作是一个完成的话语,其中事件是“基本的单元”。【当人们试图概括一本小说时,无论采取何种方式,单个的词语显然不够用,需要一系列用分句组成的复合语句】
电影画面更加符合一句陈述,而不是单个词语。
麦茨认为:叙事是“一个完成的话语,来自于将一个时间性的事件段落非现实化”。
l 二、什么是电影叙事
把镜头看作类似一句陈述的话,就允许像分析其他叙事一样地分析它。然而,当人们试图确定画面里存在什么陈述句时,又将出现一些困难,任何镜头都不会说:“XX死去。”
电影画面很难只表示一句陈述,正如人们在试图记录一个镜头包含的可见信息时所体会到的。【指的是,一幅画面、一个镜头的信息可能需要用一系列陈述句加以描述】
任何镜头都包括多个潜在的叙事陈述,它们互相重叠,也有可能互相包容。【例如一个镜头中XX死了,他是假死?真死?在表演?下一秒会不会起来?他被杀死的?自杀的?等等……】
对视觉画面作类似的语言学描述,困难在于“画面展现,而不述说”【我的理解是只有画面,没有旁白和独白】,在这样的条件下,人们才可以思考电影镜头是怎样表意和讲述的。
麦茨认为:1)首先要理解运动的画面如何表意——运动的画面可能先于叙事(参见以上沙漠的例子),由此引出另一个问题:2)直到何种程度,人们可以接受电影是一种语言?正是为了将电影与言语相对立,符号学家才竭力表明任何镜头都不等于单个的词语,相反,在任何画面里至少有一句陈述:“一座房屋的画面不是表示‘房屋’,而是表示‘这里是一座房屋’。”
但是,把这个例子放回到一个影片叙事之中,即放回到我们所说的一个整体的、叙事的、视听的话语之中,人们就会发现这样的“翻译表达”不充分。如果是主角长途跋涉之后看到远处一座房屋,可以表示“这里是一座房屋”,但放在另一个场景下,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驾车经过长途旅行,其中一人用手指着一座房屋,此时更倾向于理解为“这里是我们的家/我们到家了”。
为了研究单个镜头的叙事意义,影片就必须只有一个镜头。【相反,不联系上下文其他镜头只单独考量单个镜头的意义,就是断章取义,就是耍流氓!】
l 三、电影叙事的诞生
电影机诞生的同时,就产生了将影片首先用于讲述故事的想法。一些电影发明家似乎自觉的具有这样的计划。但当初的叙事方法十分简单,直到1900年,大部分影片仅有1、2分钟的长度,一般只包含一个镜头、一个时空单元,它们是单视点的。1900年以前,人们不觉得这种单视点是一个枷锁,也没人去探索用几个镜头表现一个叙事。这种摄影的单一性显然满足了1902年以前电影艺术家的需要。
当初摄制的这些影片遵循的是过去经典戏剧所运用的地点、事件和行动定律,因此,各种各样的影片旨在一个取景范围(唯一地点)内表现一个行动和一个时间段落,“叙事情景”也十分简单,用唯一一个镜头拍摄一个相对简单和单一的行动。
l 四、叙述与演示
任何叙事都意味着有一位叙述者,电影叙事也要假设一个“大影像师”(这是拉费的表达,直接来自18世纪启蒙哲学所宣扬的“大钟表匠”的观念。18世纪启蒙哲学用“大钟表匠”指世界的安排者)。
叙述:一段文字构成一个叙述,一个话语,人们在其中或多或少能够发现一位叙述者,这个讲述的机制按照一种确定的顺序,选择一定的词汇,通过自己的视点,向我们提供关于人物的一些连续信息。
演示:与叙述的模式同样重要的还有另一种传达叙事信息的模式,它毫不犹豫地将叙述者从交流过程中排斥出去,而让各种各样的任务相会在同一个“剧场”,登上同一个舞台,为此,人们求助于演员们,他们的任务就是在现场(这里和现在)、在观众面前,活灵活现地表现他们所扮演的任务已经历过的、各种各样的情节(他处和过去),这一模式的主要形式是戏剧演出,柏拉图称之为“摹仿”,我们最近提出将此称为“演示”。
人们在剧场里,面对的是一种“纯粹的”演示,是我们用文字就同一个“主题”所作的纯粹叙述的模仿产物。
影片演示与舞台演示的基本差别:
1)戏剧演员提供的表演与观众的接受活动具有现象学意义上的同时性:两者参与同一种现在时;相反,影片让观众看的是一个过去完成时的行动,是在现在表现以前发生过的事。
2)录制电影演员表演的摄影机,仅仅通过它的机位,或通过它的一些简单运动,就可以干预和改变观众对这些演员表演的感知,甚至能够约束和引导观众的视线。
在构成叙事的事件展开过程中,与戏剧演员相反,电影演员不再是唯一一个发送“信号”的人,来自摄影机的其他“信号”是由某个机制发送的,它存在于第一级机制、即演员们之上的某一地方,电影中这个上一级的机制可以说相当于书写的叙述者【拉费所说的“大影像师”指的正是这一机制】。这一机制在戏剧中由所有出场的人和物,通过每一次“演出”来体现。电影叙事以其不可更改性而与戏剧相对立,后者的特性恰恰在于每次演出不完全一样。
由于每一幅画面传达的潜在陈述句的多元性,无声的演示在表现某些现象方面是有所限制的,因此之后产生了无声字幕和讲解员。如果故事复杂一些的话,必须依靠说出来。
与言语受制于语句的线性连接相反,电影能够同时展现数个行动,这一潜在性在有声电影中表现得更加突出。
l 五、有声电影:一种双重的叙事
大多数情况下,对话,更一般地说是声音,用于减少视觉陈述的模糊性。
画面和词语运行两种叙事,它们互相错综复杂。
在日常消费的电影中,从一个段落到另一个段落常常就是通过一句台词来过渡的,例如A和B在一个咖啡馆,说了一句“我们去C家吧”,下一个镜头就是A和B在按C家的门铃。
当对话比看得见的行动更重要的时候,就是说叙事信息先在词语中,然后才在画面里传达与表现,米特里称之为“拍摄出来的戏剧”。
在某些现代影片中,这两种叙事的交错运作对于理解全部情节具有决定性的作用。例如女主角回忆自己的爱情遭遇时,出现一些闪回的画面加以强调;或者用画外音讲述自己的故事,画面显示的却是现在的生活……这一画面的替换与话语“总谱”的联系最终形成一个完全不同于前一叙事的新叙事。
爱森斯坦谈到无声影片时,提到通过一种多声部蒙太奇将一部影片当作一个音乐总谱写作的可能性:“一种蒙太奇,其中每一个镜头跟下一个镜头的联系,不仅通过一个简单的标志——一个运动、一个调式的区别、一个主题的展示或某一类似之物,而且通过一系列多线条的同时性进展,每一线条既保存其独立的结构秩序,又与整个段落组成的总体秩序不可分离”。【如果将此构想应用到复杂的视听体中,人们可以将五种表现材料(画面、印象、对话、文字、音乐)看做管弦乐队的几个声部,它们有时齐奏,有时对位演奏,如此等等】
词语以外的音响有助于叙事的构成:
电影艺术家/剪辑师根据声音的逼真性作出他的选择,譬如追逐的音乐发生在奔跑的时候,浪漫的音乐发生在情侣出现的时候,或者一些环境声的配合,在这种情况下,声音参与单一的画面叙事的建构,声与画的双重叙事因此而融合起来。但如果视听关系丧失了逼真性,就证明声音述说的是另外的事和主题。
手法:旋律线作用于场景上正在进行的事件,而管弦乐队的另一部分演奏与后一个情节有关的主题活与已发生的前一个情节相联系的主题,电影可以借鉴这一途径,成为完整意义上的双重叙事。
l 六、什么是虚构的叙事?
1)什么是一个虚构的叙事?
麦茨:叙事是“一个未完的话语,来自于将一个时间性的事件段落非现实化”。
2)叙事开始于何处?
3)虚构从何处开始?
任何影片都同时实行“记录/虚构”两种体制。这说明在这两种表面上看起来是矛盾的重要预期理由中存在某些真实的东西(预期理由:逻辑学概念,指在证明中以本身尚待证明的判断作为论据)。它们既要求“任何影片都是一种虚构的影片”(麦茨),又要求“任何虚构的影片可以从某种观点看作为纪录片”。事实上,观众的解读工作才使一中体制比另一中体制更显得突出。
“记录性取向”和“虚构性取向”
记录性取向鼓励观众将被表现之物视为一个“曾经的存在”,而电影用以引诱我们的虚构才是最基本的。虚构性取向以某种方式,鼓励我们将处于摄影机前的亲影片之物这些“曾经的存在”看作是“现在的存在”【我们在看《吐司》结局男主角最终离去这场戏的时候,所看到的并不是饰演男主角的男演员于此片摄制的当时,在郊外这一拍摄现场的表演(曾经的存在),而是采取一种然自己信以为真的“虚构性取向”,将一些“曾经的存在”看作为一些“现在的存在”,并使自己先心,在我的眼前,在这个郊外,男主角拿着行李箱离开】。
这样的区别有助于在早期电影的摄制中区分两类影片,摄影机前的亲影片素材在《火车到站》《婴儿的午餐》和《共产大门》这类影片就像是“自然地”展示,本身的无组织性明显地给予观众记录性取向。相反,类似《水浇园丁》,由于它向我们表现的是经过组织的素材,几乎是必然地显示虚构性取向。观众关注的不再是对亲影片的世界中(摄影师和他的镜头前)所发生的“闹剧”的记录,而是这一“闹剧”本身,它的有组织性活得了一种自主性,这种自主性使影片的行动能够通过放映机的中介而重新现实化,并得到一个自身的价值。
怎样区别对于我们以外的真实世界的记录,和对于仅仅存在于我们头脑中的世界的建构?(后者称为虚构)
l 七、非影片的现实和虚构的世界
纪录片:表现非影片的现实中实实在在存在的人和事。【非影片的现实:存在于日常世界、独立于影片艺术意外的现实,它或多或少是可以检验的,观众具有自己生活在其中的时空世界的知识。】
虚构;使用一切手段创造一个自己的世界,即使可能与我们的世界相类似。【虚构的世界部分地是一个心理的世界,具有自身的规则】
所以,某一影片叙事里发生的、在我们看来是逼真的,在另一个世界中可能显得荒诞。例如超人里的男主角可以飞,但又生活在和我们相似的人类世界中。“超人会飞”这些类似的信息作为一些公设,使我们有可能接受叙事整体的一致性。一开始公设的设定,让我们认为超人可以飞是正常的,如果是另一类影片,例如《傲慢与偏见》里的达西先生一言不合就从窗口里飞出去,我们会接受吗?当然不,因为这部影片的世界不是建立在同样的公设上。
故事:在时间顺序中被讲述的事件;
叙事:讲述它们的方式
为什么卢米埃尔的影片被视为“记录性”的零度(意思是接近记录性):举例《洗衣女》,从头到尾都是一些洗衣女在捶打衣物。人们只不过捕获了广泛现实中的一个片段,现实世界被认为与我们在影片里看见的这部分没有很大区别,是“一个真实的时空(时刻)的视觉保存”。当然,其中也存在话语,大影像师通过摄影机的机位、取景等对现实有所干预,但并不是严格的叙事。
相反,对事件的安排,即使按照时间顺序,也伴随着对时间性的一种运作(停顿、省略、相接),引入与显示时间的简单流逝不同的另一种逻辑,例如《北方的纳努克》
l 陈述和叙述
影片有别于小说,就在于它能够展现行动,而不必述说它们。
作为双重叙事的影片,在声带让人听到叙述者话语的情形下,必然求助于两种讲述的机制。然而,当一种机制公开地用活生生的声音讲述故事的时候,“大影像师”这另一种机制并不显示其自身,这是“一个虚构的和不可兼得任务在我们的背后为我们一页页翻动相册,用隐蔽的手指引导我们的注意力”。怎样思考这一机制与影片内做出口头或书写叙事的这些人物的关系?【画外音的讲述者和影片内主角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