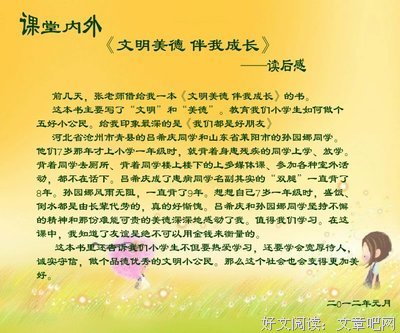
《中国古代政治文明讲略》是一本由张传玺著作,北京出版社出版的精装图书,本书定价:42.00元,页数:232,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中国古代政治文明讲略》读后感(一):中国古代国家的两种形态
在今天。只要一提起“中国”这个名词,我们很自然而然的会在心中就会有一种归属的感觉。这是我们国家的名字,我们生活在这个国家,我们每一个人都是是这个大群体的一份子。“国家”这个概念已经深入进了我们每一个人的心中,我们的心中都秉承着对于自己国家的观点与观念。我们的祖国有着五千年的悠久历史,但著名历史学家张传玺先生则认为“国家观”其实是一个现代的概念,因为历史经历的缘故,在中国的古代“国家观”其实是一个并不清晰的概念。
张传玺先生认为,中国古代的国家主要经过了两种国家形态,一是夏商周为代表的前期国家形态,基本特征是宗法贵族世袭分封制,二是前汉至明清的后期国家形态,基本特征是以皇帝为首的地主官僚中央集权制。张先生强调,我们应该把中央集权和专制主义分开来谈,中央集权制在历史上是起到了很多进步作用的。那么中国古代国家的这两种形态又是如何体现出来的呢?其又有哪些代表性的历史时期与例子呢?张传玺先生将在他的一书中,为我们进行阐述。
全书不过十个章节,表述了中国古代国家的历史特征,从华夏各民族的概述到汉民族的形成,再到历史上中央集权与诸侯分封的那些是是非非。最后两章讲述了中国历史上的丝路文化,看似与前面的内容没有关系,实则关联性很强。张先生写此两章的目的在于研究中国古代文化是怎样参与人类文明发展进程的。张先生认为研究历史是不可以盲从的,一定要站在一个客观的角度上,实事求是的进行分析。研究历史的目的是“为今天的建设提供借鉴”。这一点在他的书中能够明显的感觉的到。张传玺先生渊博的学识使得他所著的这些历史学术研究内容很值得一读,对于当下的一些问题也不乏许多启发性。《中国古代政治文明讲略》秉承“大家小书”的特色,书虽不厚但是内容颇具可读性。对于中国古代国家的形成及其制度这部分内容感兴趣的人,读过之后应该还是会有所收获的。
《中国古代政治文明讲略》读后感(二):从秦汉看国家制度的形成
著名历史学家张传玺,师从翦伯赞。他的著作《中国古代政治文明讲略》一书主要是研究中国古代国家的形成与社会制度,通过对各个时期的国家形成特征分析,帮助我们综合性地建构起古代国家的形成史。《中国古代政治文明讲略》是一本内容深入浅出的中国古代史,也是能够帮助读者建立一整个脉络分明的历史史观的普适入门书。
《中国古代政治文明讲略》是张传玺治学过程中的学术论著讲稿等的汇集,因为是文稿汇集,所以,并没有像通史之类非常明晰的时间线,又因为张传玺先生主要是研究秦汉史,所以这本书虽然名为《中国古代政治文明讲略》似乎涉及了中国各个朝代,其实不然,重点还是在秦汉方面,附带一些明清之类。但对秦汉方面的探讨也足以开阔我们的视野。秦汉,中国政治文明发展的源头,中国思想萌芽之花的初绽,此后的各个朝代基本都是在此基础上的深化与细化。
那么,对国家发展这个议题,特别是秦汉时期的宗法体制的研究就非常有必要。秦时一统天下,统一度量衡,统一文字,土地私有制——这些都是非凡的创举,一举打破了旧的宗法制的约束和羁绊,有点自由与解放的意味,从此中原大陆再怎么分分合合,有这样的基础,包容与兼并成为可能,也成为常态。
回顾秦时,在中央,以皇帝为首,由三九公卿组成中央机构——废除旧时之世卿世袭制;在地方,分郡县两级,基层分乡、亭、里——彻底废除旧的分土封侯制。郡县官员由皇帝任免,乡亭里基层官吏由本地户主推荐执掌。从中央到基层,各个约束,又有民主之处,此后的国家制度体系大多是先秦时的模式,非常先进。
对于一名对历史有浓厚兴趣的读者来说,张传玺的《中国古代政治文明讲略》是本非常好的历史入门读物。在这本不像中国通史那样大部头的书里,你可以学到许多历史书上没有讲的知识内容,也有关于国家制度、土地制度、社会形态、宗法体制、经济形态等待方面的知识梳理。这些理论,是我们学习通史类著作中,或者从大多数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之中,碎片化的知识中获取不到的精华汇集,这些知识看起来是大历史的边角,似乎不太重要,但实际相当重要,这是人类社会的结构体,影响一代代人们生存发展的根基,这些抽象的知识看起来不那么好理解,但是作者张传玺讲得生动有趣,读来并不诲涩难懂。只要你肯静心阅读,即便不具备相关知识储备也能读得懂。阅读这本书并不需要拥有特殊才能,只要你有好奇心、探索之心,对人类发展,对历史沿革,对国家制度有兴趣就足够了。
《中国古代政治文明讲略》读后感(三):我国古代国家观的转变和大一统、多民族的中央集权制的形成
追溯我国古代国家观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梁启超那一代人觉得我国积弱正是因为传统概念里没有国家。可是,我国古代数千年时间、经历了诸多朝代的统治,也曾出现过许多稳定繁荣的盛世,若说没有一丝一毫的国家概念,似乎也不妥。对此,师从翦伯赞、主要研究秦汉史的张传玺教授作了深入研究,在多篇论文中分析了我国古代政治制度和国家历史特征等问题,集结为《中国古代政治文明讲略》一书。
“国家只要存在,就有其特征”,而国家的特征与其政治制度密不可分。张传玺教授把我国古代国家特征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夏商周三代,包括春秋战国时期,实行的是以天子为首的宗法贵族世袭分封制,形成了民族主体国家观;第二个阶段是秦汉至明清,实行的是以皇帝为首的地主官僚中央集权制,形成了统一的、多民族的中央集权国家观。
前后两种国家观和政治制度的转型时期,就在春秋战国时期。转变的原因,概略地说,就是前一种政治制度在当时已经不符合时代的需求了,社会混乱失序,亟须建立行之有效的新制度。
宗法贵族世袭分封制,是以血缘关系维系的一种“家天下”制度,王位世袭、贵族世袭分封。虽然后代的一些儒家学者总是向往“礼崩乐坏”之前的所谓理想时代,但实际上并非如此,尤其到了周朝后期,状态非常混乱。混乱的缘由,春秋前期周王室大夫辛伯精辟总结,“并后,匹嫡,两政,耦国,乱之本也”,也就是当时的宗法制度已经无法维系正常的社会秩序了。
同时,民族主体国家观讲究“内诸夏而外夷狄”,是一种“民族关系双重性质的国家观”,把华夏以外的民族当作异民族。这种观点在和平时期能包容各民族,但在矛盾突出的时期,却会加大民族隔阂,加剧社会动荡。
在这种情况下,春秋战国时期,古代政治制度进行了一次大的转型,国家观也随之转变。
自秦始皇统一六国,逐渐形成了以皇帝为首的地主官僚中央集权制,大一统、多民族的国家观也随之产生。以现代眼光来看,中央集权早已是落后的制度,但在历史上,中央集权制自诞生之后在两千年内维系了历朝历代的稳定,适应了当时的时代需求。张传玺教授认为,“这套新制度的创建,是中国古代政治制度发展到更高阶段的标志,也是中国古代政治文明的典范”。
中央集权制具有“家天下”和“公天下”的双重性质,皇位世袭并且皇族有特权,而三公九卿的政府机构和郡县制的行政管理则有“公天下”的因素。更重要的是,随之产生的大一统、多民族的新国家观,推动了华夏和其他民族的融合和认同,促进了民族团结,为维护疆域广大的国家做出了不可忽视的贡献。
当然,中央集权制和大一统、多民族的国家观的形成也不是一蹴而就的,在秦朝和西汉初期,经历了一定时间的尝试也转变。对于秦始皇在政治上的功过、西汉初期分封诸侯的得失,张传玺教授也做了客观分析。
张传玺教授在《中国古代政治文明讲略》中探讨了我国古代政治制度的发展,以及相应的国家观念的转变。另外,在《中国古代政治文明讲略》的后几篇,张传玺教授还对丝绸之路的历史发展和妈祖文化的形成过程做了梳理。理解国家观和多民族观的复杂多变的历史过程,能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今天的民族文化。
2019.07.23雾凇
《中国古代政治文明讲略》读后感(四):去历史中寻找答案
在一般人看来,这些历史述评类的书,不会觉得好看,但是,如果关照当下,带着问题去读,往往能悟出不少,能读出趣味,能有更深刻的认识。
先从一个故事说起。
鸦片战争时,英国海军和清军水师在镇江江面上交战,岸边聚集大批中国百姓围观,当清军舰船被击沉时,岸上百姓并不悲伤反到不时爆发出喝彩声。英军登陆后正为食物和淡水发愁,百姓们争相将食物和淡水卖给英军。英军指挥官百思不得其解问中国翻译,翻译答曰:“国不知有民,民亦不知有国。”
的确,在一个朝代腐朽衰败时,民不聊生,人民活得像蝼蚁一样,如何知有国呢?
那么,在中国人的观念里果真没有国家观念吗?梁启超那一代人认为中国积弱是因为传统概念里有天下、有朝廷而没有国家。
如果有?那么,又该如何看待中国的国家观?这本书认为国家观这一个现代概念在古代拎不清。他讲述了我们多民族大一统国家观的历史形成。认为中国古代的国家主要经过了两种形态,一是夏商周为代表的前期国家形态,基本特征是宗法贵族世袭分封制;二是前汉至明清的后期国家形态,基本特征是以皇帝为首的地主官僚中央集权制。
近代不少史学家在评价中国历史上的中央集权制度时,给予秦始皇、汉武帝、宋太祖等时,有专制主义、极权主义、专制独裁等评价。作者认为应理性分析,他认为,为什么四大文明古国,只有中国的没有灭亡反证了我们的先人在两千多年前即选择了走多民族、大一统、中央集权国家的政治道路,是正确的必要的。当然,作者也指出,并不是要提倡固步自封,向外国、外民族学习他们优秀的文化特长很有必要,但仍应立足于本国,即要正确了解本国的历史和国情,知道我们的实际需要。
解读历史需要一个现代的开放的眼光,不应拘泥于讨论古代国家的有无问题,而是从中看到中国的历史根基,进而认识近代先贤铸就的国家观念。
大家了解中国现行的土地政策吗?我们在购买商品房时应该会了解到,是有70年产权,而且是70年的使用权,土地所有权是国家的。《土地管理法》第二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实行土地的社会主义公有制,即全民所有制和劳动群众集体所有制。” 全民所有制的土地被称为国家所有土地,简称国有土地,其所有权由国务院代表国家行使。那么,中国古代的土地政策是什么样的呢?这本书中也有非常详细的阐述。
中国封建时代的土地制度,如从西周讲起,先后经历了两个大的阶段。从西周初年到春秋末年为土地国有制阶段,从战国初年到鸦片战争以前,为土地私有制阶段。土地私有制阶段的时间很长。了解这一段历史对于理解当今的土地政策应该会有一些帮助。
中国正在大力推行“一带一路”倡议。那么,中国古代开通丝绸之路的历史背景是什么样的?当时的巨大历史价值又体现在哪里?
张骞通西域,史称“张骞凿空”,“西北国始通于汉矣”,此后,汉武帝积极经营西域。今天所说的“丝绸之路”开始于西汉在西域设置行政管理机构之时。当时的道路为由东而西:经长安经河西走廊通向中亚。在唐代,丝绸之路的交通特别发达。沿途邮驿,自长安一直设到中亚。著名诗人岑参的诗曰“一驿过一驿,驿骑如星流;平明发咸阳,暮及陇山头。”又曰“十日过沙碛,终朝风不休;马走碎石中,四蹄皆血流。万里奉王事,一身无所求。”当年丝绸之路上军书旁午、差役如梭的情景,历历在目。
今天所说的我国海上丝绸之路,是由今两广的某些口岸通向南海、南洋、印度洋的海上航行路线。明朝郑和七下西洋,在中外关系史和航海史上写下了壮丽篇章。
通过对这些历史的梳理,我们也可以对一带一路政策有些不一样的思考。
《中国古代政治文明讲略》读后感(五):中国古代国家及其制度,不可以一言以蔽之
——读张传玺先生《中国古代政治文明讲略》
张传玺先生,从1957年开始师从翦伯赞,研究秦汉史。翦伯赞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奠基人之一,张先生的历史研究秉承翦老的治学方法,尤其注重经济史和制度史的研究。张先生大半生整理老师文集,为老师立传,其尊师重道已然学林佳话。
张先生一直关注和支持“大家小书”的出版,他整理的翦伯赞《史料与史学》惠及很多读者。因为“大家小书”要做当代系列,笔者问张先生可有适合的作品,他先是谦逊以辞。后来禁不住劝说,才拿出来自己未曾结集的一撂文章供我选用。这本《中国古代政治文明讲略》便是笔者编缀而成的,大致反映了张先生近年的历史思考,它主要研究对象是关于中国古代国家的形成及其大一统、多民族和中央集权等三个根本特征。
梁启超那一代人认为中国积弱是因为传统概念里有天下、有朝廷,而没有国家。“我支那人非无爱国之性质也。其不知爱国者,由不自知其为国也。”1899年2月,梁启超在《清议报》上发表了长文《爱国论》:“国者何?积民而成也。国政者何?民自治其事也。爱国者何?民自爱其身也。故民权兴则国权立,民权灭则国权亡。”所以梁启超后来又写了振聋发聩的《少年中国说》。1900年,蔡元培《上皇帝书》提出:“国者,公司也;民者,出资之股主也;天子者,总办也;诸侯者,官也,皆总办所自辟之分办也。”陈独秀1904年在《安徽俗话报》上发表《说国家》一文,说:“我十年以前, 在家里读书的时候, 天天只知道吃饭睡觉。就是发奋有为, 也不过是念念文章, 想骗几层功名, 光耀门楣罢了, 哪知道国家是个什么东西, 和我有什么关系呢?……我生长二十多岁,才知道有个国家,才知道国家乃是全国人的大家,才知道人人有应当尽力于这大家的大义。……我们中国何以不如外国,要被外国欺负……都因为是那些国的人,只知道保全身家性命,不肯尽忠报国,把国家大事,都靠着皇帝一大胡为。”直到1907年章太炎先生在《民报》上发表《中华民国解》才大致解决了中国作为国家的历史发源。他说,华本国名;正言种族,宜就夏称;夏之为名,实因夏水而得,是水或谓之夏,或谓之汉;华云、夏云、汉云,随举一名,互摄三义。建汉名以为族,而邦国之义斯在。建华名以为国,而种族之义亦在。中华云者,以华夷别文化之高下也。即此以言,则中华之名词,不仅非一地域之国名,亦且非一血统之种名,乃为一文化之族名。随后他又发表了《国家论》。辛亥革命后,中华民国立国,这样国家的概念才落实到实际的政体。
经过抗日战争,国家这个概念已经深入人心了。但对中国古代的国家,如何历史地来叙述?前国家领导人曾给张先生命题作文:中国古代的国家观。张先生认为国家观这个现代概念在古代拎不清,所以改为缕述我们多民族大一统国家观的历史形成。他认为中国古代的国家主要经过两种形态,一是夏商周为代表的前期国家形态,基本特征是宗法贵族世袭分封制;二是前汉至明清的后期国家形态,基本特征是以皇帝为首的地主官僚中央集权制。中央集权制对于各级官府机构的设计及官吏的职掌基本完善,是古代政治文明的历史典范。张先生强调,我们需要把中央集权和专制主义分开来谈,中央集权制在历史上起到很多进步作用。
中央集权制度保证了秦汉帝国的基本统一和多民族的相互包容。本书所选第二篇文章就是论述我们多民族文化特质以及何谓汉族。文章强调,华夏和蛮夷戎狄,都是族名,既是他称,也是自称。我们今天不可以望文生义,过分强调那些反犬旁的、读音生冷的字词是贬义,甚至有人起意把古籍中那些字词都改掉。所以我们需要文化自信,历史还是本来的历史,但解读历史需要一个现代的开放的眼光。时势使然,比起上述所引梁启超、章太炎、蔡元培、陈独秀诸论述,张先生的文字更显平和雍容。我们现在不再讨论古代国家的有无问题,而是通过文献资源重新建构中国古代国家的特征。这样我们才不会将近代先贤铸就的国家概念再度悬空。
本书最后两篇是关于丝路文化的,旨在研究中国古代文化是怎样参与人类文明发展的。这也暗示读者我们不可以简单地把闭关锁国和古代中国草率对等。研究中国历史,需要一个世界的眼光和基本的人性追求。我们不可以咬牙切齿地数典忘祖,说中国古代漫长的封建制度一言以蔽之专制,或者以一言以蔽之封闭。对于历史,需要多读些材料,实事求是地分析精华和糟粕究竟是什么,不可盲信盲从,拿历史来“先前阔”,也不可拿历史来解恨或推诿。
张先生学问渊博是有口碑的,他提出研究要“文献与考古对照,历史与理论结合”,研究的目的是“为今天的建设提供借鉴”“丰富发展今天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所以张先生,并不单单是一个为学术而学术的纯书生,他很关注古为今用,所以他的文章对我们研究当下问题很有启发性。
拉拉杂杂佛头着粪,希望更多的读者能多读读这本书,随张先生思考历史,思考当下。
2018年11月9日定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