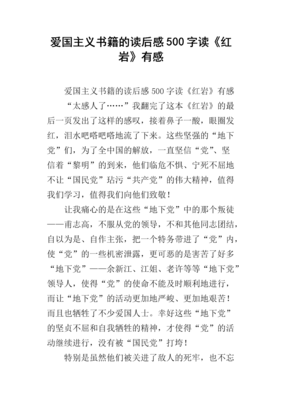
《“民主”与“爱国”》是一本由[日] 小熊英二著作,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的平装图书,本书定价:198,页数:832,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民主”与“爱国”》读后感(一):“民主”与“爱国”
https://athenacool.wordpress.com/2020/12/08/%e6%b0%91%e4%b8%bb%e4%b8%8e%e7%88%b1%e5%9b%bd/
“民主”与“爱国”:战后日本的民族主义与公共性 [日] 小熊英二 / 黄大慧 等 /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 2020-8
子扉我 2020年晚冬 申城西楼
原载回响编辑部微信2020年12月8日
《“民主”与“爱国”》读后感(二):民主与爱国,可得兼乎?
用了半个月时间,读完了这本800多页的巨著。过程中不断问自己,“花这么些时间值得吗?”答案当时是肯定的,颇多“仅仅读到这一部分内容就值得”的感慨。
整体来说,如果你想了解战后日本思想史,尤其是1945-1970这一时间段,那么这本书是不错的选择。如果你是对宽泛的政治现况、舆论思潮、群体运动等问题感兴趣,相信你也会在阅读本书中有所会意。
例如1960年反安保运动中岸信介政府强制表决的戏码,在近年来中外各类型的政治游戏中屡见。日本更年轻一代的更激进主张,让人联想到TW涌现的时力、基进;全共斗运动中的学生,则让人想到去年另一块自治领土的景况……
《民主与爱国》的作者小熊英二,国内读者对他了解比较多的,应该是他写的《活着回来的男人》。他的父亲是在东北被苏联俘虏,强制劳动三年,可以说兼具“加害者”与“受害者”双重身份。
战争体验多样性带来的不同战后思想,是本书论述的重要线索。“战前派”的丸山真男批判比自己更年长的“老一辈自由主义者”,“战时派”的吉本隆明批判丸山这代人,江藤淳、石原慎太郎批判固执于战争体验的“战时派”。
对于民主与爱国这两大主题,在战后经历着多次的论争,面对着国际政治局势的变革、日本经济的恢复与信心的提升等,也不断进行着调整。左翼与右翼、城市与乡村、学生与知识分子……一个社会的变革转型有着如此广阔的面向,不禁让人深思:如此的社会转型引发的思想混乱,对其他国家是否必需,或者应当避免?
本书在写作上引述了大量史料,真实生动,不仅有对丸山真男、荒正人、竹内好、江藤淳、吉本隆明、鹤间俊辅等重要人物的专题分析,还有形形色色的小人物。如学生兵渡边清对天皇由忠诚到叛逆,认为天皇“在敌人面前像条狗一样低垂着头”,想要“拽住他那三七分的头发,撞向岩石”。
这本书的缺点是内容太过庞杂,一些概念由于时代与异国等因素,对一般读者而言,有时候难以区分不同人的思想分歧与诉求,不过这一点作者其实也有所说明强调。
如果只是想寻章摘句,找一些感兴趣的内容来读,倒也未尝不可。
《“民主”与“爱国”》读后感(三):一书讲尽“战后日本”
若说世上最关注日本的,或许还真的不是他本国日本,或许也不是那既用着他又监视着他的美国,我倒觉得是我们,是我们中国。岂可限一衣带水而不查乎,对吧,思维方式上的相近,人种上的亲缘,还有文化上的一脉相传,等等这些都把我中国和他日本绑在一起,我们就像那观火的对岸住家,对面日本的风吹草动都明晃晃,引人注目。 但,关注并不代表了解,我们是在好奇,是在防御,是在看热闹,实话说在经济刚起步的时候还有着很热烈的向往,但我们这只是做到了关注到,即便在很多领域我们也做到了赶超,但我们仍然不是真正的了解了我们这个邻居。就比如“鬼畜英美”到“效仿民主”这一转变之快之大,就奇特得足以令人闻之震惊。 可以说我们绝大部分人,对于战后日本的真实情况,真实的发展历程一无所知,其实来说战后日本是一个新的国家,只是刚好名字叫做日本,与我们大多数人所知的并不一致,他是一个继承又全新的国家。如果想要真正地去了解现在的日本,便不能再以江户的社会,明治的风气来审视日本,必须要以“战后日本”来正视日本。 “战后日本”简单说来,一是指日本战败投降后的十年时间,又指代战败后重新建国的新日本,那么有两个词汇,是最能概括这一可短至十年,又可延长至今的时段的了,那就是一则“民主”,一则“爱国”。 这一时期之事件,之宗旨,之思想,无外乎“民主”与“爱国”,而本书正是基于此而展开而来。但有趣的是,本书并非只着眼于政客或是高官的想法、说辞与所为,而是以群众级的知识分子的言辞为研究,即是说,当某一知识分子的思想和主张,被群众所接受,被报刊传媒所广泛传播,那么他便成为能够代表其国舆论与民众的群众级知识分子,其言论便有了代表性。因此,在这些具有代表性的知识分子的言论主张基础上,来深究民主主义、和平主义,还有国家建设,便立足扎实,有理有据。 小熊英二先生的这部书如今在日本被广泛用于讲义,可见其语言平易而深入浅出,可以说是完全没有阅读的障碍,小熊英二先生全书没有多少专业术语,对于没有太多知识储备的读者也极易上手。 但我还想说,本书读来虽易,但书中道理深遂,警示刻人,若想全然领略书内思想,还需得细研慢读,深痛于时短而学浅,不得尽透此书,实不敢妄言文章,抱憾于只能写篇推荐文章以表震撼。
《“民主”与“爱国”》读后感(四):仍处在战后转型期的日本
中国大陆已经引进小熊英二的许多作品,有理想国的《活着回来的男人》,上海译文出版社的《改变社会》,社科文献出版社的《平成史》,三联书店的《单一民族的神话》等,这本《民主与爱国》是社科文献出版社最新引进的作品,是启微丛书的一种。
在这本著作中,作者认真、不懈地追求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到1960年代末有关“民主”和“爱国”的论述,并充分利用了所有主要材料。分析和评论了诸如丸山真男、大塚久雄、竹内好、吉本隆明、江藤淳、鹤见俊辅等知识分子从战争的经验中产生的各种思想和话语。
人类的思想是由强烈的原始个人经验所决定的。中日战争和第二次世界大战持续影响着战后日本人民的思想,这里也包括他们对原始经历的深刻体验。但是,这取决于每个人心目中的战争是什么样子的,以及他们在战争中有什么样的原始经历。我们都知道战争是不平凡的,现在20多岁及以上的人们生活在一个和平的世界中,而对那时的日本青少年来说,战争是日常生活的一部分,他们经历军国主义教育长大。20多岁有过服役经验的人和没有服役经验的人的感受肯定是不同的。还有的人即使是在军队服役但也没有经历过悲惨的战斗。当然还有那些在城市中经历过空袭的人,以及在农村地区中没有经历过空袭的人。尽管那个年代所有的日本人都经历了中日战争和第二次世界大战,但每个人的经历却截然不同。这些经验的差异在关于“民主”和“爱国主义”的论述中就会引起差异,有时甚至是冲突。
基于上面的论述,我认为,在接近时代的一种“感觉”的同时,专注于每种战争经验是非常困难的,比如个人是否经历过战争,或在什么情况下经历过战争。尽管如此,“战后三期(1990-)”一代的作者在谈到重新体验个人作为“战后三期”一代与战争脱节经历的困难时,将尝试重温“战后一期(1945-1955年体制)”和“战后二期(1955年体制-1990)”世代的经验。作者已经做的很好,在这本书里清楚地描绘了进步派知识分子,战时知识分子和战后知识分子等代表人物的思想,成功地勾画了日本政治思想的轨迹。
战后思想可能适合那个时代。但是现在呢?含义应该不同。有必要仔细阅读这本书,并为日本的民族主义增添新的含义。靖国神社,《宪法》第9条,日本新教科书,冲绳(琉球)驻军等等各种问题纷至沓来,如何解决需要日本政治家的智慧。这本书可能会给出一些提示。
前几天,正在读这本书的过程中,安倍晋三辞去日本首相一职,尽管他是战后在位最长的首相,但是上面提到的那几个问题都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二战仍然以某种无形的力量影响着现今的人们。未来的日本向何处去还需要进一步关注。
这些东西对中国也有借鉴意义,尤其是对“两个三十年”的认识和分析。但是,由于种种考虑,在此就不展开了。
《“民主”与“爱国”》读后感(五):“战后”的开始
战争的最后阶段,只有伤亡在不断扩大。战争带来的后果是,日本的死亡人数达到大约310万人。这个数字相当于当时本国人口的4%。此外,有1500万人失去家园,300万人因为企业倒闭而失去工作。
当时的一名大本营海军参谋说,战争最后的一年“对我方来说是战败处理,对盟军来说是扫荡残敌”。即使这样也要继续战争,这是因为对执政者和军部上层来说,“比起收拾战争残局,继续战争更为容易”。
推迟终结战争的主要理由是投降条件。在军队上层,妄图以某一处的局部战斗取得胜利,来改善投降条件的意见占大多数。所谓改善投降条件,首先是保留天皇制,其次是由日方进行战犯审判。作家小田实后来写道:“捍卫天皇制就意味着挽救天皇的生命。而挽救战争最高指挥者天皇的生命,也就意味着挽救其他二号、三号指挥者的生命。”
1945年2月,近卫文麿向天皇奏请投降交涉。但天皇以“如果不再赢得一场战争就交涉的话会很困难”为由拒绝了。那之后的半年,冲绳战役和大量的特攻战、各地的空袭和原子弹的投掷、苏联参战和朝鲜半岛的分隔以及南方战场导致了大量战死和饿死的士兵。日本的多数战死者,尤其是大多数的民间牺牲者都集中在这半年里死去。
一个人的战死,会给家人和亲属带来莫大的伤害。作家梦野久作的长子杉山龙丸回忆战后从事复员事务时写道:“我们做着十分痛苦的工作,每天对来访的军属传达着,您的儿子、您的丈夫死了,死了,死了的讯息。……多数军属都瘦骨嶙峋,衣不蔽体。”杉山某日接待了一位代替因粮食不足而病倒的祖父母来打听父亲消息的小学二年级少女。
我翻看账簿,找到名字,上面写着战死于菲律宾岛。
“你的父亲……”
我边说边打量着少女的脸蛋。黑黑瘦瘦的脸,娃娃头下细长而清秀的眼睛,努力睁大着盯着我的嘴唇。
我必须回答少女。努力控制住身体的战栗,不知道该用什么样的言语回答。
“你的父亲,战死了。”
说完后声音戛然而止。一瞬间,少女努力睁大的眼睛瞪得更大,然后,哇……好像要哭似的。……但是,少女说:“爷爷嘱咐我了,说如果爸爸战死了的话,就请主管的叔叔写下爸爸战死的地方,战死的情况,对,情况。”
我沉默了,点了点头……终于,写完后,装进信封递给小女孩。小女孩用她的小手小心翼翼地装进口袋,用手臂压住,垂下了头。
没有一滴眼泪,没有出声。
我用手拍着她的肩膀,想说点什么安慰的话,一看她的脸,小女孩儿紧紧咬着下唇,就好像要咬出血似的,突然睁开眼睛呼了一口气。我强忍着不出声,稍稍稳定一下自己后问道:“一个人,能回家吗?”
小女孩凝视着我的脸:“爷爷叮嘱过我,不能哭。爷爷奶奶给了我乘电车的钱,告诉了我电车的路线。还问了好多遍,可以去吗,可以去吗?”就好像说给自己听一样,又向我点了点头。
我的体内就好像有股热流涌过。在回家的路上,她对我说:“我有两个妹妹哦。妈妈也死了。所以,我必须坚强。我不能哭。”握着她的小手,我脑海中反复回响着她的话。
会变成什么样呢,我到底是什么,到底能做点什么呢?
使很多当地居民死去的吕宋岛碧瑶战役,发生在天皇拒绝近卫投降提案期间。
对8月15日日本战败的反应,因阶层、居住地区或年龄而异。据美国战略轰炸调查团战后进行的面对面调查,遭受空袭的城市比农村、深谙世事的老人比年轻人预测战败的比例更高。对于战败印象的差异将于第十四章和结语中再次加以分析,无论如何,战时的价值观和权威都崩塌了。
《“民主”与“爱国”》读后感(六):战后日本知识分子的“同时代集体性心情”
王升远/文
精英思想与民众观念、情感间的复杂关系是治思想史研究者始终绕不过去的问题。为纠正将精英思想之连缀等同于思想史的偏向,葛兆光提出了“一般思想史”的观念,以揭示被精英思想遮蔽的“近乎平均值的知识、思想与信仰”世界——那是每个时代的底色。作为一种研究范式,以“一般思想史”为传统学术观念中的“精英思想史”补偏救弊为我们在认识论上打开了全新的视界,同时也无异于凸显了二者之间难以逾越、弥合的巨大鸿沟。而在日本思想家小熊英二看来,“所谓著名思想家,更多的是能够将自己与同时代的人共同拥有的心情以更加巧妙的方式进行表达的人,而不是具有‘独创性’思想的思想家。”这是对精英思想与民众观念的一种新的观照和理解。在一些危机时代、异态时空中,这一视野将成为理解思想史的重要进路。战败和盟军占领就曾使得战后日本进入了空前的异态时空,它塑造了知识人与民众、与国家关系的非常态,又进而决定了小熊英二《“民主”与“爱国”——战后日本的民族主义与公共性》一书的思想取径。
小熊在《“民主”与“爱国”:战后日本的民族主义与公共性》中所呈现出的是与在《改变社会》《活着回来的男人:一个普通日本兵的二战及战后生命史》及其与鹤见俊辅、上野千鹤子的对谈录《战争留下了什么:战后一代的鹤见俊辅访谈》一致的、不以“8﹒15”切割历史的“贯战史”视野。在他的战后史叙事中,战争经验成为了重要的思想源头。借用上野千鹤子在对谈录后记中的话,该作“是以大河小说的方式描写战后思想史的大作,它采用了迄今为止书写战后思想史的人们都没有用过的方法:试着以未被讲述的战争体验作为光源,反照出每一位战后思想家的思想……战后的我们,第一次震撼地感受到了这一至今仍在摇摆着尾巴的巨大影子的存在。”
那么,战争经验又何以成为理解《“民主”与“爱国”》、甚至理解战后“集体性心情”的关键呢?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可以说战争“抹平”了日本的阶层差异和城乡差异。加藤阳子的研究显示,战争末期,知识阶层的征兵率是79%,与普通青年持平,整体上来看这已是很高的比例。相关政策一经推行,旋即得到了民众的拥戴,因为知识阶层特权不再,“不幸的均沾”使得征兵看起来更为“公平化”。同时,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曾经相对疏离政治与战争的知识人则面临着前所未有的伦理困境。
无论是对时局长期保持警惕和批判姿态的作家中野重治登报声明转向国家主义(《东京学艺新闻》,1942年2月1日),还是鹤见俊辅以“要呆在战败的一方”为由从美国重返日本加入海军,他们的抉择或多或少都与急转直下的战争局势、战时生存境遇等因素综合倒逼出的故园意识、“家国意识”有关——保卫“愚蠢的双亲”获得了最广泛的情感共鸣。若按现代正义战争论的代表性人物迈克尔·沃尔泽(MichaelWalser)的看法,自卫战争即是正义战争。那么,战局的转换似乎已让一些日本知识人的“家国意识”笼罩了一层“正义性”错觉。知识人与民众、国家至少在“共赴国难”的意味上迅速一体化,甚至连桑原武夫、市川房枝也都曾批判过“旁观者”。(当然,这也成为战后日本各界洗脱战争责任的口实)同时,就像小熊在书中所呈示的那样,盟军对日本城市的密集轰炸使得城市知识阶层被迫来到乡村寄人篱下,仰人鼻息。另外,五味川纯平、五木宽之、安部公房、木山捷平、长谷川四郎、尾崎秀树、大冈升平等后来成为战后文学、思想重镇的青年人因战败而从中国大陆、朝鲜、西伯利亚、台湾、东南亚等地被遣返归国,就像约翰·道尔在《拥抱战败》中所说的那样,他们只是“被遣往海外协助建立强盛的帝国势力范围”的650万人中之一员。知识人与大众相遇、城市人与农村人相遇、文人/学生与军人相遇,这一系列遭遇所形成的精神冲击、战时生活的困苦境遇,都极大改变了战后初期日本知识人的自我身份认同、国族认同和思想形态。
另一方面,1930年代的“转向”以及军国主义统治下的战争“协力”种种,更使得日本知识阶层斯文不复、权威失坠,不再是民众仰止的“启蒙者”和道德典范。如果说“走向民众”是战时的走投无路,那么在战后初期战争责任追究、东久迩内阁“一亿总忏悔”的风潮之下,选择与民众站在一起,重建民族的道德脊梁和政治、社会秩序则成为“政治正确”的姿态和别无选择的谋身策略——龙蛇以蛰,以存其身。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小熊英二所描述的战后知识人与同时代“集体性心情”共振的姿态,毋宁说是在异态时空之下前者别无选择的必然,这是理解本书的重要前提。《“民主”与“爱国”》译者序中有云,“该书的写作是基于这样一个前提:同时代著名知识分子的言论,与同时代集体性心情相一致才称得上‘著名’。”这一论述似可略作调整——在历史剧变的风潮中,与同时代集体性心情的共振才成就了战后一代的思想家们。
求仁得仁,与民众同在、呼应同时代的集体性心情自然会为思想家们赢得声誉,但作为“悔恨的共同体”之一员,裹挟于时代风潮中的知识人如何在与政治权力、民众情绪的共生关系中把握脆弱的平衡,在战后文化、思想重建中重获公信力和领导权,是不得不慎思之所在。在第三章“忠诚与叛逆”的讨论中,作者援引了1948年8月15日《读卖新闻》的舆论调查结果。数据显示,民众中支持天皇制存续者占了90.3%,支持天皇留任的占68.5%——这便是“集体性心情”的外化。而讽刺的是,“在当时,‘天皇制’一词作为战时强迫人们成为隶属的象征而被广泛使用。”同时,就像小熊犀利指出的那样,“议员们担心,如果赞成天皇退位,会失去那些朴素表明‘支持天皇制’的人的支持。同时,如果以天皇退位挑明战争责任,政界、财经界、地方权力阶层也有可能被追究战争责任。”也就是说,民众、麦克阿瑟所代表的盟军意志以及日本国内保守政治家之间围绕“天皇制”存续的问题再次达成了默契的一致。围绕天皇退位和天皇制存续问题,知识人不得不在“原理”与“江湖”之间做出选择,此情此景亦似曾相识。
在1946年2月召开的“文学家的职责”座谈会中,德国的托马斯·曼、法国的罗曼·罗兰成为与会者心中面对法西斯强权的完美抵抗者;而在日本国内,如小熊英二所言,坚持马克思主义信仰、被捕入狱18年的德田球一、宫本显治被释放后,旋即成为国民心中超人般的存在,成为道德上的无瑕无垢者、“良心的唯一见证”。1954年至1962年,以鹤见俊辅为核心、30多人参与的“思想的科学研究会”发起了“转向”问题的共同研究,开始系统地讨论战前、战中和战后日本各界的激进主义者、自由主义者、保守主义者的变节问题。然而,无论是哪一类“转向者”,都绕不过是否/如何在民众的价值、信念、情感之包围中坚守自己的“主义”的灵魂之问。诚如江口圭一所言,“民众对于排外主义战争的支持,正是使政府的不扩大方针归于失败、使亚洲门罗主义路线取代对英美协调路线并得以巩固的决定性条件。”民众被军国主义意识形态动员起来的结果之一便是知识人腹背受敌、遭到孤立,“同时代集体性心情”的绑架成为压倒有良知的知识人的最后一根稻草。与之协同、为之代言则名利双收,反之则将陷入众叛亲离的伦理困境。
而在战后初期,知识人面对民众的态度却发生了剧变。这自然与书中所论述的知识人饱受伤害和磨难的战争体验(主要是疏散体验、从军体验等)有关。小熊引述了大塚久雄在《近代文学》杂志1946年举办的座谈会上的发言,他坦言自己“脑海里有理想的大众形象,并不喜欢现实社会里的大众”“由于战时的经验,我有时有点憎恨大众。”丸山也在1951年指责战败后的大众“追求死气沉沉的娼妓秉性和赤裸裸的自私自利。”所谓“大众”,在大塚和丸山那里,出现了观念与现实的分裂。在观念上,他们是一个与知识阶层相对的、可以进入思想家理论体系的、巨大的、意象化的单数和论资,而落实到现实中的复数个体,则不免令人绝望。不惟自由主义知识人,日共方面亦作如是观。孙歌曾在一篇讨论日本民众史研究的论文中指出,“在1950年代中期以前,日本共产党决定放弃战后初期的和平幻想走武装斗争道路的时候,发动民众一直是日本马克思主义者的基本斗争内容。而随着‘山村工作队’武装斗争的失败,日共宣布放弃武装斗争,回到合法斗争的路线上来,这里面伴随的一个基本判断是日本民众‘觉悟太低’。”
随着军国主义政权覆灭,盟军对日改造的全面启动,围绕天皇退位和天皇制存续的问题,知识人却不意在保守政治权力与“面目可憎”的民众之间再次面对两面夹击的“极端语境”。如小熊所言,“被置于‘天皇制’对立面的是‘主体性’、‘连带’、‘团结’等词”,“当时的天皇制论争强调了天皇阻碍了伦理感、责任意识,也就是‘主体性’的确立。”而“知识分子及高学历阶层,对天皇个人的爱戴与‘真正的爱国’心情发生了分离。这种心情绝不孤立于民众。”这就形成了一幅颇具讽刺意味的图景:知识人一边在原理层面讨论导致日本近代化走向歧路的“近代的自我”“主体性”缺失及其重建问题,一边却貌似又再一次在权力与民意构成的“江湖”中丧失了“主体性”。日本近代思想的一个重要的症结就在于,引入西方观念后常将其作为学术、思想领域的对象、谈资,而鲜少经过广泛讨论、落实为共识并内化为个人行为的指针,思想与行动遂走向分裂。盟军意志、保守政治力量以及民众情感显然是其中最不容忽视的决定性力量。战后,城头变幻大王旗,而在讨论“转向”问题的时代,知识人与民众、国家的关系却再次以一种与历史相似的结构重现,这是颇值得深思的。
这并不意味着世无识者。在近年来的研究中,我越来越看重极端语境下知识人日记的意义与价值,它们为今人提供了理解那些时代不可多得的精神志,时而让人想到南宋末年诗人郑思肖以铁盒封函、深埋在苏州承天寺院内井中的《心史》。小熊英二在讨论“忠诚与叛逆”的问题时,以曾经的海军少年兵渡边清日记《碎裂之神》为例做出了极为精到的分析,让我们看到了一个有着战争体验、国际视野和独立思考能力者对战争从体制和原理层面的深刻观察与反思。《碎裂之神》是一个真诚而又极富洞见的文本,但遗憾的是,从书中注释里我们不难看到,迟至1977年此书才得以出版。无独有偶,近来我读到了数十种令人感佩的作家战败日记,其中尤以中井英夫和渡边一夫最为理性和深刻,而他们的日记则迟至1995年、2005年才公开出版。1970年代以降,美化自己的战争经验成为一股不可小视的潮流,这让一批有良知的知识人感到忍无可忍。他们意识到将自己的战争体验投放到公共空间中以正视听的必要性和时不我待的紧迫性,遂于三十多年后挺身而出,向知识界传递了诸多带着温度与实感的战争经验,其拒绝遗忘的历史责任感、“以真抗玄”的介入意识和批判精神,令人肃然增敬。但在另一方面,如果说,这些知识人提供的真诚、独立、理性的主体性思考缺席了战后初期日本的思想建设,亦大致合乎实情。那么,接下来的问题便是:他们在战败至1970年代的二三十年间之缄默又意味着什么?而对此间日本的言论空间的变化、民族主义思潮起落轨迹的阐发正是小熊是著的关切所在,亦值得读者诸君为之寓目。
鹤见俊辅在与小熊、上野的对谈中盛赞道,“小熊君这次的《“民主”与“爱国”》就接近‘全历史’,能在思想史方面践行近于‘全历史’的方法,是很少见的。”在鹤见那里,所谓的“全历史”(TotalHistory)强调的是兼顾公、私两层面历史之叙事。同时,《“民主”与“爱国”》中也暗含了对“原理”与“江湖”两个层面的尊重。在讨论丸山真男对天皇退位、天皇制存续问题的抉择时,小熊意味深长地指出,“丸山敬爱的恩师南原繁也是象征天皇制的支持者,这或许是丸山远离天皇批判的又一原因。”此即“原理”之外的“江湖”。在“原理”与“江湖”的交错中,小熊并不试图为战后思想史“制作”一条明晰的秩序链条,亦不急于为“民主”“爱国”“民族主义”等在战后影响巨大的、而涵义飘忽多变的关键词给出准确的界定,他博观而约取,以面对历史的真诚和“同情之理解”的姿态,对那些抽象概念在每个时代、每个言说者那里的差异性理解与表达都给予了必要的尊重,进而表述了一种“朦胧的确定”,也许这种方式才是进入战后纷乱混沌、多元并存的政治生态、社会语境和思想文脉的不二法门。
应以怎样的姿态面对民众、国家以及“同时代集体性心情”,应与之保持怎样的距离,这个问题不只投向了思想史叙事的“对象”,也抛给了作为历史见证者、书写者的我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