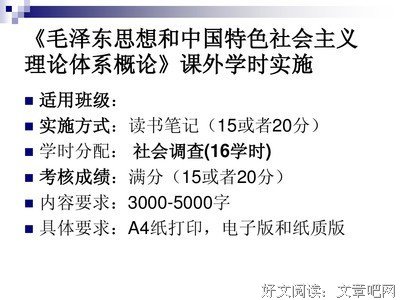
《衣柜》是一本由[波兰] 奥尔加·托卡尔丘克著作,浙江文艺出版社出版的平装图书,本书定价:29.00元,页数:124,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衣柜》读后感(一):托卡尔丘克青涩的少作
《衣柜》写于1987年,托卡尔丘克年方二十五,这个短篇象个寓言,衣柜成了一对夫妇避开尘嚣的方舟,透着青年作家敏感的想象力。《房号》是以客房服务员眼光,打量不同房客的特点,展现多彩的生活习性。《神降》写沉迷于电脑的程序猿,营造着远离现实的虚幻世界。
和后期的作品比,这三个短篇从内容到写法,都比较青涩,随便看看也无妨。如果是铁粉或研究者,倒时能看出托卡尔丘克的初心来:一是对世界无限与荒诞的天马行空思考,二是设置一个场景,展现多样的人生,这成了托卡尔丘克创作的标签,延续到今。从《太古和其他的时间》到《怪诞故事集》,你总会发现《衣柜》的影子。
青春的眼神,会伴着人的一生,随时复活。
《衣柜》读后感(二):当我不再是我,世界会是怎样的?
终于把之前一直心心念的《衣柜》读完了。嗯,今天在书店读完的。这本书,属于异类。是纯文学,却很好读。但是说把它当做普通怪奇故事,你又总觉得里面有点啥隐喻是你没get的。一直以来,我都是那种乱七八糟的各种书都在读的人。所以绝对不敢说自己是文学爱好者。非要说,就是一个单纯对书本身怀着执念的人。所以最早读托卡尔丘克的《白天的房子,夜晚的房子》是出于纯粹的标题党,所以开始读。然后,惊艳。几十个絮语般的小故事片段,混沌般地构造出一个充满幻想和生机的世界。这样的阅读体验,是过去所没有的。不,或许有过。但是这样的体验来自于更古旧的阅读时间和作品,比如《一千零一夜》,比如《荷马史诗》。记得当时被惊艳到以后去简单看了一下作者背景。发现,作者来自于波兰。印象里,这是一个充满苦难流离的国家。没想到那个遥远的国度,有着这样好的作品和作者。 后来,就是听说托卡尔丘克获奖了。而且还是诺贝尔文学奖。感到惊讶。前面说了,自己不是文学爱好者。所以提到诺贝尔文学奖,脑中会马上浮现读不懂的米兰昆德拉的《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百年无法理解的俄罗斯套娃人物结构的马尔克斯之《百年孤独》。但是托卡尔丘克的作品,不一样。不但不会让我被劝退,我还能理解里面的好。一个作品,得再多的奖,口碑再怎么爆炸,如果你读不懂,那就跟你没关系了。对吧? 回到《衣柜》,这本集子。短短百来页。而且,咳咳,高能排雷警告:小说三个故事合计62页。 剩余的部分,全是附录。内容分别是诺贝尔文学奖颁奖词和托卡尔丘克的演讲词以及一段访谈录。请注意,别小看这看起来类似掺水的附录。个人认为,这部分,才是精华。尤其是作者的演讲词。她娓娓道来了她文学的起点和对文学叙事的理解。多次强调,这个世界都是以第一人称“我”为主体。越来越多的作品都在讨论各种“我的故事”。她在演讲词谈到,她希望以一种全新的第四人称方式去表达文学。我的理解是她希望人们看到自己之外世界的模样。这样的话语让我触动。突然想到,现在每天,人们都在各种社交平台上去表达“我”。这些各种各样的“我”或许真的丰富了这个世界,让世界五彩斑斓,多姿多彩。但是,也让我们失去了看到世界,看到外界的机会。这些,是我在读《衣柜》以后的感受。 书中三个故事。被衣柜吸引而永远住进衣柜的夫妇,在各种酒店房号之间窥探猜测客人秘密的客房服务员,在计算机世界成为造物主不断寻找完美世界的天才程序员。他们,用他们的故事让我反观到了自己当下生活的片段和缩影。重新开始思考自己的存在和生活本身的意义。 这样的书,可能就是好书吧。 今天一口气读了三本书。得歇歇了。头脑中的文字被表达出来以后,人感到神清气爽。这样的体验,其实不错。这些碎碎念。只是单纯的表达,仅此而已。或许,这样的文字都不能被称为书评吧。就这样吧。
《衣柜》读后感(三):说明他已经来了
书架上,随手翻到的一本书。备忘录,一时兴起的一篇书评。
“我是忙碌、脆弱、短暂的那一个,而衣柜只是它自己 。它完美地成为它自己。”
《衣柜》隐秘地孤芳自赏,黑暗号召出一对璧人。但谁说,回避外来冲突的合理能不脆弱地表现在时间内。
小时候走路久累了,会跳上花坛缘,仿佛这种调整能让轻度痉挛的足底初始化。
其实是厌倦了恒定的重力加速度。
喜新厌旧,辞旧迎新,遂孜孜不倦。
周而复始,自此包治百病。
《房号》中的“我” ,把世界的沙漏横置着看。
洞察需要角度与深度。铺陈的通感带来快感,脉冲从头发根伸到脚趾尖,一气呵成却也让人来得及反应,俨然让读到故事的当下,完整了一点。
物化地活在他人故事剪影的对立面,是卑微而远见的存在。因为太过客观甚至怀疑自己的存在,殊不知谁都活在棱镜里。左看是右侧,右看是左侧,然后一成像,是假扮的角色。
我们都在竭力掩饰自己观察者的身份,却又祈祷着某一天、某个人,发现那个独处的自己。他用相似的观察包容了管中窥豹的自己。
篇中提及亚里士多德:“虚构总是某种事实。”
事件创造生活,情绪赋予意义。
我们自说自话地善后了事实,剥茧抽丝出最划算的经验。然后我们讨论着自由意志,重申虚构了一切的自己,不自由。然而我们只是需要自己“意志的不自由”,需要因果关系的自白,自洽到自负。
如果说书中的隐喻充斥着传递性,那《神降》一篇就是一道扶梯,等合适的踏板出现,你跨上去,然后你就活在了被传送的循环里。你觉得这种逻辑无懈可击,甚至于你想拿来攻击它的武器,都镶满了同样逻辑型号的零部件。
不过也没什么可怕的。
如果做了一场醒不来的梦,不如站在带着自己滚动的雪球上,学会推雪球。
就像黑格尔说的:“这条到达科学的道路本身就已经是科学。”
于是发现所有简单的句子都变得不那么简单:“漂亮就行”,“开心就好”,“冲就完了”。
因为它们是远远堆着的积雪,你将裹上这些零星,像好奇胚芽的萌发进程一样,思考既成事实的发展过程。
我们都是宠儿,在某个维度的世界里,自得其乐。
口口声声“难闻得以今相闻”,不过是碰巧看懂了。
在计算不到的未来,第四人称的我,诚实地叙述了一个根植于自然又充满情景的故事,然后他用最模糊的直觉,相信了。
最后,摘录书中的一段对白:
“可我都还没来到这个世界,你又怎么想念我呢?”我问妈妈。
“那时候我就知道,你会想念你失去的人,也就是说,思念是由于失去。”
“但这也可能反过来。”妈妈说,“如果你想念某人,说明他已经来了。”
《衣柜》读后感(四):小说测评《衣柜》|每个「我」都求关注和表达,但缺失了文学的魅力
作者:Jay
校对:litcave 工作室
配图:Online
测评书目:《衣柜》
作者:奥尔加·托卡尔丘克
三个短篇中,最长是《房号》,二十分钟即读完。三个故事所书写的,分别是冥想者、观察家、造物主。
第一篇《衣柜》讲述的是主人公常常想要躲进衣柜,最后和丈夫住在里面。衣柜仿佛成了一只能量坑,不断吸引着主人公。篇幅越短的故事,往往解读的难度也越高。你可以将旧衣柜看作是暂且寄存一个人身上每个身份所需衣服的容器,也可以是现代人逃避外界的最后安身之处,当两人住进衣柜,整个故事变得妙不可言。
第二篇《房号》讲述的是一个清洁工打扫酒店不同房间时的所见所思。每个房间留下肮脏或整洁的痕迹,也映射着旅客的人生姿态和生存境况,甚至暴露最丑陋的一面。清洁工就像尘世的观察者,在她的认知中,那些人没有名字,只是某个标着号码的房间的暂住者。每当旅客走后,她来负责收拾、整理,有次她不得不当着一位旅客的面换床单,情景十分尴尬。
第三篇《神降》,一位程序员在电脑构筑世界,又不断对世界感到失望,最后用洪水和火雨毁灭它。「上帝」是个悲观的、只靠补助度日的程序员。
只有将三篇小说串在一起时,读者才从中感到震撼。这些人物的身份都微不足道,但在各自的世界里,他们分别是思考者、秩序的守护者、创始者(和毁灭者)。如果读到奥尔加·托卡尔丘克的受奖演讲,就能立马发现三篇小说的内核。
今天,我们处于一个前所未有时代,每个人都在以「我」的视角做出最自然、最人性化、最真实的表达,但同时每个人都在求关注,结果导致的是相互遮蔽。
托卡尔丘克认为,绝大部分的讲述者再真诚再煽情也好,始终缺失的,是故事的隐喻维度——隐喻,能使读者舍弃自我,从而成为「小说中的人物」,找到命运的各种共同点。这种能力,当今的作者与读者,都越来越缺失。
文学的魅力就在于隐喻,隐喻从来不属于大众,它对读者的思想品质有一定要求。所以在未来,它注定是越来越小众的,但文学不会消失——它的本质在于叙事,而叙事是人必需的,它很可能会换一种形式罢了。
三篇小说,是一个纯粹的写作者面对当今世界的思想境况。躲进衣柜是为了冷静地跟不同身份的自己和生命中最重要的人单纯地相处;游走于酒店的「房号」之间,是为了站在最中心(打扫和整理每个房间,也即维持秩序的人)同时也最边缘(不起眼的身份)的位置,去观察形形色色的一切并且赋予生活痕迹以隐喻;而《神降》,是作者勇敢而悲观地在叙事上作出新的尝试。
有了托卡尔丘克在文学创作上的清醒,我们才对比看出其余绝大部分创作者的糊涂。托卡尔丘克是孤傲的,像个抱着怀旧情怀的顽固派,甚至口出「大多数人从来都不读书……文学一直都是精英的功课」这样引起大众反感的说辞。
但不得不承认,站在时代前端的「先知」,他们的观点往往是冒犯大众的,至少世界性的伟大作家从来不媚俗。如此的姿态,我们在今天很少能看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