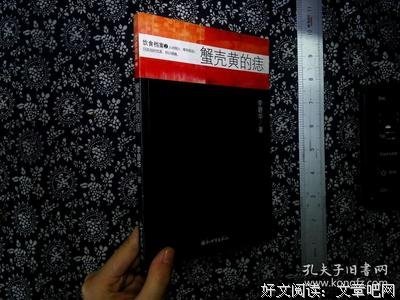
《蟹壳黄的痣》是一本由李碧华著作,新世界出版社出版的平装图书,本书定价:18.00元,页数:123,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蟹壳黄的痣》精选点评:
●还是喜欢李碧华的小说
●精美的美食散文~~
●轻阅读
●感觉广告植入比焚风要多啊= =
●美食家~李碧华就是聪明呀~
●李碧华的食评写的很好看。香港作家的话语系统,与内陆的就是有所不同。学了很多港话:士多啤梨,多士,一客……
●很想看的书,终于找到,很一般吧
●难得李碧华也写饮食,买回来看看---一个人的风格怎么都能流露在文笔里。李姑姑写吃食,像倪匡写男女,都别有味道。
●神神叨叨的老喜欢把人肉扯进去╮(╯_╰)╭
●美食集 顺便看人生
《蟹壳黄的痣》读后感(一):我想一口吃下
李碧华写一样无趣的东西,通常都写的很好。
写起来一定让我想要同样一口吃下。
虽然不理解为何连上海的沧浪亭的面都能写的让我回心转意。
但是,文已至此,我当是被迷惑了。
《蟹壳黄的痣》读后感(二):食物的叹息——李碧华《蟹壳黄的痣》
初识李碧华是在洁尘的书里,她对李碧华赞誉有加,书中摘录的李碧华语录,言辞犀利到近乎刻薄,不由的对这位香港的女作家(多写专栏和剧本)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这本《蟹黄壳的痣》是饮食档案的第二部,谈饮食,悟人生,李碧华笔下的食物永远透着人性。
她写姜,“现实生活中,在厨房拿一个小小的研磨器来磨姜,姜一边磨一边变小,直至完全变成茸状(姜茸,姜泥,姜末),它在你手中是渐渐地渐渐地消失,像生命被岁月磨走一样。”
写白桃,“日本的白桃(白凤)软腻甜蜜,特香。鲜吃更好,极贵。所以在当地吃它的前世,回港买它的今生;在当地欣赏它的灵魂,回港品尝它经过处理的肉体。”原来,一个白桃也有轮回,时移世易,经过现代化机械加工成罐头后,虽可分销各地,名声大噪,但失了原味,便是魂不附体,没了价值。
还有一段写萝卜丝酥饼的很有意思,“好的萝卜丝酥饼‘薄命’——酥皮做得轻、薄、酥、脆、化,仿佛没有重量也没有实质,如同一个灵魂,手指一拈便纷飞四散,从此难以捡拾。”“酥饼皮比一切憨厚沉实的包子皮佻健不羁,受不得压力,也不肯屈服。一个包子可以用些方法塞进不同的容器中,委曲求全,仍然活命,但一个萝卜丝酥饼情愿魂飞魄散,落絮飞花,非常不合群,亦不受思想教育,政治改造,形象转移。”李碧华喜欢萝卜丝酥饼,喜欢那样的壮烈与硬气。我比较喜欢包子,识时务,晓退让,能屈能伸,像《红楼梦》里的宝钗,而萝卜丝酥饼则像黛玉般清高薄命。
李碧华笔下的食物是一个个形形色色的人物,蒸煮煎炸好似喜怒哀乐,一道菜或是一份糕点,总能吃出悲欢离合,五味陈杂的人生来。
《蟹壳黄的痣》读后感(三):人生不外“自由”与“快乐”,活得逍遥
完全是因为李碧华才看得这本书,之前只是看过她的电影,《霸王别姬》,《青蛇》,《胭脂扣》,《秦俑》,书倒是第一次看,书的封皮上写着:人间烟火,哪有极品?只是当时饥渴,所以销魂。
有几个想着有空可以试一下,所以记下来:
1.
坊间一直流传一个瘦身,防癌,降血脂,清理肠胃的秘方,唤“五味汁”,材料如下:
青瓜半条
青椒半只
苦瓜(浅色)半条
西芹两条
青苹果一个
这是五种青色的蔬果,人人都可在家自行拌制,早晚一杯。分量亦随意调整,想甜些加苹果,怕苦减苦瓜。
2.
绿茶和红茶都是我所爱,不过与姜配衬以红茶理想。
早晨起床(有时是中午或下午),头脑混沌,身体虚冷,魂魄未齐的时候,最好喝一杯美味的姜红茶。
烧水,煮至沸腾,冲泡优质红茶,若是茶叶,由它在沸水一冲而下时跃舞一阵,释出芳香,若用茶包,一个不够,最好用两个,蒸三分钟。
然后加入已磨好的姜茸,当然,切几片姜片也可以,但没姜茸出味。亦不必勤奋地磨茸后再以细纱布裹好挤出姜汁,太费功夫了。我觉得姜茸中有植物纤维,“顺便”可促进肠胃蠕动,新陈代新。但不要过量,会酌胃。
糖方面,最好是黑糖,红糖,蜜糖。白砂糖经化学加工,又乏味,所以我很少用。
这杯花过心思做好的红茶,得趁热喝。醇厚香浓,待辣,口感极佳。身体马上暖起来,精神一振,血液循环加速,全部器官和神经系统都蓄势待发,等候一声号令,进入状态,活力充沛,这时写稿,文思非常流畅,很喜欢这种刺激。
还有从没听过的古菜:
像唐代宫廷名菜“雪婴儿”,原来取将肉壮小青蛙,经宰杀剥皮去内脏等过程后,撒上绿豆粉搅拌和保鲜嫩,下锅急炒至汁浓,即出锅上桌,色似白雪,形似婴儿,故名,变态吧?
关于可乐的一些 information:
可乐的饮用者皆视之“液体鸦片”。很多朋友(包括医生),都认为一切软性饮料毫无营养价值。只是一些糖,酸度,糖精和色素添加物,以及大量二氧化碳。对人体无益。一个可乐迷去世,火化之后骨头是黄色的,云云。有连锁快餐店已开始停售 Diet Coke 了。
没想到我们还有相同的习惯:
背包中总是有经常更新的纸片,上面写着这两天要办的事,要买的东西,或要回复的人名。做完一项,把它删去。每天都有新的杂项,每天删删。然后纸片一再更新,好像永无止境。没办法,这就是生活。
但这不是生命。
一桩桩小事解决了,半件大事还未开头。我认为,人生的记事纸中,有五大项——
1. 这辈子必须做的事。
2. 应该做的事。
3. 如果做了便可快乐些的事。
4. 轻松,方便,胜任的事。
5. 活着。
也许每个人都曾经想过,生命中有好几件事若能做得圆满,成功,便不冤枉。但那“几件事”往往因俗物缠身,一直拖延,到后来发现时间不够,时日无多,或失去热情,半途而废。来不及与办不了,都是遗憾。
听过一个比喻吗?你要把一个罐子载满大米和十颗杏仁——如果先装大米,杏仁无法装进去。如果先装十颗杏仁,徐徐倒入大米,就可刚刚好盖上盖子了。先为十颗杏仁定位吧。
《蟹壳黄的痣》读后感(四):再横,你也就是只螃蟹
“西风起,蟹脚痒”,转眼又是“蟹”趣盎然时。金风一送,菊黄蟹肥,持螯赏菊,是如水墨画一般美好的情境。螃蟹虽丑,却奇异地附有风雅之气——很难想像手捧半斤猪头肉边啃边赏菊是怎样一副景象。
自古,中国的文人雅士便对螃蟹情有独钟。晋代与阮籍齐名的隐士毕卓甚至临江而叹:“右手持酒杯,左手持蟹螫,拍浮酒船中,便足一生矣”。拿今时的眼光看,这纯属痴人说梦——毕卓的职业说好听点是“隐士”,说白了其实就是下岗失业人员,若能日日饮酒吃蟹,那大伙还不都抢着下岗?
吟诵螃蟹的文人多如过江之鲫,数量一多,水准也就分出了高下。向来以美食家自居的李渔说起螃蟹来,简直就是一副口水狂流的色情狂模样:“予于饮食之美,无一物不能言之,且无一物不穷其想象,竭其幽渺而言之,独于蟹螯一物,终其身皆不能忘之……至其可嗜可甘与不可忘之故,则绝口不能形容。”啰唆了半天,中心思想其实就是想说“螃蟹好好吃耶”,至于如何好吃,他老人家已经无法用中文来形容了,如果会英文的话,说不定会冒出一句“just do it”。
相形之下,苏轼那句“堪笑吴中馋太守,一诗换得两尖团”在意境上就要高得多,更遑论李白“蟹螯即金液,糟丘是蓬莱;且须饮美酒,乘月醉高台”的咏叹了。
近代文人中,喜爱螃蟹者同样不在少数,梁实秋曾在一篇文章中由螃蟹想起一位同学:“……我有一位家在芜湖的同学,他从家乡带了一小坛蟹酱给我。打开坛子,黄澄澄的蟹油一层,香气扑鼻。一碗阳春面,加进一两匙蟹酱,岂只是清水变鸡汤?”梁实秋向来以美食家自居,但居然拿鸡汤这种俗物来比拟蟹味之美,实是不该。
窃以为,古往今来,对螃蟹的赞美最为崇高者,当属区区在下——直接把螃蟹与爱情相提并论。曾经写过一封情书,内有一句“蟹为水族中尤物,你为女子中尤物”。不过结果很可惜,非但未能打动玉人芳心,反而因为这句话使得一段美好姻缘顿作镜花水月。后来才知,该女子从未吃过螃蟹,因此不知蟹之美。在释然之余,又为其错过如此人间绝味而惋惜。
情书中那句话其实抄袭自张潮,原话为“笋为蔬中尤物;荔枝为果中尤物;蟹为水族中尤物;酒为饮食中尤物;月为天文中尤物;西湖为山水中尤物;词曲为文字中尤物”。沈宏非曾在《蟹后》一文中对七种尤物中的六种提出反对,认为“尤物尚有一种特质,就是无以为继,是审美的终结者”,但是其他六种尤物并不具备此种特质,例如“荔枝的消解者是牛黄解毒片和抗病毒口服液”,但唯独螃蟹是令人惶惶然无以善后者。
青岛曾被评为“最适合居住的城市”,除去红瓦绿树的美景,我想面海而居可以大快朵颐地吃螃蟹大概也是其中一条原因吧。青岛特产的深海梭子蟹虽不比吴地的大闸蟹,可滋味之鲜美,亦是有口皆碑。挑好螃蟹,不加任何调味品,直接上锅蒸15分钟就可以吃了。放在桌上,红甲红螫,八足挺立,脐背隆起,威风凛凛,非常中看。
关于螃蟹的做法,自明代以来几乎就以水煮和清蒸为主,其中又以清蒸为多。清代美食家袁枚就认为“蟹宜独食”,“最好以淡盐汤煮熟,自剥自食为妙”,而“从中加鸭舌,或鱼翅,或海参者,徒夺其味,而惹其腥恶”,是“劣极”的“俗厨”所为。
名人张岱若是有幸听到袁枚“劣极的俗厨”的评价,估计要气个半死。张岱,号称“古之爱蟹者”,可他烹饪螃蟹的方法却实在让人不敢苟同:“以肥腊鸭、牛乳酷、醉蚶如琥珀,以鸭汁煮白菜,如玉版;果瓜以谢橘、以风栗、以风菱,饮以玉壶冰,蔬以兵坑笋,饭以新余杭白,漱以兰雪茶”。看似花团锦簇,实则暴殄天物,真正的爱蟹之人恐怕看到之后都要捶胸顿足。
吃螃蟹的乐趣除了尽享蟹之美味之外,剥壳取肉的过程也是一种享受。《红楼梦》里描写大观园里的“持螯会”时有这样一段,凤姐把剥好的蟹肉让与薛姨妈,薛姨妈说:“我们自已拿着吃香甜,不用人让。”正是不愿失去自足之乐。而吃蟹时“把酒持螯”自有一种高雅闲适的情趣,被文人雅士视为至乐。陆游诗云:“蟹肥暂擘馋涎堕,酒绿初倾老眼明。”可见剥壳食蟹是何等令人陶醉。
鲁迅亦是爱蟹之人,常请弟弟周建人一家到他家里品尝阳澄湖的大闸蟹。在《今春的两种感想》一文中他写道:“……我想,第一次吃螃蟹的人是很可佩服的,不是勇士谁敢去吃它呢?”自此,“第一个吃螃蟹的人”成了一句俗语,形容那些敢于尝试的勇敢者。不过我倒是一直在想,为什么第一个吃螃蟹的人一定是勇敢者,而不是一个饿到饥不择食的人?
话又说回来,吃螃蟹除了美味,那种征服感也是令人神往的,一边吃一边别忘了对那些刚才还在横行霸道的蟹子们喊上一句:“再横,你也就是只螃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