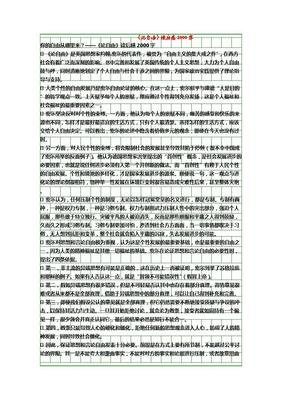
《人的奴役与自由》是一本由(俄罗斯)尼古拉·别尔嘉耶夫著作,贵州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平装图书,本书定价:32.00,页数:200,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人的奴役与自由》精选点评:
●1994版~相较之下还是逃避自由更通俗对现代性的把握更准确,也更容易取得共鸣和思考,明明两书出版只差两年。。。俄罗斯真是个神奇的国度啊
●看了一章,太唯心了,看不太下去
●这个人适合俺
●启发很大的一本书,特别是在人生的一个十字路口上为我点清了许多困惑。挣脱奴役,保存个体人格。
●传统的历史时间吞没着个体的独一无二,这将是侨民文学的唯一问题
●pku。隽永
●别氏此书很斯多葛主义,或者说唯心。主体性如果没有与客观的互动那么就没有意义,主体自由带来的错是现代性无法避免的原罪。
●最需要去除的是自我的奴役
●人无往而不在奴役之中。如何抗拒客体化,如何回归本心。
●“我既然爱、迷恋另一个冰清玉洁的高伟的世界,也怜悯、痛惜这一个卑俗受难的世界——这两个世界常在我的内心里冲突着。这是怎样一种冲突啊,它长驻于我,永不消歇。”
《人的奴役与自由》读后感(一):自以为是其他一切的主人的人,反而比其他一切更是奴隶
当然不懂俄语,但对照读的时候总感觉比城市出版社的那本要来的顺畅。
别尓嘉耶夫的论述让我想到了卢梭在《社会契约论》中开篇的那句话:人生而自由,却无往不在枷锁之中。自以为是其他一切的主人的人,反而比其他一切更是奴隶,这是关于“人”的本体体认。对于一切的不自由,发出怒吼,追寻恶的根源,追到无以复加,以致将其暴露。
将小鸟放出去,给笼子以自由。
《人的奴役与自由》读后感(二):站在高处说话的人
刚才和妻子说起这本书,我还念了开头的一小段,人是一个谜什么的,我突然有感,说,这种语气和口吻,感觉作者像拿腔作势故作深沉,或者说像站在高高的地方和我们说话。如果是个分量轻根基浅学识不很深的人,一张口,说的话稍微“轻”那么一点,就会让人觉得故弄玄虚,不值一哂;但这书的作者说出来的话很有分量,无一字虚言,每个字都如重千钧。而且,这个人,不是说一句两句,是站在那高高的地方,长篇大论的说,长时间的说,这就太厉害了。或者说,感觉作者就是一座有着很深且牢固的基础的高大的建筑,不由得让人仰视。
妻子说我平常对她说话态度也有点高高在上的感觉,我说,我没那么牢固扎实的根基,我在高处大概是因为我“轻”,所以双脚离地,浮在了空中。
《人的奴役与自由》读后感(三):读后札记
个体人格不能来自于自然,因为倘若来自自然,它就受制于社会学生物学了。个体人格自成一个完整的宇宙,永远也不能是某个恢弘整体的一部分。
社会学层面的人仅仅是表层的人,个体人格可是无意识的根基,理性仅仅是其携带物而已。
个体人格是主体中的主体,是抗拒客体的存在,个体的一切抉择必须是内在的,而不是外在决定的
个体人格的价值高于一切共相,高于一切集体,个体人格本身也是共相,不是宇宙的产物。但是同时,个体人格又总是趋向于以自我为中心的封闭状态。
个体人格的第二个特征既是自身不能满足,它是孤独的,它必须趋向于其他物,或者向上,或者向下。
个体人格存在的目的是超个体价值的实现
意识中有超个体的因素,会导引着个体人格走出“我”,但是意识又有客体化的可能,它会阻碍个体人格的超越。
个体人格在于个体人格交流的过程中容易陷入客体化的泥沼之中,宗教教条就是这样的一种客体化的结果,这是神性-人性客体化的结果。
个性是个体人格的彰显,是关于自由选择的体现。
苦修本质上是人对客体世界的抗争。
个体人格既是共相,又是整一
无神论否定的是神相,而不是神性,如果连神性也被否定了,人就不该称之为人了(人性即神性)。所谓和谐的自然也是虚伪的骗局,因为自然在这里也已经客体化了,它依旧是一个客体化的理想,不能给予人自由。
第一个阶段:识破客体化世界的虚伪
第二个阶段:经受住与客体化宇宙结合的诱惑
第三个阶段:达到精神自我对自然的突破
当人开始接纳模仿性时,便失去了性格,成为了社会分子。社会化不仅降服野人,也降服天才。
文化的产生已经意味着客体化,意味着创造的终结。
文明与文化通过树立偶像来客观化世界,最终束缚人,将人变作机械。
自我中心主义是为自己创造了一个美好的,精致的偶像存在,并受到它的诱惑,成为了自己的奴隶。
有产者不应将财产视为手段,财产是用以保证自由与独立,而不是限制自我人格发展的桎梏。
革命总是掀翻旧有的神像与统治者,但很快又要树立新的偶像。
纯粹审美者将自己的激情外化,客观化,往往不参与生活,只是消费者,而不是创造者。
真正的艺术是对生命的转换,是对客体世界重荷与畸形的消解。
人认识美—这是一项主观创造的活动,而不是客观认识。
美是以创造行动拒斥世界的奴役。
死亡是人人在劫难逃的一种恐惧,一种奴役。
人因为对死亡的恐惧而杀害其他生命,做了死亡的奴隶。
传统的历史实际吞没个体
《人的奴役与自由》读后感(四):邓晓芒:人的坚强与软弱——关于《人的奴役与自由》
近读别尔嘉耶夫《人的奴役与自由》,深为其中的真知灼见所激动,但同时也有某种失望。我虽不能说,他所想到了的我都已经想到了,但至少,我所未能解决的问题,似乎他也同样未能解决。
别尔嘉耶夫对“个体人格”的分析,特别是对其个体性与共相(具体共相)的关系的分析,真是十分精彩。现代思想(更不用说“后现代”了)从某方面说越来 越肤浅化(虽然越来越“精密”),已很少有人能真正理解从柏拉图经过库萨的尼古拉、波墨到黑格尔和马克思的辩证真理。人们从常识或自然意识的立场将共相看,作许多个体的“集合”或“共同点”,把个人看作共同体的一个组成部分,他们怎么也不能理解,在何种意义上我们可以反过来把自然、社会、宇宙都看作是“个体人格的一个部分”,也就是看作一个人形成和创造自己个体人格的“材料”。这只能表明他们作为个人对于他们被抛入其中的这个周围世界已经失去了创造力,即丧 失了个体人格。别尔嘉耶夫则极大地强调了个体人格的这种独立性和创造性。
在他看来,每个人都有天才性,天才是不分等级的,而是有无限差异的、各自独立的,但又是渴望沟通的,“人格主义也许仅仅是有关可沟通性的理论”。但这种沟通又决不以放弃自己的独立性为代价,决不能把自己完全抛出去(“奉献”出去),使之“客体化”或“异化”:“那种为克服主观性,则把共相的观念进行客体化和实体化的做法,是盲人导路,绝非真正意义上的超越”。换言之,如果有人为一个外在的共相(共同体)而牺牲,却不为自己人格中的内在共相而牺牲,他就把真正的共相本身牺牲掉了。历代“愚忠”的牺牲者就是这样,他们的一切崇高的理想到头来只是某个政治野心家手中的临时工具。别尔嘉耶夫最后将他的人格主义归结到自由:“个体人格的个性指独立性、凝聚性、自由”,“自由不应是人的权利的宣言,应是人的责任的宣言”。
但自由必定带来痛苦。“个体人格就是痛苦”,“人世间的痛苦即个体人格的生成”。人类之所以甘受奴役而不能忍受自由,正因为这自由使人苦恼,它是黑格尔所谓的“不幸的意识”。但正是在对这一点的分析上,暴露了别尔嘉耶夫在对自由的理解上尚有不彻底的一面。他没有看出(至少没有强调),自由所带来的痛苦不仅在于周围环境的压迫,而且在于自由本身的悖论。别氏到处发现悖论(Paradox,中文译为“悖异”),强调“人是矛盾的生存”,但唯独拒绝承认自由和个体人格本身存在着悖论。在他那里,个体人格是人生的“一个光灿灿的方向”,一个“冰清玉洁的世界”,而“自由人仅仅在于能拒斥自己良心和意识的异化和 外化”。对此我深表怀疑。黑格尔早已指出,外化和异化正是自由本身得以实现的条件,没有外化和异化,自由只能是一句空话,一个美好的梦。当然,外化和异化 (客体化、实体化)必然带来痛苦、奴役和不自由,这正是自由本身的悖论所在;但也正是这种自由的异化所带来的不自由,使得自由的历程不能停步,不能驻足于 某一种生存状态,而要拼命地继续挣扎前行,去打破自由本身造成的枷锁而争取新的自由。所以在黑格尔那里,自由人即使在和周围环境作战,实质上也是在和自己作战,和自己的自由的悖论作战。
正是自由的这种自相矛盾性,作为内在的痛苦和动力,迫使人把自己的自由一步步提高到更高的水平,而逐渐展示出自由的更深刻、更丰富的全部内涵来。这就是黑格尔对自由的“历史主义”的理解。从这种眼光来看,“自由人”并不在于能“拒斥”异化,而正是在于能勇敢地投身于异化,同时又积极地在异化中寻求克服异化的道路。这条路决不是“光灿灿的”,而是黑暗中的摸索,充满血污和罪孽,是黑格尔所谓的“绝望之路”和“怀疑之路”;在其中,一切发生的都不是真正愿 意的,只有那个自我超越的形式才是他所愿意的。只有这样理解,别氏的这句话才有了着落:“人是提升自己和超越自己的生存。人的个体人格的实现即不断地超越”,所以“任何一个人都不能大言自己的个体人格已经完成。”
然而,个体人格的这一悲剧性的悖论,究竟是证明了人的坚强,还是证明了人的软弱呢?看来别氏的结论是后者,因为他从中引出了一个“上帝”(虽然是特殊意义上的上帝):“个体人格的特性即在于它自身不能自足,不能自身实现自身,它的生存一定需要‘他者’。”人在奋斗中发现自己的有限性,陷入痛苦和矛盾, 这的确是人的命运;但为什么因此就一定需要一个“他者”来帮助拯救,这始终是我的一个疑问。明明是人在自我超越中创造和发现了超个体的价值,怎么会一变而为:“如果没有超个体价值,没有生命的神性颠峰——上帝,个体人格便不能走出自身,不能实现自身的全部生命”?人的自由的“黑色的”悖论怎么会一变而为人在上帝面前的这一“光灿灿的”悖论:“人就是既自由又依赖的生存”?这一转化怎么转过来的?对此,别尔嘉耶夫始终不肯明说,在他看来这正是人性最大的谜,是不能用理性、概念和哲学说清楚的,只能诉之于个人神秘的“精神体认之真理”。但这就等于说:信不信由你,反正我信。
《人的奴役与自由》读后感(五):绝望之中的希望
人的奴役与自由
可以说,别尔嘉耶夫是极具人本主义(或者他所说个体人格)的哲学家,他思考的问题,总是高瞻于全人类的视角,在看透种种黑暗后仍苦苦探索着光明与自由,他说,“我始终确信,自由高于存在,精神高于自然,主体高于客体,个体人格高于共相-普遍的事物,爱高于法则。”而这句话,也正是他思想的精华集中概括。
嘛,别这么严肃,我只是写着玩,还是通俗的说话好了。
总之,看多了科学对人类中心论的无比摧残,以及虚无主义和悲剧思想,再来看别尔嘉耶夫这本书,不能说是充满希望,但总是有“即使被各种东西束缚,我们还是能拥有自由~”的感觉。同尼采异曲同工,他塑造的虽不是超人,但也指出了人类最有希望的目标:个体人格。
个体人格与自然、物理、社会属性的个体人不同,属于自由和精神的范畴。他说:
个体人格是完整的共相。
个体人格是精神,灵魂,肉体的结合。
个体人格绝非世界的部分,而是小宇宙,世界是个体人格的部分(= =喂,中二?)
个体人格生存的奥秘就蕴含在它的,绝对不可置换性、唯一性和不可比较性中,是阐述无限主体中开启生存奥秘的主体。
个体人格是抗争、努力,战胜自我的世界;是解放、拯救,战胜奴役的世界。
个体人格是我的整体思想,我的整体意志,我的整体情感和我的整体创造行动。
个体人格是理性的生存,但是理性不能决定它,仅仅是理性的携带者。理性自身不是个体性的东西,是共相的,普遍的,非个体性的东西。
注意,最后一条对我很有启发。如果说康德思想体系的”最高统治者”是纯粹理性,人是认识有限且很难达成共识的群体,所以只有以普遍的、非个体性的理性来作为衡量事物的尺度,才能得到公正。而别说,理性不是我们追求的最后形态,完整的人格才是最重要的。看起来似乎目的不同,互相矛盾。但是反过来深究呢,别的个体人格的精神并非冲动的感性,而是建立在理性思维之上的精神,别推崇康德,更在康德之上深深思虑着人类的未来。
或许他已经看到,过多理性的危害。如同艾略特那片寂寞的荒原。
以及艾伦《嚎叫》开头的呼喊,“我看见这一代最杰出的头脑毁于疯狂。”
虽然不仅仅只是理性的影响,但是现代社会无疑病了,而且病得严重。
在《人的奴役与自由》一书中,别最多强调的是各种奴役。人受存在、上帝、自然、社会、文明、自我、国家、民族主义、贵族、金钱、革命、乌托邦、爱欲和美、艺术的奴役,涵盖之广,真的如同“他思想的百科全书”。
但是说了这么多,别想强调什么呢?
他把人类摆在精致的手术台上细致解剖,得出“太残酷了,人就是各种客体化的奴役~”论点,而其中最严重的,就是近代人把人放在自然实体上,让有限之物遮盖了人自身携带的上帝意向。而挣脱奴役,也就在于挣脱这些意向的束缚。是不是有些熟悉?好像东方自古以来的超脱、自然,和佛家思想的感觉,或者说庄子?
当然,别与他们有很大的不同。在我看来,西方哲学思想首先说是在科学与理性的道路上走了远远一条路,然后发现了诸多问题和弊端,于是又绕回头来重新认识曾被摒弃不起眼的“感性精神”,但这不仅仅是原地转圈。看过黑暗之后的光明更加耀眼,有了这么多的哲理、逻辑、分析和科学,再去欣赏老庄、佛家的顿悟,会别有体会吧。
回过头说别尔,在最后一章里,他创造性的提出了三种不同的时间:宇宙时间,历史时间和生存时间。
简单的说,宇宙时间是自然的,历史时间是社会的,只有存在时间是属于精神上的,个体自由的。人生活在多重向度和不同位置之上,生存世界突破宇宙与历史的种种限制,是人类追求价值的意义。
别尔的这种思想是在不断的矛盾和挣扎中的最后选择,他的话有时高深艰涩,但是他的思想触摸起来却十分平易近人,有冰冷也有温暖。他说“我的思想中总是矛盾交织着两项的因素,即贵族式的理解个体人格、自由、创造,又相信社会主义的需求能确认每个人的价值、尊严,能确认最下层人的基本生活权利。换言之——我既热爱、迷恋另一个冰清玉洁的高伟世界,也怜悯。痛惜这一个卑俗受难的世界,两个世界常在我的内心里冲突着。”
真的,读到他这段话,我着实被感动到了。这种痛苦和挣扎在哪位哲学家心中没有呢?同时也在我心中引起了共鸣,现在我在各种哲学和思想中孤独的徘徊,究竟哪些是属于我的真理,我能创造的又是哪些呢,我的选择将是我的思想,将是我本身,我不断回头看无知幼稚的自己,又不断在这条艰辛少有人走的路上踽踽独行,这么说恐怕有些过头,但事实上真的如此呢,那么,世界无限宽广,我将何去何从……
当然,很多人恐怕要说笑,何必这么认真,人活着干吗,就是活着嘛,想那么多自己找罪受。
或者“一认真你就输了。”那我可能早就输了,输在这些说笑中,但是我只单纯的想,不总思考的话,有一天会变笨的。
我笨吗,我应该很笨,然而又不想让自己一直笨下去,总之,这也是个纠结的问题,既然他人不是我,就让我自己纠结下去吧……
最后,以马尔库塞书中瓦尔特的一句话结尾:“正是有了那些不抱希望的人,希望才赐予我们。”
感谢别尔嘉耶夫,感谢马尔库塞,感谢康德,感谢那些不抱希望的,仍痛苦着矛盾着的人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