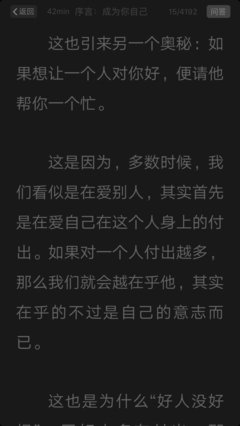
《词语破碎之处》是一本由(德) 格奥尔格著作,同济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平装图书,本书定价:22.00元,页数:288,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词语破碎之处》精选点评:
●文人布灵顿,出入需谨慎。
●翻译严重令人失望
●比如说das jahr der seele前三首季节诗还没有翻译整齐就录了进去,诗的标题也取得莫名其妙,诗的内部Strophe的题目和诗的题目没什么区分,还以为各个Strophe就是独立的诗歌 。。。如此种种,给人感觉非常不负责任。。
●这翻译……哈哈哈哈哈哈。不过我觉得即使翻译好了他的诗歌也没他人生精彩。
●欣赏不了
●对了一下德文,然后真的不是很喜欢这个翻译……
●马克西敏之后,方为可观。
●每行字数都一样什么鬼
●最后一篇讨论格奥尔格、海德格尔和词语的文章是全书最精彩之处,格奥尔格对于神秘莫测、晦暗的诗性体验进行的思性探询,那种离去般的前往和缄默的方式大概是他诗歌最大价值所在了,可以感受到他老师马拉美的影响。至于另一部分表达意志的、回溯和宣扬优秀种族的造神诗歌则乏善可陈,令人厌恶,充斥着宗教迷狂和纳粹宣言式的煽动语言,这大概是格奥尔格圈能存在那么久并在当时有那么大影响的原因吧。
●不知道是翻译的太奇怪了,还是本身写的就这么晦涩奇怪、弃读。
《词语破碎之处》读后感(一):摘:词语
我把远方或梦之奇迹
带着前往我国的边地
我苦苦守候命运女神
从泉源寻得她的名称
随即我将它牢牢握住
如今它光彩穿越疆土
我也曾历经漫漫长途
带去一颗柔美的珍珠
搜索良久她给我回复:
“无物安睡在此深处”
它随即从我指间遁逃
我国就再未获此珍宝
源于悲哀我学会放弃:
词语破碎之处无物存在。
《词语破碎之处》读后感(二):摘:七月之忧
夏花还散发着馥郁的芳馨
田旋草释放刺鼻的种子味
你拉着我干枯的扶手,在骄傲的
花园里,芝麻显得陌生
从遗忘中你诱出些梦幻:孩子
在贞节的土地上奔跑,成熟的庄稼
在收获的红的霞里,赤裸的割草人身边
有闪亮的镰刀和干涸的水罐
午间的歌谣里,马蜂昏昏欲睡
有什么滴沥在他的额头
穿过罂粟叶影构成的
绵薄防护--大滴大滴的血。
我曾有过的,没有夺走过去。
饥渴如那时,我躺在饥渴的原野
疲惫的嘴发出呢喃:我何以
厌倦鲜花,厌倦美丽的鲜花
《词语破碎之处》读后感(三):是夜微闻 稚子清歌踏月而来
George和许多许多德语诗人一样,对于我是一个陌生的存在,或者根本就不存在 (完全是因为我的浅薄无知),直到一见如故。第一次遇见这样纠结的一个男人,而且毫不羞赧于自己的纠结的不愿长大业已长大的尚有稚子之心的成年人,是因为他的一封信,一封给一位女性朋友的信:
“······也许,我应再次向您证实您知道已久的事情?我为何要对我的朋友们讲述那些伴随我全部历程的危险深渊——并且恰好是最近那些特别可怕的深渊?在那样的时候,朋友们往往都只能无助地站在同情的距离之外······对于那些毫无慰藉的事情,竟然没有任何一个能够拯救灾难的办法。无人知晓那些事情。我无法度过我的生命,除非是在最完善的外表辉煌中。因此,我为之斗争、受苦和流血的一切,不值得任何人知道。然而发生的一切,也是为了朋友们。他们那样看待我,就是他们最为巨大的生活慰藉。于是,我就那样一道为他们斗争、忍耐和沉默。我不断地濒临最极端的边沿,我所付出的,就是最后的和所有可能的····即便无人预感到这一点···”
莫光华先生的翻译中正好略去了那段要不要和这位朋友相约去瑞士的回答,那几句近似于任性和无私坦白的话,真的将一个纠结的没长大的男人诠释得淋漓尽致。而上面的这几句则是一个敏感的早醒者,在众人皆睡的孤独中,对未知的忧惧:一种对灾难的直觉感知又无从证明的不测感和无力感。这种对自己、言语、梦、民族和文明的无孔不入和无从捉摸的游离感,滋养着他的诗兴,同时也吞噬着他的诗度:就像无数人描绘过的那个黑洞,他也一样的好奇紧张和忧心忡忡。偶尔,他也会暗自骄傲,他能看见,他能听到,他能一个人在空无一人的街巷游荡。
George虽然如此纠结,依旧让人欲罢不能的大概也是因为他的纠结:他将他的忧虑不仅写进他的诗行,有时也写进了他的生命。虽然对他的真实生活所知甚少,但总有一种感觉,他好像在以自己诗的理念生活,或者说,他的生活是诗歌的具化。如果说他在他的Kreis中Performance他的诗,并因为感化了一批年轻的白纸一样的追随者而沾沾自喜,或者将之视为生命价值的话,貌似是很大不敬的诋毁,但是或许这种“表演欲”原本也是他本人无法抑制的,他是为此而生的,所以很难说这种诗行合一的诉求是künstlich, 而是Kunst本身,因为他不是有意为之,或者说他自己有意manipulieren了这种行为。
先知者的烦恼,以及不被世人所理解所认同,甚至被视为异端的苦闷,这只是硬币的一面。另外一面是,他所感知的美也比常人多,所以上帝是公平的。人生如寄,George先生和我们每一个人一样走在自己的路上,只是他感受到更多的美和恶,只是他醒着的时候比我们长了那么一点。他的难得在于,独立于世,不仅不愿受制于任何一个政党和团体,也不愿情感上依赖任何一个女人,他甚至都没有多少相知甚笃相看永不厌的朋友,他倾其所有所追求的艺术 Autonomie和Souveranität和中国文人不为五斗米折腰的清傲虽然有所相似,但绝不完全相同:应该是两种完全不同的出世入世观念和生命价值取向。很难想象,如果George先生Ohne George-Kreis会什么情形。同样也很难想象,中国文人如杜甫没了“老妻画纸为棋局,稚子敲针作钓钩”,如苏轼没了子由会是什么样子。大概是对Individuum的理解,始终不可苟同吧,中国人的家国观念深入骨髓,艺术中Individuum必须以此为依托而存在的。
我的偏见,诗歌是不可译的,被这本书完美打败。虽然形式和语言一样,被很多人视为Oberflächlich的东西,但是看到形式规整字数一致的翻译,还是着实惊艳到了。就如传言中George先生喜欢俊美年轻的朋友圈一样,我也喜欢美丽的字眼和巧妙的淘气的句式。我想,我以前那种阅读译文的方式,一字一句的对照阅读,虽然很乖,但是从此之后大概要与之告别了。因为要敢于给译者创造的空间,当然在善意的前提下。译者的贡献在于,将Ta理解的作品介绍给大家,不满足于此的读者,当然会不辞劳苦学习这门语言,否则必须sich damit abfinden。
《词语破碎之处》读后感(四):格奥尔格对词语的诗性体验
[德]F.W.赫尔曼 著 何晓玲 译
(本文节选自 Friedrich- Wilhelm von Hermann:《细微,但却鲜明的差异:海德格尔与格奥尔格》(Die zarte, aber helle Differenz: Heiddegger und Stefan George), Frankfurt/Main 1999. 文中所引诗句均为莫光华所译。)
在我们关于就语言本质进行的“思性探询”(denkendes Fragen)的阐释学基本特征的意识之中,阐释学的主导思想因为这一探询的缘故而被找了出来:语言的本质——本质的语言。海德格尔将这一主导思想理解为对被找寻到的“思性体验”(denkende Erfahrung)的积极回应。由此出发,意味着这一主导思想是“踏入一片我们在其中随时均有可能对语言进行思性体验的区域的第一步的尝试”。在这一区域里,探询的“运思”(Denken)偶遇了与“作诗”(Dichten)活动的相通性。在此所指的,不再仅仅是施特凡·格奥尔格的作诗活动。因为,作诗活动本身的完成,时时都来自一种对语言的体验。即便是“诗性体验”(dichterische Erfahrung)的本质,也存在于那一探询的运思所出现的区域。每一次的诗性体验所体验到的与诗化出的东西,或许也会从这种正在发生着的抛向当中,从诗人那倾听性的理解与以他诗性构想的方式对之作答的区域的对应之中,一跃而出地与诗人相遇。这一诗性构想,就如同那种思想家的构想一样,是一种从这一正在发生着的抛向(对应)当中得以完成的构想。
阐释学的主导思想的获得,是运思迈入那片使对语言进行思性体验随时成为可能的区域的第一步。为使自身继续进入这片区域,这一探询的运思再次转向了施特凡·格奥尔格的诗性体验。格奥尔格在《词语》一诗和《歌谣》的其余诗中所作的诗性言说,被海德格尔描述为“一种等同于离去的前往”。作为“离去”(Weggehen), 这一“前往”(Gehen)所离开的,是诗人早先在其中自视为立法者与预言者的诗性的自我认识。然而,只有当这种离去是一种以诗性词语的秘密为目标的、有经验的前往之时,诗人才可能离开那进行立法和预言的作诗活动。当这种新近体验到的诗性词语,使那些诗性之物能够存在并在存在之中保有它们之时,这种诗性词语是神秘莫测的。
组诗《歌谣》是以我们上文已顺便提到过的格言拉开序幕的:
我仍思虑我仍安排 我仍爱的,都有相同的特征在此跟随于被说了三次的“仍”(noch)之后的行为,对诗人将来的作诗活动进行了指称(nennen)。之所以说这一作诗活动是发生在将来的,是以对于诗性词语已有过的体验为依据的。从对于诗性词语已有过的体验中出发,这“思虑”、“安排”及“爱”完成了自身,并因此而具有了“相同特征”。这一格言令我们知道了,这些在该诗集中合为一体的诗作,是从相同的体验之中创作出来的,尔后,它们具有了相同的特征。在对诗性词语进行了体验之后,诗人“仍”在思考、实施和爱恋过的东西,具有了相同的特征。
在现在开始的探询的运思同格奥尔格的作诗活动所进行的第二次阐释性对话中,思性阐释完成了我们在第一次的阐释性对话里面就已经指出了的那一步。在这一步里,产生了格奥尔格用“珍宝”(Kleoinod)一词所指之物的第二种解释。(1957年底,海德格尔在弗莱堡大学作了题为《语言的本质》的演讲,1958年5月做了题为《思与诗:论格奥尔格的<词语>》的演讲。对“珍宝”的第二种解释就始于该演讲。)
在第一种解释中,珍宝代表着一种特别的、尚待诗化出的东西,一种诗人向远古的命运女神为其索要进行指称的名称的东西。在命运女神对给予这一用于指称的词语的拒绝当中,诗人获得了对于诗性词语的至关重要的体验:诗性词语不仅仅是被用于赋予诗性的想象之物以艺术的语言表达,就那些诗性之物而言,它将存在赋予了它们。这样,诗性之物从这一词语的本质出发,才成了它们所成为的东西,才得以以它们所显现的方式显现出来。根据《词语》这一演讲所言,诗人的放弃是甚合“词语那更高的支配作用”之意的。而根据这种存在来看。词语“才让物成其为物”。这样的“让其存在”是一种决定:“词语将这一物决定为物”。然而,这种发生于语言的本质之中的决定,并非是作为“任何存在之物的存在原因”的条件,相反,它“决定”(Bedingnis)这一行为本身。这一取自那更为古老的预言的词语,在此对词语性的语言的赋予存在的支配作用进行了指称。
现在开始的第二种解释,将这一珍宝解释为那种已被体验到的诗性语言因其能够赋予存在而显得神秘莫测的本质。当诗人为这一珍宝索要对它进行指称的词语时,他所追求的是一种应将其作为珍宝被体验到的神秘莫测的本质以诗意的方式表达出来的诗性语言。根据第二解释,诗人之所以找寻这种诗性语言,并非是为了这种或那种尚待诗化出的东西,而是为了那种神秘莫测、尚待对之进行诗化、尚待对其进行诗性指称的词语本质。然而,对于诗人来说,这一至关重要的词语确实被拒绝给予的。
然而,这一阐释性命题,即:格奥尔格以“珍宝”所指的,并非仅仅是一种尚待诗化出的东西,而是除此之外还有并且是首先还有的词语本身那种神秘莫测的本质——又如何才能立足呢?海德格尔转向组诗中的其他诗作,赢得了为此所需的依据。珍宝本身,便是从其意义出发提请人们留意组诗中的其他诗作的东西。因为,一件珍宝是一件被准备给予一位客人的小礼物,是一种待客的礼物。说得再远一些,一件作为礼物的珍宝,表明了不同寻常的恩宠。这一珍宝是借此处于客人与恩宠的意义关联之中的。如果我们将组诗中的诗作通读一遍,并留意珍宝、客人与恩宠之间的意义关联的话,我们就会突然看到一首描写这位客人的诗作,但对这位客人的描写却是在与《词语》一诗相近的意义中来进行。按照顺序来看,它是第五首,题目是《海之歌》,由六段四行为一段的诗节所构成。
彤红的火球轻柔地 沉下海平线 我歇在沙丘:会否 出现一位可爱的客人 此刻,家中一派荒凉 鲜花萎谢于咸的泡沫 陌生的妇人最后的屋里 不再有人落脚 身躯明亮,眼眸清澈 这时,一个金发的孩子 他边跳边唱走在路上 渐渐消失在大船背后 我眼见他来,我目送他去 虽他对我一声不响 我也不知何言以对 他短暂的目光却给我快乐 我炉灶安稳,屋顶密实 可是里面毫无欢乐 我把所有的网补全 我收拾厨房和卧室 我坐下,在海滩等候 我托着脑袋思忖: 我这一天有何意义 假如没有那金发的孩子?这首诗与《词语》一诗之间的相通性是极为明显的。第一诗节对以渔夫形象出现的诗人进行了描写。在夜晚时分的沙丘上,这位渔夫翘首盼望着一位“可爱的客人”的来临。
第二诗节告诉我们的是,诗人家中是何等模样。他走出那里,为去到那应如约而至的客人的近旁,而走向沙丘。由于诗人的家远离客人在沙丘上的可能的到达之处,因而,在那里有的只是一派荒凉。鲜花在萎谢,“最后的屋里”的“妇人”也是陌生的。这样,再也没有人在她那里“落脚”。
第三诗节对盼来了的时刻进行了描写。在这一时刻,那位客人现身了——这是一位以有着一头金发的孩子的形象现身的客人。第三诗节用这位客人、这个孩子告诉我们,他跳着舞,唱着歌,最终,再次消失于大船背后。跳舞和唱歌,是那种作为歌咏性的诗作的歌谣的必不可少的部分。这样,与语言及词语的关联,首次在突然之间变得清晰夺目起来。
第四诗节对诗人与他的客人——即这个孩子——之间的关系,以及这位客人与诗人之间的关系,进行了描写。当以渔夫形象出现的诗人在沙丘上等待着客人的来临之时,他“眼见”着后者的“来”。而当客人再次消失,离诗人而去的时候,诗人又“目送”他“去”。对于客人的来临,诗人事先便进行了预想;而对于客人的再次抽身而退,诗人则在事后进行了深思。诗人将他那位现身之后又抽身而退的客人,作为了决定自己行动的准绳。这便是他与客人的关系。
然而,第四诗节借客人还告诉了我们,他自己同诗人从未交谈过。而在诗人这方面来说,诗人在他的这位客人面前也“何言以对”。能对这位从其自身而言从未与诗人交谈过的客人作答的词语,便这样远离了诗人。然而,客人那“短暂的目光”却给予了诗人以“快乐”。他注视诗人的目光是“短暂”的,因为,为了再次旋即抽身而退,客人只是现身了片刻而已。然而,对于在诗意的画面中所展现给诗人以及远离了诗人的东西,诗人却没有对之进行指称的词语。
与第二诗节相类似,第五诗节描写了在这所独特的屋子里的欢乐的缺失,也即是说,在远离客人在沙丘上的可能的到达之处的地方的欢乐的缺失。尽管他的炉灶安稳,他的屋顶密实;尽管作为渔夫的他补全了所有的网,收拾了厨房和卧室,然而在那里面,却毫无欢乐可言。只有在盼来的客人向他现身的地方,欢乐才上身为主宰诗人的情绪。
第六与最后一段诗节将这一点表现得真切可见、清晰可闻:没有客人在沙丘上的来临,诗人的这一天是不完整的。诗人在海滩上等待着,如果这位被翘首期盼的客人并未向他现身的话,那么,他作为诗人所拥有的一天,是空虚无物和毫无意义的;即便是有这仅仅是片刻之间的现身,一切也依然如此。
《海之歌》这一描写了诗人的这位客人的诗作,对这位客人进行了指称,但却又没有对他进行指称。正如《海之歌》一诗中的客人一样,《词语》一诗中的珍宝也是一直处于一种未被指称的状态的。两首诗作互相阐明了对方。即便是在《海之歌》一诗中,格奥尔格也对诗人与既被赋予给了他却又远离了他的诗性语言的关系加以了描写。只有当他通过客人的到达、通过诗性词语的被赋予而有所获赠之时,诗人的日子才是完满的。尽管这位客人在现身之时又唱又跳,但他却不曾和诗人交谈过。他不曾和诗人交谈,这样,诗人也就不能回答他,也就不知道在自己对这位现身的客人,也就是说,对被赋予给了诗人自己的诗性语言,进行的回答中所应该使用的诗性词语了。这一在客人到达的图像中被赋予给了诗人的诗性词语,未曾向他言说,这样,诗人也就不能将这一被赋予给了他的诗性词语,在其神秘莫测的本质中,以特有的诗性方式付诸词语了。诗人所能做的,就局限在对放弃描绘这一神秘莫测的词语本质的词语所进行的诗性指称上了。《海之歌》这首诗,以对将这一诗性词语赋予给了诗人的事实进行描写的方式,对这位客人进行了指称。然而,这一诗作却又同时让这位客人处于了被指称的状态。因为,诗人是不能以一种不同寻常的诗性词语,来明确地对语言的这一神秘莫测的本质进行指称的。
《海之歌》一诗对客人所做的描写,是以诗性指称与不进行诗性指称这两种方式加以完成的。然而,这位客人即是诗性语言的诗性图像。这一诗性语言将自己赋予给了诗人。诗人等待着这一语言,就如等待着一位客人一般;而诗人能够对它进行把握的程度,就如同我们能对一位客人的到来进行控制的程度一样,是小之又小的。虽然当诗性语言将自己赋予给了诗人之时,诗人便能够进行作诗活动,然而,他在作诗活动中,对于这位客人本身进行指称、对那神秘莫测、不可把握的语言本质进行指称,却是无能为力的。用以进行这一诗性指称的,不论是这位客人也好,还是诗性词语也罢,都是远离于他的。
出自同一组诗的另一首诗,十二首诗当中的最后一首,是一首无题诗。它描写了能被赋予给诗人的最高的恩宠。然而,它却是以此种方式来对这一恩宠进行描写的:这一恩宠在诗中虽“被言说出来”,但却没有“被指称出来”。这首诗共四节,每节四行:
你纤柔纯洁如一束火焰 你像清晨的温霭和光明 你是些宝树绽放的新枝 你是一泓清泉幽密质朴 你在艳阳的苇簟上陪我 你在傍晚的烟霭中看我 你照亮我阴影里的道路 你是清风你是暖暖微飔 你正是我的愿望和思想 我从每一缕空气呼吸你 我从每一杯水中啜饮你 我从每一股芳香亲吻你 你是些宝树绽放的新枝 你是一泓清泉幽密质朴 你纤柔纯洁如一束火焰 你像清晨的温霭和光明第一节诗是一种对于被赋予给了诗人的恩宠的赞颂,这是存在于其神秘莫测的本质中的诗性词语的恩宠。诗人将这一恩宠赞颂为纤柔而纯洁的火焰、温蔼和明亮的清晨、绽放的新枝以及幽秘而质朴的清泉。
第二诗节对这一恩宠与诗人的关联进行了描写。这一赋予了诗性词语的恩宠,在艳阳的苇簟上陪伴着诗人。在傍晚的烟霭中,它环顾着诗人。这一诗性词语的被赋予,照亮了诗人阴影里的道路。对他来说,它是清风,它是给予生命的微飔。
与此相对,第三诗节对于诗人与朝他而来的恩宠的关系进行了描写。诗人渴盼着这一恩宠,渴盼着这一真正的诗性语言的被赋予。他想着它,呼吸着它,啜饮着它,亲吻着它。
第四诗节是第一诗节的一种变体。第一诗节中的第三和第四行是第四诗节中的第一和第二行,而第一诗节中的第一和第二行在第四诗节中变成了第三和第四行。第四诗节像第一诗节一样,对被赋予给了诗人的恩宠进行了赞颂。这一恩宠是被赋予给了他的诗性语言,这一语言将这一恩宠,在新枝、清泉、火焰与清晨的图像之中,来加以赞颂。
在这首由四段诗节所构成的诗作中,这一被体验到的、被赋予了的诗性词语的恩宠,被言说了出来。然而,这一恩宠却不能在某一诗性词语当中以如下的方式被指称出来,也即是说,在这种词语性的指称当中能够特意谈到这一诗性词语的本质以及它的来源。
即便是在此处,诗人也必须放弃为这一在其神秘莫测的本质之中已被诗性地体验到的语言找到一个诗性词语的尝试。在这首诗中产生于恩宠的一切,在《海之歌》与《词语》中则是分别发生于客人与珍宝之中的。这一在其已被体验到的、赋予着存在并由此而显得神秘莫测的本质之中的词语,每次都被以诗性的方式言说了出来,但却并未同时也被指称了出来。
这样的一种不指称显得就如缄默一般。然而,严格地来说,在格奥尔格那里,这关乎的可并不是一种缄默。因为,为了能够对某种东西缄口不言,格奥尔格必须知晓那一被用于那种已被体验到的神秘莫测的词语本质的词语。缄默是知晓及其已知之物的一种特殊关系。只有对于那种为我所知并且也能够用词语来加以指称的东西,我才可能因为这种用词语进行的指称远离于我而缄口不言。
然而,为诗人格奥尔格所缄口不言的,并非是那些被用于诗性语言那已被体验到的神秘莫测的本质的诗性名称。因此,他之所以对它们缄口不言,并非是因为他不知晓它们。但他却靠近了诗性语言那已被体验到的神秘莫测的本质。当他在珍宝、客人以及恩宠这些诗性的图像之中,言说出已被体验到的词语本质的时候,他正在向这一本质靠近。然而,言说出却并非就已经是一种指称,在这样一个让人能够对这种神秘莫测的词语本质进行短暂的诗性观察的词语之中,是没有指称可言的。由于诗人恰恰未能得以进行这种直达本质的观察,由于他想用于这样一种诗性指称的那一神秘莫测的词语本质屡屡离他而去,对于被用于语言那神秘莫测的本质的诗性名称,他是并不知晓的。
组诗《歌谣》中的第四首诗也指出了现在所诠释的这一意义的内在关联。这首诗,同样也是一首无题诗,它是由三段三行为一段的诗节所构成的:
倾听大地沉闷的语声: 你自由宛若游鱼或飞鸟 你身系何处,你不知晓。 稍后也许有一张嘴发现: 你正一同坐在我们桌前 也以我们的钱财为生。 你有了一张俏丽的新脸 可时间变老,已无人活着 那还能看见这脸的人 是否会来,你不知晓。将全诗合盘托起的,是这一句:
你身系何处,你不知晓正如空气的要素使鸟儿的飞翔成为可能、海水的要素使鸟儿的遨游成为可能,诗性语言的要素使诗人成为可能。然而,诗人却并不知道,当他用这一具有其自身的神秘莫测的本质的词语进行作诗活动的时候,他的作诗活动所赖以进行的是什么。只有当他或许能够再次将这一神秘莫测的词语本质自身带入诗性词语当中之时,他才会知道这一点。在这样的一种情况下,作为诗人的他,或许会向诗性语言的那种虽然已被体验到了的奥秘走得更近。相反,在这首诗中,两次谈到了一种“不知”的状态。海德格尔从这句诗中所说出的是:它“如通奏低音一般”,响彻“在组诗的所有歌谣之中”。
诗人所不知道的是:被用于词语的这一神秘莫测的本质的诗性词语,或许会被后来的某个人所发现。这个人或许会从他的发现同他那广博的体验之中,来向诗人诉说。他一同坐在我们桌前,也以我们的钱财为生。因此,诗人知道,在他面前出现了一张美丽的新脸,出现了语言那神秘莫测的存在的面容,但他却不能对之进行更为深刻的解释。他还知道,如今无人活着;他不知道,这个还能够看见他的面容的人,是否会来。确切地说,这个人发现了那仍为他自己所不明了的东西,而词语却并不会就此失去它那神秘莫测和不可把握的特质。对于这一格奥尔格式的根本体验,伽德默尔写道:“如果人们想要将这一体验,作为一种根本的人类体验,来认识清楚的话,那么,他们将必须回到完全以意识与自我意识为基础的新时代哲学以及形而上学的语言的后面去。”
在这四首诗中,格奥尔格将他对于诗性词语的体验作为主题来加以了描写。综观它们,我们可以说:格奥尔格对于词语的体验“步入了漆黑不可知的境地,在此过程中,(作为体验)它自身仍然一直是模糊不清的”。这种漆黑不可知所关乎的,是处于其赋予存在的本质之中的词语:词语将被进行诗化的东西带入了存在,在其中保有它们,并将它们扣留于自身之中。这种漆黑不可知所关乎的,是词语与“是”以及“那些被进行诗化的东西”之间的关联。尽管这一关联被格奥尔格用珍宝、客人以及恩宠这些词语给言说了出来,然而,诗人却并不知晓那个能专门对词语与尚待诗化的东西的存在之间的关联进行指称的词语。对于诗人来说,在这一关联之上,笼罩着一片他无法照亮的漆黑不可知。只要对于语言的诗性体验步入了这片漆黑不可知之中,而作为体验来说的它是处于一定程度的隐秘之中的,它自然就仍然一直是模糊不清的。
然而,格奥尔格对于语言的诗性体验对之进行了解释的思考,却必须让这一体验保持其原状,即:步入这片漆黑不可知,并保持自身模糊不清的面目。在阐释学的对话中转向了诗性体验的思考,必须让这一体验在其自身之中不受打搅。
然而,在运思对诗性体验进行解释时所做的运思当中,诗性体验已经一直处于了运思的附近和近旁。诗性体验的这一思性探究表明了,诗性体验是处于对语言本质所进行的运思的附近的,并且就此而言也是必须被运思加以考虑的。格奥尔格的濒临被思考之境的诗性体验,首先说明了,作为运思的这一思考,将转向那片格奥尔格的诗性体验已步入了其中的漆黑不可知。
在这一运思着转向已被诗性地体验到的漆黑不可知的意图中,运思摆脱了以下的狂妄之想:作为思性体验,能够轻而易举地从诗性体验之中照亮那一漆黑不可知,并揭开那层蒙面的面纱。在此,运思必须一直铭记它那阐释性的自我理解。面对这一诗性体验已在创作之时步入了其中的漆黑不可知,对于运思而言,重要的只会是:它是否能为了以阐释学构想的方式在探询与运思当中去将那被这样理解了的东西展露出来,而从被诗性地体验到的漆黑不可知之中,倾听着去理解那被允诺给它并向它展示着自身的语言的本质;如果能的话,又是以何种方式。
为了一种思性体验的可能性而对与诗性体验的相通性所做的探访,并非像人们可能认为的一样,是一种权宜之计,它并非是一条出路,一个替代品,或一条弯路。对对于语言所做的一种诗性体验所进行的探访,是发生于运思这一推测之中的:作诗和运思是彼此相通的。通过运思对诗性体验所做的探访,是从以下推测之中发生的:只有对运思与创作的相通性加以考虑和仔细考虑,才能从语言本质的允诺中体验到语言的本质,语言的本质也才能在探询之中被想到。
这样,对作诗和运思的相似性的不加考虑,可能成为以下事实的原因:迄今为止的对语言本质的决定史中,语言的这一本质还从未从其本质的允诺中来被思考过。作诗和运思是彼此相通的并且是在该相通性中彼此转向对方的这一推测,是符合阐释学主导思想中的那种要求的:语言的本质——本质的语言。语言本质的允诺只能与作诗活动的相通性的内部来被思考的这一推测,是符合这一主导思想中的这一要求的。
那么,这是在何种程度之上的呢?是在对词语的诗性体验指明了语言那证实着自身的本质去进行一种思性体验的可能性,而这一诗性体验自身作为诗性体验并不能获得这种思性体验的时候。格奥尔格的诗性体验,在其以解释的方式步入了漆黑不可知之时,向运思指明了一种对于语言的本质进行体验的可能性。这种已被诗性地体验到的漆黑不可知,并非是一种只等着被加以清除的东西。因为,作为这样的一种漆黑不可知,它蕴藏着语言的本质及其可被体验的众多可能性。这种超越于处在其赋予存在的本质之中的诗性词语之上而存在的、已被诗性地体验到的漆黑不可知,可以证明自己是那一片运思将从中去体验语言那证实着自身的本质的领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