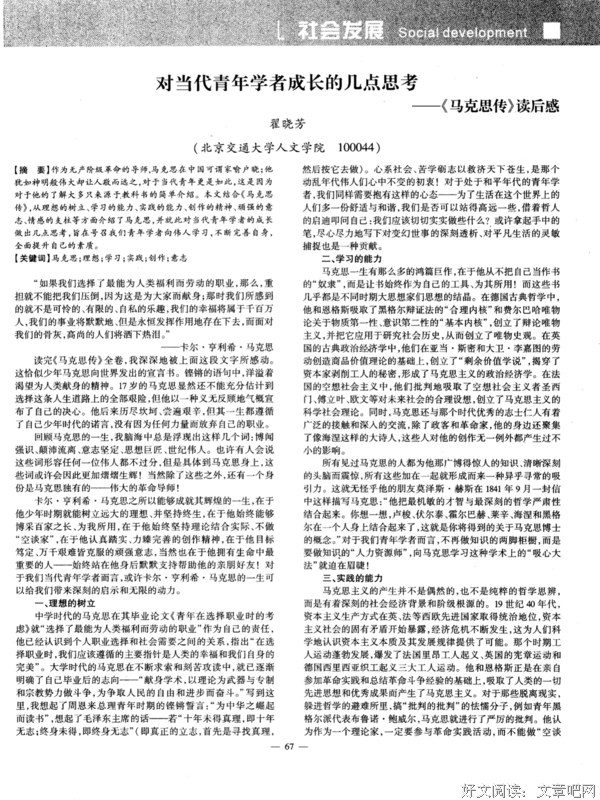
《青年黑格尔》是一本由卢卡奇著作,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平装图书,本书定价:0.75元,页数:144,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青年黑格尔》精选点评:
●黑格尔显然属于没有青春的人,青年时期就琢磨那么抽象的学问了,还被卢卡奇和马克思分成公开的和内心的两部分来研究。
●“在当前这个时代里,德意志人民正在寻找它的道路,而大部分德国知识分子还没有决定究竟自己愿意采取前进的还是后退的路线,那么在这样的时代里、对过去的精神斗争的正确认识,同时也就是对将来发展的一个指南针了。”
●不算很好读吧目前
●喜欢
●精彩的部分在选译的第四章,透过马克思这个三棱镜来理解黑格尔,敏锐地看到《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经济批判与哲学批判的内在关联,从而导引出黑格尔辩证法的现实根源。
●第四章第四节:Die Entäußerung als philosophischer Zentralbegriff der Phänomenologie des Geistes, 详细论述了在黑格尔那里历史和自然如何严格区分,而历史为何是时间上外化了的精神,很好解答了为什么黑格尔系统里精神发展的分层与历史发展分层、宗教发展分层、甚至艺术发展的分层能够相对应。后半部分是马克思对黑格尔外化概念的扬弃,也集中火力批判了费尔巴哈。翻译很好。
●节选本?
●【完满的神灵子孙, 愿你在自我斗争中勇敢而有信心, 打破你内心的宁静, 打破你与世界事业之间的和平! 即使你的努力超过了今天和昨天, 你也不会比时间更为完善, 而至多也不过是,你将即是时间。】 P106
●全无法国人那种黏糊的自我意淫,和依波利特相比也畅快直爽许多。外化的系统批评直接理顺“作为思想与行动的历史”,由此推论概念引导哲学史的环绕和政治史的戏剧,通体贯穿了不少线索。虽不多惊世之语,但眼光老辣独到。王老先生选译精细,挑选的章节直击黑格尔马克思卢卡奇三人命门,也足见当年精现译者的目力。
●如何用哲学解决现实生活的困境
《青年黑格尔》读后感(一):读后感
这书是王玖兴对卢卡契Der Junger Hegel的摘译,翻出来的部分大约是原书六分之一强,内部发行。
别看翻出来的章节不多,但很可见译者在学术上的用心、用意和针对性,这些详见译者序吧。话说王先生翻译了不少黑格尔和卢卡契的作品,形成了一个线索,因为社会主义时期的积累,中国对德国唯心主义传统的思想史研究还是很有谱的。
书中引用了黑格尔法兰克福时期的一封信,其中写道:
“我出于自己的亲身经验,曾经体会了这种心情……理性一方面已经连通兴趣和它自己的克制交织成一团混沌的现象,……另方面它内在地对整个目标的详细情节还不完全明了。这种疑病状态,我遭受了好几年,以至精神上几乎陷于瘫痪。一般地可以说,每个人在其一生中都要经历这样一个转折点,这是他的本质上的一个昏暗的收缩点;他要通过这一关,才能达到安全境地,从而确信他自己,确信普通的日常生活,而如果他已经没有能力以日常生活来充实自己,则通过这一关才能确信一个更内在更高贵的存在。”
现在读这段话很感动。比当年读到青年马克思写给父亲的那封信似乎还要更感动些。我在“日常生活”上反复加圈。这一句,如果按卢卡契的意图和我们的语言,可以解读出黑格尔绝对是唯心主义哲学中最接地气的,而且证明了唯心主义的根本意图就是接地气(其实唯物主义者更喜欢揪着头发离开大地)。确信日常生活,这是何等难以企及的境界。在我们的时代,又有谁能“以日常生活充实自己”?黑格尔会不会认为,他的同窗荷尔德林的悲剧就是没有通过这一关呢?
《青年黑格尔》读后感(二):读书笔记
《青年黑格尔》
目的:批判资产阶级理论对黑格尔的解读 P7,黑格尔指明哲学史必须落实现实的底层而不能被唯心主义绝对化、对历史牵强附会 P8。
批评:取消德国古典哲学辩证发展的做法(叔本华为先导的新康德主义,恢复形而上学传统)P9,而【帝国主义时期的古典哲学的“复兴”并不是黑格尔辩证法的更新和发展,并不是黑格尔历史主义的具体化,而是想利用黑格尔哲学改造新康德主义使之更加有利于帝国主义的更加反动的一种企图】P10,新黑格尔主义无视黑格尔对康德的批评,将康德和黑格尔结合在一起。【辩证法就是已变成了方法、变得合乎理性了的反理性主义。】P12
研究思路:讨论黑格尔哲学的发展史、德国古典哲学的发展,并不根据黑格尔个人来提出问题,而是从社会史的发展。P17将自然哲学的思辨和德国古典哲学之间的互文性重新重视起来。
马克思论德国唯心主义的根源:【康德硬把法国资产阶级意志的有物质动机的规定变为“自由意志”、自在和自为的意志、人类意志的纯粹自我规定,从而就把这种意志变成纯粹思想上的概念规定和道德假设。】P21
研究任务:【具体地找出这个“能动的方面”对辩证法的产生所起的作用】,【指明青年黑格尔思想发展的交互作用,他对法国革命的革命理想发生迷惑的时候,他对政治经济学的分析研究,他对英国的经济情况的分析研究,给他提供了指南针。】【黑格尔把人的自我产生理解为一个过程,因此,他掌握了劳动的本质,并将客观的人,现实的因而是真实的人,理解为他自己的劳动成果。】P24,从而展示【经济学与哲学、经济学与辩证法的内在关联】P25
第一章青年黑格尔共和国思想时期 1793——1796
“神学”时期:
青年黑格尔指向实践的主观主义从来都是集体的社会的,从集体的主体出发,分析其在实际社会中的行动和命运,从而分析主体瓦解而为“私人的”个体。P36
黑格尔为什么要研究宗教:【宗教和反对宗教的斗争也完全具有这种间接的政治性质】,他首先认为【古希腊城邦共和国的瓦解意味着人类自由与人类伟大的社会的没落,意味着城邦的共和国英雄市民向现代社会的纯然自私自利的“私人”,向资产者的转化】,他将基督教视为“私人”的宗教,丧失人类自由的宗教,‘他想找出一种社会条件,在这种条件下,专制和奴役的宗教可以重新为古代范型的自由宗教所代替’。P39
黑格尔虽然从开始就拒绝法国革命的极端左翼,但他终其一生毫无动摇地坚持认为法国革命具有历史必然性,【法国革命是现代资产阶级社会的基础】。【人类已以极可尊敬的姿态出现在它自己面前】,法国大革命的本质特征在于它的非宗教的本质性,而黑格尔把对基督教的批判理解为对封建君主政治的一般斗争的一个组成部分。
兴趣中心:【道德如何通过以复古为基础而创立起来的新宗教而发生的一般感化作用问题】人民的道德更新与其说是革命的先决条件,而不如说是革命的后果。宗教的共同点是,【它们永远从事于培养那些不能由国家法律来处理的思想意识】
第二节青年黑格尔的“实证性”
宗教:【总被视之为真理】(主观真理),它们要求主体对于不是它自己所建立的这些命题盲目地予以承认。也就是【主体道德自主性的扬弃】,【道德律被给予的性质乃是实证性最重要的标志】,【由道德主体本身来制定道德规律,乃是任何道德规律的本质】,虽然和启蒙运动反抗宗教类似,但黑格尔走得更远,他显然把反基督教的奴役作用作为论战的中心要点,而不是简单论述基督教的自相矛盾以及其与科学的对立。
青年谢林的哲学与黑格尔哲学之对比:理性乃是精神的绝对自由,一切精神都在自身之内包含知识世界,而不可以在自身之外寻求上帝与不朽,但谢林的反实证性更为激进,【他认为人类的解放还包括了人类对国家的摆脱】,黑格尔总是抱有较多的历史观点,【自由自主的古代国家在他眼中与罗马国家以降的专制国家并不相同】。青年谢林康德式的认识论和翻历史观点【知识论完全等于伦理学,而没有构成实践的主体的东西】也就并不被黑格尔接受。
青年黑格尔经历了从人本学走向历史主义化的过程,他逐渐将直观、表象、概念这些东西当作分类的原则和历史分期的基础。同时,他像区分记忆和想象一样区分了客观宗教和主观宗教,【客观宗教表现成僵死的知识体系和资本】,【主观知识则表现在人的感觉和行为里,是本质的内在效用和外在活动】,【记忆是停放死尸的墓穴】,【祈祷是人们试图完全为一个外来人所支配】,主观宗教则具备了【建立在一般理性上的】、【是一切生活需要的】、【使想象、心灵感觉从它这里各有收获而不是空无所得】。黑格尔一切议论的出发点显然是【主观和公共宗教的合理性】
第三节历史观和当前现实
古代的复兴往往与表述进步思想相连,这种幻想并不排斥行动的民主本质,正确的平民阶级的、民主革命的现实政策与资产阶级的发展前景抱有的奇妙幻想总是混为一体。
马克思的批评:法国大革命确实忽视了经济制度上古代与当时的差别,也忽视了无产阶级的主导力量。但需要承认【雅各宾派的幻想有一种现实的经济内核】
费希特:康德主观主义+雅各宾派的社会观,社会契约包含社会义务,社会有义务在财产相当平均的情况下照顾每个社会成员。
青年黑格尔幼稚的一点:古代共和国没有经济,没有社会分工;基督教时期人们关心的只是他们自己的财产。
而与席勒相比,黑格尔认为恢复谷底啊精神并不寄托艺术道路而要体现在古代民主的政治行动中
第二章黑格尔社会观和辩证法法兰克福 1797-1800
黑格尔在这一时期的哲学思想才开始体系化,他的中心问题改为个人,或者说人在资产阶级社会中的地位问题。
资产阶级社会是一个基本的、不可改变的事实,【在思想和行动上分析处理这个社会的本质及其规律性】
根据【主观主义】。研究人格发展和人性的亲提如何与资产阶级的社会现状和规律发生矛盾,又如何取得一致而达成和解。不再是伯尔尼时期的【主观唯心主义】,大谈集体性的主体。
同时,黑格尔认识到现代的资产阶级社会已经产生出了某种修正的基督教当作其上层建筑。【这种国家的基础不是基督教,而是基督教的人的基础】
黑格尔关注的是人行为的社会要素,个人道德范畴中的社会条件性和社会规定性。
【从青年人理想中的生活进入到资产阶级的现实社会里去,乃是一个痛苦的和充满危机的过程。】【在这种病态的心情下,认识不愿意放弃他的主观性的,认识不能克服他对现实世界的违抗的,而正因为它不能克服自己对现实的反抗,就处于一种相对的无能之中,并且这种相对的无能,很容易变成一种真正的无能。因此,一个人如果不愿意沉沦下去,他就不能不承认世界是一个独立自存的、基本上完满自足的世界。】【时代迫使人进入了一个内在世界,因而,人的状态,就只能或者是一中死亡,或者是一种企图:如果人愿意听露在这个内在世界里面,他就只能是一种连续不断的死亡而如果自然趋势他生活下去,他就只能是一种企图,力图取消当前世界的否定方面,以便能够适应这个世界。】P95-P96
【完满的神灵子孙,
愿你在自我斗争中勇敢而有信心,
打破你内心的宁静,
打破你与世界事业之间的和平!即使你的努力超过了今天和昨天,你也不会比时间更为完善,而至多也不过是,你将即是时间。】
106
第四章耶纳时期 1803-1807黑格尔与谢林的破裂和《精神现象学》
第四节中心哲学概念:外化
外化和异化:
经济学中表示货物的出售;社会契约中表示原始自由的丧失;费希特的外化则是指主体的外化即客体的建立,而客体本身可以理解为外化了的理性。
谢林认为一个没有物化的事物乃是一个矛盾,只有根本没有成为事物的东西也无法成为事物的东西才是没有物化的。
黑格尔的外化概念的三阶段:
第一阶段指与人的一切劳动、经济和社会活动结合的复杂的主客关系。历史也就被理解社会化的人产生出的复杂交互的人类发展过程。
第二阶段指拜物教意义上的资本主义形式的外化。当然对于经济社会产物的偶像化要还原到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上的想法,黑格尔也表现过此类倾向。
第三阶段,外化和物性或对象性具有相同的意义。客观性是通过主客同一体的外化而返回其自身的那种辩证环节。
但对于自然,黑格尔不承认自然和社会的相互作用。【地球作为他自己的循环运动耽搁一个环节,乃是一种僵化了的东西,一种已经从运动过程里脱离出了的东西】,【所以地球作为这个整体,只呈现着运动过程的图像而并不呈现运动过程本身】。当然,黑格尔的这一看法是为了反对费希特的主观唯心主义。
历史的辩证过程:精神向其自身返回的变化时候,本身才真正是精神,【它从自在到自为,从实体到主体,从意识的对象到自我意识的对象,也就是已经扬弃了的对象或概念的转化】,【转化是一个返回自身的循环运动,它先要有一个起点,而又只在终点里才达到他的起点。】历史达到它的巅峰时候,也就是哲学,才达到它的真正完成。
精神的广延乃是这个内在于其自身深处的自我的否定性,而自我的否定性即是它的外化或者它的实体。精神的时间指在时间过程里外化运动才在其自身中完成其自我的外化。
概念地理解了的历史,就构成了绝对精神的记忆和回顾,就构成绝对精神的王座的现实性真理性和确定性。
【从这个精神王国的酒杯里,它自己的无限性才对它泛起泡沫。】
精神的本质恰恰在于它是历史的真正推动力,但马克思认为【绝对精神只在事后才通过哲学家意识到自身这个具有创造力的世界精神,因此它对历史的推动只是发生在哲学家的思辨想象中。】
马克思优于黑格尔的地方在于他的经济学观点已经包含了从社会主义角度对古典经济学家的观点的批判,而不像黑格尔只具有有限的经济学知识。
论点:
劳动者的生产品成为不依存生产者,进而与生产行为对立的存在,这就是劳动的对象化,也是劳动的现实化,对象化表现为对象的丧失和被支配。【他将外化和客观性做出区分,前者于资本主义的社会分工出现,而后者是劳动的一般特征。】
异化的劳动异化了人类生活和个人生活,又将抽象的个人生活当作同样抽象了和异化了的人类生活的目标。【脱离自然和现实的人的思维乃是抽象的思维。】而黑格尔的问题在于他把这种思维仅仅理解为扬弃的动力,乃至陷入了“无批判的唯心主义”,【他错误地把人和自我意识等同起来】,乃至人的本质的异化,也被他当作自我意识的异化了。、
同时,马克思也对黑格尔的唯心主义做出了唯物主义的批判:在建立的动作中,客观存在并不是从它的纯粹活动中创造对象,客观的产物只是证实了客观的、自然的活动。【一个没有客观性的存在就是一个“非存在”。】马克思坚持了人的思维和人的时间的实际条件。
与此同时,黑格尔虽然坚持将劳动理解为人的自我产生过程,但又认为这个过程必须有一个主体,而这个主体首先是一个绝对自我意识的主体,也就是“自己知道自己和自己证实自己”的理念,实际的人成为这种非现实的自然的宾语。如此神秘的主客同一或者无休止的循环的绝对主体就出现了。
马克思批判道:【具体是许多规定的总结,因此是复杂的统一,它在思维中表现为结果,虽然它是现实、直觉、表象的出发点。因此黑格尔为了将抽象上升为具体,将实在理解为自在自为的思维的结果,但这并非是具体本身的产生过程,而只是思维掌握具体并把它当作一个具体在精神中再生产的过程。】
马克思最深刻的批判:【理性在非理性本身中也是在理性自身中,一个人已经认识到他在社会所过的生活是一个外化的生活,却还要在这种外化生活的本身里过着真正的人的生活,在矛盾中自我肯定就是真正的知识和生活——黑格尔对宗教和国家进行了调和,这些谎话就是他进步的谎话。】
对黑格尔的大讨论:
马克思对鲍威尔的主观唯心主义的批判:伟人之所以看起来伟大,只是因为我们自己在跪着。站起来吧!
群众之外的进步的敌人,是群众通过自我贬抑制造出来的独立自存的产物。鲍威尔绝对的批判把客观的锁链变成了只是在自我身上存在的锁链。
马克思对费尔巴哈的批评:费尔巴哈指出了肯定建立在自己本身上的肯定和自称是绝对肯定的否定之否定的区别,但费尔巴哈抽象地否定了黑格尔哲学中的辩证法因素,认为历史只是抽象的、思辨的人的产生史,而不是实际的历史。【对于事物、现实、感性只是从客体或者直观的形式去理解,而不是把它当作人的感性的活动,当作实践去理解】
目的:历史具体地指出资本主义社会的实际矛盾如何影响了最高形式的资产阶级哲学,黑格尔的唯心主义辩证法。
空洞的矛盾统一并没有什么真实的高明之处,只有黑格尔那些特别的范畴才把辩证法提高到知识的高度。
歌德和黑格尔是资产阶级最后的伟大的悲剧的时代的开端,摆在两个人面前的,是资产阶级社会不可解决的矛盾和个人与人类的分裂。
《青年黑格尔》读后感(三):《精神现象学》汇编(2006-05-04)
[1]序言:论科学认识
2 -因为事情并不穷尽于它的目的,却穷尽于它的实现,现实的整体也不仅是结果,而是结果连同其产生过程;目的本身是僵死的共相,正如倾向是一种还缺少现实性的空洞的冲动一样;而赤裸的结果则是丢开了倾向的那具死尸。-同样,差别毋宁说是事情的界限;界限就是事情终止的地方,或者说,界限就使那种不复是这个事情的东西。因此,象这样地去说明目的或结果以及对此一体系或彼一体系进行区别和判断等等工作,其所花费的气力,要比这类工作乍看起来轻易得多。因为,象这样的行动,不是在掌握事情,而永远是脱离事情;象这样的指示,不是停留在事情里并忘身于事情里,而永远是在把握另外的事情,并且不是寄身于事情,献身于事情,而勿宁是停留于其自身中。-对那具有坚实内容的东西最容易的工作是进行判断,比较困难的是对它进行理解,而最困难的,则是结合两者,作出对它的陈述。
[2]- Denn die Sache ist nicht in ihrem Zwecke erschöpft, sondern in ihrer Ausführung, noch ist das Resultat das wirkliche Ganze, sondern es zusammen mit seinem Werden; der Zweck für sich ist das unlebendige Allgemeine, wie die Tendenz das bloße Treiben, das seiner Wirklichkeit noch entbehrt, und das nackte Resultat ist der Leichnam, der sie hinter sich gelassen. - Ebenso ist die Verschiedenheit vielmehr die Grenze der Sache; sie ist da, wo die Sache aufhört, oder sie ist das, was diese nicht ist. Solche Bemühungen mit dem Zwecke oder den Resultaten, sowie mit den Verschiedenheiten und Beurteilungen des einen und des andern, sind daher eine leichtere Arbeit, als sie vielleicht scheinen. Denn statt mit der Sache sich zu befassen, ist solches Tun immer über sie hinaus, statt in ihr zu verweilen und sich in ihr zu vergessen, greift solches Wissen immer nach einem Andern, und bleibt vielmehr bei sich selbst, als daß es bei der Sache ist und sich ihr hingibt. - Das leichteste ist, was Gehalt und Gediegenheit hat, zu beurteilen, schwerer, es zu fassen, das schwerste, was beides vereinigt, seine Darstellung hervorzubringen.
(方法,陈述)
[1]p3 在文化的开端,即当人们刚开始争取摆脱实质生活的直接性的时候,永远必须这样入手:获得关于普遍原理和观点的知识,争取第一步达到对事情的一般的思想,同时根据理由以支持或反对它,按照他的规定去理解它的具体和丰富的内容,并能够对它作出有条理的陈述和严肃的判断。但是,文化教养的这个开端工作,马上就得让位给现实生活的严肃性,因为这种严肃性使人直接经验到事情自身;而如果另一方面,概念的严肃性再同时深入于事情的深处,那么这样的一种知识和判断,就会在日常谈话里保有它们应有的位置。
[2]Der Anfang der Bildung und des Herausarbeitens aus der Unmittelbarkeit des substantiellen Lebens wird immer damit gemacht werden müssen, Kenntnisse allgemeiner Grundsätze und Gesichtspunkte zu erwerben, sich nur erst zu dem Gedanken der Sache überhaupt heraufzuarbeiten, nicht weniger sie mit Gründen zu unterstützen oder zu widerlegen, die konkrete und reiche Fülle nach Bestimmtheiten aufzufassen, und ordentlichen Bescheid und ernsthaftes Urteil über sie zu erteilen zu wissen. Dieser Anfang der Bildung wird aber zunächst dem Ernste des erfüllten Lebens Platz machen, der in die Erfahrung der Sache selbst hineinführt, und wenn auch dies noch hinzukommt, daß der Ernst des Begriffs in ihre Tiefe steigt, so wird eine solche Kenntnis und Beurteilung in der Konversation ihre schickliche Stelle behalten.
[1]p3 只有真理存在于其中的那种真正的形态才是真理的科学体系。我在本书里所怀抱的目的,正就是要促使哲学接近于科学的形式,-哲学如果达到了这个目标,就不能再叫做对知识的爱(注意der Liebe zum Wissen,与传统的分离),而就是真实的知识(wirkliches Wissen)(zu sein)。知识必然是科学,这种内在的必然性出于知识的本性,要对这一点提供令人满意的说明,只有依靠对哲学自身的陈述。但是,外在的必然性,如果我们抛开了个人的和个别情况的偶然性,而以一种一般的形式来理解,那么它和内在的必然性就是同一个东西,即是说,外在的必然性就在于时间呈现它自己的发展换届时所表现的那种形态里。因此,如果能揭露出哲学如何在时间里升高为科学体系,这将是怀有使哲学达到科学体系这一目的的那些试图的唯一真实的辩护,因为时间会指明这个目的的必然性,甚至于同时也就把它实现出来。
[2]Die wahre Gestalt, in welcher die Wahrheit existiert, kann allein das wissenschaftliche System derselben sein. Daran mitzuarbeiten, daß die Philosophie der Form der Wissenschaft näher komme - dem Ziele, ihren Namen der Liebe zum Wissen ablegen zu können und wirkliches Wissen zu sein -, ist es, was ich mir vorgesetzt. Die innere Notwendigkeit, daß das Wissen Wissenschaft sei, liegt in seiner Natur, und die befriedigende Erklärung hierüber ist allein die Darstellung der Philosophie selbst. Die äußere Notwendigkeit aber, insofern sie, abgesehen von der Zufälligkeit der Person und der individuellen Veranlassungen, auf eine allgemeine Weise gefaßt wird, ist dasselbe, was die innere, in der Gestalt, wie die Zeit das Dasein ihrer Momente vorstellt. Daß die Erhebung der Philosophie zur Wissenschaft an der Zeit ist, dies aufzuzeigen würde daher die einzig wahre Rechtfertigung der Versuche sein, die diesen Zweck haben, weil sie die Notwendigkeit desselben dartun, ja weil sie ihn zugleich ausführen würde.
(路径)
[1]p4 [当代的文化]。。。(对立,冷静,循序渐进,而非当代的激扬狂放的热情。)。。。从前有一个时期,人们的上天是充满了思想和图景的无穷财富的。。。那时候精神的目光必须以强制力量才能指向世俗的东西而停留于此尘世;费了很长时间才使人相信被称之为经验的那种对现实事物的注意研究是有益和有效的。--而现在的当务之急却似乎恰恰相反,人的目光是过于执着于世俗事物了,以至于必须花费同样大的气力来使它高举于尘世之上。
[2]
Dieser Foderung entspricht die angestrengte und fast eifernd und gereizt sich zeigende Bemühung, die Menschen aus der Versunkenheit ins Sinnliche, Gemeine und Einzelne herauszureißen und ihren Blick zu den Sternen aufzurichten; als ob sie, des Göttlichen ganz vergessend, mit Staub und Wasser, wie der Wurm, auf dem Punkte sich zu befriedigen stünden. Sonst hatten sie einen Himmel mit weitläufigem Reichtume von Gedanken und Bildern ausgestattet. Von allem, was ist, lag die Bedeutung in dem Lichtfaden, durch den es an den Himmel geknüpft war; an ihm, statt in dieser Gegenwart zu verweilen, glitt der Blick über sie hinaus, zum göttlichen Wesen, zu einer, wenn man so sagen kann, jenseitigen Gegenwart hinauf. Das Auge des Geistes mußte mit Zwang auf das Irdische gerichtet und bei ihm festgehalten werden; und es hat einer langen Zeit bedurft, jene Klarheit, die nur das Überirdische hatte, in die Dumpfheit und Verworrenheit, worin der Sinn des Diesseitigen lag, hineinzuarbeiten, und die Aufmerksamkeit auf das Gegenwärtige als solches, welche Erfahrung genannt wurde, interessant und geltend zu machen. - Jetzt scheint die Not des Gegenteils vorhanden, der Sinn so sehr in das Irdische festgewurzelt, daß es gleicher Gewalt bedarf, ihn darüber zu erheben. Der Geist zeigt sich so arm, daß er sich, wie in der Sandwüste der Wanderer nach einem einfachen Trunk Wasser, nur nach dem dürftigen Gefühle des Göttlichen überhaupt für seine Erquickung zu sehnen scheint. An diesem, woran dem Geiste genügt, ist die Größe seines Verlustes zu ermessen.
(对现代性的分析?哲学必须竭力避免想成为有启示性的东西)
Diese Genügsamkeit des Empfangens oder Sparsamkeit des Gebens ziemt jedoch der Wissenschaft nicht. Wer nur die Erbauung sucht, wer seine irdische Mannigfaltigkeit des Daseins und des Gedankens in Nebel einzuhüllen und nach dem unbestimmten Genusse dieser unbestimmten Göttlichkeit verlangt, mag zusehen, wo er dies findet; er wird leicht selbst sich etwas vorzuschwärmen und damit sich aufzuspreizen die Mittel finden. Die Philosophie aber muß sich hüten, erbaulich sein zu wollen.
这种放弃科学而自足自乐的态度,更不可提出要求,主张这样的一种蒙昧的热情是什么比科学更高超一些的东西。这种先知式的言论,自认为居于正中心和最深处,蔑视规定和确切,故意回避概念和必然性,正如它回避那据说只居于优先世界之中的反思一样。但是,既然有一种空的广阔(den Horos),同样也就有一种空的深邃;既然有一种实体的光焰,它扩散到有限世界的纷纭万象里而没有力量把它们团聚在一起,同样也就有一种无内容的深度,它表现为单纯的力量而没有广延,这种无实体的深度其实与肤浅是同一回事。精神的力量只能象它的外在表现那样强大,它的深度也只能象它在自行展开种感与扩展和干预丧失自身时所达到的那样深邃。而且,如果这种无概念的实体性知识佯言已经把自身的特性沉浸于本质之中,并佯言是在进行真正的神圣的哲学思辨,那么这种知识自身就隐瞒着这样的事实:它不仅没皈依上帝,反而由于它蔑视尺度和规定,就时而自己听任内容的偶然性,时而以自己的任意武断加之于上帝。-由于这样的精神完全委身于实质的毫无节制的热情,他们就以为只要蒙蔽了自我意识并放弃了知性,自己就是属于上帝的了,上帝就在他们睡觉中给予他们智慧了;但正因为这样,事实上他们在睡眠中所接受和产生出来的,也不外是些梦而已。
och weniger muß diese Genügsamkeit, die auf die Wissenschaft Verzicht tut, darauf Anspruch machen, daß solche Begeisterung und Trübheit etwas Höheres sei als die Wissenschaft. Dieses prophetische Reden meint gerade so recht im Mittelpunkte und der Tiefe zu bleiben, blickt verächtlich auf die Bestimmtheit (den Horos) und hält sich absichtlich von dem Begriffe und der Notwendigkeit entfernt, als von der Reflexion, die nur in der Endlichkeit hause. Wie es aber eine leere Breite gibt, so auch eine leere Tiefe, wie eine Extension der Substanz, die sich in endliche Mannigfaltigkeit ergießt, ohne Kraft, sie zusammenzuhalten - so ist dies eine gehaltlose Intensität, welche als lautere Kraft ohne Ausbreitung sich haltend, dasselbe ist, was die Oberflächlichkeit. Die Kraft des Geistes ist nur so groß als ihre Äußerung, seine Tiefe nur so tief, als er in seiner Auslegung sich auszubreiten und sich zu verlieren getraut. - Zugleich wenn dies begrifflose substantielle Wissen die Eigenheit des Selbsts in dem Wesen versenkt zu haben und wahr und heilig zu philosophieren vorgibt, so verbirgt es sich, daß es, statt dem Gotte ergeben zu sein, durch die Verschmähung des Maßes und der Bestimmung vielmehr nur bald in sich selbst die Zufälligkeit des Inhalts, bald in ihm die eigne Willkür gewähren läßt. - Indem sie sich dem ungebändigten Gären der Substanz überlassen, meinen sie, durch die Einhüllung des Selbstbewußtseins und Aufgeben des Verstands, die Seinen zu sein, denen Gott die Weisheit im Schlafe gibt; was sie so in der Tat im Schlafe empfangen und gebären, sind darum auch Träume.
(黑格尔面对所有问题)
10
[1.绝对即主体的概念]
Es kömmt nach meiner Einsicht, welche sich durch die Darstellung des Systems selbst rechtfertigen muß, alles darauf an, das Wahre nicht als Substanz, sondern ebensosehr als Subjekt aufzufassen und auszudrücken. Zugleich ist zu bemerken, daß die Substantialität sosehr das Allgemeine oder die Unmittelbarkeit des Wissens als diejenige, welche Sein oder Unmittelbarkeit für das Wissen ist, in sich schließt. - Wenn, Gott als die eine Substanz zu fassen, das Zeitalter empörte, worin diese Bestimmung ausgesprochen wurde, so lag teils der Grund hievon in dem Instinkte, daß darin das Selbstbewußtsein nur untergegangen, nicht erhalten ist, teils aber ist das Gegenteil, welches das Denken als Denken festhält, die Allgemeinheit, dieselbe Einfachheit oder ununterschiedne, unbewegte Substantialität, und wenn drittens das Denken das Sein der Substanz als solche mit sich vereint und die Unmittelbarkeit oder das Anschauen als Denken erfaßt, so kömmt es noch darauf an, ob dieses intellektuelle Anschauen nicht wieder in die träge Einfachheit zurückfällt, und die Wirklichkeit selbst auf eine unwirkliche Weise darstellt.
(之后的关键部分)
19 只有当全体是在这种规定性的独特性下加以考察时,每个环节才算是得到了充分的或绝对的考察。
21 保持住死亡的东西,则需要极大的力量。。。而是敢于承当死亡并在死亡中得以自存的生活。精神只当它在绝对的支离破碎中能保全其自身时才赢得它的真实性。。。。精神所以是这种力量,乃是因为它敢于面对面地正视否定的东西并停留在那里。
22 现代人。。。流动。。。精神本质性(Geistige Wesenheiten)
23 精神的实际存在作为最初的东西不是别的,仅仅是直接性或开端,而开端还不是向开端的返回。因此直接的实际存在这个因素就是科学的这一部分所据以区别于其他部分的规定性。
27 (必须探讨的数学)结果的整个产生过程只是认识的一种过程,认识的一种手段而已。--在哲学知识里,实际存在作为实际存在其形成也是与本质或事物的内在本性的形成不同的。但是第一,哲学知识包含着两种形成,而数学知识则只代表着实际存在的形成,即是说,只代表着在认识里事实的性质的存在本身的形成。第二,哲学知识还把这两种特殊的形成运动结合起来。内在的发生过程或实体的形成过程乃是不可分割的、向外在的东西或实际存在或为他存在的过渡过程;反过来,实际存在的形成过程也就是将其自身收回于本质的过程。
38 类。。。一个名词,确切地标示着一个概念,反而为人所舍弃,而另外一个名词,即使仅仅由于它是从一个外国语里借用来的,因而把概念弄得含含糊糊,听起来好像意味更为深远,就为人所喜爱。
40 表象思维的习惯。。。与此相反,另一种思维,即形式推理,乃以脱离内容为自由,并以超出内容而骄傲;而在这里,真正值得骄傲的是努力放弃这种自由,不要成为任意调动内容的原则,而把这种自由沉入于内容,让内容按照它自己的本性,即按照它自己的自身而自行运动,并从而考察这种运动。因为,避免打乱概念的内在节奏,不以任意武断和别处得来的智慧来进行干涉,象这样的节制,本身乃是对概念的注意的一个本质环节。
导论
56 怀疑主义永远只见到结果是纯粹的虚无,而完全不去注意,这种虚无乃是特定的虚无,它是对于结果之所自出的那种东西的虚无[或否定]。但事实上,如果虚无是对结果之所自出的东西的虚无,那它就纯然是真实的结果;它因而本身就是一种特定的虚无,它就具有一种内容。。。。过渡。。。发展过程。。。
122 自我意识部分...(极其重要,主奴关系,斯多葛主义,怀疑主义和苦恼的意识.并且注意其论证的路径)
144 所以苦恼意识超出了这两派思想,它把纯粹思维和个别性结合起来并保持起来了,不过还没有提高到那样一种思维,在它那里意识个别性和纯粹思维本身得到了和解.
168 规律所以为规律,因为它既显现为现象,同时自身又是概念.
174 ...自然感觉...自身就是一个概念.
232 理性的自我意识通过其自身的活动而实现...独立的存在不仅自在地而且自为地消溶于简单的,独立的实体里.它们意识到,它们所以是这些个别的独立的存在,是由于它们牺牲了它们的个别性,而以这个普遍的实体为它们的灵魂和本质;并且,是由于这个普遍的东西又是它们这些个别的东西的行动或它们所创造出来的事业....直观...这个普遍的实体,在一个民族的伦常礼俗与法律里述说着它的普遍的语言...在一个自由的民族里,理性因而就真正得到了实现.它此时是一个现在着的活的精神,在这个活的精神里,个体不仅找到它那表示了出来而作为事物性现存着的规定或使命或它的普遍与个别的本质,而且它自己已经就是这个本质,它也已经达到了它的规定或达成了它的使命.所以,古代最明智的人们曾创出格言说:智慧与德行,在于生活合乎自己民族的伦常礼俗.(对于礼俗的一种解说)
《青年黑格尔》读后感(四):《青年黑格尔》读书笔记
1、本书为选译本,原书全名为《青年黑格尔与资本主义社会问题》,匈牙利哲学家卢卡奇著。书成于1938年,因二战爆发,至1948年出第一版。本书由王玖兴先生据1954年柏林建设出版社的版本译出。
2、本书的主要问题是,论述黑格尔青年时代的思想发展与这一时期资本主义社会重大政治社会事件的关联,挖掘和清理出真正的黑格尔,特别是,认识真正的黑格尔对于理解马克思(首先是理解马克思对黑格尔的批判)至关重要。
3、导论部分介绍本书的方法论,作者试图通过分析德国古典哲学的发生和发展史,提出一个新的哲学史的方法论。
4、导论从黑格尔的哲学史观出发。黑格尔肯定了哲学系统之间有内在的辩证的关联,第一个把哲学史提高到真正的历史科学的高度。就德国古典哲学史而言,他认为康德的先验哲学是起点,以他自己的体系为其顶峰与终结,并指出如何从康德哲学中发展出费希特、谢林和后来他自己的哲学。
但由于黑格尔把哲学视为概念的自身运动,恩格斯指出,这种纯粹的哲学关联只是现实关联的表面现象,哲学史必须落实到现实的客观基础上。于是,黑格尔对这种关联现象的肯定必然要被夸大和歪曲了。
5、在资产阶级哲学本身,黑格尔哲学史观面临着破产,因为出现了许多比黑格尔低得多的反历史的观念,而这些观念包含着对黑格尔的歪曲和利用。作者分析了几个例子:(1)叔本华认为哲学应该返回到唯一正确的康德的方法上去,并试图清除康德哲学里一切倾向于唯物主义的东西。(2)新康德学派把康德打扮成在百分之百的主观主义者和不可知论者,康德以后的哲学是误入歧途,黑格尔被当成了“死狗”。(3)帝国主义时期的新黑格尔派想利用黑格尔哲学改造新康德主义使之更加有利于帝国主义的要求,试图实现康德和黑格尔的统一。
6、新黑格尔主义者沿着反理性主义的方向篡改黑格尔的辩证法,认为通过青年黑格尔的材料,可以描绘出一个神秘主义和反理性主义的、为法西斯主义所欢迎的哲学家形象。作者的任务就是,研究黑格尔的青年发展时期,驳斥这些对历史的篡改;同时,认清黑格尔达到他的辩证法观点的道路,对于理解黑格尔成熟时期的著作也十分重要。
7、接着,作者阐述了自己的研究方法。在德国辩证法的发生过程中,自然科学曾起过决定作用,对此本书不予讨论。重点放在讨论另一个影响因素,即这一时期的政治社会事件(首先是法国大革命及其后果)对德国辩证法的产生所起的作用。
8、法国革命对德国的影响错综复杂。由于当时德国的落后,法国革命在德国哲学中的反映不可避免是一种歪曲的反映。作者引述马克思对康德的评价来说明这一点。马克思认为在康德的思想里含有以现实的阶级利益为基础的法国自由主义在德国的一种回音或余响,但由于德国的落后,问题就本质上被歪曲了。“因此,康德把这种理论的表达与他所表达的利益割裂开来,硬把法国资产阶级意志的有物质动机的规定变为自由意志、自在和自为的意志、人类意志的纯粹自我规定,从而就把这种意志变成纯粹思想上的概念规定和道德假设。”马克思在这里发现了为什么这种哲学在德国一定发展为一种唯心主义哲学的本质原因,而且哲学唯心主义必然要进行无可避免的歪曲。
9、但是,马克思同时指出了古典唯心主义的积极方面。他在批判了旧唯物主义的单纯直观性以后说道:“和唯物主义相反,能动的方面却被唯心主义发展了,但只是抽象地发展了,因为唯心主义当然是不知道真正现实的、感性的活动的。”这是马克思对黑格尔哲学进行批判的基本原则。
10、黑格尔与他的同时代人的不同,还表现在对英国工业革命问题的研究,他曾把英国古典经济学的问题与哲学问题、辩证法问题联系起来。此处,作者承认,我们这样看待黑格尔哲学,只不过是把马克思对黑格尔的观点应用到说明黑格尔的青年期发展罢了。作者是通过马克思这个三棱镜来分析黑格尔的。
11、因此,本书试图提出一个哲学史的方法论的新观点,即经济学与哲学、经济学与辩证法的内在关联。在这种经济学辩证法里,如果掌握得正确的话,会把人与人之间最原始最基本最有决定作用的关系呈现出来。所以,辩证唯物主义的诞生,与这种经济生活辩证法的发现出于同时,绝不是偶然的。在这里,作者强烈地意识到经济学与哲学之间不可分割的内在关联。
12、第一章分析青年黑格尔的共和国思想时期(伯尔尼,1793-1796)。黑格尔在这一时期的中心思想是,把实证的基督教视为他所反对的现代社会和政治现象的决定性原因,而把古希腊的城邦共和国视为改造当前社会和国家的标本和榜样,希望恢复古代范式的自由宗教。
13、启蒙运动构成黑格尔思想的出发点。黑格尔对康德的阅读,兴趣中心在《实践理性批判上》,他想把其中的观点应用到社会和历史上。这样,黑格尔把社会问题主要当做道德问题看待;另一方面,实践问题,即人对社会现实的改造问题,构成他的思维中心问题。
14、但是,康德是从个人观点分析道德问题,社会问题只是第二性的。与此相反,黑格尔的那种指向着实践的主观主义,从来是集体的和社会的。黑格尔的出发点是集体的主体概念,他没有从认识论上去说明这个概念的本质,而是分析这个集体的主体的在历史发展过程中的行动和命运。这种集体主体瓦解为私人的个体,在青年黑格尔看来只承认为一个历史事实,并没有得出进一步的哲学结论。这一时期,青年黑格尔对待狭义的哲学问题相当淡漠。
15、青年黑格尔考虑的社会和历史问题,都是以道德问题形式出现的,宗教在其中占据决定的地位。要说明青年黑格尔著作中的“神学”性质,需要回答两个问题:第一,青年黑格尔研究宗教的本质是什么?第二,提出这个问题的历史环境和条件是什么?
16、对第二个问题的回答是,青年黑格尔提出宗教问题是德国启蒙运动的一般路线使然。在十八世纪的德国启蒙运动时期,由于当时的条件尚未成熟,宗教和反对宗教的斗争具有间接的政治性质。
17、黑格尔当时在历史哲学方面的基本思想是:他认为古希腊城邦共和国的瓦解意味着人类自由与人类伟大的社会的没落,意味着城邦的共和国英雄市民向现代社会的纯然自私自利的“私人”,向资产者的转化。青年黑格尔正是将基督教视为“私人”、资产者的宗教,丧失人类自由的宗教,维护千百年专制与奴役的宗教。由于这些思想,黑格尔就沿着启蒙运动的一般路线发展。但是他的反对基督教的斗争,从来没有发展到唯物主义的无神论,相反,他想找出一种社会条件来,基督教可以重新为自由宗教所代替。
18、青年黑格尔唯心主义地高估了宗教的历史地位,把基督教视为他所反对的现代生活里一切社会和政治现象的决定性原因,要恢复古代的自由,就需要指出使基督教成为统治宗教的社会和政治原因,他的目标就是消除这整个症结。所有这些观点都是受发法国革命的影响而产生出来的。黑格尔终其一生坚持认为法国革命具有历史必然性,坚信法国革命是现代资产阶级社会的基础。当然他对资产阶级社会的看法前后变化极大。
19、既然黑格尔把对基督教的批判理解为对封建君主专制政治斗争的组成部分,在这个意义上,他与法国革命站在同一战线。法国革命与过去一切资产阶级革命相反,是反宗教的。恩格斯称之为非宗教的本质性。早期的资产阶级革命,都还是在宗教旗帜下进行战斗的,而法国革命则完全诉之于“法律和政治的观点,而只有在宗教阻碍它前进时才去过问宗教。但对于用一种新宗教来代替旧宗教的问题,他们则根本连想都没想到。”相反,许多历史学家都高估了法国革命中宗教运动的实际意义。
20、现在要分析这些宗教运动对青年黑格尔的影响。黑格尔认为,人民道德的更新,与其说是革命的后果,不如说是革命的先决条件。与席勒的悲观观点不同,青年黑格尔对人类的更新充满乐观。国家或政府只能使它的国民合法而不能使他们有德,而一个政权能否巩固,全看它是否在国民的道德观念里生了根。他最终发现,宗教是左右道德观念最有效的手段。他在《基督教的实证性》中说:“一切民族的宗教……它们永远从事于培养那些不能由国家法律来处理的思想意识。”
由此可见,青年黑格尔认为,重大的历史转变都是与宗教的转变密切结合的,无论民主或专制,都必须有与它的目的相适应的宗教才能长期生存下去。在这里,黑格尔提出的未来的宗教问题在方法论上与法国革命中的宗教道德思潮具有密切关系。可以说,青年黑格尔如此强烈地注意法国革命理论发展中次要的方面,是他的德国品性的必然结果。而且,黑格尔对宗教的历史作用的观点陪伴了他整个一生,虽然内容上有巨大变化,这是无法摆脱的哲学唯心主义的遗产。
21、阐明青年黑格尔著作中的“神学”性质后,接下来重点讨论基督教的“实证性”问题。黑格尔说:“一种实证的信仰……所以对我们来说是真理,因为它们是被当做戒律由一种权威吩咐给我们了,而我们又不能不使我们的信仰听从于这种权威……它们虽然时常被称为客观真理,现在也必须是为我们的真理,主观真理。”实证的宗教命题要求主体对于不是它自己所建立的命题盲目地予以承认,即,实证性首先意味着主体的道德自主性的扬弃。
这里所说的主体,不是康德的道德主体,而是某种社会的历史的东西。对于希腊精神而言,个别主体的道德自主性与整个民族的民主集体性合而为一。而由于希腊城市民主政治崩溃,基督教出现,基督教就与个别主体对立起来,成为一种客观的、实证的东西,而顺从基督教的戒律,就是丧失了自由的必然后果,而且使压迫和专制得以永生。
22、黑格尔想从道德里把一切神学的实证的因素都清除出去,并不是因为他像康德一样觉得神学的对象不可认识,而是因为他认为信仰与自由和人类尊严是不相容的。所以,黑格尔反对利用康德的伦理学来恢复神学,而是要清除神学因素,从而纯化康德的实践理性,人的道德自主性。此外,黑格尔还关注到宗教里实证问题的社会基础,即世俗利益。
23、在伯尔尼时期,黑格尔还试图把康德的伦理世界和知识世界的二元论予以社会历史的发展。在自由的道德意识和客观现实之间的关系上,客观世界诚然也是一种与道德意识不同并与它的主观性相对立的客观的外在世界,但黑格尔认为,这种对立不是永久的,不是哲学的认识论上的对立,而是一种历史的对立,它是中古和近代的历史特征,而青年黑格尔的未来希望的核心所在,就是这种对立的扬弃。
这里展现了青年黑格尔关于基督教的实证性问题的全部意义,相当于康德伦理学里二元论的社会现实性。未来,他的哲学里大多数独特的东西都是从这个实证性与道德主观性的对立中发展出来的。但是,只有到黑格尔看到这个原始概念里的矛盾即是社会现实的内在客观矛盾的时候,只有到认识论本身变成了现实辩证法的时候,这种发展才有可能。
24、黑格尔明确表述了实证的宗教与人的自由之间不可解除的矛盾,并且把这种对立扩展到人类全部的道德生活和社会问题上。人们在其存在与思维的整个范围里承认有一种这样超越自己的外来力量,人们放弃了道德自由,必然丧失理性的自由,从而无法对抗与实证宗教的超越力量。
对于黑格尔来说,决定性的东西不在于基督教科学与否,而在于基督教摧毁自由与人类尊严,他把这种理由当做论战的中心要点。黑格尔的这种主观主义态度,一方面产生于德国的落后状态,另一方面又是黑格尔发展出“能动方面”和历史主义的基础。
25、另一个重要问题是黑格尔关于主观宗教与客观宗教的对比。黑格尔认为,主观宗教是活的,是本质的内在效用和外在活动,他把主观宗教比为自然界的生物本身;而客观宗教包含着知性、记忆和知识,把人变成一个客体,完全为一个外来人所支配,黑格尔把它比为动物标本,这里的客观宗教就是基督教实证性的一种思想前身。这里,黑格尔把公共宗教与主观宗教,私人宗教与客观宗教密切关联起来了。主观宗教是一种真实的“人民宗教”,拒绝一切偶像信仰,只有主观和公共宗教具有合理性,这是一种民族自我解放的宗教。
26、青年黑格尔把主观宗教当成德国自由运动的基础。他的历史问题,在于首先指出古希腊是发展到最高形式的民主社会的主观主义,然后发现这种世界的没落,僵死的专制的实证宗教时代产生,通过这个对比使人展望到未来的自由解放。接着,作者说明黑格尔是如何倾向于把德国的当时的情况理解为宗教实证性的历史发展的产物。
黑格尔认为,德国民族是一个没有自己的宗教幻想和政治幻想的民族,这种缺乏民族的情感生活的缺陷,在整个德国文化里到处都有表现。而德国文化之缺乏民族特色,主要在于它没有在人民中间生根,精英文化与平民文化之间存在深刻的裂痕。这种缺乏真正民族文化的情况,与他的民主政治立场密切关联。黑格尔在伯尔尼居留期间,伯尔尼的贵族寡头政治使他终生鄙视这种制度。这样一种政治的和文化的情况,是以基督教实证宗教的统治为中心力量的社会发展的产物。因此,黑格尔对古代民主的分析和赞扬,是具有针对当时德国现状的现实政治意义的。
27、第二章分析法兰克福时期(1797-1800)黑格尔的思想危机,以及辩证法的萌芽。
28、当时德国在客观现实上不存在发生资产阶级革命的可能,因此黑格尔伯尔尼时期的社会观点与德国社会现实之间存在着很大距离。这种距离随着法国革命的发展而越来越大。随着1794年罗伯斯庇尔倒台,法国资产阶级经济和社会的发展浪潮迅速高涨,这种转变反映到落后的德国,就更加受到歪曲。德国绝大多数资产阶级的人文主义者向来不赞同法国革命极端左翼的平民化的苦行作风,从而产生了对法国这种资产阶级统治的同情,到后来就集中表现在对拿破仑的好感,在这种好感里,包含对热月政变后历史发展的一种人道主义——唯心主义的曲解。于是就产生了幻想,以为在资本主义社会里,有可能实现人道主义的理想,产生出理想的人来。
29、由于法国革命的发展,使得资产阶级社会问题成为讨论的中心问题。法国研究政治问题,英国研究经济问题,因为德国的落后状态,这种道路几乎是沿着一条纯粹意识形态的路线进行的,就是根据人道主义的观点,研究资产阶级社会里的人、人格和人格发展的情况。
30、对于黑格尔来说,在法兰克福时期,英国的经济发展成为他的历史观和社会观的基本成分。这个新成分的产生,恰恰是由于法国革命的进展,使得德国的封建专制整体必须如何通过法国革命而加以改造的问题成为具体的政治问题。(对于这一新成分的具体分析,选译本未收录。)
31、但是,此时法国革命对德国的影响,已经不仅限于意识形态,而是产生了充满矛盾的影响。法国原来的防御战争转变为攻击性战争,一方面,这些侵略战争消除了封建残余从而客观上完成了资产阶级革命的任务,另一方面,法国的征服进一步加深了德国的民族破碎和国力式微,德国的统一更加难以实现。此外,由于德国的落后,德国的民族运动企图联合普鲁士和奥地利等地的君主进行民族抵抗,又助长了拿破仑失败以后统治整个德国的那种反动势力。这种客观矛盾笼罩并表现在这个时期一切杰出的德国人身上。
32、黑格尔对于这种矛盾,无论在政治上还是在哲学上都没能提出克服的办法。但是,恰恰是接触到了德国的现实政治和社会命运,于是其中的矛盾性越来越成为他的思想中心,他向有意识的和直接的哲学问题的过度也就越来月缩短,并且社会和政治问题就越来越直接转化为哲学问题。正是由于他从具体的生活现象里把握其矛盾性的倾向,他才有时候像列宁指明的那样,非常接近于唯物主义的辩证法。
33、这是黑格尔思想的一个非常强烈的转变。这个转变的基础在于,黑格尔的中心问题变为,人在资产阶级社会中的地位问题。伯尔尼时期,黑格尔是从外面对资产阶级社会进行了观察,认为这是纯然消极的和没落的现象。现在他认识到,资产阶级社会是一个基本的事实,他必须在思想和行动上分析处理这个社会的本质及其规律性。这种分析是从一种非常主观主义的基础上开始的。问题是,个别的人如何一定要与资产阶级社会发生抵触,人格发展的道德与人性前提如何与资产阶级社会现状和规律陷于矛盾,以及两方面如何又可能取得一致而达成和解。在这里,伯尔尼时期的“实证性”问题,获得了更复杂、更富于历史意义的性质,引导黑格尔一眼就现实的社会和经济问题。
34、黑格尔对基督教的态度也发生了变化。他把基督教视为近代社会发展的推动力,这一点与伯尔尼时期没有根本差别,变化之处在于,伯尔尼时期批评基督教,而现在他认为基督教必然真正继续是当前社会思想的道德基础,因而竭力跟它和解。
35、黑格尔从个人的生活问题出发,这种现象只能在他的思想发展的法兰克福过渡时期里看到。黑格尔的思想特征,总体说来都在于,他之所以对个人感兴趣,永远只因为个人是社会的成员。所以,法兰克福时期之深究个人生活,及从个人欲望和需要出发,是他思想发展中的一个插曲。当然,在他从个人意识转向客观社会问题的过渡中,在他辩证地分析思想的与情感的世界观的个别阶段中,在他把高级阶段描写为低级阶段的矛盾的扬弃的结果时,已经孕育着《精神现象学》的方法的最初萌芽了。
36、法兰克福时期是黑格尔思想的危机时期,他强烈地体验到生活的基础是矛盾性,而这种矛盾性表现为矛盾的一种悲剧性的不可消除性。他说自己在这个时期处于不幸的疑病状态,自我摧毁和自我崩溃状态。他说,“在这种病态的心情下,人是不愿意放弃他的主观性的,人是不能克服他对现实世界的违抗的,而正因为他不能克服自己对现实的反抗,就处于一种相对的无能之中,并且这种相对的无能,很容易变成一种真正的无能。因此,一个人如果不愿意继续沉沦下去,他就不能不承认世界是一个独立自存的、基本上完满自足的世界……”这里的问题就是他自己如何对待资产阶级社会的问题,他试图为自己在资产阶级社会里找个一个位置。
37、这并不是一个纯粹私人的问题,而是伟大的德国人道主义者对待资产阶级社会的态度问题。这种矛盾为这一时期德国一切重要诗人和思想家所共有。资产阶级在法国革命与英国工业革命中取得了胜利,但同时暴露出它的可怕的仇视文化的方面。德国的人道主义者们必须承认这个资产阶级社会,同时必须公开揭发它的矛盾,而不向它的本质所带来的非人性的东西表示屈服。德国古典哲学和文学都提出试图解决这些矛盾所采用的方式。
38、黑格尔在这一时期表达了逃向自然,以免为他的社会环境所同化的想法,用一种原始的、直接的、感性的形式在表示着这种矛盾。一方面,他愿意充分掌握当时的资产阶级社会并发挥自己的作用,另一方面,他坚决不愿意把非人性的东西承认为活动东西。在这场思想危机中,黑格尔把这种矛盾提高到哲学客观性的阶段。他不仅叙述他的私人生活里亲身体验的矛盾,进而认识到资产阶级社会的矛盾性(当然具有局限性),并且从这种矛盾性里进一步认识到一切生活、整个存在和思维具有普遍的辩证性质。法兰克福危机的结果,使黑格尔初次概括了他的辩证方法,当然只是一种非常神秘的辨证方法,同时使得黑格尔跟他当时的资产阶级社会之间达成一种辩证的、在承认基础上含有矛盾的“和解”。
以上是黑格尔在法兰克福时期的思想的一般特征。
39、本书最后一部分重点阐述了《精神现象学》以及马克思的批判,围绕“外化”这一中心哲学概念展开。
40、首先回顾“外化”成为黑格尔哲学概念的源起。伯尔尼时期,“实证性”被认为是存在于僵死的客观性里,与人的主观性(首先是人的实践)互相对立。法兰克福时期,对“实证性”的理解更历史更辩证些,他开始觉得现代社会并非自来就是完全实证的,而是要分析某种东西是怎样变成“实证的”,看人的社会实践与社会机构之间的关系是怎样在历史地具体地变化和消灭的。后来,“实证性”一词的一般哲学含义消失了,但并没有消除之前用这次词所表示的问题,即人的社会实践与他自己所创造的东西之间的辩证关系问题。黑格尔愈发坚定的思想是:在人的社会实践里,原始的直接的天然的东西被克服掉并且必然被克服掉,而在这个过程通过人自己的劳动创造出来的产品所代替;而这种劳动不仅创造这些社会客体,也改造人的主体,因为它也扬弃主体里原始的直接的东西,从而主体就异化了自己。黑格尔开始使用新的哲学术语,来把他通过研究经济学和历史所发现的社会客观性提高成哲学的普遍性,发展出成熟的矛盾运动和矛盾扬弃学说,在这个过程中,“外化”或“异化”一词逐渐取得黑格尔思想体系的中心地位。
41、黑格尔的“外化”概念可以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的含义是指与人的一切劳动、一切经济和社会活动结合着的主客关系。这里产生了社会的客观性,社会的发展及其发展规律的问题,同时保留着人自己创造他的历史的思想。历史被理解为通过社会化了的个体的人而产生出来的复杂的、充满交互作用与矛盾的人类发展过程。
第二阶段的含义是指特殊的资本主义形式的“外化”。黑格尔在这一点上并没有明确的认识,他有时把仅仅是资本主义社会的一种特别的外化了的本质标志当成了劳动社会化的必然结果。这里同时产生了要把偶像化了的经济社会产物和关系的客观性还原到人,归结到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上来。
第三阶段的含义与“物性”或“对象性”具有相同的意义,用以表述对象性或客观性发生史,客观性是通过主客同一体的“外化”而返回其自身的那种辩证环节。在这样收回客观性时,其中包含着重要的神秘化倾向。
42、关于黑格尔唯心主义的神秘化,作者重点分析了黑格尔对自然和历史的本质的规定。
由于错误地统一了“外化”与客观性,黑格尔错误地区分了自然与社会的本质。黑格尔认为,自然是精神的一种永久外化,因而自然的运动只是一种虚假的运动,只是主体的一种运动,自然没有真正的历史。相反,人类社会实践里的、历史里的“外化”,则是精神在时间上的一种“外化”,因而是一种真正的实现、真正的历史。
43、基于这种区别,黑格尔从来没有探讨自然界本身的发展历史,不承认自然与社会有实际的相互作用,不承认在社会发展期间自然还有它的发展历史。黑格尔曾经试图把地球理解为人类历史的舞台,在这里,他认为历史只有一个,当人的历史开始的时候,地球已经发展齐备了,地球的历史已经完全停止了,而地球的历史本身也矛盾重重。
44、另一方面,黑格尔把人类社会发展的特殊方面突出出来,接触到人类自己创造他的历史的这一环节,提供了达到一种丰富的正确的历史图像的可能性。但是同样包含着神秘的“外化”的作用,以至于把他很彻底建立起来的东西又取消了。
黑格尔认为历史的目标就是它返回于主客同一体。历史返回于绝对主体,这是一种对时间上的“外化”,对时间的扬弃,这是客观性的扬弃的自然结果。这样一来,不仅历史的辩证过程被安置到两个神秘的界限之间来,从而重新显现了宗教里时间有始有终的创世纪范畴,而且历史过程的起点与终点本身也必然碰到一起,历史的终点必定预先存在于它的起点里。
这个终点就是绝对精神,而且绝对精神在达到它的顶峰时就是绝对知识、哲学。这样,历史就成了这样一种运动,这种运动,在现实里固然是作为过程在发展演进,但它却只能在哲学里、在对此发展道路的理解里才达到它的真正完成;而这个完成从开始就是它的内在目标,就是它包含于起点中的自在。这个思想对《精神现象学》的历史哲学具有决定性意义。精神是历史的创造者,精神的本质恰恰在于它是历史的真正推动力。这些是黑格尔“外化”概念的必然结果。
45、以下论述马克思(主要是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对黑格尔辩证法的批判。《手稿》在20世纪30年代初才被人发现出版,作者对于《手稿》的洞见极具眼力,很有启发意义。
作者认为,马克思在《手稿》中对黑格尔辩证法的全面系统的批判,是改造唯心主义辩证法为唯物主义辩证法的最重要的环节之一,在方法论上有两个特征尤为重要。
第一,马克思集中批判了《精神现象学》,特别是“外化”及其扬弃的思想,既是在哲学上瓦解青年黑格尔派和为革命的政治理论做准备的需要,也是对费尔巴哈哲学的继承、纠正与超越。第二,马克思采用了经济学和哲学相结合的方法论,他对黑格尔的批判是以他对经济事实更深刻更正确的见解作为出发点的,而只有基于对资本主义经济学的社会主义批判,才有可能发现人的经济生活里面现实的辩证运动,从而才有实际基础来批判一方面是古典经济学家的另一方面是黑格尔的见解,这是实际排除唯心主义辩证法的先决条件。马克思《手稿》中的纯经济学的部分,包含着后来哲学批判的最重要的理论根据,即从经济学上给异化事实做了说明。
这里,作者敏锐地发现《手稿》中包含着对国民经济学前提的异化劳动的经济批判、对共产主义思潮的社会批判、对黑格尔辩证法以及一切哲学的哲学批判,以及三大批判之间的密切关联。
46、接下来作者论述了马克思的主要论点。
马克思是从资本主义经济学的实际事实出发的,考察这种经济学的前提,分析异化劳动。具体来看,马克思严格划分了外化与客观性、劳动里的客观化。后者(客观性、劳动客观化)是一般劳动的一种特征,表示人的实践对外在世界的关系。前者(外化)则是资本主义里由于社会分工而出现的所谓自由工人的附随现象,在客观上,劳动的生产品表现为一种外来的、对人具有统治势力的对象,在主观上,劳动的过程成了一种与事物外化相应的自我外化。进而,异化了的劳动异化了人类生活和个人生活。
基于上述分析,马克思认为,黑格尔已把劳动正确理解为人的自我创造过程,但他没有见到劳动(异化劳动)的消极方面,那么在他那里就必然产生出哲学上的错误的分割、错误的统一和唯心主义的神秘化。发现资本主义劳动的实际辩证法,是对这种哲学进行唯物主义批判的前提。
47、马克思认为黑格尔哲学含有一种“无批判的唯心主义”倾向。黑格尔的扬弃了其自身体系中的“外化”的那种哲学,其本身乃是一种最突出的“外化”形式。“正如哲学精神不是什么别的,只不过是在其自我异化中进行思维的,即是说,抽象地把握其自身的那种异化了的世界精神。逻辑……乃是人类和自然的一种已经与一切现实规定性完全不相干的、因而非现实的本质——乃是外化了的,因而脱离了自然与现实的人的思维;乃是抽象的思维。”
这一点,黑格尔没有看见。由于他不把这种异化了的思维理解为异化了的,由于他恰恰把这种思维视为扬弃“外化”的动力,他就在哲学上把生活里外化的现实关联和规定性头脚倒置起来。在这个基础上,黑格尔的唯心主义把人的本质与自我意识等同起来。
48、“人的本质的一切异化,只不过是自我意识的异化罢了。自我意识的异化不是人的本质的实际异化的一种表现……毋宁相反,实际的异化,即看起来好像是实在的那种异化,按照它最内在的本质来说,倒是人的真实本质,亦即自我意识的异化的现象。理解到这一点的科学,因而叫做现象学。这样一来,重新占有那异化了的对象化了的本质,看起来好像就是把它并入于自我意识;掌握自己的本质的人,只不过是掌握对象化了的本质的自我意识,因此,对象的返归自身,就是对象的重新占有。”
马克思说明,错误地把人与自我意识等同起来,是如何由于错误理解了社会生活里的外化。基于这种错误的理解,在主观方面,就等同了人与自我意识,在客观方面,就等同了外化与对象性、客观性。
49、从这种错误观点出发,黑格尔哲学在扬弃客观性或对象性方面达到了错误的顶峰。“被当作建立起来了并且要去加以扬弃的那种异化的本质,不是指人的本质把自己对象化为非人的、与人对立的东西而言,而是指人的本质把自己对象化为不同于和对立于抽象思维的东西而言。……所以,应当克服意识的对象。对象性本身被当作了人的外化了的关系,被当作了一种与人的本质,亦即与自我意识不相称的关系。因此,重新把那在外化的规定下产生出来的人的对象性的本质占为己有,就不仅意味着扬弃异化,而且意味着扬弃客观性,因此,这就是说,人被当成了一种非对象性的、精神性的本质。”由此可见,这种最高形式的唯心主义辩证法,何以只有当展望到真实地扬弃资本主义的异化从而有可能对资本主义经济学作时候走呀批判的时候,才能够彻底地予以扬弃。
50、在此基础上,马克思提出了唯物主义的对象性学说(感性对象性关系)。马克思对黑格尔唯心主义所作的唯物主义批判,是以他所陈述的人的思维与人的实践的实际条件为根据的,与绝对唯心主义自称的无条件性相对立。在这个意义上,唯物主义辩证法也可以说的客观唯心主义辩证法的真理,因为前者不仅批评地消灭了后者,而且找到一条同时保存其中重要和正确因素的道路。
51、黑格尔的辩证法之所以能成为唯物主义辩证法的直接先驱,决定性的一点是,黑格尔把劳动理解为人的、人类的自我产生过程。在承认这一点的基础上,马克思批判了黑格尔把历史加以神秘化的基础。黑格尔历史的主体是上帝、绝对精神、自己知道自己和自己证实自己的理念,是纯粹的、无休止的自身循环。这个主体抽象地、神秘化地、虚构地“创造”历史,因而实际的历史过程、历史过程的实际规定就只能走后门偷偷溜进构造里面来。
“黑格尔陷入了幻想,把实在理解为自行总结、自行深化与自行运动的思维之结果,其实由抽象上升为具体的这种方法,仅仅是思维掌握具体而把它当做一个具体在精神中予以再生产的方法,但绝不是具体本身的产生过程。”
52、基于对“外化”概念的批判,马克思对“扬弃”概念进行了批判。
主体扬弃了它的外化和客观性,并将其收回于自身,因此,它在它的“他在”里也就是在它自身。马克思说,这里汇集着思辨的一切幻想。第一,意识直接自称是它自己的对方,是由于那仅仅作为意识的意识所遇到的与它发生抵触的东西并不是异化了的对象性,而就是对象性自身。第二,有自我意识的人把精神世界认作自己的外化并加以扬弃了,却又证明这个外化了的形象就是精神世界,恢复这个世界,佯言在它的他在中即是在它自身中,这是黑格尔的假象的批判主义的根源,就是费尔巴哈所说的宗教或神学的肯定、否定和再肯定的过程。因此,理性是在非理性本身中也是在理性自身中。黑格尔对宗教和国家等等进行了调和,这些谎话是他的进步的谎话。
53、马克思的批判是从现实生活的具体问题上升到黑格尔辩证法的抽象问题上来的,它是用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把问题最后地哲学地解决了的,而它又从这里出发立刻跟生活里的现实问题直接关联起来。这里出现了黑格尔哲学的中心矛盾问题,即体系与方法之间的矛盾。
这个矛盾,包含着黑格尔哲学对人类进步问题,特别是对一般的资本主义社会和德国特别形式的资本主义社会在历史过程里的地位问题的矛盾性。黑格尔的进步倾向与反动倾向之间的矛盾性,即集中地表现在辩证的扬弃过程的矛盾性上。
黑格尔式的“外化”观念——意识在它的他在里就是在它的自身中——包含着对过去、即使历史上已经克服了的过去的一个辩护。而黑格尔在对待过去的历史问题上有与此相反的倾向,说明了黑格尔的体系与方法之间存在着不可解除的矛盾。
这个矛盾以及其中包含的倾向,在19世纪40年代围绕黑格尔辩证法的论战里产生出两种错误观点。一种是青年黑格尔派直接继续发展黑格尔的唯心主义,使之进一步主观化;另一种是费尔巴哈提出的对黑格尔的扬弃概念的批判,这种批判在认识论上是正确的,但太抽象和太片面。
54、第一种观点的逻辑线索是,黑格尔认为“外化”就是意识的一种“外化”,所以它只可以在意识以内由意识来加以扬弃,他没有看到绝对知识与具有这种绝对知识的哲学家是同一个东西。黑格尔以他的客观主义为根据,竭力反对从这个同一性中发展出一个简单的个人联合体来,但这种倾向已经内含在他的态度里了,并导向鲍威尔的哲学和政治原理。鲍威尔把黑格尔的唯心主义主观主义发展到极端,把现实的、客观的、在我身外存在着的锁链变成只是观念的、主观的、只是在我身内存在着的锁链,因而也就把一切外部的感性的斗争都变成了纯粹观念里的斗争。
55、第二种形式即费尔巴哈对黑格尔辩证法的批判的功绩在于,他把那以自己本身为根据的、肯定地建立在自己本身之上的肯定跟自称是绝对肯定的否定之否定对置起来。前一种肯定正表示存在先于意识的优越性。在费尔巴哈看来,黑格尔的辩证法在扬弃过程里是把存在与意识的关系头脚倒置了,而且指明,正是由于这种颠倒,黑格尔用哲学把宗教重新在思想上建立起来。
马克思在肯定上述批判中唯物主义方面的同时,批判了费尔巴哈的片面性。一方面,费尔巴哈把“外化”当做纯粹哲学的问题,认为否定之否定只是黑格尔在哲学上的一个软弱的肯定,只理解为哲学和它自身的矛盾,所以他“直接地无中介地用一个感性上确定的、建立在自己本身上的肯定与它对置起来”,因而同样停滞于抽象的处理之中;另一方面,至于在黑格尔的外化里经济学与哲学的密切关联,费尔巴哈一点也不知道,这种局限在纯粹认识论范围以内、对一切中介的排除,就不仅否定了黑格尔的唯心主义,也一并取消了辩证法。
56、因此,费尔巴哈没有注意到黑格尔哲学中包含的最本质最重要的规定。费尔巴哈找到的只是关于历史运动的抽象的、逻辑的、思辨的表述。而马克思看到了黑格尔《现象学》中包含着人类史前史的一定特征,只不过是处于一种异化了的形式中。“精神现象学乃是隐蔽的、自己本身还不明确的和神秘化的批判;但由于精神现象学坚持人——即使只是表现于精神形态的人——的异化,它里面就包含着一切批判因素,而且这些批判因素有时甚至已经准备得和发挥得远远超过黑格尔立场的程度。”因此,马克思对黑格尔辩证法的批判,同时就发展成对费尔巴哈的黑格尔批判的片面性和局限性的批判。“从前的一切唯物主义——包括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的主要的缺点是:对事物、现实、感性只是从客体的或者直观的形式去理解,而不是把它当作人的感性的活动,当作实践去理解,不是从主观方面去理解。所以……和唯物主义相反,能动的方面却被唯心主义发展了,但只是被抽象地发展了。”
57、费尔巴哈的批判曾经导致危险的政治后果。费尔巴哈想研究跟思想客体不同的感性客体,但没有把人的活动本身理解为客观的活动,他仅仅把理论的活动看作是真正人的活动。他废弃一切具有中介作用的规定和关系而返回于直接性,反映出对待资本主义的经济社会生活持有一种盲目无知的和固执的态度,客观上可以含有一种为资本主义辩护的反动性质。
58、总结以上马克思对黑格尔辩证法的批判,可以看出,这种批判是根据黑格尔对资本主义社会和经济学的矛盾和发展规律的理解的正确性与局限性,来说明黑格尔辩证法的伟大和缺点,而且进一步又发展成为后来德国革命和无产阶级革命的思想意识的准备。这些哲学问题在黑格尔那里本来也不是纯粹从哲学上看待的,所以决不能单从哲学上来批判。正是由于黑格尔把哲学问题与资本主义社会生活的关联充当他的辩证法的基础,他的唯心主义辩证法是整个资产阶级哲学的最高形式,它是辩证唯物主义在发生的时候可以直接与之接合的那个中间环节。这是本书方法论。
59、黑格尔的历史伟大,也在于他的哲学具有深刻的现实和时代基础。全部的辩证法问题,都是从他研究具有世界史意义的时代事件里发展出来的。只是在具体建立自己的体系时,黑格尔才在思想上与他的前辈们发生实际关联。而这种思想上的关联,从一开始就是一种批判的,要冲破康德观念的思想框框的。只有当德国的社会存在导致黑格尔的辩证法表现出狭隘的局限性时,他才与他的哲学前驱们趋于一致。
60、这一部分以歌德与黑格尔之间的共性结尾。歌德和黑格尔生活在资产阶级最后的伟大的悲剧时代的开端,共同面临着资产阶级社会的矛盾以及个人与人类的分裂。他们都试图对到达了当时那个阶段的人类的诸发展环节作一个全面的理解,并将它们的内在运动、自身规律性表述出来。就这一点而论,《威廉•麦斯特》和《浮士德》与《精神现象学》、《逻辑学》和《哲学全书》具有同样伟大的历史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