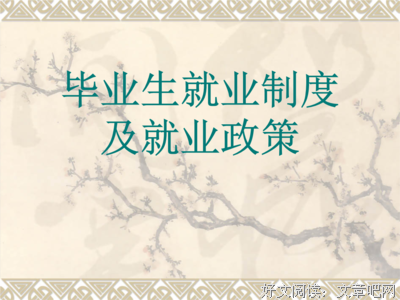
《我的大学1970-1976工农兵大学生》是一本由海天 / 肖炜著作,中国友谊出版公司出版的273图书,本书定价:28.00元,页数:2009-5,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估计是啥节目改成的书,讲的非常简单,试图以点带面。提了一些重要的事件和文件,还行。
●文章叙述较有深意。军队推荐士兵、农村推荐知青等工农兵大学生的组成者皆有叙述,涉及70至76各届大学生,期中也选取了文革期间及现代较为知名的人物。背景资料也有简略叙述。但是内容过于单薄,分析不够深入全面
●故事性很强,读来印象很深。一个时代背影下的个体奋斗或抗争。我们或许该庆幸,哪怕高考有再多的弊端,至少它不是那么的唯成份论。至少,大学里我们能够自由的阅读和思考。
●错别字太多。
●叙事性较强。
《我的大学1970-1976工农兵大学生》读后感(一):没有深度、思路混乱
很差的一本书,在机场买的,没有报很大的希望,因为本身出版社就不怎么样,可没有想到会这么差,毫无深度可言,思路及其混乱,失望!希望以后能有类似题材的好书,想了解这个时期的历史。
《我的大学1970-1976工农兵大学生》读后感(二):那個年代的那些大學生
书中通过当事人的回忆,还原那个时代的历史。有的人凭一张白卷上了大学,有些有能力的人却一再被拒之门外。在那样一个知识无用的年代,有些人依旧不放弃对知识的渴求,着实让人汗颜。他们作为历史的产物甚至尴尬的活于76之后,国家没有给予他们公正的解决方案,然而自强的人总有办法证明自己,学历算得了什么。贾平凹 敬一丹 李银河都是当年的工农兵大学生。我想的确每个时代都有其最好之处也有其最坏之处吧,纵使我现在也有些愤青倾向,但我依旧怀有希望,热爱生活。
《我的大学1970-1976工农兵大学生》读后感(三):荒芜的年代也有有价值的人和事
这本书类似访谈录。总体比较浅显,但却从中得到了许多信息。 1.原来文革期间是有大学生的。只不过是通过推荐上大学的。这种招生模式在当下其实也是值得思考和研究的。
2.工农兵大学生从1970年招收第一届到1976年最后一届,总共七年时间,全国共有94万工农兵大学生。
3.他们虽然有的文化基础比较弱,但原来也有很多很出色的很有名的,比如李银河,梁晓声,陈尚君,贾平凹,王石,敬一丹,张承志等人,可见我们应该客观对工农兵大学生作出评价。
4.工农兵大学生有的一年,有的两年,有的三年,最后被认定为“大学普通班”,大专学历,原来大普是这么来的。
5.托关系,走后门在哪个时代都存在。媒体对某些人物夸大式的宣传报道哪个时代也都一样!
6.get几个关键词,商品粮,上山下乡,知青,红卫兵,上管改,梁效,理想之歌...
总之,这本书还是挺有价值的,作为教育工作者,从中获取很多信息。对于研究高考制度,研究知青和现代中国教育变迁有一定价值。
最后,说一句,其实在荒芜的年代,也有有价值的人和事。凡是都要一分为二的来看。但是,荒芜混乱的年代还是不要有了,太折腾人了!所以要感谢邓小平恢复高考。感谢公平的高考制度!
《我的大学1970-1976工农兵大学生》读后感(四):80后的父辈: 《我的大学 1970-1976 工农兵大学生》读后感
今天看了一本书,《我的大学 1970-1976 工农兵大学生》。其中一个采访对象的经历是这样的:他上高中的时候,高考取消了,他很失望,就去当了兵,在部队里搞宣传。数年后的一天,指导员跟他说,部队准备送他去上大学。他将成为工农兵大学生,去北京大学,学印地语。 他高兴坏了,没想到当了兵还能上北京大学。他说,即使当年参加高考,也不可能考上北京大学。 他对印地语一无所知,抱着“我是革命一块砖,哪里需要哪里搬”的想法去了大学。然后他就成了著名学者季羡林的学生。
读了这个故事,我明白了为什么现在仍然有很多人对毛泽东时代怀有好感。 因为在那个时代,一个普通百姓家庭的孩子不用凭借任何关系,只凭为国家的建设奉献青春的一腔热情,就可以被国家信任,就能获得很多资源,让他们受到教育,施展才华。 虽然当时整个教育制度乃至政治制度是荒谬的,摧残人性的,但是对于出身贫苦家庭的个体来说,他们是能得到平等对待,甚至优待的。我的父亲也是一名工农兵大学生。 他在上大学前是农村出身的一名矿工。上大学后,除了学习专业课,他还被送往全国各地的工厂去实习,学习使用最先进的设备。 他大学毕业后分配到工厂,数年之后就被选为厂长。
他们这一代被国家信任的年轻人,在国家的帮助下完成了从普通人到高帅富的转变,对于国家的制度是充满信心和满怀感激的。 而我们80后,成长在拼爹时代,完全体会不到教育和就业的公平。我们的同龄人中,能从国家得到好处的都是有关系有背景的官二代富二代,而绝非平民老百姓的子女。 在我看来,已经没有80后会像他们的父辈那样真正的热爱国家。 为什么?如今的国家不信任80后,不让80后表达,不给80后自由,还弄出个房价问题来束缚80后,80后自然不爱国家。现在80后的玩东西都是80后自己弄出来的,国家基本都是反对,最好的情况也就是不当一回事。80后要重新找回对国家的爱,可能要再等30年,等到80后有话语权的时候。
《我的大学1970-1976工农兵大学生》读后感(五):教育大时代的个体
当下的困惑,总是激发历史之同情,当好大学减少了乡下娃,“工农兵大学生”制度设计的初衷与得失,以及包含的个体遭遇,需要在标榜公平与现实分化的时代,重新加以思索。这场出于领袖意志、席卷全国上下的教育试验,只有在浪漫而坚定的革命激情与集中且存魅的权力结构下,才能得以推行。一个乌托邦的理想,改变了千万人的命运。它的光怪陆离、复杂多样,随着历史的退潮息影,但知识与权力的争夺消长,却从未停止。
切入这一群体的路径,经由两本小书。一册为自传小说,一卷为节目脚本,另有两卷本的《我是一个工农兵学员:泛政治化教育中的受教育者》,则要等到时间充裕的时候认真阅读。保持一点距离,返顾曾经过往,“历史,永远是一笔财富,不管是令人心酸的,还是带来荣耀的,而要得到这笔财富,其前提之一就是正视它。劫难需要记住,生活则需要感恩”。
1966年6月13日,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发出了《关于高等学校招生工作推迟半年进行的通知》,标志着文化革命期间高考的暂停。经过一年多的动荡,1967年10月14日中央《关于大、中、小学校复课闹革命的通知》发布,教育工作得以勉强维持。动荡之下,1968年毛泽东发布“七二一指示”,提出“大学还是要办的,我这里主要说的是理工科大学还要办,但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要无产阶级政治挂帅”。经过四年的动荡与摸索,随着1970年5月27日北大、清华提交的《北京大学、清华大学招生(试点)具体意见(修改稿)》经中央批准,开始在高考停止的状态下,依据“群众推荐、领导批准、学校复审”的原则,从工农兵群体中选拔学生。这一招录方式,持续到1976年。七年期间,一共招收94万学员,他们成为中国高等教育史发展历程中的特殊群体。其参差不齐的文化水平,严重影响了高等教育的正常进程。1972年5月8日国务院科教组转发的《北京市革命委员会科教组关于高等学校试办补习班的报告》显示:“北京市11所高等学校招收的工农兵学员文化程度参差不齐;高中以上文化程度的只占20%,初中程度的占60%,相对于小学程度的占了20%……工农兵学员毕业时达到大专水平的不到20%,多数人低于大专水平,少数人低于中专水平”。
工农兵大学生的招生过程以“推荐”取代“考试”,导致“走后门”风行。1972年5月中共中央发布《关于杜绝高等学校招生工作中“走后门”现象的通知》文件,实际并没有彻底地触动。以历史上的“九品中正制”与“科举制”为对比,可以发现其中的相似。有趣在于,往昔九品制造成“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士族”的门阀统治;而教育革命的推荐制度初衷则是致力于实现“上品皆寒门”的阶级转换,以“又红又专的无产阶级专家”取代“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
文化革命时期,曾对1949年以来的教育事业加以定性,称为“十七年教育黑线”,作出“两个估计”的判断:“文革以前培养的知识分子是资产阶级分子,基本上是不能为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服务的”。建政以来,学校考试制度选拔的人才,依然是家庭地位比较优越的城市学生,而作为领导阶级的工农子弟却被挡在了校门之外。打破文化藩篱,夺取教育领导权,成为继政治革命取得胜利、土地改革与资本主义改造之后,革命力量在文化领域对“资产阶级”的思想之战、文化之战。通过充分激发工农兵学员的革命热情,实现无产阶级对文化领导权的掌握,“上大学、管大学、用毛泽东思想改造大学”成为无产阶级改造大学堡垒的主要武器。自中世纪大学诞生以来,从未有工农阶级如此深刻地介入大学改造,它所描绘的平等场景如此激动人心,即使在今天依然令人心动:向为权贵和富人垄断的象牙之塔,终于迎来了下里巴人。他们来自土地、工厂、军营,以改造世界的雄心,摈弃温文尔雅、高谈阔论,相信受苦的人,终将得救……
1993年,国家教委、人事部联合发文规定:1970至1976入学的高等院校毕业生,即工农兵大学生的学历,国家承认为“大学普通班”,简称“大普”。这是一个特殊的称谓,也呈现了一个特殊的时代。许多人对他们不屑一顾,以为他们作为既得利益者,不学无术却侵害了普通人的权益,降低了大学水准。这样的义愤,遮蔽了个体的悲观,偏离了批评的方向,并非合适的态度。高考停止的十年期间,它庚续了教育的火种,培养出陈尚君、李银河、陈力丹、梁晓声等学者作家,并以己身参与到一个改革的时代。也有许许多多的工农兵学员,在平凡的岗位上,工作,生活。
“迎着灿烂的阳光,肩负党和人民的希望,我们工农兵学员,来自祖国四面八方。带着工人阶级的嘱托,带着贫下中农的期望,带着革命部队的传统,走向教育革命的战场”。这是一首《工农兵学员之歌》,怀着革命的热情,他们奔赴文化的战场。很难说这场战役的成败,但文化的积淀,肯定与战争的胜负不同,牺牲的热情在文化的力量面前并非无往不胜。褪去宏大叙事的大氅,缝隙里的个体,在荣辱里挣扎,度过属于自己的一生。去掉标签,那是一个疯狂时代里,一群普通人的生命挣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