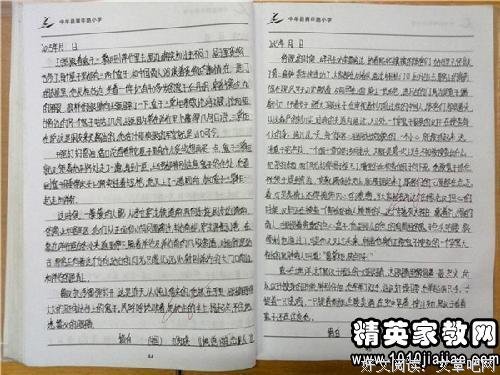
《天意从来高难问》是一本由卞毓方著作,中国文联出版公司出版的平装图书,本书定价:29.80元,页数:307,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结构设置有点儿意思,但是穿插太多作者评论,在传记里实在不该,而且很多偏执性很重。过褒过贬彰显个人。http://book.douban.com/review/2221264/ 这篇文评讽得不错。
●點讀過有點愧疚,因為只看了兩頁,寫得沒法看,盡管對季先生的生活充滿好奇,還是讀不下去。
●哦,季老!
●大器晚成之季羡林!这本书详细描述了季羡林的晚年的生活,可以看出老先生对文化以及生活的超然态度,通过记叙的一些事际,细致描述了季羡林的文化底蕴!期间穿插了很多别人的评论!这是我老婆送我的第一本书籍,当然要收藏的比较细致啦!
●只能说,客观的记述还是不错的,但是,作者自以为是的阐述,真心不赞同。一直还算挺喜欢看人物传记的,有些是把人物写得过于浮夸,而很少见这么浮夸的笔者,他不是我的菜。
●一般
●读罢此书,我不知道应当怎样来评价。书里屡屡提到季老的存在养活了一个季羡林研究所,一批季学研究者,一批媒体...季老评上“感动中国”十大人物时我还在念高中,常常在作文引用他的事例;一转眼,已经很久不写那样的文章了,而这本书则殆我们穿过季老头上的光环去解读一个百岁老人,一个孤独的知识分子。“当他选择了这条道路,其实也就选择了孤独。”这是笔者的开场白,满是“无处话凄凉”之感。
《天意从来高难问》读后感(一):建议没读过的可以把时间节约下来读其它的书
文笔平平、内容粗陋,作者虽自称是季老弟子,但字里行间多得是自以为是的卖弄,看不出弟子与老师之间的情谊。书虽厚厚一本,但形神俱散,大有灌水猪肉的嫌疑。我把全书读完后,除了不知所云还是不知所云。再配合上扉页作者的自我吹嘘,实在是令人不敢恭维。
建议没读过的可以把时间省下来读些别的。
看到这厚厚的一本书,的确我是寄予厚望的!我非常敬重季老!我的敬重是是对一位老学人的敬重,与他是否是国学大师无关。但是,在这本书里,我什么也没有看到!真的正如一位同仁所言,满本书里晃的都是卞敏方,不是他说明他如何考证季老的一些事的波折,就是自己站出来对季老进行评点。仿佛他成了主角,而传主只是为了证明他这个主角的最好的映衬!一不小心,就会觉得,这是一本对传记作者的赞美诗,反而找不出一点关于传主的精神来。里面是写了不少关于季老的一些不为人知的事情,但是,竟怎么也让人读不出季老的精神风骨。
一部好的传记是我们精神和力量的源泉!法国著名作家罗曼罗兰曾写过《名人传》,由《贝多芬传》、《米开朗琪罗传》和《托尔斯泰传》组成。罗曼罗兰没有于对名人们的生平做任何夸耀的叙述,也没有像大多数传记家们一样追溯名人们的创作历程,而是写出了他们与命运抗争的崇高勇气和承受全人类苦难的伟大情怀,可以说是为我们谱写了一曲伟大的命运之歌。
罗曼罗兰曾经说过,“伟大的心魂有如崇山峻岭,我不说普通的人类都能在高峰上生存。但一年一度他们应上去顶礼。在那里,他们可以变换一下肺中的呼吸,与脉管中的血流。在那里,他们将感到更迫近永恒。以后,他们再回到人生的荒原,心中充满了日常战斗的勇气”。他这其实就是对传记要求!季老的传记其实也应该是这样,能够给我们动力!但是,从这本书里我没有找到。
至于书名,也让人怪怪的,“天意从来高难问”,看完全书,也没有明白,为什么天意从来高难问。据考证,这名诗出自宋朝诗人张元干的一首词中,全句是“天意从来高难问,况人情、老易悲如许。”词中的意思从词面上就可以看出来,是悲凉的。我认为,中国古典诗词其实就像是中国的文化基因,是密码,大家引用的不仅仅是诗的表面意思,还也有诗词那原本的意境的隐喻!为什么,现在要用这句诗来写季老呢?莫名其妙!季老的人生也许有一些不如意,但谁能说他的一生不是圆满美丽的一生呢?
天意为何高难问,我明白了,是因为心不诚。书中就没有读到传记作者对于传主的那份敬重,那份爱的激情!他只是一位作者,一位可能和季老走得比较近,而精神的距离却很远的局外人,他无法读到真正的季羡林,所以,他也没有真正走进季羡林的心理世界。
其实,真的并不是和传主最近的人能写出好的传记,和传主同时代的人也非必写出最好的传记。林语堂在写《苏东坡传》时就说,“这就是何以评论与我们自己同时代的人是一件难事,因为他的生活离我们太近了。” 林语堂还说:“我们只能知道自己真正了解的人,我们只能完全了解我们真正喜爱的人。”我怎么一点也没有看出作者对季老的喜爱呢?也许他是有机会的,但是因为浮躁啊,他没有静下心来去聆听。其实,这是社会通病,真的不是卞敏方一个人的错!
《天意从来高难问》读后感(三):小卞写大师
这本书的副标题为《晚年季羡林》,作者自称是季老的学生,从书中也可以看出来,作者在季老人生最后的岁月里还是和季老走得比较近的,他经常会去探望季老,自然也就会掌握着一些第一手或者第N手的资料。而季老刚刚逝世不久,作者推出这样一本书可谓是“与时俱进”,自然会吸引很多的眼球。
这本书里也确实写了一些季老鲜为人知的故事,看过之后对季老的为人尤其是他晚年的行事和思考的风格也有了进一步地了解。而我在阅读此书的时候经常会产生一个想法:季羡林是国学大师,这不假,但他真的有那么伟大吗?世人对他的崇敬究竟是来源于什么呢?在本书里作者卞毓方曾记录道有人拿季老和杜甫来比较,说季老在高唱“海晏河清”之外,是不是也该想一想“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
我想,这些可能都已不再重要,季老是伟大还是幸福抑或是别的什么都不重要,因为季羡林只是季羡林。
然而我又在想,此书的作者、自称季老学生的卞毓方,究竟如何看待季老呢?
卞毓方说:“人家能量很大,是文化领域超级致密的中子星,跟他打交道,要适当保持距离,掌握进退。”这段话,又是何意呢?
其实卞毓方这本书可以写得更好些,或者干脆不如说,他的这本书写得并不好。我估计可能是出版社急于在老人家逝世之后“及时”推出这本书,才导致这本书有很多问题,也许作者都来不及统稿,有些材料——比如季老写的关于家庭的那些文字被作者反复征引,让人厌烦。
作者自称是写散文的,而他的行文风格也的确很散文化,或者可以说过于散文化,散漫、啰嗦、没有重点、没有节奏。而有些语句倒是颇能体现出作者是季老“学生”这个身份,作者的部分行文和季老的行文非常接近,极有照猫画虎之嫌。我们随便找一段:“季先生关于‘三辞’的叙述,我玩味许久,起先打算也写点东西,后来想,算了,何必凑那个热闹。有些事,你不到那个地步,就不会有那个境界。”我们找季老的一段文字对比一下:“父亲认字,能读书,年幼的时候,他那中了举的大伯大概教他和九叔念书认字。他在农村算是什么成分,我说不清。”瞧瞧,这断句,三五个字一个标点,再看看那倒装句,是不是一模一样?可是这里的问题在于,季老写《病榻杂记》是近百岁高龄,说话啰嗦点,语句断续一些都不仅无可指责,还可以说这是老人家特有的风格,可你卞毓方,也有七老八十了吗?
除了语句的啰嗦像老人,此书的行文还有点像黄健翔解说足球,动不动就疯狂一下,我们先看黄健翔:“亚昆塔!哎,点球!点球!格罗索立功啦!格罗索立功啦!格罗索,他继承了意大利足球光荣的历史和传统,在这一刻,格罗索不是一个人在战斗,他不是一个人!!!”我们再看卞毓方:“她一遍,又一遍,周而复始,反复朗诵,泪水顺着腮帮刷刷直淌。难道这是魔咒?难道这是真言?让杨锐始料不及的是:奇迹!奇迹出现了!”“格罗索立功啦!”看看,放在一起真的是同一语境,问题在于,黄健翔解说足球需要激情,你卞毓方又何来的歇斯底里?
书中大量充斥着废话和这样莫名其妙的感叹,比如“这是我无数次探望季老中的一次”,这话有什么用?还有,季老写“物无涯,悟无涯”,作者也要感叹一下,“是啊,大千世界物无涯,悟也无涯”,这话显得多么蛇足。害得我都想画两个惊叹号了。
书的结构也有问题,说是“晚年季羡林,其实写了很多季老年轻时的事,而且还说了许多有关别人比如胡适的事,感觉离主题相去甚远。
总之,此书可以窥到季老的一些光彩,但作者的文字却是绝对不敢恭维。
《天意从来高难问》读后感(四):您感觉地球转的更快了吗?
钱钟书在《魔鬼夜访钱钟书先生》一文中写道,你要知道一个人的自己,你得看他为别人作的传;你要知道别人,你倒该看他为自己作的传。自传就是别传。
先生这段议论读来相当畅快,因为那么多糟糕的传记摆在那里,事实不就如此嘛!可是,如果自己手上有一本完美演绎了此观点的传记,那就让人感觉相当不快了。读完《天意从来高难问》,我只能掩卷长叹,钱大仙人的论断又灵验了,在晚年季羡林的背面,我分明看见了满纸的卞毓方。万幸的是,此书乃卢十四慷慨赠送,翻翻封底,二十九块八毛钱,活活够我在学校吃两个星期的羊排,这笔银子要是花出去了,岂不是要悔青了肠子,大呼上当。
谁都知道,除了本人以外,没有一个别的谁可以完完全全清清楚楚的了解一个人的所思所想所为,哪怕自己有时也不可以,所以传记无法做到绝对真实,这应该也是钱钟书不待见传记、回忆录的原因之一。但是传记总是有必要存在的,也无须要绝对真实。但是,一个作者为他人作传,我觉得起码要对传主有足够的负责和尊重,要有足够的诚意,不是为写字而写字。随便捡一个例子,试看作者的诚意几何。
在“初恋•美人观•爱情观”一节中,作者又引原文又评述,讲季羡林先生如何回忆描述少时心仪的彭家四姑娘,行文已嫌啰嗦,末了又宕开一笔,说:
“季先生看美人,重点在于细腰。文章中,季先生一如上篇谈‘小姐姐’,引用了宋词中有关细腰的描述,多达九处。”
我正琢磨着这是哪儿跟哪儿,冷不防又见作者还有后着,另起一行,“分别是”,然后将九首词一一原文列出。这还没完,作者仍然有话要说,
“这些词,季先生当年肯定经常把玩,烂熟于心,否则,临时查找,以他目前的处境,是勉为其难的。”
话说到这个地步,爱算是彻底服了幼。不过卞总您知道么,残酷的压榨米粒,能整出爆米花,残酷的压榨胶体,能整出大棉花,可残酷无情的压榨本就不太富裕的文字,却整不出妙笔生花,那样只能弄出赤果果的凑字充数和无病呻吟啊。
类似或更残忍的情况不忍再举,哪位想不开,可以自己翻阅。我想说的是,如此作传,显然已经不是写作技巧方式的问题了,文字里究竟有多少诚意,读者已心知肚明。卞毓方好歹也是一个成名人物,既不穷困潦倒,何必去学古龙(无贬损古大侠之意),既不受困于应试镣铐,何必去学那焦头烂额的考生?
卞毓方在书中对季先生的生活多有评论,很嫌多余。更不明智的是,他选择了一个家庭情感类杂志小编的方式对季先生的诸多方面进行了议论点评。一般来说,像季羡林这样一个当代泰斗级的人物,他的一些具体是非纠缠,非有一定分量的人物是不便点评的,话说多了,难免露拙。卞毓方似乎并未在意这一点。
这本书的腰封也颇为要疯,我拿到书后,读了上面的文字,顺手就给丢进垃圾桶。腰封上那段文字的大意为:写作三年,季老忌日收笔。书中也一再提及,说本书是随着季老生命结束而戛然而止云云。当然也是随即出版发售,毫不耽误。只是联系到书的内容质量,很难不让像我这样阴暗的读者猜想,《天意从来高难问》欲借老人的天时才是真。继而感叹,季先生真真是一颗大树。
“在卞毓方的笔下,没有一篇不是锦心绣口,匠心独运,没有一节不是反复锤炼,精镜妥帖。”如此种种,话已说满,然而内容却让人大失所望,传主季老那样清明一个老人,关于他的整本书却一股商业气息。我不由想到卞毓方本人的一篇旧文,内容大概是讽刺文章的色、霸和炒作,夸赞自己行文不色、不骂人、不炒作。文中虚构的专擅炒作的经纪人和他说:你我联手之日,应是文坛抖三抖之时。您感觉地球转的更快了吗?……
如今有人作法不自毙,悠然推新书,那么敢问卞先生,您感觉地球转的更快了吗?
《天意从来高难问》读后感(五):自说自话
传记的优劣分为三等。上等虽然述而不评,但证据充分,内容详实客观,能将被立传者的形象丰满立体的全盘展现;中等述而简评,评论贴切中肯,能引起绝大多数共鸣;下等述而胡评,自以为优越高明,能够看透周围一切世故。
很遗憾,假如让我将这本书归类,我会将其归为下等。
这是一本典型的采访体传记,看得出来,卞毓方成文之先,也下过一番苦功夫。几乎只要时机允许,就会与季羡林相见交谈,问询季羡林生平种种。除此之外,他对季羡林周围的人也是尽可能的一一采访,四处搜集季羡林的资料。
但是,我阅读完这本书后的感觉只有一个,卞毓方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孔方兄作祟的原因。
第一个证据,是2006年8月,李玉洁患高血压,重病在床,导致卞毓方的采访工作被迫中止。这个时候,他第一想的问题不是李玉洁的生命是否无忧,季羡林失去秘书后工作是否会因此受阻,而是他的书稿是否要推出,如果推出的话,交付哪家出版社。
第二个证据,是这本书的发行。季羡林刚去逝,这本书就适时出售。天时正切,人和犹胜。
季羡林逝于今年7月11日,及至今日,我读这本书的时间,不过一月。一个月的时间,一个与季先生有深厚情感的人,正常情况下都会沉浸在缅怀情绪中,怎么会有时间与出版社商谈稿件、稿费、具体出版事宜。难道为了吸引人的眼球,拿前辈来做噱头来在所不惜么。
写传记的任何人,都有权利取舍自己手中的材料,加工、裁切、创造。但是不要忘记,被传记者才是传记的主人公。卞毓方在写的时候,显然忘记这一点。他花费大量笔墨写自己,自己的散文、历史研究、自己如何奔波劳累在寻访季羡林家人的路上。本末倒置,喧宾夺主。
假如只是如此,也还罢了。人都要生活,钱对于生活来讲,是不可或缺的存在。为了钱而忽略其它,只要没有不利于它人,别人也并不能贬低。文字也是,作者有权利写自己想写的东西,没有妨碍到别人就好。
问题在于,除此之外,卞毓方的对季羡林的敬重本身就有问题。
季羡林晚年,因为衰老的原故,不可能将每件事都清晰回忆出来。纵不提季先生,年青人又有几个能将过去的人或事物数指说来。卞毓方在这方面,不停的渲染,深描。以发现问题为奇,以解决问题为趣,以贬低季羡林晚年的记忆力为荣。在卞毓方想来,这或许是种将一个平常的季羡林展现在世人面前的方式,但是这种方式,是对一个老者的不敬。不要忘记,卞毓方也会有老去的一天。当他老的时候,他的记忆也会混乱。到那时,如果有人拿他的缺陷反复大做文章,不知他是否能够坦然接受。
季羡林曾经说过,假话全不说,真话不全说。卞毓方采访的时候,季羡林自然也秉承这一原则。有些个人至为私密的事情,也自然不会向卞毓方谈及。就是这样,那些已被卞毓方得知的真话,被他层层添火加薪,到最后就成了仿佛他才是最了解季羡林的人。比如季羡林与家人之间的恩怨,在他津津乐道的笔下,他就成了熟知别人心胸的救世主。然而在我读后,我的感觉不过是卞毓方在自说自话。真正的情感,隐藏在内心深处,有时连自己都不能获知,况乎它人。
在书中,卞毓方曾用一段话来描述他对儒家的观点。他说,“我这里斗胆冒一句:中国文化在春秋之际遭遇儒家的洗劫,在冠冕堂皇的政治需求下,大肆篡改历史,阉割文化。汉唐以后,儒学蹿升为国学,作伪的手段更是变本加厉,花样百出,乃至假话盛行。”稍有常识的人都知道,春秋战国,百家争鸣,非儒一家。那个时候,儒家也并不出彩。否则孔子也不会一生都在奔波。汉唐以后,明则儒治,则实阳儒阴法。至于作伪的手段,正宗儒家从不提倡,他们只会认为会作伪的人是小人。卞毓方在209页,用这句话来为自己的学问做了一个并不高明的总结。
还有一个小章节,用来描述金庸与季羡林在2007年的那次相见。6月18日下午,金庸在北大学演讲时,谈到当今社会侠有什么发展的空间,引用了季羡林的一句话。卞毓方说,金庸低估了学生的水平,虽然抬出季先生的大名,也无济于事。但恰恰相反,我却在这段话中看出金庸要表达的意思。金庸的中心有两点,第一是中西文化的对比,第二是路见不平、拨刀相助两个字。前者是世界性大方向的差异,后者是完成侠义要具备的心性与行为。我不知道是否因为卞毓方理解能力差的原因。卞毓方还说,金老先生明显不甘寂寞,时不时闹出一点新闻。《庄子》有云,子非鱼,焉知鱼之乐。同样,卞毓方不是金庸,不是季羡林,他永远不会知道金庸与季羡林何以如此,也永远无从体会这两人被众口烁金时的无奈。
季羡林的身份,被卞毓方定了位。他说,季先生上岁数了,文化意义已经大于学术意义,象征意义已经大于实际意义。梁启超说过,文化是学术的核心。那时的季羡林年纪虽老,但学术专著不会老去。从实际意义上说,季羡林的论文乃至他本身,假如有所象征,也是象征一个人对学术的辛勤不缀以及求真不倦。卞毓方太自大,他只看到表面,却不知道缘何会形成这个表面,也不知道表面下埋藏的到底是什么。
248页,卞毓方又说,季老的辐射只限于轮椅所及,到了官庄,就强驽之末势车水马龙能穿鲁缟了。这是错中之错。只要季羡林的作品还流通于世,季羡林就永远在辐射。
最后,我的一位朋友说,这本书是知音体、凑字数。我觉得说的很有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