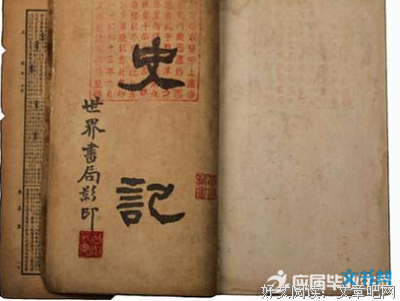
《疾病的文化史》是一本由(美) 西格里斯特著作,中央编译出版社出版的平装图书,本书定价:49.00元,页数:238,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一本捋清楚脉络的书,写于上世纪,虽说内容有点过时,但是看看人类医学的进步上一路走来的过程,还是很有趣的。
●从当年来看其实挺有意思的。一开始觉得很无聊,越读越觉得是了解那时候信息的好东西。
●超级好看一本书
●不错,就是有点老
●内容比较散
《疾病的文化史》读后感(一):疾病的文化史
因为学医,朋友送的生日礼物。说实话这里的故事我基本都看过,但从来没有慢慢的体味,决定再温习品味。
疾病的文化史也是医学的发展史,人在与疾病的斗争,疾病从来都不曾战胜人类,也不会战胜人类。人在与疾病斗争中不断强大起来,疾病也在与人斗争中变得愈加顽固,但我相信总有一天会胜利属于人!
《疾病的文化史》读后感(二):上世纪50年代的医学观
很认真地读完了,作为讲稿的综合体,本书更多地代表了上世纪中叶的医学观,从社会学层面详细解读了西方医学史。
通过西方医学史,再看看中医本身。现代医学脱胎于西方传统医学,并不是技术的进步,而是思维方法的变化。这部分可在本书疾病与宗教、疾病与科学,疾病与哲学三章中看的。
在工业革命之前,西方传统医学和中医并无二样,一样把现代医学并不怎么重视的脾作为很一个很重要的器官,从文化角度,希腊把数字四用于医学,而中国文化的熏陶下,中国传统医学用五,甚至气血的概念也基本相似。
现代思维改造中医的不成功,或许是中国传统医学的自身的张力,更或许是中医传统医学对现代文明存在着天然的斥力。
《疾病的文化史》读后感(三):读后感A0002
白人的征服,既要归功于火器,也要归功于烈酒。酒精对美洲印第安人的影响众所周知。印第安人所使用的兴奋剂一直是烟草,这玩意儿并不醉人。威士忌摧毁了他们的抵抗,使他们很容易成为剥削的牺牲品。同样的征服手段也被应用于世界上的其他地区。
紧身胸衣多半是发生在很多18世纪女士身上的抑郁症、昏厥和痉挛的主要原因。它裹得越紧,对健康的影响就越糟糕。通过压迫胸部的下半部分和腹部的肌肉,紧身胸衣严重损害了呼吸。它还使得肝脏变形,压迫肝、胃及其他腹部器官,并使它们产生位移。它极力压迫血管,以至于呼吸、消化和循环系统都受到了严重的影响。几乎所有的疾病,都可以归咎于紧身胸衣。这或许言过其实,但毫无疑问,这种该死的衣服对女人的总体健康和精神活力有着非常糟糕的影响,并因此对很多病例的发展做出了很大的贡献。总之,紧身胸衣使得女性成了柔弱无力的性别。 人穿得越少就越干净,这似乎是一个规律。热带非洲的土著人非常干净。欧洲人穿的衬裙及其他衣服越来越多,欧洲于是变得越来越脏。 为了满足自己的需求,任何时代的人都必须工作。即便是在热带地区,他也不得不去采集水果,捕鱼狩猎。整本书的行文松散恣意,与书名格格不入。书中内容经常出现上述令人抓耳挠腮的表述和逻辑,很难读完整本书。每章标题与内容不相匹配,令人尴尬。
《疾病的文化史》读后感(四):这是一本玩跨界玩出水平的书
找到这本书,源于一个设想。因为在医院工作的关系,发现不少人在大病康复之后,或多或少会在人生态度上有一个显著的变化,变得更加超脱、淡然。这让我想到,疾病对一个人的影响不仅仅是生理上的,而且可能还不是潜移默化式的,而是会留下极为深刻的心理体验的影响。可以推想,当疾病发生在艺术家、哲学家或者君王的身上,将会给人类社会打上怎样的印记?
按照这个思路,找到了这本书——《疾病的文化史》。作者亨利·欧内斯特·西格里斯特(1891-1957),美国著名的医学史家,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医学院教授,是将社会史的方法和路径引入医学史研究的开拓者。作者以跨学科的纵横捭阖,将读者领进一片少人问津的历史的旷野中。七千年的人类文明演进,疾病在其中扮演了一个自始至终挥之不去的角色,甚至在很多时候还会跳出来主导一下发展进程。“对个人而言,疾病不仅仅是一个生物过程,而且还是一段经历,它很可能是一段刻骨铭心的经历,对你的整个一生都有影响。既然人是文明的创造者,那么,疾病通过影响人的生活和行为,从而也影响着他的创造。” 疾病仿佛人类的胎记,与生俱来,不容争辩。不论地位、种族,在疾病的面前似乎只有听任摆布。有时历史的拐点也因此发生转折。一项始于2001年的由美国人史蒂芬·塔尔蒂(StephanTalty)调查所得出的结论再次印证疾病对历史转折的贡献。1812年拿破仑率60万大军征讨俄国惨败而归,最可怕的对手并非俄国人,而是斑疹伤寒,它以每天解决6000名法国士兵的速度击败了天才的拿破仑,直接改写了欧洲近代史。
“既然人类历史上任何时期都出现过疾病,那么,一切人类制度都必然受到它的影响,并且不得不以这样那样的方式对付它。法律试图控制人与人之间、以及人与物之间的关系,因此不得不把病人考虑在内。如果不处理疾病和痛苦所带来的问题,那么,宗教和哲学就不可能解释世界,文学和艺术也不可能充分地再现世界。”疾病好像佛洛依德所说的“潜意识”,在不知不觉中就把各国家和民族的历史打上烙印。鼠疫两次横扫中世纪的欧洲,持续200多年,几乎杀掉一半欧洲人,给欧洲带来了长达数百年的社会心理问题。死亡的惨烈有时让人不寒而栗,甚至1386年的维也纳城仅有5人从鼠疫中幸存,巨大的恐惧和无助使得人们对上帝的全知全能产生了怀疑,社会普遍存在“活在当下“的生存哲学,文艺复兴的社会心理基础由此形成。绘画的主题也从宗教场景逐渐让位于以对现实的描绘。鼠疫与文学同样密不可分。黑死病大流行的时候薄伽丘正在佛罗伦萨——黑死病传播最严重的城市。文艺复兴的旗帜性巨著——《十日谈》就是直接以这场瘟疫为题材,可见这场恐怖的瘟疫对作家影响之深。欧洲的不少法律溯源也与之有关,如检疫隔离(quarantine),是源自中世纪最重要的鼠疫等流行病预防措施,其观念沿用至今。而犹太人在当时被错误地认为是瘟疫传播者而大加屠戮,直到二十世纪仍然影响着一些欧洲的种族主义者。又比如疾病对艺术的影响。除了大家熟悉的梵高患有精神分裂症之外,格列柯(1514-1614,西班牙著名画家)患有散光,因此他笔下的人物总是很长且扭曲。画家华托(1684~1721)一辈子都是结核病患者,当时结核病还无法治愈,“因此他的画有很多无忧无虑嬉戏的优雅女士、意大利喜剧演员、勇武的士兵。这表达了一个人对自己被无情地排除在外的那种生活的向往,表达了一个知道自己的生活注定在劫难逃的病人的情感喷发。”2001年,荷兰一名叫费拉里的神经病学家指出:毕加索之所以能绘出抽象画,是源于他当年身患一种罕见的偏头痛,那些抽象画很可能是他发病时看到的影像。看来,疾病影响着艺术,现在仍有新的证据。
西格里斯特博士出版这本书的时候,是1942年,稍留意一下历史纪年就会知道当时的世界发生了什么。在本书的结语中作者写道:“当所有的智力资源、人工技能和自然财富似乎都被动员起来用于毁灭文明的时候,写这样一本关于文明的书似乎是徒劳无益的。然而,我们必须始终记住,在人类历史的长河中,文明是一个非常年轻的现象,向原始野性倒退的事情注定要发生。在短短5000年的时间里,我们已经实现了很多,我们创造出了炸弹无法摧毁的文化价值。这个世界比过去更自由,更公正,更健康然而还远远不够……”
西格里斯特博士拥有渊博的医学史知识,而且通过他在全世界很多不同国家的旅行和逗留,获得了大量的个人经验,这使得他对医学与文化史的理解更加独特和深刻。本书的贡献不仅在于为我们揭示了整体文明与疾病之间的密不可分的联系,包括更为详尽的疾病与经济、社会、法律、历史、宗教、哲学、科学、文学和艺术之间的关系。而且,我们还能够从书中体会到作者作为医学家的人文情怀。 “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泪水?因为我对这土地爱得深沉……” 西格里斯特博士以他科学的冷静和对生命的悲悯,致力于开启一扇从医学的角度研究整个文明史脉络的大门,以至于70年后的人们重读此书,仍能感受到那份穿越了时间的温度。
《疾病的文化史》读后感(五):读书笔记
《疾病的文化史》作者西格里斯特(1891-1957)是把社会史的方法和路径引入医学史研究的开拓者。这本书探讨了医学与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的关系。
(英国)在1848年的《公共卫生法》开创了一系列的公共建设工程之后,卫生状况得到了改善。1824-1825年间,工人组织工会的权利在英国得到承认,在一个多世纪的奋斗过程中,他们成功地逐步改善了他们的工作和生活条件。(P50)
今天,尽管医学已经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但全世界依然有10亿人(主要在亚洲和非洲),其生活和卫生条件,比西方世界在整个历史上所经历过的最糟糕的情况还要糟糕。因此,我们的问题决没有得到解决。它不仅需要医学的手段,而且更需要采取广泛的社会和经济措施。所以说,公共卫生问题归根到底是一个政治问题。(P57)
1377年7月27日,拉古萨城议会下令,所有来自疫区的旅行者都被禁止入城,除非他们在梅尔卡纳岛上先呆上一个月。威尼斯如法炮制,把国外旅行者隔离在圣拉扎罗岛上。期限从30天到40天不等,因此,检疫隔离(quarantine)这个名字就是为一项源自中世纪的最重要的流行病预防措施而发明出来的。(P83)
玛丽·贝克·艾迪(1821-1910)创立“基督教科学教派”,注重以信仰手段治病救人,这个教派在当时美国医学发展一套极其机械的治病方法、忽视心理因素的时候大受欢迎,后来医学心理学和精神病学得到发展才使这一趋势停滞不前。基督教科学教派处心积虑地从医生那里抢患者。20世纪初,从以马内利教堂开始,发展出一场完全不同的运动。其创始人埃尔伍德·伍斯特是一名牧师,曾在莱比锡师从冯特研习过心理学,是费城的精神病学家S. 韦尔·米切尔的朋友,对精神病领域颇有兴趣,他在1905年前后开始与约瑟夫·H. 普拉特博士合作举办了一个“肺结核班”,面向的是贫民窟里的病人。“治疗方法包括被认可的治疗肺病的现代方法,加上训练、友谊、鼓励和希望。简言之,就是把身体元素跟心理元素结合起来。”这个榜样被广泛效仿,下一步就是建立“以马内利健康班”,为的是在“神经病和精神病患者”中展开工作。
这场运动跟科学医学决不是敌对的,正相反,它与当时首屈一指的医生开展合作,只接受由医生检查过的病人。换句话说,它是精神疗法,主要是暗示,由牧师、而不是由医生来实施,并利用宗教元素。毋庸置疑,很多精神病患者都通过这样的方法被治好,至少是有所改善。千万不要忘,在那年头的美国,普通的医生没有多少精神病学的经验,受过良好训练的精神治疗医生并不多。
现如今,美国的医生既是身体的医生,也是心理医生。他所受到训练包括心理学和精神病学,有很多的专家可用。他们很重视与牧师的合作,只要患者碰巧是一个信仰宗教的人。信仰无疑是一个重要的治疗因素,无论你所信的是科学,还是宗教,亦或是二者都信。然而不管怎么说,把精神病诊所交给医学去运作,总比交给教会更安全。(P134-136)
自阿斯克勒庇俄斯时代以来,科学医学已经取得了巨大的进步,但它依然有着严重的局限性。依然有很多疾病现象科学不能解释,有很多疾病科学既不能预防也不能治疗。大多数人依然死于疾病,而不是寿终正寝。只要医学尚没有达到它彻底消灭疾病的目标,就始终会有患者希望出现奇迹,向宗教、甚至巫术寻求帮助。任何时候,医生只要是低估了病源中的以及治疗方法中的社会因素和心理因素,他就会在重视这些因素的牧师那里发现一位强有力的竞争对手。(p137)
历史告诉我们,一个国家的政治哲学总是对它的科学发挥着重大的影响。医学是一门理性的学科,因此,当基础哲学是神秘主义的时候,它不可能繁荣,中世纪就是这样的情形……另一方面,在那些基础哲学是理性主义的地方,医学科学总是有最好的发展机会。
医生不应该害怕从事哲学研究。如果他不想仅仅做一个狭隘的专家,他就必须以更宽阔的视角去看待医学,必须知道医学在我们的知识体系中所占据的位置。如果他是一个真正的科学家,他的思考就会受到束缚,他就不会让自己迷失于不着边际的猜想中。(P150)
医学是一门手艺,也是一种世界观。(P211-213)
医学的任务是促进健康,预防疾病,当预防失败的时候治疗病人,并在病人被治愈之后使他们恢复正常的生活。这些是高度社会化的功能,我们必须从根本上把医学看作是一门社会科学。医学仅仅是社会福利制度链条中的一个环节,每一个文明国家都必须发展这样一套文明制度。如果说我们今天出现了失调,那它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因于这样一个事实:我们忽视了医学的社会学。长期以来,我们一直把我们的努力集中在科学研究上,并假设:科研成果的应用会水到渠成地自动解决。事情并非如此,医学技术跑得比医学社会学更快。(P221-222)
(美)亨利·欧内斯特·西格里斯特《疾病的文化史》,秦传安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9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