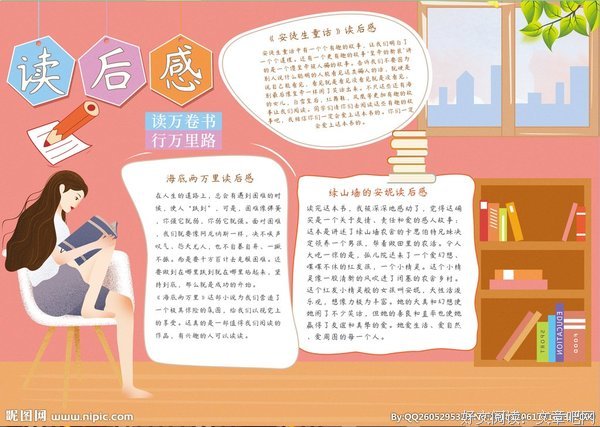
《穿皮大衣的玛利亚》是一本由[土] 萨巴哈丁·阿里著作,古吴轩出版社出版的平装图书,本书定价:42.00,页数:208,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世界上总有些悲哀的人,他们的生活十分不幸。他们都背负着生活的枷锁,有的人穷困潦倒为生活所逼,变得很卑微,小心谨慎的压抑自己。在这个世界上,他们找不到几乎找不到幸福和快乐。有的只是和别人的疏离和孤独的内心。如果你对这样的一个人感兴趣,那么就来看看这本书《穿大衣的玛利亚》这本书写出了一个人是如何变得孤独和悲凉。 这本书的作者是著名的土耳其小说家,他先是在土耳其师范学院毕业。1928年赴德国留学, 他在法国留学时接触到马克思主义以及马克思主义著作和法国革命运动。回国后担任教师教授德语,并开始从事文学活动。他最初创作风格因受到法国浪漫主义的影响,所以也是浪漫主义的,1933年是他创作风格的分水岭,因为这一年他结识了许多现实主义的作家,因此,风格转向现实主义。 因反对暴政揭露黑暗支持革命,而被人追杀, 主人公的家庭极度的不幸福,特别是对主人公来讲,他的家人尖酸刻薄,看不起主人公,学的主人公没本事,赚不来钱无法满足他们的愿望,即便是这样,主人公还是努力工作。靠自己微薄的薪水养活一家人,他的家人也包括他的一些亲戚。他妻妹的丈夫是一毛不拔的。 作者一开始并没有直接进入主人公的故事,而是以主人公一个好友的回忆为开始。这个朋友一开始对主人公比较好奇,因为主人公是一个极度隐忍,非常卑微的人。在主人公重病的时候,主人公的朋友央求主人公他的把日记留给自己,然后就开始讲述这本日记的故事。主人公无意间看到一幅画,这是一幅自画像。自画像上的人和主人公幻想之中的女性完全一样。 但后来他找到了这个女人,发现她和画上的大有不同,但是美好的印象却深深烙印在了主人公的心上,主人公接受了这个女人的一切,后来这名女性还了主人公的孩子,因难产而死去,而主人公也没有认回这个孩子。就在主人公的朋友拿到日记后不久,主人公九因病去世。 本书可以让我们更加了解那个时代的德国,本书描写的是一个爱情悲剧,虽然这个故事是带有时代烙印的,但是即便到了现在,类似的悲剧还在发生,什么时候这个世界才能真正的只有美好,只有幸福,我们要达到这样的目标,还要经历些什么?
《穿皮大衣的玛利亚》读后感(二):一个丧丧的爱情故事
这是一个丧丧的爱情故事,却又不完全是。
那时,一战刚刚结束,害羞少语又孤僻的男主人公莱夫听从父亲的安排从土耳其来到德国。他浑浑噩噩的生活因一幅画的出现而被打破,这幅画的作者就是自由热烈的女艺术家玛利亚。玛利亚给他的生活注入新的生机,莱夫的人生也在玛利亚的出现之后变得有意义起来。
可是,外表奔放,玩世不恭的玛利亚似乎有着坎坷波折的过往,她拒绝对任何人敞开心扉,对莱夫的爱也躲闪逃避,殊不知自己却深切的爱上了莱夫。
后来,莱夫接到了父亲去世的消息,即便莱夫认为他和他的家庭他的父亲之间仅仅是冷漠的亲情,他也不得不回到土耳其,参加葬礼,接手他被姐夫们算计过的微薄而荒凉的遗产(父亲众多土地中最贫瘠的一块)。
至此,莱夫和玛利亚的感情只有信件来维系了。然而,玛利亚的来信和信上的言语都变得逐渐稀少,本来就害羞多疑的莱夫,就更加质疑他们的感情。一错就是十几年。他和玛利亚终究都没有再相见……
-
这个故事更多是在莱夫的视角,讲述他的心理感受,从遇到玛利亚之前的孤独,到和玛利亚相遇之后的兴奋,幸福,再到和玛利亚分离之后的人生又再次陷入无限的绝望和黑暗。
莱夫表面看来是懦弱,多疑,焦虑和绝望的,除了和玛利亚相遇的那段时间,莱夫的人生仿佛一潭死水,他不和任何人分享自己的任何情绪,想法,经历,感受。
那些谨小慎微的心理活动在我这个读者看来有时候甚至是矫情而无意义的。我想这个故事安排在一战之后,是不是也想表达zhan争对人们精神上的影响?它让人失去希望,失去快乐,只是活着就精疲力尽了。甚至人与人之间的情感都是陌生的,这在后来莱夫对待家人的态度里也可见一斑,他觉得是在养活一群和自己没有情感联系的陌生人。
-
莱夫说:“我活得像棵植物,没有知觉,没有抱怨,也没有意志。我已经失去了感受的能力,既不悲伤,也不快乐。”
时代的创伤,在人们的心里留下了深刻的印记。
《穿皮大衣的玛利亚》读后感(三):《穿皮大衣的玛利亚》——不仅是在书写爱情,也是在书写时代
二十世纪二十年代,第一次世界大战刚刚结束,世界格局发生了重大改变。在社会本身遭受重创之后,人们的精神生活自然也会受到打击,固有价值观被推翻,传统信仰遭到质疑。保守的知识分子和艺术家大多感到十分空虚和迷惘,激进派则积极地重建着一种崭新的现代价值体系。
《穿皮大衣的玛利亚》这个故事的舞台是二十世纪二十年代的德国柏林。当时德国正值战败,经济不景气,就业艰难,人们活的没有什么尊严可言,人们热衷于政论,人人脑子里想的都是如何替德国“雪耻”。男主的祖国土耳其也是当时的战败国之一,失去了70%的领土,同样,人民的屈辱感被印刻在脑海深处挥之不去。
就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之下,去德国学习香皂工艺的土耳其人莱夫和德国画家玛利亚相遇了。莱夫是个出生于中产阶级家庭的腼腆的小伙子,他热爱文学,年轻时喜欢读浪漫主义作家的作品,成年之后成了俄国现实主义作家的狂热爱好者。他自尊心强烈,害怕自我表达,因为他和这个疯狂的社会本身格格不入,别人完全不能理解他的想法,他孩子气的性格导致他不能适应这个社会的生存方式。玛利亚是个骄傲的女性,她有半个犹太人的血统,童年悲惨的经历促使她形成了独立且多疑的个性。她看不上周遭那些追名逐利的普通人,也不想和有着大男子主义的男人交往,讨厌被人掌控,被人怜悯。她也和社会有一定程度上的脱节和矛盾,但她比莱夫更现实,更有应变能力,所以尚且能找到一份工作生存下去。
当莱夫在画廊中看到玛利亚的画时,这个腼腆且自尊心强的男青年瞬间读懂了画中人眼神中睥睨一切的傲气,他被这幅画深深吸引了。玛利亚的自画像和安德烈·德尔·萨托油画中的圣母玛利亚有着相似的神情,可以说承接了古典绘画中圣母玛利亚的意象。所以当玛利亚一开始问莱夫你觉得画中的女人像谁的时候,莱夫脱口而出说像妈妈。比起现代绘画纷繁复杂的流派,莱夫更喜欢古典绘画含蓄逼真的传统美。然而莱夫比起顺从又听话的传统女性,他更欣赏强大而又独立的新女性,认为这样的女性可以给自己指引的力量,让自己摆脱丧失了信仰的深渊。换句话说,玛利亚的自画像无意中重塑了莱夫丧失了的信仰,在他眼中,画家玛利亚本身就是自己崭新的信仰。
莱夫和玛利亚可以称得上是灵魂伴侣了。他们的共同特征是对周遭发生的一切变故都很敏感,不仅都有卓越的艺术敏锐度,而且都是崇尚理性之人,两人的灵魂至少有百分之八十左右是相似的。对于爱情,两人的态度倒是不甚相同。莱夫对玛利亚的态度是百分之一百信任,百分之一百追随,只要能待在玛利亚身边,他不惜牺牲任何事物。而玛利亚多疑的性格则促使她无法打开自己的内心,无法相信有一个人会爱她到把她当成了自己的信仰,这就是两人第一次矛盾的根本原因。
后来,当两人矛盾迎刃而解的时候,却被现实的洪流所袭击,最终阴阳相隔。作者书写的不仅仅是爱情,更是通过莱夫和玛利亚的眼睛写出了当时社会的混乱和不稳定,人们的自私自利,以及信仰丧失所造成的道德沦丧。失去玛利亚的莱夫彻底成了一个“活死人”,每天机械地活着,挣着一点点工资供一大家子人糊口,没有灵魂,没有慰藉,一心盼着自己早点死亡。
但是作者还是在小说的末尾埋下了一颗希望的种子。玛利亚怀上了莱夫的孩子,她宁愿牺牲自己的生命也要保全孩子的生命。莱夫和玛利亚的爱情虽然是个悲剧,但是也曾开花结果。他们孩子的身体虽然不好,但是对世界充满了好奇。孩子拥有无限可能性,只要世界上还有孩子,人类就不会落入绝望的境地。
《穿皮大衣的玛利亚》这本小说兼具浪漫主义和现实主义文学的特征。作者虽是土耳其人,但是在德国接受教育,作品中融合了东方和西方的思维特征,既含蓄又热烈。现代人可以说也是信仰丧失的一代,读这样的作品很容易找到共鸣,也能从精神上的空虚无望中窥见希望。
《穿皮大衣的玛利亚》读后感(四):自己无能,就不要把不幸生活的责任推卸给“爱情”
01 “爱情”和“生活”能混为一谈吗?棉花的答案是不能。 爱情是爱情,是两颗心灵的激情碰撞,是两个灵魂在五线谱上针锋相对奏出的乐章。 而生活是生活,生活里可以有爱情也可以没有。它的宽广复杂可以包含爱情以及其他很多感情的存在和消失。所以无论从体量意义上还是精神意义上,生活都应该大于爱情。 但总有人分不清,觉得没有爱情就没有生活。或者说要先有爱情才能有生活。 我听了真是害怕:一个连生活都没有的人怎么跟他谈爱情?难道跟这种人产生爱情的价值,就是为了帮他建造生活? 要知道生活本来就是复杂多变的,需要人费心费力的经营。寄希望于爱情既不现实,也不公平。 最可悲也最可怕的是,作为“工具”的爱情一旦消失,那些寄希望于爱情的人想得永远只有一件事:我落到这步田地,都是爱情欺骗了我。 02 棉花最近读了一本土耳其小说《穿皮大衣的玛利亚》,主人公莱夫是一个天生就没什么“男子汉气概”的男人,连他父母都说他像个女孩子一样羞怯扭捏。而且外界对他的评判越多,他就越不敢表达自己的真实想法。 就这样,他前面24年的人生就这么一直小心翼翼的走在人生的边缘。或者说,生活与他之间始终缺少一座衔接彼此的桥梁。 虽然莱夫的性格孤僻不讨喜,但他也有自己喜欢的东西,比如他十分希望可以根据“默契”来实现灵魂上的交流,而不是非要“说话”不可。毕竟他一直恐惧于向外界表达真实的自己。 也是孽缘,有一天,真的让他碰到了这么一个恰好跟他性情相投的姑娘,她的名字叫玛利亚。 03 玛利亚比莱夫大几岁,她厌恶男人将女人视作财产的大男子主义,这她忍不住排斥绝大多数男人。所以玛利亚在一定程度上讲也非常孤僻。但她跟莱夫不同,她仍有自己的生活。有一天这两个人相遇了。 介绍完人物性格后面的剧情似乎就不用多说了,那自然是“同时天涯沦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识。”两个人迅速的靠近,一起分担着双方多年来隐藏心底的想法和往事。 一开始莱夫不敢直接跟玛利亚谈爱情,因为他怕失去她。玛利亚也不想跟莱夫谈,因为她无法相信别人。但是某一天,长久的陪伴和习惯最终让两个人坦白心意走到了一起。 幸福来得这样突然,这样意外。所以它离开的也那样决绝。 04 莱夫的父亲过世,他必须从玛利亚身边回到老家去。他和玛利亚的关系只能靠写信维持。那是他最辛苦也最有盼头的一段日子。 遇见玛利亚前他根本没有生活,他始终活在自己的想象里,就像《白夜》中的“梦想家”,而事实上他既头脑也无才能,难成大事。 遇到玛利亚后他发现一切都变了,他终于找到了掩埋多年的“人生壮景”。只是好景不长,他们很快就面对分离。 但是没关系,玛利亚留给他的幸福的回忆一直支撑着他面对棘手的生活难题。他等啊等,等啊等,有一天他突然联系不上玛利亚了。 莱夫在失去爱人消息的绝望里逐渐消沉下去,就像蜡烛灭了以后只剩下葳蕤干涸的蜡泪和虚无缥缈的轻烟。失去了玛利亚的莱夫,就像永远失去了骨头的狗,再也无法恢复好不容易燃起的对生活的希望。 他开始因爱生恨。不仅恨玛利亚的欺骗,更恨这个无情无义的世界,恨一切人。他从一潭死水彻底变成了散发着毒气的沼泽。 而他将这一切不幸都归罪于那逝去的爱情。 05 土耳其作家萨巴哈丁·阿里的这部小说《穿皮大衣的玛利亚》是土耳其文学史上著名的小说之一。作家对莱夫这个人物角色的刻画既凄婉动人又惹人非议。 在一部分人看来,莱夫是个无法独立生活的可怜虫,他只能紧紧依靠着另一个可以理解自己灵魂的人生活,只能通过玛利亚搭建起走向真实世界的桥梁。而另一部分人,比如我,则不这么看。 莱夫的痛苦和软弱确实值得同情,可是当他把厌世和自轻自贱的理由归罪于爱情和女人时,他的人物性格就只剩下让人讨厌的怨天尤人的部分了。 莱夫之所以会这样其实是因为从一开始他踏入生活的方式就错了。他的自闭、恐惧,都让他无法与生活中的一切正常沟通,他觉得是别人不理解他。 而事实上是他因为害怕而拒绝揭示自己的内心,是他自己拒绝被理解。所以他需要一个翻译,一个转换器,一个能搭建他与生活的桥梁。 那个桥梁,他叫它“爱情”。 但敢问爱情何罪之有?要为你自己不向自己负责的人生负责?敢问女人何罪之有?要帮你背负你自己不愿背负的生活重担?这是我一开始同情莱夫这个人物,后来又对他产生鄙夷的原因。 诚然,莱夫是不幸的,好不容易用爱情做媒介打通了与生活和解的可能,却又突然间一切都失去了。而在我眼里玛利亚更不幸。因为即使她后来没死,跟这样一个仰赖他人的支持才能面对生活的男人在一起,早晚也会遭遇其他的不幸。 莱夫的根本问题就是他的性格导致的无能,而他把对于人生的全部痛苦和无力转嫁给一段“爱情”,则彻底毁灭了这个人物留给读者正面形象的可能。 06 再说说玛利亚这个女性形象。玛利亚虽然也有自己的转变过程和曲折内心,但相对于莱夫来说,她更像是以一个“圣母玛利亚”的象征存在。 她以坚强、独立、宽和的品格接纳了莱夫的稚嫩和天真,无为和软弱。她像母亲那样让莱夫第一眼看到就产生了无法抑制的爱和依赖。 但与此同时,玛利亚穿着时髦的皮大衣,用她特立独行的思想超然于同时代的所有女性。她是一个丰满的双面角色,既有独立的一部分又有与男性结合的一部分。她试图用自己的方式治疗被男人创伤的心灵,试图寻找女性在这个社会里的另一种生存之道。她像古典圣母又超越古典圣母。 穿皮大衣的玛利亚代表的不仅是输给生活的女人,也代表了在面对“生活”这个对手时,所有人都仰赖的那种生存意志和希望。玛利亚的死亡不仅是爱情溃散的开始,也意味着人失去“圣母”的关怀和引导所堕入沉沦的开始。 但人跟人是不一样的。在莱夫身上沉沦是彻底的,决然的,至死方休的。在别人身上可未必。他的一切举动在玛利亚的衬托下,就只剩下惨淡和不堪了—— 一个因为丧失爱情和怨憎爱情甚至人生的人,实在与人间的“圣母玛利亚”,也就是穿皮大衣的玛利亚,不相匹配。 07 最后用书里的一句话收尾吧:“我们别无选择,只能顺从的接受这些意外,接受生活压在我们肩上的所有重担。” 与玛利亚分别是因为生活里的一个意外,与玛利亚永远更是因为一场意外。其实仔细想想,当初莱夫踏入那间美术馆看到那幅玛利亚的自画像是时,又何尝不是一个意外呢? 虽然这些意外带来了美好的爱情,可他们终究抵挡不住生活的磋磨,改变不了莱夫心里厌世软弱的本性。就像圣母画像,即使栩栩如生,也不可能走入现实。
《穿皮大衣的玛利亚》读后感(五):年轻的时候,故事遗憾多,爱情遗憾多。
「爱情意味着伤痛,就像你献出自己供人剥去皮肉,并且知道任何时候,对方都有可能带着那皮肉离开。」上个世纪,苏珊·桑塔格就已经如此敏锐地描述爱情。
时至今日,选择孤单还是陪伴,都由「人」自己去思考,如果你认为爱情是高风险的投资,你可以频繁的更换;如果你觉得爱情伤透了脑筋,你可以脱离传统婚姻的绑定。
但有所选择就可能有所遗憾,你选了爱情的陪伴,就要面临失去时的痛苦,这些,总会有多多少少的遗憾。有句话叫做“得不到的最宝贵,过期的糖最苦”,最近读的《穿皮大衣的玛利亚》就有这种遗憾的感觉。
《穿皮大衣的玛利亚》是一本土耳其小说,是以主人公莱夫·艾迪芬的视觉讲述他离开家乡去德国柏林学习手艺继而遇上他珍爱一生的玛利亚的故事。
故事确实很精彩,但我读下来,总替男主感到愤怒,愤怒他为何会那么多“无用”。比如初遇时玛利亚时,他紧张、恐惧、孤独,不敢去了解并接触玛利亚;和玛利亚相识之后,被玛利亚的坚强、坚定感染,他才会将玛利亚深深烙印在心上,爱上了这个恰好跟他性情相投的女人。
因为玛利亚可以给他带来阳光,是他生活里的一束光线,可和玛利亚分离之后他的人生又恢复了黑暗、孤独,就像永远失去了骨头的狗。以至于他只能在日记中去记着这一切,却没有胆子去承认自己犯过的错。
玛利亚就好像一个意外一样,匆匆出现在莱夫的生活,给他的生活带去些许温暖和色彩之后,又被丢失在时间洪流中,正如小说最后那句话一样:“我们别无选择,只能顺从的接受这些意外,接受生活压在我们肩上的所有重担。”
与玛利亚分离是因为生活里的一个意外,与玛利亚相遇更是因为一场意外。他们的缘分源于他在柏林逛了画展的意外,终于他生活上父亲去世的“意外”。就是这样的意外,造就了莱夫的遗憾,错失爱人的遗憾。
读到最后,我倒不觉得这是一本纯粹的关于爱情的书,倒认为《穿皮大衣的玛利亚》更是一部作者萨巴哈丁·阿里的生平缩写。
我了解下这位作者的生平,发现他是出生于奥斯曼帝国的一个军人家庭,他早年的教育在贫瘠的故土上被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炮火打断,而故事背景也是被安排在一战之后,莱夫也是在一战后的伊斯坦布尔沉溺于空想与艺术。
21岁时作者去德国留学,而莱夫也是这时,孤身一人来到阴郁的柏林。正是在柏林,莱夫遇到了玛利亚,而作者萨巴哈丁·阿里,遇到了德国浪漫主义文学。于是爱人来了,幕布拉起,作者隐身,灯火转亮,故事开始。
莱夫也从旁观者的身份,转向了参与者。书里的莱夫说:“我活得像棵植物,没有知觉,没有抱怨,也没有意志。我已经失去了感受的能力,既不悲伤,也不快乐。”
这句话,就好像是作者本人在讲述他的经历一样,他曾经揭露了本国为德国法西斯效劳的文人的丑恶面目,因此书被焚毁,战后还被列为禁书,获释后被迫脱离写作,靠当搬运工糊口。
他真的就像一株漂浮于战争中的野草,没有知觉,没有抱怨,也没有意志。所以他写出了这一个纠缠不清、短暂而又永恒的爱情故事来,用故事来讲述自己不被理解的悲剧。
可《穿皮大衣的玛利亚》中到底有多少是萨巴哈丁·阿里的自传色彩很难说。但这不妨碍这个故事备受喜欢,不管是内向软弱的莱夫,还是谁也不信的玛利亚,都是吸引我的角色,用译者秦沛的一句话形容就是“一根破损的羽毛,一颗残缺的玻璃珠”或者是萨巴哈丁·阿里说的“一朵被雨水浸湿的白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