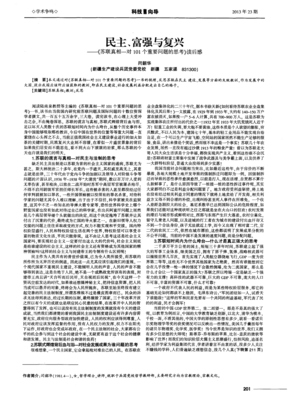
《为什么民主需要不可爱的新闻界》是一本由迈克尔·舒德森著作,华夏出版社出版的平装图书,本书定价:39.00元,页数:281,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舒德森的书一贯接地气的好读
●舒德森的每一篇论文都富有洞见,但总是显得有些散乱,可能是文字编排和翻译的原因。此外,秋风的序平易有余,欠缺足够深度的思考,容易令人在舒德森的著述中浅尝辄止。
●不算舒德森最好。但《1890年-1930年——作为大众艺术的美国报业的浮现》和《为何对话并非民主之魂》两章实在很棒。
●阐述为主,论述不多,导论比内容有point。“新闻服务于民主的七项主要功能:告知公众、调查报道、分析评论、社会同情、公共论坛、社会动员、宣传代议制民主”、“大众媒体在当下发生的这种巨大变化并不预示着新闻业的终结……这种散点分布和多种声音,并表现出难以驾驭和不好驯服等特征的信息体制,可能正是民主得以有效运转的最为宝贵的财富。”“对根本不存在民主的地方,新闻业不会产生民主,但如果新闻业认识到它向自治政府提供的各项服务、鼓励和宣扬支持这些服务的美德,为新闻记者和公众澄清和阐明新闻对于民主这一目标所贡献的诸多礼品,那么新闻业就能够做出更多有利于民主的事情来。”
●讲真,是我不懂还是作者叙述我不习惯,感觉有些地方就拎不清,美国具体的经验,很多感觉是伴随着整个民主进程下的一些问题,其实不一定非要扯上新闻界,以及十分赞同媒体的第七项功能,可惜没有展开太多。论述对话与民主的一段也十分精彩,不过我还是觉得和媒体没啥关系
●没有宪政制度和政治制度的支持,孤军奋战的新闻界不会促进民主,推动政治民主化的努力也往往会付诸东流
●保持中立是多难的事
●书名跟内容不是很合。理论上跟国内学院论文比没什么太大新意,完全换成美国经验来填充论据倒是很好看。
《为什么民主需要不可爱的新闻界》读后感(一):为什么这本专著遭遇不专业的编译者
第27页,“参议员弗兰克·沃尔什”被印刷成“弗兰14克·沃尔什”(同样的错误还出现过一次,读时恕未作出标记,以至现在找不到。)
第101页,顶格正文中为詹姆斯·赖斯顿,同页第71号标注上则译为詹姆斯·莱斯通。
第233页,“最为人们所周边的熟悉的此类案例。。。。”看不懂,语序、表述都有问题。
上述虽是瑕疵,但仍让本书蝇粪点玉。
《为什么民主需要不可爱的新闻界》读后感(二):浅谈新闻界和民主
我一直在思考,到底如何定义“新闻界”,又是如何定义“民主”。专业主义是什么,自由又是什么?这些新闻的学生天天挂在嘴边的词, 当你真正在新闻行业从事工作的时候,还会把这个当做自己的准则吗?新闻媒体和记者,是两个不同的主体。
新闻本身就是社会制度的组成部分,我不是很赞同建构论这种观点,更大的程度上我偏向于反映论,当然其中也有程度的问题。民主的理论来源应该是自由,可以追溯到古希腊、古罗马的自由民主,新闻界是随着社会的发展逐渐出现的一个事物,我觉得不是民主需要新闻界,而应该是新闻界本身就是依附于政治、经济发展起来的,就像寄生生物,并没有自己的根基,他们具有依附性。
关于民主、新闻专业主义的讨论有很多,我觉得这些讨论其实都是无关痛痒的,因为新闻这个东西本身具有它不可取代的存在的价值,即使我们把它批驳地一无是处,批判它与政治、经济勾结、批判它失去了客观性等等,在可预见的时间范围内,我觉得新闻不会消失的,它始终存在,并且会以不同的形式存在。
同样,我也不赞同一些将西方理论来分析国内新闻界和政治的观点,这样的分析在一开始就带有一种偏见,认为西方的理论是合理的,分析就是批判。但是,中国没有西方那种理论传统,中国几千年的传统是儒家思想,二者似乎不具有可比性。
一些不成熟的看法而已。
《为什么民主需要不可爱的新闻界》读后感(三):“不可爱”的新闻界=“恰当的专业”?
在导言「事实与民主」中,迈克尔·舒德森首先确立了代议制民主的优越性:接受批评;允许异议;重视各种相对独立的社会力量。如果结合全书的论述,我会概括为这样一句话:民主社会需要(1)出色的制度安排;(2)专业的新闻机构;(3)关键的专家团队以及(4)必要的公众参与。 当然,作者最想要说明的,是美国的新闻业究竟如何“不可爱”以促进民主社会的进步。而这种不可爱,在我看来其实可以概括为“恰当的专业”。
其“恰当”体现在,作者无意批判美国新闻业与各种社会力量的复杂勾连,仅着重描述新闻业如何与美国社会实现“无缝”接合;
其“专业”体现在,冷静的判断(对冲突与矛盾的偏爱;对政治事务的审慎评判;对报道社区的中立情感)与灵活的叙述(依据情境转变新闻报道策略)。 至于“出色的制度安排”,如开头所述,作者赋予了美国民主/传媒体制合法性(尽管个人认为理由不够充分);至于“关键的专家团队”,作者与李普曼的想法类似,都肯定了所谓“政治观象台”的重要作用(在第十章「专家的问题——为何民主社会需要他们」中,作者给予了完整的论述);至于“必要的公众参与”,作者着墨不多,但依然能够看出其对公众的肯定态度。 个人认为,第九章「为何对话并非民主之魂」和第十章是全书最精彩的部分。关于两章的收获如下。 民主与对话的关系绝不是“越对话,越民主”。可以说,在某些情况下,民主不仅要求放弃关于某一普遍公共主题的讨论,比如宗教;而且也可能要求放弃文明本身,比如罢工。(九章) “李普曼与杜威的交流拉开了20世纪60年代及之后全面而深入攻击专业知识的序幕”,随后作者提及知识社会学的核心观点、托马斯·库恩《科学革命的结构》以及福柯著名的“知识/权力”论,建立了合理可信的联系。(十章) 最后记录一句全书最喜欢的一句话:“权力与知识互相纠缠,这并非真正的知识的堕落,而恰恰是知识的特点,并且永远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特点。”
《为什么民主需要不可爱的新闻界》读后感(四):民主不需要新闻界,新闻界才需要民主
这本书是作为导师读书会的书目来读的。最后其实得出的结论正如我标题所说,新闻界对民主贡献其实甚微,作者站在新闻人立场上,把这个作用夸大了。而民主对新闻界的作用却太大了,不用说谁都知道,民主政策决定新闻尺度。下面列下读书会上的发言,留备将来之用。
首先,作者并不认同美国报业从党派性向客观性转型是因为经济原因,他不认为为了让大众都买我的报纸而中立起来的。这是我头次看到的一个观点,因为我们教材上其实普遍都是这么认为的。作者觉得“激烈的党派纷争与政治运动,再加上报纸对这些运动的高调参与,都是扩大而非减少发行量的因素。”
他提出了另一种原因,因为当时美国的公关和宣传是比较盛行的,很多信息就被那些宣传者操控,新闻记者意识到了这个问题,就开始整肃自身以维护集体荣誉,然后就出台了执业行为规范,从而确立了客观性。这个转变是从内部开始的,不是市场受众这种外部力量左右的。同时美国政治环境的变化也有一定原因。我觉得这对美国的客观性报业的起源研究是挺新的一个说法。
还有一个说法我觉得也挺有意思的,他说“新闻像面包、香肠一样,是人类制作加工出来的东西。专家学者强调制作过程,而记者强调原材料。”我觉得作者一定程度上站在了记者的角度,他觉得新闻事件是原封不动摆在那的,记者没办法去捏造、扭曲、改变它。所以他并不同意新闻是一种社会建构。他说“如果一定要说,只能说记者对事件进行了社会重构,但这一点都很难做到。”也就是说原材料比怎么加工制作更重要。
我想了很久这个问题,一开始他提出来我本能地觉得有道理。后来想想似乎又很难彻底说服我,如果如作者所说,那所谓的拟态环境便跟现实环境是相差不大的了。虽然记者多数情况不可能扭曲、捏造事实,但他可以选择报道或不报道,选择报道这个事实而忽略另一个事实。放大一个事实而缩小另一个事实。这都是对事实的一种加工制造,一种以所谓新闻价值观为标准的解读和建构。
作者也说,“几乎所有的媒介批评都源于对这种建构落差的不满,学者对现实的解读与媒体对现实的简化之间存在差异而已。”但是如果没有媒体的报道,现实世界更不得而知,所以作者认为,媒体绝对有存在的理由,它被骂只是因为做得还不足够完美,但这不完美也非常能理解。另外作者也驳斥了一些人认为新闻被政治官方操控的说法,因为他觉得“一些突发的新奇事件,会决定性地击败官方对媒体操纵的企图。”其实这个在国内的媒介环境上说了也白说。
《为什么民主需要不可爱的新闻界》读后感(五):新闻界——为了解决问题的对话
新闻界是为了解决问题的对话而存在的,它是对话的规范化、规模化,是对话的系统化、体制化,同时又是对话本身。这里的问题与对话都指人类社会治理方案范畴的,具体到本书,即代议制民主语境下的。
在这里,我有必要澄清两个概念:对话的主体,以及对话的形式。
我在此处所论及的对话主体是统治者与被统治者(治理者与被治理者),或者说精英群体与平民群体,但并不绝对指双方之间,也包括同一群体内部。正如书中所说:为公民提供作出理性政策决策的必要信息;对权力的运作进行调查,通过分析评论帮助公民理解社会、政治、世界,这是自下而上的对话。通过报道他人的生存状况帮助公民相互理解,唤起社会同情、塑造和维系共同体的感觉,这是(公民)群体内部对话。动员公民支持某个政策观念和立法草案、政策方案;以及传播关于人的尊严和权力的价值观,这是自上而下的对话。即新闻可服务于民主的主要功能。
对话的形式是“受规则支配的,本质上是公民参与的”。对话应该是专业的,严肃的,其必须是有规则的。因为民主的治理本身就是一项严肃认真的事业,是需要参与者付出物质与精神双重代价的事业,而不是一种轻飘的智力游戏。不是纸上谈兵,空谈误国,而是对事实与理论的探讨,是给各方为维护自身权利作出努力,是交换意见。对话的基础不是虚构,不是想象,而是事实,是理性的思考和冷静的判断,以达成共识。说到底,对话只是一种途径,其最终要通向的是解决问题。
我们为什么需要这些对话呢?
人的一切问题都可归结为存在问题,或者转化一下概念,人类社会的一切问题都可归结为生存问题:最基本的“怎么生存下来”到高级一点的“以什么样的方式生存”。为了解决这些问题,人与其所生存的环境是要进行对话的,要尽可能多的获得环境相关的信息,以达成最大限度的地降低环境未来变化的不确定性、不可控性所带来的生存风险。而民主所需要的对话,就是能够使应该参与到社会治理与管理中的公民群体,更准确地来解读认知这个世界、社会以及用作引导治理的政治环境,从而做出相对理性、正确的判断(与直接民主中的直接由公民做出决策是有区别的)。
由于哈贝马斯的“公共领域”概念的提出,人们认识到“对话”这种形式对文化发展和政治演进的巨大推动力,但很大一部分民众误解或者是一厢情愿地曲解了“对话”的内涵——天真的以为咖啡馆这类情调的场所就可以成为公民生活舞台,小资文人们就可以堂而皇之理所当然的想象自己是政治领域的中心人物。——但是,这类“对话”并不是我所论及的“对话”,就像舒德森一针见血直截了当的观点“(因自由和机智而常常备受推崇的那类)对话并非民主之魂,……民主对话从本质上说并不是自发的,其本质上是受规则支配的,本质上是公民参与的”。
对话其本质上是要解决问题的。而新闻业正是这样一个社会建构的角色,它给予“对话”一个展开的平台和一套不断完备进化着的规范。
“新闻业的角色作用应当是民主的,而非民粹的。”民粹与民主的最大不同之处在哪里呢?后者相信专业主义。并且新闻界很好地将看法和态度凝聚成强有力的观点,从而能直击问题。我们应当知道专业的知识和集中的权力是民主的必要组成部分。
所以这种对话注定是不可爱的,因为它是批判的,所以可能难免苛刻;因为它是专业的,所以难免大多时候有着严肃而不讨喜的面孔;因为它是为了改变的,所以难免触及利益与灵魂,带来阵痛。但这种苛刻正是鞭策改变的外在动力,但这种严肃正是对待问题所应有的态度,但这种阵痛正是民主制度成长与深化所必经的道路。
………………
To be continu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