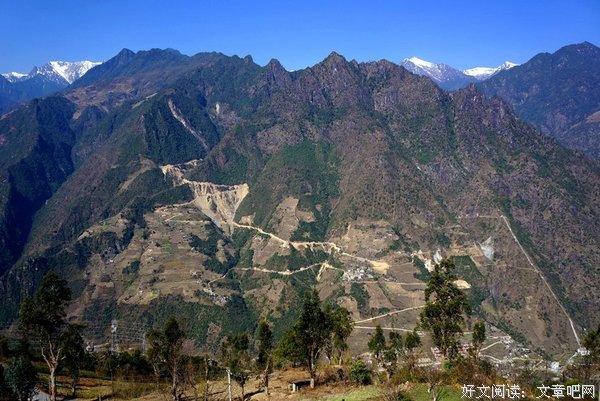
《光年3:出生之城与记忆之城》是一本由戴潍娜著作,广东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平装图书,本书定价:68.00元,页数:310,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光年3:出生之城与记忆之城》读后感(一):【雨枫试读】美丽得犹如思想的影子——读《光年3:出生之城与记忆之城》有感
诗,在我印象中更多的唐诗宋词,对于现代诗,除了课本里学的,真了解的不是很多,至今记得的只有徐志摩的《再别康桥》,诗中“轻轻的我走了,正如我轻轻的来;我轻轻的招手,作别西天的云彩”,感到万般的飘逸和淡薄,对诗充满了敬仰之情。读过很多经典著作,但是对于诗歌类大神的著作,比如泰戈尔的著作,我基本不碰,因为,除了读不懂其诗所孕育的意境之外,更多的是读不懂诗里人的七情六欲。
每一首名诗都来源于一段刻骨铭心的爱情。比如罗马尼亚新生代诗人斯特内斯库,谈了一场接着一场的恋爱,19岁就经历了第一次婚姻。在其写诗的同时,也是其恋爱、结婚,离婚、再恋爱,再结婚,不断从一个家搬到了另一个家,从而奠定其抒情诗的志向,更让他写出了忧伤但优美的情诗。比如《忧伤的恋歌》中写道:“唯有草木懂得土地的滋味,唯有血液离开心脏后会真的满怀思恋。”写出了真正的爱情是相互珍惜、休戚与共。忧伤会传染、会导致现在的生活仿佛进入地狱的深底,一切都会变得不再重要,正如诗中所写“马死亡的日子正在来临,车变旧的日子正在来临。”再比如《追忆》:“她美丽地犹如思想的影子。茫茫水域中,她是唯一的陆地。”
每一首诗的背后都有一段不可诉说的时代背景。狄更斯在《双城记》曾经说过“这是一个最好的时代,这是一个最坏的时代;这是一个智慧的年代,这是一个愚蠢的年代;这是一个光明的季节,这是一个黑暗的季节;这是希望之春,这是失望之冬;人们面前应有尽有,人们面前一无所有;人们正踏上天堂之路,人们正走向地狱之门”。在社会的大环境下,每个人都有着不同的经历和思路,比如生于南斯拉夫的马其顿的诗人尼古拉·马兹洛夫在《显露》一诗中写道:“历史是我必须跨越的第一道边界”。俄罗斯诗人舒瓦洛夫在《这个城市像个吸毒者……》里写到“这个城市像个吸毒者,我已经无处可去。我把一个小飞机从桥上丢下,任他漂流到哪里。我们的生活远离噩梦,河面上烟霾弥漫。”吸毒者的典型体征是精神萎靡,这个城市也萎靡不振,反映了经济低谷时期整个社会低潮和人的生活质量全面下降,人们到处充满不安和懈怠,到处都是堕落的放纵。
《光年3:出生之城与记忆之城》读后感(二):他“美丽得犹如思想的影子”
【雨枫试读】诗歌是什么?诗歌是其他一切学术文化活动的起因;诗歌是一种能言的图画;诗歌的目的在于教育和怡情悦性;诗人是艺术的创造者。
文人为诗歌辩护的传统古已有之,当柏拉图说要把诗人驱逐出自己的理想国时,亚里士多德写出了著名的《诗学》,替诗歌正名。当中世纪教会试图以基督教神学统一众人思想时,锡德尼愤然写出《诗辩》替诗歌在人们的思想领域中保留了一席之地。当启蒙时代人们疯狂推崇理性时,雪莱写出了《诗辩》替人们的感性开了一扇天窗。《光年3:出生之城与记忆之城》是一本当今社会罕有的诗歌杂志,在这个时代还能看到内容如此先锋、文章形式如此多样的诗歌杂志,对文艺爱好者来说是一件幸事。这证明诗歌作为当下一种先锋的文体,依旧在创造着一种感性和理性交融的艺术形式。
说到东欧,我首先想到的是一望无际的东欧平原、碧蓝如洗的波罗的海、一个个精巧的小国家、米兰昆德拉的《不可承受的生命之轻》、以及杨史云梅耶氛围诡异的定格动画。对于东欧的诗坛,我的认知是空白的。当我读完了这本《光年3 》之后,对东欧当今诗坛有了一些粗浅的认知。
罗马尼亚的尼基塔·斯特内斯库是个多情的人儿,写出了“她美丽得犹如思想的影子/她的后背散发出的气息/像婴儿的皮肤/像新砸开的石头/像来自死亡语言中的叫喊”这样迷人的诗句。尼古拉·马兹洛夫出生于南斯拉夫的马其顿,他给自己建立了一座记忆之城,让人想起卡尔维诺《看不见的城市》这本著作。他的诗句梦幻又轻盈,刺痛又充满哲理,比如“在废纸篓,我看见你刷下来的/几缕头发,在鸟与世界醒来的时候。/镜中,我看见一个注视/那注视里有着一些家园和天空”。雅罗斯拉夫·塞弗尔特是捷克诗人,在塞弗尔特的诗歌中,诗人写出了普通人的苦难、痛苦、死亡和忧郁,很具有社会性和革命性。比如“邪恶依旧/从人类的骨髓中升起/溅满血污,像牙科诊所的楼梯。”
这些东欧诗人作品的译介,对中国现代诗自身的发展起到了正面的影响。因为诗歌属于对语言很敏感的实验性文体,在翻译诗歌的时候,我们其实也在更新和拓展汉语的边界,不仅仅是词汇,还有文法。就和《光年3》诗人志中对保罗·策兰的儿子艾略克·策兰和策兰研究专家贝特朗·巴迪欧的访谈中说到的那样:艺术家要是想对艺术进行源源不断的更新和再创造,就得抱有一个开放的心态,广泛吸收来自世界各地的不同风格的艺术作品。希望我们的诗人和艺术家能从新译介的东欧诗人的作品中汲取养分,吸收他们创作的精髓,同时勇敢地应用到自己最新的作品中去。
《光年3:出生之城与记忆之城》读后感(三):【雨枫试读】诗的旅途,我们还有许多光年
诗的旅途,我们还有许多光年
人生如逆旅,如果沿着诗歌的进程去回溯生命的旅程,我想,我们发现得最多的应该是“匆匆”,诗歌很难给他做具体的定义,但是我们知道,那就是美好。我们把眼光放到辽阔的文明领域去,在世界的每座时光之城里,总有一些记录下自己的时光的诗歌在那里可以让人们兜兜转转,路过宽窄巷陌的人类,在这里留存的文明不管熟悉抑或陌生,沿途无论是新亭美景,还是旧时繁花,时光都由文字或者语言记录。而留存的最好好的那些就是诗歌了。
诗歌翻译丛书《光年3:出生之城与记忆之城》是偶然是书店邂逅的,因为那时有个小小的标语,叫“世界中的世界”,在这个茫茫人世间有诗歌来留存一个王的世界,这是一种让我们为之感动的力量,后来再去追寻《光年》这个杂志的刊载,知道了“诗歌共和国”,在一个多世纪前的我们,曾经有先辈在追寻“命运”,这个命运在风雨飘摇的时代曾经超越了时代。他们寻求的是“政治共同体”和文字的“命运共同体”,对于旧文学的推翻,胡适、陈独秀、鲁迅等人都做过不同程度的努力,而在当时,最佳的方式是“取代”,诗歌的翻译在几乎每一个文明的领域都是承载着文明。文字与文字的交流以为着一种语言可以用另一个语言来展现,而在展现的过程中,语言和观念都会呈现出不同的创新和不同的意义,人类的知识从生活中存在,但是人类的个性便在存在中拓展了边界。诗歌,在这里是思想的延续。也许一路旅途都只是久寻归人未得,但是某个冥冥中已有盟约的承诺却会借助文字来与之相遇,徐徐而来的无意偶遇,和匆匆离散的偶然重逢,天涯咫尺的守望,或者千里之外的对视,得到的未必就是真心和挚爱。诗歌就是如此,我们投入的哪一些注定很多时候都是难以离散,但是又羁绊情在。
比如东欧的诗歌,斯美塔那曾为交响曲《伏尔塔瓦河》写下文字首先激荡在心中“伏尔塔瓦河从斯维特扬峡谷的激流中冲出,在岸边轰响并掀起浪花飞沫。在美丽的布拉格的近旁,它的河床更加宽阔,带着涛涛的波浪从古老的维谢格拉德的旁边流过……”;《光年3:出生之城与记忆之城》介绍的则是出生于罗马尼亚石油名城普洛耶什蒂的尼基塔·斯特内斯库也是如此,在这里他热爱的是音乐,同样的,文字承载音乐和思想的承载,他的努力没有白费,在诗歌的革新运动中,年轻的尼基塔·斯特内斯库试图突破教条主义的束缚,让自我的灵魂在这里可以自由飞翔,在思想感情的躯壳之外,让他们有一件可以触碰的外衣,就是他的诗歌最大的特色,再如南斯拉夫的尼古拉·马兹洛夫,诗歌都是穿越灵魂所存在的文字,他们这一代人的突破与创新,在诗歌的领域里,单调的科学概念、严密的逻辑哲学思维、朴实的辩证观点甚至是枯燥乏味的数字都可以是想象的对象,在他们的诗歌里,这些都是不是虚无的概念,而是真实的生活存在,可以由想象给予他们展翅的羽翼,然后在思想的天空中自由翱翔。“太阳是一块坠落的石头/人类正在缓缓地推动------/他们是作用于运动的运动/你看到的光明来自太阳!”这个世界,我们给与的一切都是如此。
《光年》的第三辑主题“出生之城与记忆之城”致力于去追寻诗歌的本质与意义,对中国而言,我们建立的基础是发达的农业文明,传统的土地的眷恋让我们对待天空有着极度的渴望,所以尼古拉·马兹洛夫说:“城市是我们新的本质,是一片不结果实的新森林,一个神话般的童年多边形,一个充满希望和抱负的陵墓。”于是我们可以开始去漫溯一个不同的文明的时代,乡村与城市,给予一个传统的中国人而言,其实都是在语言和文字结构的重负下的挣脱。也正是这种挣脱让我们知道了世界的广大和海洋的深邃,穿越过城市和乡村,我们在古老的文明之间看到了不同的交汇,当代人便是在此中遗址、辉煌、覆灭与真切的重生中不断穿行的。也许,诗歌无法改变我们的生活,但是他可以重塑灵魂,当灵魂以诗歌为立足点去构建文明的城堡的时候,我们都是建筑者。
《光年3:出生之城与记忆之城》读后感(四):《光年》:语言转化中母语的美感(叶美)
那天,在好久没动静的微信《光年》编辑群,潍娜说《光年3》杂志已经刊印出来了,我们立刻表示了祝贺,沉寂的编辑群一时热闹起来了,潍娜要了每个人的地址,说要寄书给大家,而且也向每一位译者要联系方式,出版社要打译稿费了。算一算,离上一本出刊时间已经有两年了,因2019年出版的大环境加上今年的疫情,第三期《光年》能够跟读者们见面,不难想象,背后是多少具体与点滴的排除工作。我在拿到《光年3》之前,已经在家坪和诗人王家新的微信中,看到了封面、目录和截屏的译文片段。有人会问,当下办诗歌翻译杂志的意义在哪里,如果想要找什么文章或是哪位译者的译文,足够耐心的话,各网站或微信平台的推送中,十有八九是能够找到的,幸运时还可直接下载pdf,或购买电子书。是的,这些都是选择,可是和正式出版的书相比,电子书总叫人感觉好像不是书。
《光年3》实拍图一《光年》的选稿是在市面上未出版过的首译,栏目的每一位译者大多是诗人,比如王家新,臧棣,朱朱等。这期里的《越界》是东欧诗人尼古拉·马兹洛夫的作品,国内知道的人应该不多。汉语诗坛对东欧诗人历来有很重的情结,但耳熟能详的也就三个波兰诗人,一个是备受写叙事诗的人推崇的米沃什,最早的译本是绿原的译本,其后河北教育出了张曙光的译本,《光年》这一期正好收录了连晗生新译的米的长诗《劳达》。从九十年代起,米的诗歌能在汉语诗坛有持续的阅读,一部分原因可能是,从波兰文译成英文,再从英文转译成汉语时,散文化的语言正好被推崇叙事诗的人拿来作了反对朦胧诗和第三代的依据。
另一个是女诗人希姆博尔斯卡,一个跨性别的获得了同等尊敬的女诗人,诗风严谨而优雅,国内年轻诗人中一直有被起影响的痕迹。中央编译出过她的文选《诗人与世界》,2000年之后陆续见到了陈黎和胡桑、林洪亮的译本。
还有一个是1945年出生的加扎耶夫斯基,算是米沃什和希姆博尔斯卡的晚辈了。他的诗歌一译介过来,就收获了很多读者,尤其这首《我赞美残缺的世界》,应该算好诗但不是一流诗。他的很多诗歌相当口语,师承也挺明显,主要是英美诗人希尼、沃尔科特等。加扎可算是东欧20世纪第二代诗人的代表,不过总给人老气之感。
《光年》这期译介的尼古拉·马兹洛夫,很值得一看,可以说他代表东欧诗歌的一种新写法,没有米沃什因道德感导致的沉重诗风和希因苛求客观而失于精巧的缺陷,也没有加扎只书写日常感受所带来的俗气诗意:
我成长而我和自己一起缩小,无畏地跑向起源的深处每样环绕我的都在运动石头成为一座房子岩石——砂的谷物当我停止呼吸我的心依然在大声跳动(王家新译)此外,《光年3》的《当代国际诗坛》栏目有一位女诗人安·科顿,简介里没有出生时间,译者是臧棣。《光年》一直本着诗人译诗的传统,把写作的经验运用到翻译,会尤其注意语言转化中母语的美感。在这里,你能从科顿的汉语翻译诗中,读到字词和诗行间恰当的留白和跳跃:
而人们来了,看着,戒指在手指间他们怎么说!‘那时,谎言在哪?’再重复,‘谎言在哪?’音乐正冥冥虚拟,比时代的表达更可人。 更殷勤更假,文化人儿那说辞他们优雅地把玩一切,给缝隙加个漂亮的盖子,围道栏杆站上去,即使它斜着然后小声开口,谁都看见那真容易啊。但一个人不是所有人,不!这是一首非常有力的口语诗,比照一下国内,当代诗坛的感受力似乎存在断层。可以和安·科顿拿出来一起欣赏的,是最近很火的陈喜年的诗歌《帝国大厦》,让我们来看下:
我向来不喜欢高大的事物我童年的天空 充斥着高举的拳头一些荒唐的声音直抵云宵高耸的塑像布满山河...现在 我站在它最高的观景台上朔风从四面吹来让我更加惶惑:帝国,你到底意欲何往?...这些我们共同的小学将教授风雨所有的课程《光年3》的《随笔》栏目有远洋的译文《有蛛网琴弦的苹果树——塞弗尔特和他的诗歌》。文章对塞弗尔特一生的生活和文学活动做了简要梳理,看完令人对捷克人心生羡慕。塞弗尔特在1984年获诺贝尔文学奖的时候,汉语新诗才刚刚重新朦胧着起步,而当时塞弗尔特就是人家民族诗人的代表了。正如作者所说,对于有“自由组合的意象和强烈的情感”的捷克诗歌,要把这些特质带入其他语言,是有难度的,这多少也造成了塞弗尔特诗歌获得国际认可的推迟。拿汉语新诗来说,能让各国翻译家头疼的,应该是张枣。先不说张枣的主题构思多数来自文言文学,就说他在语法上的突破。曾经听有人说,某位前辈的诗译成英语,很多人尤其刚刚去世的沃尔科特夸这人的作品有气势。我不否认年龄带来的惺惺相惜感,但这位的诗歌之所以获得这样的赞誉,更因他的诗的英译版正好契合了英美语言的喜好,若是拿德法的译本再让外国人瞧一瞧,应该不会有这么高的评价。翻译中往往出现吊诡的现象,比如是白居易而非杜甫、李白影响了日本文学——二流诗歌往往就这样流传出去,而一流诗歌需要同时代人的慧眼识珠。塞弗尔特的幸运是自己活得长,创造力也没有衰退,而且翻译、散文、评论,样样都做。
更多精彩内容,请见《光年》!
《光年3》实拍图二说明:本文为叶美先生为《光年3》所写评论稿,万分感谢叶美老师供稿;本文所用图片由“吉它木影”拍摄,非常感谢摄影师为《光年3》拍照。
《光年3:出生之城与记忆之城》读后感(五):希望这本先锋MOOK里,包含新一代人对世界文化的想象和把握——就《光年3》与戴维娜对谈(不觉)
诗歌被视为“出版毒药” 已经很长时间了。但仍不断有人中毒,中毒也就是上瘾。今年上半年,诗歌翻译刊物《光年》面世,又让人发现了一批中毒者。记者采访了《光年》的主编戴潍娜,听她讲述了创办《光年》的经历、抱负和寄托。
从“译者”到“译作者”
记者:怎么想到去做这么一本刊物,能讲一下它的缘起吗?
戴潍娜:其实最初是“大道行思”的刘明清先生提议的。我们之前有过一次合作,他还在中央编译当总编时,我那本《天鹅绒监狱》顶风作案和他合作出版。
后来他成立了大道行思出版集团,专注做一些曲高和寡的情怀书,想做一本诗歌类杂志书,就找到我,我们一拍即合共赴火场。在这个年龄上,做事情也好,交朋友也好,基本上建立在价值认同和审美共识的基础上的友谊才更牢靠,做事才更靠谱。
我们很快开始筹划创刊号《诗歌共和国》。我跟刘老师开玩笑说,诗歌是剂毒药,一朝中毒,终生服药。他也是很年轻的时候就喜欢诗,做了多年出版之后,还忍不住回头去赶赴当年的梦。我觉得诗歌某种意义上是一个大的公益。就我个人而言,诗歌给我的回报太多了,像我这样的既没有功德又没有苦劳的人,无所事事地活着,还能够拥有一支笔写几句诗,我觉得自己应当做一点诗歌公益的事情,邀请了家坪、东东几位诗人,一起来做《光年》。
记者:那怎么想到去做了一个翻译类的刊物,而没有去直接做原创?
戴潍娜:专门介绍翻译诗歌的刊物在国内非常匮乏。虽说诗歌是目前最国际化的文体,信息如此爆炸,目前市场上专注诗歌翻译的同类产品只有单品的《当代国际诗坛》。
翻译学作为一门学科,其实从来也没有真正完整地建立起来。而诗歌的翻译,又是翻译学当中尤其不被信任的部分,但我恰恰认为,诗歌翻译最能够体现“翻译作为一门学科”在未来可能的延展。
翻译不仅仅是二度创造,它跟原作之间有追随,有调情,有决斗,是伟大的对手戏。所以我们这本书里第一次把“译者”作为“译作者”来介绍,就是加了一个“作”,不只是“译”者。此外,翻译也是一种批评。没有比翻译更烂熟的学习,也没有比翻译更不加掩饰的批评。我们目前对于翻译的观念,依然停留在所谓的忠而不美,美而不忠的讨论上。而翻译这门学科,甚至可以跟当代艺术、行为艺术完全打通,它有很多可能的玩法。在国外有很多对于翻译的艺术性的玩法,我有一次听西川聊起过一个他认识的诗人,这人翻译一首诗,完全按照音译,把意思统统抛弃,就是按那个原文的发音把它译出来。从严谨的翻译立场来说,这肯定是对原著摧毁性的背叛,但它翻译出的是原著另外一部分——音色,就是诗歌本身的声音。诗歌有时候抛弃内容跟形式,单单是迷人的音色就足以让一个瞬间臻至完满。这个翻译者就单单去译那个声音了,也可以说,他特地去译了在以往翻译中失去的那部分音色,算是一种对翻译的补偿。
翻译在未来有很多可能的延展空间,我们也希望这本杂志能够打开翻译学在未来的可能性,它不仅仅是匠人的手艺,而是原创性极高的艺术活动,同时也可能是非常严谨的学术批评,也可能是玩疯了的当代艺术。
记者:你想过怎么样去实现你刚才所说的这些想法吗?你所说的这些实验性怎么落实?我们现在所能够看到的国内对西方诗歌的译介,有这种实验倾向的,其实不多。
戴潍娜:极少。大家在翻译的观念上比较封闭。
我们落实在具体的专题策划上,第一期创刊号集结了各个不同民族的作品,我们特别关注那些所谓的边缘世界的声音。《光年》不是一本欧美中心主义的杂志,它是一本世界主义的杂志。现在已经有一些专题正在策划,比方说接下来我们正在做的一期专题为“回译”,中国的《离骚》《诗经》这些经典被翻译出去以后,再从译文把它重新翻译回来,将得到一个全新的文本。这里面体现出的接受美学,一个文本在不同时代不同语言里的更新、变形,以及文化中潜藏的诉求和目的性,会是非常微妙而有揭示性的东西。
记者:也就是说你还是很重视它的实验性、“有意思”?
戴潍娜:《光年》的定位是一本很先锋的翻译刊物,能够体现新的一代跟这个世界的连接,刷新我们跟世界的关系,跟语言的关系。
光年3 -宣传片_腾讯视频“诗歌共和国”
记者:中国现当代诗歌基本上是在西方的范式和体系下面延伸出来的,也非常依赖对西方作品的译介,这个过程也有一百年了。那么,我们这一代人对这种东西的需求跟前面几代人是不是已经有所改变了?
戴潍娜:我以前也聊过这个话题,中国新诗的母亲是确定的,就是中国古体诗,它有一些可能的父亲,其中一个父亲就是西方翻译诗歌。这是新诗无法回避的血统,中国新诗是在古诗跟翻译诗歌双重滋养之下成长起来的。你提的需求改变,是个好问题。微妙而深刻的变化一直都在发生,迅速的发生。翻译这个学科最能知觉国际关系、地缘政治的变动。
记者:整个文化格局上的变化其实是非常影响这种接受的。
戴潍娜:文化格局、政治诉求、主体话语权的变化,深刻影响着这门学科的走向。所谓的“世界诗歌”到底存不存在,这是个被争论的话题。宇文所安说过,“一首诗里的地方色彩成为文字的国旗”。新的一代人去插国旗的方式,一定是跟过去不一样的。
记者:我觉得世界整个话语模式会从世界主义转回地方主义,甚至原教旨主义,这似乎是越来越明显的状态。在这个时候我们面对诗歌,是应该用一种什么样的眼光,比如说我依旧用世界主义的眼光,还是说我对你的问题不理解的就是不理解,让它纯粹封闭在那个地方的纯黑暗当中。你认为世界主义是不是仍然是一种值得我们现在去坚持、甚至是继续完善的一个理解框架?
戴潍娜:文明当中有很多的黑洞。糟糕的是,现在全世界都有封闭化和偏执主义的危险倾向,原教旨主义甚嚣尘上。《光年》是世界主义者和艺术公民的阵地,是一本世界主义的杂志。世界主义跟地方主义并不是两个矛盾的概念,它们恰恰是相互滋养的,共同保持了这个世界的弹性。
记者:我觉得有的封闭是被动的。而有些东西是在文化选择上的封闭,是主动的。
戴潍娜:“最后都不是政治冲突,都是文明的冲突”。我们所有的选择,到头来也都是文化的选择。
记者:我现在的感觉是,西方现当代诗歌,成立、成长到成熟,直到现在,它这个过程我觉得已经差不多到头了。我甚至感觉,在“二战”以后,西方现当代诗歌的原动力差不多耗尽了。在这样一种情况下,我们去译介的时候,对于选择文本的标准,甚至对待我们所选择的文本的方式,是不是该有更多自觉?
戴潍娜:你说到原动力,诗歌就是语言最重要的原动力。如果说现代性的能量已日趋耗尽,这一代人不应该是在一个已经破烂的袍子上修修补补,他们要去创造自己新的一套话语体系。我们对待文本的方式,折射出来的是对待另一种文化的态度和思考。希望这本先锋MOOK里,包含新一代人对世界文化的想象和把握,更新鲜的声音更新鲜的意识。在一个时代精神发生深刻变化的转折时刻,在急速奔向人工智能的最后的人的时代,去充分而得体地表达新一代人的文化思考。真理时不时在迭代更新,一切都是文化选择的结果。
记者:哈贝马斯认为现代性是未完成的,但是我觉得现代性本身有一个限度,至少现在已到了需要深刻调整的时段。在这个时候,我们怎么再去面对从国外引进的东西?你刚才谈到不再去做成一个以欧美为中心的刊物,我觉得是挺有意思的一件事情。但这些非欧美地方的东西可能已经被改造得很厉害,你在选取这些东西的时候,它有多少东西还是真正属于这一地区文化基质的东西。现在我们所能够看到的这些地区的文本,一般也是去靠拢世界主义信念,或者普世主义价值体系的,是首先被欧美世界所发现和接受,然后我们通过欧美的眼睛发现了这些人的重要性,而有一些真正的带着文化原质的东西可能还沉在湖底,是不是应该打捞这些东西?
戴潍娜:大江健三郎说,“村庄”等于“国家”等于“小宇宙的森林”。这些远离帝国中心的边缘,这些永恒的局部,并不是割据,描述它们可以更好的展示出历史、变迁。文学中的打捞,有时比发掘更困难。《光年》设置了“重译”栏目,希望重新打捞一些沉没的矿山;“当代国际诗坛”栏目则是致力于挖掘一些真正带有他自己文化原质的“文化土著”的作品,而不是一味的追逐经典的大师作品。
《光年3》实拍“既微小又盛大的东西”
记者:你提出了一个观念,“诗人翻译诗人”。这句话该怎么理解?
戴潍娜:诗歌这朵花,只有在诗人手上才能叫作玫瑰。我们做的事情,是在另一种文化里伺候这些诗。诗要得到诗的优待。第一期创刊号《诗歌共和国》邀请了国内著名诗人西川、杨炼、王家新、周瓒、高兴、谷羽、汪剑钊、傅浩等担当翻译;第二期《世界中的世界》邀请了张曙光、树才、伊沙、王东东等;这一期《出生之城与记忆之城》邀请了高兴、杨炼、王家新、唐晓渡、臧棣、西渡等著名诗人翻译家。力求以最精准最敏锐的笔触,展现世界诗歌前沿的创作风貌。翻译是两个灵魂真正的相遇。当一行诗在另一种语言中醒来,迎面向它走来的第一个人,是一个诗人。
记者:这岂不是让那些不是诗人的译者很难堪吗?
戴潍娜:不懂诗歌,那可以去翻译别的啊,这不丢人,不丢自己的人,也不丢诗歌的人。另外,我认识的不少诗歌译者,他们可能没有诗人这个头衔,但是懂诗的,很多私下里写的诗还很不一般,这种也是诗人,隐身的真诗人。
记者:这样的话,这个标准又不称其为一个标准了。
戴潍娜:你对于诗歌有没有感知,有没有认识,懂不懂诗写不写诗,这是终极的标准,而不在于一个所谓的名头——如今遍地伪神和假诗人。诗人不是一个职业,诗人是注定的。
记者:我觉得这个界限是非常模糊的。
戴潍娜:不是模糊,是更精微的择选,拥抱一种复杂性。一分为二粗暴的界限,那是法西斯主义。
记者:我觉得我们现在有些说法,比如说“乌托邦”“法西斯”,用起来似乎过于方便了。
戴潍娜:是有问题的。很多词汇需要重新被清理、被清洗,比如像“优生学”这类,现在一提“优生学”就要打入无间地狱。
记者:斯巴达人就搞“优生学”。
记者:你在选择译者的时候,有没有一个自己的考量,除了诗人翻译诗人之外,你在趣味上,或者认同上,更倾向于选择什么样的译者?
戴潍娜:我虽然有一颗有偏见的脑袋,但是有一个广袤的胃。不同趣味的,不同学术见解的,只要他她是好译者,《光年》都是以非常开放的心态去接受。
记者:现在有多少人参与这个事情的,组稿编辑?
戴潍娜:目前一共有四位。此外有一批不同语种的世界各地的通讯员,一个松散的语言意识共同体。
记者:我还想知道一件事,做这个事其实是很辛苦的,大家运作这个东西有什么报酬吗?
戴潍娜:大家做这个事情的初衷都不是为了报酬,出版商做这本书,无疑承担了很大的风险。但就像做公益绝不意味着不盈利,否则公益将无法长久一样,我们也在寻求一个良性持久的运营机制。译者也都是有稿费的,后面争取再提高一些。现在译者酬劳太过于低廉,已经损伤到了这门学科本身,损伤到了读者的利益。事实上,酬劳低伤害不了好的译者,伤害的是读者,大量四六级都达不到的从业者译一本毁一本。真正好的译者大多不是为了报酬而翻译,内在的驱动力是那种无法抑制的创作的冲动。
记者:现在做一本刊物确实很难。你做这个事情感觉有障碍么?联络、统筹肯定也要花精力。
戴潍娜:诗人一般都不愿张罗事儿。当然这事肯定占用我的时间精力,但那又怎么样呢,才华不用白不用(笑)。本来活在这个世界上每天都在消耗嘛。再说世上90%的事情都是没意义没结果的,姐也习惯了,何况做的还是件有意义的事嘛,投入精力又如何?
当然,咱们也不能把一本杂志的意义吹得无限大,也许最终这本杂志提供的就是一个词,一个标点,那种既微小又盛大的东西。年轻一代写作者往往有宏大的野心,对于文化、文明的那种革新力,但到最后,你究竟能够为这个世界,或者为文学提供什么?哪怕是一个标点,一个休止符呢?那就是全部的意义了。
《光年3》实拍图注:本文系不觉根据采访《光年3》主编戴维娜老师的记录稿整理而成,文中插图由“吉它木影”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