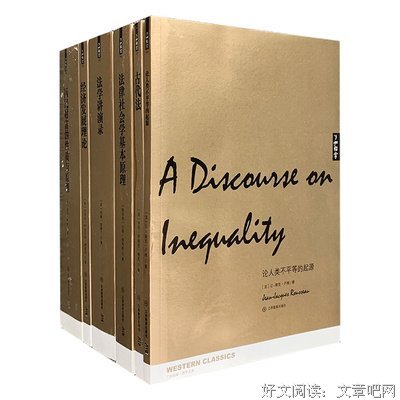
《西方正典》是一本由[美] 哈罗德·布鲁姆著作,译林出版社出版的平装图书,本书定价:58.00元,页数:516,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当工具书翻,挑了几个看过的作家作品。布鲁姆每句话都是带subtext的,以我功力实需多年咀嚼。
●布鲁姆诚不我欺,读到“哀伤的结语”果然哀伤,身处新神权时代行将(或业已)回归的文学迟暮年代,文学(艺术)或是以政治、社会、道德的进步为鹄的,服膺于意识形态,或是在代表瞬间的不朽之可能性的流行与通俗文化潮流间浮沉,最终被束之高阁(实则为弃之如敝屣),在此种文学腹背受敌的境遇下,为在审美力量照耀的熠熠星空下歆享自我内在孤独的普通读者和文学批评家前所未有地陷入了何以自处的危机。布鲁姆试图完全摒弃憎恨学派偏好语境的方法转向以偏好文本的文学审美方法切入,以作家之间影响的焦虑重新建构西方经典传承与背叛的互文体系,将陌生性、原创性视为遴选经典的准则,从西方经典中心的莎士比亚之深沉的、吞噬万物的自我(自由的自我艺术家)发散开去,在贵族、民主、混乱时代间四散流布,于自我最深处描绘一幅后基督主义的诺斯替式图景。
●著名莎吹布鲁姆先生233 这一版挺好的但是和英文原版结合起来看会更好
●指路之灯
●他是有多喜歡莎士比亞,個人化傾向太明顯了!
●看了几章来着
●读过另一个版本,老爷子走好,愿在天堂遇故交,继续唇枪舌剑。
《西方正典》读后感(一):大有“不管你信不信,反正我是信了”的神韵啊
粗略看了一下打高分的距离现在时间比较久,打一般分数的都是近几年的。这是否是不同时间段人们的文化差异呢?这部作品,粗一看大有道理,可细细再读,恍然觉得里面太多观点都带着强烈的主观意识,有时甚至觉得是作者在给各类作品、研究学派在扣帽子。莎氏作品经典都不容置疑,稍有不同声音便成了理想主。作者赞同约翰逊博士的座右铭:“除了傻瓜,无人不是为钱写作。”这种毫无调研基础,纯想象的结论,是整部作品的一个缩影(试问作者推崇的但丁、托尔斯泰,甚至卡夫卡是为钱写作吗?若托尔斯泰为钱写作,何必散财解放农奴?若卡夫卡为钱,何苦留遗嘱让友人烧了手稿?)。大有“不管你信不信,反正我是信了”的神韵。可对于个人而言,时代的声音并不代表你自己的声音,每个人都有独立的世界观和看待问题的思维方式,跟着带有强烈主观意识作品的思路走,可能会迷失的。这是我认为的作品最大的败笔。
当然,书中对于经典的评价方式和方法,对于阅读的理解和态度是发人深省的,在对一代一代写作者的定义和受到影响的描述也是精辟的(诸如:创造力强的作家不是选择前辈,而是为前辈所选……这种悲伤的论调恰如其分地表达了当代作家们的一种焦虑,有野心者每时每刻都在徒劳地想摆脱先辈们的影响。这些精辟的见解大抵是这本书得如此高分的原因之一吧),对于在文学评论方面没有经过系统学习的人,是不错的拓展读本。
《西方正典》读后感(二):面向伟大
这个时代谈论经典,似乎是一件很羞耻的事儿。“经典”一词被污名化,丧失了其美学的优越性、内涵的丰富性、人本的延展性。商品化标签,肆无忌惮地消费“经典”仅存的威信,成为“文化资本”被不断反刍后的渣滓。一个明显的事实在于,文学作品被视奸,成为本雅明笔下机械复制时代的“艺术品”。哈罗德·布鲁姆说:“当今大行其道的学术道德是鼓励人们放弃要历经艰难才能获得的快乐,而去追求那种容易获得的、到处可见的乐趣。”
AVI, RMVB, MP3, MKV鼓励人们沉湎观感,鼓励人们放弃反思,鼓励人们停止自洽。“娱乐至死”这一骇人听闻的理论,绝不是这个时代所独有;相反,更多地表达了对手段失控的担忧。我们不再做着各自的“白日梦”,想象力——作为画面的想象力,被影讯消耗殆尽。其代价是,我们对文字不再敏感,甚至木讷。如果机器、程序可以写新闻,我们究竟在看什么?如果人工智能可以登上神坛,猴子敲打键盘写出“莎翁全集”,有何不可?
文字首先是人,其次才是工具。颠倒顺序的后果是,语言作为工具的合理性日益僭越人的符码属性,使得人成为韦伯科层体系下的螺丝钉——可被取代。这或许成为焦虑的一种可能的解释。时代的风气是效率至上,却从不体味效率——意欲何为?靠近经典,我想看看文字究竟是什么,人究竟是什么。
一个朋友,曾给我发过这样一段文字:
语言的存在方式及其发展轨迹被置入了新的路径——参照生活的路径,并受制于有关意义准确性的全新概念。然而,一旦实际生活的桎梏在某种方式下松动,语言便会从禁锢状态下挣脱,任其回到本来世界并恢复其自身法则。于是,在其内部产生一种回溯,一种逆向式流动,语言退回到开始时的组合状态,并再一次达至完美真义——语言的这种朝向原始状态的回归,渴望找寻本源,回归文字故乡的冲动,我们称之为诗。诗是藏匿于字词间真义的瞬接循环,是对原生迷思急躁而凶猛的重建。
涉猎文艺理论有限,仅凭对亚里士多德《诗学》、莱辛《拉奥孔》的粗浅认识,艺术,作为文字的艺术,是诉诸想象力,是诉诸感知的。它以最靠近形而上的方式,完成对人、向人的言说。读者,能以亲历者的姿态,参与文字的再创造过程,本身就是人类文明的奇迹。经典不是时间被动筛选的结果,她被发现,并被供奉,而至瞻仰。
我要对过去的一个想法进行修正:认为文学作品,旨在拓展人的生命宽度。我不再羡慕唐璜的绰约潇洒、不再哀悼费多尔、德米特里、伊万的苦难、不再吟唱“谁此时没有房子,就不必建造”……因为他变成了我;或者,我变成了他。先成为知识分子,再成为世界公民。
“面向伟大”。
《西方正典》读后感(三):正典,正点!
「吴按」没想到自己重归文学的处女文献给了布鲁姆,可能是真爱吧。
电子化的时代带来一个令人兴奋的事实,那些曾经体量巨大的书卷再也不需要用牛车承载了,如果说学富五车是一个令人向往的境界,那么这个时代令这样的可能性成为了每个个体都可以实现的境况。诚然,这样的技术手段彻底改变了观看的习惯,甚至从电影诞生的时刻起,文字与阅读的关系就已经彻底的割裂成了一道传说。正如同本雅明描述的,故事,歌谣,那些曾经经由口传耳闻流通的想象疆界已经变成了廉价如路边摊上煎饼果子一般的存在。或许对于那些喜爱煎饼果子的人而言,这些尚且还能被称之为文学的存在依旧是值得阅读的。但失去了努力获得的快感不正像是硬盘间传阅的爱情动作片与三块钱能获得的槟榔一般,这个崩毁的时代起源于审美已经成为了能被金钱换来的享乐,那些需要努力才能体验的乐趣逐渐被唾手可得的电玩所取代,经典的悲歌在每一个时代都回响在庙堂之上。
如果对当今批评界稍有了解的人,大概很难抵制因发文和研究为名对文学的杀戮。那些被布鲁姆冠名为憎恨学派的团体们纷纷组成了各路军团抵达了阅读的中心。不幸的是,无论是精神分析、新历史主义、符号学、马克思主义、文化研究都在不断尝试这把人类想象的万神殿拉下神坛,他们正如同在阿里斯托芬笔下的云中鹁鸪国一般的鸟雀们,误把自己作为文学代理人的身份嫁接在神坛之上。(不幸的是,我自己也是其中之人,不免难以下狠手加以大加批判。)要死的是,现今文学院盛行的依旧是这些玩意,他们变成了所有文科教授们换取俸禄的必备武器,于是乎,不会批评理论的人就像是文学研究的异端,那些大谈品味的人总是最早被拉去开了一场批斗会,因为人人自媒体的时代,又有谁关心品味,当知识与金钱紧密挂钩时,又有谁会关心那个产出知识的人是不是一头猪。
我们有理由阅读布鲁姆,也有理由把他放置一边,虽然他被人置身耶鲁解构学派中坚人物,可却是最为正统的审美卫道士。正如同他论述的那些经典作家一般,他自身在把这些经典作家推向神坛之后也与他们同辉,当然,你可以辩论说,为什么要听一个老古板的胡说?为什么我们还有去阅读这样艰涩的文学?又为什么我们不去听ted或者知乎上搜索出那些已经被update 的答案?那些追新逐异大可以挥挥你的鼠标,把这篇文章关闭,因为想象的疆域并不为你而敞开。
正如同他自己在开篇的经典悲歌中所言,审美的努力是孤独和自我心灵丰富的产物,正如同那些充斥着想象力的隐喻在其自身发展的王国中自立为王。每一个作家总是被这人类心灵庞大而丰厚的王国所吸引,每一个写作者总是在和他的前辈博弈,也与他的同代人作战,为了赢得精神胜利,他需要在不断的撕扯中寻找隐喻的新生。那些僵化的语言规律便是那些憎恨学派所热爱的产物,他们总是相信隐蔽在万物之中有迹可循的心态,他们把人的精神拉入机械、生物学、脑神经科学、商品交易甚至是物理学这样遮蔽了陌生感的空间。也正是这些充满了教条、规律和秩序的世界崩解了想象力,并把那些原本只属于神之世界的空间拉入凡尘。请让我们重新请回神祗,老王已死,新王当立,在那心灵的废墟中,又能诞生出怎样的娇花?若果正如本雅明所预感的一般,这是一个充斥着复制品的时代,是一个失去了灵光的时代,是一个期待着秩序、规则和法度的时代。所有的一切都看起来是一样的,那么流水线上产生的心灵需要的只是阅读,去阅读吧,去飞翔吧,去循着那隐喻的生命,追寻那灵光飞逝的疆土。如果你也想在孤寂中召见新生,请阅读至死!
《西方正典》读后感(四):《西方正典》:谁的“西方”,何为“正典”?
在这个信息爆炸的时代,上一秒发生的事件到了下一秒恐怕会成为旧闻。不过,前段时间,有则消息还是引起了广泛关注:文学评论家哈罗德·布鲁姆去世,享年89岁。作为所谓的“耶鲁四人帮”的一员,哈罗德·布鲁姆以其独到的见解、激进的措辞、一以贯之的立场,既为许多文学研究者(比如曹文轩)推崇,又招致了来自各方的敌意(如约翰·厄普代克的回击——布鲁姆称“兔子四部曲”无聊)。我们不禁要问,布鲁姆何以会造成两极的反应?
走进布鲁姆的世界,如果要选一扇门,除了那本时常为人提及的《如何读,为什么读》之外,不妨看向《西方正典》这本书。尽管最初是应出版社之邀写作本书,但是,布鲁姆丝毫没有因为面向大众而降低自己的标准。极高的标准、讲究的修辞、繁复的长句,都标志着这场阅读之旅丝毫不会轻松,“正典”(Canon)一词更是令人生畏:需要我们拥有能够攀登高峰的勇气和见识,而非通俗文学那般取悦我们。
在《西方正典》一书中,布鲁姆仿效维科在《新科学》里的做法,把文学进行了时代划分,依次是文学的神权时代、贵族时代、民主时代,以及混乱时代,“只是将神权时代略而不论”。至于论述对象的选择,布鲁姆给出的标准是作家们的“崇高性和代表性”,在二十六位代表人物中,莎士比亚(感兴趣的读者可以参看他的《莎士比亚:人的发明》)尤其是重中之重,也即“经典的中心”。
尽管布鲁姆以“审美自主性”为准绳,将不许多语种的杰出作家都囊括在内,比如英语作家莎士比亚、弥尔顿、萨缪尔·约翰逊博士,法语作家蒙田、莫里哀,德语作家歌德、卡夫卡,西班牙语作家塞万提斯、聂鲁达、博尔赫斯,等等,但他们就堪称构成了“西方”正典吗?北欧的作家们恐怕会有不同的意见。在某种程度上,“西方”可能不过是布鲁姆这个盎格鲁-萨克逊传统的继承者的“西方”,其他语种的批评家自有另一套标准。
那么,布鲁姆所说的“正典”,又是怎么一回事?布鲁姆的回答是,经典是拥有“陌生性”,“一种无法同化的原创性,或是一种我们完全认同而不再视为异端的原创性”的作品,所有的经典作品都不例外,它们“要么不可能完全被我们同化,要么有可能成为一种既定的习性而使我们熟视无睹”。显然,这里仍然是基于其“审美自主性”,一种近乎绝对的判断标准,它甚少历史的维度,或者说是超越历史的。
熟悉布鲁姆的,都晓得他是个地地道道的“莎翁迷”,《西方正典》在某种程度上也可以称作是部以莎士比亚为中心的著作(如前所述)。布鲁姆的一大核心论点是,莎士比亚同时代及之后的作家,都存在一种影响的焦虑(显然,布鲁姆“推销”起了自己的“焦虑”理论),他们都试图超越莎士比亚。这种情况在《尤利西斯》的作者詹姆斯·乔伊斯身上格外明显,不过,其他作家都是如此吗?布鲁姆的断言或多或少令人生疑。
批评《西方正典》是容易的,比如声称它是以盎格鲁-萨克逊文化为中心的著作,忽略了对其他民族优秀文学作品进行深入探讨,又比如责难它没有将布鲁姆的观点和其他学者的观点区分开来(格式的问题),类似的批评尽管存在一定的合理性,但可惜的是没有正中靶心。布鲁姆的确是傲慢的,因为哪怕他阅读量丰富,显然不是全能,却斗胆用起了“西方”一词,担任文学的立法者。
布鲁姆的激进,可能是脾性使然,也可能是他的一种写作策略:他在鞭策你与他进行辩论。(尽管在他那里,他主要充当一言堂)但不可否认的是,布鲁姆的批评态度是真诚的,他的责骂与赞扬(比如对菲利普·罗斯、保罗·奥斯特的肯定),也都发自肺腑,这与今日不少批评家的场面话形成了鲜明对比。但也必须看到,布鲁姆出于智识的傲慢也妨碍了他,因为后殖民主义、女性主义、生态主义等一系列理论思潮的洗礼对理解文学并非毫无助益,相反,它们与布鲁姆所说的“审美自主性”在相互补充,而非相互对立。
《西方正典》读后感(五):小总结
布鲁姆开宗明义就说了女性主义、后殖民主义、马克思主义以及结构/解构主义、符号学、形式主义盛行的文学批评环境下,让文学离开语境分析,不必刻意否认“欧洲白人男性作家”的霸权身份,也不必因为他们歧视女性就要因着某些字句大书特书——这样都损害了文学。布鲁姆认为,文学应该回归到审美功用本身。
他把莎士比亚当作这近四百年来西方文学的祖先,带领我们看了莎翁后代们各式各样的变形。布鲁姆对于一些作家的解读也没有重蹈常轨,比如他看到但丁创作的贝阿特丽采这个人物作为但丁的基督教“知”的意义,比如华兹华斯将诗歌引入民主的时代,看到众生的悲苦与哀痛,比如我们常说托尔斯泰是救世基督思想,他却认为托尔斯泰是唯我英雄主义,在解读乔伊斯与普鲁斯特时也刻意回避了“意识流”,而是从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学里看到普鲁斯特的“性嫉妒”和乔伊斯与莎士比亚的竞争,还有歌德《浮士德》里的masturbate,惠特曼的同性恋的意识等等。觉得分析的最好的是弗洛伊德那篇:到底是“俄狄浦斯情结”还是“哈姆莱特情结”。关于弗洛伊德对莎士比亚的刻意回避以及焦虑,可以足见布鲁姆的明晰的洞察力。
我觉得在布鲁姆的西方正典里,祖先是莎士比亚,而莎士比亚创作的一众人物里,后代作家更乐意于在哈姆莱特与福斯塔夫的焦虑影响下写作。福斯塔夫在布鲁姆这不再是个酒色之徒,是个十分真实的人物,十足清醒。(或许可以这么说,按弗洛伊德分析法,他把人最见不得光的卑琐的潜意识都表现出来了)他所有的卑劣让后代作家在创作形象时不会再写出英雄史诗里那样完美却不真实的人物,所以“后来者”一直在戳破完美的假象,就像《亨利四世》里福斯塔夫对着已死的飞将军的尸体狠戳两下然后将功劳归于己一样。
哈姆莱特在弗洛伊德的分析里一直是作为俄狄浦斯情结的典型例证被摆出来的,布鲁姆指出的是,首先莎士比亚在《哈姆莱特》这出戏里精神分析已经写的非常到位,他把哈姆莱特各种癔症般的精神都给写出来了,也许《李尔王》里有俄狄浦斯情结,但《哈姆莱特》里绝对没有。其次,哈姆莱特这个形象太过于丰富与复杂,如果只是把他局限在杀父娶母的思考里,那么很多研究都失去了意义。第三,弗洛伊德的出发点并不是哈姆莱特的俄狄浦斯情结,而是作家自己的俄狄浦斯情结。俄狄浦斯王杀父娶母,俄自己什么都不知道,他不知道十字路口出现的三个人里其中一个是他的父亲,是索福克勒斯有杀父娶母的思想。所以弗洛伊德在证明哈姆莱特有这种情结,他所做的却是在努力挖掘莎士比亚的潜意识——然而莎士比亚的创作太丰富了,这种潜意识根本挖不出来。所以把弗洛伊德逼急了,只能力证莎士比亚是个假身份,而真实身份是位牛津爵士。
在混乱时代的最后,布鲁姆让两位作家出场,一位朝后悲哀一瞥,一位朝前远眺虚无。这两位分别是博尔赫斯与贝克特。博尔赫斯的意义在于他驳杂的知识,他的作品知识量太丰富了,这也是他作为文学界迟来者的焦虑:他到的太晚,所以他不知道该以怎样的身份挤进这修盖了几千年文学苑林里。贝克特则不一样,他解构了一切,以最为干净的方式,把前人的一切都抛空,让两个傻子站在地平线边,等着夕阳落下,等着戈多出现。(一个新神权时代的到来)
另外我比较好奇的是,布鲁姆居然忽视了拜伦与马尔克斯。(其实还回避了艾略特,不过看到最后《哀伤的结语》里他明确批判了艾略特新基督教式的新批评,那我就不必多说了)忽视了拜伦,那自然,普希金、雨果、斯丹达尔、巴尔扎克等人就要一并被忽视,毕竟拜伦式的忧郁英雄是他们的“父亲”。我觉得有一点可能是,拜伦式的孤胆英雄,在布鲁姆的眼里是对哈姆莱特拙劣的重复。然而从我个人价值来说,我觉得拜伦式的英雄把那份“生存还是毁灭”的痛苦以一副嘲讽的嘴脸给引入了普通人生命里,所以才有了普希金创作的叶甫盖尼•奥涅金(《叶甫盖尼•奥涅金》)、冈察洛夫的奥勃洛摩夫(《奥勃洛摩夫》)、斯丹达尔的于连(《红与黑》)这样的人物,俄国文学里叫做“多余人形象”。这与哈姆莱特作为一个丹麦王子,伸手是王冠、缩手是为他掘好的坟墓,唐吉诃德把他的人文式的理想全部寄托在过时的骑士精神上完全不一样。所以拜伦是个非常有意义的创新,他值得挤入西方正典之列。
对马尔克斯的回避,我不知道是不是就像对爱伦坡、大小仲马、勃朗特三姐妹的回避一样,因为太过于通俗。至少博尔赫斯一直在营造着文学的迷宫,而马尔克斯营造了雅俗共赏的新奇观。然而我觉得,就按布鲁姆的分析而言,马尔克斯的《百年孤独》所创造的魔幻现实,打通的正是这样一种福斯塔夫式背景,即各路人马,贵族和下等人都轮番在其中登场,语言也是又雅又俗,内容又现实又奇幻,一场绘声绘色的大杂烩。以至于我们国家的当代作家们几乎都致力于模仿马尔克斯的文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