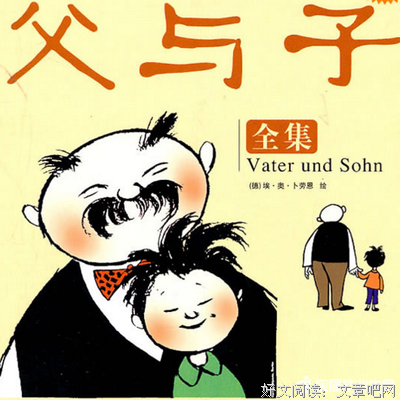
《我与父辈》是一本由阎连科著作,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平装图书,本书定价:35.00元,页数:239,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中国这片土地上的父辈总是如此相似。 父亲部分写得最好,大伯部分前面欠一点,四叔部分最有同感。
●我爱这片土地上淳朴的人们,无论城市还是农村,平凡的人总有一些不平凡的事迹使他成为一个“人物”而不单单只是一个人。阎连科的书里讲述的是他的父辈,可我也透过他的视角也看见了我父辈的缩影,那是整整一代中国人生活啊!阎连科想知道他的大伯如何渡过苦难的“三年自然灾害”,我也想知道我的奶奶如何渡过那艰苦的年月,可我再也没有机会当面问她,一想起这个,泪水总能模糊我的双眼。
●就关于命运、尊严、死亡、生活和日子的突如其来的抒情,让我有点猝不及防的觉得尬,,,其他的,整体都写的挺真挚诚恳了 多少年了,中国的父母依旧把儿女的婚事当做自己的责任,甚至是活着的目标……可怜天下父母心啊
●落泪。到如今,父辈依然这样过着日子
●某些章节段落使用了过多的非常规叠词,有些影响阅读。但情感真实剖析细腻,十分令人唏嘘。这种写法还是很需要勇气的。还有,从另一个角度看知青。
●在书页里嗅到泥土的腥气…填补了脑海中对那一代人,以及对乡村的空白。
●三星半。最让我感动是大伯和四叔欸。以前的人过得好苦啊农村人过得更苦。呜呜呜呜,希望家人朋友身体健康长命百岁
●为什么你连叙事都写得那么美啊!
很喜欢这样的书,真实贴切,也许是我来自农村,有很多美好的记忆都是来自农村的。我是一个念旧的人,时常都还会想起儿时在农村的快乐时光。我是幸运的,我生下来的年代,已经没有了我父辈所经历的那些苦难,更无法去体会我爷爷他们那一辈的艰辛。时常听我父亲讲起他们小时候的故事,讲讲他父亲那一代的故事,每次听到未曾听过的,我的心里都是酸酸的暖暖的。我的血液里流淌着农民的血液,我曾经感到过自卑,渐渐的长大,这种自卑慢慢的消失,而是对于自己这农民的血液而感到满足和自豪。时常会在梦中,梦见我已经仙逝的奶奶,我与她经常在梦中对话,我在梦中清晰的记得她已经不在人世,已经在另外一个世界了,但是并不能成为我们祖孙二人之间的,沟壑。爷爷在我一岁的时候去世,他在我的脑海里没有清晰模样,他的故事,他的好,却在我心留下了一个坚毅而又高大的形象。每一次的祭奠都是对于这座已然隔世亲情桥梁最好的一次搭建吧。
《我与父辈》读后感(二):文字自有它的力量,逝水流长,一个生命的消逝往往是另一个生命的出发
粗略地把书翻了一遍,说实话,对整本书的没有太多记忆,但又有一种淡淡特殊的感觉。作者应该算是和我的父辈同一时代的人,那个时代日子的艰辛是现在所很难体会的,四十年、五十年前中国有中原地区的农村,人们的生活的种种艰难与痛苦、种种辛酸,当贫困面对疾病、当贫困面对上学、当贫困限制着一切一切的时候,就象最近一句流行语,贫困限制了我想象力,部分内容互通。书上具体描写作者的姐姐,父亲在面对疾病时,那种无助、无耐的情景,“为了给大姐手术,一家人父亲、母亲、大哥、二姐和我就站在院门口等着抽血”,“一根清冷白亮的针头…那只空瓶里的血浆随着大哥的脸色由黝黑转为浅黄,再由浅黄转为苍白,便从无到...”很多事若非身临其境,设身处地又如何能理解呢。
《我与父辈》的序和有几句话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作者写这本书的目的并不是想感谢或取悦读者,作者“只想感谢在逝水流远中那属于父辈的岁月和逝水流长中永远凝视着我的生命的灵魂。”书的引子中说到:“他们一生里,所有辛劳和努力,所有的不幸和温暖,原来都是为了活着和活着中的柴米与油盐、生老与病死”。文字自有它的力量,逝水流长,一个生命的消逝往往是另一个生命的出发。
《我与父辈》读后感(三):想说点什么,又好像没什么好说的
这不算一篇书评,就当作自己的读书笔记吧。
不长不短的一篇散文。 可能我跟作者年龄差距较大,并不是很能体会其中的一些情感。 以前看季羡林,看杨显惠,看余华,无一不提到"三年灾害",但都没有详细说到这场灾害是怎么回事。后来去问我了爸,才大概了解了一点,“三年自然灾害”就是**和**谐**。 从这本书又知道一个冷知识:有房才能结婚从五六十年代就已经开始了。父辈为了子女的男婚女嫁,甚至能付出生命去盖房子。一家之主会为家庭付出所有,中国的传统观念父母一定要看着子女成家立业。就像作者说的一样,出生在八十年代以后的人,是无法明白父辈们,是如何为了生存而奋斗,为了婚姻而丢掉了做人的尊严和舒展。 在这本书甚至还能学习到哲学知识。人生不会因为某一场灾难,就把苦难的岁月从你命运中剔除掉。死是哲学的诞生和证明,也是生的延续和延展,死亡也就没那么可怕了。面对死亡最为痛苦的人,正是我们这些识字又读书,可又读书不多、思考不够的人,既不能把死亡升华到学理的境界里,又无法简单地去相信死亡是生命的转换与转移,无法相信人生是有着自己的去向与去处的。 还有一点是作者描述的大伯是一个把尊严放在首位的人,却好赌成性。自己的小儿子在部队里死的不明不白也就这么算了,实在是与“把尊严放在首位”自相矛盾啊。 “人生要么彻底做农民,要么彻底设法做一个城里人,而倘若你半是农民、半是城里人时,你就既没有在农民眼中城里人的快乐与幸福,也没有城里人眼中农民的散淡和自由。而你所有的,却是城里、乡下同时共有的烦乱与不安。”
《我与父辈》读后感(四):情深
《我与父辈》
作者:阎连科
纸质书
6月4日在家中读完
听说过阎老师的名字,有浅淡印象。大约是蒋方舟的新书推荐,有阎老师的序。再有散见于《读者》的散文。心里疑惑:阎连科,不是做文物鉴定的吗,怎么写起来文章?后来才弄清,原来与马未都老师混淆了。及至读到这本书,还是一次次地翻到封页看阎老师的照片,在脑中更改过去错误的信息。
第一次读他的书。一本讲土地、父辈的书。像是初次见面的人徐徐讲起自己的过往,幼年、曲折求学离开土地、父辈的经历。全面的介绍,带着深情,骨子里刻下的痛和爱,有些沉重。是那个年代自农家走出的孩子特有的厚重。
他生于1958年,与父母差不多的年岁。一家人在土地上挣扎求生。物质缺乏、生活贫苦。高中辍学养家,在工地下重劳力,高考恢复后有机会参加但不中,之后参军。
书中分了四个部分:我的那年代、想念父亲、大伯一家、我的四叔。
可能人到中年之后对往事的回忆有了更加清晰的脉络。亲人故去,在这个事实面前回溯,回溯,寻找因由。书中讲到对父亲故去的愧疚、懊悔,是自己背离了土地、背离了对家的责任,才让父亲一步步靠近死亡。
那一段读起来感到重得受压一般。心里存着疑问:儿女怎样算是对家尽上责任?他奔了前程,回想时懊悔,是不该奔自己的前程吗?
也许心上已经有了答案,同时又怀疑着,不敢理直气壮地讲出来。
参军后读军校、坚持写作,如今在人大教书。这是阎老师后来的经历。
不禁想到自己:如果初中之后不读书,现在会是怎样呢?是村中的农妇?还是城市的农民工?是否会有轻松舒展的生活?但至少不会被父亲责难说白读了书还不懂事云云。因为父母供给自己读了书,心上背着沉重负担,像是得了恩典却不知感恩戴德,涌泉相报。
是谁说过:回忆往事像是重走一遍荆棘的路。阎老师的记忆通道让我开启自己的,有一些苦涩的回忆。不知待过些年头,我会否从这苦涩中尝到回甘。如今,我仍怀念童年、故乡,只是乡村生活的底色是美的,如果在那贫乏的生活之上再多些温情该多好。
阎老师说自己生长在一个有着温情的大家族里。在对父辈的回想里,看得到这份情深。
《我与父辈》读后感(五):埋在土里的爱
当下中国文坛,阎连科是我喜欢且敬佩的作家之一。他行文风格独特,“大跃进”式的表达,朴实甚至有些土味的词句,使得著作品尝起来既疯狂,又苦涩。我们习惯用“神实”或“魔幻现实”来概述他的作品风格,只是在我看来,他的那种“夸张”表述,恐怕远不止于“神”似,反而是真真切切上演的现实。脆弱的我们哪里能够接受如此荒谬、滑稽、吊轨的真实呢! 依阎先生所言,《我与父辈》完全随心所至,没有精雕细琢写作技巧,蓄意构造设计情节氛围,而只是跟着自己的心声,随着情感去回忆,所以特别受读者欢迎(相较于他的其他作品)。但即便如此,我仍能从阎先生这部作品中读到那些骨子里的土腥味:拗口的叠词,怪异的搭配,甚至有些啰嗦的类比,不过这些都是在传达一个“野蛮的真实”,一个略带宿命感的农村家庭命运和千千万万个不幸与无奈的生命体,而非他其他作品中所呈现出的“疯狂的真实”。 阎先生的这本书给予了我一些认知上的启发。比如这本书丰富了我对知青的认识。关于上山下乡的知青,在我有限的阅读体验中,他们的形象总是美好的,并和灾难、不幸捆在一起,他们是那个时代的产物,是那个时代权力对知识的践踏和对理想的亵渎。尤其到了当代,对知青的同情和知青们艰辛的经历更是把他们供奉上了理想主义的神坛。从未曾接触到上山下乡的知青们也有像如今一些干部走基层那般荒谬,未曾想象过那些拥有“特权”的知青们可能增加了原本贫困村民们的压力,甚至会出现《枪毙》一文中不同身份违法后的差别对待。 阎先生在刻画父辈们面对生死时的不同形态引发了我情感的共鸣。父辈们(他父亲、大伯、四叔)和他的对话像极了我的亲人们,而他父亲最后对活着的期盼和我爷爷极其相像。要是搁在几年前,我定不信农村人会在苟延残喘之际还坚定的抱着对活下去的一根稻草死死不放(这大概是根生于内心对农村人价值的自我否定)。直到我爷爷在晚年的倔强才刷新了我的认知:与其说我们渴望活着,不如说我们不舍离开,不舍与我们所过活的幸福告别。越是幸福,越是不舍,便越是挣扎。爷爷的离开让我对活着有了新的理解:活着从来不是一种状态,而是一个有生命力的动词。 阎先生在对自己不孝的罪孽反思时震撼到我了,尤其面对病重的父亲他无法释怀的那个邪念:“只要父亲在世,我们家就不会有好日子过。”该是有多大的勇气和真诚才会直面人性之恶,而且这种恶是国人最唾弃的:不孝就罢了,还盼着父亲早死!我时常想,道德评价太容易了,我们可以在对错之间,没有任何交易成本的自由切换评判,颐指气使,气宇轩扬,振臂高呼······可是这种邪恶的念头是专属的吗?我们能保证这种恶念不侵蚀我们的思想吗?我们该如何限制这种恶念的滋长?比起表态和站队,我大概更愿意看到的是构建性的力量。因为,于我个人而言,我无法抵挡这些恶念。我相信没有人可以抵挡住人性的弱点,如果文明源自于克制,但愿能在克制的背后加上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