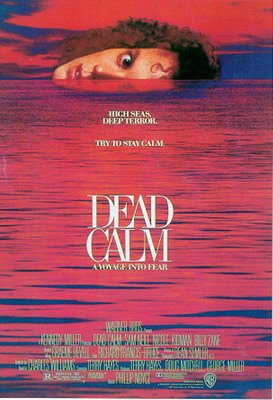
《无粮的土地》是一部由路易斯·布努埃尔执导,Abel Jacquin / Alexandre O'Neill主演的一部纪录片 / 短片类型的电影,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观众的影评,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无粮的土地》影评(一):无题
此片向我们展示了比今村昌平的《楢山节考》更为撼动人心的画面,其力量可与阿仑雷乃的《夜与雾》相比。这是法西斯主义对人道主义的残害,无产阶级沦为专政制度的牺牲品。
时至今日,又有多少人对此地予以关注?此地现状如何?不得而知。
《无粮的土地》影评(二):这个村子
抛开影片深沉的批判性与宗教性,看到的是数十片石片叠成的屋顶掩映于群山当中,接下来是石块累成的户,石头铺成的路,房间内是石头搭起的火坑,树叶铺成的床,对我来说,这是一个很震撼的:材料真实的有些超现实,人无赖的与自然这样直接的接触,有些"美",但太凝重了。
《无粮的土地》影评(三):关于还没看过的《无粮的土地》
歪曲事实,改变现实,捏造证据的纪录片,可能会危害其自身作为纪录片的性质,然而对于某些假纪录片以及“挑衅性”的电影人,这可能恰好是他们想要做的。 对看似注定颓败的文化进行尖刻而又不失偏颇的画外音评论。 反身模式电影,关注那些对纪录片制作起支配作用的假设与惯例,使我们进一步了解影片呈现现实的建构方式。 ——比尔·尼科尔斯《纪录片导论》
《无粮的土地》影评(四):男人与驴
大家等了一个上午
后来来了几个农妇
在同伴走远后仍躲在石头背后偷看
姑娘远远地笑了
她真可爱
在这片无粮的土地上
我们弄死了一头好牲口
她走之后
我们接着等苍蝇
《无粮的土地》影评(五):超现实主义的剃刀
超现实主义纪录片也许还会再有,但像路易·布努埃尔这样的超现实主义纪录片鲜有今日世出者。
超现实主义的电影里,叙事元素和对演员情感的强调都积极地要求观众在心理上参与进来,观众经常会被混乱或者吓人的画面或者快速闪动的蒙太奇剪辑搞得心烦意乱。超现实主义电影的代表作里最广为人知的是那部《一条安达鲁狗》,其割眼睛的臭名昭著的片头让开始的我在有心理准备的情况下仍为之一颤,弗洛伊德式样的暧昧的解读也比比皆是。超现实主义在大卫·林奇的《穆赫兰道》及拥有神秘与诡异、惊吓的影片里也有延续与增强。
然而,与多付诸精神外显层次讨论的虚构性电影而言,《无粮的土地》却是非虚构性影片。这使得超现实主义不是那么“超现实”。传统的超现实主义是有令人惊奇的影像表达技巧,以致被主流电影吸收成为一种并置的画面震慑力,而本片的超现实主义则是摘取实实在在的客观纪录以示威慑。借用“剃刀”一词,该片的记录性质反而以一种客观存在的简单方式剔除原本的影像设计,且批判与冲击力毫不减色。
影片的剃刀甚至剔除了主要的、外显的主观性评价。关于贫穷、落后、残酷、死亡的影像是刻意、毫不遮掩地直现,一般的拐弯抹角的讽刺在此都被抛弃,一切活生生的或死气沉沉的事物都在眼前。这种毫不讳忌的直视让观者颇感不舒服,强烈的视觉感受来自于人类天生对恶的排斥与对死的恐惧,尤其以一些密麻恐惧症、暴力、死亡现场的特写消减观者距离,个人在威慑的同时意识仿若得到一种强迫性思考。这可能与布努埃尔的表达意愿有关,若以产生同情贫弱者的效果则大可不必如此直白强调,环境描写与对白、隐藏的残酷故事即可完成;故他更可能是将对人类与生俱来的残酷性、动物性、宗教性作为主题构建的。个人观感,正是源自人类文明进化与不可改变的残酷内性,使得在贫弱的一个村子里的人生于痛苦又死于疾病,又热衷忽视残酷与恐惧死亡的宗教安葬仪式感。贫弱的村子是作为一个极端样式,纪录的同时旨在引申。
最后还是觉得,本片更加倾向于达达主义那种破坏与否定观众的观感享受,但是符合超现实主义使得电影这种媒介发挥着“透明”的作用。
粗读《达达主义和超现实主义》,片带回劲,因缘作此简析,不正之处请指正。
《无粮的土地》影评(六):《無糧之地》與 “藝術的政治化”
《無糧之地》與 “藝術的政治化”
《無糧之地》(land without bread)是西班牙導演Bunuel的作品,在短短的28分鐘內,導演把鏡頭對準西班牙中西部山脈地帶的貧窮村落——拉斯赫德斯(Las Hurdes),展現了當地人原始赤貧、與死亡相伴的生活狀態。該電影的特殊之處在於明顯的紀錄片特征和超現實主義特色並行不悖,甚至有些學者將其稱為“超現實紀錄片”。
本文雖不意將該片放在超現實主義的框架下分析,但是同樣注意到它與其他記錄片的不同之處——比如冷漠無情如科教解說般的旁白、人為製造拍攝場景、攝影機入侵到被拍攝者的生活等等。因而將本文嘗試從鏡頭、旁白和畫面等電影語言來分析該片對於紀錄片類型的突破。
影片中旁白與畫面的矛盾是對紀錄片類型的一種探索和反思。在紀錄片中,旁白擔任解釋并連接畫面的功能,同時也能傳達導演的觀點。在介紹人文風情的紀錄片中,旁白一般充當著導遊的角色,帶領觀眾去遊覽。《無糧之地》旁白保持了冷靜客觀的語調,片頭先用4分鐘講述目的地附近的富裕小城,再轉而介紹拉斯赫德斯的地理位置、周邊環境和當地人貧瘠的生活狀況。當懸殊的貧富差距隨著影片進行而得以展現,旁白便愈發顯得缺乏人文關懷,愈發給人以荒謬感,進而難以對其內容產生信賴。
以影片12分10秒的小女孩為例,旁白只是寥寥交代:她在路邊趴了三天,工作人員假扮醫生為她看病,以便拍攝她發炎的喉嚨,此外他們什麼也沒做,2天后她死了。從畫面來看,小女孩的愁苦的神態會引起觀眾心中的同情憐憫。但是旁白用事不關己的語調講述這此事時,就與畫面之間形成了強烈的矛盾。這種聲畫的不協調使觀眾對旁白產生懷疑,進而驅使觀眾自身要主動從畫面中尋找“真實”。 這一點也體現在電影畫面中故意顯露的破綻。比如在13分40秒,旁白講山羊只有從懸崖跌落摔死才能讓村民吃上山羊肉,伴隨的是山羊墜落的鏡頭,但右上角的槍彈煙霧卻表明山羊並非意外死亡,山羊的死亡只是剪輯建構出的“真實”。
紀錄片強調真實,在觀眾觀看聲畫協調的紀錄片時,很容易被影片的邏輯引導,從而認為所展現的畫面即為客觀真相,忽略電影本身的可建構性和紀錄片中的主觀性。《無糧之地》則開啟另一扇通往真實的大門,導演看似用人文風情紀錄片的方式介紹一個地點,卻用旁白(文字)對畫面進行居高臨下的說明,引導觀眾接收特定的含義,而這種主觀性的意見會引起觀眾的驚覺,使他們在荒謬中重新思考,從而跳出“紀錄片記載即真相”的思維定式,也是對推崇理性主義的反思。
另一方面,女孩張嘴的狀態的畫面也同樣引起對於記錄片畫面“寫實”的反思,把一個活人的病症放在鏡頭下展示,將其變成一個可觀察、可研究的客體。裝成醫生的工作人員和記錄的攝影機無疑已經侵入了女孩的生活,並不只是處於旁觀者之位。他們可能為女孩帶去希望,卻又任她死去。在冷酷的鏡頭下反而會引起對女孩個體的關懷。進而想到,鏡頭下的當地村民的生活狀態,是純然的日常還是帶有在攝影機前“表演”的呈現呢?伴隨著這種疑慮,觀眾發現自己所見與當地生活之間的距離,意識到自己是無法通過電影的再現而了解該處,於是在這個過程中,拉斯德拉斯人不再被預想成一個可以被瞭解的文化客體,而是有著主體性的人。
在20世紀30年代,電影作為一種新生的媒介,被用來表現創作者反法西斯主義的政治立場並不罕見。班雅明在同一時期的《機械複製時代的藝術作品》的結尾,將“藝術的政治化”總結為對法西斯主義的政治審美化的回應,亦可與《無糧之地》相呼應進行解讀。
班雅明所講的“藝術的政治化”是與當時“為藝術而藝術”的藝術理論相對立的、為適應新的生產力發展(機械複製)而引發的對新的生產關係(大眾作為藝術的佔有者)的要求。為了更好地了解這一觀點,下文將從起源、權力關係和接受方式三方面進行分析。
從起源來看,藝術本身具有可複製性,最早可以追溯到古希臘時代的手工複製。但在機械複製時代到來之前,原作與複製品相比具有本真性(authenticity),原作的唯一性和它見證過的歷史使它充滿靈光(aura),觀賞者和原作之間的距離感和宗教上的神聖感賦予原作以膜拜價值。 [1]而機械複製打破了作品與觀賞者之間的距離感,複製品可以在不同的景況(context)中被觀賞、詮釋甚至是佔有,打破了原作的權威性,可被多元接受的現實性(actuality)賦予複製品以展示價值,藝術的社會功能也從建基於儀式(ritual)變為建基於政治實踐。[2]《無糧之地》中關於教堂、資產階級生活掛畫等因素在當地人生活中處於膜拜地位,卻完全無益於生活改善,電影則成為宣傳反法西斯獨裁專政的作品發揮作用,一定程度上體現了生產力發展要求所有制關係的變革。
從權力關係來看,機械複製時代產生的藝術作品指的是攝影和電影——徹底打破原作和複製品的分野,作品的展示價值第一次超過了膜拜價值。[3]電影改編了傳統戲劇中觀眾與演員的關係,二者之間的認同變為觀眾與攝影機的認同,因而觀眾可以採取批評家的立場,而不必膜拜演員。[4]雖然現實並非如此理想:資本家通過明星制度重新製造膜拜對象、壟斷展示的權利從而牟利并控制大眾,政治上對應著興起的法西斯主義。但班雅明反對向電影強行灌輸膜拜價值的行為,反對“電影只能表現資產階級高雅生活”的觀點。他認為,“每個現代人都能提出被拍成電影的要求”,并通過20年代蘇俄左翼電影說明電影應使演員與觀眾的區別被打破、所有人都有被展示的權利。[5]雖然法西斯主義電影賦予了大眾展示的權利,但出發點在於展示戰爭美學、歸結至對獨裁者的個人崇拜,根本在於膜拜而非展示、維護而非改變所有制關係,因而與蘇俄電影不同。
從接受的角度看:攝影機能記錄大眾無意識視覺中的日常事物,有意識地揭示日常中不被關注的瑣碎細節,能夠豐富觀眾的感知經驗、洞察更大的生活空間,從而獲得震驚效果。[6]同時,文字說明(旁白、前言、結語)引導觀眾以特定的角度理解畫面信息,觀眾在震驚於《無糧之地》中的窮苦生活後被結語引向對反法西斯獨裁的結論順理成章。此外,由於膜拜價值被壓抑,電影院中的觀眾並不會用欣賞繪畫的靜觀方式去接受電影信息,而是採取消遣的、心神渙散的態度。[7]這種低門檻的集體性的接受信息方式無疑有益于建立與大眾(即廣大無產者)的交流。兩種接收方式的變化實際代表了藝術的生產關係,即藝術的佔有者的改變,預示著大眾具有改變所有制關係的權力,體現出革命、解放的傾向。
[1] 瓦爾特·班雅明著,王才勇譯,《機械複製時代的藝術作品》(北京:中國城市出版社,2002年),第92-94頁。
[2] 同上,第85-87,89-91頁。
[3] 同上,第95頁。
[4] 同上,第102-105頁。
[5] 同上,第109-110頁。
[6] 同上,第119-120頁。
[7] 同上,第126-128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