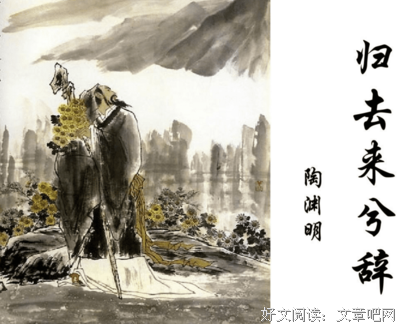
《陶渊明批评》是一本由北京出版社著作,36.00元出版的2016-8图书,本书定价:精装,页数:,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陶渊明批评》读后感(一):悠然见南山 淡墨书陶公
“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问君何能尔?心远地自偏。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南山的美景与采菊时悠然自得的心境,合成物我两忘的“无我之境”;在南山那美好的黄昏景色中,飞鸟结伴飞返山林,万物自由自在,适性而动,正像陶公摆脱官场束缚,寄情于山水,如飞鸟般翱翔于山林,他到底是怎样的人?为何不走寻常路?带着疑问,我翻开《陶渊明批评》,跟随萧望卿先生的脚步走近陶渊明,看看他人眼中的陶渊明。
《陶渊明批评》分为四个部分:由朱自清序起笔、到陶渊明的历史影像、再到陶渊明四言诗论、最后落笔于陶渊明五言诗论。四部分从不同角度阐释,朱自清序强调陶渊明诗歌来自日常生活、语言平白的亲切特质;历史影像主要勾勒六朝以来历代文人对陶渊明的认知;四言诗论,则从四言、五言的风格比较角度指出,四言束缚了陶渊明的性情,算不得成功;五言诗论,则详述陶渊明的独特创造。
从晋到唐,陶渊明在一般人眼里,是个高雅旷达的隐逸之人,钟嵘评他为“隐逸诗人之宗”,读异书,一张素琴伴着南山素菊,喝酒吟诗,直到昭明太子发现他,对他的文章,爱不释手,替《陶集》做序,才给陶诗带来黎明。
我们由渊明想起东坡,东坡爱渊明的诗,钦慕他的为人,叹服他的“绝识”,白朗宁说,“我们接近诗,必须接近诗人的人格”。陶渊明的诗与人格契合无间,或者说诗是他人格照出来的一片幽辉,魏晋时期人窒息于政治霉烂的黑暗,厌倦乱离,他的精神永远是积极的,他在当前境况与意志欲望冲突里不断痛苦挣扎,他懂得顺任自然,五十四岁,还在奋斗,热情孤愤不能挽回坍塌的世界,我们听到远处深沉悲凉之声…..
我恍惚看见一人坐于石上,金黄的菊花,映照他的葛巾和斑白的鬓发,从多露的荒径,带回一片明月。我在萧望卿《陶渊明批评》里,看到陶渊明游走于田园之间,朝听鸟鸣,暮观落日,寄情山水,慢慢体味闲适的心境,感受他能以光风霁月之怀,写冲淡闲远之致……
《陶渊明批评》读后感(二):“悠然见南山”外的陶渊明
读了朱自清的序以及杜志勇为其写的前沿,感觉在文章的名称方面,我只能词穷到使用《读<陶渊明批评>》这个名字了。
于我,对陶渊明的了解,除了上学期间读过的他的文章,还有前两年写过一篇关于他诗歌中色彩词研究的文章。因为是专项研究,兼以文学理论素养不够,所以我对陶渊明的诗其实了解更少,至于理论层面的更是浅显。所以,今日读《陶渊明批评》,虽然其篇幅小,作者在某些方面可能也没有展开论述,但于我这种门外汉,却真的有很大的启发。
陶渊明写诗,不论内容如何,总是基于一定的感受、情感才能发,朱自清既然认同萧望卿在书中所言陶渊明的诗是生活化的,就证明陶渊明的诗的确来自生活,并且还被他赋予了自然、真挚的情感。内容的生活化,决定陶渊明的诗歌在语言风格上不是华丽奢靡的,而是清新自然的。这一点也是今人喜欢陶渊明诗歌的一个重要原。毕竟,生活已经芜杂化、快餐化,能到文字世界中寻得暂时的安逸、恬淡,也不失为一种暂时的解脱了。
但陶渊明诗歌能具有这样的特点,其实是对当时诗歌风格的一种重大的创新和变革。在《陶渊明历史的影像》一文中,萧望卿指出,“晋朝的诗大都穿着玄理的衣裳,粉饰太重的词采,真的情思因而掩没。”陶渊明的诗歌特征是他人格的一种体现,“不为五斗米折腰”“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诗句背后,是他对自己心态及人生境遇的一种描写,也是他对自己人格的一种诗性概括。从《陶渊明历史的影像》一文中可以看出,陶渊明在诗歌内容和风格上的改革、创新,说明晋朝文风之奢靡很多人都已经无法忍受。
《陶渊明批评》一书呈现了萧望卿研究陶渊明的的多视角性。《陶渊明历史的影像》是从诗歌的角度出发研究陶渊明的人生,《陶渊明四言诗论》《陶渊明五言诗的艺术》是从陶渊明诗的每句的字数出发研究,《关心世乱,怀念亲友》则是其诗歌内容方面出发研究,《自然真率的诗》则是从艺术风格出发研究陶渊明的诗。以上种种研究视角,几乎囊括了我们研究陶渊明诗歌的所有大的范围,具有重要参考价值。
正如被我们所认同的,一千个读者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那么,一千个读者就有一千个陶渊明。所以,萧望卿只是诠释了他这个角度的陶渊明,我想,这对于其他人诠释自己视野中的陶渊明也有着很大裨益的。
《陶渊明批评》读后感(三):俯仰终宇宙,不乐复何如
萧望卿的《陶渊明批评》帮助我们更深刻更系统更全面地认识陶渊明,认识陶渊明山水田园生活背后的苦乐辛酸,寄予山水田园之中的乐天精神。萧望卿的角度并非是老生常谈,而是从陶渊明的历史影像、陶渊明四言诗论、陶渊明五言诗论几个方面具体有理有据地阐述陶渊明的性情与价值观。
其中,《陶渊明历史的影像》里综述了对陶渊明的评述。作者对比同时代的诗,“晋朝的诗大都穿着玄理的衣裳,粉饰太重的词采,真的情思因而掩没”,与之相比,陶渊明的诗“看不出一点影子”。与陶渊明同时代的人看陶渊明,“近识悲悼,远士伤情”,陶渊明孤高和寡,高远清雅,这种作风很符合晋时的风气,被当时人推崇。但很悲哀的是,人们推崇陶渊明风雅一面,却并不太欣赏他的诗,因为诗不符合玄虚轻绮的文坛风气。
好在对晋人来说,行为艺术比艺术本身更重要,陶渊明爱读异书,一张素琴伴着南山秋菊,这种姿态就足以“高趣”“高雅”和“旷达”。所以,直到去逝多年后,陶渊明的诗到了昭明太子手中,才得到伯乐的赏识。昭明太子为陶渊明文集作序说:“渊明文章不群,辞采精拔,跌宕昭彰,独超众类,抑扬爽朗,莫之与京,横素波而傍流,干青云而直上,语时事则指而可想,论怀抱则旷而且真,加以贞志不休,安道守节,不以躬耕为耻,不以无财为病,自非大贤为笃志,与道污隆,孰能如此乎?”评价非常高。
在《陶渊明历史的影像》一文中作者仔细考证了陶渊明之后各朝各代评论家们对陶渊明的评价,得出宋时对陶渊明的研究已有纲领,而明清两代未有什么发展的结论。
对作者来说,他人的评价是帮助我们理解陶渊明的一方面,而陶渊明自己对自己的评价则是另一方面,而这一方面更加深刻和精准。壮年后的陶渊明会在诗中回忆少年时,“少学琴书,偶爱闲静,开卷有得,便欣然忘食”——其实已有陶然的意象。到“少年适俗韵,性本爱丘山。误落尘网中,一去三十年。”此时,更是明了不惑。
解读人物,从外到内,从旁人评价到个人诗作佐证,再到分析诗人所处社会环境,社会风气与思潮,诗人的面貌更加有血有肉,立体起来。精神的外化,精神的呼号和挣扎,构筑独一无二的灵魂世界——这才终于完成对一个人全面深刻的分析。读萧望卿的《陶渊明批评》除了让我们深入理解陶渊明和他的诗文,更让我们看到如何对一个人进行有力而精道的分析评述。
大众对于陶渊明的印象,大约停留在“不为五斗米折腰”的“隐士”五柳先生阶段。陶渊明做此类诗的年龄已是中晚年。然而这位隐士也曾经是热血少年,胸怀壮志,意气飞扬。他在《 拟古 》中记录曾经的自己:
少时壮且厉,抚剑独行游。 谁言行游近?张掖至幽州。 饥食首阳薇,渴饮易水流。
谁还没有年轻的时候呢?想当年,淡泊名利、忘怀得失的五柳先生也是响当当的一位小英雄,一身侠骨闯荡江湖。那么这位小英雄是如何从“侠客”变成了“隐士”呢?萧望卿先生在《陶渊明批评》中对陶渊明做出了全面、深入的分析。
萧望卿先生被称为朱自清先生的最后一名学生,1945念入清华大学文科研究所中国文学部,师从朱自清、闻一多两位先生。这本《陶渊明批评》最初为1947年开明书店版,是由朱自清先生作序并介绍出版的。
陶渊明所处的东晋时期一百多年的时间,玄言诗长期占有统治地位,粉饰词采,淹没情思。当时玄学流行,人们喜欢高谈阔论老庄哲理,形成了玄言诗的风尚。陶渊明也不可避免地受到了时代的影响,但他不直接宣扬老庄玄学,只是用最简单质朴的语言,描述自己的日常生活和心情感悟。在那个热爱绮丽词藻的年代,陶氏的诗文并不受欢迎。诔文中只是范范地说些套话:”近识悲悼,远士伤情。”
陶渊明死后一百年,《文选》的编者双目失明的昭明太子因为喜爱陶氏文章,倾情为陶氏作序,陶氏在历史中的地位被向上略微提了一下。及至唐宋时期古文运动开展,北宋时期古文代替骈文占据文坛统治地位,陶诗才身价陡增,被认为诗汉魏六朝时期最杰出的大诗人。
萧望卿先生拨开历史的云雾,让陶渊明的影像在时间线上清晰起来:“他是接受了儒家持己严正和忧勤自仛的精神,追慕老庄清静自然的境界,也沾了点佛家的空观、慈爱与同情,奇怪的是他也兼容游侠的精神。”陶渊明是一个立体而多元化的形象。
本书的另一大成就是对陶氏的四言诗和五言诗进行了比较和评价。陶渊明以五言诗传世,人们对他的四言诗知之甚少。同是《答鲍参军》,四言与无言相差甚远。萧先生说,“在四言诗里,渊明似乎不曾找到他自己特有的韵律。”
萧先生的这本关于陶渊明的文学评论,不像是研究论文,而像是在优美的散文中徜徉,每一段文字都蕴含着深刻而真挚的感情。萧先生说,韵律是内心的音乐。读者坐在乐谱之中,随着音符起伏,不时发出对美的惊叹。
《陶渊明批评》读后感(五):陶渊明的诗与人生
陶渊明是生活于晋、宋之交的诗人,他的诗跳出玄言诗的藩篱,给当时的文坛吹进了一股清新的风气,却长期不见容于主流,这和我们今天的极力推重相去甚远。
研究离我们这样遥远的一位诗人,通常的做法是花大力气加以饾饤式的考据。而萧望卿的《陶渊明批评》另辟蹊径,他采用文学批评的视角来研究陶渊明的诗,进而解读诗人。
《陶渊明的文学世界》的作者孙晓明有一个观点,”文学与现实相关,甚至我也可以说它来自现实,但是,当它一旦成形,便超然于现实之上,成为一个自足的世界。文学是历代作家用自己的想象堆积成的一个专属于人类精神领域的崇高殿堂,它有许多功能可以在人类体现了人类的自由意志,以及对于摆脱现实束缚的永恒追求。”
诗是反映现实的,是现实在诗人精神世界的映照。陶渊明生活在被玄言诗包围的压抑世界,而能“将诗的疆域扩展到田园,不唯带来了新鲜的景象,新鲜的声音,而且创造了一种新诗体。(萧望卿)”。
陶渊明同时及其后的人是如何看待他的呢?与陶渊明交情不浅的颜延之在《陶徵士诔》中说他“文取旨达”、“文体省净”、“ 不枝梧”,隐含质直的微意。陶渊明是以高雅的隐士被时人所尊重的,却不欣赏他的清新的诗风。从晋到唐,他都被看作一个高雅旷达的隐逸人物,“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仿佛不食人间烟火。而他的诗,一直埋没下尘,得不到足够的重视。南朝梁昭明太子说他“辞采精拔”、“独超众类”,他的弟弟简文帝也喜爱陶渊明,常常将他的诗集带在身边欣赏。钟嵘的《诗品》将陶渊明列为中品。说他的诗是“田家语”,把他作为古今隐逸诗人之宗看待。陶渊明和杜甫一样,只有到了宋代,才开始被极力推崇。宋人偏爱杜甫,也偏爱陶渊明。苏轼说陶渊明贵在“真”,认为他的诗有奇趣。欧阳修、黄庭坚诸人更是对他喜爱有加。
萧望卿认为,“要了解他情思与艺术的发展,只有向他自己的作品里去探寻。”陶渊明的《归园田居》六首,在其作品中占有很重要的位置。其一中说“少无适俗韵,性本爱丘山。/……/久在樊笼里,复得返自然。”“自然”是庄子的思想;《饮酒》诗中说”少年罕人事,游好在六经。”,六经是儒家经典;《拟古》中有“少时壮且厉,抚剑独行游。”从小有侠客仗剑天下的志向。
正是在研究陶渊明诗歌的基础上,萧望卿认为:他是接受了儒家持已严正和忧勤自任的精神,追慕老庄清静自然的境界(却并走入颓唐玄虚),也染了点佛家的空观、慈爱与同情,奇怪的是他也兼容游侠的精神。
陶渊明的诗分四言和五言。针对其四言,除了《停云》和《归鸟》,萧望卿认为无甚可取。四言诗到了汉代可以说走到头了,自身的不足使得四言诗的创作难有佳作。模仿《诗经》,不会造语,缺乏新创的意象,等等。
而陶渊明的五言诗,语言简练,有乐府诗的明白生动,诗风平淡真挚,使人读来感觉亲切。萧望卿认为在《诗经》中没有得到多少营养,而《离骚》也只是在气氛和情调上产生了一点有益的影响。“陶渊明的源泉是在建安的诗,和古诗十九首,更重要的是曹子建和阮籍。”
萧望卿把握住了陶渊明的诗歌风格,对于题材、节奏、语言、内容、思想,都有十分深刻的认识。他从诗歌本身出发,研究陶渊明的诗与人生,让读者在不长的文字中得出一个清晰的印象。
关于陶渊明,萧望卿是从诗歌上解读的。而李长之的《陶渊明传论》则是以传记的形式加以研究的。我们不妨可以参考来读,从而了解一个立体的形象的陶渊明。
《陶渊明批评》读后感(六):杜志勇:《陶渊明批评》前言
编者按: 近得友人书云:“比自整理者杜志勇先生处,索得所撰萧望卿公《陶渊明批评》之前言并书影,专此呈上,俾《徵文考献》之采择也。萧氏肄业西南联大,系闻一多、朱自清之最后研究生,平居淡泊,有古君子风。其为文山高水长、儒素自持,真堪有以表章之也。唯以专注授课,不事攀缘,遂尔空山夜雨,寂寥平生,观此可以觇出处。‘大家小书’近又重刊罗庸论著数种,读之皆可润德养志。”今特为刊布,以飨读者。
不少看似久远的作品至今读来依然让人眼睛一亮,甚至惊异。其中有的曾经一度饱受赞誉,然而因为地域、政治等非学术原因,今天知道的人不多了。“大家小书”希望挖掘这些价值不菲的遗珍,我不假思索地要推荐萧望卿先生的《陶渊明批评》。
“大家小书”平装本《陶渊明批评》封面《陶渊明批评》最早于1945年9月至1946年1月分三次连载于《国文月刊》,后由沈从文先生推荐给李健吾,继而介绍给叶圣陶,纳入“开明文史丛刊”,由开明书店在1947年7月出版。好评不少,因此1949年即获再版。此后尽管台湾又重印过六次,而大陆一直没能重版。加之萧先生的主要学术活动集中在1949年以前,以至于萧望卿这个名字诚如陶渊明唐前的影像,对于普通读者实在太朦胧了;他的著作的真晖也不幸隐没多年。
1947年开明书店版《陶渊明批评》封面萧望卿(1917-2006),原名萧成资,又名肖望卿。湖南宁远人。1940年考入西南联大师范学院英语学系,旋即转入中文系,结识沈从文先生,在沈先生的关怀和指导下开始文学创作。1945年入清华大学文科研究所中国文学部,师从朱自清、闻一多两位先生继续深造,也结识了林庚、季羡林、王瑶等先进学长。萧望卿1946年先行返京,闻一多师相嘱大家到清华会合,一起讨论唐诗。不料闻师在当年7月15日遭到暗杀,其导师只剩朱自清先生一人了。1947年6月,萧望卿参加毕业初试,论文题目为《李白的生活思想与艺术》,考试委员有陈寅恪、浦江清、俞平伯、余冠英、雷海宗、张岱年、游国恩等诸先生。研究生毕业后,历任河南商专、广西桂林艺术师范学院、东北师范大学、河北师范学院讲师、副教授、教授。
萧望卿先生北京大学杜晓勤教授认为萧望卿是“为数不多的对李白思想做全面、深入分析的学者之一”,但他最成系统,最为人熟知的作品当属《陶渊明批评》(以下简称《批评》)。《批评》一书的最早发表时间,恰好是萧望卿研究生入学的时间,应该是在其读本科时完成了本书写作。
关于这本书的导读,朱自清先生的序——《日常生活的诗》,已经成为经典文章,读者自可展开欣赏。本人只拟在综合前辈学者相关评论的基础上,谈一谈本书的学术史意义。
第一,作者扬弃了传统考据的立场,而是在对陶渊明抱以“了解之同情”的基础上,采用文学批评的视角来研究陶诗。
这种视角是以前不多见的,所以朱自清先生在本书《序》开篇就为这种方式正名,“这是一个重新估定价值的时代,对于一切传统,我们要重新加以分析和综合,用这时代的语言重新表现出来。”进而又言:“我们这时代认为文学批评是生活的一部门,该与文学作品等量齐观。”这种观念和罗兰·巴特的话很近似,也是朱自清、闻一多、沈从文等那班代表当时文化最前沿的有识之士的共识,他们集学者、作家于一身,并以西南联大、清华大学等地教席为阵地,培养出一批践行他们主张且一专多能的优秀支持者,萧望卿和穆旦、汪曾祺、王道乾、郑敏、吴小如等人皆身列其中。《批评》出版后,吴小如以少若之名撰文评论《陶渊明批评》,发表在1948年1月的《文学杂志》上。“我相信,治文学所应走的路,单凭饾饤的考据或渺茫的创作是不够的,到终结,还该回到‘欣赏’与‘了解’古典作品这一条路。此书虽小,却不啻为后人开的一扇法门,点一盏明灯。”这实际上是指出了《批评》介于考据与创作之间的典范意义。吴小如还以《批评》的语言为例,指出文学批评应该达到的境界:“作者的情感,却用一种不假雕饰便成绮绣的词采铺摛绩织而成。这本小书,不独可作为专门读物,且可用来当纯文学的作品看,即此已合于‘文学批评’也应该是‘文学’作品的条件与标准。”充满文学创作激情的萧望卿,以飞扬的想象力、细密的逻辑、隽永的笔致从容道来,直把《批评》锻造成为名副其实的学术美文。
第二,有新视角,自然会看到新风景。“从艺术性方面分析渊明四言、五言诗的优劣,这是《批评》一书的最大特点。用一部书中绝大部分篇幅对渊明诗进行艺术分析,这不仅在萧望卿此书之前所未见,即其后亦极少见。这一特点,便是萧望卿在陶学史上的贡献。”[1]详人所略,知难而进,这是朱自清序言所一再褒扬的。
作者如此做,具有明显的西方“新批评”的印记。他读书期间,接受瑞洽慈、白璧德等西方一线批评大家的课程是自然的,《批评》一书的引文除了艾略特、瑞洽慈,还有叶芝、瓦雷里、蒲伯、朗吉努斯、西密拉等人的观点,精细到从音调、节奏的语言内部探求文学风格的养成,这在今天读来还是让人钦佩的。
《陶渊明批评》目录《批评》一书是在西方诗学参照下讨论陶渊明诗歌的一本标志性著作。关于陶渊明诗歌的评述重要的此前有两波:一波是梁启超和陈寅恪,一波是林语堂、朱光潜和鲁迅。梁启超的《陶渊明》是用传统诗学知人论世方法,结合西方政治社会学分析来立论的,赞赏陶渊明“真能把他的整个个性端出来和我们相接触”,“渊明的一生,都是为精神生活的自由而奋斗”;随后这引起了陈寅恪的论争,陈文《陶渊明之思想与清谈之关系》,特别强调陶渊明的士族出身和气节、天师道信仰和新自然观思想。随后林语堂在《生活的艺术》中标举陶渊明“这位中国最伟大的诗人,和中国文化上最和谐的产物”,“因为陶渊明已经达到了那种心灵发展的真正和谐的境地,所以我们看不见一丝一毫的内心冲突,所以他的生活会像他的诗那么自然,那么不费力”。接着有朱光潜《诗论》有陶渊明专章,融合西方心理学知识,同时引用温克尔曼的观点,提出陶诗“如秋潭月影,澈底澄莹,具有古典艺术的和谐静穆”,他后来又在《说“曲终人不见,江上数峰青”》接着说:“艺术的最高境界都不在热烈。……屈原、阮藉、李白、杜甫都不免有些像金刚怒目,愤愤不平的样子。陶潜浑身是‘静穆’,所以他伟大。”这引起鲁迅的针锋相对,他说陶潜“正因为并非浑身静穆,所以他伟大”,并指出:“陶诗中除论客所佩服的‘悠然见南山’之外,也还有‘精卫衔微木,将以填沧海;刑天舞干戚,猛志固常在’的金刚怒目式,在证明着他并非整天整夜的飘飘然。”萧望卿的《批评》汲取了这两次大论争的营养,有兴趣的读者可以参看并比较。
作者在新的批评参照系上,表达一个新的态度,也使用了新的概念,并对后来文学史写作产生了重要影响。据笔者查阅各类文献,“玄言诗”这一概念在出版物中首次提出和使用,当归于萧望卿先生名下。《批评》中多次使用“玄言诗”一词,“陶渊明的四言诗也是从《诗经》导引出来……而玄言诗的影响就只在说理一方面。”[2]不仅使用了这个名词,更是指出了玄言诗的特点:说理。于是,玄言诗这类作品有了自己的专属称谓,成为文学史上的重要范畴,为后来的文学史所沿用。一般说来,这个概念的提出被追溯到朱自清的《经典常谈》和《诗言志辨》,但两书的初版分别在1946和1947年。至于玄言诗这个概念的最早提出,也许是萧望卿直接接受了朱自清的影响,也许是师生学问相长的一个范例。
除《批评》之外,作者还有《李白的思想与艺术观》《艺术的透视—李白新论》《论陌上桑》等研究生论文成果,“当时评论界就认为:袁可嘉、萧望卿的论文已经成为‘替换老辈’的优秀成果。”[3]而此时萧望卿年仅三十岁。
值得敬重的还有:作者不仅在古代文学批评研究方面卓有建树,还同时涉足于文学创作、诗歌理论、现当代文学研究等诸多领域。在沈从文先生的鼓励和指导下,相继发表了《李其芳》(1942)、《七月》(1942)、《乌鸦》(1946)、《山城的小湖》(1946)、《桂花林里》(1948)等作品,他在平津文坛崭露头角,成为“‘新写作’的新生力量”。[4]其散文创作尤其突出,被评价为“能于绵密深厚,委曲周至中得疏宕空阔之趣者”[5]。作者不仅创作新诗,还是新诗理论的积极思考者,他把关注视野投向现实题材,发表了《诗与现实》、《新诗的动向》等文章,被看作是“活跃于平津文坛的评论家”[6]。这个平津作家群对接当时西方思潮,希冀一个中国的文艺复兴。作为其中的一员干将,萧望卿积极放眼国外优秀作品,凭借扎实的英文功底,翻译了英国J.罗斯金的《山雾》、W.H.赫德逊《她自己的村落》等作品,为当时的新文学创作带来一股新鲜的给养。
萧望卿先生手迹建国之后,萧先生颠沛流离,精力被严重分散,无法进行正常的创作和研究。1988年退休后,他准备重拾河山,把浪费的时间追回来,不幸罹患白内障,几近失明,直至1995年手术之后才见好转,他能接着做的也主要是接引后进。萧先生总是慨叹这辈子没有什么成绩,最对不起朱自清、闻一多两位导师,也对不住沈从文先生的期望。先生如此自责,充满了对流逝光阴的无限惋惜,但其已经取得的学术成就是不该被遗忘的。
2013年12月
于河北师范大学文学院
注释 [1]吴云《陶学一百年》,《九江师专学报》1998年第1期。 [2]《批评》,第32页。 [3]傅秋爽主编:《北京文学史》,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332页。 [4]段美乔:《论1946—1948年平津文坛“新写作”的形成》,《文学评论》2001年第5期。 [5]吴小如:《陶渊明批评》(书评),《文学杂志》第二卷第八期。[6]张松建:《现代诗的再出发:中国四十年代现代主义诗潮新探》,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7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