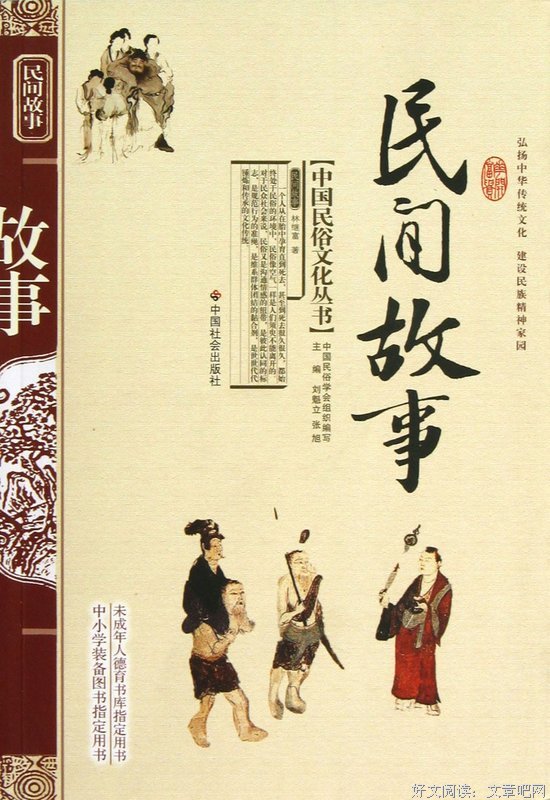首届宝珀•理想国文学奖自2018年3月正式启动以来,历经长、短名单的两轮选拔,将于9月19日由阎连科、金宇澄、唐诺、许子东、高晓松等五位评委决选出最终获奖者,并在当日举办的颁奖典礼现场揭晓。
入围决选名单的五位青年小说家:双雪涛、王占黑、阿乙、张悦然、沈大成,乃是五位风格迥异的写作者,在某种程度上,也是我们时代青年小说家的代表。因此,文学奖委员会近期组织了对五位青年作家的访谈,9月12日起将陆续刊出,希望能在短名单的群像之余,呈现这些优秀的青年小说家各自的面貌。正如宝珀•理想国青年文学奖所揭示的那样:“青年”与“文学”,永远在“奖”之前。
按:“生活就像一盘消消乐”,这是90后新锐小说家王占黑处女作《空响炮》扉页上的一句话,据王占黑自己说,这句话是编辑想出来的,灵感可能来自书中的一个短篇《美芬的故事》,因为美芬喜欢玩一个叫开心消消乐的手机游戏。
《空响炮》一共收录8篇小说,小说主人公都是身处新旧交替的空间之内的街道小人物,他们的人生没有什么惊涛骇浪,过着像消消乐一样的生活。这个短篇集源自王占黑一个叫“街道英雄”的写作计划,该计划第二本《街道江湖》也即将出版。
王占黑生于1991年,浙江嘉兴人,毕业于复旦中文系。她给自己起了一个男孩子气的网名,叫“占黑小伙”,也有读者喜欢叫他“占黑伙计”。
与许多同龄作家不同的是,王占黑的创作起点并不是个人的女性的内部经验,而是更广阔的街道空间和平民社会,尤其喜欢写老年人的故事。按照评论家的说法,王占黑就像本雅明笔下的游荡者,而她书写的都是上世纪九十年代的昨日遗民。此外,吴语方言的运用、老成的文风、不加引号的对话、白描的手法,这些都构成了王占黑的标签语法。
1
《路边野餐》剧照
王占黑:这个计划高中的时候就有了,那时觉得小区里很多叔叔阿姨都很厉害,有本事,我是说平常社交、生活技能和精神面貌上。当时写了第一篇,小区看门人,后来上大学,就此搁浅了。
直到研究生才拾起来,重写了最初那一篇,发现不该美化、传奇化、英雄化,他们老了,大半辈子也并不称心如意,于是想要更真实、细致地去写,但仍然保留了“英雄”这个称呼,觉得这个词可以是平民的,甚至反英雄的。不知不觉就写了很多人,但写的过程中仍然在努力规避重复,希望能做到“什么样的人都有”。
文学奖:“街道英雄”是一种写完就可以结案的个人经验,还是长久以来的主题?
王占黑:街道英雄和王占黑这个写作者,以及我这个活人一样,都是在持续生长着的,行走着的。现在看来,它也四五岁了。而我从一个学生变成了社会人。我一直在反思,在调整,脑中的文本,落笔的文本,和我本身,一起成长,长久磨合下来,我们之间难以做个告别或了断。
文学奖:你写市井小人物的悲喜,在年轻一辈里,这种“生活流”也不乏其人,但对于这类小人物书写,似乎还得问一个问题,就是写出了这些人的悲喜,然后呢?如果只是简单的世情小说似乎就没有太大的意思。不知道你写“街道英雄”系列背后会不会有一个更大的问题意识?
王占黑:好像没有。也许我在写《街道英雄》的时候,我的思考水平就到这里了。也许我还难以用言语表达出自己脑中一些混沌的想法。问题意识这个词,我从大学第一次听到开始,就答不上。
文学奖:你在创作谈里写过说自己经验和知识的顺序,你是由经验到知识,但作为一个中文系科班出身的作者,你肯定很清楚文学史的一套叙述,比如对于尤其90年代以来过度沉溺在自我的书写里的批评,这个会不会也是一个原因?你在一开始写作的时候,就开始意识到那种过度挖掘自我经验的写作是有问题的,你会有意避免吗?
王占黑:如果我和你是面对面问答的两个人就好了。这样我就能及时问你,文学史的哪一套叙述?我真的不知道。可能我在学业上太差劲了。但我的创作好像也是在挖掘一己之经验,街道的经验,某种程度上就是我的生活经验,只是不够那么“个人”、“私密”而已。而且我也时常担忧,一直写下去,我是否会过度沉迷和消耗,最后没东西可写,卒。(不过可以找点别的事做,也许不错)
文学奖:你书写的主要是新旧交替的社区里的人物,在《社区、(非)虚构及电影感》这篇文章里,你特别谈到你很喜欢贾樟柯、毕赣的电影,他们的电影似乎有很强的空间感,但是在你的小说里,似乎并没有花很多笔墨去描摹那个社区空间,似乎主要的笔墨在人物上,不知道你怎么处理空间的问题?
王占黑:贾樟柯早期几部很喜欢,毕赣一般。他们对待故地的姿态十分启发我,倒没怎么留意电影中的空间感。但我自认为,我对社区这个空间有过较为细致的描摹,不在《空响炮》,而在《街道江湖》里面。某种程度上,《街道江湖》是个固定画圈的系列,人物在同一个范围内相互穿插,彼此联结,而《空响炮》更像是一个补充,范围更广,人物关系更散。比如我记得《阿祥早点铺》、《老马的故事》等都对生活环境的描摹。但我不会特意去单独处理空间,本身“街道”就是一个较大且固定的框架在这些人物之上了。
文学奖:划定一个具体的故乡,然后书写这个故乡,这是很常见的写作模式,但你这个集子里的小说都没有点出具体是哪里,只是泛泛地称之为街道、社区,这是出于什么考虑?
王占黑:我是故意的,不给这个文学世界中的社区起名字,哪怕最开始确实以自己生活过的地方为原型。圈地没有意思,“老社区”本身就是大小城市里常有的,这些人物也随处可见,他们很普遍,不是什么特殊的人,不需要特定的架构。就像鲁镇一样,每个人,不管是过去,还是当下,读到鲁镇里的角色,都会觉得好像跟身边的谁谁谁有点像。它不是个需要被固定的地方,而是很多地方的影子。
这也是我为什么用很含糊的吴语,而不是用特征明显的沪语,或是标明嘉兴话。读者只需要大致感受到,这是江南某个城市的某个小区就可以了。包括地点,我也是天南海北地用着。事实上,我写的时候,脑子里也并不限定在哪个特定的空间盘旋。
2
文学奖:因为语言某种程度上也是我们的思维方式。你在那篇《麻将的故事》的创作谈里讲过,有朋友问你的小说里如果抽掉方言表达,会不会逊色大半,你觉得会吗?
王占黑:对于有方言的人来说,方言是母语的底色。你说得没错,语言影响思维,我用吴语来思考和叙述,我自己边写边读的时候,是用方言来念的。但我并没有只在对话里放方言。当然,刚开始我觉得方言可以让人物对话逼真,因为这些人物不会说普通话。后来发现不止如此,方言中有很多词汇的表达和形容比标准汉语生动,有趣多了,有时恰恰展现了不上台面的口头语言所具有的高级的文学感,可谓一笔深厚的宝藏。但最终,方言是行文游走的支撑,也是写作者思维流动的支撑,我认为我正在努力靠近这个趋势。
文学奖:虽然看起来也是在写小镇畸人,但与我们普遍理解中的“乡土文学”、“小镇文学”并不相同,你似乎是在用一种当代的视角处理传统的文学题材。这是出于什么考虑?你会把自己的书写放到哪个序列里?
王占黑:乡土作家?我这算是城市吧……虽然比较土味,贫穷,但确实是在城市里发生的事。有时候放假去乡间玩会很开心,很有收获,但确实不太有农村经验,也不了解乡镇。
用当代视角处理传统题材,好像是这样。也许因为我比较喜欢现代文学三十年(也许可以称之为过度沉迷),对当代文学不太了解,我感觉自己的写作风格还是很老派,很古旧的,但处理的却是当代生活。咦,不对,这样一来,似乎就成了“用传统视角来处理当代题材”?
说真的(我不是在插科打诨),我希望我的书能出现在城市图书馆的新增序列里,一种实体的序列。至于分类和序列,我无所谓啦,反正《空响炮》都被建议上架“青春文学”了。
文学奖:《空响炮》里的八个故事大部分都是全知视角,但也有几篇里有一个叙述者的“我”(比如《怪脚刀》),你怎么处理哪一篇里要放进一个“我”,而哪一篇不用?这个“我”起到什么样的作用?怎么定义叙事者的身份?
王占黑:《怪脚刀》是从《街道江湖》里单独抽出来的一篇,里面出现过的阿金,小官,都在另一本书里。我最早的写作都会有个“我”,比如《空响炮》里很稚嫩的三篇,《吴赌》、《地藏》和《老菜皮》,以及《街道江湖》里的很多篇都是,“我”的成长和老伙计们的衰老,是共同发生的。但写到后来,我渐渐尝试把自己隐去了,就写了《空响炮》《麻将》《美芬》《偷桃换李》。所以你会发现,《空响炮》里有两种形式、质量都断层的作品。但今年我写了一个中篇叫《小花旦的故事》,那个作为小区的游荡者的“我”又回来了。“我”和小花旦的交往串联了十多年的历史。我很喜欢,大家都很喜欢。而且那个“我”,和真实的我,和文中的小花旦,都有很真挚的关系。
关于叙述者身份的处理,每次出现的不同,可能要看我愿意站得离我的文本有多远。这个距离,可能是由我对这个尚未出生的文本的情感所决定的。
文学奖:我有注意到豆瓣上有的读者说《空响炮》里的小说有点参差不齐,似乎他们普遍比较喜欢的《麻将,胡了》《空响炮》这样的作品有一个共同点,就是小说味更强(比如《空响炮》的结构性很强,而《麻将,胡了》最后则有点欧·亨利式结尾的意味),而有几篇则不太像小说,就像一般的散文或是人物素描,所以有的人会觉得气质不太统一,你自己怎么看?
王占黑:后面三篇短的是很稚嫩的习作,我当时确实不想放上去。但是出版总有一些无法控制的原因。所以这本书很单薄,撑不住,我也很心虚。比较好看的几篇是在写完《街道江湖》之后写的,所以前后差很多。希望《街道江湖》出来之后大家能看到我在《空响炮》两类参差不齐的作品之间的成长和过渡吧。另外,书《空响炮》中我个人最喜欢的是《偷桃换李记》。
3
“新的命题,可能是寻找文学之外的世界”
文学奖:你似乎很推崇沈从文和萧红,还做过萧红的研究,这两个人对你创作的影响主要是什么?你的小说的那种市井气、烟火气也会让人想到张爱玲,但你似乎比较少谈到张爱玲的影响,为什么?
王占黑:称不上特别推崇,这三位我都看过,因为上过精读课,仔细研习,比较熟悉。我研究生的课题本来想做晚清知识分子张德彝,因为对晚清和文化史感兴趣,后来做不下去了,就换了一个题目,选了萧红。她的《呼兰河传》我很喜欢,其他一般。
其实我没有最喜欢的作家和作品,但最近常常被别人问起,如果非要说,那就是《海上花列传》,算是我目前最喜欢的文学作品。韩邦庆的苏白好看,张爱玲的国语翻译本也好看。
文学奖:注意到你说过自己认同已经是一个行动者,你很关注社区共建和公共空间自治的问题,比如你参与定海桥互助社的活动,跟他们玩得挺好,你会怎么理解你的文学创作和这些基层实践之间的关系?又或者说,你觉得在今天这个时代像“文学的行动性”这样的问题还重要吗?
文学奖:你觉得对于今天的青年作家来说,面临的新的命题是什么?你会怎么处理它?
王占黑:新的命题,可能是寻找文学之外的世界。
文学奖:在读《空响炮》这一篇的时候,其实已经是群像了,出现了好几个人物。你如果写长篇,会不会用这种开头让人物全部出场,然后接下来各自讲述他们每个人的故事但又各自有关联,形成一个王安忆讲的“一曲套一曲,曲牌如海”的长篇叙事结构?
王占黑:因为穿插的人物都在《街道江湖》里。很抱歉拆成了两本,而第二本没有及时跟上。有计划写长篇,目前还没开始,全职社畜太累了。
王占黑:想写一个长篇,和我生活的这片土地的历史关联更强一些。如果写不出,或者没有新的想法,就不写了,干点别的。
9月19日
阎连科、许子东、唐诺、金宇澄、高晓松
五位评委将齐聚北京颁奖典礼现场
一同揭晓首届“宝珀·理想国文学奖”最终得主
2018 宝珀•理想国文学奖
在任何领域,青年的参与和活跃度永远是决定该行业是否有前途的重要标志。 “宝珀•理想国文学奖”是为发掘有潜力的文坛新锐,支持有才华的青年作家,鼓励汉语小说创作而设立的文学奖项,由瑞士顶级腕表品牌宝珀Blancpain与中国最具影响力的文化品牌理想国联合主办。
作为中国最具影响力的出版品牌,理想国一直致力于发掘中文世界最好的书写者,赋予有思想的文字以有尊严的出版,想象书籍的另一种可能。木心、白先勇、西西、张大春……这些作家的文字历久弥新,滋养了一代又一代读者的精神宇宙。理想国坚持出版时间长河中的文学经典,同时又汇集当下最具活力和思考力的青年作家群,他们以多元的写作、开放的见解关怀眼下人类的处境。
作为创始于1735年的高级瑞士腕表品牌,宝珀已有283年的历史。“经典时计的缔造者”,对于时计的“经典”的理解是,超越物质,归于信念、审美与人性。“缔造”则意味着,在漫长时光中的坚持,为了每一枚腕表的结构、细节乃至主题,运用灵感与技艺、付出毅力与耐心,为了顶级的品质标准,不惧推翻、重来。这,与经典文学的内核及其创作过程,享有一致性。文学,是时间的延长线。“宝珀”+“理想国”=“恒长坚持在写作上的青年文学”。
青年的参与和活跃度永远是决定该行业是否有前途的重要标志。在文学创作领域,有才华的青年作家需要一个机遇,文学出版平台需要发掘有潜力的作者,吸引更多人关注和参与。
当代经典作家中,许多人在青年时期被发掘和认可,青年文学奖对他们意义非凡。如奈保尔、库切和新晋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石黑一雄都曾获“布克奖”荣誉,并于成熟期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日本重要作家如远藤周作、大江健三郎和村上龙也曾在青年时期获得“芥川奖”肯定。在今天这个世界里,对青年作家而言,文学写作乃是一条孤独而漫长的路,这一文学奖项衷心期盼寻找一笔一划如手艺人般炼字的未来希望。
附:
1.首届"宝珀•理想国文学奖"作品征集启事
2.首届"宝珀·理想国文学奖"启动仪式暨论坛
3.首届"宝珀·理想国文学奖"初选长名单
4.首届"宝珀·理想国文学奖"决选短名单
商业合作或投稿
请发邮件至:rq@.com.cn
转载:联系后台 | 文学奖:点击“阅读原文”